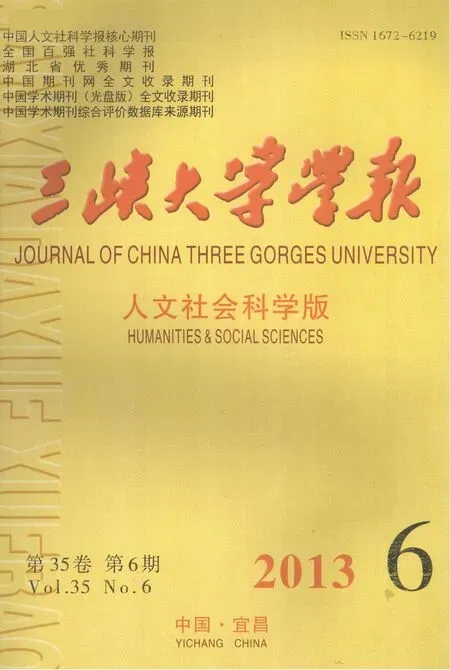宜昌妇女抗战的历史作用考察
李 芊,李敏昌
(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从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开始,中国妇女在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抗战胜利,从战场到后方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唐辉认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广大妇女“无论是上层知识分子、女学生还是广大的农村妇女以及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妇女都积极地投身到这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运动中来”,体现了妇女抗战的广泛性[1]。丁卫平所著《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1937-1945》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妇女抗日斗争史的专著。该书以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为线索,将中国妇女运动史划分为四个大的历史阶段,通过对各个时期妇女抗日斗争的内容、组织和特征的阐述,揭示了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性[2]。夏蓉则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性质,认为它不属于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而是一个动员全国妇女参加战时工作的民众团体[3]。很多学者也分析研究了如宋庆龄等有影响人物的妇女抗战思想及影响。少数学者如鲁南则分析了云南的妇女抗战运动。总体来看,学术界对各地方妇女抗战史料的挖掘还不是很深入,对各地普通妇女抗战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本文以宜昌妇女训练团为视角,分析宜昌妇女在抗战中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为抗战作出的贡献。
一、宜昌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重要地位
宜昌位于长江中、上游的西陵峡口,素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距离武汉300公里,东依荆沙,西抵重庆,鄂湘川豫四省交通枢纽的宜昌,作为华东、华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内迁至西川的重要战略枢纽,一时成为战时湖北全省抗战运动中心,全国抗战的重要城市,战略地位日益重要,成为拱卫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和大西南的前哨阵地。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而在1938年武汉失守前夕,宜昌逐步成为国民党在湖北省抗战的中心。1938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宜昌设立了鄂湘川黔边区主任公署,一并成立了第五战区预备军司令部”[4]28,国民党迁移驻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部分机关也随之转迁宜昌或经由宜昌迁往重庆。宜昌由边缘地带转变成为全省抗日运动中心,是抗战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1938年,宜昌成为华东、华中工业企业内迁转至四川的重要战略枢纽,史称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就是中国军民在宜昌上演的气壮山河、力挽狂澜的一个壮举。这是一次事关国家命运的战略大转移。这是由一位民营企业家和宜昌民众组织的一次影响整个民族命运的大撤退。从1938年10月24日至12月初,仅40多天时间将其堆积在宜昌的9万多吨工业物资和3万人员安全抢运送到战时大后方,创造了战争史上非凡的奇迹。1938年宜昌大撤退期间,转移的机器设备,它几乎是中国航空工业、兵工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全部家当。如兵工系统的就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厂、兵工署巩县分厂、兵工署汴厂、湘桂兵工厂等。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著名的枣宜会战发生于1940年。是年5月,日本侵略军发起攻占重庆的大门——宜昌作战(中国方面称为枣(阳)宜(昌)会战)。6月1日日军突破国民党襄河防线,6月8日当阳、远安陷落,6月12日日军攻占宜昌。鉴于宜昌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日军即以精锐师团分别盘踞在宜昌北岸之南津关、镇镜山、慈云寺、龙泉铺、双莲寺、鸦鹊岭、当阳、河溶、淯溪及宜昌南岸。在控制区的交通线汉宜、襄沙、荆钟、荆当等公路上遍设据点,并在宜昌土门垭、当阳县城、荆门掇刀石修建飞机场,作为轰炸重庆的基地。国民党也组织了著名的枣宜会战,张自忠率部浴血奋战,拖延了日军侵占宜昌的计划,瓦解了日军的战略图谋,为防御重庆东大门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宜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938年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西迁宜昌,同时为加强对鄂西抗战的领导,于1939年4月成立了中共湘鄂西区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宜昌地区党组织在人力和物力上积极支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正面战场作战。宜昌地区先后建立了县级以上党组织20多个,区级党组织100多个。先后建立县级以上抗日民主政权10多个,区级政权30多个,乡级政权累计近百个。根据地面积达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0万。拥有地方人民武装、民兵及其它抗日武装数万人,成为抗战的主要力量。
二、宜昌妇女抗战团的历史考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宜昌人民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先后出现了宜昌抗战剧团、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全国慰劳总会妇女服务队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宜昌妇女训练团就是其中之一。
1.抗战训练团的组建
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界领袖于1937年7月22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战。何香凝在成立大会上号召中国妇女“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5]262。同年8月1日,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其宗旨是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为抗日“输才尽力”[6]25。随后抗战救亡组织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纷纷组建成立。高桥、苏州、长沙、定海、永嘉、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妇女抗敌救援会[7]31。全国各地的妇女不论老幼、地位高低,不论文化程度、职业层次,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全国形成了一个全体妇女参战支前的蓬勃局面。
1939年4月初,鄂中战事吃紧,宜昌前线急需大量救护人员,为解决前线救护人员需求,宜昌抗战剧团、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全国慰劳总会妇女服务队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先后出现在宜昌,宜昌妇女训练团就是其中之一。宜昌妇女抗战训练团由女兵作家谢冰莹发起成立①,最初是从重庆到宜昌开展服务工作的“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服务人员训练团”。“1938年初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在武汉成立,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总会迁址重庆,并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分别成立 4个大队”[8]17,谢冰莹任协会妇女部名誉主任。
宜昌妇女抗战训练团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成员中年龄最大的34岁,最小的仅16岁。如34岁的袁芝英是浙江人,入队前做过上海纱厂的女工,参加过地下党,在重庆开办过幼儿园,专门救护抚养抗战烈士遗孤。24岁的女大学生甘和媛,在加入训练团之前是重庆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出生于富贵之家。国难当前,拥有大小姐身份的她毅然抛弃学业,投奔革命事业[8]16。最小的是刘星玉,只有16岁。团员们都是笃定心志、下定决心加入到训练团中来的。当17岁的谭淑萍因患有扁桃腺炎而被谢冰莹婉拒时,她流着泪哭诉,“如果你不许我去前方,我非自杀不可”[9]28。聋哑女孩李慧君也是“下了十二万决心要去前方,她一天走一百六十里,在训练团出发前从长寿县步行赶赴重庆加入到训练团中来”[10]661。她们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舍身忘死,慷慨赴难。
2.抗战训练团的活动轨迹
1939年4月,宜昌抗战训练团挂牌为“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服务人员训练团”,地点为宜昌小北门中心小学,抗战训练团于1939年4月20日开始正常运转,其训练重点是“术科”即救护常识学习,也涉及“学科”即文化知识学习,另外还有野外训练、军事训练和支援前线等相关工作的培训。包括“怎样设置伤兵招待所,怎样发动民众参加伤兵服务工作,伤兵中的宣传工作,怎样编壁报,怎样写战地通信,怎样写士兵家书等[9]28。
训练团用较短的周期培养出一批战时服务人员。每天早晨五点钟,训练团的教练和团员们就开始训练。女士们每天和男兵接受一样严格的军事训练。在训练中“团员们一律身着草绿色军装,打绑腿,每日紧张的训练,过的是严格的军事化生活”[8]18。她们一天工作十个小时,其中四个小时的术科,三个小时的学科,一个小时的特别演讲,一个小时的小组讨论。“从徒手各个训练开始,再经过持枪各个训练,其中包括班训练,排训练,步枪射击训练,手枪训练,一直到野外演习”[9]27。只有短短的两个星期快速、高强度的学习培训,团员们便学习到了各种战时知识。聋哑人李慧君在训练团训练的时候“因为听不到,就借队友的笔记来抄写;参加军事操的时候,听不到口令,就模仿别人的动作,从立正、稍息开始再到向左转、向右转;并认真学习开枪射击”[10]663。“她们口袋里从没有离开过书本,只要有几分钟休息的时间,便可以看到他们看书写字的狂热”[9]28。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训练团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开展各种训练的。宜昌地区几乎每天都有日机轰炸,“有时从早到晚整天在轰炸中过日子”,“训练团是4月20日开始上课的,第二天就遇着警报”[9]28。所有在宜昌的各机关和救亡团体,在时间上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宜昌妇女训练团的工作并未因战争的严酷形势而大受影响。只要轰炸一开始,团员们就带上笔记本,转移到安全地点继续进行培训,所有的工作仍然像平时一样进行。而日机的狂炸,只会“更加促进她们抗战报国的决心,促使她们更加紧迫的学习和工作”[9]28。
训练团原本计划在宜昌完成一个月的训练,但因敌人嗅到了集训的风声,以为有一支重要部队在这里行动,所以日机每天不停地围绕在驻地周围轰炸。在其中一次轰炸中,防空壕被炸塌了半截,其中一名团员的腿被炸伤,训练团的食堂土墙也被震倒,掩埋了一名女队员,使她失去了知觉。在1939年5月8日这一天,日机对宜昌进行了更大规模狂轰滥炸,使全城陷入火海[8]19。鄂中战事陡然紧张之时,因前线迫切需要救护工作人员,训练团只得把训练的时间缩短为两星期,训练完毕之后,她们都迅疾奔赴前线。
三、宜昌妇女抗战团的历史意义
1.救护伤员,支援抗战
抗战时期,无数男子出征前线,以生儿育女为天职的半数妇女,也表现出了“为国民一份子”的醒悟,为抗敌救国增加了一支新的生力军,也给民族解放战争奠定了更加胜利的基石[11]30。宋庆龄曾经说:“救治一名伤兵,就相当于消灭一个敌人!”
宜昌妇女训练团的女子接受跟男子一样严酷的军事训练,同时学习救护伤员的知识,训练完毕直接奔赴前线开展救治伤员的工作。当时,在当阳至十里铺设有12个伤兵招待所。队员按4个一组被分派到土门垭、鸦鹊岭、当阳、河溶、十里铺等地。其中在当阳的是“伤兵招待所第四服务总队”。大队部设在当阳长坂坡旁的湘乡会馆,袁芝英任所长,甘和媛负责大队的文书、经费、联络等事务,李慧君、刘星玉分别做协助工作。“伤兵一来就是两三百人,一个人当做十个人用”[10]663,聋哑人李慧君并未因听不到而影响她的工作,谢冰莹在《三个女性》中写到:“她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做得多,做得切实而有成绩。她编壁报,管账,替伤兵换药,整天都在忙碌着,无论怎样忙,她从无怨言”[10]664。团员在最前线,为伤兵提供热水、热饭、治疗伤痛、写士兵家书等服务,使伤兵在精神上得到了抚慰,身体上减少了苦痛,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她们尽职尽责地救护伤员,支援抗战,对于全国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促进宜昌的妇女解放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维中,女子处于从属地位。“很多家庭宁愿把多的钱给男子去打牌、抽大烟、嫖娼,也不愿给女子买书学习”[12]15。妇女在旧中国的社会文化中一贯被视为男子的附属品。“宜昌的旧道德很深,仅有的五六所中学,全都没有男女同校”[13]104。
抗战以来,特别是宜昌训练团挂牌“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服务人员训练团”成立以来,“便有许多武装的男女同志涌进了这扇小门”[8]27,无数宜昌爱国青年男女加入到这一阵营,广大的女同胞与男同胞一起并肩作战,奋发向上。他们共同学习生活,一起为抗战建国奉献自己的力量。包括“向来不与报纸发生关系的一般妇女,不是坐在一团聚精会神地听人讲解报纸上的消息,便是立在一处向人询问壁报上的真情。还有一些不识字的妇女,常自动地拿出钱向卖报纸的人争购一份当天的报纸,去请求别人讲解”[14]14。整个妇女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提升。
宜昌妇女在参加抗日救亡团体的工作中,激发了当地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与民族解放斗争的热情。在参与过程中,广大妇女的权益意识逐渐增强,通过为国家贡献力量,妇女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不再是男子的附属品,妇女从心理上感到应该和男子一样享受权利和义务,推动近代宜昌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3.宣传抗战,唤醒民众
19世纪20年代宜昌社会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社会经济上,“宜昌的吸食鸦片者大约占总人数的80%,赖以烟土交易生存的人成千上万,全市营业烟土商铺满目皆是,达到两千余家”[15]43。路上随处可见乞丐,娼妓馆也比比皆是。在基础设施上,“马路破旧,电车没有,汽车稀少,设施古老。文化教育上,最高学府仅是初中学校,而且没有男女同校”[13]104,其实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经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樊篱,取消女禁,男女同校学习。舆论宣传上,“各地报纸仅二三份,供人阅览,图书只有几本鬼神、剑侠”[16]14。“书店很少,新文化书籍更是少见,更多的是代售教科书及帝王剑侠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13]104。社会风俗上,“民众封建迷信成风,乡民凡生老病死都要求神问卜,乡绅、官吏更是迷信此道”[17]64。中国大多数妇女,因受着几千年来旧道德礼教的压迫和束缚,文化水平低,思想不开化,导致国家民族意识淡薄。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宜昌,“绝大多数妇女依然是浑浑噩噩过日子,对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漠不关心”[18]26。
宜昌妇女抗战团在宜期间,“在战场比较平静时,重点是宣传民众”[8]19,动员抗日。在唤醒和组织千百万思想落后的妇女参加到抗战救亡运动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宜昌妇女抗战团工作的推进,妇女们谈论的不再是“年货办好了没”,“肉腌了没”的家常话题,而是“近几天仗打得还好吧”,“我们的军队打到了哪里”[14]14。17岁的训练团成员谭淑萍说:“我生平没有经历过这么忙的生活,但也生平没有经历过这么有意义的生活。”[9]28面对每日10小时的训练与艰苦的环境,团员们从不叫苦叫累,反而觉得“睡在地上比睡在家里的床上舒服多了,一觉睡到天亮,不做梦也不醒来”[9]28。她们把个人与国家的救亡图存紧密联系在一起,妇女团在宜昌的工作宣传了抗战,唤醒了民众,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风尚。
四、小结
宜昌妇女抗战训练团是由进步女青年组成的抗日救亡团体,既不属于国民党党政系统,也不属于共产党领导,是中国进步青年在抗日救亡这一特殊背景下建立的群众性抗战组织。其抗日救亡运动不仅直接支援了抗战,而且逐渐影响到宜昌社会群众的思想,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当地妇女解放的作用。毛主席曾经说过:“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19]44可以说,宜昌妇女抗战团对于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推进宜昌民众思想解放都是功不可没的。
注 释:
① 谢冰莹:1906生,湖南新化县人,在1926年参加武汉军政学校女兵队,在此期间,用自传体形式写成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被译成多种文字传于世界。
[1]唐 辉.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广泛性考释[J].群文天地,2013(1).
[2]丁卫平.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1937-1945[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3]夏 蓉.抗战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性质探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4]程 伊.日形重要的宜昌[N].内外什志,1937年第5卷.
[5]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孙晓梅.中外妇女运动简明教程[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
[7]卫.妇女抗战工作在各地[J].战时联合旬刊,1937(1):31.
[8]甘和媛,邵荣霞.忆女作家谢冰莹与战地服务队[J].武汉文史资料,2000(11).
[9]冰 莹.宜昌妇女训练团[N].上海妇女,1939-3-4.
[10]谢冰莹.谢冰莹作品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11]徐镜平.“一·二八”抗战中的妇女[N].文摘,1937-1-2.
[12]沈兹九.抗战妇女教室[N].妇女生活,1938-6-10.
[13]杨晋豪.宜昌的旧历年风俗[N].青年界,1935-7-2.
[14]清 萍.抗战期中的湖口妇女[N].妇女生活,1938-5-8.
[15]匿 名.烟土世界之宜昌[J].拒毒,1927(27):42-43.
[16]大 信.地方通讯:宜昌社会情形[N].人民周报,1933-2-76.
[17]于曙峦.宜昌(地方调查)[J].东方杂志,1926,23(6).
[18]啸 云.全面抗战中知识妇女的当前任务[J].东方杂志,1937,34(18-19).
[1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