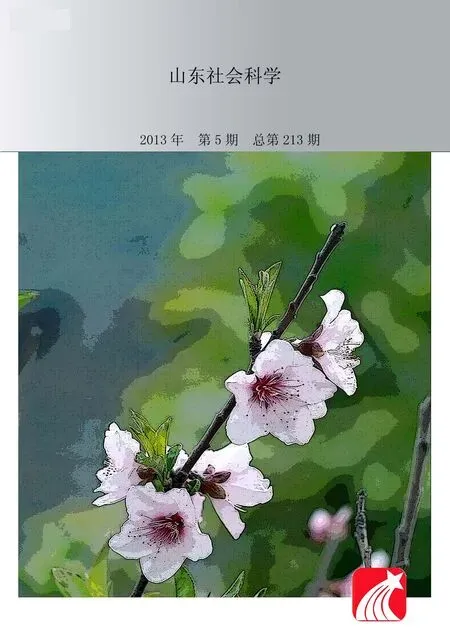“唯一者”真正走出了“意识的内在性”吗?
龙 霞
(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在马克思与形而上学关系问题的探讨上,一个始终无法忽略和回避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因为对这一问题作何种解说,将直接制约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关系的看法。我注意到,在国内学术界,吴晓明教授与刘森林教授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极具分歧性的看法。吴晓明教授透过其所主张的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阐释,认为施蒂纳是“谋求对形而上学给予最终打击而又复归于复辟”,而马克思的施蒂纳批判则“意味着终止全部形而上学,并使之从根基上不再成为可能”;而刘森林教授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施蒂纳“对抽象的拒斥过了头”,“危险地抛弃了形而上维度”,而马克思的施蒂纳批判,乃是“通过施蒂纳的刺激”,使马克思在反形而上学的道路上及时地止住了脚步。上述两位学者近乎相反的看法,无疑使得马克思的施蒂纳批判更具阐释张力。而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源头上关涉到对施蒂纳的“唯一者”作何种理解,尤其关涉到唯一者是否走出了形而上学的“意识的内在性”。笔者不揣浅陋,力图澄清以下问题:施蒂纳的“唯一者”究竟是否走出了“意识的内在性”?
一、唯一者是“身体”吗?
贯穿《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全书的逻辑主线是消除“人”的抽象性,最后达到“唯一者”。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个接一个地剥除“人”的抽象思维规定之后,“唯一者”最后剩下了什么?刘森林教授认为,施蒂纳乃“把以感性存在取代和消解超验本质的思想努力激进地贯彻到底,表现出了一种彻底拒斥形而上学﹑拒斥超验性存在的虚无主义态度”,而“去掉一切抽象﹑普遍意义上的‘最高本质’﹑‘神性存在’﹑‘人’,唯一者也就只能剩下一个纯感性的﹑经验的﹑本能的层面了。”而这个“纯感性的﹑经验的﹑本能的层面”又是什么?刘森林教授的回答是,施蒂纳“从思想主体转向身体”。换言之,“唯一者”即是“身体”。
“唯一者”即“身体”,从文本自身来看,我们似乎不难找到支持这一解释的文本证据。施蒂纳在反对观念之“我”﹑作为意识之我时说道,“对于你来说,我是什么?就是这个有肉体的我、走动和站立着的我?绝非如此。这一有肉体的我连同其思想、决心和情欲在你的眼中均是个人事宜,与你是毫不相干的,是一种‘自为之物’。作为一种‘为你之物’只有我的概念、我的类概念存在着……”,施蒂纳就“我”所想要谈论的,似乎就是纯粹的肉体,是“与思想不同的他物”的身体。但须注意到,施蒂纳刻画“唯一者”还有一个关键词——“无”。唯一者之作为“无”,说穿了,就是维护人的“可能性”,使人的“可能性”不受任何抽象固定本质的侵犯。这是宣称“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的施蒂纳意图之所在。“无”与“可能性”是同质的。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唯一者作为“身体”,与它作为“无”,二者的内在关联是什么?
在刘森林教授那里,二者的关联在于,施蒂纳“人的‘现实’在他看来就是独自性的我,与其本人一模一样,当下(这儿﹑现在)的这个或那个我……就是偶然﹑片段﹑多元异质的当下所是,就是不能被任何本质整合为统一性和连续性整体的无限开放性”。①刘森林:《追寻主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因此唯一者作为“纯粹感性”的身体,“把自己彻底放逐进了瞬间﹑片段﹑偶然﹑裂变﹑易变﹑空无﹑消耗﹑享受和最后的死亡中”,这就意味着“力图摆脱掉必然性的关联”,达到“没有任何必然性和确定性关联的自我任性状态”。这就是唯一者之作为“身体”,同时也作为“无(可能性)”之意谓。
但是,这个看法里头是否有矛盾呢?我以为,需要暂且抛开文本,就其逻辑自身来考察:剥离了意识维度、无思想、非思想的纯粹身体,它所谓的“可能性”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纯粹身体”,它所谓的“可能性”可能是一种随机飘散着的状态,没有任何必然或确定的方向,一切显得那么的随机和任意。它是易变的,就像空气中飘散的尘埃,无从知晓下一刻会落到哪里,因此充满了最大的任意性和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此中不得不察的一种状况是,这样的“可能性”状态,随时可能逆转或颠覆为其“反面”。换言之,其“可能性”状态可能被打破,转而建立起某种稳定性的关联,从而转向一种实在化和固定化状态。从何理解这种状况的发生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那随机飘零着﹑无从知晓下一刻会落到哪里的“某物”,完全可能在毫无定向的飘零过程中,在下一瞬间顺从或随附于某种他者,与之建立恒定性关联——即使此关联的发生可能是完全随机和偶然的。但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则意味着它身上的“可能性”状态在瞬间丧失,从一种原有的“可能性”状态,瞬间被颠覆为“实在性”状态。就像一阵飓风扫过,尘埃下落并固着于地后,从此失却了随机飘荡的可能。
作为一种“可能性”,蕴含着两种走向:一种是停留于毫无定则的随机飘零,并无任何必然性和确定性关联,持续性地保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开放性;一种是其“可能性”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被打破,随时可能顺从或随附于某种确定性关联,从而在随机飘零的下一瞬间逆转其“可能性”,转变为固定性和实在性。
这样两种看似相反的状况,却是完全可能统一于对“纯粹身体”的理解上的。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从尼采到福柯﹑德勒兹,身体相继被拖出了意识(主体)哲学的深渊,意识的宰制地位被摧毁而“身体”被突出出来。但是,尽管共同以身体为出发点,福柯对身体的态度与尼采和德勒兹截然不同。“身体”在尼采那里是主动的,身体即权力意志本身,它充斥着积极的活跃的自我升腾的力量。与之相反,在福柯那里,身体只是一个等待判决的对象。身体和权力展示了被动和主动的对偶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和尼采在身体的被动性和主动性上所拉开的距离,恰恰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本文对“纯粹身体”之作为一种“可能性”状况的描绘。也就是说,剥离了意识维度﹑无思想﹑非思想的纯粹身体,完全可能一方面犹如尼采的权力意志那样,成为主动撕开一切封闭的真理体系的“身体”,展现为生成、偶然、此刻和瞬间;另一方面,它也完全可能是福柯式被动、呆滞的身体,“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①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7页。这样的身体是备受蹂躏的,是被宰制﹑改造﹑矫正和规范化的对象。福柯的“身体”对应的正是上文描述的“可能性”的第二种走向,即其“可能性”状态不稳定,随时可能被颠覆的状态。
不难看出,区分尼采与福柯两种“身体”的不同,正在于“主动性”和“被动性”的不同,换言之即自主性的拥有抑或匮乏的不同。缺失自主性支撑的“身体”,只能作为随时可能认同或依附于某种他者、其“可能性”状态随时可能被颠覆的存在。故而唯其因为内在自主性的匮乏,才会出现福柯意义上任外在权力摆布的身体。而此种“身体”的“可能性”注定是不稳定、随时可能被颠覆的。进而,即使福柯意义上的“身体”是可变的﹑易变的,它的“可变性”也只是外在权力施予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那种能够持续性地保持其“可能性”状态不被颠覆,维系住无限的开放性和可能性的“身体”,必须依赖于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它必须是内在自主的。
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的话,依刘森林教授的判断,“唯一者”即身体,那么它应该归属于哪一类身体?尼采式的主动性身体抑或福柯式的被动性身体?换言之,唯一者之作为身体是否具有内在的自主性呢?
很容易得出结论。要求向一切可能性开放,以维护人的可能性不受任何抽象本质侵犯为最高目的的唯一者,当然决不允许那种随时可能顺从于某种他者关联从而其可能性被充实﹑被颠覆的状况出现。唯一者决不会允许内在自主匮乏完全抗拒不了对他者的随机顺从而颠覆自身之作为“无”、作为“可能性”的价值。就此而言,显然可以认为,唯一者必须立足于某种内在自主,从这种内在自主中汲取最大的能量,来尽可能地防止自身被任何抽象本质所固化和吞噬,也就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作为区别于一切固定观念的“可能性”价值。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当中,施蒂纳在说明自身与思辨哲学家的区别时指出:“我的思维,并不是思维指导我,而是思维由我指导、继续或中断,一任我之所愿。”②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7页。什么是唯一者意义上“一任我之所愿”的“任意性”呢?显然不可能是那种纵使摆脱了任何确定性关联看似充满了可能性及任意性,但其“可能性”却随时可能被颠覆的“任意性”。此类“任意性”其内在是空洞的,是缺乏内在根基支撑的,它的“可能性”本质上属于非自主状态和随附性质的。唯一者的“任意性”必须结合其“独自性”进行理解,它是“独自性”的另一种表达。“对于你来说,我是什么?……这一有肉体的我连同其思想、决心和情欲……与你是毫不相干的,是一种‘自为之物’。作为一种‘为你之物’只有我的概念、我的类概念存在着……”。施蒂纳的“独自性”即“自为之物”。作为“自为之物”,它的任意性,就决不能是一种蒙昧性质、全凭摆布之下而产生的“任意”,也决不允许因内在自主匮乏而导致随时可能认同和随附于他者。否则它就不再是“自为之物”,而是“为你之物”,就丧失“独自性”了。
故而,施蒂纳的唯一者只能是内在自主的。“唯一者”要始终保持自身为一种“无”及“可能性”的价值,就必须依赖某种内在的自主性。那么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便是:内在于唯一者身上的自主性是什么呢?
二、何种自主性?
首先,贯彻其消解一切抽象本质的逻辑,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区分了两类批判:“隶从的批判”和“自主的批判”。他说:“如果我在为了某个最高本质的前提下进行批判,那么我的批判就是为本质效劳的,是为了这一本质才进行批判的。举例说……如果我在批判中把人当做‘真的本质’而加以信仰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一切就首先区分为人与非人等等。”“善以万千名称和形态周而复始,却总是保持为前提,对于这种批判来说保持为独断论的固定点,保持为固定观念。”“无论何时我们进行批判都是对某个本质的爱。一切隶从的批判均是爱的产物。”施蒂纳说得很清楚,“隶从的批判”实际上仍然属于唯一者被禁锢其中的观念。唯一者彻底拒斥一切固定观念的禁锢。这样的话,如果认为内在于唯一者之中,存在着某一特定的“前提”作为其自主性之源,那么这一“前提”决不会是某个固定的“观念”。
自主性不能来源于观念内部。那么,唯一者的自主性会是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意义上“把已经潜伏在内部的东西外化为自我的不可替换的独特内核”这样一种自主性吗?①[美]刘易斯·亨齐曼:《自主性、个性和自我决定》,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诚然这个答案也不可能。尽管施蒂纳的“唯一者”支持“独自性”和个别之我,但唯一者对其“内在所有”并不加以任何的肯定和确定。它没有以任何肯定性的语言,认可过存在于个体内部真实而独特的东西,它的目标也决不是“发现﹑培植和再现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自己和他人内部的东西”。
这样看来,最为接近“唯一者”之理解的,似乎就是尼采或德勒兹意义上“主动”的身体。但,“唯一者”是它们吗?
诚如前文所言,尼采的身体是积极和能动的。在这里,“无处不在的力乃是忽而为一,忽而为众的力和力浪的嬉戏,此处聚集而彼处削减,像自身吞吐翻腾的大海,变幻不息,永恒的复归……作为变易,它不知更替,不知厌烦﹑不知疲倦”。②[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22页。可以说,尼采的身体就是“力”本身。可是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支持唯一者作为“身体”乃是一种力的肯定描述或说法,也无法凭其内在逻辑来进一步作此推断。实际情况是,相比较而言,唯一者更多的是一个否定性概念,而尼采的“超人”则是肯定性概念,强调其超越和创造的力量;因此,唯一者会维护包括一切可能性在内的“欲望”,而尼采的超人则是有原则的择取“欲望”,“假如利己主义意味着人的轨迹的升高,那么它的价值的确是很伟大的;假如利己主义意味着下降的轨迹,意味着衰退和慢性病患,那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③[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49页。唯一者作为否定性概念,因此也决不可能是尼采意义上的身体。德勒兹的欲望机器身体亦属同样。
那么,“唯一者”内在的自主性究竟是什么?维系唯一者向一切可能性开放的内在自主力量之源究竟来自哪里?我以为,这种内在的自主性,只能是内在意识本身;唯一者之“力”,不是身体之“力”,而是意识的反思之“力”;唯一者的背后,昭示着的恰恰是精神的自主反思维度本身。
吴晓明先生曾经援引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唯一者”的达成与建立本身仅仅立足于这样一个理论过程:“桑乔由于从头脑中抛开了‘人’而获得了唯一性。……他从头脑中抛开了观念,因而就成为唯一者”。唯一者的形成本身立足于这种理论态度,它的核心体现为“抛开观念”﹑“把圣物从头脑中挤出去”——这样的抛开或排挤本身不能不是纯粹理论的。据此,吴晓明先生认为,“‘唯一者’的一双脚都站在形而上学的基地上并从而赋有形而上学的全部抽象本质”。④吴晓明:《马克思的施蒂纳批判及其存在论意义上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3年01 期。正是这种看法遭到了刘森林教授的强烈质疑,他认为:“与其把施蒂纳的唯一者看做是逻辑抽象,更不如把它视为一种价值应该,一种当下仍然不能很好地做到却仍须努力的理想目标。而且,唯一者不是概念,而是可能性,是一种在逻辑上被揭示出来并在价值理想层面提到崇高地位的一种可能性立场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可能﹑努力方向,抗拒必然﹑普遍性力量压制的空间集中和方向凝聚。”⑤刘森林:《现实的人与唯一者——马克思与施蒂纳的主体论之别》,《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第3 期。笔者很认同刘森林教授的这种看法。这一看法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当中的唯一者形象作了很好的提炼。但是,认为唯一者乃是一种“可能性”,这与吴晓明教授所指出唯一者仍是一种逻辑抽象,实际上并不冲突。需要指出几点:
其一,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那样,唯一者作为一种可能性,从前提上必须依赖于某种内在的自主性,否则,我们无从理解唯一者为何要“力图摆脱掉必然性的关联”,以达到“没有任何必然性和确定性关联的自我任性状态”;它也将无从维系自身作为一种“可能性”的价值立场。
其二,笔者更愿意认为,所谓唯一者之站在概念的﹑反思的立场,不仅因为在“性质上”,“‘唯一者’同样可以‘作为概念固定下来’”,或用马克思的话来形容,“他所提出的不是完整的综合体,而单就是一个纯反思的特质,以与某一个特性以及全部特性的总和对立的就仅仅是这个反思的特质,某个我,自己想象的我”,又或用徐长福教授的话来表达,即“把‘唯一者’作为唯一的本质重新加到每一个个人的头上”,也不仅在来源上,唯一者在形成过程中,是依靠一个接一个地在“反思”中剥除“人”的思维规定而达成的,而毋宁更应该认为:唯一者自身作为一种可能性的“价值”,从根本上需要依靠内在的反思力量来加以维系。舍此我们难作他想。其实,刘森林教授自己说得好,施蒂纳“采取了从自我的内在性中汲取力量﹑成就自我的路子”。①刘森林:《追寻主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而所谓“自我的内在性”当中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是自我反思的力量,是纯粹精神的批判力量。唯一者之“可能性”至多只能说通过我思、通过意识反思来维系,而并未如同尼采所明确指示的那样,权力意志在“永恒轮回”和自我指涉之中保持开放性与“可能性”。因此,当刘森林教授援引马克思批评布鲁诺·鲍威尔的话用于点评施蒂纳“力量就在它们的意识中,因为它们是从自身中﹑从自己的行动中﹑从批判中﹑从自己的敌人中﹑从自己的创造物中汲取力量的;人们靠批判的行为才获得解放……”,“遗憾的是,终究还没有证明,在其内部,即‘在自身中’,在‘批判’中有什么东西可资‘吸取’”时,我看不出来,它与吴晓明先生所援引马克思批评施蒂纳的话“恰恰正是有一些反思的人,他们相信在反思中并借助反思之力,能够超越一切,然而实际上他们却未能从反思中超脱出来”,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0-291页。二者又有何本质不同?因此,唯一者之站在概念的、反思的立场,与唯一者之作为一种可能性立场之间,是并不冲突的。
内在自主的(意识)反思力量,正是维系以及成就唯一者之作为一种“可能性”的价值应该的根本前提。因此,当刘森林教授概括认为唯一者乃一种“典型的内在性自我观”,我极为认同这一概括。但是当刘森林教授认为,唯一者意味着“从‘思想’的内在性到新式内在性”转变,而这种新式内在性即“从思想主体转向身体”时,我便无法苟同了。
在我看来,诚如尼采的工作所展示的那样,对“(意识)主体”的消解,从“主体”到“身体”的迁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转换工作。“权力意志从两个方面反对形而上学。就横向而言,它反对主体和主体的行动这一主谓划分;从纵向的角度而言,它反对表象和理念的深层和表层的表象性划分。”③汪民安:《尼采与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如果认为施蒂纳的确处于身体与(意识)主体的一争高低中,那么唯一者是否超越了意识主体的基点,彻底转换到“身体”了呢?我认为并没有。倘若放在尼采的批判谱系中,这个“思维由我指导﹑继续或中断,一任我之所愿”的唯一者,无疑仍旧是个明确的“主语”,而非打破了“主体和主体的行动”的主谓界限的尼采式身体。因此,当施蒂纳逐个地批判了抽象本质之后,唯一者的形象渐渐又无可避免地“重聚”为一种主体。对此,徐长福教授的分析倒是有些中的:“施蒂纳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弄清楚,个人事实上杂有众多异质性属性跟个人应该成为这些属性的主宰并不是一回事。”唯一者要承担作为一种追求“可能性”的价值应该,成为“这些属性的主宰”,他就必须保有某种内在的自主性力量。而这种内在性力量不是权力意志之“力”,而是意识反思之“力”;唯一者并非脱离了意识维度的纯粹身体之我,而仍旧是思想之我、思维之我。唯一者虽非概念,或者只是一种概念的否定性表达,但并不代表在它本身之内反思力量的不在场。就此而言,唯一者仍然没有超越意识主体的基点,仍然没有走出意识的内在性。
当施蒂纳说“自由思维全然不同的思维是自己的思维,我的思维,并不是思维指导我,而是思维由我指导、继续或中断,一任我之所愿”时,某种程度上,他似乎确认了主体意识的非自主性。但这相较于尼采等人从身体出发主张主体意识的非自主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盖因施蒂纳从未跳出过意识主体,从外部对意识主体加以研究。巴塔耶尚在色情中发现了主体意识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德勒兹则将欲望机器而不是自我看做是决定性和生产性的。而施蒂纳做了什么?它难道不只是在批判概念和抽象本质的过程中,却一再地反身确证了主体意识的自主性而已吗?因此,正如吴晓明教授所说,施蒂纳对主体意识的批判仅具有“有限的理论意义”。他所支持的那种“自主的批判”,无论如何区分于从固定观念出发的“隶从的批判”,其本身作为一种从意识之我﹑思想主体出发,全凭反思的自主力量而进行的批判,却是无可否认的。
因此,我以为,唯一者并不是身体。唯一者作为一种“可能性”的价值应该,它所全部依凭、须臾不可抛开的内在自主精神维度,使我们不能将唯一者纯粹还原为“一个纯感性的﹑经验的﹑本能的层面”,还原为纯粹身体。
但是,唯一者内在的自主精神维度却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文本所正面没有揭示的,对此施蒂纳本人似乎也是无明显意识的。事实上,对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种很深的阅读感受是,它在自身理论的立论逻辑上显得相当混乱和不明晰。因此,某种意义上,拨开表面的文字迷雾,深入其内在的逻辑支撑,乃是阐释清楚“唯一者”性质之必需。
总之,唯一者决非“身体”,其身上须臾不可抛开的内在自主的反思维度,从根本上喻示了它决没有走出意识的内在性,决没有超越意识主体的根基。由此进一步关涉到有关马克思的施蒂纳批判问题、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等,都应基于对唯一者性质的重新澄清而予以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