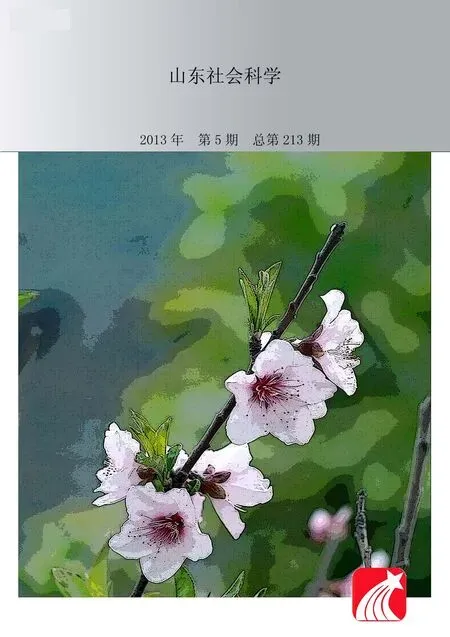何为“现实的个人”?何为“真实的共同体”?
——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与超越
李丽丽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也使用das Individuum(个体、个人)、das Person(个人)这样的概念,但是总体而言,马克思对“个体”、“个人”概念的使用都是无意识的、未经反思的,受启蒙思想和黑格尔的影响较大。正是施蒂纳那种利己主义的、为所欲为的、完全否定普遍性的“唯一者”,促使马克思开始重新思考个体(Individuum)以及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施蒂纳的“唯一者”这种现实的个人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自己关于“现实的个人”(das wirkliches Individuum)的理解,并且从异化的角度,把国家看成虚幻的共同体,他认为虚幻的共同体只会对个体自由造成压迫,必须用“真实的共同体”取而代之。施蒂纳企图用“利己主义者的联盟”来代替国家、社会等普遍性的东西。马克思所谓的“真实的共同体”虽然与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有相似之处,但马克思认为,能够实现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同体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也不是施蒂纳那种“利己主义者的联盟”,而是共产主义这一“真实的共同体”。总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描述以及对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关系的讨论都与施蒂纳有很大的关系。“正如施蒂纳高扬个体,强调‘现实的个人’的概念而引起马克思对个人的瞩目一样,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及其对个人地位的确认,也必然逼迫和促使马克思去深入思考和阐明现实的个人在共产主义这一联合体中的地位和意义。”注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一、“唯一者”(Der Einzige)与“现实的个人”(das wirkliches Individuum)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强调的是作为类本质的国家生活,在《穆勒评注》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中,他强调的仍然是个人的社会本性。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开始关注“现实的个人”,即使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稿中,马克思原本也是从客观的社会总体出发来确定“人”的,而到了第四稿则直接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进行论说,[注]刘森林:《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不得不说这个转折与施蒂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马克思在读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后受到了他的影响。
施蒂纳的“唯一者”是直接针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等思想提出的,他认为费尔巴哈虽然把神的本质归还给了人,但是“对人的敬畏就仅仅是对神的敬畏的一种变化了的形态”[注][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99页。而已,因此,费尔巴哈的人仍然是对个人的压迫。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分为两部分:人(Mensch)和我(Ich)。施蒂纳认为,不论是古代人还是近代人都是不现实的人,所体现的都是人(Mensch)对个人(Individuum)的压迫。施蒂纳指出,要使人成为现实的、自由的,就要使“我高于一切”,使人成为利己主义的,这个真正现实的个人(Individuum)就是“我”、“唯一者”。
在施蒂纳眼里,普遍与特殊、个体与共同体是完全对立、势不两立的。我要获得自由,获得现实的存在,就必须摆脱一切普遍物,包括家庭、社会、国家等,因为“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注][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从古代到现代,从神降到人,虽然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背后仍然隐藏着国家对个人的压抑,抽象物对人的统治,神对人的压迫,所以施蒂纳认为“我”必须是独立的才是真正现实的人。
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批判引起了马克思的深思,使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现实的” (wirklich)以及“个人”(Individuum)等词汇的使用与施蒂纳都是相同的,比如马克思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历史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wirkliche Individuen)……”。[注]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Werke,Bd 3, Berlin :DietzVerlag,1969,s.20“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menschliche Individuen)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diese Individuen)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注]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Werke,Bd 3, Berlin: DietzVerlag,1969,s.20-21而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也经常使用“现实的”、“个人”这样的词汇,比如施蒂纳说,“为了人类的发展,它让人民和个人(Individuum)在为它效劳的过程中受折磨……”。[注]Stirner,M.,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Stuttgart:Philipp Reclam jun,1972,s.4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最后一章“唯一者”中,施蒂纳更是讨论了现实与理想、现实的人与非现实的人。他说:“斯多葛派的非现实的‘智者’、这个无形体的‘圣人’在有了肉体的神之中变成一个现实的人物、一个有形体的‘圣人’;而非现实的‘人’,无形体的自我在有形体的自我、在我之中则变成现实的(wirklich)。”[注]Stirner,M.,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Stuttgart:Philipp Reclam jun,1972,s.408这说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词汇的使用、问题意识方面都受到了施蒂纳的强烈影响。然而,虽然马克思赞同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同意施蒂纳对个人价值的崇尚,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施蒂纳走得那么远,在马克思的眼里,费尔巴哈的人仍然不够现实,但是施蒂纳的个人(Individuum)——“我”又现实得过了头,走向了虚无主义。为了对费尔巴哈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和施蒂纳极端抽象的“现实的个人”进行双重批判,重新定义“现实的个人”对马克思来说就变得迫在眉睫。
首先,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种有生命的个人不是想象中的,是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物质生产决定了人的现实存在,因为人是什么样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人为了生活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所以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需要的物质生活本身。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又引起新的需要,这就是第二个生产活动。此外还有第三种生产活动就是生命的生产。总之,从事物质生产是人得以存在的基础。
其次,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是具体的。不管是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人的生命的生产,都会产生一定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因此,“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页。所以,抽象的人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
第三,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他有凭之生存的能力,而这主要是由于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注]Michael H. Mitias,Marx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Vol.12,No.3(Sep.,1972),p246.人在社会交往、文化传统中获得各种各样的生存能力,这说明现实的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现实的个人是在社会中获得现实性的,离群索居的人是不现实也不存在的。
马克思指出,作为历史前提的现实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是与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因为不论是施蒂纳那种离群索居的个人,还是费尔巴哈那种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都是从意识而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得出的结论。但是无论如何,施蒂纳对“现实的个人”(Individuum)的高扬是马克思重新思考“现实的个人”的主要动因,然而“施蒂纳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理解个人的,他反对政党、国家等共同体以普遍利益的面目压抑个人利益,认为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安排世界,就要取消国家等统治力量,代之以利己主义者的联合体。只有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人、现实的人。”[注]李淑梅:《个人概念的变革与唯物史观的创立》,《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因此,施蒂纳除了使马克思开始重视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外,也使马克思开始思考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地位问题。
二、“虚幻的共同体”:对个体自由的压迫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用虚幻的共同体来指代资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国家展开实际的批判。究其原因有二:其一,这与马克思重新确立的历史前提相关,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但是当他考察现实状况时却发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获得现实性的途径也可能使他丧失现实性,这是因为市民社会发生了异化,分工导致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国家成了压迫个体自由的虚幻的共同体。其二,施蒂纳高扬个体,对国家等普遍物的拒斥,使马克思反思大众化给个体带来的压力。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还把国家生活作为类生活,渴望个人向类生活的复归,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资产阶级国家就被描述成了虚幻的共同体,这其中马克思肯定吸收了施蒂纳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开始重新确定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因此,从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可以看出施蒂纳对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从《博士论文》至《德意志意识形态》,曾频繁地使用过“共同体”一词。其中Gemeinschaft、Gemeinde、Gemeinwesen、Gemeindewesen 等词都可以用来指称共同体。虽然这些词语翻译成中文皆为“共同体”,但是这些德文词之间还是存在着细微差别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区分了真实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并且在指代共同体时由之前的Gemeinwesen变成了Gemeinschaft,这个细微的差别并不是马克思进行的简单的词汇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理解从逻辑走向了历史。望月清司认为,Gemeinwesen“ 属于最顶端的概念,在它下面才是没有异化的‘人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和‘人的社会’概念。Gemeinwesen相当于类本质概念,共同体(没有异化和中介的社会)和社会(异化了的共同体)是Gemeinwesen两个结构种差。Gemeinwesen 与有没有被异化无关,它指的是贯彻在共同体和社会中的社会联系原理。”[注][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由于马克思一开始受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影响,把国家共同体视为一种普遍性得以实现的领域,后来又受费尔巴哈类本质的影响,认为国家生活才是符合类本质的生活,所以,国家共同体在马克思那里就代表了一种普遍性,因此,当马克思一开始用Gemeinwesen指代共同体时,就像望月清司所说更像一个类本质的概念,是一种社会联系的原理,而不是立足于人的实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于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来理解历史,因此,共同体概念也更加具有了现实性。由此,笔者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共同体的指代由Gemeinwesen变为Gemeinschaft,并且用了一个负概念虚幻的共同体来指代资本主义国家,这代表了马克思哲学观的巨大转变——由逻辑走向历史。
由于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被看做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对现实的个人是一种桎梏,对个体自由造成了压迫。马克思以生产和分工为基础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变为虚幻的共同体的原因。人们为了生活必须进行生产,而生产的发展又导致分工的出现,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共同利益不仅存在于观念当中,而且存在于现实当中。正是因为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的这种矛盾,所以为了控制特殊利益,共同利益就采取了国家这种与特殊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这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要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工具,“由于资产阶级已经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阶级了,因此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是在一个地区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须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0页。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虽然它表面上代表了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但是实际上只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
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是一种与人的力量相异化的外在力量,在这种虚幻共同体中,人是不自由的。不论是统治阶级中的个人,还是被统治阶级中的个人,都是不自由的,只不过是不自由的程度不同而已。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个人是作为阶级中的个人存在的,而阶级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因此,人无法获得充分的自由,“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体关系中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页。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作为被统治阶级,作为整体都是没有自由的,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即被统治阶级中的个人而言,国家是新的桎梏,只有推翻这种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才能获得自由。而对于统治阶级中的个人即资产阶级中的个人来说,他们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只有他们是该阶级的成员时,他们才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总体来说会使个体自由受到压制,要使现实的个人、个体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把虚幻的共同体变为真实的共同体。
三、“真实的共同体”:人的全面发展与个体自由的实现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中,个体自由受到剥夺与压抑,只有在真实的共同体中,人的全面发展与个体自由才能最终实现,这种真实的共同体就是共产主义。只有在这种真实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自身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共同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为了反对国家等普遍东西的压迫,施蒂纳提出了“利己主义者的联盟”来取代国家、社会等。联盟是为了我的利益而存在的,不受任何自然和精神的羁绊,对待联盟的态度全凭“我”的兴趣。联盟与国家和社会不同,在施蒂纳看来,“利己主义者的联盟”能够实现“我”的所有能力与自由,而社会与国家对“我”来说则是障碍与束缚。在“自由主义者的联盟”中,“我”可以随心所欲,因为联盟是“我”的创造物,“我”高于一切、高于联盟,施蒂纳把“利己主义者的联盟”的建立完全看成是纯粹个人的事情,不具有社会和政治性质。马克思认为施蒂纳的这种联盟是虚幻的,他“把与世界的交往变成与自身的交往,他从这种间接的自我享乐直接过渡到直接的自我享乐,他自己吞食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8页。因此,与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联盟相同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希望能实现个体的自由,但是与施蒂纳的联盟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也承认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但是这种“个人”、“自己”应该是既有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想象出来的纯粹个人或“唯一者”。
马克思认为真实的共同体能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能够实现个体自由,但是如何从虚幻的共同体过渡到真实的共同体呢?马克思同样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认为真实的共同体也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且这种共同体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国家之所以以“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与个人发生异化,是因为市民社会发生了异化,是分工和私有制造成的,归根结底又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所以,要消灭虚幻的共同体,建立真实的共同体,就要消灭现有的分工和私有制,发展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私有制的灭亡,“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也就建立起来了,生产力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而是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所以,为了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各个人就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种占有受三个方面的限制:首先,受占有的对象即生产力的限制,由于这个缘故,就需要发挥个人本身的才能。其次,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限制,以前的革命虽然主体不同,但是他们都从一定的局限走向了新的局限,而现代无产阶级,由于他们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所以只有他们才能实现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最后,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和革命才能最终实现。总之,只有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在主体和各个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真实的共同体——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也只有在这个阶段,“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在这个阶段,全面的个人得以实现,个体自由也得以实现,因此,在真实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体自由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解了。
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确立了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基础;通过批判自由主义的政治解放,马克思确立了人类解放的目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的理论已经渐趋成熟,他以“现实的个人”为基础,以市民社会批判为方向,把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从现实出发,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分工和私有制的角度来考察历史,“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马克思力图克服市民社会的异化,让“现实的个人”真正实现全面发展和个体自由。总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之所以从现实出发,之所以重新定义“现实的个人”,之所以开始重视个体的价值和地位,之所以建立真实的共同体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体自由,施蒂纳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