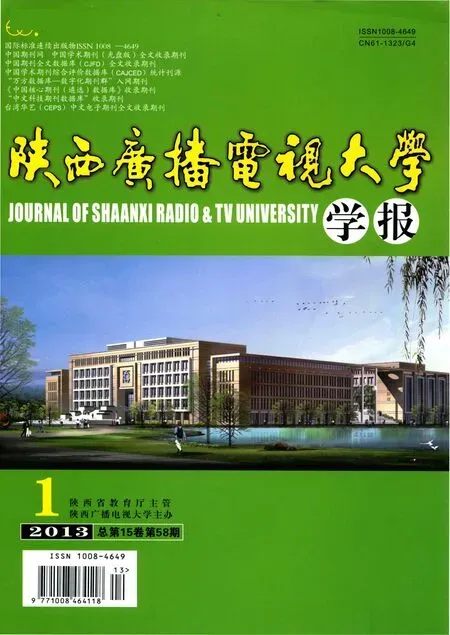从元好问的词《摸鱼儿·雁丘辞》说起*——谈写作主体的审美感悟能力三题
张海珍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金章宗泰和五年 (1205),元好问在赴并州 (今山西太原)应试途中,“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摸鱼儿·雁丘辞》词前小序)。面对一对殉情而死的大雁,元好问感悟到的是美好的至死不愉的爱情,于是他为殉情而死的大雁写下了《摸鱼儿·雁丘辞》:“恨人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在词中表达了他对这一对大雁生死至情的深深感动,谱写了一曲凄婉缠绵、感人至深的爱情悲歌,其中深深寄托了元好问进步的爱情理想。
从元好问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到他所具备的对美的感悟能力。在面对同一景物时,有的人灵感顿生,百感交集,有的人却一片茫然,无动于衷,这正是由于审美感悟上存在差异性所表现出的不同反映。审美感悟能力强的人,时时留心,处处在意,遇事敏感,善于发现生活的美,于是写作时充满了“灵性”;而审美感悟能力弱的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所用心。元好问因为具备了一定审美感悟能力,他才能够不仅观其形,更见其神,从一对殉情而死的大雁身上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寄人生哲理于情语之中,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流传八百年的作品。写作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写作过程也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结合着多种心理活动,包含着写作主体对外界信息和内在体认的分析与综合。北宋张载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经学理窟》)。今人钱钟书也说:“学道学诗,非悟不进”。写作主体只有具备了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各种事物、现象的审美价值进行分辨和评定时所需要的感悟能力,才能在对自然、社会的观察体验过程中,领悟到客体所隐含的意蕴,并在“应会神感”(宗炳《画山水序》)的精神状态中,把握、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与奥义。这种体验往往超越了有束缚的感性生命的有限性而进入到无限的精神生命的自由境界,深刻、真切、发自内心,并达到彻悟与洞明。写作主体的这种彻悟和洞明,能够在把握客体的感性形态的同时,又能够直取其审美底蕴,准确辨别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挖掘出蕴藏在客观事物深处的本质,也才能够写出意义深刻感人至深的作品。因此,写作主体应该具备一定的审美感悟能力。因此分析审美感悟能力应该就从“感”、“情”、“理”几个方面入手。
一、审美感悟之“感”
写作活动不仅仅是对生活的反映或表现,而且是人对自然、对世界、对自我生命存在的一种对美的感知和感悟,以及由这种感知和感悟而后产生的创造冲动。东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序》中说:“诗人之兴,感物而作。”写作动机的产生也正是在写作主体对客体有了特殊而深刻的审美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写作主体首先要具备审美感知能力,“感”是“悟”的基础,审美感知是审美感悟活动的起点,没有写作主体对客体的直观和对其感性面貌的整体把握,就不会有审美感悟活动的产生。而要感知的对象不限于自然景物,还包括了各种社会人事的现象与遭际。朱光潜先生说:“美感起于形象直觉”。宗白华先生在他的一首诗中形象地说明了审美感知能力的产生:“啊!诗从何处寻?在细雨下,点碎的落花声,在微风里,飘来的流水者,在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1](P14)意思是说诗人必须从耳濡目染的世界中去寻找美、感知美。写作主体在对变幻的大自然和纷繁的社会现象的观察、感知过程中才能有所发现,发现了美,才能形成写作能力中的审美感悟能力和美的创造力,也才能产生传达美和表现美的审美愿望和理想。
南宋杨万里说:“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元好问创作《摸鱼儿·雁丘辞》过程也是如此,他通过听觉和视觉等感觉器官了解到大雁的故事,从大雁的行为中感受到的是爱情的永恒魅力和内蕴,最后用词的形式进行传递,表现出作者敏锐的审美感知能力。因此,写作主体要注意扩大自己的视听世界,注意观察、感知客观世界,这样才能产生审美感悟和创作灵感。在感知过程中“不仅是大宇宙,小小的事物也不可忽视。诗人华滋沃斯曾经说过‘一朵微小的花对于我可以唤起不能用眼泪表达出的那样深的思想。’”[2](P16)同时,生活中许多美的事物常常是与平凡、杂乱甚至丑的事物混杂,这就要求写作主体耳聪目明,对美的对象有敏锐的反应,能够在大自然中、在纷繁变幻的社会现实中发现美、感受美、创作美。这除了一定的先天条件外,还可以通过后天的生活实践和审美活动得以训练,刘勰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心雕龙·知音》)。久而久之,审美感官就会变得敏感起来,以致独具慧眼,“见常人所未见,闻常人所不闻”,从而获得独特的感受,提炼出深刻的思想,并在写作中反映出来。
二、深邃体验之“情”
审美感悟基于观察和感知但远不止于观察和感知,在审美感悟中,还始终渗透着深入的情感体验,这种带有情感体验的审美感悟对于写作主体来说如同催化剂,它时时伴随着写作的智力活动,推动思维积极运动,对写作主体的思想认识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人在审美感知过程中,由“感”而生发“情”,由“情”抒“志”,而后成其为诗、文。刘勰也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在面对客观万物时,某种物象触动了人的心灵,往往迸发出深沉的情感,或悲或喜或怒或怨,这种情感的渗透使得审美感受更为深刻。“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写作主体有了敏锐的情感投入和独特的价值判断,才有了独特的审美感悟,从而产生了传达情感的愿望和理想,也才有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诗句。正是由于大雁的殉情引发出元好问对世间生死不渝的真情感动而热情讴歌。元好问另一首词《摸鱼儿·双莲》与《雁丘辞》堪称姊妹篇,写的是人的殉情,主题也是歌颂“至情”,这首词同《雁丘辞》一样,元好问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客体之中,感受到的是相亲相爱、生死不渝的真情。他为这情所感,对至情深情礼赞,同时也悟到了封建势力摧残至情的残酷和无情,在词中表达出他对争取爱情自由而牺牲的青年男女的深深的同情。可以看出,审美主体在审美感悟活动中由于情感体验的渗透才能深入到对对象深层意蕴的把握,情感愈强烈、愈丰富,所获得的审美感悟也就越深刻,心理积淀也愈明显、愈深厚。写作主体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在文字中表现出真情实感,渗透着情感的文字才能显形出生命的体验,才能传达出深刻的思想认识以及对社会、人生意义的深刻揭示。
三、心理体验之“思”
审美感悟是一种理解,是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一种理性把握,因此,审美感悟产生还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认识。《说文》曰:“悟,觉也。从心,吾声。”可见,古人已经发现“悟”是一种认识、明白和启发,是人所具有的一种思维活动方式。清人陆桴亭说:“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思辨录辑要》卷三)在审美感知中引发、形成的这种审美感悟,“悟”到的是人生、社会、生命的真谛、奥秘与深层的意蕴,所“悟”既是一种心理体验也孕含着理性的思维。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在世界之中的生存,就是一个与世界万物进行接触和交往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由感而悟或由悟而感的意识活动和理性思维的活动。写作主体对客观事物反映不同于感官的单纯的生理反应,要发现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要正确认识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就要在审美感悟中渗透深刻的理性思维。元好问从大雁殉情的故事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情,他悟到的是人间“至情”的美好、爱情精神的不朽,以及摧残“至情”的社会现实的残酷,大雁身上还寄托着他进步的爱情理想。写作主体在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感知过程中要“入乎其内”,要进入其内在生命,感悟其内在神韵,进行理性认识与分析,又能够出乎其外,由形及神,由表及里,由粗及精,从具体的感受中领悟,在切身的体验中品味,感悟人生本质和生活的真谛。写作主体具有了理性的思考与认识,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正确地区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写作中才能表现正确的思想、健康的情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总之,写作过程包括了敏锐的感知能力,深邃的情感体验和深入的理性累考,这和审美感悟是一致的。审美感悟之“感”,既是感知,又是情绪,而所谓“悟”,既是一种心理体验也孕含着理性的思维。
]
[1]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雁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