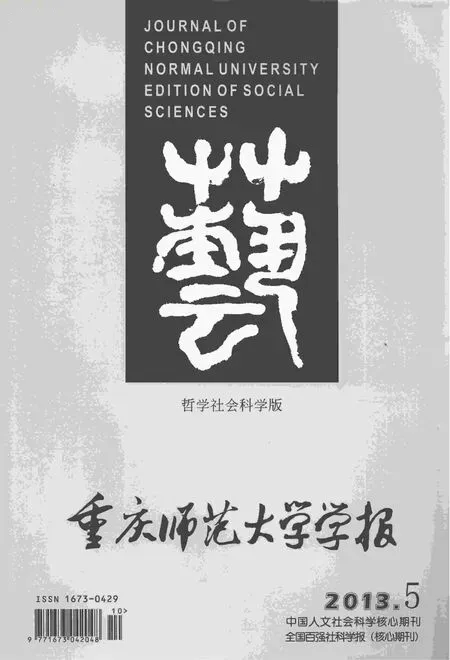《镜花缘》中李汝珍尚才主智的价值观
陈 呈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一、女子的才学展示欲
李汝珍笔下的才女可以被看做一个整体来讨论,学者夏志清曾在文章中调侃:“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性格悬殊、出身迥异、智勇不同。但那百个女子,全属绮年玉貌、蕙质兰心,要分辨她们,更戛乎其难。为了帮助读者记忆,所有孟家女子,作者都在其名字上着一‘芝’字。而所有嫁给章家的,则着一‘春’字,有些名字则提示我们,某某女子擅长绘画、音乐或书法,或某些又长于什么。否则,就没有什么容易的办法去辨认那百个女子中较不重要的了”[1](31)。虽然这是小说文本技巧上的缺陷,但也正因为才女们的太过相似,由此构成了群像,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观。
作为《镜花缘》的主角,那一百个名字被刻于泣红亭玉碑上的女子,其第一重身份就是才女,李汝珍也因此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数量最庞大的才女群像。她们各怀才学,既有经史诸子、医卜星相、音韵算法、经商习武等社会实用性的才能,也精通传统女学里琴棋书画及文人宴乐中灯谜酒令、双陆马吊、射鹄蹴毬、斗草投壶百戏之类,可谓文武双全,刚柔并济。然而,与李汝珍同时代的亲友序跋中并没有表现出对《镜花缘》中女性才能的强烈关注和兴趣。究其原因,当与同时代的女性创作之繁荣、才学活动之频繁有关。
从整个古代社会的女性作品中来看,清代女性的创作无论从数量上和文体上都达到了高峰。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是目前关于女性著述最全的汇总。此书中用十五卷的篇幅专列清代妇人的作品,而之前的明代不过两卷。就人数而言,据初步统计,汉代至元代有116家,明代244家,清代一朝就有3518家。胡文楷在该书的自序中概括云:“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2](5),可见当时女子创作的盛况,在这些女子中,尤以李汝珍长期居住的江苏一带为盛,学者史梅在其《清代江苏妇女文献的价值和意义》的论文中,除了《历代妇女著作考》中著录女作家1425人,著作1707种外,还从江苏各地250部地方志中辑得其未收的118名女作家,著作144种。
《镜花缘》从第六十九回《百花大聚宗伯府,众美初临晚芳园》到第九十三回《百花仙即景露禅机,众才女尽欢结酒令》,百位才女在宴会中切磋诗艺,聚于雅室小亭或小园香径,赏鱼逐蝶、弈棋抚琴、泼墨挥毫,俨然是当时女子结社的写照。清代女子对才学展示和实践的欲望增加了,她们与当时的才子名士一样,以地域为范围结社结派,著书立说,往来唱和。《历代妇女著作考》中录入的《清代闺阁诗钞》清晖楼主序曰,“至有清一代,闺阁之中,名媛杰出,如蕉园七子、吴中十子、随园女弟子,至今犹脍炙人口”[2](927)。这些闺秀互相结社、酬唱应答、品评诗文。据学者王英志《随园女弟子考评》统计,最有规模的随园女弟子,其人数至少在50人以上,大大超过有记载的男弟子数量20余人。这些女弟子经常自发地聚在一起进行文艺创作,如《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庚戌(乾隆五十五年)春,扫墓杭州,女弟子孙碧梧邀女士十三人,大会于湖楼,各以诗画为贽”[3](693)。女子诗社之类的文化社团的兴起和流行,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清代才女们的生活。
随着习得的才学种类增多,书中才女们对施展才华的领域也有了更多的想法,除了传统的闺阁范围,更将理想伸向了长久以来被男子独占的社会朝堂。本来,有关才女对科考抱有积极态度的叙述在更早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见,但如此群体性地对科举产生向往却是罕见的。由百花仙子化身的唐小山是一百才女中的领袖人物,她出生在普通的文人家庭中,在年少时期就开始对科考向往。小山四五岁就喜读书,能过目不忘,而且文武双全,时常舞抢耍棒。长大些就询问叔叔唐敏女科考试的时间,以便早早用功,早作准备。书中的才女们在经过和男子一样的经史诗文发蒙教育以后,自然想要有一番作为。即便是商人林之洋的女儿婉如和多九公的侄女在女试盛典颁布后也赶去一试身手。世家大族中的才女群体对科考的向往就更不必说。卞、孟、蒋、董等官家的闺秀因父亲是考官不能应考,各个闷气,其父母将其聚在一块散心,散心不成,她们还要卜卦看有没有机会补考,算得上签才各个舒心高兴,可谓应考心切。书中最特别的一位应考才女还要数黑齿国才女卢紫萱之母缁氏,她自幼饱读诗书,只是一直没有考试机遇,虽然已经嫁作人妇,却仍想证明自己的才华,在亭亭(卢紫萱)要随唐小山去天朝赴考时,她以女儿为要挟,要求小山带自己同去天朝一试。到了天朝,缁氏的科考也是一波三折,但她越挫越勇,终于因考官的体谅拿到了才女匾额,这才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这个百折不挠,不顾老脸的喜剧角色身上也带着些许辛酸,她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真才实学,努力寻求舞台的平凡读书人。
二、他者的才学保护欲
女性有了才学展示的自觉和要求,但毕竟处在弱势地位,要想实现她们的需求必须借助外力的支持。李汝珍首先从社会认同方面为才女们的才学提供保护。《镜花缘》中的“他者”就是才女们展示才学的社会思想舆论上的坚强后盾,“他者”普遍对才女的才学持赞美、肯定和支持。书中第六回,上官婉儿被命与群臣一同做诗,一连两日都没有一人在上官婉儿之先交卷。满朝大臣对于输给一个女子并没有表现出气恼,反倒是大大方方地认输并称赞:“天生奇才,自古无二”[4](17)。就众才女的家庭看,由于对才女的教育投入了大量心血,所以对她们参加科考也是多加鼓励的。主考官卞滨等人的女儿出身官宦之家,自小受教育自不用说。即便在落魄文人家庭出身的唐小山也是自幼读史通经、舞枪弄棒,不但无人约束,还得到了叔叔的指导。商人林之洋对女儿婉如酷爱学习的行为也是欣喜与鼓励的。
不仅如此,李汝珍还直接将社会认同的力量扩大至朝廷统治者,以最高权威来为女子才学正名。作者将故事发生的时代定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女皇统治下,才女们自然有一展抱负的机会;二是唐初正是科举制度的确立时期,如果能在此期形成传统,那么今后才女们的命运便会大大不同。于是李汝珍借武则天的身份为才女们创造了一个旷世盛典。第四十一回中,唐敏说出了武则天设立女科考试的原因:“太后自见此图(《苏氏蕙若兰织锦回文璇玑图》),十分喜受。因思如今天下之大,人物之广,其深闺绣阁能文之女,固不能如苏蕙超今迈古之妙,但多才多艺如史幽探、哀萃芳之类,自复不少。设俱湮没无闻,岂不可惜?因存这个爱才念头,日与延臣酌议,……即于前次所颁覃恩十二条之外,续添考才女恩昭一条”[4](193)。归根结底,兴此制度还是因为爱才。此后颁布恩诏,其中外籍可参加考试的规定颇有大国的胸襟气魄,同时也保证了诸如黑齿国红红和亭亭、女儿国阴若花等漂泊海外的才女能有同样有参加考试的机会。并且“因生病或路远可补考”一条规定也化解了影响才女参加考试的不利因素。其后更是宽容地表示,恩诏颁布突然,恐诸女学业未精,所以专门延迟到圣历三年三月部试,这就保证了此次考试的有效性。考试期间,武则天的爱才与惜才的表现也层出不穷。担任部试主考官的官员子女本应避嫌缺考,武后却特发谕旨,钦赐各才女至期一体殿试。在部试中“俱因污卷贴出”的花再芳、毕全贞、闵兰荪三名女子,再三乞求殿试,武后也能体谅其少年要强之心和千里迢迢赶考的辛苦,姑念污卷乃无心之失,准其一并殿试,以彰显求才若渴之至意。这次特殊的女子科考从惜才的角度出发,既有严格的条例规范作为制度保障,又处处体现着对人才的珍视与宽容,以官方的权威作为女子展现才能的最坚强的支撑。
其实女子以自身才能为社会所用早已见诸各种文学作品,比如南北朝时期描写女子替父从军、卫国立功的《木兰辞》、徐渭所撰杂剧《女状元辞凤得凰》等。但这些作品中,花木兰从军、黄春桃参加科考,无一不是变装过后的巾帼英雄,都是以个体身份单枪匹马地在男权社会里小心翼翼,或者可以说是偷偷摸摸地争取自己才能的展示机会。她们以男性模样在社会上风光无限,然而一旦女性身份被识破,只能被打回原形,重新回到闺房,回到男权的压制中。而《镜花缘》中的才女能够以女性的身份公开地参加科举考试,光明正大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这是李汝珍爱才的集中体现。
三、尚才主智的价值观
李汝珍对才的重视和褒扬不只是对于女性而言,这种审美观是普世性的。这一百才女是作者树立的有才之人的典型。他在全书中表现了自己鲜明的立场:以才学作为衡量人高下的基本标准,无关性别。有真才实学的人值得真心实意地赞美,而那些不学无术或不懂装懂的假儒士就该被毫不留情地嘲笑。从书中对海外黑齿、白民、淑士三国的描述可以看到李汝珍明确的态度。
李汝珍在文本中塑造了一个女子教育极其发达的黑齿国。黑齿国是作者对女子才学认同的体现,更是作者想要塑造的理想审美观中“以才为美”的集中体现。这个国家以才作为衡量女子的最高标准,男人对女性之美的评判不再是品头论足。林之洋见此处女子长得黑,以为是没有脂粉用,怀着奇货可居的心态想要带脂粉去售卖,却发现这里的女子反觉脂粉丑陋,倒是买书的很多。唐敖见识了两位女子的才学之后,走在黑齿国的街上,只觉得每个带有书卷气的黑女都美貌无比。这里的风俗是“无论贫富,都以才学高的为贵,不读书的为贱。就是女人,也是这样。到了年纪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亲。若无才学,就是生在大户人家,也无人同她婚配。因此他们国中,不论男女,自幼都要读书……这里向来分别贵贱,就在几本书上”[4](77)。腹有诗书气自华,作者借黑齿国的习俗明确地矫正着世人的审美观念。
白民国是作为黑齿国的反衬而出现的。白民国的人个个面白如玉,美貌异常。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吃了亏,见白民国人生的清俊,以为他们是天资聪颖又博览群书,于是在学塾前毕恭毕敬地听候老夫子训诫,正当准备离去时,却听见夫子在里面“切吾切,以及人之切”,[4](96)本以为又是什么深奥学问,突然反应过来,不过是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幼”字读错了,两人好不羞恼,原来这夫子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又喜欢自吹自擂的骗子。
淑士国则是作者用来讽刺名不副实的酸腐之士。这里的人个个儒者打扮,人人斯文,处处书声。可惜这些儒生皆为腐儒。不通文墨的林之洋胡编的《少子》竟令一群“好学”的生童欢喜不已。酒楼中酒保戴着眼镜,还拿着折扇,一开口便是“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4](102)上的下酒菜尽是青梅、齑菜。林之洋喝了一口酒,连忙吐出,原来那酒太酸,误以为是醋。这一吐引起旁边一个本来晃着身子“之乎者也”吟个不停的老者的注意,接下来一段长篇大论,一口气五十一句,句句带“之”:“先生听者:今以酒醋论之,酒价贱之,醋价贵之。因何贱之?为甚贵之?真所分之,在其味之……倘闹急之,我惟跑之;跑之,跑之,看你怎么了之。”[4](103)林之洋以俗人的角度一针见血地评道:“你这几个‘之’字,尽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也弄酸了。”[4](103)与唐敖谈分科考试的“大儒”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酒保一定要留好喝剩的两杯酒和吃剩的酱豆腐、糟豆腐,已经走了两步,见旁边桌上放著一根人家吃完饭剩下的秃牙签,“取过,闻了一闻,用手揩了一揩,放入袖中。”[4](104)这些人外表倒是像儒者了,但透过点滴小事表现出的却毫无儒者气度。这些人的作为与作者尚才主智的价值观背道而弛,自然受到作者的无情嘲讽。
四、尚才主智价值观的形成
1.汉学学风
李汝珍对博学多识、真才实学的赞赏和对空疏无识与迂腐僵化学风的讥讽所体现出的褒贬鲜明的态度,与当时主宰整个时代的汉学学风分不开。作者所处的时代,恰好是考据学的鼎盛时期。乾嘉汉学的门户确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日渐充斥文化界的空疏不学、虚谈性理的风气划清界限。清代的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谈到经学之所以自两汉后衰落而在清朝复盛的原因时就曾说过:“一则明用时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阎若璩谓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时文者而极。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5](299)
胡适曾以李汝珍身处一个博学时代的无奈来解释《镜花缘》掉书袋的嫌疑。从汉学的启蒙时期到兴盛时期,汉学一脉的学者无一不是穷经通史,博学强记之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吴派代表惠栋的治学范围是“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6](5)。皖派代表戴震则是17岁师事经学大师江永,学习声律、音韵、天文、历数、典礼。李汝珍的老师凌廷堪是乾嘉时期的礼学大师,其友阮元对其学问多次称赞,“次仲于学无所不窥,九经三史过目成诵,尤精三礼,辨析古今得失,识解超妙。”[7](88)阮元《凌母王孺人寿诗序》戴震弟子朴学大师卢文弨为凌廷堪《校礼堂初稿》作序时,将其列于顾炎武、戴震、程瑶田实学一脉,而“顾、戴不能为诗与华藻之文,而君兼工之。诗不落宋元以后,问责在魏晋之间,可以挽近时滑易之弊。”[7](169)卢文弨《校礼堂初稿序》凌廷堪自幼擅长诗文,乾隆四十七年,翁方纲看过凌氏所作辞后惊叹为“不朽之业也”[7](78)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并收其为弟子。凌廷堪也通金石,曾勉牛坤留心于此,“诚以其有益于考订。”[7](109)凌廷堪《答牛次原孝廉书》至于音韵,李汝珍《李氏音鉴》里曾说“母中麻韵,即夫子所赠也。”[7](163)李汝珍《李氏音鉴》第三十三问此外,阮元在编篡自然科学家列传《畴人传》时,也得到了凌廷堪的帮助。李汝珍的妻舅兼好友许乔林是扬州派的重要人物,除了贯通经史,在小学方面也颇有研究。比如算术方面曾向凌廷堪请教戴震《勾股割圆记》中的疑难问题。许乔林之父与作《畴人传续编》的罗士琳之父为至交,许乔林与精通算术天文的罗士琳也时有唱和互访的交流。被李汝珍引为莫逆之交的许祥龄,“性喜吟咏,业医”[7](336),想必《镜花缘》中的几张药方正是与此人相关。李汝珍本人被许祥龄称为“博物君子”,对音韵、围棋十分精通,著有《李氏音鉴》、《受子谱》两本专著。李汝珍与友人往来时不仅有寻常文人聚会的诗文唱和,更有技艺切磋,譬如乾隆六十年李汝珍在板浦举行公弈,与颜希源、沈谦、李汝璜、吴焯等对弈。嘉庆七年,与许乔林、许桂林、徐鉴、徐栓、吴振勃、洪棣元等切磋时,为《音鉴》新添11个韵母。可以说,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关于种种学问的獭祭展示,既是他对博学实证学风崇尚的一个表现,也是他受汉学学风浸淫的证明。
2.师学脉承
考据学在经历了清初启蒙阶段之后,于乾嘉时期大兴。清代学术自兴起之初便有求实求真,精审博证的优良传统,至李汝珍师友凌廷堪、许乔林一代,汉学虽以地域分派,但扎实朴素的学风是各派均尊奉的基本治学方法。此外,自戴震起,这一脉学者开始真正试图从思想上充实汉学,虽然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说,大概主要部分只是新瓶装旧酒,是对朱子思想的回归,但仍是对当时思想界的一个矫正。戴震义理学说中很重要的一点,即德性至当,必先务于知。“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不能尽其才,言不扩充其心知而常恶遂非”,“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学问,贵扩充”[8](22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凌廷堪在《荀卿颂》中以上智下愚分划善恶两性,他的学友焦循论性善时也说:“性何以能善?能知故善……禽兽不知,则禽兽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则人之行善矣……人之性可引而善,亦可引而恶。惟其可引,故行善也。”[8](107)焦循《性善解三》“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8](38)凌廷堪《复礼中》无论文才武德,还是小学经义,都是格致工夫。除了德行教化的强调,其实还包含了诸如天文、历算、金石、堪舆等。
李汝珍每每将才、德放在一起,以才学之高成全德行之美,又以德行之美验证才学之高。最明显的表现是作者的“才女薄命论”逻辑。才女们因为有较之平庸女子更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于是以才学践行道德价值观,并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名节。“红颜薄命”在第一回出现后,第四十八回又在泣红亭的对联“红颜莫道人间少,薄命谁言坐上无”中再现。第七十一回中,将泣红亭匾额念给众才女听之后,师兰言劝诸女“但行好事,莫问前程”[4](327)。锦云问及颜子并未妄为,却何愆而夭,兰言道,“他如果获愆,那是应分该夭的,夫子又哭他怎么,就同叹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一个意思,因其不应夭而夭,所以才‘哭之恸’了。”[4](47)这里作者已经开始引经据典地说明薄命观的真正内涵。第九十回,宴会上无意得知了自己命运的众才女,在经过道姑的点化后,大多对这样悲剧命运的态度发生转变,如玉芝所说,“及至听到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几句话,登时令人精神抖擞,生死全置度外,却又惟恐日后轮不到自己身上。只要流芳百世,就是二十四分惨死,又有何妨!不知区区日后可有这股福气。”[4](429)小说中花再芳等三个才女是一百才女中的倒数三名,才疏学浅又不懂谦逊,以致在科考前后以及才艺宴会上频频出丑。此三人对玉芝所谓死得其所的观点全不认同:“妹子情愿无福,宁可多活几时,那怕遗臭万年都使得,若教我自己朝死路走,就是流芳百世,我也不愿,现成的真快活倒不图,倒去顾那死后虚名,非痴而何。”[4](429)这种反应与小说前几章中,这三人不顾道义,卖主求荣,为保命而应武后开花之诏,导致一百花仙下凡,其言行可谓一致。很显然,在作者的观念中,才疏学浅的人更容易为名利性命而不顾名节,是应该遭到否定的。
3.理想自寓
《镜花缘》中,作者给才女们安排了最宽容的社会环境来保护她们的才学。科举是官方对一个文人才学的最高认可,李汝珍就如同书中身怀各种才学的才女,也在寻求着自己才学被认可的机会。关于李汝珍身世的文献所存不多,胡适在《<镜花缘>的引论》中说,“《顺天府志》的《选举表》里,举人进士队里都没有他,可见他大概是一个秀才,科举上不曾得志”[9](369)。孙讯佳在《<镜花缘>公案辨疑》中以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所列受业于凌氏的弟子中乔绍侨、绍傅两兄弟为证,其一为举人,一为廪生,而无李汝珍,那么很有可能“恐怕连个秀才都不是”[10](5)。嘉庆六年,李汝珍曾得豫东治水县丞之职,有许乔林送别诗《送李松石县丞汝珍之官河南》可证,其官职性质类似于投效河工。但河南方志同样没有李汝珍做官的记录,《<镜花缘>丛谈》中的推论是:一种可能是这是候补县丞,后来也并未实授;另一种可能是嘉庆四年七月在黄河砀山附近的邵家坝决口,朝廷允许捐资投效河工,李汝珍的官是捐来的,因为清朝捐纳制度规定,捐纳官不能实授正印官。据孙佳讯的考证,石文煃在《音鉴序》中所言“今松石行将官中州矣”一句,李汝珍确实有再度“之官河南”,但极有可能是嘉庆十五年《音鉴》付刊时,李汝珍深感这次河南行并没有如石文煃所言“黼黻皇猷,敦谕风俗”,于是把这段删掉,导致了页心同样有“宝善堂”字样的两个版本的石序中,一个有“将官中州”一段,一个却没有。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传统文人,从仕宦生涯的贫乏可见其不得志的程度。李汝珍在一生仅有的两次官宦经历中所担任的都不是重要职位,他空有一身才学,却无人赏识。
《镜花缘》的科举有两个鲜明特点,都带有李汝珍的个人理想色彩。一是武则天开设女科。人分男女,阴阳平衡,缺一不可。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读书仕宦向来是男子的人生道路,女性被科举这个朝廷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所抛弃,她们的才华被局限在家庭里,最终也只能做自我消遣之用。作者在书中提出女试,既是在为才女争取才学展示的机会,也是在借此安慰同样怀才不遇的自己。所以女科的开设,并不简单只是因为当时的李汝珍有了男女平等的先进思想,而是女科考试弥补了社会上另一半人才被闲置的缺憾。作者以跨越性别界限的女科考试制度,表达了自己渴求社会上终有一天能“野无遗贤”的愿望。二是分科考试。淑士国不但实行全民教育,也实行全民考试,士、农、工、商各个行业莫不从考试出。因为考试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辞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只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顶头巾,一领青衫。”[4](104)以分科考试选拔各种人才,从事任何行业都要有才学,确实达到了其国王勉人读书上进的目的。而且这些才能的列举让人不禁想到李汝珍本人,余集在《李氏音鉴》中评价他,“少而颖异,读书不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11](605)余集《李氏音鉴序》在普遍重道轻器的社会传统中,经学被奉为至高无上、甚至是惟一的正经学问,那么李汝珍这样的全才可能在当时文人的眼中根本只是“卖弄稗贩拉拉不休”[11](605)王之春《椒生随笔》的失败者。李汝珍当然会为自己的满腹才学抱屈,考试一直是正统的但并非最好的挑选人才的方式,李汝珍设想以分科的形式最大化地保证考试可以发掘与鼓励不同领域的人才,使任何只要具备一种专长的人都有机会通过考试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这两个“创意”无疑正体现了李汝珍想要为自己才学正名的欲望,亦即对理想科举寄寓的改革期望。
李汝珍以才女为主要载体,呈现了自己尚才主智的儒者理想。他写才女们的各类才学,写她们渴望展现才华的愿望,为她们提供最宽容的环境和最高的舞台。李汝珍对真才实学毫不吝啬地赞扬,对不学无术、装腔作势或只知死读书的假儒生则是毫不留情地嘲讽。这种价值取向的形成,既与当时名士大儒对女性才学的包容,以及汉学兴盛带来的崇尚博学的社会风气相关,更有李汝珍对汉学中戴震、程瑶田、凌廷堪一脉经世思想的服膺相关。同时也不能忽略李汝珍本身怀才不遇的遭际。博学真知是知礼崇德的基础,越是才高越是德备。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展现的价值观,是一位儒者对社会殷切关注的产物,是对世人,特别是读书人的深切关怀。
[1]夏志清.人的文学[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4]李汝珍.镜花缘[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皮锡瑞.经学历史[M].中华书局,1959.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东方出版社,1996.
[7]李明友.李汝珍师友年谱[M].凤凰出版社,2011.
[8]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9]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0]孙佳讯.《镜花缘》公案辨疑[M].齐鲁书社,1984.
[11]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Z].齐鲁书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