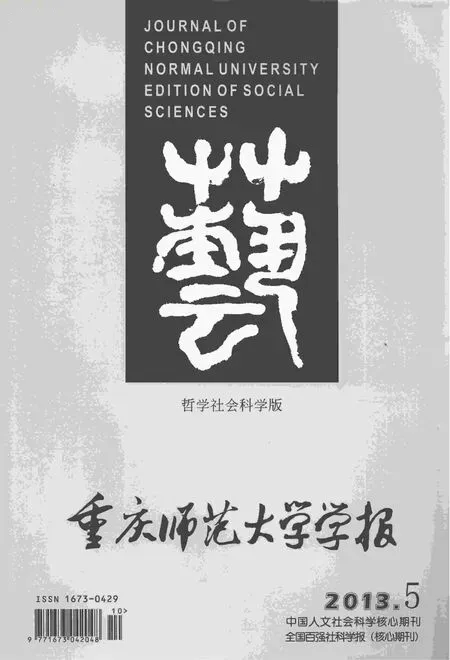论文学翻译的符号美学
肖 娴
(重庆理工大学 语言学院,重庆 400054)
翻译是人类社会最复杂、最艰巨的一项活动,它的建立和发展与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美学和文化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美学与翻译的联姻又是中国传统译论的一大特色。刘宓庆(1986,2005),黄龙(1988),毛荣贵(2003),吴文安(2003)从不同侧面谈及翻译美学的范畴、标准以及实践方面的问题。然而,在笔者看来,传统翻译美学侧重于描述而非解释,关注审美主体的直觉经验而非客观规律,理论解释力不强。基于此,本文试图以符号学为理论框架对传统翻译美学做出补充,以求全方位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规律和美学实质。
一、传统的翻译美学
中国传统译论深深植根于古典美学理论中,大致经历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对文艺作品中形意的探讨,反映在译学中则是文派与质派的论争;另一条是翻译的艺术派,源于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哲理性思考。关于文质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支谦在文中引用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来阐明佛经翻译的原则“因循本旨,不加文饰”。[1](6)强调翻译注重的是质朴的文风,词藻修辞应让位于语义的忠实,这种好质贬文的翻译思想引发了后来的文质之争。另一方面,翻译的艺术派强调原作艺术意境的传达,将翻译完全纳入美学范畴,如陈西滢的形似、意似、神似论,林语堂的翻译美学论,茅盾的“神韵”说,朱生豪的“神味”,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等等。相比之下,钱钟书的“化境”可谓是对“意境说”最高层次的要求:“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格”。[1](418)纵观译学历程,无论是“文质之争”还是“意境说”,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以哲学为基础,美学为辅的走向。
然而,翻译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一定情况下其优势会转化为劣势。翻译美学的标准倾向于主观,在具体评价过程中操作性不强。中国传统译论受哲学思想的影响,推崇体认、灵感、自省、意会、凝思、悟性等直觉性思维方式,力求心领神会美学的最高境界“道”以及万物合一的“意境”,如严复的“神理融合”、傅雷的“深切领悟”。然而这些都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用逻辑去论证。曾文雄指出,“中国传统美学呈现出的不是对客体的反映,而是对客体的评价;不是给翻译的艺术属性以客观的美学解释,而是给以主观的美学规范。”[2](191)基于实践经验的译论大多为语录、评点式的随感,以此为关照的译本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美学视翻译为一门艺术。要真正做好翻译,必须从美学角度去理解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美学实质。“美”不是具体语言层面上的机械对等,而是脱离语言形式束缚的神似,在神韵上近似于原文。我们不否认文化因素和美学成分的影响,翻译过程的确有主观能动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有客观性的一面。“意境说”、“神似说”一直延续的是古代的一套模糊评价体系,虽涉及句法形式、风格等问题,却只是一个宏观的架构。而翻译最终都应落脚到语篇、句子、短语、字等各个层面的转换。忽略语言系统中的内在规律和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描写,必将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
在翻译美学看来,文学反映的是主体的审美意识。主体是文学是出发点,作品必须依赖于主体而存在,反映在翻译中则是译者和读者对译作的双重制约作用。作为原文信息的接受者和译语信息的发出者,译者首先以读者的身份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在体会原文意旨之后,揣摩其神情,加入自己的所感、所思并转换为文字,又具有“再创造”的主体性。而译作一经完成,就具有独立的价值,其意义就脱离原作的约束,依存于读者的阐释。作品通过读者主体而显现自身,每一位读者都会赋予原作个性化的阐释,但是译者和读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可绝对化,其再创造活动必定以原作的意图为限度。
至此,我们似乎陷入了困境:一方面,纯语言的转换必以牺牲原作的美学形态为代价,另一方面,艺术事实又不可完全还原为语言事实。“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译者对原作不单单是进行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而且还要进行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3](14-16)。如何在科学与艺术,美学与语言学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呢?笔者认为,符号学和翻译的联姻可以为我们提供全方位的审视文学翻译实质的平台。
二、文学翻译的符号美学
现代符号学之父皮尔士是全面研究符号学的第一人,他的符号学理论之于翻译美学有诸多契合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注语言的表征性。符号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滋生出语义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逐渐固化下来、脱离语境成为相对稳定的阐释项(interpretant),叫做符号的意指。但是,符号的意指过程是一个无限递归系统。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总处于变化的状态。在一级符号的基础上,符号再次回指,产生出新的阐释项称为意蕴。但是,符号与阐释项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符号的存在是为了表征事体,但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能代表某事物。经过无数次的阐释,符号与阐释项建立起一对多的表征关系。另一方面,说明语言具有有限性。符号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作为一种表现手段表征客观世界,然而作为表征的符号是不完善的,正如道家有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实际交际中,因为人类认知机制的局限,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处理所有的信息,往往提取其中一些有用信息,而另一些就作为缺省值(default value)。但正是这种局限造就了语言的美,“意犹未尽”、“玄外之音”才得以产生。
(二)注重符号逻辑结构的研究。按照符号的表征关系,皮尔士将符号划分为指示符、象似符及象征符。指示符体现为符号与所指物之间维持的某种因果邻近关系,遵循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且符号与所指物保持同一性原则。但这种对应关系必将减损原作的艺术价值,封闭原作的意义潜势。苏珊·朗格在谈到艺术符号的审美特征认识时指出,“指明一个事实的是记号,它与其所代表的对象是一一对应的,而符号所代表的更多的是观念和相像的东西,它包含着多层意义。”[4](66)象似符和象征符就并非遵循逻辑的推理。象似符是阐释主体基于符号与所指物之间的共享特征而创建的,表明的是纯粹的、先于任何思想的直观感受,重译者的直观体味。象征符号则是符号的抽象阐释,处于符号的最高层,具有不可确定性、创造性和多义性。二者皆属于艺术符号,服从作者感情抒发的需要。“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以及“天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中所堆砌的虽是一系列的意象,但指示符“鸡”、“茅店”、“天山”、“鸟”等都不再单单指向语言所描绘的客观事物,而是借景抒情,渲染了游子的浓浓情思和孤寂之感,这就是象征符号激发的形象意义。
(三)翻译标准的客观性。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翻译美学的一大特点是审美标准的主观性太强。虽说审美价值的再现离不开主体的审美意识,但单单以认知主体的“顿悟”、“意会”来评价译作,难免陷入自说自话的囹圄。著名翻译家林纾的译文可谓是涵盖古今、旁征博引、语出典雅、语言风趣幽默,钱钟书曾提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也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作。那么林纾的译本是否超过原作呢?笔者认为在艺术创造上固然不错,但脱离原作的肆意翻译或任意枝蔓的“意译”已算不得翻译。诚然,翻译需要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保证读者最大程度理解原文,但不可过多地干预原作,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作者——译者——读者三元关系的平衡,以原作为旨归,尽量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任何一方都不应偏执。
(四)符号学的包容性。翻译美学中争论最久的莫过于形意或者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了。翻译的神似派强调内容的优先地位,当文本中内容与形式、意义与风格对立的时候,应牺牲后者保全前者。然而我们不禁提出质疑,失去了诗歌形式的诗还算不算诗歌?国内神似派的代表翁显良就主张不要因韵害义,在准确译出原文意义的基础上再现原文的深层韵味,其英译本《登鹳雀楼》如下:
Westward the sun,ending the day’s journey in a slow descent behind the mountain.Eastward the Yellow River,emptying into the sea.To look beyond,unto the farthest horizon,upward!Up another storey
其实,“重神似”并不是说形式可以完全忽略。就诗歌来讲,除了具备美的意境,还须有美的韵律。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都应是翻译美学关注的范畴,“象似符具有某种结构特性,可以直接在阐释者主体心中激发认知联想”。[6](157)诗歌本身的外部结构特征虽属非语言符号,但可以激发认知主体的情感,因此应作为重要的审美要素之一。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符号学和翻译美学在对语言和翻译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兼容性,而符号学对翻译美学的发展又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因此我们试图以符号美学为框架,探讨文学翻译中具体的策略和评价标准。
三、符号美学的原则
传统翻译美学侧重于实践,缺乏理论上的指导作用。许多译者虽试图全面描述翻译的整个审美过程,对每个要素做了细分,但其中不乏啰唆、重复之嫌。对原作审美要素的分析属于横向切分,这样的划分还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直至无穷无尽,因此不具备纵深分类的科学性。基于此,我们在结合符号学和美学特征的基础上,总结出符号美学的三个原则,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即标记性结构原则、弱隐含原则和意义的多项性原则。
(一)标记性结构原则。对标记性的探讨源于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可依和雅克布逊对音位学的分析。侯国金(2005)将其引入到翻译中,提出“语用标记等效原则”,即以有标记和无标记为标准,分析语言各个层面的转换。他指出认知主体出于某种特殊的意图会采取一定的语用手段,如使用特殊的、不常用的表达式,称作“标记项”(marked item/term,缩写为M)。相反,那些常用的、处于“默认值”状态的言语,则为“无标记项”(unmarked item/term,缩写为U)。[7](1-23)文学语言的特殊性就在于通过违背常规的符号组合,获得自身的分量和价值。例如李白诗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中两个“之日”明显属于语义冗余,与意义没有太大的关系,似乎可以改成“弃我去者昨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多烦忧”。但小小的符号变动,破坏了诗歌整体的谐和感,因为“之日”的增添是考虑到音韵的效果,故意拖长了元音,这样读者听起来才有如叹息、哀怨感。标记性结构原则指的是以符号的结构特征为线索,着眼于不同语言系统内的结构重组,再现原作的审美构成。请看下面的例子。
例1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a.我在看到厄尔巴以前是强有力的。(钱歌川译)
b.不见棺材不掉泪。(许渊冲译)
c.不到厄倒我不倒。(许渊冲译)
d.落败孤岛孤败落。(马红军译)
e.若非孤岛孤非弱。(马红军译)[8](66)
该句据说是拿破仑战败被放逐于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所写。从符号的组合上来看,原作具备一种均衡美,无论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符号的排列顺序都是一致的,这在修辞上称作回文。同时,符号的重复构成韵式上的押韵,读起来乐感很强,被赋予强标记性价值(M+)。译文(a)考虑到意义的传达,肆意将符号之间的关系重组,改变原作的形式特性,失去了原作的“韵味”。同样,译文(b)和(c)牺牲形式以求产生类似于原作音韵效果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而译文(d)和(c)从翻译的审美实质出发,首先在字数上对等于原作,创造性地以“孤”指涉第一人称“我”、“孤岛”代替“厄尔巴”,并以“落败”和“败落”对比拿破仑当下和以后的处境,再现音韵、词汇及句式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符号结构特征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好的译文不仅要求意义等效,而且要标记价值等效。
(二)弱隐含原则。在语言学家荷恩看来,语言是由一系列按信息强弱大小或语义力度排列的语言成分组成,说话者的陈述A(S)总体信息上弱于对方知道的程度,听话者对话语的推导必须遵循荷恩等级,即S和W的词汇性质相同(因此,没有<iff,if>的荷恩等级关系,不能进行“条件扩充型的推导);A和W的语义关系相同,即来自同一语义场(因此没有<since,and>的荷恩等级关系,不能进行‘关联强化型’推导)”。[9](174-175)在荷恩等级关系中,强项蕴含弱项,弱项否定强项。换句话说,语义的弱项不能推出强项。弱隐含原则与翻译美学概念中的“空白”理论是相符合的。文本的“空白”是没有直接明说或明确写出的一部分,依赖于读者的想象去填补,如果把含蓄的说白了,把虚的说实了,势必会封闭译文意义的潜势系统,译本则毫无美感可言。下面我们以双关翻译来进行阐释。
例2“Why is the river rich?”
“Because it has two banks.”
译文1“为什么说河流是富裕的?”
“因为它有两个银行啊!”
*原文bank是双关,一指河岸,二指银行。
译文2 问:问什么说河流富有?
答:因为它总向前流。
或:因为它年年有鱼呀。 (马红军译)[8](33)
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译文1未能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采用直译加注的方式进行翻译。虽然照顾到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但丧失了原文的标记性特征,译语读者丝毫不能意识到作者的独具匠心。更为重要的是译文显化原作中的隐含信息,没能给读者留下任何思考和遐想的空间,从而造成审美构成和信息的减损,译文也失去了美学上的价值。而译文2巧妙地将语义双关转化为谐音双关(“前”谐“钱”、“鱼”谐“余”),既保持了原作的结构特征,又构建了类似的语境效果,有助于引发读者与原作之间审美情感的共鸣。可见,与关注原作形式特征的标记价值原则不同,弱隐含原则侧重的是符号的意义层面,如何以有限的符号组合彰显无限的意义潜势系统。
(三)意义多项性原则。在符号意指过程中,符号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会产生意义的两个层面:意指和意蕴。意指在共时系统中运作,具有明晰性和离散性。意蕴与外部历时平面联系,指向的是意义的潜势系统。一个符号可能同时蕴含多个阐释项,既包含意指,又包含意蕴,由此形成语言的模糊美、含蓄美或朦胧美。正如吕俊所说,“文学语言符号具有返回能指性,具有‘透明性’,而更具有多义性、多重阐释性、无限衍生性等特点”[10](54),这即是意义多项性原则。翻译时,译者须通过形象思维,挖掘出语言表象背后各个层面的意义。以下举例说明。
例3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译文1 Withered vines hanging an old braches
Returning crows croaking at dusk
A few houses hidden past a narrow bridge
Down a worn path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comes plodding
The sun dips down in the west
The lovesick traveler is still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丁祖馨and Burton Raffel
译文2 Dry vine,old tree,crows at dusk
Low bridge,stream running cottages
Ancient road west wind,lean nag
The sun westering,
And one with breaking heart at the sky’s edge
Cyril Birch[11](77-79)
寥寥28字,宛若天成。前三句没有一个动词,只有名词排比,指代的是九种不同的物象。它们互相交叠,形成一个新的意象复合体,产生出无限抽象的内涵,意指升格为意蕴——苍凉的暮色中,羁旅人投宿荒落人家,一脉断肠情,一种荒凉的意境萦绕在字里行间。从符号构式上看,原作故意切断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联系,以加强物象的独立性和空间感。译本1动词“hanging”、“croaking”、“hidden”、“comes”的添加强化物象之间的语法联系,但在句式上拖沓、累赘,失去原作的标记性特征。此外“断肠人”译作“lovesick”,将读者局限于为情所困的可能性中,以弱项推出了强项。然而,这里作者是有意模糊该词的意指,留下读者可填补的“空白”:主人翁为谁断肠,为什么断肠等,激发读者的想象。相比之下,译本2以原作符号组合方式单置各个意象,其中的“one with breaking heart”既遵循了意义的多项性原则,又有效地传达原作的意境,总体上稍逊一筹。[12]
本文从翻译的审美实质出发,探讨文学翻译的符号美学问题。[13]通过回顾中国翻译美学的整个历史脉络,指出其理论上的薄弱性。在此基础上,结合皮尔士的符号学指导翻译美学的具体实践,侧重分析翻译符号美学的优势以及相应的翻译原则。总之,符号学与翻译美学的联姻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曾文雄.中国语用学翻译美学思想[J].学术论坛.2006,(3).
[3]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4]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5]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Dinda L.Gorlée.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Pierce[M].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1994.
[7]候国金.语用标记价值论的微观探索[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8]马红军.翻译批评散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9]何兆雄.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10]吕俊.吕俊翻译学选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1]张红.模糊与文学翻译[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4,(7).
[12]胡胜高,谭文芬.西方隐喻研究理论概述[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6).
[13]黄信.译学悖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从民族文化负载词谈起[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