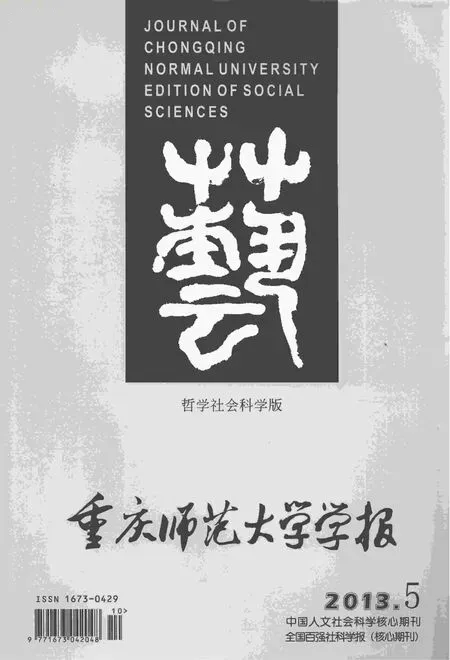论抗战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原罪”意蕴
张育仁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一、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双重身份
由于左翼政治文化思潮以及“五四”民粹主义的持续影响,在抗战文化运动的演进中,宣教者,亦即启蒙者常常又是以“被改造者”,亦即被启蒙者的双重身份出现的。文艺服务于抗战,首先必须服务于大众,因此,文艺必须大众化。而文艺大众化的前提必须是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迫使其重新站在大众的立场、向大众学习,并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这种理念占压倒性优势。几乎同一时期,重庆及大后方文艺界广泛展开的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中,这一“改造自我”使之转变到大众立场,进而通过服务大众,更好地服务战争的“逻辑思路”,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回应,其中诗人的回应更富有激情。田间写道:“人民,每一分钟在前进着,我必须每一分钟跟着人民前进。为着取得我与人民的共鸣——谨防为一朵花而耽误,谨防为一杯酒而耽误,谨防落伍,要不断改造自我。”【1】(36)
也就是说,若不虔诚地“改造自我”,是根本没有资格作民众的宣传员和启蒙者的。1942年,“边区诗人”严辰的表态传到重庆,竟获得重庆和整个大后方文艺界广泛而热烈的喝彩。他在《关于诗歌大众化》的文章中阐述说:“我们必须先被大众所化,融合在大众中间,成为大众的一员,不再称大众为‘他们’,而骄傲地和我们一起称‘我们’,不只懂得大众的生活习惯,熟知大众的语言,更周身浸透大众的情绪、情感、思想。以他们的悲痛为悲痛,以他们的欢乐为欢乐,以他们的呼吸为呼吸,以他们的希望为希望……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不会矛盾,我们的创作才不会有两面性,我们的大众化才不是勉强而是自然的了。”【2】我们因此又不能不注意到,抗战文艺大众化除了战时宣教目的外,更是以文艺家“自我改造”为深层原罪背景而提出来的。从抗战时期诗文艺家的主观愿望来看,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无疑也为日后他们能“自觉”投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埋下了具有悲喜剧意义的伏笔。抗战文艺运动在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与这个强势运动所提出的“大众化”、“通俗化”口号紧密联系着的,是同时又提出了文艺工作者以及所有服务于抗战的知识分子,必须迅速达到自身的“大众化”的要求,就实质而言,这是一场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轰轰烈烈的身心改造运动。电影界知识分子势所必然地被这股强劲的运动浪潮所裹扶。
在这场“被大众所化”的运动中,反明星、反技巧、反蒙太奇等等,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精神强制性的政治文化势头。这种政治文化“惯性”及压力,反映到电影编创者、表演者乃至所有的电影知识分子那里,就形成了电影和电影人“被大众所化”的一种政治文化奇观。与戏剧、诗歌、小说等艺术样式的创作者所遭遇的情景不完全相同——在电影和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语境中,蕴含着很深的原罪意识。
二、从资本的“原罪”到电影的“原罪”
戏剧(除了话剧)、小说和诗歌在民族身份认同方面,几乎没有太多的原罪意识。它们大多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因而,电影以外的文艺知识分子在“被大众所化”,特别是在向民族传统文化“认祖归宗”的过程之中,很少产生认同和被接纳的文化心理障碍,尤其是文化自卑心理。但是,由于电影和电影知识分子思想深处有着浓重的原罪意识,因此这种“认祖归宗”的过程就相当的艰难,其文化自卑意识也就在所难免。由于与民族传统艺术缺乏血缘关系,电影在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谱系中,其地位就显得十分尴尬——它不是民族文化艺术的“亲子”,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外来的“养子”,而且是“来路不正”!只是因为,电影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商品经济“唯利是图”的产物,其原罪之深重可想而知。
在抗战之前,电影界知识分子就已经发表了大量文章,对这种产生于“资本”的电影的“原罪”进行过凌厉的批判和深刻的控诉。最早,我们可以在郁达夫的《如何救度中国的电影》中,见到他对电影“原罪”的批判和调侃。之后,陆续在郑正秋的《如何走上前进之路》、嘉谟的《电影之色素与毒素》、唐纳的《清算软性电影论》,舒湮的《中国电影的本质问题》、尘无的《中国电影之路》,特别是席耐芳的《电影罪言》等等批判文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目睹这种“原罪”批判者的风采。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虽然电影知识分子对中国电影的“大众化”乃至“民族化”转型充满了热情与焦灼,然而,惭愧于电影艺术本身不是民族艺术的“亲子”这样的文化心理障碍,就使得他们在检讨和反思电影“大众化”和电影人的“被大众所化”时,显得负罪感十足,因而对这种来自“资本”和“商业属性”的原罪耿耿于怀,痛苦万分,在批判中充满着深深的自责。这种源于非“文化血亲”的心理自责,在电音的《电影是什么东西》一文中有十分具体生动的控诉描述:“当欧美影片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把欧美的习惯也传到中国来了。在银幕上映现出一男一女,扭抱着亲嘴,甚至做出种种难堪的行为,于是场中的观众,‘吱……’地做怪声大闹。最近我看了一部歌舞片,表演的人,穿了薄到像蝉翼一样的衣服,简直就和没有穿一样,一面唱些下流的歌曲,还把接吻的声音,插在歌词里,跳舞的样子,淫荡极了。当时使我想到疯人院里的情形,看到一些神经病人,脱光了衣服,手舞足蹈的样子,毫无差异。这时,我又看到了环绕的观众,大都兴高采烈,甚至模仿这些下流动作。我真怀疑我是在疯人院里面而不是在电影院里。还有一些欧美片子,描写强盗如何打劫银行,如何绑票,如何杀人……”他因此还特别强调说: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马和浩洒的调查,在110个男犯中,有40℅说电影引起他们带枪的欲望;28℅说电影教他们怎么去愚弄警察;12℅说看了电影,他们便计划去绑票。又年龄在14至18之间,在252个女犯中,百分之25℅说看过描写热情的恋爱影片后,她们引起了性欲而有性交行为;38℅说电影使他们逃学去过放荡的生活;72℅说电影教他们如何打扮使男人注意;30℅说因为电影的缘故和他们的亲生父母有了冲突。【3】
电影知识分子的困惑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电影,为什么热衷于拍摄这样的反文化、反道德,甚至是反审美的影片呢?这种带着“原罪”输入中国的现代艺术形式,为什么又总是乐于被中国的编创者和制片商接受并仿效呢?电音在这篇文章中解释说,这是因为——“有人说,电影的生意,是一宗冒险的买卖。各位试想想,事先花上那么大的一笔款,万一赚不回来,岂不糟糕了吗?可是,我们不必替他担心,平均来说,这一批买卖,很少亏本的,有些竟大赚其钱,一本万利。这又是什么缘故呢?上面说过,电影是大众的情侣,每一个人,只要他耳目不残,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他,只要是好影片,没有不赚钱的。所以,一般聪明的商人,便乐于投资在这桩事业上面来。”
批判者们一致认为,“资本”的原罪,体现在电影从一开始就把它看做是“一桩冒险的买卖”。所以,电影和资本一样,一出生就带着深重的“罪孽”——“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电影最先引入中国,是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资本家视电影为赚钱的工具,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到了抗战期间,绝大多数电影知识分子都忌讳说“电影是商品”,而只能说,电影是“教育民众的工具”或者“电影是战斗的武器”。这种对电影商品属性的有意识的规避,其实就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原罪感”。中国电影界此时甚至还以一种痛不欲生的口吻苦诉道:
我们知道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摇篮中的电影艺术,如果我们不能意识着其内容的政治警觉性,而批判地去接受,势必流为城市小市民层所欣赏的单纯的娱乐品的。电影移植到我们这古老的民族里来,这一危机不仅随带着,甚且无形中构成中国电影界一种传统的症像。抗战虽然使我们的制作方针在大体上进了一步,但严格地讲,我们在抗战初期的电影,无论内容与形式都还是停留在小市民群中。换言之,那时我们的作品,还够不上走向街头、走向农村与战地的条件,因而起初我们实在没有使电影对于抗战中国的大众与士兵,负起了教育和宣传的作用。【4】
这段中国电影知识分子致苏联电影界的说辞,就是深负“原罪感”而痛不欲生的又一富有悲喜剧意味的生动证明。
三、声讨电影“原罪”是一条政治文化主线
中国电影在抗战中为何没有像戏剧、小说和诗歌等艺术品类那样,很好地负担起“教育和宣传的作用”?没有很好地转型为“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战斗利器?在“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战协会”的精英们看来,说白了,就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移植”而来。它既是资本家赚钱的商品,同时又是“小市民层所欣赏的单纯的娱乐品”。所谓的“危机”是与生俱来的,这“危机”其实就是“原罪”。许多电影知识分子之所以坚持认为“中国电影的路线”只能走“国营化”的道路,其实也是为了试图使其摆脱“原罪”;电影“国营化”论者之所以要对“电影商人”作“最深苛的谴责”,也是尖锐地针对这种“原罪”而生发的:“自反侵略战争发动以后,战线的延长使国家对于每个民营事业,不能予以切实的管辖,电影事业也不能例外,尤其中国电影的生长地都是处在半殖民地的租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电影商人在大量制作虽与抗战无关,可却是充满极麻木毒素的电影,香港电影商人照样还在粗制滥造着所谓言情武打电影。一方面由于国家管理上有鞭长莫及之势,再由于敌人恶势力下被威逼利诱;更由于每个电影商人的利益关键所在,我们当然要对他们作最深苛的谴责。”【5】在“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的讨论中,对电影“原罪”的声讨,自始至终作为一条政治文化主线,贯穿在几乎所有的讨论者的意识之中。刘念渠说:“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在基本上是中国电影的内容问题。如果我们不像电影商人那样专从营业上着眼,而认识到电影是一种艺术;把握住艺术的社会任务,来制定摄片计划,使每一部电影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能够反映现实,预示将来,无疑的,中国电影可以走向一条光明的道路。目前,像上海各公司竞相摄制民间故事,只是一种投机取利,有意无意的帮助了敌人做粉饰太平的工作。”然而更严重的是——“抗战电影也还是一页空白。它没有为抗战中的中国留下划时代的记录,这都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6】“电影商人”“专从营业上着眼”,这就是一宗“罪恶”。电影要想摆脱“罪恶”,只有走反映抗战现实、预示和指示未来建国的道路。而上海的电影商人之所以“有意无意的帮助了敌人”,也是源于利用电影“投机取利”的本性。不仅如此。王平陵的声讨,更将“资本家”的谋利本性与封建迷信的旧路划了等号。他说:“关于今后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个人觉得在消极方面必须打倒噱头主义。必须肃清上海电影界开倒车的倾向。例如,仍回到过去神怪、迷信、封建的旧路、为娱乐而提倡电影、死抱着赚钱主义,把电影尽量迎合一般有闲者的嗜好。”【6】其实,这样的声讨,无不是着眼于电影的商业性“原罪”。在这样的语境中,所谓“封建的旧路”,所谓“为娱乐而提倡电影”,所谓“死抱着赚钱主义”,所谓“迎合一般有闲者的嗜好”等等,说的几乎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电影是有“原罪”的。针对电影的这种“原罪”,田汉更愤慨地提出要坚决肃清电影戏剧界的准“农奴制”。在他看来,这种准“农奴制”的形成,就是电影被“资本家”视作商品而必然产生的另一重“罪孽”。为此,他义愤填膺地高喊出“这种可恶的准农奴制必须打倒!中国无数的‘肃蔗普钦’(俄国农奴制时代的名伶)必得解放!”【7】苏怡甚至提出应该掀起一场激进的“电影清洁运动”的倡议,说到底,其实都是针对电影的原罪发出的。他说:“我们试一回忆,中国自有电影史以来,有没有过清洁的时期?没有的。尽管有不少制片公司、制片家、工作者曾经做过不少的有益于社会的清洁巨片,但是不清洁的神怪打杀、诲淫诲盗的片子,却依然未曾绝迹。粤语片兴起以后,尽管也有不少优良的巨片,但到了去年,整个影业所表现的事实,已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过去,现在,为什么不能清洁呢?”【8】
四、“电影清洁运动”与电影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
苏怡本人也是一个坚定的“电影国营”论者。在将资本的罪恶与封建的罪恶做等量齐观的评价和批评方面,他与田汉、王平陵他们一样充满着对电影原罪的文化道德批判激愤。在这篇名为《电影清洁运动之我见》的批评文章中,他义愤填膺地控诉道:“实在说,在今日这种封建残余迄未肃清,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里,真正的艺术,已经得不到本身忠实的评价,何况作为一种商品的中国电影事业,其不能尽如人意,自是当然。所以我们不提清洁运动而已,一提起清洁运动,便需积极的从根本问题着手,然后乃能改良整个电影事业的机构,然后才能谈得到清洁”。
他们认为,为电影赎罪的第一步,就是必须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洁运动”,否则,中国的“电影事业”无法赎回清洁之身,中国“电影事业的机构”,亦无法担当起抗日救国乃至复兴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然而,为电影赎罪若不深刻地延伸到对电影知识分子自身“原罪”的反省这一层面,这“清洁运动”恐怕是开展不起来的,中国电影事业的前途亦是令人担忧的。
电影的原罪与电影界知识分子的“原罪”,从一开始就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如前所述,电影知识分子认为,电影不光是“西洋文化”,特别是“资本文明”的产物,而且也是西方“殖民化”的产物。在半殖民地的租界上,既生长了中国电影,也生长了中国的电影知识分子。由于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亲缘”关系,因此,很长一个时期中,都无法在中国传统文化谱系上找到它的合适位置。电影“民族化”或者“民族本位”的身份焦虑,其实深刻反映出的,不仅是“中国电影”试图在民族文化谱系上急切寻找合适位置的精神焦虑,而且更反映出电影知识分子同样急切地寻找自身合适位置的精神焦虑。在整个抗战文化运动向“民族化”和“大众化”推进的过程中,电影界知识分子与戏剧界、小说界、诗歌界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其奥秘就在于他们的“出身”,或者说“出处”,自来是有问题的。因为,站在“出身论”或者“发生学”的视角来严厉地审查他们,他们“屁股上”与生俱来的“殖民化”或者“半殖民化”的纹章,是如此的醒目。还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上,他们投身于“自我改造”和“被大众所化”的内心苦衷,以及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也就明显的要比戏剧界、小说界和诗歌界知识分子要深重和困难得多。
电影知识分子当然渴望自己“被大众所化”,并且能“融合在大众中间,成为大众的一员”,也当然渴望能骄傲地和大众融合在一起,共称为“我们”。但是,就如同王小波调侃的那样,驴子在草原上见到了马群,自以为找到了“同宗”,而急切地飞奔过去,而马群却发现身边来了个“怪物”,反而急切地逃离,故而形成了“炸群”的文化奇观。电影在农村大众——我们必须承认,抗战文化运动发展到“电影下乡、电影入伍”阶段所说的“大众”和“大众化”,其实主要说的是“农村大众”和“农村大众化”——那里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即“炸群”的奇观。就实际情况而言,所反映出的却是电影知识分子渴望融入“我们”,而普遍遭遇到的困难和尴尬。葛一虹所亲历的一个细节就非常有意思的反映了这一点。他说:“我看过一场抗战电影,其中的一节是描写的英勇作战的游击队。它是以这样的画面开始的:在森林中跳出一个神采奕奕的游击英雄,穿的是马裤和翻领衬衫。一枪打去,一个美丽的脸蛋从一顶大草帽下翻露出来了……这样便展开了全部游击队的故事。那时候,我虽然还未去过战场,也未见过真正打游击的英雄。但是我感到老大的不舒服。我想,看过这个电影的人们,一定会有着我同样的感受。影片所描写的并不是我们在深山密林中艰苦游击着的匹夫匹妇,而是好莱坞制出来的武侠片中的英雄和美人。”【9】的确是具有戏剧性。中国电影的知识分子本意是好的,但滑稽的是,这种以好莱坞西部片的殖民化叙事模式塑造出来的“游击英雄”,在农村大众那里,怎么能产生“同宗同族”的接受心理?美国西部片中的武侠人物,怎么可能与农村大众所认识和理解的本土抗日英雄划上等号?由于“自我改造”不得要领,因而“被大众所化”的渴望就必然成为这样的笑料。这种悲喜剧情景,不光使广大的农民大众不得要领,甚至连电影知识分子,即我们习称的“电影艺术宣传家”自己也感到无地自容。刘念渠的另一段描述,毋宁说是在自我解嘲,或者说是自我挖苦。他如是写道:“最容易的事情是找一个现成的故事,分幕、分镜头、开拍。但老是《三笑》或者《玉蜻蜓》之类,那就比较麻烦。不妨编一个新故事,有男有女,有恋爱有抗争,有歌唱有战争,然后分幕、分镜头、开拍。连这个还不行,要创作典型,那真就使人感到困难了。这一件工作,从剧作者起,导演以及演员(明星们哪)都要知道得更多一点:摄影场上的艺术知识和电影艺术修养以外,还必须加上对现实的正确认识、理解与把握。”【10】
五、中国电影的“原罪”与美国电影的“罪孽”
对苏联影片的极致赞赏,特别是对能生产这种“人类杰作”的苏维埃国家体制的极致赞赏,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是左翼力量“设置议题”、“生产意见”的重要“功课”。与此形成鲜明反照的,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商业电影”的批判。这也一直是左翼力量“议程设置”中乐此不疲的论题。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电影知识分子从苏联电影和苏维埃国家体制中,获得了创造“抗战电影”和未来自由民主“新中国”的巨大启示和灵感。这多少意味着,曾经出尽风头的美国电影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精神境域中的败落。
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在讨论电影的“民族形式”,讨论“大众化”和“通俗化”问题,在反明星、反技巧,以及怎样才能体现电影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甚至在探索怎样才能使抗战电影真正沿着正确的工具理性道路前行等等问题时,无不将苏联电影作为正面典型,进行极致的称颂和膜拜,而同时将美国电影作为反面典型,进行尖锐的鞭挞和批判。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泾渭立判的价值取向,虽然在战前已经形成了某种政治文化态势,特别是在左翼电影运动中,这种价值判断早已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但就其发展势头而言,在抗战期间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电影知识分子在检讨中国电影和他们自身“原罪”时,对美国电影长期以来“麻醉”和“奴化”中国电影和电影知识分子“罪孽”,在进行控诉和批判时,更是不遗余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潘孑农的《释“美国作风”》和《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致苏联电影界书》等大量的文献资料中,已经有了充分的领略。尽管美国和苏联一样,被我们视为“帮助中国抗战的民主国家”,特别是因其与中国的“战略同盟”关系,而受到中国朝野的认可与尊重,但具体到美国电影和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态度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这与他们对苏联电影和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极至称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难道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不也同样代表“人类正义”和“文明科学”的方向吗?可是,具体到美国电影及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却并不这样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电影知识分子在寻求“中国电影的出路”时,就是以毫不犹豫地批判“美国作风”和坚定不移的选择“苏联道路”为立论的前提的。实事上,这种态势正深刻地反映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寻求民族国家现代转型道路时,在思想文化意识上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出于政治家或军事家那样的策略性考虑,而根本原因却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辨”,特别是对“仁爱”和“大同”理想的执着追寻,终于在体制化的苏联和苏联电影中找到了“文化同构”的重要启示和“准确答案”。
“在社会主义国家,电影艺术是件庄严的工作”,而在美国则“把电影作为纯粹的娱乐品”;【5】“电影在苏联是更迭人类的世界观的武器和文化革命的兵种。”【11】可是在美国,电影则“被利用为宣传工具,是利用来麻痹大众的意识的”【12】。这种深刻浸入中国电影知识分子灵魂的文化意识和价值定论,并非出于简单的民族主义好恶,以及政治审美偏至,而是来自中国文化人在为整个国家民族寻求现代化出路时,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判识和文化确认。
爱森斯坦说,苏联电影的艺术功用在于鼓舞苏联人民和整个人类“去建设新社会”,苏联电影所“提供的电影的真实”,正是“苏维埃国家”“现实的真实”反映。相反,美国电影的政治目的却是在“麻痹人民”,逃避对“现实”的“干预”,特别是在抗拒革命、瓦解人民“建设新社会”的意志上面。苏联电影所体现的“电影辩证法”和“新的美学原则”,极大地有助于人民去积极参与电影的政治审美过程,而美国电影却顽固地排拒革命,宣扬“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爱森斯坦所说的那种“电影辩证法”和“新的美学原则”在这种腐朽和堕落的境地中是无法生长起来的。【13】(542)这样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电影知识分子来说,可谓影响深远。
[1]田间.抗战诗抄[Z].新文艺出版社,1955.
[2]严辰.关于诗歌大众化[N].解放日报,1942-02-11.
[3]电音.电影是什么东西[N].新蜀报,1944-02-03.
[4]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战协会致苏联电影界书[J].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
[5]唐煌.电影国营论[N].国民公报,1939-02-12.
[6]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记录[J].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
[7]田汉.怎样从苏联戏剧电影取得改造我们艺术文化的借鉴[J].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
[8]苏怡.电影清洁运动之我见[N].国民公报,1940-05-19.
[9]葛一虹.关于民族形式[N].文学月报,第2期第1卷,1940.
[10]刘念渠.在银幕上创造典型[J].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
[11]罗亭.苏联电影观览席[N].国民公报,1938-03-20.
[12]宋之的.略论电影通俗化问题[N].扫荡报,1939-04-10.
[13]西顿.爱森斯坦评传[Z].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