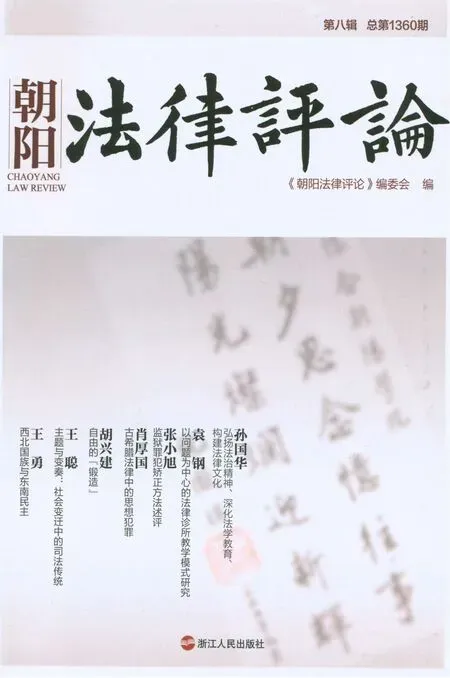简易程序出庭机制中诉讼与监督职能的优化配置
——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杨圣坤
简易程序出庭机制中诉讼与监督职能的优化配置
——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杨圣坤*
从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置初衷来看,效率在简易程序中具有价值优先性。刑诉法修改前,在刑事简易程序中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配置情况产生了效率折损。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简易程序出庭机制,该机制中两大职能应当在效率原则的指导下实现优化配置,以弥补此前出现的效率折损。
刑事简易程序 效率 诉讼职能 诉讼监督职能 法律经济学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2012年3月14日通过了最新刑诉法修正案,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最新刑诉法修正案在简易程序上的修改是一大亮点,修改后的简易程序在关注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同时,对检察资源的科学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最新刑诉法修正案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简易程序出庭机制的实行,要求检察机关重新优化配置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这关系到简易程序出庭检察人员的角色定位、人员选择与职责履行等问题。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优先价值及其衡量标准
任何法律,只要涉及资源使用——而事实恰恰如此——都无不打上经济合理性的烙印,即使它与市场行为无关或只与不完全相似于市场行为的行为有关。法律的实施无疑涉及对可供选择的匮乏资源的合理使用。同样,不同法律程序的设计,也就相当于正在对资源使用的各种可能进行明确或不明确的比较与选择。无疑,法律程序的设计必须依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这一原则进行。①[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置就是对这一原则的一种实践。二战以后,基于诉讼负担加重而司法资源有限的状况,各国根据刑事案件存在轻重、繁简的差别而采取了一种程序分流的举措,将诉讼程序分为普通和特殊两大类。对那些按特殊程序处理的案件,则注重在确保最低限度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刑事简易程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置初衷决定了效率应是首要价值目标。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置目的就是通过简化普通程序和规则,缩短诉讼周期,减少诉讼资源的投入,从而使审判迅速进行,最终提高刑事审判程序的整体效率。所以,刑事简易程序在本质上讲就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这就决定了在刑事简易程序中效率的价值优先性。①周丽娜、王琳:《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效益与公正机制》,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对于效率的衡量标准,法律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智力支持。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最大特点就是确立和突出对法律的效率分析,即以效率为标准来研究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问题。在以效率作为价值目标的法律经济学那里,通常用到的效率概念是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这主要指的是,如果不存在另外一种可选择的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的处境变差而至少有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那么这种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状态。②[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施少华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这就意味着,当满足给定的约束条件时,一种资源配置的状态已经使没有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偏好在不损害别人的条件下变得更好,那么就是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如果一种变化能够使没有任何人处境变得更坏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处境变得更好,这个变化就被称为帕累托改进。一般来说,如果一种状态不是处在帕累托最优状态,就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通常证明一种资源配置改变是帕累托改善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求受这一交易影响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一交易,也就是同意原则。③柯华庆:《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博弈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这种效率概念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由于对帕累托效率标准的不满,经济学家发展了新的效率概念:卡尔多—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受益者所得到的收益足以补偿受损者的损失而且有所剩余,尽管并没有要求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实际的补偿。如果受益者对于受损者进行了事后补偿,那么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就成为一个现实的帕累托改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只是潜在的帕累托改善。由此可见,与帕累托标准相比,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条件更宽。因为按照前者,只要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受损,那么某种变革便无法进行;而按照后者,只要能使总收益最大,某种变革就可以进行,剩下的就是如何确定补偿方案的问题。因而从理论的角度看,采取卡尔多—希克斯有效性标准是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法律经济学在研究中所运用的效率标准主要指的是卡尔多—希克斯意义上的。这主要是因为,帕累托最优往往只能适用于市场中的自愿交易场合,而在许多社会活动中,法律规定的权利是无法在市场上交易的,或者是无法通过市场自愿交易来转换的。①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页。
对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灵活运用的一个著名案例是1947年美利坚合众国诉卡洛尔拖轮公司一案,在该案中,美国著名法官利尔德·汉德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②这个案件是关于纽约港停泊的一艘驳船因为拴系不牢撞毁另一船只的情形。案件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船主有无过失。在该案的判决中,汉德法官形成了他的著名法则:既然每只船都有可能冲出泊留位置,并且如果冲出来,便构成了对其周围船只的一个威胁,那么船主的责任在于防止产生伤害,它是三个变量的函数:(1)船只冲出泊留位置的概率(probability,简称P);(2)如果冲出来,其产生损害的实际损失(loss,简称L);(3)充分预防的负担(burden,简称B)。如果B<PL,则驳船船主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法院可以以此断定船主的行为存在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汉德公式提出后便成为美国法院在侵权案件中经常使用的判定有无过错的标准。在一系列的案例中,法官会问及进一步的预防是否是成本优化的。如果采取足够预防措施将给当事人带来的负担(B)大于发生损害的概率(P)与损害的实际损失(L)的乘积(即损害的预期损失),当事人便不必采取预防措施,因为法律要求当事人进一步预防便不是成本优化的,是不合理的和无效率的。反之,如果B≤PL,而当事人却未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则法院可以判定当事人因没有采取成本优化的预防措施而负有责任,该当事人被认定存在过失。参见[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施少华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268页。汉德公式最富有启发意味的地方在于它自身隐含的一种立场,即实现社会总成本(事故的预期损失与为预防该损失发生而支出的费用之和)最小化的立场。这也是笔者在本文要从汉德公式中吸取的一种观念,即把事后的矫正正义的实现转变成考察事前的分配正义,或者说分配效率。这和刑事简易程序隐含的立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虽然说刑事简易程序追求效率的价值优先性,但是刑事简易程序本身并不能直接和“效率”画等号,③刑事审判效率不等于庭审效率。反言之,单一的庭审高效率,并非刑事审判效率提高的真实反映。如果只是为了追求庭审时间的缩短,而在庭审中产生了一些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或出现了一些错误判决的结果,则不但不能真正实现投入与产出之间相比较的效率优势,还可能浪费更多的诉讼资源,产生更多的社会成本。因为在刑事简易程序中我们一味地追求程序的简捷就可能会导致一些违法行为和错案结果的出现,如果把刑事简易程序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和错案结果看成是一种“事故”,那么这些“事故”的发生以及事后纠正这些“事故”就会产生新的社会成本,所以,我们就应当在这种“事故”实际发生之前,投入恰当的预防资源,将简易程序设计得既便捷简易,又会对可能造成“事故”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遏制,以避免额外成本的产生。当预防“事故”发生的成本(B)小于或等于“事故”发生的概率(P)与“事故”的实际损失(L)的乘积时,即B≤PL①P与L的乘积也就是“事故”造成损失的预期成本,也可以视为由于避免“事故”发生而得到的收益。时,刑事简易程序的设计便是有效率的。这一结论是站在实现社会总成本(“事故”的预期损失与为预防该损失发生而支出的费用之和)最小化的立场上得出的。
二、刑诉法修改前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配置情况及效率折损
在检察机关的诸项职能中,公诉、侦查、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以及对部分司法行政机关活动的监督等各项职能所针对的对象和行为都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检察机关在参与简易程序的过程中主要有两项职能,即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凡是法律明确规定由检察机关自己行使的诉讼权力都是诉讼职能的体现,其本质上更像是诉讼一方当事人,权力属性上具有主动性和自发性的特点。在刑事简易程序中,诉讼职能应当是通过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来实现的。凡是法律规定并非由检察机关自我行使而是针对其他与诉讼有关的国家机关行使的权力,属于诉讼监督职能的范围,具体包括: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和对判决执行情况的监督。这些职能的共同之处在于其行为指向上均针对的是诉讼中的其他国家机关,且以监督这些机关行为的合法性为目的。②徐啸宇:《论检察机关配置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的原则》,载《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在刑事简易程序中,诉讼监督职能应当主要是通过对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来实现的。
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尽管这里规定的不是“应当”不出庭,而是“可以”不出庭,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检察机关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很少会派员出席法庭。在公诉人不出庭的情况下,由于控诉主体的缺失,诉讼职能的履行便主要借助于法官得以实现。缺少公诉人出庭的庭审,由法官代替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由法官来出示和宣读证据,被告人和其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无法就案件事实和证据与公诉方展开辩论,其各项辩护活动也由于控方的缺失而失去了针对性,法庭审理的直观效果和说服力大打折扣。尤其是如果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有新的辩解或出现其他新证据提供法庭,法官将无法组织有效的举证、质证和辩论。①祖鹏:《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9页。这样,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庭审似乎变得简便,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有的时候庭审时间并没有被缩短。在检察人员不到庭的情况下,控辩双方可能会难以找准案件争议的焦点和需要调查的中心问题,而且遇到需要询问检察人员案情的时候还需中止审理,以便就有关问题通知检察人员予以答辩,使庭审活动浪费了时间。而如果检察人员到庭,控辩双方就可以尽快在法官面前摆出争议的问题,遇到对方的反驳也可以及时答辩,案件的调查和辩论更加具有针对性,使案件的诉讼效率得以提高。②高一飞:《刑事简易程序审判中检察制度的完善》,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7期。另一方面,错案的风险增加。如果检察人员不出庭,那么应当由其行使的诉讼职能便主要由法官代行,原有的指控和举证的职能难以实现,也无法开展相互质证和辩论程序,法官既是案件的控诉者又是案件的仲裁者,集控审于一身的法官,更多的是从先行移送的案卷,而不是通过控辩对抗的庭审,来寻找判决书拟确定的事实,由此增加错案的风险。
在检察人员不出庭的情况下,诉讼监督职能的实现受到很大限制。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1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发现法庭审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人民检察院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由此可见,检察人员不出庭,很难监督庭审中是否有侵犯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很难监督庭审中是否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也很难发挥量刑建议在限制法官可能存在的恣意和过度的裁量权方面的作用。量刑建议主要是通过控辩双方充分阐明本方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同时反驳辩论对方的量刑观点,使得诉讼各方都可以获得积极影响法院判决量刑结果的机会,其实质是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在法官面前关于对量刑的相互论辩和理性说服的对话。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可以压缩法官利用量刑权力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促进量刑由现行的行政审批模式到诉权制约模式的转变,增强法院量刑的透明度。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不出庭,因此,一般是在提起公诉时,以书面的形式提出量刑建议,与起诉书和卷宗材料一并移送法院。不但使得公诉人当庭提出口头量刑建议失去了机会,对法官量刑决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由于法官不可能,也没有义务主动提出控方的书面量刑建议内容,使得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机会与公诉方就量刑情节及依据展开辩论,量刑辩护意见也随之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和空间,进而也失去了对于法官量刑决策积极参与和施加影响的机会。①王军:《简易程序中,对公诉人“可以不出庭”的追问》,载《检察日报》2009年7月17日。可见,公诉人出席法庭是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主要途径,公诉人不出庭不利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在公诉人不出庭、法官单独面对被告人的诉讼格局下,检察机关对法官的审判实行法律监督出现了“缺位”。而这种“缺位”往往是通过当事人申诉以及检察机关事后的抗诉来弥补的。监督缺位直接导致的后果,不仅是庭审中违反法律规定以及错误判决等情形的出现概率可能会攀升,而且事后的申诉和抗诉导致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刑诉法修改前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配置情况可能会造成效率折损。如果把刑事诉讼程序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和错案结果看成是一种“事故”,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庭对B(预防“事故”发生的成本)、P(“事故”发生的概率)、L(“事故”的实际损失)三个变量的影响来对刑诉法修改前两大职能的配置情况是否会造成效率折损进行定性分析。对于变量B来说,在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B的数值应当减小,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有的时候,由于检察人员的不到庭,法官和当事人可能会难以找准案件争议的焦点和需要调查的中心问题,而且遇到需要询问检察人员案情的时候还需中止审理,以便就有关问题通知检察人员予以答辩,这使庭审活动浪费了不必要的诉讼资源和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B的数值减小的幅度不会太大,甚至B的数值可能会增大。对于变量P和L来讲,在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由于诉讼职能由法官代为行使导致的错案风险增加,再加上检察监督的不及时甚至“缺位”,简易程序中出现“事故”的情况便会增多,P的数值可能会出现增大,L的数值可能会出现攀升。在这种情况下,B>PL的情况便可能会出现。这就意味着,在刑事简易程序中,公诉人不出席法庭,刑事审判的整体效率可能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
三、简易程序出庭机制中两大职能的优化配置
修订前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在简易程序中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了刑事审判整体效率的折损,偏离了效率价值的要求,违背了简易程序设计的宗旨。为此,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在这种情况下,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应当如何配置才能实现效率上的优化呢?法律经济学理论为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法律经济学的逻辑基础是“理性选择假设”。在吸收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的基础上,法律经济学对理性选择假设在最广阔意义上的解释是“手段—目的”理性。这种理解认为,理性选择的行为应该是“达成目的的适当方式”(suiting means to ends),①Richard Posner,“Rational Choice,Behavioral Economics,and the Law”,50Stanford Law Review1551,1575(1998).而对于在此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目的”指的是什么,这不是这种主张所关心的。波斯纳在《法理学问题》中就将“理性”界定为“手段—目的”理性。正如上文所述,在刑事简易程序中,效率具有价值优先性,因而我们这里的“目的”指的是效率,“手段”则是指能够以最低成本实现最优效果的途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从职能履行的成本出发来决定谁是某项职能的承担者。这一思路将指引着我们对两大职能承担主体履行职能的成本优势进行考察。
在刑事简易程序中,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的,其诉讼职能应当由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履行。这是因为,公诉部门的职责就是提起公诉,并因此积累了许多出庭经验、公诉技巧、信息优势和技术优势,由其承担诉讼职能既可以减少简易程序出庭诉讼的风险,也可以减少这种风险产生的诉讼成本,进而增加社会总产出,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笔者认为,公诉部门出席简易程序的法庭,其所担负的职责,与适用普通程序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公诉部门对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可以提出建议或认可,可以当庭宣读起诉书,可以出示、宣读主要证据。经审判人员许可,公诉人可以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互相辩论。
对于诉讼监督职能的履行主体,却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由一般公诉人承担诉讼监督职能具有很多积极意义。其一,有利于落实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使追诉更加客观公正。检察官担负法律监督职能,需要秉持中立和超然的立场。检察官秉持这种立场,有利于其在行使追诉职能时超然于控方立场,促进客观公正义务的落实,从而使追诉更加公正。其二,有利于公诉人防止和克服片面的控诉倾向,从而更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公诉人同时身负法律监督职能,有利于其超越控方立场,防止和克服片面的控诉倾向,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正确履行公诉职责,全面关注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各种情况,既依法指控犯罪,又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做到有犯罪就追诉,有违法就纠正,有合法就保护,从而有利于控辩平等原则的实现。其三,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增强法律监督效果。①朱孝清:《检察机关集追诉与监督于一身的利弊选择》,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3期。另有人认为,诉讼与监督是内在规律与职能取向存在明显不同的两类权力,两者的内容互不包容,应当有机地分离诉讼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否则,其结果就可能是诉讼职能被监督职能异化,或者相反,监督职能为诉讼职能所异化。所以,应当由承担诉讼监督职责的专门人员来出庭履行诉讼监督职能。②陈卫东:《检察机关角色矛盾的解决之策——法律监督职能与诉讼职能的分离》,载《法制日报》2011年2月23日。
笔者认为,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确是两种不同的职能,但这并不应当成为两者截然分立的充分条件。相反,公诉部门在履行诉讼监督职能方面更具有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由公诉部门承担诉讼监督职能更符合“目的—手段”理性。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承担着诉讼职能的公诉部门更了解案情,更容易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等实体问题进行监督。公诉部门在进入庭审程序之前,就已经开始对案情进行了解、认识、熟悉甚至研究,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已经形成了初步意见。在进入庭审程序之后,公诉部门会通过质证、辩论等环节,充分阐明本方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同时反驳辩论对方的定罪和量刑的依据,这样可以压缩法官利用定罪量刑的权力进行寻租的空间,防止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出现错误,从而促进诉讼监督工作的开展。如果让所谓的专门的监督部门出庭履行诉讼监督职能,那么该监督部门就应当不仅全程参与庭审前对案件的了解、认识、熟悉甚至研究的过程,以更好地把握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选择等这些重要监督点,而且还要全程参与庭审过程以实现对诉讼行为的实时监督,这样就难免重复了许多公诉部门已经做过的工作,造成了诉讼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更重要的是,基于对诉讼业务的熟悉,我们有理由相信公诉部门能够比这种专门的监督部门更能履行好诉讼监督职能。第二,承担着诉讼职能的公诉部门,更熟悉诉讼程序,更容易对诉讼的程序问题进行监督。公诉部门的职责之一就是出庭控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出庭经验的积累使得公诉部门对诉讼程序非常熟悉,为公诉部门监督并纠正程序违法问题提供了技术保障。如果让所谓的专门的监督部门出庭履行诉讼监督职能,那么该监督部门应当充分熟悉诉讼程序,对于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能够及时识别并能采取正确措施来纠正,若要做到这些,需要付出高昂的学习成本、积累丰富的出庭经验才行。对于已经充分掌握诉讼程序相关知识和积累了丰富出庭经验的公诉部门来说,让其承担起诉讼监督的职能,能够发挥其现有的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节约司法资源,增强监督效果。
公诉部门在出席法庭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时候,如果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不应当不分具体情况地全部“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因为有些程序性问题对实体的处理有重要影响,如果在庭审后提出,可能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甚至会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公诉部门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法院审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非常严重,与案件的证据审查、事实认定密切相关,并且若不当庭及时指出就有可能影响公正裁判的(比如,出现了案件错判或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等情况),那么公诉部门应依照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关于在出示物证、当庭宣读有关证言笔录、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文书时,“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和第一百九十三条关于“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规定,及时向法庭善意地提出意见。如果法院审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不那么重要,与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审查等关系不密切,不当庭指出也不会造成案件错判或对当事人诉讼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由于不会影响公正裁判,所以公诉部门应在庭审后报经检察长同意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①朱孝清:《检察机关集追诉与监督于一身的利弊选择》,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3期。
四、结 语
从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置初衷来看,效率在简易程序中具有价值优先性。刑诉法修改前,在刑事简易程序中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配置情况产生了效率折损。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简易程序出庭机制,在该机制中两大职能应当在效率原则的指导下实现优化配置,以弥补此前出现的效率折损。这样的配置方案能够提高刑事审判的整体效率,节约社会总成本,进而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然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却往往引起许多人对公正的质疑,他们往往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才是首要价值,在效率原则指导下设计制度方案可能会使得公正价值大打折扣。这种质疑是不必要的。实际上,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的“公正”这一类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它依赖于人的主观心理发生作用。同时它也是受特定物质条件制约的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倘若从长远的或者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视角来看,公正与效率则是完全统一的,两者并无冲突可言。一种利益分配方案如果能够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那么在经济学家看来就是有效率的,而在法学家看来它就是合乎公正的。站在法律决策者的高度上看,公正与效率只是为同一种东西创造的不同词汇而已。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具有优秀的制度品质,它确立了实质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制度,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美国社会的福利水平。然而,就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马伯里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法律救济,然而很少人为此抱怨这一制度的不公正。这是因为,人们通常会认为,为了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是一种有益的损害。因此,我们评价一种制度或者公共项目是否符合公正/效率的,应该站在社会总体以及历史的高度来权衡利害。因此,尽管人们一直在讨论公正和效率之间的冲突,但却从未有人发现过一种制度性措施,当它违背公正的时候还能真正是有效率的。公正与效率的矛盾只是人们依靠有限的理性和丰富的情感以及根深蒂固的伦理观所做出的直觉性认识。但是传统法学家总是依据直觉把二者对立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比法律经济学家对公正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初审编辑 陈国飞)
Optimization of Allocation of Litigation and Supervisory Functions in Appearance Mechanism of Summary Proceeding: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
Yang Shengk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itial purpose of criminal summary proceeding,efficiency is a priority value.Before amendment of criminal summary procedures,efficiency is already decreased in the allocation of litigation and supervisory functions.The appearance mechanism in summary proceedings is prescribed in the amendment.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two major functions should be opti-miz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fficiency doctrine,in order to compensate for prior efficiency loss.
Criminal Summary Proceeding Efficiency Litigation Function Supervisory function Law and Economics
*杨圣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干部,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