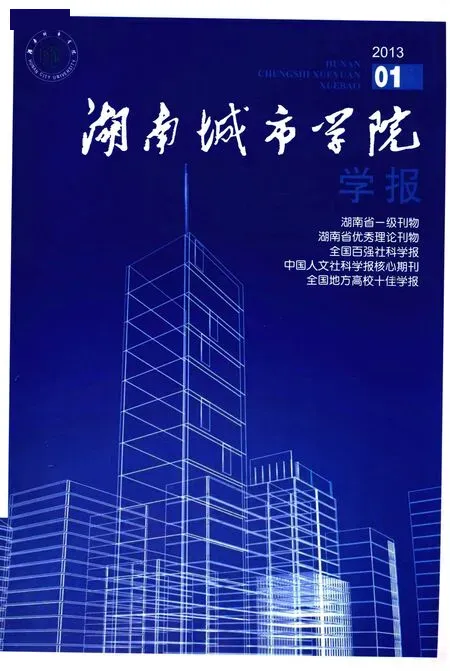不安于成,百尺竿头再进——评赵炎秋教授《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
周子玉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长沙 410004)
当今时代,“后殖民”一词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专业术语。随着“文化殖民”概念的普及,建构本土文化的迫切要求被反复提出,部分学者将“反文化殖民”与全面排斥西方文化划上了等号,将建构本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精华放在完全的对立面,由此,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开始变得地位尴尬。但不少清醒的学者脚踏实地地探索对西方文化的合理研究和利用方式,用自己的实际研究成果对这种观点做出了有力的反驳。赵炎秋教授的《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之一。
从形式上看,《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是一本论文集,作者在书中精心选择了自己研究生涯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西方文论、文学与文化研究论文共27篇。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西方文论研究。在这一部分,作者从作品的角度切入西方文论的研究,对西方形象论文论与语言论文论的产生发展、特点与局限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是西方文学研究,研究范围宽广,涉及莎士比亚研究、涉性文学的研究以及西方20世纪文学宏观研究等。第三部分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在这一部分,作者思索了在建构民族文化的大环境中,外国文学研究的困惑和出路,从宏观上探讨了中西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这其中的意义。
通览这本论文集,可以发现作者的研究姿态和探索方法是一以贯之的:深刻的理性洞察、广阔的文化视野和鲜活的发展眼光是这本论文集最突出的特点。
深刻的理性洞察并不仅仅意味着作者在研究时表现出的严密逻辑性,而是在整体观念架构中对文化立场的冷静审视和理性对待。在《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一文中,作者思考着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清楚地指出:“我们既要看到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殖民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同的文化之间正常交流的一面,看到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学习、吸收强势文化于己有用的东西的必要性。看不到前一方面,甚至把对强势文化的盲目崇拜、不加分析的照搬也说成是正常交流,是不对的;看不到第二个方面,把对强势文化的任何接受都说成是“被殖民”,同样也是不对的。”这种对双方文化理性审视的观点贯穿了作者整个研究生涯,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了这本集大成的著作中。
因此,在整本论文集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西方文论、文学特点的总结,对其影响的剖析研究,又能够看到对西方文论和文化缺陷的探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者在西方文论研究中选择的切入点:形象。做出这一方向性选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作者对西方语言论文论和传统形象论文论的特点和局限都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传统了如指掌。这一研究清楚地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我们形成‘我们的’话语体系和方法论,同时把它们推向世界,同时,我们也要大量地吸收‘他们的’话语体系与方法论,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于我们有用的东西,这样,才能繁荣与发展‘我们的’话语体系和方法论,繁荣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因此,论文集中对于整个中西文论、文化的研究,就建立在有意识地对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去芜存精、有机整合的基础上,也建立在作者客观理性、不卑不亢、不偏不倚的研究态度上。
广阔的文化视野是作者研究姿态的第二个特点。尽管这本著作取名为《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但实际上,无论是文论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包括西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作者都是将之放在大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从20世纪末开始,文化批评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界中成果最丰硕、争论最激烈的领域,文化的重要性成为理论界的共识。作为西方文论研究的先行者,作者显然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信息,广阔的文化视野成为他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
文化视野对赵炎秋教授来说,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一种世界观。因此,对文化的关注不仅体现在他针对中西文化所做的比较研究上,而且体现在他研究的各个方面:即一方面用文化批评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另一方面借助文本来研究文化。作者在开始研究之路时,便认识到:“由于文学与文化、社会是紧密相联的,不联系文化与社会,很多文学问题说不清楚。”这样,无论是作者的微观文学研究(如狄更斯相关研究),还是宏观文论研究(如对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的研究),都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分析,有自觉的文化批评精神。可以这样说,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互证是这本论文集的研究特点,也是作者研究眼光的独到之处。
鲜活的发展眼光是文集的第三个特点。只有用不断发展的眼光来做研究,把鲜活的思维触角伸向研究领域的最前沿,才能不断扩大思维空间,打破思维定势。鲜活的发展眼光首先是内容上的。从作者涉及的诸多研究领域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固步自封,安于所成,而是不断探索,以已经成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并将这些不同的领域的研究有机联系起来,构建出一个独特的西方文学与文论话语系统。
鲜活的发展眼光也是研究方法上的。作者并不拘泥于某一种研究范式,某一个研究角度,而是打通中西,各种理论工具都能信手拈来,与时俱进,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在《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一文中,作者对这样一种研究境界表示了心向往之:即“打通古今中外人文学科”,“站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思维规律”。并明确提出,方法和话语只是一种工具, 因此没有国别民族之分。因此,作者对研究方法、方向的选取跨度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既有前沿的文化批评、后殖民研究,也有传统形象学研究等。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实现了他所向往的不拘一格、纵横古今中外的境界。
总的来说,《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并不是简单的论文收集,而是赵炎秋教授建构起来的一个完整有机的话语系统,这一系统包含着他在几十年研究生涯中对西方文学、文化的独到理解和深刻洞察,为中国的西方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当今外国文学研究的出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作者在第一版的后记中提到:“我不是屈原,自然无所谓‘修名’,但屈原似的责任感还是有的,这种责任感也不‘雄伟’,不过是希望这本书不是完全的文字垃圾而已。这种希望也许不至于是奢望。因为这本小书既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一个段落,它也许就能像黑夜里的一个火把,虽然昏暗,却也能给感兴趣的人一点帮助。”这虽是作者自谦之词,但这样一部学术成果的出版,对于现在及未来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确实有照亮迷雾的作用,对于西方文论与文学的学科建设更是有着积极的意义。
[1]赵炎秋.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M].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