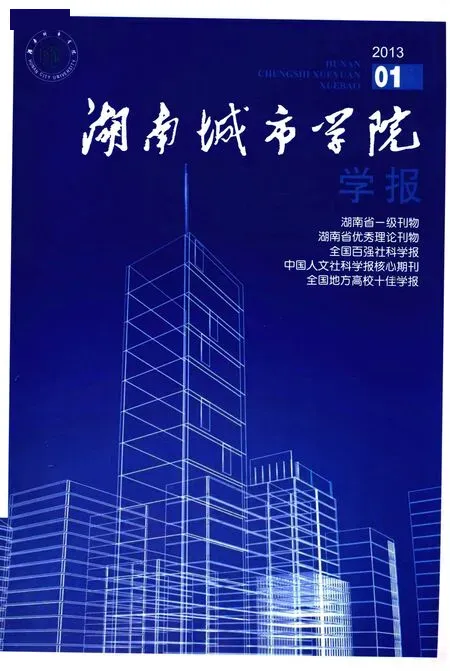文人相轻:文学评论与评论文学
龚祖培
(成都师范学院 中文系,成都 610017)
文人相轻之有害毋庸赘言。自曹丕《典论·论文》论定其无益于人之后,更有学者比之为“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霆”,视之为洪水猛兽般可拍,告诫子孙“深宜防虑”。[1]222自古及今,它都在“不道德”的囚笼之中,不过这是旧有的以儒家道德标准为主流认识的判词。如果抛开“道德论”,那么文人相轻还会不会有“有益”的东西?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对它进行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其实,即使“道德论”也贫弱而苍白,其方法论缺位,判断缺乏两面关照。或许文人相轻并非全都“不道德”。它与文学那样多的牵扯和影响,没有人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而今只有功利驱使的现实分析浅层面话语,真正研究学术的人似乎都忘记了这一块荒芜得实在可怜的处女地。本文为筚路蓝缕之举,但愿能以粗疏和错误引出方家通人之宏论。
这里不做方方面面论述,只集中讨论与文学关联的问题:文人相轻对文学评论的促进和深化;文人相轻因其不同的评论形式所产生的文本的文学价值等。
一
文人相轻的对象都是文人,而十之八九是对文学现象的价值判断。简言之,是以文学为对象所作的评论。这些评论有的直露,有的含蓄,有的盛气,有的婉转,风格各异。以语言为中介,有口头的;有书面的;还有不立文字,仅用肢体语言的。一般说来,因文人相轻产生的文学评论,往往带着感情倾向,因而对“公允”多有排斥。其形式和类型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先举几个与文学评论密切相关的例子说明。
钱谦益认为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复古论调是“婴儿学语”,使“二百年以来,正始沦亡,榛芜塞路,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2]311-312这是对文学流变不满的评论。《随园诗话》卷5针对不同的诗歌流派尽情讥讽:“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谓之木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好叠韵、次韵,刺刺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者,谓之骨董开店。”[3]112各派均遭贬斥。有研究者指出,袁枚这里讥讽的对象是有确定的诗歌理论的主张者:“‘贫贱骄人’是指学王、孟的神韵派王士禛;‘权门托足’、‘木偶演戏’是指仿李、杜的格调派沈德潜;‘走宋人冷径’是指学宋的浙派厉鹗等;‘古董开店’是指以考据为诗的肌理派翁方纲。”[4]422敖陶孙评秦观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5]19元好问《论诗绝句》奚落秦观:“‘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6]124这是审美趣味不同的评论。庾信瞧不起北朝文人,采用横扫式的贬低,即使给温子升留一点面子,有所谓“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的话,但将薛道衡、卢思道等文人贬为“稍解把笔”、“驴鸣犬吠”[7]120。这是文化对峙下的评论。叶燮以作品数量多少论优劣:“诗文集务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传之作,正在不多……宋人富于诗者,莫过于杨万里、周必达,此两人作几无一首一句可采。”[8]606《太平广记》卷265引《宾谭录》说:“杜审言初举进士,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妒。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参选试,判后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当羞死矣。’又向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9]2073明代文人桑悦“敢为大言,不自量,时铨次古人,以孟轲自况,原、迁而下,弗论也。而更菲薄韩愈氏曰:‘此小儿号嘠。’”[10]1041这是性情狂傲的评论。
其实,从钱谦益以下的评论主体都是“自我评价过高的人”,“过度自我赞赏”之文人。[11]330相轻之所以发生,最突出的心理驱力就是嫉妒和骄傲。在这种心理基础的影响之下,如果只讨论其话语论断是否“公正”和“科学”,那是弄错了对象,因此没有意义。如果要全面地研究文人相轻对文学评论是否有益,那就不能以“公正”和“科学”为唯一标准审视,而应该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关注其话语文本,探讨为什么这些话语论断能达到“片面的深刻”的“精彩”;为什么它们能够因文人相轻而成为经典的评论文本,对文学影响甚巨;为什么成为文人的集体记忆,即荣格所说之“原型”。还应该科学地发掘其中的确对文学评论的语言建构有益的“内存”,促进文学评论的艺术表达,深化文学评论的研究。即使那些不道德的评论是负面的,也可能存在艺术的、审美的因素,可以扬弃而用。满足审美体验的需求,研究其艺术价值,借鉴其艺术技巧。所谓审美需求,对今天的受众关系甚大。道德与否的标准虽可超越时空,但也可因时空的距离阻隔而淡化,对没有切肤之感和功利关联的现代以及将来的人来说,上述那些古典的评论是否道德,那是疏离而淡化的。简单地说,很多读者恐怕首先会觉得评论“精彩”。这就是直觉的审美体验,就是文本与受众交流的第一切合点。而没有做出道德判断,也无需道德判断,因为道德判断需要很多相关的知识,需要深入进行。当深入进行分析解读的时候,审美的体验已经消失,分析结论会不同。当然,如果专业的和相关背景的知识的介入,那么审美的体验完全可以升华为理性判断。就这一点说,所谓文人相轻的评论话语不道德的内涵也消解了,还可因审美愉悦加深理性思考,使文学理论的内涵丰富。文人相轻与文学评论的关系及其作用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最促人反思的是为什么那些所谓不道德的评论话语能够在时空的风尘中穿越,“经典”地来到现代以至未来?事实上除了艺术的原因之外,还有文人爱其文本的强大的心理需求的原因,代代积淀传承,就成了文学评论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概括地说,集体记忆抹不掉,构成要素就将合理地存在。既然是合理的存在,那就要科学地研究,发现其价值,利用其价值。纵观中国古代的文人相轻现象,魏晋时期形成理性判断,以其有损于道德而加以排斥,之后说教者、论述者代不乏人,“道德论”可谓强势话语。可是,文人相轻的现象并没有受到节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明清时代的知名文人,很多都主动发起或被动牵连与文人相轻有关的论争。什么“屠沽儿”、“婴儿学语”、“魔窟中作活计”、“说他人梦”、“野狐外道”、“已陈之刍狗”等,频繁地
使用于文学评论的语言之中,事实上这些话语又是频繁发生的文人相轻的标志。为什么文人相轻的恶劣影响,甚至丢掉性命的严重后果,“道德论”强势话语的叮咛警告,未能使本来应该读书明理的文人警醒?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或许文人喜爱其文本的根因就是审美愉悦的自由象征,就是《庄子》所讲的绝对自由的精神逍遥,哪怕只是释放自由和心领神会那一瞬间的快感。其次就是共同喜爱的创造语言的艺术之根。不道德的文人相轻的文本,恐怕只有象征自由的美和巧妙的语言艺术才能沟通历时的和共时的文人。因此,不认真研究文人相轻于文学无益而有损;只用“公正”和“科学”检验文人相轻是否符合文学评论标准是错接枝干;仅靠“道德论”封杀文人相轻是将水和婴儿一起倒掉。
文人相轻对文学评论最明显而直接的意义在于将其发展而求其真,将其深化而求得定论。上举之例尽管也不乏精彩,但总归是平面的、单一的、偶发的,而且某些狂傲而盛气凌人的背后是粗陋的直露,浅薄的张扬。下面讨论几个因其评论所引发的思考和论争的持续和深入的例子。
元好问如果不讥讽秦观诗作,争论就无从发生。而其大论一出,引来众多的反对者。瞿佑云:“遗山固为此论,然诗亦相题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亦可谓女郎诗耶?”[12]1241袁枚也针锋相对地说:“此论大谬。芍药、蔷薇,原近女郎,不近山石;二者不可相提而并论。诗题各有境界,各有宜称。杜少陵诗,‘光焰万丈’,然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分飞蛱蝶原相逐,并蒂芙蓉本是双。’韩退之诗,‘横空盘硬语’,然‘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坐添香’,又何尝不是‘女郎诗’耶?《东山》诗‘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周公大圣人,亦且尚谑。”[3]112他还意犹未尽,又批评说:“余雅不喜元遗山论诗,引退之《山石》句,笑秦淮海‘芍药蔷薇’一联为女郎诗。是何异引周公之‘穆穆文王’,而斥后妃之‘采采卷耳’也。”[3]79薛雪也有相似的观点,只是较袁枚温和一些:“元遗山笑秦少游《春雨诗》:‘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瞿佑极力致辨。余戏咏云:‘先生休讪女郎诗,《山石》拈来压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云鬟玉臂也堪师。’”[13]424-425蔡梦弼引《诗眼》以“理”为说:“世俗喜绮丽,知文者能轻之。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然文章论当理不当理耳。苟当于理,则绮丽风花,同入于妙;苟不当理,则一切皆为长语。”并引用杜甫的很多诗篇说明“皆出于风花”,“然穷理尽性,移夺造化。自古诗人,巧即不壮,壮即不巧。巧而能壮,乃如是也矣。”[14]201-202因文人相轻而起的论辩,夹带着文人相轻的评论,结果却在逆势的对垒之下论出了“公允”,论出了“道理”。各执则一端,合则为一体;分则为“偏”,合则为“正”。审美趣味的不同因评论者地理、禀赋、气质、修养、经历等不同形成,不同正是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这些都是永远有倾斜却绝不失重的合理的存在。这一结论今天已是不争的定论。
文人相轻由于出语警策或幽默调侃,给人的印象十分鲜明,因此一个问题往往可以吸引众人共时的和历时的参与论说,论争之后,最终收获的是澄清,真像成为必然。不仅促进了文学评论生产,而且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是非得以分辨。这也是对文学评论“有益”之一。司马光《续诗话》云:“惠崇诗有‘剑静龙归匣,旗闲虎绕竿’。其尤自负者,有‘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时人或有讥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岗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诗句犯师兄。’”[15]274这个例子虽然用了“讥”、“嘲”等字眼,但并非真正意义的嘲讽,无刻薄之意,实质为调侃。惠崇诗句融入了前人诗句的内容,既可以看作是剽窃,同时也可以视为化用。这在文学生产的继承和创新的实践之中是常有的现象。肯定和否定的标准很难统一,关键要看前人作品中的内容是否与其创作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如果为其意境和艺术表现增强了效果,那是值得肯定的。众人皆知晏幾道《临江仙》一词,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两句,一字不差地套用五代翁宏诗歌的原句,却水乳交融般成为全词的有机成分,为词的意境凄迷,优美的幻象、深情的相思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接受欣赏此词的人都由衷地叹美。其作是成功的再创造。不过惠崇此诗,即《访杨云卿淮上别墅》用了前人诗句,而奚落、调侃者却不少。仅以宋人的看法论之,司马光如彼。刘攽《中山诗话》有所不同:“僧惠崇诗云:‘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然唐人旧句。而崇之弟子吟赠其师曰:‘河分岗势司空曙……’杜工部有‘峡束苍江起,岩排石树圆’,顷苏子美遂用‘峡束苍江,岩排石树’作七言句。子美岂窃诗者,大抵讽古人诗多,则往往为己得也。”[16]284不以惠崇为剽窃,还“弟子吟赠其师”云云,不仅没有奚落、调侃惠崇,似乎还为其辩护。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之三“诗犯古人”条针对“有僧嘲其蹈袭”说:“此虽戏言,理实如此。作诗者岂故欲窃古人之语,以为己语哉!景意所触,自有偶然而同者。盖自开辟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风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态。”[17]174他的话很值得玩味,颇有道理,竟是完全赞赏惠崇的诗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18也认为是惠崇徒弟嘲讽其师之作,惠崇用前人诗句“可轩渠一笑也”。[18]491更有与这两个系统都不同的看法。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说:“宋九释诗惟惠崇师绝出,尝有‘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之句,传诵都下,籍籍喧著。馀缁遂寂寥无闻,因忌之,乃厚诬其盗。闽僧文兆以诗嘲之,曰:‘河分岗势司空曙……’”[19]34文莹是与欧阳修同时的僧人,又是知名学者,所记是僧徒与文坛之事,可信的程度很高。众人的评论都涉及“师兄”一语,只有依据文莹的记载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惠崇的弟子不能称他为师兄,《续诗话》中的“时人”一语也意义不明,只有同辈的僧人文兆称呼惠崇为恰当。由此可以辨明这一桩很多书籍涉及的公案,《湘山野录》近于事实。此事是因妒忌而发生的文人相轻,尽管主客体都是僧人身份。文兆嫉妒惠崇之名,借机嘲讽,决不是开开玩笑而已。“厚诬其盗”显然是过甚其辞,试图玷污惠崇的名声,以引起世人注意。此事因文人相轻引发,最终真像大白,还涉及文学作品与再创作的艺术理论问题。
关于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的评论更为典型。文学评论常常观点相左,争论不休,甚至百代而下也难寻结果,孰优孰劣永远也不能成为定论。然而林逋的诗作却因文人相轻的介入,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成了磐石不移的定论。当其诗作很快就得到欧阳修等人的赏爱时,黄庭坚还有些不解地说:“欧阳文忠公极赏林和靖‘疏影……’之句,而不知和靖别有咏梅一联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何缘弃此而赏彼。”[5]370司马光也十分赏爱“疏影”一联,誉之为“曲尽梅之体态”[15]275。或者因其名气太大,于是就有逆其势而毁之者。周紫芝说:“林和靖赋《梅花诗》,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语,脍炙天下殆二百年。东坡晚年在惠州,作《梅花诗》云:‘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于参横昏。’此语一出,和靖之气遂索然矣。张文潜云:‘调鼎当年终有实,论花天下更无香。’此虽未及东坡高妙,然犹可使和靖作衙官。”[20]347这是迷恋苏轼造成的情感倾斜,过度贬损林逋及其诗作,“作衙官”一语更是文人相轻时常用语。周氏还不是最早贬低林诗的。王楙《野客丛书》卷22引苏轼语云:“诗人有写物之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物不可当此。林和靖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杏诗。皮日休白莲诗:‘无情有恨何人见,月白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王楙又进一步引申苏说加以评论:“仆观陈辅之《诗话》谓‘和靖诗近野蔷薇’。《渔隐丛话》谓‘皮日休诗移作白牡丹,尤更亲切’。二说似不深究诗人写物之意。‘疏影横斜水清浅’,野蔷薇安得有此潇洒标致?而牡丹开时,正风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风清之气象邪?”[21]247梁章钜视陈辅之之论为“无理取闹”,他说:“至林和靖梅花诗:‘疏影……’脍炙人口,而陈辅之以为有类野蔷薇。夫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影散漫,焉得横斜?此则肆口诋諆,无理取闹矣。”[22]198-199梁氏此辩驳有所本,宋人费衮《梁谿漫志》卷7云:“陈辅之云:林和靖‘疏影……’,殆是野蔷薇。是未为知诗者。予尝踏月水边,见梅影在地,疎瘦清绝。熟味此诗,真能与梅传神也。野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阴散蔓,乌得横斜也哉!”[23]741。“传神”之评,是费氏实践出真知之论。没有细微的观察体验,怎能写出景物的传神之笔。“疏瘦清绝”一语,非水月相映之时的认真观察,决不能得梅枝风神。有了费氏的实践之后,不仅陈辅之、周紫芝之说的幼稚和偏见暴露无遗,还更突出了林诗之美。事实上这正是陈、周等人的轻贬林诗,才将文学评论引向深入的结果。如果没有陈、周的轻贬林诗,就不会有费氏认真投入的仔细观察,也就不会有梅枝“疏瘦清绝”与“疏影横斜水清浅”的形象和神韵的关合。如果只停留在评论家主观感觉的争论之中,就不会引出了费氏以生活实践立论的深入。同时,费氏的观察描写能与林逋的诗句关合,正好可以林逋的生活实践为证,证明他的梅诗不仅仅是文人脱俗的心理投射,高傲性情的外化,而是有长期对“梅妻”的爱的生活实践的深深印痕。费氏的实践,同时也让受众明白了林逋为什么能写出梅的神韵的道理。还可以强化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的理性认识,即使是主体性和感觉的艺术特征鲜明的文学也不能背离。这样,将品评诗句的优劣与创作实践、生活观察与主体感悟等关联,林诗的优秀便由“脍炙天下二百年”的“感觉”公论而成为“实验”定论,而定论的形成首先得归功于陈、周等人的相轻评论。古代诗歌中写梅花的很多,真正能达到海德格尔所说的“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独一的诗来作诗”[24]25。林逋的诗就真正算得上是写梅花的“独一”。
综上所论,文学评论可以借助文人相轻的话语创造“精彩”,可以因此顺势或逆势推进,可以使论说丰富,可以深化而成为不刊之论。
二
文人相轻之“评论”,又是文学生产、艺术创作。由于参与者多是佼佼者,因此产出之作品往往优秀。有时“事出于沉思”,有时脱口而得,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表达方式不同。有盛气攻击、有辛辣讽刺,有含蓄奚落等,不一而足。然而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什么内容,都既是方式,又是体裁。很多时候形式大于内容。皮亚杰说:“每一个成分对于比它高级的成分来说是内容,而对于比它低级的成分来说是形式。”[25]19的确,有时候内容和形式相互转化,轻重不一。如果将文人相轻的个案纳入审美体验之中,那么有时感受到的只是形式,而非内容。其次,评说他人他作的文本常常为只言片语,难以“正经”的文学作品目之,往往因其微小而以微不足道视之,因其难用结构分析而以不入流视之。但是,从来的文学理论都没有将一切作品的大小及其形式划定标准,倒是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行其所当行,止其所不可不止”的“行云流水”之说深入人心。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之中,很多文学作品都是以短小著称。北岛以内容只有一个“网”字的《生活》诗闻名,恐怕就不符合任何“标准”,也没有任何“标准”将其拒之“文学”门外;恐怕这首诗最成功之处就是那一字,就是它的形式。文人相轻的表达重在语言,事实上体现了文学作品构成要素的关键之处。现在先就形式发端,以明文人相轻之文本价值。
最典型的就是不立文字的嘲讽和奚落。阮籍的“白眼”可能是最经典的不立文字的肢体语言,虽然多对礼法之士,但其间难道不存在文人相轻?不用申论,“白眼”的形式已经足以构建美,它不需要文字,也无所谓内容,能将话语意义包含即可。明代也有一个仅靠肢体语言就完成了文人相轻文本创作的人,那就是吴明卿。蔡子木在众宾之中吟诵自己得意诗作时,吴明卿就以假睡的鼾声表示鄙夷。吟诵之声高,鼾声亦高;吟诵之声停,鼾声亦停。在场的其他文人都觉得吴明卿过了头。不过这是吴明卿有意为之,恰恰是文人相轻中的相轻,是教训蔡子木对他人的轻视。王世贞《艺苑卮言》卷7云:“谢(榛)时再游京师,诗渐落,子木数侵之。”或许还因谢榛相貌眇一目,又是布衣,而蔡却为京师司法官员,潜意识中有小瞧别人的心理。无论怎样,吴明卿的鼾声当时就把蔡子木羞辱得“面色如土”。然而想不到的是这一特殊形式的文人相轻还产生了道德警示的效果:“后五岁,子木以中丞抚河南,子舆守汝宁,明卿谪归德司理、张肖甫谪裕州同知,皆属吏也。子木张宴,备宾主,身行酒炙,曰:‘吾乌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寻具疏荐之。”王世贞不禁赞美说:“余谓子木雅士不俗,居然前辈风,近更寥寥也。”[10]1065要文人虚心下气真不容易。王士禛评论蔡子木之事也认为:“今观明卿诗品亦未能过子木也,文士护前,往往夜郎王自大,适足为识者轩渠耳。厥后蔡巡抚中州……子木固盛德,不知尔时明卿当复置身何地?”[26]53二王都以道德立论,的确此事关系道德风操太大。后来做了河南巡抚的蔡子木,竟不计前嫌,还谦恭下士。为什么会那样?恐怕正确的解释只能是被吴明卿的鼾声羞辱之后自励改过,吴明卿鄙夷奚落其吟诵诗作的行为促使其变恶为善,变俗为雅,因为他小瞧谢榛的确有违道德,尽管是“被酒”之后,但醒来应该察觉。所谓君子三省,事后他不可能不比较思量,尤其是经历了较强的刺激之后,他很可能就以此为戒,做人、行事小心了。遇上吴明卿等人,又是酒宴场所,不忘前辱,一定会格外谨慎在意,所以才亲自斟酒,说出那样谦虚的话来。文人相轻从魏晋而下,就是历代引以为戒的话题,既警告他人,同时自己也在警醒、反省之中,这样能够带来“自新”的变化。因此,文人相轻也可以因祸得福。以此而论,吴明卿之举不仅是艺术的成功,而且还证明了文人相轻可以促进文人的道德修养。
韩熙载之事与其形式相同,性质相同,作用相同,但创作的匠心却异,还靠了文字辅助。韩熙载“见诗文荒恶者,令妓以艾熏其卷”,[27]54这是纯粹的肢体语言。龙衮《江南野史》卷4《宋齐丘传》云:“凡建碑碣,皆齐丘之文。命韩熙载八分书之。熙载尝以纸实其鼻。或问其故,答曰:‘其辞秽而且臭。’”[28]90同传又有“齐丘性度不能洪绰,襟器斗筲,苟不附己,莫之容忍。汪召符讥其名字,潜沉深渊”的记载。[28]90马令《南唐书》卷20宋齐邱入《党与传》,并言其“益树朋党,潜自封殖”。其人狂傲自大,文学“自以为古今独步”,“书札不工,亦自矜衒,而嗤鄙欧、虞之徒”。[29]341-342《十国春秋》卷20《宋齐邱传》评其“躁悻热中植党自用。迭起迭废,卒以不良死。史谓其狃于要君,闇于知人,其信然哉”。[30]202宋齐丘死后谥号为“丑谬”,即可知其人大略。韩熙载个性鲜明,虽文人习气浓厚,名士风度不拘,多有被人讥议之处,但就政治方面而言,却有忠正之称。马令《南唐书》宋齐邱本传指出其罪过,有“逐常梦锡、韩熙载、江文蔚以间其忠言”可证。[29]341-342因此,韩熙载的文人相轻其实质也是道德批判;其表达方式奇特而艺术,其文本可称经典。
还有一例可资比较。今本《隋唐嘉话》记载:“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31]55徐陵也用肢体语言,也用话语辅助,只是肢体语言的幽默奚落的艺术效果远不不如韩熙载,而话语鄙夷的分量却重于韩熙载。各有各的特色。据《北齐书》卷37《魏收传》云:“收每议陋卲文。卲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两人都抹去了修饰,不顾脸面,袒露了心声,道出了实情。他们相互嘲讽、诋毁的言语固然生动而精彩,更重要的是由此看到了南方和北方文人心理好尚的中心问题。为什么北方的文人领袖魏收和邢卲都在南方的文人任昉和沈约的文集中“剽窃”和“做贼”呢?换句话说,魏收和邢卲为什么都向任昉和沈约学习文学写作呢?为什么不是任昉和沈约向魏收和邢卲学习呢?答案很简单,南方文人瞧不起北方文人,这还不只是文学方面的文风、技巧、修辞等写作差异的问题,而是文化影响之下的文人心理结构的问题。南朝强势,北朝弱势。徐陵此举,只是文化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或许徐陵真为魏收着想,怕他的文章真的会被南方文人嘲笑。对比之下,徐陵的文章一出,顷刻之间就会不胫而走,传到北朝。《南史》卷62《徐陵传》记载:“每一文出,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传于周、齐,家有其本。”《陈书》徐陵本传亦云:“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 然而,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的文人,在相轻之中都留下了优秀的文本。
至于纯粹以语言为载体创作的文本,多得不计其数。不论是书面还是口头的创作,既表现作者鲜明的个性,又常常充满生气,不乏精彩,可以为文学生产提神。这些作品多以精巧而深入的构思以及精致的语言表现为特色,极有艺术欣赏的价值。从文人相轻创作的这些作品切入,可以深刻的理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理论价值,印证高尔基那句老生常谈的“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其实是万古常新的结论。[32]322托马舍夫斯基说:“艺术作品的本质不在于具体表达的特性上,而在于将表达结合成某些统一体,在于词语材料的艺术构成。”[33]84这些文人相轻的作品,一般都不会太长,常常是几个字或一句话,因此需要“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才能形成艺术的“自由的整体”[34]157。特伦斯•霍克斯认为文学语言要尽可能地创造出丰富的“内涵意义”,而不只是言语的简单沟通与交流。[35]13乔纳森•卡勒将文学作品所影响的各个方面做了理论阐述,认为“意义是由语境决定的”,只有语境才能包括语言的全部规则,还有“作者和读者的背景”以及“任何其他想象得出的相关的东西”。[36]70-71下面举证论述的文人相轻所创作的文本,充分体现了这些理论要点,尤其是突出了语言艺术,丰富了语言层面之外的“内涵意义”。从“道德论”的角度看,它们可能是不道德的。
《后汉书》卷80下《祢衡传》说:“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祢衡一生短暂,却留下了不少无缘无故鄙视、诋毁其他文人的故事。为什么会那样?恐怕正如休谟所说:“因为骄傲有一种自然倾向,容易借一种比较作用引起他人的不快。这种效果必然会更自然地发生,因为那些毫无根据而自负的人永远在作那一类的比较,而且他们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支持他们的虚荣。”[37]639《后汉书》本传说:“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或问衡曰:‘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对曰:‘吾焉能从屠沽儿耶!’又问:‘荀文若、赵稚长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丧,稚长可监厨请客。”李贤注引《典略》云:“衡见荀仪容但有貌耳,故可弔丧。赵有腹大,健噉肉,故可监厨也。”陈、荀都是当时著名文人,竟然被祢衡那样嘲讽,非出自其天性狂傲是难以有其他解释的。祢衡的话语是不道德的,但他所创作的文本却是经典的。它实现了形式和内容的“独立完整的统一”,是艺术的“自由的整体”。祢衡不因荀彧的标致美貌而加赞语,却以“借面弔丧”贬之,自己的愉悦带给别人极大的不快,然而这却是逆向思维的艺术创作,是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的新颖比况。正如康德对想象力的赞美那样:“想象力是一个创造性的认识功能,它有本领,能从真正的自然界所呈供的素材里创造出另一个想象的世界。”[38]115一个人的标致美貌,应当在喜庆、爱情等方面体现其自豪和荣耀,但祢衡却反其道而用之,本来应与亮色、热烈等映照的,而以弔丧的沉郁灰暗色彩反衬,标致和美貌反而成了负担和累赘,成了厌恶和悲哀。稍作比较,如果祢衡用“借面相亲”来表达,那么符合了世俗的价值判断和心理期待,然而这一文本却没有美感,更不要说创意了。如果说“屠沽儿”之斥还是高傲的情感宣泄,只是直露的表达方式,那么“借面弔丧”才是真正的艺术构思,值得从修辞表达的角度去研究。从表面上看,祢衡不仅横扫了文人,还践踏了道德中的和善,但他同时又创造了审美的文本,使“借面弔丧”不仅成为经典,还影响了后世许多文人的构思表达。钱锺书先生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夫‘弔丧’独曰‘借面’者,无哀情而须戚貌,方为知礼,荀彧必生成愁眉苦脸如所谓‘哭丧着脸’、‘丧门弔客面相’耳。”[39]2405如果这样看,那么祢衡的表达就无艺术可言,而是事实陈述,似乎荀彧的相貌也变丑了,这大概是钱先生智者千虑的误解,忽略了荀彧的相貌本来就标致的事实。凭借想象力创造新颖比况或比喻的文本,并且用于文人相轻之中,恐怕祢衡是首创。就以“屠沽儿”为例,已经成为后世文人常用的评论语汇。王士禛《香祖笔记》卷3转引刘祁《归潜志》的话说:“金翰林学士赵秉文,尝述党承旨怀英论诗云:‘律诗最难工,五十六字皆如圣贤,中有一字不经炉锤,便如一屠沽儿厕其间也。’”[26]50这一比喻真是形象,屠沽儿与圣贤相并,更反衬其俗态。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和论著,常被人誉为“妙语连珠”,其中多有比况、比喻修辞之例,也不乏文人相轻之用,论其艺术渊源,似可与祢衡沟通。例如:“有清名家悼亡诗多者无过俞曲园,次则尤西堂,斗多夸靡,如官庖宿馔,香积陈斋,方丈当前,实寡滋味。”[40]472“余称王静庵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非谓静庵优于公度,三峡水固不与九溪十八涧争幽蒨清泠也。”[40]70“曼殊悯刚毅杰士,以为柔脆,怜豪华公子,以为酸寒,以但丁言情与拜伦言情等类齐观,而己于二家一若师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听途说,而谬引心照神交。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40]131恐怕这正是时空难以阻隔的性情与艺术思维之“心印”。
《南史》卷 45《王敬则传》云:“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也,侨居晋陵南沙县。母为女巫。后与王俭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时孝嗣于崇礼门候俭,因嘲之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王俭乃“王”家大族子孙,出身高贵,又有文才,因而骄傲,瞧不起王敬则,说出了鄙视王敬则的话“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瞬间便创作了优秀的文本。抛开道德论,仅就构思表达说,他十分巧妙地借用了史传中的一个典故,即司马迁《史记》中将老子和韩非并列在一篇传记之中。这一典故常用于文人相轻之时。文人以此显示其高傲和鄙夷对方的意思。王俭的话语表面看平淡,但内在的判断却激烈而尖刻,有更为丰富的艺术构思的内涵。其次,王俭创作的文本运用了双关修辞手法。“老子”既指道家人物,又指世人粗话语义的“我”,即王俭自指;“韩非”既指法家人物,又指王敬则。这样,尽管讽刺的意味很浓,但含蓄的内涵不仅仅在语言层面,没有给对方留下反驳的直接把柄。王俭大概是将此典故用于文人相轻的第一人,对后世文人影响很大,因此原创的功劳应归属于他。
如果说王俭的双关话语中还能感觉出激烈而尖刻的鄙夷和讽刺,那么谢庄与颜延之的相轻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含蓄之至。
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绝,隔千里兮共明月”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当时文人颜延之却偏偏以此作为奚落材料。《南史》卷 20《谢庄传》载其事,而唐人孟棨《本事诗·嘲戏》一段文字更为清楚,既可以弄清文人相轻的内涵,还可以了解谢赋何以有名:“宋武帝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邪。’延之对曰:‘诚如圣旨,然其曰“美人迈兮音信阔,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为然。及见希逸,希逸对曰:‘延之诗云“生为长相思,殁为长不归”。岂不更加于臣邪?’帝抚掌竟日。”[41]22细玩《南史》“始知”一语,才明白颜延之是以谢庄“才懂得”千里人共明月的基本常识嘲讽他,将其视为刚学知识的小儿;谢庄当然还以其人之道,也以颜延之“才懂得”死后长不归的道理奚落。宋孝武帝因此笑了很久。两人的话语似乎不经意中便轻轻道出,事实上正是文人深沉而狡狯的思维表达特色,正是最高明的含蓄。谢庄《月赋》为皇帝吟赏,的确可见它的艺术感染力。此前很少有如此开阔视野的月景描写,对后世诗文写作影响很大。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先引述颜、谢互嘲之事,又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加以说明。[42]496同书卷10还大量引述杜甫诗句,证明来自谢赋的影响:“月轮当空,天下之所共视,故谢庄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盖言人虽异处,而月则同瞻也。老杜当兵戈骚屑之际,与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观之,岂能免闺门之念,而他诗未尝一及之。至于明月之夕,则遐想长思,屡形诗什。《月夜诗》云:‘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继之曰:‘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对月》云:‘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继之曰:‘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娥。’《江月诗》云:‘江月光于水,高楼思杀人。’继之曰:‘谁家挑锦字,烛灭翠眉颦。’其数致意于闺门如此,其亦谢庄之意乎?颜延之对孝武,乃有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说,是庄才情到处,延之未能晓也。”[42]563-564葛氏对谢赋的赞美以及对杜诗的影响之论很有见地,但说颜延之“未能晓”《月赋》之美则不尽然。事实上颜延之是心知其美而有意贬低。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审美趣味的差异,但更可能是妒忌心理使然。看见喜爱文学的皇帝那样赏爱谢庄的作品,竟然不是己作,大概有一点狐狸嫌葡萄酸的味道。钟嵘《诗品》卷中引汤惠休评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评颜延之诗“如错彩镂金”,结果颜延之“终身病之”,[43]13-14可以略见其人性情。《南史》卷 34《颜延之传》说:“延之每薄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都能证明他对谢赋的感觉和理解绝不是“未能晓”,也能证明颜延之文人相轻的本质。不过,颜延之所创造的意在言外的文本也堪称优秀。
因文人相轻而创造的优秀文本不可历数,它们反过来又对文学评论的思维和用语产生深刻影响,有些文本究竟是文学评论的诙谐、风趣,还是文人相轻的讥讽、奚落,很难分辨清楚。苏轼评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44]308,论孟郊、贾岛“郊寒岛瘦”等,都是优秀文本,早已成为经典的文学评论,事实上其中也有文人相轻的讥讽、奚落或戏谑、调侃意味。元好问接着以“高天厚地一诗囚”的“桂冠”赏赐孟郊,[6]124当然得苏轼文本的启发,含有轻蔑之意,同时元好问也创造了优秀的文本,以至清人薛雪认为“诗囚”一语“新极,趣极”[13]705。汤显祖用“等赝文尔”、“冠玉欺人”八字就划清了与李、王等人的文学主张,[45]1365表达了对明代复古派文学的鄙夷之情。苏轼、元好问、汤显祖等人,都是在文学评论的同时又完成了评论文学的创造,在评论其对象的同时,也注入了文人相轻的情感。这些优秀的文本为文学生产和艺术欣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想象,无论是思想深刻和语言凝练的文本,还是讥讽、奚落中的诙谐、风趣的内容和形式,都能给受众以深深的思考和想象,才使得零散的、片段的材料变成一个整体。正如斯图尔特•霍尔那一个贴切的比喻一样:“正是我们对一堆砖和灰浆的使用,才使之成为一所‘房屋’;正是我们对它的感受、思考和谈论,才使‘房屋’变成了‘家’。”[46]3文学评论是独抒己见之事,差异甚大,小瞧、讥讽、诋毁无处不在。优秀的评论应该在美的追求中去创造,在艺术的精彩中去追求公允。而那些毫无个性的面面俱到的评论。四平八稳的各打五十大板,既对创作者无促进作用,更可能对受众产生昏昏欲睡的影响。这样的评论有何益处。至于那些套话满篇、阿谀应酬的文本,曾国藩称之为“米汤大全”的货色,更是在不齿之列。古人留下的精彩的文本,创造的评论文学,即使有文人相轻的内容,也可以扬弃而取其精华。事实上那些精华是有生命力的,自然会不胫而走,来到现代。孔德有一句名言:“知道历史以知道你自己”[47]94-95现代的文人与古代的文人在时空中交汇,记忆的遗传,使得“以往的印象不只必须重复,它们还必须被安排和定着,并且关涉到不同的时间中的各点去。这样的定着,如果不把时间当作一个一般的架构,一个包含一切个别事件的系列秩序看待,是不可能的。对时间的认知,必须隐含这样一个系列秩序的概念,与另一个我们称之为空间的那个架构相应。”[47]72
[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3]袁枚.随园诗话[M].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0.
[4]王英志.袁枚评传[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5]魏庆之.诗人玉屑[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6]元好问.遗山集[M].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7]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8]叶燮.原诗[M].王夫之等撰《清诗话》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9]李昉等.太平广记[Z].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10]王世贞.艺苑卮言[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1](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瞿佑.归田诗话[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3]薛雪.一瓢诗话[M].王夫之等撰《清诗话》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4]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
[15]司马光.续诗话[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6]刘攽.中山诗话[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
[17]罗大经撰.鹤林玉露[M].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8]胡仔编.苕溪渔隐丛话·后集[Z].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9]文莹撰.湘山野录[M].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0]周紫芝.竹坡诗话[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
[21]王楙.野客丛书[M].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2]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M].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3]费衮.梁谿漫志[M].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4](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25](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M].倪连生, 王琳,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6]王士禛.香祖笔记[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27]金埴.不下带编[M].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8]龙衮.江南野史[M].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9]马令.南唐书[M].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0]吴任臣.十国春秋[M].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1]刘餗.隋唐嘉话[M].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32](俄)高尔基.论文学[M].孟昌, 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3](俄)托马舍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方珊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34](德)黑格尔.美学: 卷2 [M].朱光潜,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35](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36](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37](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38](德)康德.判断力批判: 上卷[M].宗伯华,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39]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0]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1]孟棨.本事诗[M].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42]葛立方.韵语阳秋[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
[43]钟嵘.诗品[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
[44]陈师道.后山诗话[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
[45]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46](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 陆兴华,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47](德)恩斯特·卡希尔.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M].刘述先, 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