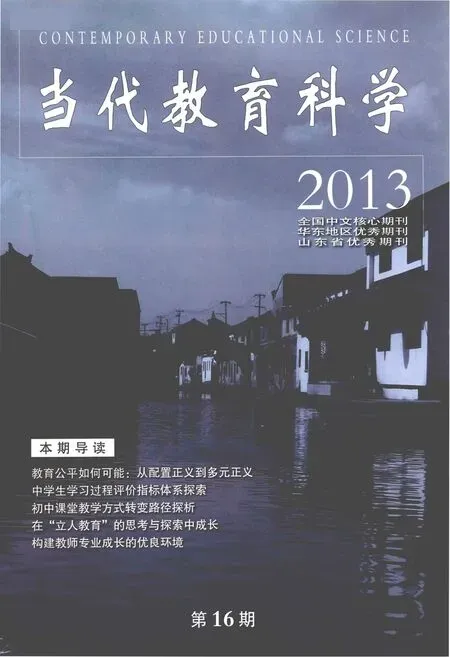“学习共同体”:理论价值与实践困境*
●屠锦红
一、“学习共同体”理念向教育教学视域的引渡
在教育教学领域掀起“共同体”研究的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标志是塞吉欧维尼于1993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举办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该讲话中,塞吉欧维尼倡议将学校的隐喻从“组织”转换成“共同体”,认为这样的转向会给学校的运作带来重要的变化,将激发教师、学生、领导层的动机。之后,很多学者尝试着将“共同体”的概念引入教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中。例如,李普曼提出的“探究共同体”,布朗和坎培恩设计的“学习者和思想者的共同体”,斯坎德玛利亚和伯瑞特研究的“知识建构共同体”,等等。
美国教育学家博耶尔于1995年发表了题为 《基础学校:学习的共同体》的报告,提出并具体阐释了“学习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认为在有效的学校教育中首要的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共同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学校必须:有共同的愿景,能够彼此交流,人人平等,有规则纪律约束,关心照顾学生,气氛是快乐的。那么,何谓“学习共同体”? 按照博耶尔的解释,学习共同体是所有人因共同的使命并朝共同的愿景一起学习的组织,共同体中的人共同分享学习的兴趣,共同寻找通向知识的旅程和理解世界运作方式,朝着教育这一目标相互作用和共同参与。
本世纪初,日本学者佐藤学把“学习共同体”理念引入到具体的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对“学习共同体”给予了较高的厚望,认为“学习共同体”是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愿景与哲学。这种改革哲学由三个原理组成,即所谓的“公共性”、“民主性”与“卓越性”。[1]“公共性”,即学校是旨在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这样一个公共使命而组织起来的“公共空间”,学校必须成为个性交响的场所。“民主性”,即在这种学校里,学生、教师、校长、家长,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的“学习权”和尊严都受到尊重;各种各样的思考方式与生活方式都受到尊重。“卓越性”,即学校同时必须是追求“卓越性”的场所,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必须是卓越的。这里所谓的“卓越性”并不是指谁比谁优越,而是指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无论是教师的“教”抑或学生的“学”都能各尽所能追求最高境界。
当前人们对“学习共同体”的理解事实上已远非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学习者群体合作的“组织”,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教育“理念”。“学习共同体”这一理念蕴含着丰富的教学理论价值;与此同时,“学习共同体”这一理念在我国当下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亦遭遇着重重挑战。
二、“学习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教学理论价值
(一)教学目标:彰显“和而不同”
愿景,是关于未来一种美好的愿望与意象。“在人类组织中,愿景是唯一最有力的、最具激励性的因素。它可以把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2]共同愿景,是学习共同体内部成员共同约定的奋斗目标。它是共同体中每个一成员相互紧密联系的纽带与共同的情感归属,每一个成员因共同的愿景而走到一起,并朝着共同的方向迈进。共同愿景体现了学习共同体总体的运作方向。从学校教育教学目标来看,共同愿景体现了一种普遍性目标,以“全面和谐”、“均衡发展”为基本指向。但是,学习共同体除了强调共同愿景外,还追逐个体愿景;除了塑造每一个共同体的“自我”,更要塑造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学习共同体珍视每一个个体的差异,宣扬“一切的差异万岁”。对学习共同体而言,“差异”不仅是教育教学的资源与财富,而且本身就是教育教学所追求的方向。学习共同体认定:一切试图“抹平”差异的教学,都是与人性相抵牾的。只有坚持“和而不同”,方能真正为每一个学习者的充分发展提供适切性教育,才能达成真正的“教育公平”。学习共同体所坚持的这种“共同”、“共性”与“个体”、“个性”协调推进的双重目标取向,顺应了新课程改革所秉持的“在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有个性的发展”这一基本理念,彰显了课程改革的时代精神。
(二)教学内容:追寻“意义世界”
在“教学什么”的处置上,学习共同体的关注点不是将“必须掌握”的信息“灌进师生的大脑”,而是关注师生在面对各种问题情境时所进行的“对话”过程中的思想生成和持续改进。[3]学习共同体要做的是让师生在和睦相处的温馨氛围中,在物我合一的沉浸体验中,实现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的和谐同构。对于学习共同体而言,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不仅是动态生成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对象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和谐统一。传统的课程内容过多地执着于认知存在,它把世界看成对象,以对象性思维方式使主体与客体相对立,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使世界规则化、逻辑化、标准化。这些虽是学生认识世界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学习的全部意义。这种课程内容仅仅涉及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图式,而无法关照学生整体的生命世界。注重生命发展的课程内容,不是概念、原理的简单组合与堆砌,而是作为人存在的生命意义的阐释。学生学习它,不只是把它看作为客观对象去认知,以获得关于世界的理性阐释,而是与它相遇并进行对话,基于自身的人生经验来体验它。通过这样的课程内容,师生不断领悟到世界的意义以及人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样的课程内容培育出的学生,将会是既具有知性与理性,也充盈着灵性与感性的完整的人。学习共同体坚持——“对象世界”只是手段,“意义世界”才是目的,手段与目的须统一。学习共同体的这一思想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根本旨趣。
(三)教学策略:倡导“对话体验”
对话,是学习共同体基本的“生命体征”,学习共同体运作的过程,首先是一种对话的过程。对话是共同体内部各个成员之间在相互尊重、彼此平等的基础上以语言为中介所进行的话语、知识、思想、情感等的沟通与交流。基于对话的教学,是在民主平等、尊重信任的氛围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彼此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在经验共享、双向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创生知识和教学意义,从而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教学形态。基于对话的教学充分调动了师生双方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批判、合作、交往、沟通、创新等多方面的意识和能力的养成。学习共同体的运作不仅强调对话,而且十分重视学习者内心的体验。体验,既有认识论意义,也有价值论和本体论意义。从认识论意义来看,体验的方式使认识方式发生转换,消除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本体论和价值论意义来看,体验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追求自身生命意义的方式。体验使学习者不再是一个只会理性思考的动物,而是要成为知、情、意协调发展的“全人”。[4]学习共同体强调对话与体验的运作过程,真正解放了人,让师生都能作为真实的存在者“生活”于课堂空间,真正“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四)教学环境:构建“生态课堂”
基于学习共同体构建的课堂努力将学习者置于知识产生和应用的情境中,为其创造一个真实的或虚拟真实的学习环境,即学习共同体始终要给学习者努力呈现这样的鲜活的课堂图景:通过真实的或仿真的实践活动,实现师生间与生生间的异质交往,将真实世界的学习方式带到学校、带到课堂。传统的课堂教学则将课堂打造成一个封闭的世界,把教学对象孤立起来,把教学内容抽象起来,让教学世界成为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孤岛,并且依凭不同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去情境化的知识来驯化学生。毋庸讳言,这样的课堂是“死”的,是没有生机的;这样的课堂培养出的学生是“呆”的,是没有灵气的。这样的课堂教给学生的那些知识也是“假”的,是没有大用的。教学本身是为了让儿童过有意义的生活而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传统课堂培养的学生离意义的“生活”很远,他们从学校走入社会,就如同跨越一道文化的鸿沟般艰难,这可谓是我们教育莫大的悲哀。基于学习共同体构建的课堂环境,主张“教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亲近与融通,这为我们重建课堂生态指明了方向。
(五)师生关系:恪守“主体间性”
在学习共同体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而存在着,每个人的个性差异都会得到彼此的尊重,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会得到彼此的关注,师生的主体性存在得到了充分凸显。学习共同体的建立,“意味着师生走出原子化的‘自我’,通过与其他人进行平等的交往与对话,围绕共同的主题内容,在‘学习场域’中建构一个充满学习自觉性且具有独特文化氛围。”[5]学习共同体中,师生主体性并不是“孤立”的主体性,而是“交互”的主体性,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是一种“我—你”、“我—我们”的关系。这种主体性表征着主体之间完满的、既有中介物又是自由联合的、彼此之间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关系。作为个体学习者的“我”,是与作为全体学习者的“我们”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世界中,“我们”共同认知和建构着教学世界的意义。总之,学习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单纯的主体性神话,它告别了“教师中心论”或“学生中心论”的教条,跳出了孤独的“教”与“学”的樊笼,从根本上纠正了或过分强调教师为主导、或一味张扬以学生为中心之任何一种片面的取向,呈现了一种更加本真与和谐的师生关系。
二、“学习共同体”理念面临的实践困境
(一)工厂化的学校组织结构的钳制
学习共同体的组织结构是相当“自由”与“人性化”的。在这里,教师既是“教”者,也是“学”者;学生既是“学”者,也是“教”者。在学习共同体中,没有绝对的、严格的“等级制”。当然,学习共同体内部也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以确保共同体成员更好地朝着一定的目标有序迈进。但是,这种规章制度并非来自共同体外部意志的强加,而是共同体内部成员共同约定的、符合师生内心需要的“游戏规则”。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校组织基本上沿袭了行政机构的设置模式,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科层组织”。在这种组织中,按照权力等级和严格的纪律理性化地建立其组织结构,学校由校长——主任——组长——教师——学生等这些层级构成。美国教育学者戴维·W·约翰逊和罗杰·T·约翰逊兄弟二人则称其为“批量生产的组织”。[6]基于这种批量生产的方式,教学由此成为阻抑师生生命活力的“人工窒息机”,学校则变成了非人性化的“工场”。这种“环境”是很难适合学习共同体生存的。
(二)僵化的班级授课制的束缚
班级授课制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即假设所有学生都具有同样的学习能力,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速度学习同样的内容,并达到同样的要求。这显然与学习共同体蕴涵的“和而不同”的理念相违背的。学习共同体它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异质性以及课堂教学的建构性、多变性与协同性,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的处理上,是弹性的、灵动的、多姿的,而传统班级授课制却更多散发出固化的、教条的、呆板的气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无论是时间维度上还是空间维度上,班级授课制均束缚着学习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在时间方面,整个一节课绝大部分时间常常均是教师在演绎,课堂变成了报告厅,学生成了看客;在空间方面,为了便于教师的宣讲,学生座位更多的是“秧田式”设置,学生多维的合作、讨论与互动,被无情地阻隔掉了。班级授课制为学生建造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在这里学生无法体会到内心真正的喜悦,很难怀有真正的自我提高内驱力,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为了教师的脸色与家长的悲喜。这一切均与学习共同体的世界背道而驰。
(三)强大的灌输式教育思想的沿袭
在学习共同体的世界,没有“驯服”,没有“霸权”,师生在平等对话、相互协作中建构着共同体的集体智慧以及每个成员自我的人生经验。在共同体的有效运作过程中,蕴含着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的此消彼长与循环共生,蕴含着个体意义建构(形成“个体知识”)与共同体的意义建构(形成“公共知识”)的相互促进与共创共赢。然而,我国的教育文化蕴含着浓烈的灌输式教育思想。学生从“集体”中学会的更多的是“保持安静”、“认真听讲”这样的奴性思想。“集体失语”是课堂的常态。整个教育活动“遵循着各种预先规定了的程序和预先套装的价值,它只关心如何把人培养成预先严格规定的类型的人,却不关心每一个独特的生长环境,不关心他们内心世界潜藏着的愿望、热情等现实生命冲动所指的方向”。[7]然而可悲的是,我们的教师乃至学生早已对此习以为“常”。
(四)保守的课堂管理的阻抗
课堂管理模式主要有:权威模式、放任模式、教导模式、行为矫正模式、人际关系模式以及群体过程模式等。适宜于学习共同体运作的理想的课堂管理模式应是人际关系模式与群体过程模式的融合。人际关系模式侧重为课堂创设良好的氛围,师生之间都能相互设身处地的理解和信任,从而创生一种“建设性”的课堂人际关系。群体过程模式,它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和群体动力学基础上的课堂管理模式。主要特征是:发展群体内聚力,创设开放的交流通道,让学生能自由地表达观点和情感,相互影响与促进。上述两种课堂管理模式,为学习共同体的运作提供了理想的“气场”以及动力保证。然而当下实际的课堂管理趋于保守,常常显性或隐性、有意或无意地去竭力维护所谓的“师道尊严”,课堂管理的权威模式时有发生。权威模式,往往是教师采用各种命令的方式来控制学生,各种规则较为严格与刚性。无疑,这与学习共同体的有效运作是格格不入的。
(五)匮乏的课程资源的制约
基于学习共同体的视域,认知被理解为一种分布的现象。人类活动中的智力过程其实超越了个体行动者的疆界。认知既分布在一个群体的个体成员之间,也分布在个体的心智与外部物质环境之间。学习者只有共享“人”及“人工制品”的智慧,才能完成复杂的任务和发展认知。具体而言,在学习共同体中,知识分布在共同体的各个要素中,只有包括学习者个体、助学者和各种工具及信息资源(如文字材料、书籍、音像资料、CAI 与多媒体课件以及Internet 上的信息)等各个要素密切地交往合作,共享认知活动,才能达成对知识较完整的理解,共同建构所学内容的意义。因此,为了真正能支持学习者的主动探索和意义建构,在学习过程中,必须要开放与创设一切可以利用的课程与教学资源,要保证每一个学习共同体、共同体中的每一个学习者,都有使用一切资源的权利,要做到资源共享。[8]课程与教学资源的丰富程度,将直接影响学习共同体运作的成效。然而审视实际的学校教学,课程与教学资源往往局限于校内,局限于课堂,局限于教科书、粉笔、黑板等;虽然也会见一些其他辅助的工具与媒体,但这些工具和媒体的使用多是由教师来操作的。学习者除了孤独地对一些教材的运用之外,其他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较为匮乏。
[1](日)佐藤学.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M].钟启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3.
[2](美)戴维·W·约翰逊,罗杰·T·约翰逊.领导合作型学校[M].唐宗清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7.
[3]刘光余等.课堂学习共同体的构建[J].中国教育学刊,2009,(4):65 -67.
[4][7]余文森等.解读教与学的意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9,40.
[5]程玮.学习共同体实践路径[J].中国成人教育,2010,(15):139-140.
[6]刘忠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学校重建——基于“学习共同体”的理念[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6):21-24.
[8]屠锦红,潘洪建.大班额“有效教学”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学习共同体的视域[J].课程·教材·教法,2011,(11):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