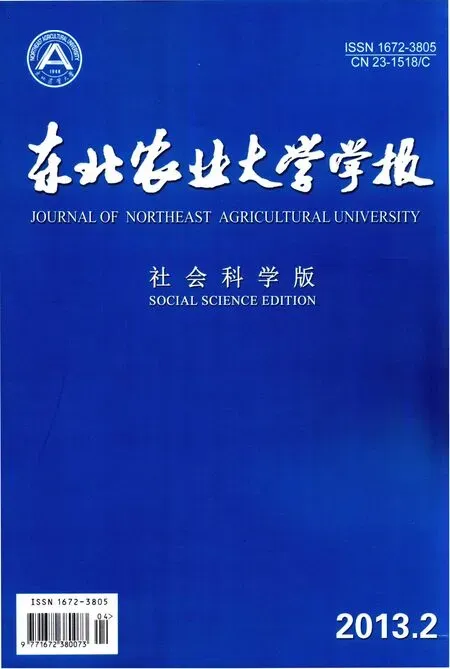从《灶神之妻》中的母女关系论故国的角色转换
杨亚丽 李 庚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1989年推出首部作品《喜福会》并大获成功后,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于1991年发表第二部作品《灶神之妻》。该作品延续其倒叙、讲故事等叙事风格,依然着眼于复杂纠结的母女关系,以此为基本框架构建全文。取材于母亲的真实经历,以中国抗日战争及内战为大背景,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饱受旧中国封建礼教束缚和男权制度压迫的传统东方女性雯妮,从迷茫到追寻,从麻木到抗争,从“失声”到“呐喊”的心路历程。文中,以雯妮为中心展开的两对母女(即雯妮与女儿珍珠、雯妮与母亲)关系,体现了三代人文化与精神的冲突和传承,跨越了东西方文化的鸿沟与障碍。
作为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承受着来自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力,犹如置身于边缘文化的最后一块危石之上。谭恩美在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困惑与迷茫,对故国不由自主的亲近和不明所以的抗拒,徘徊于东西方文化之间无法融合、无从选择时的无助失落,以及摆脱不掉的危机感在她创作的“美国女儿”身上都有所体现。珍珠的形象正是华裔女性的普遍形象,其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华裔女性的普遍问题,包括如何看待特殊的华裔身份,如何平衡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如何利用这一特殊身份在文化碰撞中发挥积极作用等等。对于情感更丰富、心思更细腻的华裔女性来说,这些问题需要更多时间和经历来积淀和领悟。而具有东方文化传统形象的“中国母亲”正是故国的象征和体现,母女关系是分析故国在华裔女性成长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最佳切入点。《灶神之妻》中,“中国母亲”雯妮和“美国女儿”珍珠是这一关系的直接载体。两人在珍珠的成长道路上有过多次“交锋”,却从未尝过胜利的滋味,而是身心俱疲、伤痕累累的失败者,是一对彼此深爱却又无法靠近的“亲密敌人”。这是双方所属的文化系统赋予二人的特殊关系。而两人最终互相理解、互相接受,代表作者心中对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美好希冀。雯妮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正面体现华裔女性和故国的关系,但谭恩美始终以华裔女性的视角来处理,遣词造句中流露出以谭恩美为代表的华裔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对“中国母亲”的态度及对故国的情感。本文将从这两对母女关系入手,解读故国在华裔女性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两对母女
(一)雯妮与女儿珍珠
雯妮与女儿珍珠之间的关系在开篇便借由珍珠之口点明:“每当我母亲跟我说话,一开头总像跟我吵嘴似的。”以珍珠为叙述者“我”的一、二章中,字里行间弥漫着这位美国女儿的困惑与无奈。“菲力老是说我无论干什么总爱盲目地担心和内疚。我则反唇相讥说他自私,我说,人活着有时总得干一点不痛快或不方便的事。”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特征,是东方思维的集中体现。虽然珍珠以这种东方思维为自己辩护,但也会质疑:“而如今——比方说今天——我真无法断定为什么我非得背起娘家的责任。”可以看出,珍珠虽然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接受美国教育和西方主流文化熏陶,但家庭(尤其是母亲)带给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正因如此,珍珠才挣扎在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中无所适从。
雯妮与珍珠之间并不存在“真枪实弹”的冲突或攻击。母亲对女儿隐瞒自己在旧中国痛苦可怕的婚姻经历,女儿对母亲绝口不提自己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情。本应亲密无间的母女处处流露尴尬与不和谐,这对于感情敏感、细腻的女性来说,无疑更为可悲与可怕。对于同一件事,母女俩总是给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评论,这是母女各自熟悉和归属的文化系统赋予她们的独特视角。珍珠在参加杜姨婆葬礼的归途中,曾发出感叹:“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同时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母亲之间,把我们分开了。”但无论“横亘”着怎样的“距离”,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始终维系着母女二人。最终,双方在互相坦露心声后,成为一对“可以共同承担生活中很多大事”[1]的母女。
(二)雯妮与母亲
文中并没有用过多笔墨介绍雯妮的母亲,但寥寥数笔已经勾勒出这位母亲果敢、独立、富于斗争精神的女性形象。雯妮在母亲离家出走后,被父亲送到崇明岛的叔叔家,如同离开故国来到一个全新国度。这里没有熟悉的家庭环境,没有母亲的朝夕相伴,雯妮就在这样一个陌生而冷漠的“异国”家庭中,完成了自己的成长。这与华裔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处境如出一辙。雯妮的母亲,经常出现在雯妮孤独无助时的回忆与思念之中。可以说,虽然雯妮与母亲只短短共处六年,但母亲给雯妮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雯妮对母亲的态度,是雯妮自身精神成长的标尺。从最初不相信、不接受母亲出走,到不理解、不确定母亲是对是错,直至最终将母亲作为榜样并勇敢地追求幸福,母亲始终影响着雯妮。私奔的母亲和上海的父亲家在雯妮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谭恩美心中故国角色的写照。
二、故国在华裔女性成长过程中扮演的消极角色
(一)失职的母亲
中国家庭体系中,母亲是维系关系的根本,也是评价和考量子女的标尺。母亲的出走是雯妮痛苦的导火索,不仅给雯妮带来负面影响,也造成雯妮“女儿”身份的缺失。在“异国”叔叔家中,雯妮并未遭受虐待,却无时无刻不承受来自情感缺失的冷暴力,无法确立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雯妮心中永远保留着这样的疑问:母亲究竟去了哪儿?为什么不回来接她一起走?雯妮心中也永远保留着这样一种期待:自己仿佛还是那个六岁的小女孩,等待妈妈归来。母亲是雯妮的一块心病,这种复杂纠结的感情,在雯妮心中演化为怨恨与依赖的矛盾综合体,时刻折磨着她。
故国,正如雯妮的母亲“缺席”雯妮的成长一样,“缺席”于华裔女性的成长。在以谭恩美为代表的华裔女性成长的时代,中美交流存在很多障碍。华裔对故国的了解,多来自长辈的回忆和描述。但回忆和描述毕竟是模糊的、片面的,依靠这种间接了解还原的故国只是想象中的故国,就像雯妮对母亲残存的回忆一样虚幻。华裔女性无法依靠一个根本不了解的故国来构建文化身份,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失去与之对等的文化支撑。相比之下,华裔男性虽然同样面临文化冲突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困境,但在自己的族裔中,他们占有绝对优势,享有绝对优越感,并借此建立社会人格和社会身份。当华裔女性转而在美国这个熟悉的环境中努力寻求归属时,又总有反对的声音不断提醒:“你本不属于这里!”故国,好似一位失职的母亲,不但没有尽到责任,还剥夺了子女在“别人家”获得幸福的机会。这种“无家可归”的尴尬境地,使华裔女性在遥望故国时,心生惆怅和怨恨。
(二)无奈的“敌人”
如果说雯妮母亲对于雯妮来说是阴影一般虚幻压抑的“敌人”,那么雯妮与女儿珍珠之间的矛盾更为具体切实。雯妮用中国传统方式教育珍珠,教导她的言行,限制她的交际,努力将珍珠塑造成自己心中完美的东方女性形象。然而这一切对于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珍珠来说,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母亲眼中合情合理的种种要求,对于珍珠这样对东方文化毫无概念的华裔来说是可笑、不可理喻的。另一方面,雯妮也无法成为珍珠心中理想的美国式母亲。珍珠回忆儿时万圣节的南瓜灯,当她误以为有鬼魂出没时,雯妮没有第一时间安抚她,而是先问鬼魂在哪里。当继父吉米安慰珍珠时,母亲的眼神又令她不安。珍珠无法接受母亲对爱的表达;母亲苦心隐藏的过去,更让珍珠对母亲的很多行为无法理解: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似乎都透露着不和谐。珍珠母女间的冲突在吉米的葬礼上达到高潮——珍珠没有如母亲希望的那样痛哭流涕。她没有哭泣,同时拒绝承认那个躺在棺中苍白恐怖的人,就是自己幽默慈爱的父亲。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儿在失去父亲时悲痛至极的表现,此时,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母亲的理解、关爱和支持,但她得到的却是母亲的一记耳光。
雯妮与珍珠之间的矛盾,实际是中美文化之间的冲突。正如美国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赛义德所说:“西方和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2]代表西方强势文化的珍珠,在母女关系中却处于“女儿”这个在东方家庭文化体系中的弱势地位;雯妮虽然身为母亲,但她所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母女二人不得不在东西方文化和单位小家庭这两对关系中,不停地进行强势与弱势的角色交替,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当出现冲突时,母亲雯妮采用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虽然这是雯妮在情绪失控时的无心之失,但对珍珠来说,无疑是在其探寻故国的路途中增设一道屏障。母亲的行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东方主义定义下,东方人粗暴野蛮的刻板形象。在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故国最终被动地成为华裔女性成长过程中无奈的“敌人”。
三、故国在华裔女性成长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一)确立自我的镜子
“镜子”在雯妮回忆母亲的短暂篇幅中出现频率相当高。“这个字眼总要使我母亲在镜子前坐好几个钟头,骂那个盯住她看的第二个二姨太。”“我母亲坐在梳妆桌旁,正在梳头,她对着镜子喊‘第二个二姨太!第二个二姨太!’”雯妮为自己挑选的嫁妆中,最心爱的东西是有着一面镶银边大圆镜子的梳妆台,“我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张梳妆台前,看上去就像我母亲那样”。到美国后,雯妮又为女儿珍珠买了类似的梳妆台。“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它。所以你要明白,我买这张桌子不是用来折磨你的,那是我心爱的东西。”雯妮母亲痛恨镜中那个身为“第二个二姨太”的自己,更无法忍受这个身份带给她的屈辱和束缚。她透过镜子审视自己,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建构后最终觉醒,离家出走。这种追寻自我的勇气和实现自我的力量,正是雯妮从母亲身上继承,同时又希望传递给女儿珍珠的。雯妮向珍珠坦白自己在旧中国的苦难经历,珍珠在母亲的讲述中踏上故国寻根之旅。她找到了母亲敏感、胆小、迷信的根源,体会到母亲为保护自己做出的努力,更感受到母亲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勇气。对母亲和故国的理解,帮助珍珠跨越文化和民族障碍,让这朵漂浮在东西方文化间的浮萍,最终寻得精神上的归属和依托。
华裔女性的成长总是伴随着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困惑和无奈,这份困惑和无奈也是多数华裔女作家的灵感源泉和作品主题。故国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帮助她们找寻“我是谁”“我要成为谁”的答案。任何人只有接受过去,才能创造未来;只有确立自我,才能告诉别人“我是谁”。对于华裔女性来说,认同并接受自己的民族属性是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渠道,是拥有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权的根本。这是谭恩美作品中“美国女儿”的共识,也体现故国这面“镜子”在华裔女性成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停泊心灵的港湾
雯妮心中母亲的形象在时间与地域的经纬中不断拉扯,逐渐模糊,但她却始终记得母亲“黑亮黑亮”的头发:“我怎么忘得掉我母亲头发的颜色呢?”“头发”在雯妮回忆母亲时被反复提及。中国古典文学中惯以纤细而坚韧的意象,比拟女性柔中带刚的品质,如“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孔雀东南飞》),以蒲草的坚韧表现女子对爱情的忠贞和坚守。“头发”与“蒲草”异曲同工,体现雯妮母亲柔弱外表下坚韧强大的内心。雯妮始终珍藏着母亲的一缕头发,那是雯妮唯一可以抓牢的属于母亲的东西,是她危难时汲取力量的源泉,困惑时寻找方向的指引,更是停泊心灵的港湾。谭恩美以“头发”这一意象作为连接母女精神的纽带,与传统东方文学审美不谋而合,体现了故国在作者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影响。
“美国女儿”珍珠在母亲回忆旧中国经历的讲述中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之旅,心中许多深埋的困惑都得以拨云见雾,眼前母亲的形象渐渐明朗化:迷信的背后是她的恐惧,多疑的背后是她的关切,专制的背后是她的隐忧。她爱自己的女儿,又无时无刻不担心女儿属于魔鬼般的前夫文福。珍珠的每个微小举动都牵扯着雯妮最敏感的神经,这是一种过分的忧虑。在珍珠对母亲的过去一无所知前,这种忧虑带给珍珠的只有压抑。母女间彼此的坦白将深深的压抑化作浓浓的爱,最终帮助珍珠确立了自我在现实与精神上的归属。她愿意尝试用中药治疗,并接受母亲送给她的“莫愁夫人”,这无异于将生命和精神都托付给这个“迟迟”才走入她心底的故国。寄希望于此便是寄心灵于此,珍珠终于在迷茫困惑中找到方向,安心地停靠在故国的港湾。
四、结语
复杂感人的母女关系是谭恩美作品的动人之处。母女间从误解到理解,从冷漠到温情,从冲突到融合的漫长旅程,是以谭恩美为代表的华裔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而故国在这段旅程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正确处理与故国之间的关系以完成故国角色由消极到积极的转换,是每个华裔女性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论哪种角色,无不说明故国在华裔女性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影响。
谭恩美笔下的“美国女儿”与“失职的母亲”博弈,与“无奈的‘敌人’”抗争,却在母亲的引领中依靠故国这面“镜子”确立自我,从而避免在西方主流文化中迷失方向,最终寻得精神归属,停泊在故国的“港湾”。这正是谭恩美一直秉承并力图传达的理念:无论相隔多么遥远,无论文化上有多少冲突,无论精神上存在着怎样的隔阂,华裔女性终将在成长旅程中感受故国、了解故国、接受故国,并最终以故国为支撑,成为一个可以昂首面对世界的真正的“我”。
[1]谭恩美.灶神之妻[M].张德明,张德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2]Edward S.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