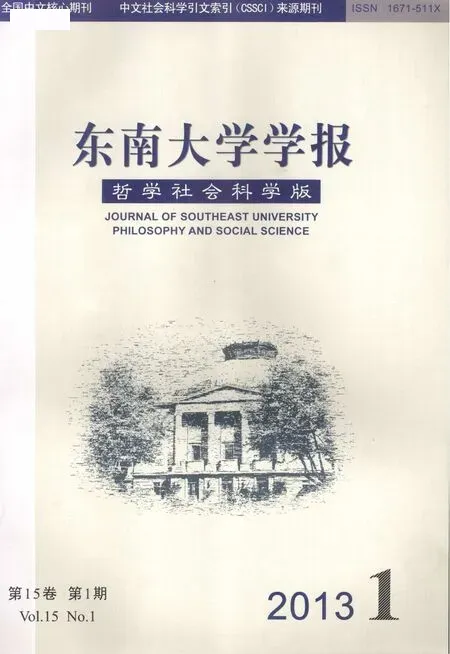爱、外在性与责任:列维纳斯的爱的伦理解读
林华敏
(广西大学 政治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爱是哲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哲学史上,从柏拉图到康德以及后现代思潮,爱都是哲学绕不开的议题。德里达曾将爱视作哲学思考的源头;而在后现代伦理学家列维纳斯的思想中,爱则是更为核心的。列维纳斯的哲学“思索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个体的、伦理的和政治的关系,而这些关系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1]58在列维纳斯那里,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自我与外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首要地在我和他人面对面的相遇中被揭示,这种相遇引发的第一个伦理行动表现为“召唤”与“回应”(责任),其伦理核心便是爱。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伦理和后现代伦理的基本分野在爱的主题上,进一步地,表现在“我和他人”,也即“同一性与异质性”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导致了它们对“我-他人;理性-情感;自由-责任;平等-非对称”等问题的不同伦理立场。本文将首先分析爱的内在基本特征,接着在现代伦理的背景下阐述列维纳斯的爱的伦理学,从而理清二者的基本分歧,探求列维纳斯爱的伦理的现代意义。
一、爱的矛盾性特征及其内在困境
在《整体与无限》“爱的矛盾性”一节中,列维纳斯描述了“作为与他者的关系的爱”的介于需要(need)和形而上学的欲望(desire)、内在性和超越性之间的矛盾性。爱是一次既回到自我但又同时保持超越性的冒险,它以对方的外在性为前提。一方面,“作为与他者的关系的爱,它能够被还原为基本的内在性,被剥夺所有的超越性。”爱的欲望,一个无止尽地朝向一个无限未来的运动,它能够被需要的自我主义所打破和满足。在这个意义上,爱是回到自我;另一方面,“这个需要以他者、被爱者绝对的、超越的外在性为基础。”[2]254他者的外在性使得爱作为不停的生成的运动得以持续。内在性与超越性,自我和他人构成了爱的基本结构。而根据列维纳斯的隐喻的使用,这种矛盾性结构在爱人之间的身体性爱抚中得到更为清晰的展现。“在首要的意义上,爱抚是爱欲的行为,它使得伦理关系中不可见的东西可见化;爱抚代表着爱。”[3]92爱抚体现了作为“两个”的存在状态,展示了其不可超越的二元性特征。在爱抚中,“欲望”与“永远无法满足”,“触摸”和“隐匿”共存。作为欲望的行为,爱抚没有“占有”“把握”和“认知”的意图。爱抚就像“和隐藏着的东西的一场游戏,一场没有任何方案和计划的游戏,和一些并不试图成为我们或者成为我们的东西的游戏,和一些总是外在的,永远不能抵达、永远要到来的东西的游戏。……爱抚是和异质性、神秘性、未来的关系,和一种既在、又不在那儿的东西的游戏。”[3]93列维纳斯关于爱的谈论始终缠绕在身体(爱抚)的谈论之中,因为身体是超越于意识意向性把握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这个维度他者出现而不会被我对象化,纳入到我的意识把握之中。
爱的两人团体的形成,其基本条件是双方作为“两个”而存在,这是列维纳斯所说的“没有关系的关系”状态。[2]80在这种关系中,对方的外在性绝对在场揭示自身,但同时又不在这种揭示中穷尽自身。这使得爱的关系成为一种模棱两可的、超越于意向性和对象化行为的直接切近和永远无法完成的等候共存的状态。鲍曼在解读列维纳斯的爱的伦理时,指出这种矛盾性是爱人之间伦理关系内在困境的根源。爱作为“两个”人的关系,它以神秘性(对方身上的异质性)为生。但是,一方面,如果这种神秘性过于封闭而不展现自己,那么它会失去它的诱惑力;另一方面,如果神秘性只试图敞开自身,在一个没有惊奇的日常生活中耗尽自己,那么它也会失去诱惑力。这构成了爱的不可超越的二元性困境。在这困境的两端都是爱的陷阱:爱可能因为好奇心的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而疲惫,最后死亡;爱也可能因为好奇心的被满足而走向无聊乏味,最后也导致死亡。这两种危险是爱的关系中所隐含的陷阱,无论如何,只要爱是基于“两个”,两个相异者,那么这种困境和陷阱就必定存在。这就是爱的关系自身内在的困境。
以下我们将分析指出,这种令人烦恼的矛盾性成了现代性伦理学家努力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正是这种努力,构成了现代伦理学的主要内容。而列维纳斯关于爱的伦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凸显其“另类”与意义。
二、现代性对爱的矛盾性的克服
1.现代性:理性和自由的诉求
理性是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的关键词之一。正如康德所总结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4]22现代性与科学密不可分,而这种密不可分的背后是理性对权威和宗教的束缚的摆脱,努力恢复自身的自由与权利,构建一个能够被理性主导和把握的清晰有序的世界图像。恰如鲍曼指出的:“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建立秩序的任务……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将其他所有的任务仅仅当作自身的隐喻)——凸显出来。”[5]7这个任务所针对的是陌生性和矛盾性。“典型的现代实践(即现代政策、现代智力、现代生活之实体)乃是为根除矛盾性而作的努力,是一种为精确界定——并为压制和消灭不能或不会被精确定义的一切而作的努力。”[5]12-13在这种现代性的任务背后,可以看到,在启蒙之后,人的主体性的苏醒以及它对把握自身和把握世界的强烈的渴望。
现代性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自由。在根本上,理性和自由共享着一个重要的理念,那就是“主体性”。无论是对理性还是自由的诉求,二者都立足于人的主体性,即“我”。理性扩张的同时必定伴随着自由的膨胀,但是二者共同的结果是主体性的膨胀。而按照列维纳斯的批评,这种主体性扩张的过程是从属于西方整体性对外在性暴力的一部分。
2.对爱的超越的矛盾性的“治疗”
在爱的伦理上,现代性将爱的矛盾二元性看成是一种疾病,试图去克服和治疗它。而在这点上,爱的矛盾二元性自身内在已经蕴含着对其“治疗”的途径:“避免第一个陷阱,爱可能会把主动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且,偷偷地地用自己的‘解决’来取代迷惑。为了避免第二个陷阱,爱仅仅需要撤退。”[3]95这两种内在的努力促成了现代伦理对爱采取的两种策略:固定(fixing)和漂流(floating)。“固定”是将爱的关系从不稳定的、忽隐忽现的感情中解放出来,以确保——无论对方的情感发生什么——一方将继续从另一方的关注、关心和责任中获益;它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境地:在这种境地中,一方能继续获得而不需要付出更多,或者付出不超出对方所要求的。[3]98“固定”策略通过规则和惯例代替爱、同情以及个体的其他情感,以此来摆脱爱的模棱两可性带来的痛苦。
根据鲍曼的观点,伦理学上的“固定”策略的经典构思源自康德。康德将道德律令定义为普遍和抽象的、超越于个体情感冲动的一切理性的本质,它对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都是普适的。康德的伦理原则被其后的许多伦理学家所接受,从此,固定的策略逐渐形成:义务取代爱,规则取代个体情感与道德冲动。我们看到,爱由于自身的模棱两可而显得晦涩与困难重重,相比之下,作为规则的义务是清晰而毫不费力的,而义务在实践中不断被重复成为惯例。在爱本身令人烦恼的模棱两可和简单可重复的惯例之间,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惯例,用惯例化的义务代替爱。个体情感冲动具有的不稳定和复杂性,现代性的伦理立法者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点,因而试图用抽象的原则来代替这些不稳定的情感冲动,排斥或者消灭矛盾性,从而构建起伦理体系。
另一种逃离爱的矛盾性的策略是“漂流”。与“固定”一样,漂流同样源于现代性对矛盾性的拒绝。漂流“拒绝承认爱之中艰难的任务和努力,为了减少责任与付出,逃避爱的不安全,它通过减轻风险和允许在事情变得不能忍受之前脱离来平息爱的痛苦。”[3]104漂流采取的不是把爱固定住,而是逃离,它害怕责任的沉重或好奇心失去后的无聊,在爱的痛苦来临之前,赋予爱的双方随时逃离的自由。与“固定”相比,漂流走向的不是规则(统治),而是冷漠与自我关注的自恋。在这种模式中,爱的任何一方随时都可以从关系中脱离,从而结束爱。
这种以自由为核心的“漂流”状况,在吉登斯所描述的现代性的“纯粹关系”和“融汇之爱”中得到了描绘。“纯粹关系,它是指这么一种处境,在此,一种社会关系的达成没有外在的原因,它只是因为个人可以从与另一人的紧密联系中有所收获……。对大多数在性关系上‘循规蹈矩’的人们而言,爱曾经是通过婚姻而与性相联系;而现在,两个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地通过纯粹关系来实现。”而“婚姻关系正在日渐改弦易辙,变成一种纯粹关系形式。”[6]77相应地,“融汇之爱”则显得更加自由与主动,它“积极主动但又飘忽不定”[3]105,爱的双方各自作为平等独立的主体,交汇但并不寻求永恒与唯一,因为永恒与唯一意味着责任与牵连。与“固定”不同的是,“漂流”试图摆脱规则和束缚,以个体自由的名义,以双方各自的需要为出发点,建立和解除关系。
3.拯救还是死亡?
无论是康德的先天伦理规则,还是绝对的自由主义取向,它们以规则或自由取代矛盾性和责任,虽然缓解了爱的矛盾二元性带来的烦恼,最后却把真正的爱送进了坟墓。根本上,现代伦理将爱的矛盾性——他者的异质性——当作一个“问题”来解决,其实质是对陌生性和异质性的同化或排斥,以此获得主体的确定性或自由,即安全感或者无责任背负。可是,如前所述,爱的前提是作为异质性的“两个”而存在,它以异质性为生。一旦爱的关系中异质性伴随着的矛盾作为一个“课题”被解决,其结果就是爱的死亡。这就是鲍曼所说的“固定延长了爱的生命但是仅仅以幽灵盘旋在坟墓上的方式;漂流取消了稳定和不自由之间令人气愤的契约,但是却以阻止爱访问爱的充满快乐、危险和神秘的深度为代价。”[3]108-109在“固定“和”漂流”的 模式中,只 有规 则 与自由,没有原始的情感冲动与责任。这种建立在规则和自由之上的“爱”成为了一种典型的以主体为出发点的互惠关系,它已失去了伦理的品质。①关于平等与非对称,互惠与无条件的给与之间的政治和伦理的差异,在列维纳斯那里的基本路向是:平等互惠是政治性的,非对称的、无条件的给与是伦理性的。伦理体现为爱,政治体现为公平正义。爱为正义奠基;伦理为政治奠基。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伦理的爱死亡了。
三、列维纳斯:爱的非对称性和无限责任
1.外在性的进入
现代伦理是建立在启蒙之后所确立的理性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上的,在这种背景下,爱以一种平等、互惠、自由的姿态出现。在根本上,这种姿态源于现代性的主体性特征。从笛卡尔以来,知识的确定性就奠基在“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之上,康德的先验统觉的先天综合统一,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无不是寻求清晰性、明证性的主体。这是一个作为主体的“我”对世界认知和统筹的整体性的过程。处于整体性之外的模糊的情感冲动,以及陌生性要么被整合到这个清晰的整体中(被认知和理解),要么就是被彻底地排斥在外。
作为对西方传统“同一与差异”的伦理主题深刻反思的一个重要人物,后现代思想阵营中的一名重要旗手,列维纳斯试图打破西方整体性的暴力,将差异作为伦理的基础,突出在爱的伦理关系中他者的奠基性和优先性。这种努力立足于对意识的现象学考察:经过一个超越性的反思,意识发现自己是被奠基的。意识的内在性——胡塞尔理解为构造性的和先验的——发现自己已经是被建构的,意识在建构对象之初就已经被建构了。意识是在投入到已经在那儿的人的世界后浮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不与他者相遇,自我意识就不可能出现。与他者相遇的“回应”(作为责任的最原初的形式)唤醒了我的意识和良知,而后伦理才具有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鲍曼指出,后现代伦理是一种他者伦理,它“重新将他者作为邻居,作为与手、脑亲近之物纳入道德自我的核心,……重新恢复了亲近性自主的伦理意义;将他者重新塑造为伦理自我成为自身的进程中的决定性的角色。”[3]84这种他者伦理从外在性的视角出发对主体及其与他人的关系进行了一种新的观视:主体的发生基于他者的外在性,爱的关系首先不是以我为中心的主动性(占有),而是对他者的欢迎与回应(责任),伦理关系的起点是他者。
2.形而上学的欲望:欲望他者
在列维纳斯那里,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欲望,这种欲望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需求意义上的“欲望”,而是对整体性之外的绝对他者的不可被满足的意义上的欲望。真正的爱的对象是超出自身的一种绝对的外在性(他者),是不可被欲望者;换句话说,是被爱者身上的异质性,是不同于自身、并且永远不能为自身所把握的东西。在《整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将欲望(desire)和需求(need)作了区分:欲望的特征是不可满足性,它的本质是朝向不可见者(the In-visible)。在欲望中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欲望与不可满足性;超越与不可超越性共存。这种张力导致了它永远处于没完成的状态。而需求,则可以通过主体对需求物的占有而得到满足,一旦满足,需求也就完结了。形而上学的欲望不渴望回归,它朝向完全陌生的土地,绝对的他者,它是一个不能被满足的欲望。[2]33-34绝对的他者具有绝对的他性,这种他性不同于食物、住宅等需求物的他性;欲望的对象不是可以被满足的东西,而是绝对的他者外在性,是不可被主体(我)所占有的。形而上学的欲望是向无限的趋向,被欲求的无限可以支配欲望,但却不能以其显现而使欲望得到满足。相反,这种欲望不但不会得到满足,反而会不断强化。因此,欲望是在无限性面前无限的耐心与等待。也正是这种永远不可能完成的状态牵引和维系着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
在对列维纳斯的著名评论中,德里达指出:“欲望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指的则是将他者当作他者来尊重和认识,是意识应当禁止自己僭越的那种形而上伦理学的时刻。”“无论是理论意向性还是需要的情感性都不能穷尽欲望的运动:因为它们都以在同一整体性与一致性中自我完成、自我满足、自我满意的作为意义和目标。欲望则相反,它受到他者那种绝对不可还原的外在性的召唤,而且它必须无限度地与这个他者保持不切合性。欲望只与过度(démesure)相等。任何整体都无法在它上面合上口。因此,欲望的形而上学就是无限的隔离之形而上学。”“无限他者是不可见的……,无法企及者、不可见者就是至高无上者。……无论高度有多高,它总是可以企及的;而至高无上,不管怎样却比高度更高。任何高度的增加大概都不能衡量它。它既不属于空间,也不属于现世。”[7]156-157从德里达的阐释中,我们看到,作为形而上学的欲望的爱有着一种绝对的孤独性。爱与被爱者之间亲近性的尽头是对方身上遥不可及的外在性,是双方绝对的异质性,这是爱之中绝对的孤独境地。而按照列维纳斯的观点,这种个体绝对的分离状态,恰恰是超越性得以保持的基础。爱的欲望、爱与被爱者之间关系的伦理品质在这种孤独(外在性)的深处漫溢出来。
3.爱的非对称性
在对现代伦理“我与他人”关系的颠覆中,列维纳斯将曾被归属于自我的优先权给予了他人,将内在性让位于外在性。他指出:“主体间相互关系是一个非对称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他者负责,而不期待任何互惠。”[8]149也就是说,与他人的遭遇先于我的主体性的绽现,我始终是被命令和召唤的。我对他人的回应(责任)先于我对这种回应的计算与考量。这种非对称的关系的基础是他者的外在性。他者的外在性超越(高)于主体性,不能被我的意识所把握,超越于意向性和对象化行为;他者不是和我同等的另一个主体,相反,他者始终在我之外,超越于主体性这个层面。这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我与他者的相遇“不是可被概念化的关系。概念化就是用思想把自我和他者重新同一于整体性之中。因此,与整体性的断裂不能通过思想综合,不能通过介人一个术语使他者的他异性还原于自我之中。与整体性的断裂只能通过发现自我自身面对着一个拒绝被概念化的他者而实现。”[7]169在列维纳斯那里,他人的超越性构成了我和他的关系的基础,而这种超越性也决定了这种关系是非对称的。这种超越性与非对称性构成了伦理的高度的前提。于是,爱的关系不是基于两个对等的主体,不是基于理性和自由基础上的平等互惠,而是基于我和那个外在与我的他者的相遇以及随之而来的召唤和回应(责任)。
与“付出—回报”的对等交换模式相反,对于爱的任何一方而言,爱都是单向度的回应(负责),是无限的给予和耐心。这种非对称和无限的回应(责任)是一种自我让位、无己的伦理姿态。与克尔凯郭尔一样,列维纳斯认为“只有无私的(self-giving)爱才能使得人类成为人类。自我通过爱他人而找到自身,自我通过舍己而成为自身。”[9]这是一个从“为自己服务”到“无私”的转变,从“以我(主体内在性)为起点”到“以他人(外在性)为起点”的转变,它表现了真正的爱的伦理内涵。
4.责任先于自由
他者的外在性打破了主体绝对自由的幻象,为人的伦理性进行了一种新的定义。伦理关系的前提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他者外在性的欢迎和回应。“存在的外在性是道德自身。自由构成了我,但是与此同时,也保持着和外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防止存在的整体化。”[2]302外在性的进入使得自身性被打破,整体性的暴力出现裂口,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才成为可能。而在列维纳斯那里,外在性的进入通过与他人的相遇而达成,通过“面对面”(visàvis)的相遇,外在性揭示自身。他者的脸孔是一种脆弱和裸露,它以直接迫近的请求和命令召唤我的回应(response)(责任的最原初形式)。同时,绝对的他者从上面接近我,质疑我的占有(内在性),使得我的占有丧失。①这不是空间的“上面”,而是伦理形而上学的“善”、“至高者”,这个概念来自于柏拉图的“善的理念”(the idea of the good),在列维纳斯的文本中常用 “the Above”“the dimension of height”等表述,它体现了伦理的绝对性和非对称的品质。参见Totality and Infinity,p.171,p.34,p.86,p.215。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伦理的人的第一要义是欢迎他者,是回应,是放弃主体内在性和占有,而不是占有和自由。列维纳斯指出:“对他者的欢迎是去质问我的自由”[2]85,“如果我们把质问我的自由这样一种境地称为良知,那么对他者的欢迎就是良知。”[2]100这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作为伦理的人的“为他人而活”的基本内涵。在这种姿态下,自由才得以可能。“我是负责任的我,他是使我负责任的他,正是在这种他者也因此是我自己的意义的创造中,我的自由,我伦理的自由才形成。”[3]86对列维纳斯而言,自我在与他人面对面相遇时才成为自由的,因为自由不是别的,而是我对他人请求的回应,自由源于与他者的相遇。“存在并不是现成地被宣判为自由的,而是被邀请为自由的。自由 不 是 裸 露 的 。”[2]84
现代性伦理凸显主体性,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却忽略了作为自由的根基的责任——对他人的回应。结果导致了现代真正伦理性的缺失。列维纳斯看到了主体性发生之前的伦理事件,即他所说的“超越的形而上学事件——对他者的欢迎与好客。”[2]254对他者的欢迎和好客奠基了主体性,从而也孕育了真正的伦理品质。在列维纳斯那里,这种和外在性的关系的超越的形而上学事件并没有作为爱而被穷尽(事实上,在《整体与无限》全书中,这个超越的形而上学事件也构成了社会正义发生的基础),但是,真正的爱必定和与他者的对话的超越性相连。只有这样,爱才能是伦理的。责任比自由具有优先性和艰难性:责任的优先性在于与他者的遭遇这个事件先于主体性的发生;责任的艰难在于其无限性与永远无法完成的状态。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永远无法完成的责任,使得爱作为需要和欲望、内在性和外在性交织着的冒险得以持存。
四、结语:立法者抑或道德完美主义者?
从自我到他人、从内在性(主体性)到外在性、从同一性到异质性,在这个转向中,我们看到,列维纳斯的爱的伦理学试图在主体性、理性与自由之前,澄清爱的发源地——他者的外在性,探寻爱真正的伦理品质。如果说列维纳斯作为一个严格的现象学家,始终遵循着胡塞尔现象学提出的“回到事实本身”的基本原则,那么在列维纳斯的伦理学里,这个原则就体现为通过对主体性之前的原初伦理经验的现象学描述,从而回到使得伦理成为伦理的根基,回到伦理发生的那个境遇。伦理的根基是被爱者的外在性。基于这种外在性,爱才可能并且持续。
列维纳斯的爱的伦理是现代社会原始情感和责任缺失的背景下的一种回归。但是我们看到,在工具理性和自由话语仍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这种以主体性的让位和对他者负无限责任为出发点的伦理还很难实现。自由很艰难,但是比自由更艰难的是责任,是爱。真正的爱是一种自我的让位,是由“以自我为中心”走向“以他人为中心”,是列维纳斯所说的“成为他人的人质”。这个过程先于认知理解和对象化(把被爱者当作我认知和理解的对象),它是直接的但同时也是隐匿的。因此,爱并不是现成在手的,而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实现的。列维纳斯意义上的爱的伦理并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的准则和体系,但是它给我们提出了超越于伦理规则体系的基本的承诺与要求,那就是在他者面前无限的谦卑与责任;它所展示的是真正的伦理的根基,是作为伦理的人所应具有的最为根本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伦理是德里达所说的“伦理的伦理”。只有在与他者“脸对脸”的相遇,在保持他者的异质性的情况下,责任以其最原初的回应、“言语-回应”的形式产生[10],伦理以及作为伦理的人才可能产生。这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圣洁的圣 洁性”(the holiness of the holy)[11]4之 所 在 。 人 不 是现成的,而是在成为人的过程中。换言之,是“外在性”牵引着我们走向爱,走向伦理,走向伦理的人。
著名的列维纳斯研究专家西蒙·克里奇认为有两种伦理哲学家:立法者和伦理完美主义者。前者,如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他们提供详细的概念、规则和原则。后者,像列维纳斯和卡维尔,他们相信伦理必须建在一些基本的超越于正义的理论规则和社会制度的伦理规则的承诺或者命令的形式之上。[12]54如果我们认同对列维纳斯的这种定位,那么我们应注意到,列维纳斯要做的是揭示那先于现成给予的东西(对于伦理学而言,这些现成给予的东西就是伦理概念和规则)的人类原初的伦理经验,而正是这种经验构成了罗尔斯和哈贝马斯这类“立法者”工作的前提。
]
[1] Linnell Secomb.Philosophy and Love,From Plato to Popular Culture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
[2] 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M].trans.A.Lingis.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69.
[3] Zygmunt Bauman.Postmodern Ethics[M].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3.
[4]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 齐泽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M].陈永国,汪民安,等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8] Emmanuel Levinas.Ethics and Infinity: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pe Nemo[M].trans.Richard A.Cohen.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5.
[9] Thomas G Casey.Kierkegaard and Levinas on More Perfect Human Love[J].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2010,75,p.16.
[10] Jill Robbins.Visage,Figure:reading Levinas’s Totality and Infinity[J].Yale French Studies,1991,No.79,p.135.
[11] Derrida.Adieu To Emmanuel Levinas[M].trans.Pascale-Anne Brault,Michael Naa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2] Levinas in Jerusalem:Phenomenology,Ethics,Politics,Aesthetics [M ].Edited by Joelle Hansel,Springer,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