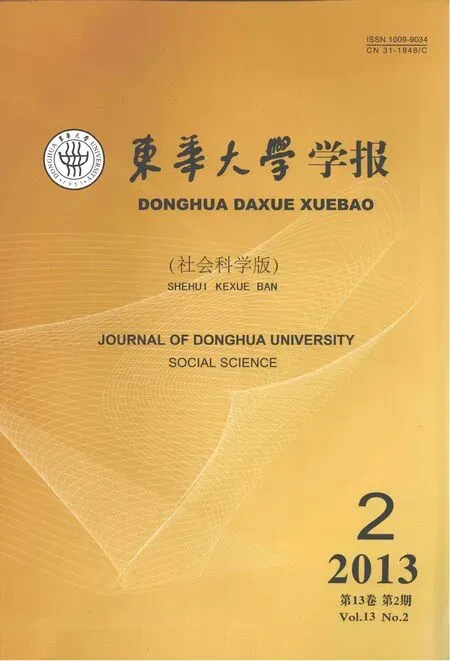女性话语权力在翻译中的争夺——以评析祝庆英所译《简·爱》中文译本为例
何渝婷
(东华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界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语言之外的文化因素,比如意识形态、政治或哲学等。性别,作为文化范畴内的一个影响因子,也为翻译研究增添新的视角作出了贡献。盛行于西方社会的女性主义思潮和运动也推动了翻译中性别研究的力度,标榜“为女性和译者正身,让她们获得地位和话语权”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同时,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再一次深入发展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明确指出话语即权力,于是要为女性夺得权力,要让译者赢得主体性,唯一的途径就是尽一切可能在翻译中争夺话语权。翻译也因此不再是一个关于语言转换的简单活动,而是运用语言争夺权力的政治场域。
一、福柯“话语权力”理论
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因其突出的权力学说对后世以及学术界影响深远。就连他理论上的对手,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哈贝马斯都承认:“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1]福柯思想的形成过程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他也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他们都热爱自由,热爱生命,并坚定地相信人的自我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人应该是发明自己,而非发现自己。
“话语权力”理论是福柯思想的核心。传统的话语是一种早已为人所熟知的语言学方面的概念。然而,福柯理论中的“话语”不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语言或言语,他认为“话语并非词汇与句子简单的组合,也不仅仅限于语法规则的控制,而是蕴含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2]话语在权力运行场中形成,同时受到来自社会和历史等条件的制约。它作为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权力的参与,总是处于一种流动对抗的状态。因此,随着权力的变化,话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此外,权力不是个人或群体可以独家占有的,不是一种规定性的制度或结构,没有人是它的拥有者。它也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多样性的复杂关系,是一个不断斗争、对立的过程。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争不到话语权的权力就不叫权力,话语的秩序决定权力的秩序,这就是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核心思想。[3]
换言之,话语就是权力。一方面,话语生产权力,它既可加强权力也可削弱权力;另一方面,权力也生产话语,权力的施展可以不断地创造新的话语。所以,权力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人们通过对话语的争夺来赋予自己权力,对权力的争夺实际就是通过争夺话语实现的。
二、话语权力、性别与翻译
对话语的争夺即是对权力的争夺,到底谁会去争夺话语,他/她争夺话语后真的获得想要的权力了吗?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她采用何种方式去争夺话语,其手段是合理正当还是霸道无耻?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或者说是一种通过争夺话语来获得权力的典范。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不仅仅是拜翻译界文化转向的东风所赐,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三次女性主义运动凸显出的性别问题也是促使该理论形成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女性主义运动为我们揭示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写照: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女性没有身份和地位可言,她们总是隶属于男性,被视为“第二性”或“他者”;她们生活在男性的话语世界中,没有资格触碰语言,更加不可能通过语言发出女性的声音。语言是专门为男性服务的机器,女性则一直被迫接受父权制影响的思想价值体系,没有自己的话语空间,只是一味地重复并复制男性的话语。
性别问题的提出绝非仅仅让社会看到女性所受的不公及歧视,更是旨在唤醒女性对于自我身份重建和对社会平等地位争夺的意识。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指导,该理论认为话语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而权力作为一种支配的力量,它影响并控制着话语的运动,决定着话语主体是否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女性对于话语的缺失和不在场,正是她们之所以得不到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双重认同的根本原因。所以,20世纪70年代,一个耳熟能详的呼声:“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4]女性只有获得了语言的解放,获得了女性自己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同时,让语言为女性说话,让女性的声音被世人所听见,这样才能动摇父权制中心主义的根基,才能建构女性的政治权利和身份。
通过“话语权力”理论,暂时明确了争夺权利的方向即争夺语言,女性的首要任务便是考虑如何争夺语言,或在什么场域中去争夺语言。翻译,作为一种语言转换的机制,与语言及语言的运用密切相关。那么,女性是否可以尝试在翻译这个场域中实现对话语的争夺,从而最终实现对权力的争夺呢?翻译本身的政治性为女性在翻译中争夺话语权力提供了可能:翻译本来就不是一个只关乎于语言的活动,而更是一种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它是社会、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共同参与的行为。因此,译者可以借助翻译这个平台突出他的性别和文化身份,以便在翻译中实现对话语权的争夺。
三、《简·爱》译本中超越原作的女性反抗和话语权争夺
《简·爱》因其独具风格的女性主义色彩以及恰如其分彰显出的女性主义思想,不仅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广泛认可,同时也激起了中国学者对它的普遍研究,大量的中文译本的产生便可证明其巨大的影响力。本文旨在重点欣赏祝庆英译者的中文译本,同时列举黄源深和吴钧燮两位译者的翻译作品,试图通过对比研究的方式来窥探不同译者在处理具有强烈女性主义色彩的原文时所采用的不同翻译手段,验证女性译者是否在此方面更加理解和体会原文的风格,从而在翻译中更能有效还原作者的思想和主张。文章选择祝庆英的译本主要考虑到该译者与原作者勃朗特一样都身为女性,并且都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思想和意识,都可以称作是女性主义的拥护者。鉴于祝庆英译者和原作者勃朗特思想和情感间的交融性,文章大胆假设:若选取原文中极具女性主义色彩和代表勃朗特女性主义思想的内容,借此参考祝庆英的中文译本,便可窥见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译者如何在翻译中保留原文的特色,以及如何让女性在翻译中实现对话语和权力的争夺。为此,文章试从原文中表现简·爱在不同人生阶段所遭遇的困境和发起的反抗内容中取材,为文章的论证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一)盖兹海德府中的反抗
盖兹海德府给年幼的简·爱留下了可怕的回忆,她在本可以感受家庭温暖的舅妈家,经历的却是一个孩子承受不起的欺压和侮辱。在那里,她与所有的人不合,比所有人的地位都低下。那家的儿子约翰·里德时常用言语或行动挑起与她的战斗,她也就慢慢地习惯于服从他的责骂。但终有一天,她被约翰狠狠扔过来的书打在身上,跌倒后,头又撞在门上,这时的恐惧和其他情感已经超出了忍耐的最高点,她终于反抗了,大声地发出强硬的反抗声。
例1 “Wicked and cruel boy!”I said.“You are like a murderer— you are like a slave-driver— you are like the Roman emperors!”[6]
祝译:“你这男孩真是又恶毒又残酷!”我说。“你像个杀人犯——你像个虐待奴隶的人——你像罗马的皇帝!”[5]
这是简·爱不堪凌辱后发出的首次激烈反抗。从她内心深处发出的强烈呼声不仅让她自己惊讶,更是吓坏了残暴的约翰。译者绝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让女性发出呼声和行使话语权的绝好机会,因此在译介过程中必会谨慎处理,以达到不仅完全还原原作思想,而且是更加突出、甚至超越原作思想的效果。原文“wicked and cruel boy”,在祝译本中“你这男孩真是又恶毒又残酷”,“真是”二字带有很强烈的肯定意味,刻意加重了译者对约翰的憎恨;“又……又……”的结构也显著增加了约翰的可恶程度。对于此句,其他的一些译者有的译成“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7],也有的译成“你这残酷的坏孩子!”[8]。对比祝庆英的翻译,黄、吴二人的译法显得不很痛快,情感也不很强烈。祝的中译本比原作更加表现对权势一方的憎恶和不满,通过富有渲染力的字眼来加强情感,译本成功表现了女性向权势提出的挑战和蔑视。
此外,原文“You are like a slave-driver”,祝译为“你像个虐待奴隶的人”。“slave-driver”按其字面的本意来讲,仅仅指代驱赶奴隶的那类人。或者,如其他译者所译,“你像是个监工头”[8],或“像个奴隶监工”[7]。很显然,“监工头”远远不如祝译“虐待奴隶的人”那么强烈。祝的译法不仅涵盖了权势对奴隶的监管、控制,更加希望突出的是对奴隶的虐待和欺辱。祝的译法帮助体现了在约翰虐待下的简·爱的悲惨童年,也增强了简·爱的那种憎恶、厌恶和仇视权贵的态度。祝的译作再一次超越了原作“驱赶奴隶的人”及其他中文译本“(奴隶的)监工(头)”的情感程度,再一次让女性的呼声和诉求在译作中找到了实现的良机,译作不再是原作的复写,而是突出女性主义色彩的新创作。
(二)劳渥德学校中的反抗
在摆脱了盖兹海德府后,怀着满心希望的简·爱来到了劳渥德义塾。在学校中,简·爱努力想博得他人的喜爱和同情,海伦·彭斯——一个时常受老师责骂和欺辱的女孩与简·爱做了朋友,两颗寂寞、孤独的心紧靠在一起,相互喜欢和依赖。这一阶段中,透过彭斯的凄惨遭遇,简·爱直截了当地表露了渴求平等、向往自由的反抗精神,每一句呼声都是对权威的挑战。作为译者的祝庆英势必会抓住这个良机,力图译出原作中的女性主义反抗精神,甚至有意增强那种精神的表现力度。
例2 “And if I were in your place I should dislike her;I should resist her;if she struck me with that rod,I should get it from her hand;I should break it under her nose.”[6]
祝译:“我要是换了你,我就讨厌她;我就向她反抗;她要是用那个教鞭打我,我就把它从她手里夺过来,当着她的面把它折断。”[5]
原文中的“should”在祝庆英的译本中表现为“就”,而其他的译者则译成“我会讨厌她,我会抵制。……我会从她手里夺过来,……”[7],或者“我会讨厌她,我会拒绝她。……我会从她手里夺过来,我会当着她的面把它折断。”[8]吴、黄两位译者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会”字来翻译原文里的“should”。就“should”本身的意思来看,它可以表示:(1)(常用于纠正别人)应当、应该;(2)(提出或征询建议)该、可以;(3)(表示预期)应该会;(4)本当、本应;(5)(与I/We连用代替would,表示虚拟结果)就、将。从整个句子的语法层面来看,祝译的“就”较其他译者的“会”更合适,因为这是简·爱假想自己是彭斯而发出的反抗宣言,“should”表示一种虚拟的结果。另外,从感情色彩方面来看,祝的译法是更贴近原作者意图的做法,女性主义译者对表现女性反抗的言辞更加关注和重视,在译介过程中会格外突出女性的反抗精神。“就”字坚定了女性反抗权威和权贵的决心,表明一旦简·爱受到了类似于彭斯一样的欺辱,她必会反抗和斗争的态度和心愿。相反,“会”字多少带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不肯定的语气,她可能会反抗,也可能畏缩,所以无法表现出原作的内涵和作者的心境。
(三)桑菲尔德府中的反抗
桑菲尔德府中的经历对简·爱一生来说意义非凡。简·爱在此获得了新工作,尽管这份家教的工作在当时的社会被认为很卑微,但对于她来说却是崭新生活的开始。简·爱在此也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和他人的尊重,不会再受里德太太、约翰·里德、布洛克尔赫斯特等人的欺辱,现在的她可以一边努力工作、一边享受得之不易的自由。更值得一提的是,简·爱在此尝到了爱情的滋味,虽然一波三折,但这份爱最终还是结出了让人欣慰的果实。简·爱从最初的抵触罗切斯特,到之后渐渐接受并爱上这个人,她的内心实际经历了复杂的情感变化。一贯被贴上“穷酸、相貌平平、矮小、地位低下”标签的简·爱在受到男性关注后,显得又激动又惊讶,而且对这一切都感到难以置信。缺乏自信和勇气的她更是经受不起外界任何因素的挑衅,但现实偏偏安排了英格拉姆小姐这个插曲。面对比自己漂亮和富有的竞争对手,简·爱感到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为了赢得爱情,她选择了直面困难,选择了反抗权势。发生在桑菲尔德府中的反抗,让我们有幸目睹了简·爱对爱情的执着和热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简·爱。原文中让读者印象最深的是简·爱看到罗切斯特要娶英格拉姆为妻,而又想把自己留在他身边的时候,怒气冲冲地作了一通要求罗切斯特把她放在平等地位的大胆宣言。简·爱用铿锵有力的说辞,反抗爱情中的不公,所做一切只为维护自己的尊严。
例3 “Do you think I can stay to become nothing to you?Do you think I am an automaton?— a machine without feelings?And can bear to have my morsel of bread snatched from my lips,and my drop of living water dashed from my cup?Do you think,because I am poor,obscure,plain,and little,I am soulless and heartless?You think wrong!—I have as much soul as you,—and full as much heart!And if God had gifted me with some beauty,and much wealth,I should have made it as hard for you to leave me,as it is now for me to leave you.I am not talking to you now through the medium of custom,conventionalities,or even of mortal flesh:—it is my spirit that addresses your spirit;just as if both had passed through the grave,and we stood at God's feet,equal,—as we are!”[6]
祝译:“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你觉得无足轻重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能让我的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让我的一滴活水从我杯子里泼掉吗?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5]
原文“And can bear to have my morsel of bread snatched from my lips,and my drop of living water dashed from my cup?”一句的翻译在大多数译者的笔下可能很容易表现为一种被动的感觉。例如,有译者为突出“bear”(忍受)一词的意思,译为“能受得了别人把我仅有的一小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把仅有的一滴活水从我的杯子里泼掉吗?”[8],或译为“能够忍受别人把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把一滴生命之水从我杯子里泼掉?”[7]。从翻译忠实观的角度来看,吴、黄二人的译法似乎更加贴近原文的意思,他们忠实地译出了“bear”一词的意义,并保留了原作的风貌。然而,女性主义译者却回避了像“忍受”、“容忍”、“受得了别人”等这样一些可能置女性于底层的词汇。她们希望通过语言改变妇女的地位,因此在翻译中经常用主动替代被动,时常有意识地通过改变原文以实现为女性争夺话语权力的目的。所以,祝的翻译只译出“能让我……从……,让我……从……?”,她显然是在刻意避免指出“一口面包”和“一滴活水”到底被谁抢走的问题,也避免去表现简·爱会因此变得容忍别人的心理状态。女性主义的翻译干预策略成功地维护了原作的女性主义精神,也突出了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
其次,原文“—I have as much soul as you,—and full as much heart!”一句在其他译者的笔下是:“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8],或“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7]。吴均燮的译法只能说明简·爱也有灵魂和一颗心,但这个灵魂及这颗心与罗切斯特的灵魂及他的心有无关系呢?似乎读者很难在其中推敲得出来。黄源深的译法则较好地把简·爱的灵魂及心与罗切斯特的联系在一起,读者能获得“原来他们二人有一样丰富的心灵和一样充实的心胸”的信息,而且黄译出了“much soul”与“full heart”的意味,看起来与原文的意义和思想很贴切。然而,祝的译法却更加让人感动和欣喜,她的译法不仅表达了简·爱与罗切斯特都有一颗心及一个灵魂,还强调了它们“完全一样”的性质。特别在后半句的翻译中,祝有意增添“完全”二字用以强调一致性,增强了简·爱在作这番陈述时的强烈情感,也表现了简·爱对平等的渴求与向往。
最后,原文“...equal,—as we are!”在其他译者笔下分别为:“彼此平等,——就像我们本来就是的那样!”[8],“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7]对于此句的译法,可能大多数译者都会采用类似于吴、黄二人的译法,规规矩矩地译出原文中“—as we are!”即可,很少有译者会在“as we are”的翻译上花心思。但作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祝庆英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表现简·爱争取平等,反抗不公的机会,她有意地将其译为“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相比之下,吴、黄二人的译法显得既不明确也比较苍白无力,尽管想要表明“他们本来就是平等的‘地位’”,但读者无法体会出“他们本来是怎么样”的情况。祝的译法就比较直截了当,一语道破原作的意思和作者的意图,读者立刻就能明白原作想要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简·爱与罗切斯特在根本上是拥有同样的地位和尊严”的观点。祝的译法可能在字面上显得不很贴近原作,但从女性主义翻译观来看,这正是女性为了在翻译中获得话语权力的尝试,她们抓住每一个缝隙,把女性追求平等和自由的精神渗透进读者的心中。
四、结语
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指导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第一次认识到了权利与话语之间的联系,权利即话语,对话语的争夺确能实现对权力的争夺。女性唯有利用语言才能脱离父权制及夫权制的摆布和控制,才能不受男性话语的束缚,才能逃离那个黑暗的世界;女性唯有利用语言才能实现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认可,实现女性话语空间的构建,以及实现女性权利的争夺。夏洛蒂在《简·爱》中塑造的一个独立坚强、敢于反抗的女性形象简·爱,通过祝庆英的翻译让读者见识了更加富有女性主义精神的简·爱,此举不仅还原了作者和原作的女性主义色彩,也彰显了译者自己的女性主义主张,最终实现了女性话语权力在翻译中的争夺。
[1]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
[2]刘杰,张迎肖,马宏.博弈——论翻译中的性别话语权力[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9,11(1):58-61.
[3]王蜜.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及其对翻译的镜鉴[J].黑河学院学报,2012,3(1):100-103.
[4]Simon,Sherry.GenderinTranslation[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6:8.
[5]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6,60,301.
[6]Bronte,Charlotte.JaneEyre[M].New York: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1983:5,55,271.
[7]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7,7,53,252,252,252.
[8]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吴钧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6,55,270,270,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