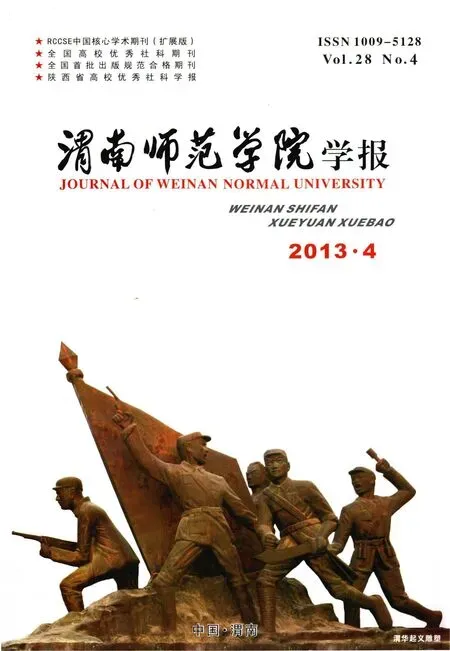浅析鲁迅短篇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
李联现
(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推动跨文化交际的发展。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方面。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而且是文化的转换,因此,在将语言信息翻译成目的语时,如何克服文化障碍成了翻译中的一个中心问题。[1]126不同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审美观念等,使得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积淀了独一无二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文化负载词反映出来。如何翻译文化负载词,会直接影响翻译的效果。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尤其如此。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以深刻的道德启迪、辛辣的讽刺和洋溢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而独领中国当代文学。频繁使用文化负载词构成了鲁迅短篇小说的一个特征。如何将这些词语和表达方式从汉语翻译成英语,将辉煌的汉语文化介绍给英语读者,促进相互理解和交流,是每个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要将这些文化负载词翻译好是跨文化交际和汉英翻译的难点之一,也是最大的障碍之一。
一、文化负载词的分类
E.A.Nida说过,“作为翻译者,如果想要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所作为,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五种亚文化类型:(1)生态文化;(2)语言文化;(3)宗教文化;(4)物质文化;(5)社会文化”[2]98。参考Nida的分类我们可以把文化负载词分为五类: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语言文化负载词。下面就鲁迅短篇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作以分析。
二、案例分析
1.生态文化负载词
由于明显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人们对自然的认知不同,这导致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生态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反映某一社会群体生活场所的气候、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的特征的词。
例1,这是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的如同六月里喝了雪水。(《阿 Q 正传》)[3]48
六月里喝了雪水(drinking snow-cold water in June):因为中国在北半球,夏天正处于六、七、八月,天气非常炎热。此时喝雪一样凉的水一定非常享受。中国人用此词语来表达快乐时的放松和高兴。而另一方面,一些位于南半球的国家六、七、八月是冬天。要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这种氛围中的感受,译者要么解释清楚,要么把这句话改成“12月喝了雪水(drinking snow-cold water in December)”或诸如此类。
2.物质文化负载词
这类词反映的是某一语言群体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的特征。通常来说,这些词主要是食物、医药、化妆品等。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能找到它们的对应物。汉语物质文化负载词在鲁迅小说中很多,这些词包含了特别的物质信息,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
例2,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鼓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 Q正喝了两碗黄酒。(《阿 Q 正传》)[3]47
黄酒(rice wine):即米酒,一种中国文化中常见的酒,但对外国读者来说可能是理解上的障碍。因为西方的气候和天气条件最适宜种葡萄,他们对葡萄酒很了解,但对其他东西酿的酒缺乏了解。中国的米酒是稻米所酿,而非西方的酒是以蒸馏的方式提取。品质上的差别反映在颜色上是米黄对褐色。在翻译目的语读者不熟悉的信息时最好加上额外的解释。
例3,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去进自由党。(《阿 Q 正传》)[3]49
黄伞格(written in a way that has the shape of a yellow umbrella):旧时的一种书信格式,都用骈体,在八行书上每行都有颂扬或表示敬意的语句,这些语句都跳行抬头写,因而每行都不写到底,只有中间一行写受信人的名号,比别行抬高一格,字又特别多,一直写到底,矗立于两旁短行当中,像旧时官吏仪仗中的一柄黄伞,因此而得名。当然,西方人对此格式可能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原文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英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因此,相对详尽的解释也是必须的。
3.社会文化负载词
这种词汇反映某一社会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社会生活、历史背景和一个国家或种族的行为方式。社会文化负载词在鲁迅短篇小说中构成了文化负载词相当大的一部分。
例4和5,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祝福》)[3]108
理学(The seek for the way things develops by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这里是指古代中国学者为寻求事物发展的方法而进行的研究,而理学对西方学者来说是他们一直追寻的作为人应有的根本的思想状态。不同的研究目的,造成了很多的误解。
本家(the same-family-named people):在中国,许多姓从中国文化起始就经过了许多代人的传承,因此,中国人认为同姓的人就如同兄弟姐妹一样。在这种信念的背景下,一些中国人就与同姓的人建立起关系作为将来使用的资源。相反,西方人对同姓并不如此看重,因为许多西方的姓源于聚居地和职业等,与血缘毫无关系。
例6,出门便是八抬大桥,还说不阔?(《故乡》)[3]42
八抬大轿(a sedan carried by eight people):在古代中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常坐轿子在城里出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轿子也变得更大而且装饰得更漂亮了,而轿子的主人也用轿子来表明自己的财富和权势。衡量轿子的标准也成了“越大越好”。因为大轿子需要更多的人来抬,因此抬轿子的人数也成了衡量的标准。小轿子常由四人抬,简称“四人小轿”,大轿子要八个人来抬,此所谓“八抬大轿”。高标准的东西应该被高层次的人来使用,这种思想在西方也是存在的。但在翻译作品中需要额外的解释以表达他们所掩盖的真象。
例7,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阿 Q 正传》)[3]53
秀才(certified students):正如古代中国许多用于学生的头衔一样,这个词西方人很少知道或了解。这类头衔用于古代中国的国考中。从低到高依次是:秀才—举人—贡仕—进仕。在公布皇帝的考核结果时,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在翻译此类词时,译者一定要给予解释。
例8,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实终日坐着一位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故乡》)[3]43
西施(the most beautiful woman):中国文学中的一个著名人物,她会让中国读者想起最美丽的女人。“西施”是春秋时期越国国王当作礼物送给吴国国王的美女。此后,她成了美丽的象征。在鲁迅的小说中,他把杨夫人看成了西施一样的美女。然而,残酷的生活使她从一位美女变成了丑陋而粗俗的一个女人。通过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比,小说的主题被加深和突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人性的消失和对美好事物的渴望。
例9,阿Q奔入舂米场,一个人站着,还觉得指头痛,还记得“忘八蛋”,因为这句话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阿 Q 正传》)[3]44
王(忘)八蛋(turtle spawn):这是中国人常用的粗鲁的语言之一。从字面讲,它是指“乌龟蛋”,这无论是在汉文化中还是西方文化中都没有什么蕴含的意义。它之所以有粗鲁之意,是因为这个词是由“忘八端”而来,意思是指一个放弃了八种道德准则的人,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西方,”Shame on you”指这样的意思,但在翻译中,如果译者要保持文章的原味,解释是必要的。
例10,他比先前并没什么大变化,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祝福》)[3]108
胖了(being plump):许多西方人认为,变胖是有消极意义的,因为在西方文化中追求的是苗条和漂亮。然而,中国人认为胖是肯定词,有积极意义。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许多人生活在贫穷状态,甚至食不果腹。从此意义上讲,变胖表明吃得好,生活富足,被认为是好的迹象。在翻译此类物质文化负载词时,应添加一些解释信息,如“在富足的生活中变胖”或“享受如此富足的生活以致变胖了”。
例11,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咒骂。(《阿 Q 正传》)[3]53
鬼子(invaders):这个词首次出现是用来指19世纪末的日本侵略者。在那时,中国很贫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受害者。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个日本代表说了一句话让中国代表来对: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举戈独战。意思是说日本等八个强国会继续压迫中国,而中国永远不会以孱弱的力量击败他们。此时,中国代表也回敬了很好的一句话:倭委人,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意思是说日本只不过是一恶鬼,很容易被中国擒获、驯服。此后,“鬼子”一词被用来指那些入侵者。[4]105
例12,“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阿 Q 正传》)[3]54
断子绝孙(no offspring):这个成语是汉语中的诅咒语,但常被有教养的人使用。对西方人而言,诅咒常是针对那些该诅咒的人或事本身,但在汉文化中,诅咒的对象往往不是事物或人本身,而是那些诅咒对象最爱的人或事物,如父母,孩子等。这样,诅咒一个修养很差或行为恶劣的人,中国人会谴责他的父母没教给他好的行为方式,或希望他没有后代,没人继承他低俗的本性。当翻译这种带有西方读者不熟悉的文化蕴含时,在文中或注释中,解释是很有必要的。
4.宗教文化负载词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了解一种文化,了解其宗教是必不可少的。宗教文化负载词是宗教信仰特征的反映,是一定语言社团传统特征的反应。中国人与西方人巨大的宗教信仰差异使得西方读者在理解汉语宗教文化负载词时困难重重。
例13,说是“外传”,“内传”在哪里呢?徜用“内传”,阿 Q又绝不是神仙。(《阿Q 正传》)[3]51
神仙(God):在西方文化中,掌控他们生死的神灵只有上帝,但在中国,这个词指的是那些生活在天堂,拥有超自然能力和永恒生命的人。根据道教的说法“上帝/神灵是指那些通过努力培养而能预见事物发生的方法的人。然而,在基督教文化中,人们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们会把赎罪作为其一生的目标,以便在其死后能升入天堂而不是遭到惩罚而进入地狱。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使得没有中国神话和文化知识的读者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上帝”真正指什么。
例14,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谷祠里。(《阿Q 正传》)[3]50
祠堂(土谷祠)(church):在西方,人们所能看到的与宗教关系最密切的建筑是教堂,人们在这里祈求上帝的保佑。但在中国,人们崇拜很多的神仙。人们可以见到不同风格的用来祭拜的庙宇等建筑物。庙宇在南美的玛雅文化中用来祭拜上帝,在中国也用来祭拜土地神和五谷神。在翻译时这可能会给读者一种印象——庙宇与土地或者谷物有关系。这种想象进而演绎成人们期望土地肥沃和粮食的好收成,这与中国宗教文化的意义很相近。这样就会更加有利于读者通过获得对原词的想象而了解中国文化的特别部分,这也是“外化”所需要的。
5.语言文化负载词
这类词是对某一语言社团语言的语音、语法及构成特点的反映。这类文化负载词最重要的特点是其所产生的语音和视觉效果。鲁迅短篇小说中的这类文化负载词说明了这样的特点。
例15,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孔乙己》)[3]15
之乎者也:这四个字是古代中国人,特别是学者们,常用于口语中的助词,在写作中也常见。然而,古汉语对当时的普通百姓而言有点难。因为他们没接受过多少教育,故而包含这些词语的文章或俗语被认为容易产生含混意义。更甚者是,一些所谓的学者,他们不学无术,为掩盖自己的无知也用此类字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开始用“之乎者也”来指那些不合格的学者或说话人,因为他们重形式胜于内容。
例16,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阿 Q 正传》)[3]50
讳(avoid speaking out any character(s)contained in the names of ancestors,emperors):为了表示对祖先、皇帝的尊敬,中国人会避免说出与其姓名有关的字或音,而用相近的意思表达或代替。这有点像西方人不叫他们父母的名字,但区别在于西方人只是不叫名字本身。比如,如果一位中国父母的名字中有“炎”字,意思是大火,其后代在遇到这个字时不说“炎”,而用“火”来代替。在小说中,鲁迅有讽刺意味的挑选了阿Q,一个无家可归,穷困潦倒的人物来用“讳”字,表明他的精神胜利。他想成为上流社会之一员,但始终不能如愿,他就开始学上流社会的一些说话和行事方式,以达自重之目的。这种自欺的行为就是著名的阿Q精神胜利法。
例17,“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阿 Q 正传》)[3]53
癞皮狗(People who like to lick other’s boots,or those who would give up all principles simply for some material comfort):这个词的跨文化因素在于中西方人对狗的不同的态度。西方人把狗看作友善和忠诚的象征,把狗当家庭成员一样对待,与狗分享他们的情感。而在汉文化中,狗带有贬义的意思。被认为是逢迎巴结之徒,为了物质享受而放弃原则的人。正因为如此,狗在汉文化中受到人们的鄙视。
例18,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的飘飘然了。(《阿 Q 正传》)[3]54
而立(The age at which people should be independent)、不惑(The year people reached and should be with little doubt)等表示年龄的俗语,这些俗语都出于《论语》一书。这是一本古代教育中国年轻人如何在成年后自立于社会的极其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包含这些俗语的句子频繁出现,他们就变成了年龄的代名词:如,而立,30岁,指人应该独立的年龄;不惑,40岁,表示人到了做事不再困惑的年龄。因为西方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论语》,更不用说内容了。因此在翻译时一定要对这些词做以解释。
三、结语
从分析鲁迅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可以看出,翻译过程涉及到多元文化,这就要求译者对文化因素更加重视。好的译者不仅要了解母语文化,也要了解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5]136。只有这样在翻译时才能对这些文化负载词进行必要的解释或说明,以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更好地了解原作的真正意义,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1]Hsien-yi,Gladys Yang.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3rd)[M].Pek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2.
[2]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Education Press,1993.
[3]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
[4]王宇.文化翻译与经简阐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