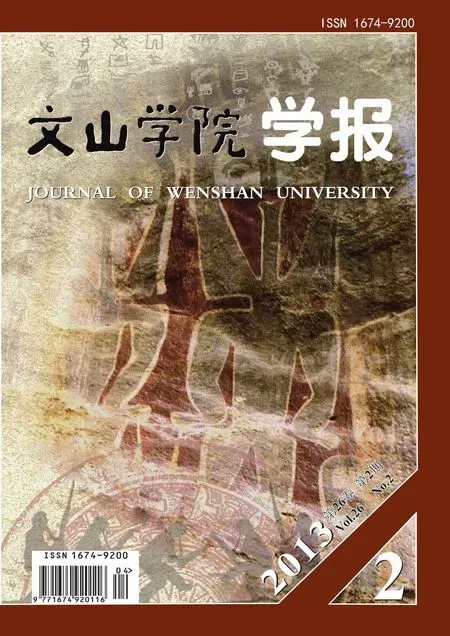清初流放贬谪诗与文人心态
李彩霞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清初文化氛围紧张,文人士子及各级官员被贬频繁。据李兴盛《东北流人史》统计,清朝流放东北的有150 万人,清初百余年就有数十万之众。其中仅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康熙七年(1668年)短短23年间,流放尚阳堡的就达5814人[1]。刘献廷《广阳杂记》“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一、进入官场前所受的重重打击
顺治末年,清政府为了制裁不与当局合作的江南士大夫,相继以拖欠赋税、科场舞弊为借口,制造了“科场案”“奏销案”“哭庙案”“通海案”等案件,对江南乡坤士子给予了一次次沉重打压。
1.“科场案”与文字狱
清初发生了多起规模很大的科场舞弊案。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天举行乡试,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告发陆其贤等多名考生贿赂考官,科场舞弊。结果主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7人被斩首,被录取的举人陆庆曾、孙旸、张恂、张天植、张绣虎等人及其家属流放尚阳堡。同年江南亦发生科场案,主考官方犹、副主考钱开宗等20人亦因“纳贿作弊”被处死,考生吴兆骞、方章钺及数百名家眷流徙尚阳堡,家产籍没。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顺天再次发生乡试舞弊案,翰林院编修严虞惇因子侄连售,主考李蟠、副主考姜宸英皆同年被罢官。
清初文字狱之盛是历史上空前的,康熙朝的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开清初文字狱之先河。洪升好友陆寅全家受《明史》案牵连,兄长死亡,父亲陆圻出狱后愤而出家,不知所终,陆寅也因寻找父亲积劳呕血而死。雍正时的“吕留良诗文案”也因为强调“华夷之辨”,使死者戮尸,生者遭凌迟、绞杀或流放,牵连数百人。
吴兆骞乃江南著名才子,与华亭彭师度、宜兴陈维崧有“江左三凤凰”之称,又与兄兆宽、兆宫并称“延陵三凤”,当他罹罪流放时举国震惊。吴伟业、徐乾学、陈维崧、宋荦、王摅等人均为他题诗述怀。23年后他被赦南还,徐乾学于宴会即席有《喜吴汉槎南还》诗,和者多至数十百人。王士禛诗句“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还”最为人传诵。
李蟠流放东北,3年后证实为诬告蒙赐归里,此后终生未做官,《户部山探梅》《白燕十首》等诗抒发了其积蓄已久的哀怨之情。姜宸英曾为“江南三布衣”之一,70 岁才出仕考中进士,也同时被劾下狱,病死狱中,友人陈苌有《挽姜西溟》悼之。陈维崧《刘逸民隐如》讲述了与吴兆骞一同遣戍尚阳堡的刘隐如,到边地后遭遇窃贼,夫妇二人同时遇害,令人深为痛惜。许虬《折杨柳歌》“居辽四十年,生儿十岁许。偶听故乡音,问爷此何语?”写无辜文人身罹“科场案”和文字狱而谪居东北40年,在流放地出生的儿子听不懂家乡话,还问父亲是何语言。
2.“江南三大案”
清初在江南发生的“奏销案”“哭庙案”和“通海案”,统称为“江南三大案”。清代各州县每年将钱粮征收的实数报部奏闻,叫做“奏销”。顺治十五年(1658年),朝廷派专人清理赋税缴纳情况,拖欠者一概加上“抗粮”罪名,革去功名或官职。在这过程中,催缴钱粮的县令隶卒们逼迫追呼,恶如狼犬,名门望族多遭威逼勒索而破产,许多生员因拖欠田赋遭到鞭笞毒打,甚至毙命杖下。
“奏销”案牵连广泛,大批官员、文人甚至普通百姓被捕入狱。江南地区以欠赋而遭黜革的乡绅士子达到1 万余名。文化界许多重要人物如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王鸿绪等全被罗织在内,秦松龄被削籍,韩菼几被迫自杀。翁叔元因无力交税出逃十余年,妻儿在家乡靠野菜米糠度日。叶方蔼因欠税银一文被革去“探花”之名,民间传扬“探花不值一文钱”。钱谦益族孙钱陆灿因“奏销案”被革除举人功名后,客居金陵、武进30 余年,以授徒为业,布衣终身。董含亦被革去进士之名,此后愤恨终身,再未出仕,历50 余年著成著名史料笔记《三冈识略》。董含之弟,刚刚考中举人的董俞亦被除名,遂弃举业,终身灌园锄菜,啸歌自得,曾作《赠西陵吴兴公》诗云:“昔人事业随流水,高歌击筑浮云徂。”
彭孙遹本已考中进士,授官中书舍人,此时也受族人牵连而遭革职。此后十余年遍游天下,历尽漂泊艰辛。现实的无奈和理想的破灭,使他时刻心怀隐逸之思,《登湖口县城》“何当便作移家计,终卧沧洲寄此生”等诗句,流露出了其空寂落寞的情调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这种归隐之思,逐渐成为其晚年诗作的重要主题。《送张毅文归郁洲山》“明年决计脱羁鞅,青鞋布袜与子偕”,《月夜舟中宿》“渺渺沧洲何处是,忽听渔唱起孤篷”等无不是心声的吐露。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进入长江,与张煌言会师,相继占领丹徒、焦山、瓜州,后郑成功兵败,清廷以“通海”为名,下令追查。江苏金坛官吏与土豪劣绅乘机勾结,嫁祸仗义执言的正直诸生,史称“通海案”。在这起冤案中,冯征元、王明试、李铭常等无辜士人65人被砍头,魏阱、钱缵曾、潘廷聪、祁班孙等被遣戍宁古塔,祁理孙、陈三岛忧愤抑郁而死。“(金坛)海寇一案,屠戮灭门,流徙遣戍不止千余人。”[2](P500)两年后,即顺治十八年(1663年),吴县知县任维初追逼交纳钱粮赋税,苏州百余名秀才乘“哭庙”悼念顺治之际举行集会,反抗贪官横征暴敛。结果18人以“谋反罪”处斩,其中就有著名才子金圣叹,酿成著名的“哭庙案”。
二、仕进道路上的艰难苦恨
顺治初至乾隆初年的文人士子们在踏入官场之前就经历了科场案、抗粮案、明史案等重重打击,以致身心俱疲。进入官场后,仍然是动辄得咎,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过各种流放贬谪。
1.或因直言进谏,或受亲友、上司牵连
文人在进入官场之后,往往因直言进谏,或受亲友、上司牵连而获罪。兵科给事中季开生直言敢谏,以仗言著称,顺治十二年(1655年)因上疏谏点选秀女一事,被流放尚阳堡,5年后死于戍所,年仅33 岁。严沆、施闰章等分别作诗对他表示同情。张贞生考中进土后累迁至侍讲学士,“时议遣大臣巡方,贞生言徒扰百姓,无益察吏安民,当责成督抚。以出位言事,降二级,然卒罢巡方之差”[3](P5290)。沈荃、王士祯分别有《送张篑山学士归庐陵》诗送之。王士祯一改其含蓄蕴藉风格,在诗中写道:“上殿似闻辛庆忌,行吟休拟楚灵均。千秋公议存青史,应为朝廷惜此人”,直言同情与婉惜之意。
清初为了思想一统,大兴文字狱,实行“连坐制”。清初连坐的范围相当广泛,有亲属连坐、领伍连坐、职务连坐等等,花样繁多。“明史案”中《明史》作者庄廷鑨已死,仍被开棺戮尸,其兄弟子侄及刊刻书稿者、《明史》读者和保存者、事先未察觉的地方官员共70 余人被处死,受株连被发谴充军流放者达700 余人。顺治十一年(1654年),陈名夏因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而被绞死。陈名夏长子陈掖臣杖四十后,流放尚阳堡。沈恺曾曾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及山西、浙江、河南道事宫御史,“三十八年,……以广东运使罣误事连坐,罢官。”[4](P10173)豪情满怀的他,被迫在40 岁不到的盛年离开官场,10年后便去世。沈元沧官文昌知县,颇有政绩,后因亲属获罪牵连贬至宁夏,不逾年而卒。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丁澎之婿顾永年亦受上司漕运总督董讷牵连,谪戍盛京。
顺治十四年(1657年),年已六旬的方拱乾,因第五子方章钺罹科场案,与长子方孝标、次子方享咸共4人同戍宁古塔。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方孝标因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再次遭受文字狱。方孝标被开棺戮尸,子方登峄、孙方式济(后二人皆死于塞北)及族人方世举、方贞观、方苞等被流放黑龙江卜魁城,隶旗籍。从方拱乾到方贞观、方苞,前后四代,打击范围已出“五服”之外,方氏一族元气尽丧,这在中国流人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2.因党派、皇权之争
清朝前期党争不断,各种政治迫害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许湄《拟古》云:“而何阶前筿,攒出如蒿莪。托根一失所,过者寻斧柯。”阶前筿、当门兰本是花中君子,但因托根失所,遂遭斧柯之灾,这实在是清初党派之争的真实写照。
皇权的高涨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使清初贬谪事件频繁。赵执信18 岁考中进士,23 岁就担任山西乡试正考官,25 岁升右春坊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可谓少年得志。然28 岁时,因与查慎行、洪升一起,于佟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而被以“大不敬”之罪革职除名。此后,赵执信“高才被放,纵情于酒,酣嬉淋漓,嫚骂四座,借以发其抑郁不平之概”[5](P501),其诗时而表现出安于命运、颓废享乐的消极思想,时而又流露出愤激不平之情。“《长生殿》剧祸案”乃清初党派之争的产物。因赵执信在“南北党争”中与“北党”领袖明珠关系密切,查慎行则担任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的塾师,遂成为“南党”排挤的对象。
清初贬谪事件多以文字狱的形式表现出来。帝王以文字为罪证,随意打击政敌和臣子,以巩固、加强皇权。如汪景祺作为年羹尧的记室,因《读书堂西征随笔》内容“悖谬”而被杀,钱名世因在诗文中吹捧了年羹尧被定为“名教罪人”。此外如徐骏“清风”案、陆生楠《通鉴论》案、谢济世《大学》案和吕留良案等,无不如此。高其倬出身于铁岭官僚世家,祖、父、从兄弟辈皆政绩显赫,高官辈出,其倬本人历任山西学政、内阁学士、广西巡抚、云贵总督等,可谓一门光耀,仕途坦荡。然雍正十一年(1733年),高其倬因上奏疏时书写不当,将贝子胤禵之名抬写,用了同皇帝一样的敬体而遭贬。其曾作《与熊敏思登蟠龙山顶望都城值大风有感呈敏思》一诗表露出繁华已逝的抑塞不平之意。
佟法海为康熙舅舅佟国纲次子,康熙十三子胤祥、十四子胤禵的老师,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受“废太子案”牵连,降为检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佟法海作《送查悔馀还乡兼寄贾奠坤》诗送别查慎行,兼寄贾奠坤,诗歌深沉蕴藉。雍正四年(1726年),佟法海在兵部尚书任上短短数月,又“坐事免,诏发西陲”。[6](P33)雍正即位后,严厉镇压了参与皇位之争的兄弟,各王府的门人、同党也受到了牵连。已退职回原藉的刑科给事中陈沂震被人告发贪赃受贿,与曹寅一同被抄家,陈沂震自杀,其子逸出为僧。秦道然曾在皇九子允禟处教书,也因以汉人身份任允禟贝子府管领,被革职下狱。
三、文人及官员被贬后的人生态度
官员被贬后,往往生活一落千丈,心中难免失落惆怅。于是有的人从此谨慎自戒,时时自我反醒;有的人消极悲观,纵情山林,隐居避世,或转向学术,专心著述;有的忿忿难平,郁郁寡欢,呈现出不同姿态。
1.惊恐不安,谨慎自诫
官员遭贬后,很多人出于对政治的恐惧和害怕,往往固步自封、谨慎自诫,时时自我警醒。明末御史曹溶在入清后的18年里屡遭贬斥,52 岁裁缺回乡后不再复出,晚年号“倦圃”,室名“敬惕堂”,作品结集为《敬惕堂诗集》《敬惕堂词》《敬惕堂文集》,含“厌倦”“恭敬、谨慎”之意。无独有偶,徐乾学晚年将其全部作品命名为《憺园集》。“憺”乃“安然、恬静、害怕”之义,与“惮”通。解职南归后仍屡被控告,终日忐忑不安,以至“知有使者来,而不侧祸福,遂卒,盖悸死也”[7](P365),用生命解读了“憺”字的宿命色彩。查慎行原名嗣琏,字夏重,因观演《长生殿》被除太学生名后,改名慎行,字悔馀,以示悔过自新之意。佟法海因受“废太子案”牵连降职后,亦为别集取名《悔翁集》,盖回首往事多有悔恨。
乾隆时期诗坛泰斗沈德潜在90 多岁时做梦,竟梦到皇帝对自己严加斥责。以德潜之高寿隆遇,尚且如履薄冰,旦夕难安,清初官员的贬谪状况可见一斑。鉴于官场之危险,诗人们在诗歌中对后人多有告诫。沈天宝《公无渡河歌》将大河之风浪险阻比作宦海风波,劝诫人们慎入官场,“吁嗟乎!宦海风波随处多,岂独人间公渡河”,真是震聋发聩,震撼人心。沈用济《黄河大风行》对应现实,“岂惟黄河为畏途,波澜平地无时无”,告诫世人“要知蹈险非良图”,处处语带双关,催人警醒。
2.远迹官场,诗游寄怀
经历过风波的人们对于残酷的政治事件有着切肤之痛,以致多年后仍心有余悸,故而当朝廷再次征召时,都不约而同地退避三舍。状元孙承恩之弟孙旸,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乡试中举,因“科场舞弊案”流放尚阳堡,被放还后以诗画自娱,拒绝出仕。“三藩之乱”时,吏部以地理之才推荐他前往福建,孙旸作《甲寅四月宋蓼天少宰以边才特疏荐余诗以谢之》,明确表示不合作态度。康熙举“博学鸿词”科时,邓汉仪以养亲固辞不许,考试时故意不用四六句作赋而得罢归。孙旸作《送邓孝威南还》赠别:“到来京洛文章贵,归去江湖天地宽。”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频繁的贬谪,官员之间的政治斗争,使清初官员多具有隐士情怀。顺治十五年(1658年),丁澎任河南主考官时受科场案牵连,流戍尚阳堡5年之久,此后“不问户外事,而自娱于文”。施闰章考中进士后,授官给事中,谁料第二年就因事被坐降职,7年后又受“陈名夏案”牵连再次被贬,心灰意冷的他遂以养母为由弃官不出。陈廷敬是清初名臣,曾任职于礼部、吏部、刑部等重要部门,政绩不凡。50 岁时却因亲戚贪赃受连累,自请解任回乡。《施愚山见寄长歌和答》“儒术用世行已矣,浮名寂寞何为哉!不如放意游八极,扫除文字栖渊默”,表现出强烈的消极悲观情绪。钱曾外孙汪绎30 岁便考中状元,后出为会试同考官,录取了查慎行等大批名士,号称得人,不久却遭排挤,遂挂冠告归,归隐后沉醉山水田园,诗歌多生动表现田园至乐。
3.怨恨不已,愤激难平
在被流放贬谪的众多文人当中,不乏性格刚强、不甘屈服之人。赵执信被革职后,诗歌多矛盾、怨愤、感伤情绪,如《记蝗》《题搜山图卷》鞭挞荒淫无耻的大小官员,恺切直言;《碧波行》冷眼观世,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皇帝,与诗坛盟主王士祯的宗派之争,更暴露其偏狭、狷急的性格。顺治十三年(1656年),时年39 岁的尤侗任永平推官时,因“擅责投充”旗丁被降职,愤而辞归,写下《南归杂诗》24 首表达心中的不平之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唐孙华任浙江主考官时因失误落职,遂坚卧不出,终日游宴。《东山即事》“文到无情真悔作,口除饮酒只宜缄……破砚生涯今更拙,谋身端合托长镵”,充满愤世嫉俗的无奈。
江南是清初民族思想和“夷夏之防”反清意识最浓重的地区,清兵南下时,就曾遭到江南人民的惨烈反抗,顺治、康熙年间政局渐稳,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刀剑相向的战场厮杀,转变为一场无形的心理较量。“文字狱”“科场案”“奏销案”等一系列政治事件,长久而深远地影响了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文网的严密,文化上的专制政策,摧毁了士人的人格尊严,使读书人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他们在一次次的政治打击和迫害中,变得谨小慎微,噤若寒蝉。文人受祸大多出于非主观原因,很少有人真犯贪污、失职、纳贿等罪,多数是含冤或出于忠心而受牵连。在康熙盛世的光环下,隐藏的是文人饱经风霜的心灵。他们原本胸怀青云之志,却无辜被贬谪,被迫咀嚼长年的孤独和哀怨,忍受着年华早逝、人生无望的煎熬。于是愤世嫉俗者有之,自暴自弃者有之,纵情山水者有之。在各种消极悲观情绪的影响下,清初诗歌往往缺少昂扬的气势,散发着浓浓的忧伤情调。乾隆中期以后,考据学日渐兴盛,文献整理和文化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虽然有利于学术的进步,但牺牲的却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批判性思考,阻碍了文人的个性解放和对自我尊严的追求。
[1]廖晓晴.清代辽宁流人与流人文化述论[J].辽宁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78-84.
[2]计六奇.明季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4.
[6]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M].同治八年(1869年)循陔草堂刻本.
[7]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