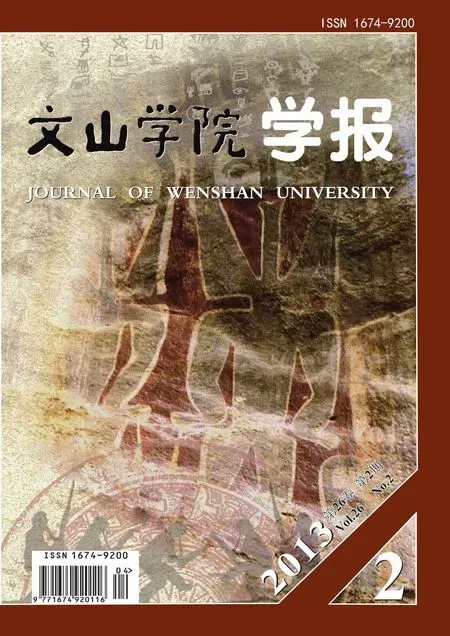论汉式命名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及影响
吴连才,杨雪礼
(1.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2.云南科技信息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5;3.文山学院 政史系,云南 文山 663000)
命名是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为了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而人为的对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事物赋予的,用以区别各个体的标识性的称谓符号,包括对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事物的命名,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人的命名。随着汉族陆续移民云南并逐渐在人口上占据大多数,汉族的命名文化也随之传入云南,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所接受和采用,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命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汉式命名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
自秦汉以来,云南各民族一直处于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中,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将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定程度上说,云南少数民族命名文化的形成就是云南各民族之间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
(一)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命名文化
1.连名制命名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中都存在或者是曾经有过连名制命名。所谓连名制命名,是指一个命名人在出生以后,其长辈为了使其在以后的社会活动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称谓符号,而依据本民族的命名习俗,将当事人本名缀上其直系长辈中一代或一代以上至亲本名以构成当事人正式用名的命名方式。
连名制在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至于具体该连缀亲属中谁的名字则在各民族中略有区别,主要有以下典型的连名方式:一是父子连名制。其主要特征就是一个家族中出生的男性婴儿,采用其本身的名字与父亲名字连缀在一起构成正式用名的命名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基诺族、独龙族、怒族、佤族、苗族、瑶族等民族在部分地区曾保留这一习俗。二是母子连名制。即在起名时,将母亲的名连在孩子的名字后面,构成孩子的名字。以这种方式命名的民族以布朗族最具特点。三是兄弟连名、姐妹连名。在目前所知的资料中,采用过兄弟连名或者是姐妹连名的少数民族以拉祜族为代表。
2.宗教性命名
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信仰宗教,宗教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反映在人的命名方面也就很有特点了。
由于云南民族众多,世界五大宗教都有人信仰,本文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族进行讨论。 一是傣族的命名。傣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傣语称为“布塔纱散那”,该教对傣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深的影响。一般来说,8~10 岁的男孩都要送进佛寺里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僧侣生活,并在佛寺里学习傣文和经书,经过1~5年的佛寺教育后便可以还俗回家,开始过世俗生活。孩子在进入佛寺以后,要接受洗礼,由佛爷为其起一个佛名(也叫和尚名)。佛名一般是将世人对小和尚的称呼“帕”,与本人原来的乳名连在一起构成。比如原来乳名叫“岩英”的,佛名便叫“帕英”,原来乳名叫“岩甩”的,佛名就叫“帕甩”。二是藏族的命名。藏族几乎是全民信教,佛教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藏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名字多为活佛所起。活佛为小孩举行简单的起名仪式,主人带来哈达及其他礼物,接着活佛念经,最后对孩子说一些赞颂和吉利的话,然后才起名字。许多人的名字里都有很浓郁的宗教气息,如:丹巴——佛教、圣教,达杰——繁荣、发达,江央——妙音等。三是回族的命名。 回族通常有自己的教名,即经名,又叫回回名。回族起经名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而且成为回族命名文化中最能表现民族习俗的内容之一,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回族在婴儿诞生的当天或三天之内,就必须请一位阿訇给婴儿举行命名礼,称为“吹邦克”。当阿訇举行完这种仪式后,便从伊斯兰教众多的先贤中选出一个美名,告诉家人以示吉庆、俊美。男孩一般命名为“尔彻”“努哈”“尤素夫”等。[1](P420)
3.排行制命名
排行制命名是广泛存在于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中的一种命名方式,在彝族、景颇族、佤族、傈僳族、傣族、拉祜族、德昂族、苗族中都存在。这种命名一般仅涉及到同一代人中的命名,不仅能够反映同代人,而且还可以看出很多代人的关系。
拉祜族的排行制命名。一般只有大小两极,中间的孩子不参与排行命名。对第一个孩子,男孩一般起名为扎儿、雅儿、扎倮,女孩一般起名为娜儿、娜倮。“儿”和“倮”有“大”和“首先”的意思。最后一个孩子,男孩一般起名为扎列、雅列、扎列八,女孩一般起名为“娜列”“那列妈”,“列”是“末了、最后”的意思。[2](P139)与拉祜族相比,景颇族的排行制命名要规范得多。景颇族家庭所生的孩子一般都会用排行的方式为其命名,在人名的前面会冠以一个“麻”字,从一到十都有一套固定的叫法。佤族的排行制命名与景颇族的排行制命名有相似之处,都是按孩子出生的顺序和性别来命名的,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佤族的传统认为多子多福,因而在过去一对夫妻有十几个子女的情况屡见不鲜。佤族的孩子在出世以后,父母就会按照排行的方式为其命名。
4.其他形式的命名
云南的少数民族由于受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命名文化。除了以上所举外,还有一些很特殊的命名文化。
在云南的傈僳族、拉祜族、彝族等几个民族中,还有以自己本民族的图腾来命名的情况。如傈僳族的姓里面有虎、熊、蜂、猴等动物的名称,一般认为是傈僳族氏族社会阶段的图腾标志。有关这些图腾转为姓氏,还有很多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例如傈僳语中虎的音为“腊扒”,传说一个姑娘进山打柴的时候,遇见了虎变成的小伙子,两人结婚后所繁衍下来的后代就以虎为姓。当傈僳族与汉族接触后,由于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虎又转化成了汉式的胡姓。而拉祜族和彝族也有很多类似的神话传说,如彝族的都卑普氏族,意为蜂氏族,以后转化为张姓。此外,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还有用长辈名、名人名,用景、物,用孩子的身体特征等来命名。这些命名方式多样,分布广泛,成为云南民族文化中最具地方民族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汉族命名文化在云南的传播
1.移民通婚,民族交融
汉族与云南少数民族的通婚由来已久,并与汉族移民云南的历史紧密相关。文献中记载的有关内地人口移居云南的历史,是从战国后期的“庄蹻入滇”开始的。庄蹻入滇一事,《史记》和《汉书》记载大体一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3](P2993)庄蹻是楚国人,率领着一支军队到了滇池地区,并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中。从人员的性别看,这支军队应主要是男性,移居云南后,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亦属必然。至于这支军队“变服,从其俗”融入当地少数民族后,其子孙如何命名的问题,限于史料也无从知晓,但不管怎么说,庄蹻开滇为汉文化在云南传播的先河。
秦汉时期,秦通“五尺道”,汉武帝“开西夷”,置益州郡和大规模移民屯田。大批内地汉族人户进入云南后,在汉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少数民族中开始陆续出现汉式姓名的历史人物。据鲁刚教授考证,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最早具于历史文献记载的是今天白族的先民两汉之际的“僰虏孟迁”。[4]以后又有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的“叟帅高定”[5]“夷帅刘胄”[6],西晋时期的“五苓夷帅于陵承”[7]等等,表明汉式姓名文化又进一步传播到了今天彝族的先民等更多的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中。再往后,到唐代中期史载今洱海沿岸的“白蛮”中,有“杨、李、赵、董、数十姓”[8]和“西洱河大首领杨附显”“潘州刺史潘明威”“和蛮大首领王罗祁”[9]以及“其族多姓李”的滇中“独锦蛮”和滇东南“桃花人”大首领“李由独”[10]等等,涉及到白族、彝族、哈尼族、壮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先民有关的人群,空间上则进一步拓展到了更为广大的地区。
从上述可见,移民通婚是汉族命名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即通过民族融合把汉式命名文化带入到少数民族中,并进一步传播开来。尤其是到了宋、元、明、清时期,这种情况更加普遍。
2.赐姓赐名,加强边境治理
帝王赐予姓名是命名文化政治性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在古代,一个人的姓名受自父母长辈,一般不能随意改变。只有遇到特殊情况,实在迫不得已才会改易姓名,赐姓就是改名的一种特殊形式。封建帝王对下级可以生杀予夺,对自己喜欢的、忠于自己的大臣则会恩宠有加,对忤逆、背叛自己的则会大开杀戒。姓名的赐予就有这两方面的作用。对有功的大臣赏赐姓名,是对属下的一种恩宠,获此殊荣的大臣也会倍感荣耀。[11](P195-198)这种赐名不但是皇帝对大臣赏赐,更是帝王用以笼络臣下、壮大自己统治集团力量的一种手段。史载尧舜禹时期就有了赐姓赐名。自西周开始,中国古代就进入了一个宗法伦理社会的发展阶段,秦汉姓氏合一以后,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热衷于修撰谱牒,甚至用国家行政的方式对天下姓氏进行排名,以达到彰显家族、光耀门楣的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赐姓赐名也就成了一种资源,并被赋予了极高的精神奖励价值。
赐姓赐名制度也曾被推广应用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上。赐姓赐名作为封建帝王笼络属下的一种政治手段,因其代价低廉而又效果显著,在古代曾被广泛应用。汉族命名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与封建王朝对云南统治的深入程度有一定关联,尤其又与“改土归流”密不可分,改土归流打破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地域上的人为障碍,为民族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而凡是完成了改土归流的地方,汉式命名文化的传播都相对较为广泛和深入。就云南少数民族而言,历史上也曾被赐予过汉姓汉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唐玄宗赐南诏皮罗阁名“归义”[12](P17)并封“云南王”,以后又有明王朝赐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姓,赐德宏傣族土司龚姓,广为人知的“郑和”一名也是明代皇帝赐予云南回族马三宝的姓名等。
3.兴办儒学,传播儒家文化
在2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云南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是多方面全方位的,从政治思想到生产技术,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可谓是面面俱到,其中又以儒家学说在云南的传播最为典型。自西汉武帝时经董仲舒的倡导,在内地取得了“独尊”地位以后,中国历史不论经历多少朝代更替和兴衰变化,儒家学说一直被当作正统思想而备受尊崇。
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更多的也是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的学习和借鉴的过程。大批汉族移民云南地区,除了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以外,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汉文化也随之传入了云南。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以儒学教育的形式出现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汉肃宗元和年间,蜀郡王追任益州郡太守时,史载王追“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尽管详细情况史无明载,但可以推知应为儒学教育。而从“渐迁其俗”来看,也应有少数民族的子弟在其中。由此对于汉族命名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的传播,必然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经过秦汉以来的发展,到了唐宋时期,尽管雄据西南一隅的南诏、大理两大地方民族政权与封建中央王朝各自为政,但云南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未中断,《南诏德化碑》自诩“本唐风化”,而南诏王室子弟多受教于汉族士大夫出身的清平官郑回,并连续遣人前往成都学习,史称异牟寻“颇知书,有才知”,寻阁劝的诗作《星回节游避凤台》还被收录进《全唐诗》,都反映出汉文化在云南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尤其被上层贵族认可。元明清以后,随着官私儒学的陆续设立,汉文化在云南更是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汉族在云南上升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和清初“改土归流”后,包括命名习俗在内的汉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加广泛与深入。
二、汉式命名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影响
随着汉族陆续移民云南并逐渐在人口上占据大多数,汉族的命名文化也随之传入云南并不断地在少数民族中间传播开来,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所接受和采用,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命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在保持本民族传统命名文化的同时为了更好地融入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历史大潮中也起汉族名。
(一)丰富了云南少数民族命名的方式
从文献来看,整体上少数民族使用汉名人数经历了由少到多的变化。汉式命名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使用经历了秦汉之际的零星出现,这之后的逐渐增多实现了元明清以来的蓬勃递增。云南少数民族命名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历经2000 多年来的演进与变迁,其命名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下列三大类型:
一是与汉式命名基本趋于一致。主要以白族、回族、满族、纳西族、壮族和部分彝族、苗族、瑶族等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为代表。特点是在普遍采用汉式命名的同时,又具有诸多的地方民族特色。如白族中的杨、赵、李、董、尹、高、段等“大姓”,回族中的马、纳、丁、沙、桂、保等姓特别是人数最多的马姓和较罕见的虎(读如“猫”)姓,以及纳西族的木、和两姓,彝族中特有的自姓、字姓、起姓等等。二是继续保持传统的命名方式。其中又以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迪庆藏族和部分彝族、佤族、傈僳族,拉祜族、景颇族较具代表性。特别是在这些民族的聚居地农村,传统的命名文化得以较完整地传承直至今天。三是双名制。即在保持本民族传统命名文化的同时,又部分接受了汉式命名文化。通常表现为同一个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其中一个是“汉名”,另一个是以本民族传统习俗命名的民族名。这种情况,又多见于在本民族聚居区传统命名文化保持较为完整,但经过学习进入城镇工作的少数民族公职人员和大中专在校学生中。
云南各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命名文化间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又保留了本民族自身特色的交流。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汉族与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交往联系的日益密切,特别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通婚的日趋普遍,汉式命名文化的传播将会更加广泛与深入。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和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的传统命名文化也会得到保护与传承,在一定情况下,还会有所强化。命名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也与其他的文化一样存在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今天的命名文化由古代发展而来,还将会不断发展下去,形成与时俱进的命名文化。
(二)有利于传播汉文化,促进边疆发展
汉文化进入云南与封建王朝对云南的开疆拓土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汉式命名文化在云南的传播,有利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
秦汉时期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大量汉族移民通过驻军、置吏、屯田、发配等形式进入云南,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汉文化,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治理的不断深入,以兴办儒学、建立庙宇、讲求礼仪等独特而规范的汉文化逐渐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得以传播,并逐渐成为云南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命名文化作为汉文化在云南传播的一种典型代表,充分反映了汉文化在云南传播发展的历程。这一历程与云南融入祖国大家庭的发展轨迹相一致。时至今日,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在不断地学习并融入到汉文化的生活圈里,而广泛地使用汉姓汉名无疑是汉文化在云南传播的一种典型代表。
人的命名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因袭、传承并不断变革、演绎着的文化现象,是每一个民族自身文化总体中的重要方面。研究一定区域内的民族命名,不仅对认识某一具体民族的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就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地区而言,对于认识历史上由命名文化反映出来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现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命名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发展和演进具有稳定性和相对滞后性的特点,因而研究人的命名,能够帮助人们了解那些曾经的历史岁月,对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林新乃.中华风俗大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2]王正华,和少英.拉祜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3]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
[4]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王莽传[M].
[5]陈寿.三国志·蜀志,李恢传,后主传[M].
[6]范晔.华阳国志·南中志,华阳国志·蜀志[M].
[7]司马光,等,纂.资治通鉴·唐纪四卷188[M].
[8]欧阳修,等,纂.新唐书·南蛮传卷239[M].
[9]张九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等书[A].全唐文卷287[M].
[10]樊绰.蛮书卷[M].欧阳修,等,纂.新唐书·南蛮传卷239[M].
[11]王泉根.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
[12]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