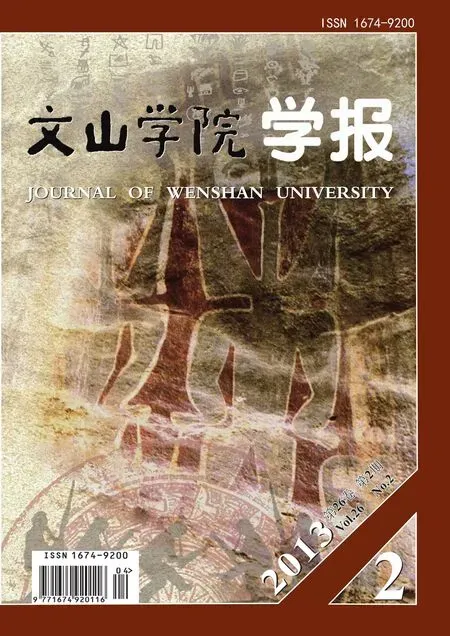楚图南抗战文艺思想简论
布小继,沈 慧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蒙自 661100)
身为云南文山人的楚图南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声名卓著的学者、文学家。1937 至1946年间,在昆明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先后担任了云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会长、民盟中央委员等职,在《大国民报》《云南日报》副刊《南风》《昆明周报》《诗与散文》和《文化岗位》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出版了《刁斗集》《旅尘杂记》等文集,对抗战时期的云南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现代云南的本土文人中,楚图南的抗战文艺思想是极有价值的,他既立足于云南本土的实际情况,呼吁云南要不断壮大文艺创作的队伍,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措施和要求,试图改变云南现代文化孱弱的局面,为抗战建国①目标的早日达成尽一个文人学者的本分。
具体来看,楚图南的抗战文艺思想有如下内容:
首先,抗战文艺要有现实性和针对性,要多方面、多角度去描写抗战现实中的社会生活。针对有些文学作品描写虚假、反映社会现象不够深入的问题,他认为:“真实的文学作品必须从多面的去描写,去接触到现实的每一个角落,无论那是阴暗面也好,无论那是细小枝节的问题也好……作者如果对于现实问题,既有理解又有热情,则描写任何问题,都可以发生所应当得到的效果,否则主题如何伟大,内容如何惊人,仍然会令人感到不够真实,觉得无力。”文学作品虚假一者是由于作者耽于想象缺少生活经验,一者是由于与社会现实脱节而导致表现的无力,内容的空虚。楚图南从文学创作本质出发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明确鹄的的,也和自身的文学创作经验吻合。他又说:“云南过去因为环境的关系……很少有根据于现实问题之分析和研究之真切的讨论。空洞肤廓的思想,支配了整个的思想界或学术界。在一般的刊物上所提出来的问题,不是大到不能再大,就是小得不能再小,不落边际,避开了现实,使你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是使言之者无罪,听之者也不起作用,天下太平,于是乎云南成为乐园,成为天国的了。”这确实击中了当时偏于一隅的云南文艺发展过程中的要害,不关注现实,不放眼全国,没有宽广的视野,甚至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依然沉醉于小天地中的安逸生活,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缺少积极向上的动力,慵懒、保守、折中平和,自然有悖于文化人的职责和良知。这还触及到了云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迫切和紧要的问题,即文化发展应该具有相关性和当下性——要和云南以外的世界变化密切联系,要着眼于当下;云南的文化人要具有危难意识和国家意识,切不可苟且偷安,以小国寡民的心态抱残守阙。
当然,楚图南并没有一味地贬损,更多的是怀着一种呵护善佑的心情来看待云南文化。“云南最近文艺界的情形,比较总算是很好,很可乐观的。因为云南的文艺,已经有着一种自来所没有的新的倾向,一种健康的倾向了……云南社会的任何现实问题,自然与抗战问题有着深切的关系。这里的任何典型的事件,任何典型的人物的描写,实在如同描写台儿庄大战,描写飞将军一样的有价值,一样的重要,一样的是抗战文学中极真实,极伟大的内容和主题……我们理解云南,感到了云南社会隐藏着许多悲伤和痛苦,知道了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可做,知道有许多的重担不能不担负在我们的肩头,也知道了云南正在觉醒着,动着,并且就要咆吼,就要刚强地站立起来,来支持了抗战建国过程中的许多艰巨而繁难的责任,来作为长期抗战的后方的堡垒,作为悲壮惨烈的后盾。”[1](P541-542)他再次强调了书写云南现实尤其是“悲伤和痛苦”的现实之重要性,特别是要写出云南人民的觉醒,以此作为全国抗战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可以视作最低限度的要求,早在全国抗战之前,东北作家群就有不少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苦难的作品问世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可以视为最高的要求,因为云南处于大后方,当时尚未有战火,抗战对云南广大人民的影响还是间接的。文艺工作者对它的表现就应该从底层百姓的生活入手,把这种间接的影响书写出来。同时,楚图南还注意到了云南文艺在后方是能发挥其效用的,希望有更多的文艺工作者不拘泥于题材大小和地域远近,以沉潜基层的决心、勇气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创作出更多的、有益于唤醒鼓舞民众斗志的现实主义作品出来。
楚图南说:“怀着满满的希望和欢喜的心情,看到了许多青年的九月应征的作品……作品的内容,有的是小说,是速写,是杂文,也有着木刻。将这些摊开来在眼前,云南社会的诸相,和许多不认识,然而也不陌生的青年人们的心思和努力,都好像活现在眼前了。虽说那些作品,除了少数的一两篇,大多数是很幼稚的。然而作者的态度却很真挚,他们的努力,亦令人钦佩和欢喜。”社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实际上是对楚图南呼吁的回应,文艺青年行动起来,云南文化才有希望和未来。对青年创作者,他又不忘谆谆告诫:“我们宁喜欢于幼稚而真实的写作,即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错误,这究比恶气味的所谓的名家,所谓成熟作品无毒……文学和艺术的精魂,便在于最忠实的生命的极活泼而有力的血液里。”[1](P544-545)为人要真,为文亦如是。鼓励奖掖后进正好体现了一名成熟文化人的智性和责任,这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有例可循的,如鲁迅对萧红、萧军,郁达夫对沈从文的无私帮助都被传为佳话。如何让云南本土文艺工作者茁壮成长起来,始终是楚图南工作的一个重心。他认为要从遵循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原则起步,不能好高骛远,贪大求全。在《写给云南漫画工作的朋友们》一文中,主张“我们当如战士一样的坚凝、沉雄而辛苦,要从我们的生活上剜却了过去的艺术家所有浪漫、疏怠和肤廓的恶气息。咬定了人生,咬定了现实,这样我们的作品,就不会是浮在纸上,而是雕刻在纸上,雕刻在人心的底里……而是血汗和斗争中的现实生命,现实社会的最深处的面影,和最深处的精魂”。[1](P559)“咬”就意味着深入思考和深入现实,“雕刻”就意味着作品的深度和思想容量。这些要求也符合列宁所说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应该把自己最深的根扎进广大劳动群众之中……它应该把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应该鼓舞群众。它应该在群众之中唤起艺术家来并且使他们得到发展”[2](P124)。楚图南重视艺术家与人民生活的血肉联系,重视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效用。对抗战建国和云南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促使楚图南全面、深入地考虑云南文艺究竟应该如何与现实打成一片,又能够帮助更多的文艺青年成长的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其赤子之心。
与之相关联,就是抗战文艺的战斗性和地方性问题。楚图南认为:“所谓的战斗性,并不仅限于描写游击战、空军战和前线血腥的争斗……也一样凡是中国的传统的,有毒害的一切,现实社会的畸形的或不健全的部分,以及在抗战建国中所暴露出来的任何的流弊和民族的劣根性,凡是足以阻碍中华民族的解放,凡是不利于抗战建国的大业,或者凡是危害于中华民族的新创造的成分,一个明智而有力量的抗战文艺工作者,都不应当轻轻放过。”显而易见,楚图南的目光是长远的,他并未对抗战文艺的范围作狭隘的理解,而是着眼于民族解放大业和民族劣根性的问题,希望借助文艺,来继续鲁迅毕生所致力的国民性改造事业。这不仅可以见出其深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而致的文学自觉,也可以见出楚图南的不凡之处。地方性是为补救抗战文艺中的公式主义之流弊而提出的,“更能增加文艺的真实性,使文艺的内容更其充实、活泼,对于读者有更伟大的效果和影响”,“抗战文艺地方性的看重,也便是这种准备工作之一,是产生伟大作品所不能不有的修持”。[1](P586-589)也就是说,地方性是要求作者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去观察去描写,创作出与所处环境相适应的文艺作品来,要具有地方特点和内涵,并为今后产生与抗战这一伟大题材相匹配的伟大作品做好准备。
其次,对云南文化发展的认识。在纪念聂耳逝世三周年的日子,楚图南写了《聂耳何以是伟大的》一文,认为聂耳是“一个山国里的青年,一个崭新的幼年的狮子,他的一声咆吼,叫出了中国人的反抗的呼声,唤起了中国民族的新生和前进”。并认为他成了“划时代的音乐家”[1](P537),充分肯定了聂耳在音乐、在中国文化建设上所作出的贡献。楚图南致力于云南文化建设的拳拳之心,对云南文化人才的挖掘与彰扬,于此亦可见一斑。他又说道:“看了《前夜》《黎明》和《黑地狱》的同时演出,令人感到云南的话剧运动的活跃;在云南的文化工作,也似乎以话剧的运动最有成绩,最为进步。”同时又对话剧提出要求:“更虚心地相互学习,更诚恳地彼此合作,来开展了云南的话剧运动,来发挥了在抗战建国过程中戏剧运动对于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的伟大功能和作用。”在对演员做了评点后指出,如果能够将前述话剧中的优秀演员聚集起来,演出伟大的剧本,必定能够给云南社会“以更伟大的影响和更良好的印象”。“我们爱护话剧运动,爱护真实的演员和导演家,更爱护从事于神圣崇高的艺术工作或话剧运动的那坦诚护爱,和严肃合作的精神。”[1](P555-556)这进入到了对具体文艺门类的评价了,在看到优点的同时也不忘提出希望。在《一年来云南文化工作的检讨》中,对新近出现的刊物和金马剧社话剧《夜光杯》的演出做了肯定后再指出不足之处。事实上,话剧这一艺术形式对文化层次普遍偏低的老百姓来说更易于接受,更易于在宣传上出成绩。对真正的文艺,只要有良好的发展势头,楚图南不吝其赞美之词,充分发挥了指路明灯的作用。
爱之深必定责之严。《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中,在承认云南过去的文化落后的前提下,又提出云南的文化无疑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了,“由于对日抗战的发生,云南成为后方的军事准备的重镇,和文化思想的保育和培养的摇篮。历史课给云南以最伟大的责任”。这一看法在本土作家、学者中是有先见之明的,也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外来移民的到来,为云南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成分,所以云南文化进入了“一个最伟大的时代”。那么,作为云南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人的尊重和对学术的宽容”,面对外人的恭维、客套,“云南更要切实反省,自我批评”,因为那些恭维“都好像是背熟了的老文章一样,反映了云南社会的落后、幼稚、无知才有着这种需要”。所以提倡云南社会要有宽容的雅量,“才会使云南文化能够加速度地度到一个新阶段,这便是云南现时应当采取也必须采取的态度”。[1](P627-628)余斌认为,该文“大约与李长之那篇杂文《昆明杂记》引起的风波,即施蛰存先生所谓李长之‘被云南人驱逐出境',有些关系”。[3](P48)换句话说,该文是在李长之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论争特别是本土文化人士的反感后,针对云南人的劣根性进行批评的,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持平之论。要想在抗战建国过程中有所作为,云南人就不能再闭关自守,抱着小国寡民的守旧思想,在外人有意无意的吹捧中自我陶醉,而是要学会包容,尤其是对像李长之这样有思想锋芒而言辞不够敛束的专家学者。从另外的方面看,别人不中我意的批评或许正是云南人可以反躬自省的地方。
再次,对抗战救亡文化的理解。在楚图南看来,“救亡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临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为抢救危亡,为保持生存所不能不有的一种生活的样法,必须采用自我教育、普遍训练干部人才和团结组织全省乃至于省外文化、教育工作者等方式来推动其发展。而此时期的中国文艺要为此服务,就必须做到内容的彻底现实化、技术上尽可能大众化。在云南,流行于农村的灯剧(花灯)在文艺工作者改编后上演就完全实现了大众化而达到教育大众训练大众的目的。文艺“可以尽了抗战过程中的杠杆或推动的作用,即文艺工作者,也才算是尽了他的民族解放的战士的责任”。[4](P65-66)与此相关,又有对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论断。在中苏文协云南分会讲稿《抗战以来的文艺及民族形式问题》一文中,他在分析了对文艺民族形式的理解上有歧见的两派后,提出自己的主张,“文艺的民族形式是可以提出也应该提出”,其先导观念有:(1)时代进化和社会进化所带来的新责任;(2)通俗化大众化而非专一大众化和通俗化;(3)民族形式不能认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制造品,是民族的,即在时间上可以接受了中国过去,人类过去的优良传统;空间上可以容纳和吸收了一切外来的经验。这样的民族形式,才会是民族性,才是一种合理的统一,一种相得益彰的调和。[4](P85-86)围绕该问题,他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即发挥民族精神、吸取传统精华和吸收外来经验,以进步的法则满足中华民族之需要等等。凡此,才可以使民族精神真正得到宣扬,并与民族形式有机结合起来,起到振奋和鼓舞人心的作用。这不妨看作是其对民族文化构建的切实努力,对五四以来民族文化形式建设上的新发展,也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相关论述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楚图南绝非空头理论家,他还不断地进行创作实践,以此来带动、提升云南本土创作的质量和水平。蒙树宏在《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一书中认为楚图南抗战时期的作品有如下特色:善于从宏观上考察历史和现实,描绘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生以及作品风格受鲁迅、尼采的影响等。[5](P151-154)他的《碧鸡关的故事》《记棕树营》等文章,读起来就颇为感人,尤其是弥漫于其中的人道主义情怀很是深厚,既有对平民百姓生活的忠实描写,又有对民生疾苦的慨叹,有几分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时忧世精神。楚图南与白平阶、马子华等人,为描写云南、展示云南尽心尽力。
检索云南抗战文化资料可以知道,在经济、文化不甚发达的云南,真正关心本土,热情地为本土文化摇旗呐喊、奔走鼓吹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的,除了沈从文、穆木天、光未然等一些知名文艺家有过类似表现外,更多的人是不屑的。而且云南在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形,在学者云集、各色人等齐聚的大后方,楚图南以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本土人士身份在文化建设上率先垂范,并呼唤更多的青年起来有所作为且眼界开阔、具有包容情怀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楚图南的远见卓识和爱国爱家的炽热情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偏僻的云南要真正出现文艺繁荣的局面,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涌现出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和成熟的创作队伍同样是极不容易的。因而,楚图南的抗战文艺思想对于当时的云南文艺来说,更多的具有启蒙的性质,也是对马列主义文论在具体实践中的阐释和发挥。许多在文化发达地区一般知识青年已经了然的常识问题,在云南依然值得提出来。总而言之,楚图南抗战文艺思想的价值在面对云南家乡父老,希望云南文艺建设在新的形势下有所突破、有所提升这一点上方能被完整地凸显出来,也具有了超越云南地方性和时代性的意义,对文化落后的地区同样具有启示作用。
注释:
①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计七项三十二条。以此作为统一全党、全国思想和争取抗战早日胜利的法规性文件。
[1]楚图南.楚图南文选[C].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
[2]毛泽东.给周扬的信[A].毛泽东文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余斌.西南联大·昆明记忆①[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4]楚图南.楚图南著译选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5]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