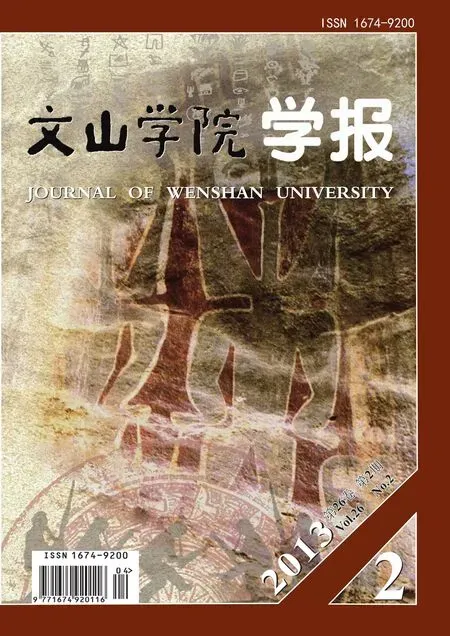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对云南农村经济的影响
何廷明 ,崔广义
(1.文山学院 政史系,云南 文山 663000;2.衡水第二中学,河北 衡水 053000)
民国时期,云南是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省份之一。据统计,1912~1949年间,云南几乎无年不灾,且多种自然灾害并发,如“云南先旱后涝”,“云南洱海中发生7 级地震……震后全省霜冻”,“云南48 县被水旱虫疫等灾”,“云南90 余县遭水旱风虫雹等灾”等等,[1](P333,338,348,349)发生死亡人数在10000人以上的特大灾害6 次,平均6年一次,其中1923~1925年滇东的冻灾导致死亡人数达30 余万人。[2](P397-399)如此频繁且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云南农村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民国时期,云南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农民即使辛勤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一旦遇到自然灾害,便衣食无着,陷于饥馑,生产停滞,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一、自然灾害对农村耕地的破坏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民国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空前扩张,大量现代技术的应用,更使得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着周围的环境,使农村的生态环境降到了极度薄弱的程度。这一切又间接地助长了自然灾害的发生,加剧了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
云南多山,森林覆盖率高,发展林业经济极有潜力,但是云南落后的农村经济使其开发变成了原始的掠夺。在民国时期,云南山区仍普遍存在着刀耕火种的现象。人们为缓解人口增长导致的生存压力,不断砍伐森林和开垦荒地,因毁林开荒以及大量煮盐、冶炼金属的燃料消耗,使森林的覆盖率越来越低。过度的砍伐,破坏了林区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23年,云南省政府派调查员下乡巡视,发现人为破坏森林的情况和后果十分严重,如景谷县“天然森林虽极丰茂,然以香盐、益香、抱母、茂蔑四井盐材之需用浩繁,而采伐又漫无限制,附井一带,已成童山。若不速谋所以保护之方,则将来不但建筑用材取求不易,即薪炭亦将感受困难矣”;姚安县山地“已一望童山,材用腾贵,樵采维艰,故无论矣。即征诸近年水旱偏灾之发生,亦从可知该县林业之亟应提倡保护”。[3]人为造成的生态破坏,促使干旱、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频发,使农村的生存环境愈加艰难。
民国时期,云南因灾致荒的耕地面积较大,特别是洪水、泥石流等灾害对农田、耕地造成的毁坏最为严重。洪水、泥石流等灾害一旦发生,耕地被沙埋石压,就不能完全恢复原貌或造成复耕的成本过高,变为长期不能耕种的荒地。1931年,易门县暴发洪水,盘龙镇1374 亩地被水冲沙埋,198 亩被毁;1948年洪水,2916 亩稻谷无收,186 亩永荒。[4](P100)1934年,江城洪灾,清畴变为沙地,腴地尽为石田。[5](P117)1935年,晋宁县被水淹沙埋的农田达5970 亩。1948年昆阳大雨,沿滇池农田被淹,耕地被冲埋,不能复垦。[6](P107)元谋县山洪暴发,水势高涨一丈有余,泛滥无涯,沿河两岸耕地,不但农作物悉数淹没,连同耕地变为沙洲,无法开垦耕种。[7](P7)1949年,富民县稻田被沙埋1458 亩,少数冲成河床,旱地水土流失319 亩。[8](P66)1946年,滇西地区雨量过多,山洪暴发,淹没稻田逾二十余万亩,冲毁桥梁二百余座,房屋、人畜之损失,不计其数。……该区耕地面积总计三百二十五万余亩,荒芜约计一百三十余万亩。[9]
可见,自然灾害造成的土地荒芜数目十分惊人。灾后农民生存艰难,无力改造受灾土地,只能任其荒芜。耕地荒芜,可耕地面积缩小,致使农业生产严重减产,粮食严重短缺,农民饱受饥馑折磨。由于大量受灾农村土地的长期荒芜、废弃,使世代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自然灾害使云南灾区的农村经济陷入崩溃境地,并由此造成恶性循环,加大了云南农村的贫困与凋敝。
二、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业生产易受气候、环境等自然因素和其他非人为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当年的减产或绝收;人口过量死亡造成劳动力缺乏;灾荒的破坏造成生产工具的缺乏;土地的抛荒等,给本来就已经极端贫困的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恶性循环。“灾荒发展之结果,非但陷农民大众于饥馑死亡,摧毁农业生产力,使耕地面积缩小,荒地增加,形成赤野千里,且使耕畜死亡,农具散失,农民与死为邻,自不得不忍痛变卖一切生产手段,致农业再生产之可能性极端缩小,甚至农民因灾后缺乏种子肥料,致全部生产完全停滞。凡此严重现象,无不笼罩于各灾荒区域,其所表现者,非仅为暂时之生产物减少,而实往往为长期经常之生产事业之衰落。”[10](P184)面对灾害打击,灾民无计可施,只能压缩或恶化生产条件,或变卖耕牛,或抵押转卖犁耙等农具。灾后他们更是无力更新和补充农具,也不能通过施肥、休耕等方式增进地力,于是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纷纷破产,他们失去了自己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为求生存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荒。
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一经发生,会直接破坏田地中的农作物,要么根本无法栽种,要么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引起大面积的减产或绝收。1932年,罗平县“自夏至秋,淫雨为灾,禾苗不实,收成仅十之二三”;[11]1939年8~9月,“昆明阴雨绵绵,山洪暴发,市内各江河水位陡涨。……市郊田亩被淹十分之八,秋收无望”,“安宁、富民、路南地势低洼,水位高出平地数尺,田亩十分之八化为泽国。……受灾黎民枕流而居,哀鸿遍野”。[12](P349)农产品的大量减产,意味着用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匮乏,从而引起劳动力素质的下降,使农业再生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农业再生产本身也会由于种子的缺乏而中断其生产链条,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水平的下降,“灾区农业再生产过程陷于瘫痪,并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2](P167)。
农作物的大量减产或绝收,势必要引起饥荒,这样就会发生大量的人口死亡和逃亡现象,从而造成劳动力大量短缺。灾后幸存的人口,也因为营养不良或疾病缠身,身体备受摧残,有的时间不长即死亡;有的体能下降,丧失劳动力。这就从整体上削弱了农业生产水平。而精壮劳动力在灾荒的打击下逃荒外出谋生,导致灾区人口结构失衡,是劳动力缺失的一个方面。
自然灾害对生产的破坏也包括对生产工具的破坏。大型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首先破坏的是人民的屋舍。1933年,昆明大水,房屋受到破坏的居民仅第六村公所造册上报的就有二百四十八户[13]。虽然房屋不属于直接的生产工具,但是在旧中国的云南农村,房屋不仅仅是农民遮风避雨的安身之所,也是一种用于储藏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蓄养家禽家畜的多功能生产场所。对灾民来说,房倒屋塌的打击可谓仅次于人口的死亡。重新修缮或购买房屋,在当时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势必要影响农业的再生产。同时,大的灾害还会造成牲畜的大量减少,也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恢复。1925年丘北大饥荒,不少人家开始用牛、马、骡、驴、羊兑换粮食,最后找不到粮主兑换,只有全部宰杀充饥[14](P312)。1925年大理地震,仅大理、凤仪、宾川、弥渡、祥云、邓川六县属,压死的牲畜就达17075 头[15](P422)。这样,灾后本来身体孱弱的灾民想恢复生产,但没有足够的畜力可以依赖,只能依靠人力或租用别人的耕牛,致使农业生产的恢复十分艰难。在滇东地区,农忙时节租用耕牛,在曲靖一年内一头耕牛需支付120 元,沾益和宣威84 元,昆明86 元,马龙86 元。[10](P26720)灾害打击下一贫如洗的灾民根本无力租用耕牛。由于农具被变卖或抵押以及耕畜的严重缺乏,使灾后的农村已无再生产能力,灾民只能用减少种植面积来缓和危机,这严重影响了灾后的生产恢复,造成生产的不足、粮食的短缺和粮价的上涨,并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自然灾害对粮食价格的影响
灾荒发生后,因生活和生产资料严重缺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成为必然趋势。灾荒对粮食价格的影响,通常表现为灾荒时的物贱粮贵和灾后的物贵粮贱。
在云南,稻米是最主要的食物,灾害到来之时,米价急剧上涨。在史料中,灾荒导致米价上涨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宣威“上年九月到本年(1919年)三月无雨,忽大霜,麦尽枯,米价大涨,每升二元五、六(平时市价四角)”;1923年,罗平三月严霜,豆麦、烟苗收成仅百分之一,造成未有之奇灾,石米价三十元;1925年,宣威大霜,豆麦枯萎,斗米价涨至四十五元,苞谷斗价三十五元(涨十倍);[16](P241)文山马关县,1919年山洪之后大旱,粮价上涨达60倍;1925年大霜,斗米价银十七、八元,饥民用草根、树皮、野菜充饥;[17](P13)在呈贡,养猪的豆糠都卖到每百斤十三元,约相当于1920年以前米价的三倍。[18](P190)当然,这是有粮出卖的情况。随着灾荒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危机心理进一步加深,除去见利忘义的奸商,人人都想着存储粮食,维持生命,最后市场上就无粮可卖。1925年,丘北县发生饥荒,市场上前期有少量粮食出售,价格升米(10 斤)价高达银币5 元(原来2 角),后期无粮出售,农村多数人家断炊,全县死亡人口达20000人。[19](P11)因此,虽然灾后粮价飞涨,但即便有钱也买不到活命的粮食。
粮价上涨的同时,其他一切非必需品的价格又在急剧下降。因为何时能渡过灾荒,人们心里没底,于是对于灾荒的恐惧,使人们不顾一切的储蓄粮食,以备活命。对于一切暂时无用的物品,都想办法换成粮食,“今既无取收获,则惟有典当田庐,暂为残息”[18](P200)。为了充饥活命,饥民们总是不顾一切代价的变卖家产、田地、房屋、车辆、牲畜、衣服、器具,甚至卖儿卖妻。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无不拿到市场上廉价拍卖。只是在饥荒的笼罩下,此等物品的市场变成了无人问津的市场,其价格低廉的程度可想而知。在丘北大灾荒中,一头大牛、一匹大马只能换取50 至60 斤包谷,每只大羊只能兑换5 斤或6 斤。[14](P312)1941年,大理鹤庆饥荒大起,1 斗米换耕牛一头。[20](P16)在市场上出卖的饥民子女,其价格也并不比其他物品高。1925年滇东大灾,在弥勒公开出现的卖人市场上,一个妇女的价值不超过一斗米。[21](P16)这些妇女被辗转其他地区又可卖上高价,巨额利润全部落入人贩子手里。
灾情缓和之后,粮食和物品的价格又会发生变动,其实这并非粮食生产过多之故。民国时期的云南,即使在丰年,人民有余粮的时间也是不多。这时期粮价下降而物价上升,是因为人们急于恢复生产,原先出卖的物品现在成为必需品,从而需求量大,价格上升。经过灾害和饥馑之后,灾民们已是两手空空,他们只能卖出收获的粮食,以换回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因此,自然灾害对粮价、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
四、自然灾害对地价及地租的影响
民国时期,云南多发的自然灾害对农村的地价和地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通常,地价的高低决定于土地的肥沃程度,越是贫瘠的土地价格越低。自然灾害对地价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灾荒到来之时地价的疯狂下落。原因是拥有少量田地的自耕农为了购买维持生命的粮食,不得不廉价出卖或抵押自己的土地,于是造成地价下跌。地主、富农、商人及官吏等,在灾区贱价购买田地,已成为普遍现象。据载,“石屏人卖田,可不能卖地契,多半是典契,等至米价涨地价落的时候,别人用很少的钱便把它取赎回去了”[22](P8)。另外,多发的自然灾害打击了土地投资者对土地投资的信心,使得土地无人问津,致使地价下落。表1 是禄丰县与马龙县6个村1928~1934年每亩农田买卖价格情况[23](P142)。

表1 禄丰县与马龙县6个村1928~1934年每亩农田买卖价格情况
通过表1 可以发现,禄丰县6个村的地价在6年内总体上涨了35%,而马龙县6个村的地价则总体下降了7%,这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上升的特殊实例。土地肥瘠的程度只能解释禄丰地价总体上高于马龙地价,但是无法解释其地价的走向问题[23](P229)。《云南省农村调查》一书对禄丰县的地价上涨是这样解释的:“禄丰近三年来是丰收之年,农产品、米谷尚有向外输出,故农村经济趋于进展。”[23](P142)可见,由于投资农业有利可图,使土地成为农村中的抢购对象,故而地价上涨。马龙则属于滇东北的灾害高发区,“且土地投资之人对土地利益可靠之信念发生动摇,有田者急欲出卖,收回资本,改营它业,而购者亦恐灾害继来,不愿出高价。是故灾害频仍,则地价下落,虽物价高涨,亦不能上涨也”[24](P44980)。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有钱人不愿投资收益不稳的土地,地价当然难以上涨。
与土地价格有关的另一农村经济因素为地租,既然灾荒会对土地价格产生影响,也势必会对地租产生影响。通常,土地肥沃,地理位置优越,抗灾能力强,产量稳定的田地,收获量比较高,土地价格就会高,相对应的地租量也会较高;反之,土地贫瘠,灾害频仍,产量低且不稳定的土地,价格就会较低,地租当然也较低。地租量一般与土地产量、地价成正比。那么上表中灾害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在地租中是不是通用的?我们发现,1934年,禄丰六村中则田地租平均占产量的74%,而马龙六村的中则田地租占产量的29.83%[24](P161,244)这与地价的走势是一致的。可见,频发的自然灾害依然会对土地的地租量产生影响。
[1]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云南建设厅档案.云南省档安馆档案,77-5-123.
[4]易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易门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俞承商,主编,云南省思茅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思茅地区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6]晋宁县志方志编纂委员会.晋宁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7]云南赈济会呈报元谋水灾.云南档案史料(第四期).
[8]雷峰,主编,云南省思茅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思茅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9]滇西灾民嗷嗷待哺:灾民三十万食草根树皮,土地荒芜逾百分之四十[N].大公报.1946-10-22.
[10]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1]罗平县长魏泽民电告灾荒[Z].云南档案史料(第二期).
[12]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第八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昆明市养济院档案.昆明市档案馆藏.32-17-21.
[14]洪兆权,刘光汉.1925年大饥荒的回忆.李道生.云南社会大观[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15]民国云南通志馆.续云南通志长编(上)[M].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校发行,1985.
[16]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云南天气灾害史料[M].昆明: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印行,1980.
[17]刘锦龙主编,云南省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马关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18]陆复初.昆明市志长编(卷十一)[M].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印行,1983.
[19]云南省丘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邱北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0]孙浩总编,云南省鹤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鹤庆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21]肖鹏,罗荧.牛年纪事.中共弥勒县委会,弥勒县人民政府.弥勒县民国史话[Z].中共弥勒县委史志办发行,1993.
[22]马子华.滇南散记[M].昆明:新云南丛书社,1946.
[23]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云南省农村调查[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4]聂闻铎.川滇铁路宣昆段地价及土地征收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5 辑)[Z].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美中文资料中心,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