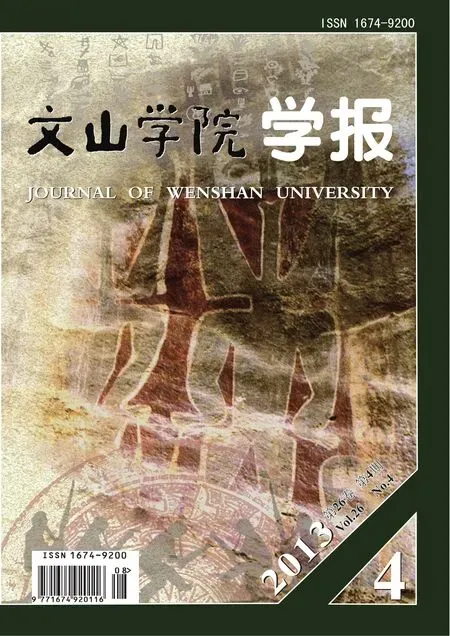吕思勉《中国民族史》解读
李明奎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大概取于《中庸》一书中“诚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意,江苏常州人。六岁时,接受私塾教育,十二岁后,因家道中落,改由其父母、姐姐等教授,开始系统的学习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之书。据吕思勉先生自述,由于他性好考证,故逐渐进入史学一路,二十三岁后,即专意治史。其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社会史、通史和断代史,后来,受屠寄的影响,乃留意中国民族史研究。当时,日本侵华逐渐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西方宣传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咆哮漫天;而民国政府肇建,一切方兴未艾。如何抟成一新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维护新兴的民国政府,吕思勉先生遂写了这部《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这两书出版后,曾一度分别再版。近年来,学界以吕思勉与民族史为题的研究日益增多,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对吕思勉先生的民族思想进行探讨。①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吕思勉文集”为题,将《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两书题为《中国民族史两种》,合为一刊重新出版发行。笔者即以此版本为主,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对吕思勉《中国民族史》进行一简单的解读。
一、民族见解
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以往主要分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种。吕思勉先生于1934年写成的《中国民族史》一书是以横向叙述的方式对中国民族进行研究的。该书以族别史为主,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划分为汉族、匈奴、丁令、肃慎、羌族、藏族、白种等十二个族群,进行横向的论述。每个族群为一章,一一叙述其起源、政治变迁,然后论述该族类的风俗文化,有分析也有综合,并将专门的考证附录于相关篇章之后,以供读者参考。在这十二章之前,又贯一篇《总论》,叙述全书的体例和作者对各个族类的基本看法,可算是本书的总纲。在《总论》前,又有友人陈协恭写的一篇《序》,对该书做一言简意赅的评价。由于吕思勉先生采用族别史的方法,故没有对民族进行分期,也没有对民族提出明确的看法,②只是认为汉族的由来,虽一时难以确定,但是自有史以来,汉族确实是生活于中国本土的;而且,吕思勉先生还认为“汉”字用为民族之名,久已不关朝号,而“夏族”二字,旧无此辞;华族用于民族之名,则嫌与贵族相混;若称中华民族,词既累重,而与合中华国民而称为一民族,仍复相淆。既然称名不能屡更,而涵义则随时而变,故“片辞双语,其义俱有今古之不同。训诂之事,由斯而作。必谓汉为朝号,不宜用为民族之名,则今日凡百称谓,何一为其字之初诂哉?废百议一,斯为不达矣”。[1](P11)(以后所引,凡是出自《中国民族史两种》一书的,为节省版面,均不再一一注释。)因此,在吕思勉先生看来,“汉”用于吾民族之称谓,还是很恰当的。
不仅如此,吕思勉先生在排比、归纳史料的基础上,对十二个族群提出许多精辟的看法。如《貊族章》认为箕子立国朝鲜,必不在今天的朝鲜境,度其大较,当在燕之东北,与貊杂居。《苗族章》言今之所谓苗族,实际上应为汉代长沙武陵蛮之后,而与古之三苗没有关系;今天所谓的苗族,其本名大概为“黎”,我们以其居于中国之南方,遂称为“蛮”。这些都是该书中的精彩处。而且,吕思勉先生对于中国之历史极为熟悉,又有极深的经学、小学功力,故对于文献中的记载,往往目光如炬,一眼就能看出其本质。《鲜卑章》叙述奚人首领死,其兄弟吐干继位,因与大臣可突干不和而奔唐,国人立其弟邵困。吕思勉先生于此自注:“从《辽史》。《唐书》云李尽忠弟,必误。”又《肃慎章》论古代之肃慎,即后世之挹娄、靺鞨,吕思勉先生于此举了两例,其一为汉代时只有挹娄,虽然《晋书》说“肃慎,一名挹娄”,此必是晋朝时挹娄人仍以肃慎之名自通,不然,《晋书》当云“挹娄,古肃慎国”,不得云“肃慎,一名挹娄”也。吕思勉先生于此自注云:“《魏书・勿吉传》:‘旧肃慎国也。’‘旧’字盖指晋时言之,若指三代以前,则常用‘古’字矣。”如此如必误、必是、一望而知等措辞,均可以看出吕思勉先生深厚的史学素养。
由于吕思勉先生深厚的经史功底,对文献极为熟悉,许多论断,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轰动,即在今天,仍有不少的声音与吕思勉先生的观点相同或相似。如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方位命名,是否古时即是如此,还是后人所加?是否可据此方位来判断各民族?对于这些问题,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提出:“夷蛮戎狄,其初自系方位言之。然游牧之族,迁徙无常,居地可以屡更,名称不能数变,则夷蛮戎狄之称,不复与其方位合矣。居地迁徙,种族混淆,皆常有之事。故书中夷蛮戎狄等字,不能据以别种族,并不能据以定方位也。”“夷蛮戎狄之称,其初盖皆据方位,其后则不能尽然。……故见于古书者,在东方亦或称戎,西方亦或称夷也。”此见解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民族和阅读古书,实在是一个极好的提醒。台湾学者刘义棠在《中国边疆民族史》中加以发挥,认为:“所谓夷狄,是诸夏以外各民族的通称。有时,亦以夷蛮戎狄等名称以泛称诸‘异族’,但却无严格的分际与特殊的意义存在。……夷蛮戎狄,若依其出现次序而言,戎与夷见于殷墟书契,而狄与蛮则见于宗国鼎彝。典籍之中,四名通用。……夷与戎可以互用,……戎与狄亦复相通,……蛮与夷亦可合称。……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方位,而成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之专名。古来并无此说,似肇始于春秋而完成于汉初。……在春秋以前,族称上冠以方位者亦有,但并不固定,常相互混用。”[2](26-29)此段可以看成是对吕思勉先生观点的最好注脚。又如《鲜卑章》,吕思勉先生在附录的文章中,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当时的地理知识,认为后魏之先,出自西伯利亚。此语不仅在当时被看成荒诞不经,即便在今日,也有许多人难以置信,然亦有学者持类似的论断。刘义棠先生结合《后汉书》记载、丁谦地理考证以及西方学者、日本学者的语言学研究成果,认为:“鲜卑族人,在上古之世,初居于今西伯利亚;‘西伯’即‘鲜卑’之音转,‘利亚’乃语尾词,故其义为‘鲜卑之居地。’”
二、文化价值评判
吕思勉先生不仅具有极精湛的经史功底,而且对中国古代以文化区别种族的传统有极深的体会,并加以透彻的发挥。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就说:“其实,为人类相亲爱、相了解的障碍的,是心理而不是体质。所以,画人类鸿沟的,是文化而不是种族。”“文化之为物,是最能使人爱慕,而忘掉人我的界限的。两种文化相形之下,亦是最易使文化劣等的民族,自惭形秽而愿舍己从人的。”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吕思勉先生高扬文化评判的旗帜,认为汉族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其文化发达最早,故在与其他种族的交往中,常以文化较高的缘故,在民族交流、融合中起主导作用。在该书第一章就明确表明:“一国之民族,不宜过杂,亦不宜过纯。过杂则统理为难,过纯则改进不易。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他族虽或凭恃武力,陵轹汉族,究不能不屈于其文化之高,舍其故俗而从之。而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藉武力以自卫,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灭,用克兼容并包,同仁一视;所吸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巍然以大国立于东亚。斯固并世之所无,抑亦往史之所独也。”其后又于《鲜卑章》议论:“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致之。过于朴僿,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若其所居近塞,乘中国丧乱之际,能多招致汉人,则其兴起尤速。”因此,吕思勉先生认为,在各民族的交往中,汉族是起着主导作用的,而各民族因其进化较为迟缓,故多保存着汉族古俗。如《匈奴章》对匈奴风俗、文字的看法,《苗族章》对苗族风俗与汉族古俗的叙述等均持此见解。
由于吕思勉先生较为重视文化在区分种族中的作用,故论述每一族群时,均先介绍其起源、居地,然后叙述其风俗文化,且多与汉族文化进行联系与比较,指出何时与汉族交往,何处吸收汉族文化,何处又同化于汉族文化。更可贵的是吕思勉先生对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也并叙不讳。在吕思勉先生看来,培育民族精神的养料是历史上的光荣与苦痛。光荣自是人人所乐道,至于苦痛则多避而不讲,害怕挑起民族恶感。然而,苦痛之为养料,与光荣正同。或许其力量还要深厚。因此一个民族曾经受过的挫折,大可不必自讳;而从前各民族间的冲突也不能一笔抹杀,避而不谈。准此,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的《序》中宣言:“为要求各族亲近、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本书不取这种态度。”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吕思勉先生也对各民族间的冲突并叙不讳。
三、民族主义之阐述
吕思勉先生幼承庭训,对古圣先贤之教,默契于心,其后接受新思想,关注国计民生。因此,吕思勉先生极为欣赏大同社会并认为大同社会是一个可以实现的蓝图,其关键在于民族的自信与自兴。故,吕思勉先生积极提倡一种国民自兴的全体民族主义,反对狭隘的种族主义。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一书中,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创痛、中国民族之现状进行了简洁的叙述,对郑思肖、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民族思想进行了诚挚的发挥。在彼书的结尾,吕思勉先生写到:“我们要尽力于大同,要尽力于全世界,对于本族的文化,就不可不善自保守,发扬光大。……所以民族主义,在今日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必须提倡的。只不要过于陷于偏狭就是了。”“民族的自信力,是不可以没有的。近来有人,因中国一时的衰败,……竟怀疑到中国民族的能力。甚而至于有人说:‘中国民族,已经衰老了,不可复振的了。’这真是妄自菲薄了。……请再追想我民族居于此土之久。……我们要追想已往的光荣,我们亦勿要忘掉已往的创痛;我们要凛然于目前的危机,我们要负起目前的责任;我们要服膺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我们该鼓起民族复兴的勇气。”
这番思想,在《中国民族史》中照样洋溢着,只不过略显沉郁而非彼书的大声铿锵。在第一章《总论》的末尾,吕思勉先生就指出:“今日所遇诸族,则非复昔时之比矣。狃于蒲骚之役者,虽遇小敌,亦不免败绩失据。况今之所遇,固大敌乎?可不深自念哉?”就蕴含着民族自信、民族自兴的信念。至《貊族章》论朝鲜之向华时云:“朝鲜当元时,薙发易服,几举国同化于胡,然卒能自振拔,洗腥膻之习,而沐浴中国之文明,可谓难矣。不幸其尚文治而忽武功,逞义气而好党争,亦与宋人类。至酿成近世之局面,卒为东邻所吞噬,亦可哀矣。然宗尚中华,感恩向化,列国中无如朝鲜者。”此下,便例举史实,证明当清之兴起时及清人入关后,朝鲜的统治者和朝鲜人民是如何心怀明王朝的。这段史实亦见于吕思勉先生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所不同的是两处吕思勉先生所寄发的感慨。彼处云:“终李朝一朝,始终没有用清朝的年号,奉清朝的正朔。天下最可贵的是人情!这种深厚的感情,在历史上遗传下来;将来中国人和朝鲜人,总有互相提携的一天的。”[3](P509)而在《中国民族史》中,吕思勉先生则感慨:“终李朝,未尝用清年号,奉其正朔。呜呼!以数千年之史籍观之,中国之于朝鲜,诚犹长兄之于鞠子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而今中国之于朝鲜何如哉?”一句“而今中国之于朝鲜何如哉”,蕴含吕思勉先生多少的愤概与辛酸。
由于吕思勉先生素抱大同思想,倡导全民族自兴的民族主义,故对推行狭隘民族主义的做法极为不满。以清朝为例。清人未入关时,极力拉拢汉人为其效力;及其入关后,发布薙发令,强迫汉人薙发,又大兴文字狱,摧残天下学术风气,导致读书人不敢轻议国是,而将精力投入到考据、训诂和歌功颂德;又组织人力,编纂大型图书,以耗磨天下士子的精力。后之治史者,多对清朝统治置不满之词。柳诒徵先生曾感慨:“前代文人受祸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有思想才能者,无所发泄,惟寄之于考古,庶不干当时之禁忌。其时所传之诗文,亦惟颂谀献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时序及寻常应酬之作。稍一不慎,祸且不测,而清之文化可知矣。”[4](P813)此乃从清人的统治政策而评论其文化。吕思勉先生在该书中则直接针对清王朝的统治政策,认为:“清承金元之后,文化稍高,又能粗知书史,故其待汉族,暴虐无异金元,而又益之以深鸷。 ……清代深谋,尤在联合满、蒙,以制汉族。不特关东之地不许汉人屯垦,即于蒙地亦然。奉天将军岁终例须奏报‘并无汉人出关’,至末叶犹然也。然而究何益哉?藏舟于山,夜半,有力者负之去矣!坐使满蒙之地,广田自荒,致生异族之觊觎,此则其禁阻汉人之效耳。今日关东,欲求一但知满语之满人,岂复可得?升允崎岖,终于齑志,蒙人之所以助满者,又何如乎?沃沮叶鲁,终即华风;白水黑山,转滋异类。清朝之祖宗,何毋令后人效汝拙乎?然此皆汝曹自为之,又何咎也?”其感慨极为深沉。
四、读书门径之指示
从来青年读书,常感无门之苦。吕思勉先生沉浸于传统历史文化的熏陶中,对于教育极为热忱,对于青年读书常给予亲切的指导。在《白话本国史》中就说:“这一部书……虽然和《新史钞》的体例相去尚远,然而其中也不无可取之处。给现在的学生看了,或者可以做研究国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这一部书卷帙虽然不多,然关于参考的书,我都切实指出(且多指明篇名卷第);若能一一翻检,则这部书虽不过三十多万言,而读者已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且不啻替要想读书的人,亲切指示门径。”③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亦说:“我希望中等程度以下的人,读此而可得一大概的观念。……惟程度高一点的人读之,或者觉得略而无所据。如有此一类人赐读,我希望他以本书当做一种引线,依此篇所依据,自行翻阅原书。……此书悬拟的读者,是中等学生,我的意思,务求为之多输入常识,多指示读书的方法。所以此书的注语,特别详尽。”笔者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极便于初学,故就其目前所知,将《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指示读书门径之路,分类例举如下。
1.指示如何读《中国民族史》。此书以文言文撰写,且多专门的考证,对于初学者来讲,极为难读。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所附的参考书中就说:“此书(指《中国民族史》)内容,专门的考据颇多,……但为普通读者计,却亦有一优点,即其于各族的文化,叙述颇详,不徒可见各族进化之迹,且亦颇有趣味。……读者取其普通的叙述和议论,将于专门考证之处,暂且搁过亦好。”读者先读普通的叙述和议论,而先略过专门的考证,此不啻是吕思勉先生自告读此书的钥匙。而且,吕思勉先生把专门的考证附录于相关篇章之后,于正文叙述时,大多直接采用其考证的结果,并自注:读者欲知详情,请参阅前所述某某章或详见作者附录某条。如此的安排,将正文与所附录诸考证联为一体,前后照应,读者自可依着吕思勉先生的提示一一寻览。
2.指示对某一问题的参考资料。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初学者常感觉资料不足或难以搜寻,故其研究,多浮于表面,泛泛而谈,十分空疏。吕思勉先生对于此问题,也给出自己的建议,常以“可参阅某某书”之类的语言表达。如《汉族章》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语,意同辞异,古书往往有之,可看俞氏樾《古书疑义举例》。”又大夏之名,古书常见,难以明白,吕思勉先生自注:“大夏之名,古籍数见,虽难确指其地,亦必不得在葱岭之西也。详见近人柳诒徵所撰《大夏考》,载《史地学报》。”又内陆腹地,多尚文,故民风文弱,而边境和严寒之地,多右武,故民风剽悍。此即前人所讲的地缘因素。然其具体的论述有哪些,初学者多不易明白。吕思勉先生即于此书中点出:“春秋时强国,曰晋、楚、齐、秦,其后起者则吴、越,皆与蛮夷杂处。其居腹地者,如鲁、卫、宋、郑、陈、蔡等,皆寖弱以即于亡。一由无与竞争,一亦由四邻皆文明之国,非如戎狄之贵货贱土,拓境不易也。梁氏启超《中国之武士道・序》,论此义颇悉,可以参看。”如此的提示,于该书中比比皆是。
3.指导如何阅读某一本(类)书。初学者读书,往往不了解某书之特点在何处,读时从何处入手,常因不得其门而中途放弃。对于这些问题,吕思勉先生也给出自己的建议。如孔子所修的《春秋》,极为简洁,初读时应注意哪些问题,从何处入手,前人多讲《春秋》之义,告诫读者读《春秋》当重大义,然读者在具体读时,应如何来了解《春秋》之义?对于这一问题,吕思勉先生给出他自己的解答,认为能分别其事与义,乃治《春秋》者之金科玉律。“能分别其事与义,则《春秋》作经读可,作史读亦可。不然者,则微特不能明《春秋》之义,于《春秋》时事,亦必不能了矣”。又如对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体例的见解,均足发人深省。
4.对某一代学术的总评。在中国历史上,朝代不同,学术自异。其相互间的区别、高下如何,某一朝代,其学术之特长处又如何,是读中国书学中国史的人应该知道的。如两汉均以经学著名,然两汉之经学,是否一致,其间孰高孰低?吕思勉先生在《汉族章》所附录的《夏都考》一文谈到:“西汉经说,多本旧闻,虽有传伪,初无臆造。东汉古文家,则往往以意穿凿。今日故书雅记,百不一存,故无从考其谬。然偶有可疏通证明者,其穿凿之迹,则显然可见。……魏晋而后,此风弥甚。”就认为西汉诸儒说经,远胜东汉及以下朝代。又宋人讲学,极重心性之磨练,清人认为其空疏无用,遂自标其学为“汉学”,以与“宋学”相抗衡,深沟高垒,门派森然。其间有无偏激处?宋人之学有无可取?清人之学,又是否真是汉学?柳诒徵先生、钱穆先生等均对宋学、汉学提出自己的见解,极为发人深省。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对于清人所谓的“汉学”亦多所纠正。清人以满洲语重新改译《金》《元》《辽》三史中的人名、地名和官名,纂成《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一书,甚为自得,然实际上徒增烦扰。吕思勉先生就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大抵研习四夷事,专据音译附会,最不足信。清人自谓能知北族之语,于旧译辄好妄改,或加解释。姑无论北族言语,不皆同于满洲。即女真确与满洲同族,其语亦有今古之异,地域之殊,安得辄武断邪?其谬误百出,宜矣。”此段批评,可谓实允。又清圣祖把“哈剌乌苏”译为“黑水”,遂以康、卫、藏为三危,犹中国之三省。吕思勉先生感慨:“其说殊为荒谬。然世多信之者,以哈剌乌苏译为黑水耳。其实舍‘泸水’之‘泸’字不取,而转以‘哈喇’二字相附会,真所谓舍近而求远也。”书中关于此类的评述,举不胜举。暂不论是否能得到每个人的首肯,但其角度实能令人耳目一新,循着吕思勉先生的指示做深长之思。
五、本书之瑕疵
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一书,本文仅从上述几个方面加以解读,希望对阅读此书的读者有些许帮助。最后,本文想谈谈此书在史料运用和行文方面的一些小瑕疵,以便读者更好地运用此书。吕思勉先生在使用《二十四史》等书籍时,多为当时石印或排印的线装书;[5](P144-145)而且,吕思勉先生在运用史料时,常概括其大意,有时将几种史料经过组织、排比归纳而连在一起,故有些地方与今本原书不太一致。而今人排印出版时,对此未加注意,或者为保持此书原貌,未作改动。今选择几条分析。
《貊族章》叙述貊族丧祭之风俗时,在夫余以“殷正月祭天”下自注:“此从《三国志》,《后汉书》作‘腊月’。”然后又引史料叙述句丽、濊、马韩的丧祭风俗,最后又在马韩一条下自注:“以上据《后汉书》。”至此,读者不禁疑惑,此“以上”断自何处?高句丽耶,濊耶,还是上自夫余?今检《三国志》,知吕思勉先生此段叙述与《三国志》大异,再检《后汉书》,细心勾稽,方知此处只有“夫余以殷正月祭天”几字采自《三国志》,其余自夫余以下至马韩所云,均采自《后汉书》,然文字略有小异。今分别列之于后。1.夫余“以蹄占其吉凶”,《后汉书》作“杀牛,以蹄占其吉凶”;2.句丽“灵星”,《后汉书》作“零星”;“隧神”,《后汉书》作“襚神”(《校勘记》云:“《校补》谓‘襚’,《魏志》《通志》并作‘隧’。”);3.濊“常用十月祭天,……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后汉书》“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一句在“常用十月祭天”之前(《三国志》同《后汉书》);4.马韩“亦如之”,《后汉书》作“亦复如之”;“建大木,悬铃鼓,以事鬼神”,《后汉书》作“建大木以悬铃鼓,事鬼神”;5.马韩“又立苏塗”,吕思勉先生引《魏志》自注曰:“诸国各有别邑,为苏塗。”而《后汉书》章怀太子注引《魏志》曰:“诸国各有别邑,为苏塗。诸亡逃至其中,皆不还之。苏塗之义,有似浮屠。”[6]注释比吕思勉先生自注较详,然《后汉书》此处仍与《魏志》原文有别,考《三国志・魏志》,原文为:“又诸国各有别邑,名之为苏塗。立大木,悬铃鼓,事鬼神。诸亡逃至其中,皆不还之,好作贼。其立苏塗之义,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恶有异。”[7]吕思勉先生于后叙述貊族之人喜好歌舞时,引《后汉书・夫余传》赞之:“行人好歌吟,无昼夜,音声不绝。”而今本《后汉书》作:“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羌族章》所附录之《鬼方考》一文,引用清人宋翔凤之《过庭录》时,把“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见《诗・小雅・小明》)引成“我征自西,至于艽野”,把“脯鬼侯以享诸侯”引成“脯鬼侯以享鄂侯”(见《礼记・明堂位》)这些差异或者疏误,可能跟吕思勉先生所引用诸书的版本不同有关。
又吕思勉先生著述,因对文献极为熟悉,常将不同文献的记载,经过其细心的归纳组合在一起,极为流畅但初学者有时不容易把握。如《貊族章》引用史料叙述夫余之丧俗时,自“丧皆用冰”至“有棺无槨”一段,乃采自《三国志・魏志》原文,然与《三国志》原文略有小异。自“停丧五日”以下至“大体与中国相仿佛”一段乃采自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之文。吕思勉先生于此将两种不同的文献别出心裁的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家之言,缺憾在未分别标注引自何书。又如《羌族章》,在所附的《鬼方考》一文中,引用宋翔凤的《过庭录》证“鬼方即九方”时,吕思勉先生概括宋氏原文,而以己意出之。
这些均是吕思勉先生此书中的小瑕疵,然亦不能算是瑕疵,因为各人使用的版本不同,故文字稍有异同,且前人引述,多节录原文或概括原文,以己意说之,未必如后人这般严格。而且,笔者认为读一本书、评一部书,应看其大处、看其精彩处,而非纠缠于一枝一节的考证与纠缪,尽在小题目小问题上大作文章,以讥诮前人、彰显自己。这样的心态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厚道、不谦虚的。个人认为,此书中的考证极为精审,书中用文化区分种族的方法、对民族主义的阐述以及对初学者读书门径的指示等,都很精彩,也很实用。诚然,此书作于上世纪,一些提法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而且,书中的一些叙述,由于材料的局限,不免有疏误之处,这是很正常的。但若因吕思勉先生非民族史专业出身,其书叙述,错误较多,因而得出此书不值得参考的看法,笔者实在不敢赞同。今人好用专家之学的眼光来审视、批评前人的通人之学,自见其漏洞百出,难以满足今人之需求;今人好从承平时代的角度来考察前人的乱世之学,自难以明白其中一言一语的深意所在,故讥其无所为而为;又清人治学,率多门户之见,其持论自难以平允,前人多所指责与纠正,今人不知,一面高抬“学术自由、学术客观、学术公平”之旗号,一面对自己熟悉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人物及其著作,则高抬入天,不允许别人轻议其非,而对自己不熟悉、与自己专业无多大关系的人物及其著作,则任意讥诮,就其某处失误,大力发挥,又岂非门户森然、派别林立?又岂非重蹈前人之覆辙而不自知?又岂是学术之客观与公平?
因此,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一书,尽管不少学者对其诸多批评,但笔者仍不虑学识之浅陋,将其介绍给广大学习和研究中国民族史和中国历史的读者。
注释:
①姚大力:《润物细无声——读吕著<中国民族史>》,(载《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2期)对此书的特点做了介绍,并说“最近重读这部著作,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受益于他的书,甚至将他的书置于案头,当作工具书随时翻检的人们,或许会远远多于在自己论著中直接引用吕先生的作品的人”。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在《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文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该书的内容和价值。另外,曲阜师范大学袁振堂在其硕士论文《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述论》(2008年完成)中对此书略有介绍。赵学东、王东合写的《吕思勉与中国早期民族史学科体系的构建》,(载《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从构建民族史学科体系的目的、如何理解民族的概念、如何理解民族的构成、如何理解民族关系、如何理解民族起源、如何理解汉族、时于其他学科的借鉴等七个方面探讨了吕思勉先生对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的构建;随后王东在其硕士论文《论中国民族史学科构建——我国20世纪早期三本〈中国民族史〉对读研究》中(此论文在赵学东教授的指导下于2007年完成)从结构、资料、内容、成书目的、民族分期、民族关系、民族起源、民族分类、汉族观念等方面对吕思勉、王桐龄、林慧祥的《中国民族史》进行了细致的研读讨论,从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构建的角度探讨了三书的贡献与不足。
②作者对中国民族的分期及其定义,略见于《中国民族演进史》一书。在书中,作者将中国的民族从整体上分为“中国民族的起源、形成、统一中国本部、第一次向外开拓、五胡乱华后的中华民族和近代以及现状”七个时期,进行纵向的叙述;并将民族定义为:民族,是在具有客观条件(种族、语言、风俗、宗教、文学、国土、历史和外力)之基础上而发生共同(对外即可称为特异)的文化;并由此产生民族意识而相团结的集团。(见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3页。)
③吕思勉.白话本国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页。作者于此书中亦有许多对初学者的具体指导,不胜枚举,读者若真能细读一过,真不啻得到许多有益的教导和读书门径。
[1]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M].台北:中华书局,1982.
[3]吕思勉.白话本国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G]// 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6.
[6]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M].台北:中华书局,1973.
[7]陈寿.三国志・卷30[M].台北: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