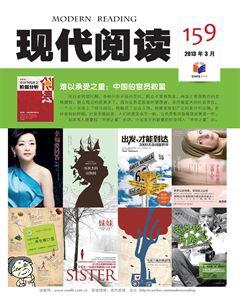一个人和一本书的命运
早期的经历
顾准,生于1915年7月1日。1927年从黄炎培所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后,经人推荐、介绍进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在潘序伦的指点下,顾准发愤自学,几年后甚至兼任了之江、沪江等几所大学的教授。1934年,他写出第一部会计著作《银行会计》时,年仅19岁。
1934年初,以顾准为核心,成立了一个自发的秘密进步团体——进社,主要研习马克思主义。1935年2月,顾准正式加入中共地下党。不久赴北平,参加了闻名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翌年2月,他回到上海,先后出任中共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江苏省委职委宣传部部长、书记,江苏省文委副书记。1940年8月,他离开上海,进入苏南抗日根据地,任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部长、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和财政厅厅长等职,其间还一度赴延安中央党校进修。
1949年5月,顾准以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干部队伍)队长的身份,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随即被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并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权重一时。可是,他很快就运交华盖,成了几次重大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政治运动的落难人
顾准学历不高,但自学有成,在中共建国初期的干部队伍中,实属屈指可数的财经管理人才。大凡真正有知识、有才华的人,在国家机器新的管理者们普遍以“土包子”自居并自诩的时代,就难免不被摒出局了。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有一次与朋友吃饭、谈天,顾准兴之所至,脱口说了句:“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是可以当副总理的。”1952年,在中共发起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顾准被突然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罪名是什么,至今都不清楚,档案中都查不到。但前述与友人闲聊时的半句“大话”,肯定是一个不成文的罪过,则不会有什么疑问。
第二年,顾准奉调举家进京,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海阳工程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都是无足轻重的职务。而在1957年和以后的1965年,又两次被划为“右派”分子,打入另册。随后,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只能以笔名从事著译工作。
“文化大革命”对顾准这样的人,更如同一场灭顶之灾。1968年4月,妻子汪璧被迫害致死,连遗体也未获一见。5个亲生子女,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不得不与父亲划清界限,中止了往来和联系。
孑然一身的顾准,并没有向精神的高压和物质的困窘屈服,而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孤寂和清贫的环境里坚持读书和思考。这期间,他拟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以十年时间,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先做一番“漫游”,随后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历史的“探索”。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除了生重病被迫休息之外,全部时间都在写作和读书。他当时的感觉是:仿佛又回到了30年代流亡到北京的那种生活,因而是那样高兴。可是,对于这位老共产党员,这样的人生对比,实在也太冷酷了!
踽踽独行的思想者
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批判孔子的问题。后来,又说已经折戟而死的政治对手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一时间,各种报刊杂志的“批林批孔”文字难以枚数,不仅几亿平头百姓被卷入了进去,连一向研究有素的文豪、学者也痛改前非,披挂上阵。
在这种社会意识疯癫、学术是非颠倒的政治气候下,身居北京的顾准却恍若远离尘世,不附势,不媚俗,在与上海的胞弟陈敏之的通信里,提出并讨论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理论课题。其中,有的是答复陈敏之所提的问题,有的是和他讨论甚至争论某一问题,有的是他所写的读后感。顾准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清醒的理论思维写下的这些笔记,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读来,仍可感受到难能可贵的思想超前性和理论穿透力。
例如,在谈到民主政治时,顾准承认,“我赞美革命风暴”,然而问题在于革命胜利以后,是“继续革命”,强化“革命神话”,还是改弦更张,转而以经验主义的立场安排现实层面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机制。他指出:“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好吗?“以此比喻一九一七年,那就是斯大林、布哈林等轮流当了总统,并且联共分成两个党,先后轮流执政。设想一下,这么办,十月革命会被葬送掉吗?我不相信。”至于对所谓人民当家做主的直接民主论,顾准的独到见解是:“一七九三年法国国民公会是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则是无产阶级直接民主制的历史根据”,而所有关于直接民主制的原则教义,则出自马克思对法国这两次政治事件的理论总结——《法兰西内战》。这一原则教义虽有道德理想之热忱,但从未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所以,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要不奢求人民当家做主,而应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影响力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
有谁能想象,20年前那个黑暗的历史隧洞里,竟有这样一团思想火花在默默地燃烧、发光!可遗憾的是,1974年12月,身心久已遭受摧残的顾准,终因肺癌不治病逝,京、沪两地的学术通信戛然而止。
辗转问世的磨难命
顾准离开人世后,生前的大量著述和译著均相继出版。唯独这本《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问世,跟著者的人生际遇一样,称得上是一波三折。
1977年,即顾准辞世后的第三年,陈敏之将亡兄当年陆续寄来的笔记式通信,加以整理分类,重新抄写了一遍,并装订成册。当初并不存有出版的奢望。
1984年,文化界一位友人读到顾准这本笔记体的通信集,赞叹不已,热心地推荐给北京三联书店,希望能出版。编辑审读之后,写下评语:“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见识。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问题,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那种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三联书店负责人也认为:“今后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对于各色各种的单本的‘奇书始终要给予支持。……顾准之作,我想是属于‘奇书之列的。”然而,到1986年,这部“奇书”通过那位友人,被默默地退了回来。
第二年年初,陈敏之又满怀希望,把请人重新誊写并校正的这份书稿,送到上海三联书店。和在北京一样,编辑也认为很好,可以出版,但结果还是退回。
这年年底,一位在文化单位工作的年轻人,读了这本书稿后,主动热忱地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写了长信推荐出版。该社的有关编辑认真审读过后,惊叹“作者竟能在文化大革命万马齐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一系列真知灼见,他的智慧和勇气实在令人钦佩”。三审通过,书稿出版已成定局。1989年年初,陈敏之校读了清样,又请王元化撰写了一篇序言。不料,这年春天,政情丕变,这本书又一次夭折。
此后,又是整整3年过去。经过王元化大力推荐,顾准的这部遗著,终于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尽管这样,清样中原有的两篇文稿还是被抽去了。一曰《直接民主制与“议会清谈馆”》,一曰《民主与“终极目的”》。从内容看,对照中国现实政治,这两篇似乎有着更为直接的启蒙和醒世意义。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书名,是编者陈敏之提出,并征求过王元化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仅体现了书中每篇蕴含的主要思想和精神,而且也如实地概括了著者顾准一生的思想历程。其实,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都经历过理想主义时代。不同的是,顾准是这中间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的一位先行者。
然而,上述一个人和一本书的命运,仿佛在昭示人们:在这个有着贡献思想家的传统的古老国度里,当代知识分子的行列中,也不乏勇敢的思考着,但他们缺少的,正是一个培育和造就思想家的社会环境。
(摘自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书里书外》 作者:贺越明)
——第十七届《哲学分析》论坛专题研讨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