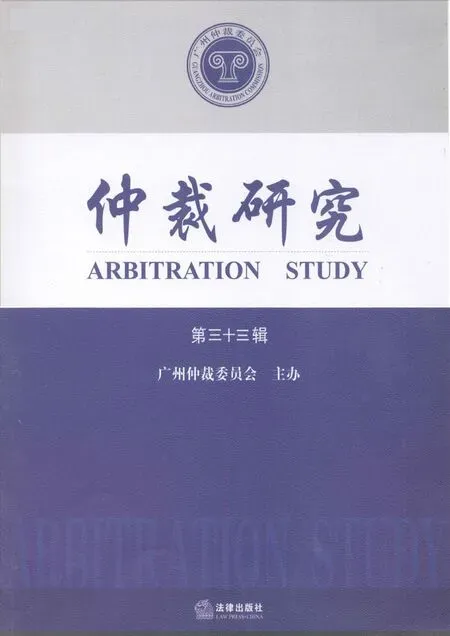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去身份化及其属地性(下)
张春良
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去身份化及其属地性(下)
张春良*
(续上期)
三、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性
(一)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因素
属地性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存在方式,它意指国际商事仲裁总是具有特定地域身份,这一身份的获得是通过与特定国家或者地区的属地连接点的指引和关联而完成的。属地性为国际商事仲裁确立了它在世俗国家体系中的“立锥之地”,生成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身份并赋予它“原产地国”印记,通过与特定国家的关联而为该国设置了司法支持和司法协助的责任,但国际商事仲裁也在同等程度上以对价的方式将自身托付给了特定的国家。即便在国际商事仲裁这一概念上坚持“最大化主义”(maximalist)的人也只能“最小化”(minimalist)但不能“虚无化”(de-nationalize)它的属地联结。“最大化主义”表征一种倾向,即不论各国立法之分歧如何,一切现代国际仲裁法都承认并表达出增加国际仲裁相对于国内法的独立性;“最小化主义”则在相对的意义上指出,只要涉及外国因素该仲裁即为国际仲裁,但一俟属地联结得以确立,则该仲裁终究会被“再国内化”(re-nationalized);在最大化与最小化主义的对决之间,最小化显然更为务实,因为“把仲裁从各国立法体制之中分离开来的观念将受限制,只要仲裁裁决的执行这一终极补救措施被控制在国家之手。在如下事实之下就是这种情况,只要国家拥有唯一的权力来调动确保仲裁裁决得以执行的公共力量(police)和其他组织。已有人提议,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法院,以使它作出的撤销或者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能拘束所有国家法院。要求许多国家乐于同意把真正的国际仲裁观念延伸到后仲裁程序阶段,这是不可能的。”①在这一意义上,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联结的“虚无化”也就不可能。
谈及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联系因素,则不得不转向法律关系本座说,因为后者开创了属地联系的先河。在国际私法中,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代表了最为辉煌的成就,站在萨维尼的肩上英美法系国际私法得以可能并获得新生。法律关系本座说就是典型地关于属地联结的学说,它按照性质不同将法律关系划分为若干种类,并为每一类型的法律关系指定一个本座(seat),该本座将特定法律关系与特定国家进行配对,从而完成属地联结的指引过程。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化同样必须诉诸于直接的或者需要转化的连接点以获取自己的特定身份。据学者研究,由于国际商事仲裁涉及面广、程序阶段多,而各国仲裁立法态度不一,这导致相关可能的连接点非常多,这些可能的连接点包括:②
“独任仲裁员或多人仲裁员的国籍与住所;当事人的国籍;当事人的住所、居所或公司总部所在地;与争议实质问题相关的其他连接点(诸如合同签署地、履行地、一切所涉财产所在地与损失发生地);仲裁机构国籍或总部所在地;仲裁地;裁决执行地;仲裁程序法;仲裁实体准据法。”
这些连接点中尤以仲裁地和仲裁程序法所属国为典型,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它们有所侧重。究其原因在于,首先这两个连接点在国际商事仲裁的各个环节,包括仲裁管辖权、法律适用、司法支持和司法监督、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因为涵盖大部分国际社会的《纽约公约》明确规定了这两个联系因素,以致于即便国际社会不可能有统一的仲裁规则,但却在仲裁地和程序法所属国这两个连接点上却受到国际社会统一的关注。
上述连接点在不同的环节将国际商事仲裁与众多国内法体制纠缠起来,使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性”名存实亡,而“国际仲裁”也就成为在很多程度上属于某国仲裁之涉外仲裁的代名词。因此,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性支撑并束缚了它的身份定位。
以国际商会仲裁为例,尽管该会仲裁院属于一个相对超脱的机构,其作出的仲裁裁决具有较高的国际流通性,而且在“去身份化”方面该仲裁院已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将这种兴趣持续地转化为仲裁规则及其仲裁实践,但它仲裁的案件“一直受各种各样‘守夜狗’(sleeping watching-dogs)——国内法所控制。必须指出,国际商事仲裁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与对其程序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国内法有密切联系或深留着国内法的烙印,有远见的律师、审慎的仲裁员都能意识到这一点。”③具体而言,国际商会仲裁在如下几个方面常常遭受特定国家的属地管制:④
其一,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如同《纽约公约》一样,绝大多数主要的仲裁机构所在国法都要求采取书面仲裁协议,但对于何谓“书面”却存在很多重要的区别。
其二,仲裁主题事项的可仲裁性。某些国家规定,诸如竞争、专利、证券、歧视事项等与公法相关的争议不具有可仲裁性,必须提交国家法院。
其三,仲裁前提条件。某些司法管辖区域规定,唯有法院方可决定仲裁请求是否在明示的或者默示的期限内提交。
其四,中间措施。为支持仲裁,国家法院常常会迫使当事人提交证人证言、确保证人出庭、保全证据、安排出售容易腐烂的货物、或者撤换不履行职务的仲裁员。此外,具有适格管辖权的国家法院还可直接处理仲裁协议之外、或被ICC仲裁规则第23条第2款所涵盖的诸如保密责任的履行或安全协议等紧急事项。
其五,审核仲裁裁决。仲裁地法院通常可以撤销仲裁裁决,只要仲裁程序不公平或者仲裁员超越权限。某些国家的法院也可以就法律问题举行庭审。
可见,即便超然如ICC仲裁者,因仲裁的属地性而引发的国家管制也是广泛的,有时甚至是强硬的,这也是为什么将仲裁理解为“司法阴影下的仲裁”的原因。
更为突出的论据是ICAS仲裁,ICAS作为与ICC类似的国际性机构,它超然的地位和国际属性甚至比ICC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但其仲裁裁决仍然要受到属地管制尤其是仲裁裁决地的属地管制,甚至其仲裁裁决不唯一地受裁决地国管制,尽管其仲裁规则倾向于该机构仲裁唯一地受制于裁决地管制。由于ICAS仲裁规则明确将仲裁裁决地指定为该机构所在地即瑞士洛桑,也就赋予ICAS裁决以瑞士国身份,按照一般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撤销该仲裁裁决的国家法院为瑞士国法院,一如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某一个案件中再次非明确宣明的观点:“为仲裁庭选择一个瑞士法律住所,当事人就清楚地表明将他们之间的争议委付给瑞士仲裁法律的意志,他们没有规定把仲裁地作为排他的仲裁庭庭审地……特定仲裁地的确定是重要的,以致于仲裁裁决被认为是在该地作出。仲裁庭审或者仲裁裁决是否在仲裁地有效进行或者有效作出,这无关紧要。”⑤但是有学者表达了一种担忧,即“倘若一方当事人向Nagano地区法院寻求撤销日本奥运会期间(CAS)所作出的仲裁裁决,情况会怎样呢?该法院会拒绝行使管辖权吗?如果我们考虑到将来举行的奥运会,则澳大利亚,美国和希腊法院会如何呢?他们会拒绝采取措施吗?由于管辖权决定于所涉法院的国内法,明显地这里没有统一的答案。并且即便考虑到迄今为止的情况反映是相当积极的,也仍然具有不确定性。”⑥可见,ICAS仲裁即使作为一种国际性仲裁,也需要获得属地支持,在其管制上,不仅仲裁裁决国籍国即瑞士国要施加影响,而且其他属地联结点所指向的国家也存在加入管制的空间和可能。一言蔽之,国际商事仲裁具有终始属地性,依托相关属地因素它得以成立并进行,也因依托相关属地因素,它被监督和控制。
(二)国际商事仲裁属地性的表现
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性首先表现为它在性质上的司法权论。这种理论主张,“国家对其司法管辖范围内所进行的所有仲裁有监督和管理的权力。司法权理论的提出和实行,使仲裁员的自主权受到较大限制,因为它要求仲裁裁决遵从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并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⑦事实上,只要“司法保障不容剥夺”就必然为国际商事仲裁确定属地的司法监督,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性也因此而被宏观确立。
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上,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性广泛分布在仲裁进程中。如果按照国际商事仲裁所涉属地连接点的用途区分,它们与国际商事仲裁进程四大环节相呼应可大致划为四类:一是为确定仲裁管辖权所需。它是建立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属地优越性基础之上的。一是为法律适用所需。它们是建立在仲裁的契约性(如仲裁实体准据法)和属地优越性(如仲裁程序法)上。一是为获取司法支持所需。它们是建立在属地优越性的基础之上的。一是为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特指与司法支持相对而言的消极司法监督)所需,它是建立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之上的。也因此,国际商事仲裁属地性就表现在这四个方面。
1.仲裁管辖权成立的属地依赖
凡是有过诉讼经验的人都知道,管辖权的争夺是诉讼策略中的一个要点⑧,它甚至是影响仲裁裁决“国际追偿”的重要因素,其重要程度据说要优先于案件的“谁是谁非”。⑨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确立有赖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而对于效力的认定则需要确立管辖权主体,因此国际商事仲裁属地性在管辖权方面的体现又可分为如下三个问题。
(1)仲裁协议效力生成的属地依赖。仲裁协议是一种严肃的要式法律文件,它的有效性满足如下三个要件:必须建立在法律规定的要素上;必须满足仲裁协议的形式要求;必须满足可仲裁性要求。
首先,在仲裁协议的要素上,各国内立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通常都作了一些硬性规定,仲裁协议必得符合这些强制规定方始有效。在诸如仲裁协议缔结地法或仲裁地法等特定的国家法律对仲裁协议构成要素施加强制性规定时,它表明国际商事仲裁一开始就遭遇了属地联结的约束。尽管国际商事仲裁“去身份化”运动强调仲裁协议的自治性,排除国家法院对仲裁协议的干涉,要求采取“支持有效”(favorem validitatis)的原则来赋予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如施米托夫就认为,即便是最拙劣的仲裁协议,也应包括两个方面: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和由谁来充当仲裁员;⑩更为激进的观点是认为,“可以说,今天合约中只要有仲裁(arbitration)一字,都逃不了要去仲裁解决争议。”⑪但这一观点过于理想,即便简约如ICC仲裁示范条款者也规定一个有效仲裁协议的必要要素为:仲裁合意、提及国际商会仲裁院以及仲裁事项。而且为了确保这一示范条款被当事人引用后不被相关国家法制否决,ICC仲裁院在推荐自己的示范条款时,“国际商会总是会警告所有感兴趣的当事人,某些国家的法律可能会对仲裁协议有具体形式的要求。”⑫为了兼容相关属地国家的国内法要求,尽量避免病态(pathological)的仲裁协议,有人曾经对主要的仲裁机构推荐的示范条款进行比较分析,抽取出它们共同的因素并认为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仲裁协议所必须的要素:提交仲裁的争议;直接或者间接选定仲裁员;选定实体法;直接和间接确定仲裁程序规则;确定仲裁地;放弃可能的对仲裁裁决的攻击;仲裁语言的选择。⑬这些共同因素充分考虑了一份仲裁协议可能涉及的属地联结及其所指向的国家法律的要求。法国1981年5月12日No.81-500号法令也规定:“仲裁协议必须确定争议事项,确定仲裁员或仲裁庭且必须订立任命方式。”我国仲裁立法则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等三项要素,尽管将仲裁委员会列为仲裁协议的必备要素,这种立法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各国仲裁法“罕见的。”⑭
一旦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在要素构成上没有满足相关国家的立法规定,则因属地关联而导致的国家管制立即会否决仲裁协议的效力。1992年巴黎上诉法院在Sté Viennoiserie Fine vs. Negie et al.⑮一案中就认为,只规定“位于巴黎的仲裁庭”的仲裁协议是无效的,因为它既没有说明当事人的名字,也没有说明仲裁机构或选定仲裁庭的程序。在我国海事仲裁实践中,由于我国仲裁立法要求仲裁协议必须载明仲裁委员会,这使得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在1996年和1997年每年均有20%的案件因当事人订立的没有约定仲裁机构的、以“在北京仲裁”这一措辞表达的仲裁协议无效而导致无法受理。⑯
其次,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方面,根据国际私法中“场所支配行为原则”,仲裁协议的形式应当符合仲裁地的法律要求。综观各国立法,主要存在“共识主义”(consensualism)和“形式主义”(formalism)之争,“共识主义”颠倒了“形式主义”之处在于,它坚持认为当事人的共同主观意愿足以完善仲裁协议。⑰可见,“共识主义”在仲裁协议形式上要弹性和宽容得多。
在国内立法上,对于仲裁协议的形式多要求采取书面形式,《意大利民事诉讼规则》第807条规定:“根据有关无效的法令(sanction of nullity),仲裁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且必须确定仲裁事项。” 第808条规定:“在合同或后续文件中当事人可协议将由之产生的争议提交仲裁,只要该种争议可提交仲裁。仲裁条款必须根据有关无效的法令以书面形式作出。” 1976年《瑞士仲裁协定法》(concordat on arbitration)第4条规定:“仲裁协议应以承诺书或仲裁条款形式达成。当事人可通过仲裁承诺书将现有争议提交仲裁。仲裁条款只能将未来的、于特定的具体法律关系中产生的争议提交仲裁。” 1998年《比利时司法法典》第1677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由当事人签署之文书或者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并表明其诉诸仲裁意愿之其他文书构成。”1981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43条规定:“仲裁条款应以书面规定于主协议或者主协议援引的文件中,否则无效。”1993年《俄罗斯联邦国际商事仲裁法》第7条第2款规定:“仲裁协议以书面形式订立。……”1986年荷兰《仲裁法》取消了原仲裁法关于口头形式的仲裁协议可以成立的规定,要求仲裁协议必须以书面文书证明。
在仲裁实践中,巴黎法院曾经对形式要件不符合相关国家属地管制的仲裁协议予以否定。该案两名原告之一是黎巴嫩公司Cassia,之二是巴基斯坦公司,被告是一家在sharjah组建的公司。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一份提交ICC仲裁的合同,后发生争议,Cassia寻求ICC仲裁。仲裁庭于1986年9月25日的初步裁决中认定自身拥有管辖权,裁定当事人已经同意提交争议于仲裁。然而,巴黎上诉法院于1988年4月26日裁定,撤销该仲裁裁决,理由是:“尽管国际仲裁中,仲裁协议完全独立于包含它的合同,但它的有效性必须依据指引准据法的冲突规则予以审查,只要它宣称——一如本案之情况——仲裁协议因主合同未有效签署而不存在。”上诉法院裁定,尽管付款地是在黎巴嫩,合同履行地和签署地都暗示巴基斯坦是当事人关系的重力中心。在查明巴基斯坦法律后上诉法院得出结论:“在完全意识到巴基斯坦法对一份有效合同的形式要求(盖章、日期、签名和起草文件者的授权)下,当事人没有遵守这些法定要求,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无意把争议中的文件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一份有效的合同;因此,不存在有效的提交产生于上述仲裁合同的协议。”⑱英国上诉法院于1991年在Aughton Ltd.vs. M.F.Kent Service Ltd.一案中虽有所犹豫但仍然裁定,当事人之间缺乏一份书面仲裁协议,因此不能提交仲裁:“然而,本案并不满足需要一个书面仲裁协议或者发现仲裁条款的书面指示这一法定要求,……要求以明晰和具体的文字包含一条仲裁条款,而不是来自其他合同的、没有包含此类字眼以致于不含有仲裁性质的合同条款。”⑲
仲裁立法的趋势是,在仲裁协议形式要件上从形式主义转向共识主义。如根据日本法律规定,仲裁协议可以是口头甚至默示推定的;英国普通法也允许默示仲裁协议存在;⑳美国法院也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仲裁协议形式要件方面的宽松要求,在立法精神上倾向于共识主义。从形式主义向共识主义的转折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突破的:
一是对传统“书面”定义予以扩展理解。如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是书面的。协议如载于当事人各方签字的文件中,或者载于往来的书信、电传、电报或者提供协议记录的其他电讯手段中,或者载申诉书和答辩书的交换中当事人一方声称有协议而当事人另一方不否认即为书面协议。在合同中提出参照载有仲裁条款的文件即构成仲裁协议,如果该合同是书面的而且这种参照足以使该仲裁条款构成合同一部分的话。”英国1996年仲裁立法,该法第5条对书面仲裁协议作了极为宽泛的规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书面协议之外,还包括:“2.下列为书面协议:以书面形式达成(无论当事人签署与否),或者协议以交换书面通讯达成,或者协议有书面证据证实。3.如当事人非以书面形式同意援引某书面条款,则其达成书面协议。4.如非以书面达成之协议由协议当事人授权的一方当事人或第三方予以记录,该协议被证明具备书面形式。5.仲裁或法律程序之文件交换中,一方当事人宣称存在非书面形式的协议,且对方当事人在其答复中不作反对,该文件交换构成具有所宣称效力的书面协议。6.本编所指之书面或书写形式包括其得以记录之任何方式。”
二是发展出了长臂仲裁协议的概念。长臂仲裁协议理论认为仲裁协议对未签字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它典型地表现在合同转让、揭开公司“面纱”等情况之下。美国司法实践就反映了这一趋势,美国地区法院于1990年在GB Marine Services Co.vs. M/A Stolt Entente一案中裁定,一方当事人受制于由其附属公司(affiliate company)的独占代理人所签署协议中含有的仲裁条款,因为根据《合同法(第二次)重述》之规定,该公司是协议的潜在受益人,因此应当受仲裁条款的约束。在Genesco Inc. vs. T.Kakiuchi & Co.一案中,美国一法院裁决,“即便仲裁协议缺乏签字,当事人仍然受其约束,这已经被有效确立。而且,尽管‘联邦仲裁’法要求采用书面形式,但它并没有要求当事人签署该书面文件。”在1992年Mcpheeters vs. Mcginn,Smith.& Co.一案中,该观点得以重述并被发展,法院裁决,“根据一般合同原则,没有签字人仍然属于仲裁协议的范畴,只要它是当事人的意愿。”[21]
可见仲裁协议形式要件的立法规定因国家不同而异,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性决定了在仲裁协议形式要件上主要受制于仲裁地国法、裁决作出地国法等行为地国法,但如果按照《纽约公约》之规定,则仲裁协议准据法所属国、仲裁实体法所属国、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国也可通过控制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来对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施加属地管制。
再次,可仲裁性事项也受制于相关国家的属地管制。可仲裁性问题包括主观可仲裁性和客观可仲裁性两种情况,主观可仲裁性(subjective arbitrability)又称作属人理由的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 ratione personae),其判断某一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标准在于当事人身份或者功能,诸如国家、地方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机构履行特殊职责者不得参与仲裁程序,尽管诸多学者反对这一观点,但主观可仲裁性问题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和承认。与此相对,客观可仲裁性(objective arbitrability)又称作属物理由的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 ratione materiae),其判断某一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标准在于立法是否作出规制。[22]查遍诸国的国内立法几乎都对仲裁事项的可仲裁性作了强制性规定。《意大利民事程序规则》第806条规定:“当事人可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下列事项除外:受第429条和459条调整的事项,有关配偶之间地位或分居的事项,以及当事人不能自决的事项。”1988年《西班牙仲裁法》第1条规定:“以缔结仲裁协议的方式,单独的个人或者法律实体可将已经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与依据法律他们能够处分的事项相关的争议提交一名或多名仲裁员仲裁。”第2条规定:下列事项“不能以仲裁方式解决:1.已经作出终局裁决的事项,除非是与其执行相关的事项;2.不能与当事人不可自由处分者相分离的事项;3.因当事人缺乏行为能力或缺乏正式授权的官员而使Attorney General必须介入代为行为的事项。”巴西《民事诉讼法》第1072条也规定,诸如与公民个人身份、家庭问题、破产或公共政策等事项不能仲裁。我国仲裁法把婚姻、扶养、监护、收养、继承争议以及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1998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30条规定,涉及经济利益的事项具有可仲裁性,如果争议不涉及经济利益但当事人有权就争议问题缔结和解协议部分可仲裁;在德国境内的住宅租赁合同关系存在与否的争议不具有可仲裁性;其他法律规定不可仲裁事项不能仲裁。尽管各国立法趋势是将可仲裁性范围放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在一案中采取结果导向性的裁决,即“就联邦法而言,与某一争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相关的任何疑问应根据有利于仲裁的方式予以解决。”[23]但无论如何,有关国家在可仲裁性问题上的设限是基于其本国公共政策的需要,具有不容置疑、不能妥协和不可交易的权威性,国际商事仲裁在这一问题上必须让步于相关国家的属地管制,《纽约公约》显然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并助长了各国的属地主义态度。在仲裁进程中,对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施加管制的国家首先是仲裁协议缔结地国法,其次是仲裁地国法,还包括被请求承认和执行地国法。《纽约公约》至少确定了仲裁协议准据法所属国、裁决作出地国、仲裁实体准据法所属国以及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等国家的属地管制。
我国法院于1988年在“江苏省物资集团公司轻工纺织总公司诉香港裕亿集团有限公司、加拿大太子发展有限公司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24]中涉及争议事项性质是否具有可仲裁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中得出的结论是,侵权案件具有可仲裁性,因此当事人之间签署的仲裁条款有效。[25]
(2)仲裁协议自治性的属地依赖。仲裁协议独立性要求摆脱相关国家法律和它建基于其上的合同的影响,尽管这一努力已经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确立起了仲裁协议独立性的原则地位,但透过更为深层的制约关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被视为国际商事仲裁“去身份化”最为成功部分依然承受着来自相关国家的属地管制。
在仲裁协议自治于诸国法律体系方面,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具有属地依赖。当代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主要通过意思自治、冲突规则和结果导向的实体规则三种方式确定法律以裁判仲裁协议是否存在和有效。意思自治和“与其使之无效,不如使之有效”的结果导向性实体规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仲裁“去身份化”[26]的风采,但前者首先是一个选法性冲突规范,当事人选择是否有效这取决于相关国家法制是否支持,即便内国法肯定意思自治的选法有效,但意思自治的方式、时间、范围等等要素仍然严格受制于内国法之规制,[27]再进一步言,即使意思自治成为国际社会主流原则,它的成立基础仍然是各国国内立法通力协作的结果,它本身并不保证任何国家必须遵守这一原则。而结果导向性实体规则的采用仍然取决于相关国家的法制弹性和开放程度,即便宽容若法国者,也仍然在这一实体规则上划下了“国际公共政策”的禁区,其立法本质上仍然具有鲜明的属地特征,仲裁协议的存在或者有效性只能在它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度地波动,“越轨”无效,“换言之,法国法下调整国际仲裁协议存在性和效力的实体规则在该国法律体制内构成了自由主义的最小和最大标准。”[28]
至于根据冲突规则确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方式更将仲裁协议的生死存亡与特定国家的冲突规则并间接地与特定国家的国内实体规则相勾连,抵消了仲裁协议超越属地管制的努力。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和实践表明,为仲裁协议确定准据法的冲突规则在属地联结因素的选择上通常采取仲裁协议缔结地、仲裁地、专属于特定仲裁协议的连接点,有时乃至是仲裁机构总部所在地。[29]采取仲裁地法对仲裁协议施加管制这是最为正统的做法,据说它是建立在国际法机构1957年和1959年所作的决议之上,这些决议将仲裁地作为缺乏当事人意思自治情况下的强制性连接点,因此,仲裁地作为连接点被广泛适用并不是因为它反映了仲裁协议的程序特征,它甚至不过是在较低程度上满足了便利仲裁的地理需要和中立于当事人的需要,而当为了给仲裁协议确定一个准据法之目的时,仲裁地作为连接点甚至更不具有正当性。即便如此,仲裁地指引下的仲裁地法“在一定情况下仍是决定性的和不可忽视的。”(韩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仲裁协议缔结地在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指引过程是“极其微弱”(extremely minor)的,ICC仲裁院1988年第5730号裁决表明了这一看法,究其原因在于仲裁协议缔结地的确定不仅困难,而且其选择也是比较偶然的。[30]专属于特定仲裁协议的连接点在如下情况下出现,即当事人从某一特定国家的专业性组织起草的标准格式合同中取用仲裁条款,则当事人的取用行为很可能被认为是愿意将该仲裁条款委诸于该国法律调整的主观意图。在少数情况下,仲裁机构总部所在国也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连接点,当事人倘若通过仲裁协议指定某一纯粹的内国仲裁机构或者位于西欧或远东的内国或准公共性仲裁机构,则可正当地断定,当事人愿意由仲裁机构总部所在地国法调整仲裁协议。
在仲裁协议自治于主合同方面,其自治性同样具有属地依赖。关于仲裁协议相对于主合同的自治性,学界主要存在三类观点,一是将仲裁协议与主合同捆绑在一起,仲裁协议之存在与效力取决于主合同;一是将仲裁协议与主合同分割开来,认为二者应当分别对待;[31]一是将主合同与仲裁协议进行辨证联结,指出二者是一种连锁合同关系[32]第一种观点已经受到普遍的否定,当代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仲裁协议的独立性,但第二种观点过于前调二者的分离性,却斩断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学者评价道:“仲裁条款‘独立性’的用于并不精当,因为,仲裁条款的效力固然不与合同正向相关,因而在这一意义上,仲裁条款独立性才有其意义,但是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仲裁条款生效与否与合同生效与否的反向相关,在这一意义上,二者具有相关性,也就是说,仲裁条款的效力不具有独立性”。[33]更确切地说,仲裁条款效力的发挥不具有独立性,它取决于主合同的法律状态,只有当主合同处于比较异常的紊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缺乏契约当事人的合意、或缺乏其签名授权、或契约无效,这些削弱因素不会终止仲裁协议,相反仲裁协议正因此而被激发。[34]”而主合同的法律状态,尤其是主合同及其包含的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有效,这除了可求助于仲裁庭解决之外(倘若如此就是仲裁庭行使自裁管辖权),还可以求助于国家司法系统,这就使得仲裁协议的效力和存在问题有可能被操纵在国家的属地管制之下,除非实行唯一排他的自裁管辖,显然这在世俗国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即便在最能体现国际商事仲裁身份的特立独行方面,国家的属地管制也是弗远不届,而一当抓住国际商事仲裁这一根基,国家的属地管制就在仲裁自治的领域开启了一扇阿里巴巴之门。自此后,国际商事仲裁就在司法介入的属地管制下痛并快乐着。
(3)仲裁自裁管辖权的属地依赖。仲裁庭管辖权的取得以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条件,而仲裁协议的有效与否则可诉诸于仲裁庭的管辖。这一逻辑回环典型地具有解释学循环的味道,但重要的或许不是我们应当如何跳出这一个轮回,而是以何种恰当的方式进入这一循环,因为仲裁自裁管辖权是保障仲裁制度自治和“去身份化”的关键环节。如果说在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仲裁过程中临时措施的采取等方面国家介入带来的属地管制对保障仲裁机制的有效运转是必然和必要的,那么仲裁庭取得管辖权的正当性还需接受相关诸国的审查则是被迫的。仲裁管辖权的成立采取国家和仲裁庭的平行审查这本身就在赋予国家过多的属地管制机会和可能,并且在这一形式“平行”中却存在效力等级的实质性差异,即法院审查决定的效力优先,倘若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存在和效力发生疑问,一方提交仲裁庭仲裁,另一方则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并将这一异议诉诸相关国家司法裁定,此时,形式上的平行体制被无情的现实撞得粉碎,转化为司法优先的等级秩序。司法决定的优先性强有力地狙击了国际商事仲裁自裁管辖权的自治倾向,并充分显示了国际商事仲裁自裁管辖的“虚幻性”,当法院裁定与仲裁庭裁定相一致时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自裁性方可得以成立,一旦二者产生冲突时,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司法裁定优先的保守做法,即“同一仲裁协议,法院认定无效,仲裁庭认定有效,在此情况下,根据‘司法最终决定原则’,一般应以法院的认定为准”。[35]我国仲裁立法就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的确,如学者所言,依据仲裁协议自治性而逻辑产生的仲裁自裁管辖权是有限制的:“从程序法的角度看,除非仲裁协议另行规定,仲裁协议必须按照首先由仲裁庭裁定仲裁协议效力的方式进行解释,否则仲裁庭的裁定将受到质疑。”[36]尽管包括法国等在内的仲裁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自裁管辖权予以最大程度的包容,并且在“支持仲裁”和严格自律的思潮下与在其境内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保持了良好的合作,但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断言当司法裁定与仲裁庭裁定发生冲突时,仲裁庭的自治性会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保障,除非国家立法明确界定二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界限,否则这一区域永远都是司法和仲裁的敏感地带,并为二者的良好发展造成障碍。
应当指出的是,德国语境下的 “competenz-competenz”并不等同于“competence-competence”,据学者考证,“competenz-competenz”在德语中表示一种与“competence-competence”存在重大差异的涵义,前者除了包含后者的意义之外,还同时意指授权仲裁庭就其管辖权作出终局裁定,而不经受任何国家法院的审查;[37]后者则在这一问题上更加务实地满足国家的属地管制。毫无疑问,“competence-competence”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做法,[38]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是根本拒绝仲裁庭的终极性决定权力的,他们更多的是采取司法裁定优先原则。不无遗憾地是,法国、其他一些欧洲学者,乃至UNCITRAL示范法的正式文件和评论所仍然在将二者等同适用。
国际社会主流立法与实践在“competenz-competenz”与“competence-competence”之间选择了后者,这使国际商事仲裁的“去身份”化运动在仲裁协议效力认定这一环节受到重大挫折,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自治性在决定性意义上亦赖于相关国家的司法态度,而1958年《纽约公约》的制度安排看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秩序,公约将认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留给了有关国家法院,包括仲裁地国、承认和执行地国、仲裁协议准据法所属国等国家法院均有权通过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这一国际商事仲裁终端环节在管辖权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制约着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态度。在这一意义上,仲裁自裁管辖权仍然离不开相关国家的属地支持和管制。
2.法律适用的属地依赖
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主要包括程序法的适用和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并在适用过程中形成“比附国际私法”的潜规则。在国际私法领域,程序问题一般适用法院地法,其理由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阐述,一是从程序性质上看,程序问题多属于公法问题,而公法具有严格的属地性,因此法院地法应当排他地作为程序规范;二是从国际惯例看,“场所支配行为”是一个共知共守的选法规则,诉讼程序应当按照诉讼场所即诉讼地法予以调整。类似地,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规范一般采取仲裁地国法,但与国际私法领域中程序问题排斥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同,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程序法,甚至在临时仲裁的情况当事人还可以拟制仲裁程序法。但应当指出,尽管程序法允许意思自治进行选择似乎展示了一种“去身份化”的倾向,但很多“表面上看似乎属于非内国仲裁理论或实践的仲裁立法与判例,而实际上这些立法与实践并不是非内国仲裁的结果,而是这些主权国家的仲裁立法与实践的结果,……恰恰是国际法上的地域理论在立法和实践中的体现。”[39]即实质上不外乎是仲裁属地依赖的别样表达。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法律适用的非当地化的兴起是建立在相关国家尤其是仲裁地国法的属地管制之下的:
首先,是否允许仲裁程序“非当地化”,即是否授权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程序规范这一行为是仲裁地国法的自主规制,允许仲裁程序的非当地化“并不意味着仲裁可以摆脱当地法律且不受该法的限制,正相反,恰是由于该地法律许可,当事人才可能在仲裁中适用外国规则和程序。”[40]换言之,仲裁程序非当地化实现路径之意思自治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仲裁地国法的立法态度。
其次,即便肯定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的有效性,也不能认为这一程序真正地免除了仲裁地国等相关国家的属地管制。一般而言,仲裁程序受很多程序规范的控制:第一,当事人选择的程序规则,这一规则并不必然等同于仲裁地法和任何其他程序法;第二,仲裁地的程序公共政策;第三,可能的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国之程序公共政策。[41]可见,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的程序规则即便能够有效成立并运行,但其效力仍然主要地受仲裁地国和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地国公共政策的限制,“不得违反仲裁庭所在地或者仲裁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否则,仲裁裁决可因当事人一方的请求而被有关法院认定无效或者予以撤销。”[42]但由于各国法院仅依本国标准判断仲裁程序是否合法,这就为仲裁庭与相关属地管制的国家法院之间造成了紧张,二者完全可能在公共政策的判断上发生冲突,这是否意味着仲裁庭在确定程序规范的时候必须揣摩法院的心理感受,以有效降低仲裁裁决可能违背程序公共政策而面临被撤销或者不予承认和执行的风险?学者的建议大胆而令人费解:“在仲裁地公共政策或裁决执行地公共政策与仲裁庭自己的有关真正的国际公共政策的概念发生冲突的罕见情况下,我们的观点是仲裁庭应当以后者优先。”而ICC仲裁院4695/1984号案件恰好为上述建议作了一个诠释,完全可以设想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该案仲裁裁决在一个司法管辖区域被承认和执行,但在另一区域却被撤销。[43]
最后,仲裁程序的属地管制是广泛的,除仲裁地国法、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地国法之外,还可能包括当事人国籍国法、合同缔结地法等。ICC仲裁案件从表面上看似乎只依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没有任何一国国内法或司法机关进行干涉,事实上,这些案件一直受各种各样“守夜狗”(sleeping watching-dogs)——国内法所控制,为提高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ICC仲裁规则间接委婉地表达了要充分考虑和尊重可能审查或者执行其仲裁裁决的国家的立法。如ICC仲裁规则第35条规定,对该规则没有规定的事项,仲裁院和仲裁庭都应当根据该规则的精神办理,并尽一切努力确保裁决能够依法执行。仲裁地国法和裁决承认和执行地国法对ICC仲裁裁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有学者指出,主体的仲裁能力问题受当事人住所地国法律管制;诉讼豁免受国际公法原则管制;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受当事人国籍国法、合同缔结地法、仲裁地法和裁决执行地国法管制;当事人授权的合法性受被授权人所在地国法或者代理行为实施地国法管制。[44]可见仲裁程序的属地管制形成了以仲裁地法、裁决承认和执行地法为基础,广泛涉及其他国家法律的属地管制体系。
现实中,某些国际商事仲裁的名义仲裁地与现实仲裁地并不完全一致,这尤其表现在某些国际性仲裁机构的规则之中。以ICAS仲裁为例,该委员会仲裁规则就规定,无论仲裁是否在瑞士进行,瑞士均视为仲裁地。这就使ICAS奥运特别分庭在奥运会承办国实际进行的仲裁被视作在瑞士进行,且其程序规则应当适用《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中有关仲裁部分。但无论如何,事实仲裁地的程序法必将对在该国进行的仲裁施加管制,这是一国属地优越权的表现,ICAS即便作为一个地位超然的仲裁机构,在他国进行仲裁也必得遵守该地的强制性规则,尤其是可仲裁性事项等涉及公共政策的问题。
在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上,各国一般都给予当事人相当程度的尊重。按照康德的见解,一个人只有在遵守自己的意志的时候才是道德的。这种意志不是一个人的恣意和任意,而是每一个人据之自己为自己立法,以使这一意志能够上升为普遍的绝对律令。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规则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性人和道德人的基础之上的。首先,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实体问题准据法,在没有选择的时候,则由仲裁庭根据一定的冲突规则或者仲裁庭直接采取其认为适当的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法律原则、标准合同条款、国际贸易惯例等)来裁决案件;在友好仲裁的情况下,仲裁庭甚至可以基于良性体验裁断案件。客观地说,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表现出非常突出的“去身份化”属性,但仍然存在相关国家的可能属地控制:
其一,国际商事仲裁实体准据法的一切选法方法都必须获得仲裁地国或者相关国家的属地许可。且不论仲裁庭依据仲裁地冲突规则确定案件实体准据法,包括意思自治、一般法律原则和商人习惯法(lex mercatoria)等在内的跨国规则(transnational rules)的适用必须首先符合仲裁地等国家的立法许可,倘若仲裁地法或者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地国法禁止跨国规则的适用,则仲裁庭强行采取此类规则的法律后果是仲裁裁决或者被撤销或者得不到承认和执行。
其二,意思自治法或跨国规则仍然要受相关国家的属地控制。在意思自治法的运用上,有很多问题各国立法都作了规制,且其内容并不完全一样,如“当事人能否选择冲突规范来间接选择实体法?当事人能否选择非契约性商事纠纷的仲裁实体法?”以及当事人选择仲裁实体法的方式、范围和性质又如何?[45]以我国为例,我国立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准据法作了如下要求:在方式上必须是协商一致和明示的;在适用的范围上,诸如在中国境内成立并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不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只能适用中国法;在选择的法律性质上,必须是实体法不能是冲突规范;在选择法律的资格上,不得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等。[46]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立法要求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的准据法必须与案件存在最低限度的联系。
在跨国规则的适用上,尽管跨国规则“标识了一个明确的倾向,即对狭隘的国别立法的超脱和对跨法系、跨法域法律精神的看重,多多少少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47]但它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运用的适当性必须接受相关国家的属地控制。跨国规则相对于一国内国法制而言毕竟是一种含有异质因素的外来文明,在两种法观念的碰撞和对话之中必然存在融合和对抗两种形态,如果跨国规则的适用与有关国家的公共秩序或基本法律原则相抵触,则跨国规则的运用必将因其挑战和质疑内国公序的权威而遭到内国法制的否定,“无论当事人于何时排斥国家法的适用,并只指定那些贸易惯例或习惯,该种选择似乎站得住脚(只要它没有与任何能适用的强制性法律条款相冲突)。”[48]那些所谓的强制性法律条款即是国际公共政策,这些基本规则即便是当事人特别授权友好仲裁也必须得到满足和尊重,ICC仲裁院1984年第4265号仲裁案件就表明,担任友好仲裁员者仍然不能无视国际公共政策规则,违背该类规则将为仲裁裁决被撤销或被拒绝执行提供根据。[49],“根据衡平法则进行裁决的仲裁员仍然有责任遵守并确保当事人遵守公平程序的基本要求,……友好仲裁员仍保持一个裁判者的身份,应当遵守为适当地实现正义所要求的根本原则。”[50]
其三,意思自治法和跨国规则的缺陷和不足也可能会导致其被属地法制的取代。由于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或多或少地规定了不同程度的法律规制,这使得当事人在进行选法时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逾越此类法律规定以最大化自己的私益,当事人趋利避害的行为极有可能被有关国家认定为恶意逃法或法律规避,从而否定当事人的选择效力。这或许会使仲裁庭在确认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的准据法的适格性问题上保持谨慎,并在当事人同意或说服当事人的情况下以相关法律规则取而代之。同样地,跨国规则作为案件准据法的适格性仍然要受相关国家的属地牵制,跨国规则作为准据法的弊端已经引发广泛的质疑,包括:观念上的疑虑,即跨国规则能否以国内法或国际公法同样的方式缔结一个真正的法律秩序?意识形态上的疑虑,即商人习惯法有时仅对合同关系强势者,尤其是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当事人有利,它能否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实践上的质疑,即在实践运用中难以确定一般法律原则等规则的确切内容,该类规则被认为是模糊和片面的。[51]这些质疑已经转变为有关国家国内立法对此类规则的不友好态度,这使具有更高责任感的仲裁员会在自由裁量某一跨国规则是否属于能作为准据法的“适当”规则时保持警惕,并在拿捏不准时咨询相关国家的人员或者更换为相关属地规则,以确保仲裁裁决不因准据法的不适格而被撤销或者不予承认和执行。
3.司法支持的属地依赖
国家法院承受了太多的来自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苛责以致于他们满腹怨言,的确司法监督本身就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含义,积极的司法监督是国家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支持和保障,而消极的司法监督则是国家法院对仲裁及其裁决的消极评价。就其本意而言,司法监督都可以转化为司法支持,因为即便是消极的司法监督本身也是保障国际商事仲裁良性运转的不同表达方式。司法支持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仲裁与特定国家司法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决定着国际商事仲裁必须在国家属地控制之下换取支持。
国际商事仲裁庭为查清案件事实、便利或加速仲裁程序的进行一般会在仲裁过程中发布一些命令或请求,采取某些措施,这些命令或请求、措施在遭受相关人员拒绝后,仲裁庭能否强制实施?这取决于各国立法的态度,据现有仲裁实践和立法来看,国家法院对包括法院裁决和仲裁裁决等在内的一切司法性决定的执行权限均垄断性独占,[52]当事人即便是在仲裁协议赋予仲裁庭采取和强制实施临时措施的权限,这一约定也是无效的,除非得到执行地国的同意,其原因在于这一约定内容超越了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范畴。国家法院的属地管制和支持以此为契机开始介入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商事仲裁的进程。
从理论上将,国际商事仲裁庭在仲裁进程中颁布的一切命令或采取的相关措施但凡需要借助强制力予以执行的都必须获得国家法院的司法支持。当然,仲裁庭颁布的决定或命令并非都需要国家司法支持,例如即便是对查清案件事实至关重要的证据问题,倘若仲裁庭颁布命令要求一方提供,被要求方拒不提供的,仲裁庭也并不一定寻求国家司法支持,它或许会采取对拒不提供证据方不利的“反向推定”(reverse reference)来认定事实,通过可能的对其不利的仲裁裁决以间接胁迫该当事人满足命令的履行要求。因此,分析仲裁庭可能颁布的命令或采取的措施以辨别出需要获取司法支持的类型对于在保证仲裁庭的权威和独立的同时又能在必要的关键环节得到司法支持,以满足当事人对仲裁效率和速度的需要。
在为数不多的对国际商事仲裁庭可能颁布的决定或命令进行精致分析的学者中F.Ramos Mendez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人。他认为仲裁庭颁布的决定、命令或要求可以纳入广义的“中间禁令”(interlocutory injunctions)一词,并且按照其效力、适用对象等可以作如下划分:[53]仲裁庭的决定总体上可划分为命令、请求和建议。命令是仲裁庭决定的主要部分,它通常是针对当事人颁发的,普遍具有强制性,其功能既可以是保障仲裁程序的正常进行,如命令当事人遵守仲裁规则的命令(orders to comply with the arbitration rules),采取某些措施的命令(holding measures),要求当事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命令(orders to a party to act or omit);也可以是促进仲裁裁决的先予执行,如要求一方当事人支付部分仲裁请求金额的命令(orders for payment of a part of the claim);还可以是涉及当事人自愿为或不为行为的中间禁令(interlocutory injunctions)。而仲裁庭颁发的请求主要是针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进行的,它不具有强制性,其功能在于便利和加速仲裁程序的进行。仲裁庭颁发的建议是针对当事人进行的,它作为仲裁庭命令的补充,其效力不具有强制性,只具有道德警醒(moral reminder)的作用,当事人不执行该建议至多不甚光彩(negative light),但不意味着他的仲裁请求会受到漠视,因此这一类型的仲裁决定通常有助于、且仅仅有助于加速和便利仲裁的进行。
这些命令中存在交叉重叠的部分,如采取措施的命令与中间禁令,前者具有更强的强制性(stronger coercive),后者则关涉相关当事人的内心自愿(volition);这两类命令同时与要求当事人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命令相交叉重叠,但它们侧重点不同,holding measures的常见种类是扣押/查封财产等维持现状(preserving the status quo)的命令;interlocutory injunctions与当事人自愿因素相关,无须在当事人或第三人之间确定某一关系,即使没有第三人的合作在某些情形下该禁令不能被执行,此类禁令在理论上作为一种建议更容易让人接受;而orders to a party to act or to omit要求当事人采取例如继续工作或提供担保等行为,或者不采取某些行为或冻结支付特定款项等。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初初将仲裁庭之决定列示如下:

上述分类从仲裁庭决定的表现形式着手提供了一种较为全面的理论视角,毫无疑问需要获取司法支持的仲裁庭决定显然只有命令一类,而仲裁实践中经常采取且需要国家司法支持的命令从功能上看主要是保全措施和先行支付两类。而这两类措施都极其明显地传递了国家对仲裁的属地管制信息。下面以保全措施为例论证国际商事仲裁司法支持这一环节中国家属地管制的体现。
(1)国家法院属地管制的正当性基础。保全措施和先予支付都可能动用强制力以保证其有效实施,这就为国家属地管制提供了可能。以保全措施为例,保全措施(conservatory measures)是通过对与争议有关的财产、证据或行为采取强制性措施,如暂时查封、扣押、冻结有关财产、证据,命令证人出庭作证等,以保证仲裁程序的正常进行和将来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54]进一步清晰界定,保全措施的功能有三:一类是防止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害;一类是保全案件证据;一类是加速仲裁裁决的执行。[55]有争议的问题是,法院能否行使此类权力以及此类权力如何在法院和仲裁庭之间配置?
在法院能否行使保全措施的权力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相反的理论。[56]按照国际商事仲裁的一般理论,它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之上,当事人提交仲裁的法律后果是尽可能地减少法院的司法介入,这在其他许多制度上已经表现出当事人和仲裁庭对国家司法介入的敌意和警惕,以此逻辑一以贯之,似乎在保全措施的问题上,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法院不得擅自侵入当事人自治领域。与之相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仲裁协议自治性只是排除了国家法院裁决案件事实的权力,但并不排斥国家法院采取中间措施的权力,一如学者所言:“从司法干涉仲裁而言,《纽约公约》所排斥的仅仅是在当事人协议提交争议于仲裁时法院对仲裁实体问题的干预,但并不排斥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采取扣押的方式来支持仲裁。”[57]显然,当事人意思自治并不能有效排除国家司法的介入,国家对国际商事仲裁施加属地管制的正当性尽管不能以意思自治为基础,但却建立在更为深层的底线正义根基之上。按一国宪法之规定,唯有司法机关才具有最终的正义守护权,“司法保障不容剥夺”,即便当事人以协议排除司法机关在这一问题上的介入,但在这一界限上,司法机关的决定才是最为权威的终极意见。
(2)国家法院属地控制的程度。国家法院在这一问题上是完全、排他的吗?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的仲裁庭能否享有这一权限及其程度如何?在保全措施中,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的主流做法是实行决定权和执行权的两权分离,在国家法院和仲裁庭之间或者通过立法或者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予以配置。对于保全措施的执行权一般由各国司法机关所专有,这项权力通常被认为与执行地的公共秩序直接相关,迄今为止的立法与实践并不授权仲裁庭享有这一权力,仲裁庭也从未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过分的野心和热情。对于审查和裁决权则存在多种分配模式,大致上有二:其一,共同管辖。这种模式赋予仲裁庭和法院同等的管辖权限,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选择由其中一个机构行使这种权力。它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原则,[58]受到包括德国、瑞士、美国、法国、瑞典等典型的仲裁大国的立法接纳。其二,法院专属管辖。采取这种立法的国家日益减少,它们倾向于保守的理念,不愿放宽法院的权限同时也非常吝惜给予仲裁的应得宽容,我国立法即是如此。
在司法支持这一环节,国家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控制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执行权的根本控制。无论上述两种模式如何,它们的建立前提均是法院的最终执行权,这使国际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获得了属地管制的根本权力。第二层次,决定权的延伸控制。大多数国家法院的属地控制并不满足于司法支持环节的终端控制,而是进一步向前延伸,在决定权限上与仲裁庭享有共同权力,在某些国家甚至这一权力也为国家法院所独享。第三层次,权力冲突中的优先控制。由于仲裁庭与法院在决定权限上实行二元机制,则倘若仲裁庭与法院均作出一致的裁定,这种情形不发生冲突;倘若其中之一拒绝受理,而另一方作出决定要求采取保全措施等,只要二者不相互否定,则后者优先;倘若二者作出完全冲突的决定,则国家法院的决定更具有可执行性,从而表现出属地控制的优先性。[59]总的说来,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支持本身就是一种属地支撑,更确切地说,国际商事仲裁司法支持的属地支撑是严格地建基于被请求地国地域之上的,且只能适用“执行地国法。”[60]
4.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的属地依赖
即便是最高傲、最脱俗和最接近纯粹自治境界的国际商事仲裁也不得不在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环节谋求与世俗国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61]并希冀通过国家权力的介入以促成仲裁裁决的实现,尤其是当仲裁败诉方拒不采取合作态度之时更是如此。国家权力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介入,这取决于被请求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态度,并以国际商事仲裁接受被请求国的监督和属地控制为对价。在仲裁裁决这一国际商事仲裁终极层面上,世俗国家得以此为契机突入仲裁的自治领域,赋予国际商事仲裁以属地色彩。在Sanders先生广为人传的言说中透露出了这位无限向往国际商事仲裁自治境界的理想主义者的属地情结,他认为:“国际商事仲裁就像一只试图飞翔的年轻的小鸟,它高翔在空中但却随时跌落回它的故巢(home nest)。然而这只年轻的小鸟成长迅速。在很多情况下,国际仲裁能在国际性的气氛中自由地抒展它的羽翼……则仲裁裁决能从国家领域解放出来并趋向于去国家化。”[62]正如上文所述一样,国际商事仲裁即便是一只飞翔空中的脱俗的风筝,它也摆脱不了左右它的那根长长的系属于特定世俗国家的导线,一如迎空高翔的小鸟也难舍对故乡的牵挂。国际商事仲裁在裁决环节寄希望于国家权力的介入或者据此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必然导致被请求国的属地控制,这种属地控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仲裁裁决环节的属地控制是根本性控制。在自治语境下的仲裁,其仲裁裁决的执行有赖于仲裁庭的权威、商业团体的舆论和败诉方的道德戒律,然而这种自力救济式的冲突解决机制由于过度地推崇和信任非强制性的力量常常不得不面对拒不遵守商业潜规则者的无赖抵抗,或者在裁决双方当事人对仲裁裁决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之时不得不陷入仲裁裁决无法实现的尴尬境地。在允许私力救济的时代,仲裁的自治性或许能够保障仲裁裁决以暴力或者非暴力的形式得以完成,但统治者“渐知从来个人间之私事,与团体存续讼事,大有关系。由知觉积成经验,公权力乃渐次发达,而法律之效用,亦甚形显著。”私人之间的暴力救济遂被国家立法剥夺,至此,一切暴力救济归于国家。当国家垄断一切暴力救济,并明令禁止社会民间保留这种救济方式时,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需要运用强力实现仲裁裁决的权利义务分配效果时,它不得不求助于特定的国家。在这一意义上仲裁裁决环节的国家管制是根本性的控制。然而国际商事仲裁界似乎仍在不懈地努力以在这一环节上也能抵达真正的自治,从而营造出纯粹的仲裁自治境界,于此处,它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仲裁上诉院的方案和它特有的自执行机制。[63]
按照该方案的构想,国际仲裁上诉院应当以国际公约为基础并在缔约国同意的条件下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进行救济并保证仲裁裁决在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得以履行。国际仲裁上诉院的作用机制是,仲裁一审程序由当事人任命的独任仲裁员(临时仲裁情况下)或者由仲裁机构任命的独任仲裁员(机构仲裁情况下)实施,持续期限不超过一年;仲裁上诉程序由三人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实施,持续期限不超过一年,并由新的国际仲裁院或者复兴的常设仲裁院予以监督实施;仲裁上诉令的取得须向仲裁庭提交一审仲裁裁决所确定之金额为条件,除非仲裁庭在特殊情况下豁免该项义务,上诉裁决的执行直接由该提交的金额予以保障,此即为自执行机制;仲裁裁决在所有缔约国均作为一份具有执行性的文件并因此豁免于诉诸国家法院的袭击。
应当指出,该方案的有效运转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国家法院的世俗干扰,从而为仲裁的自治和去身份化展示了一条鼓舞人心的途径,但是它仍然具有根本的属地依赖性:首先,该方案的实施仍然有赖于世俗国家的同意,是世俗国家属地控制的一种变相延伸。其次,当一审裁决败诉方既不履行裁决义务,也不申请仲裁上诉令,此时该方案设计的精致的自执行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仍然不得不诉诸国家法院的属地管制。最后,国际仲裁上诉院只能保障缔约国之间的仲裁裁决得以自足地实现,但超越缔约国范围之外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则仍得诉诸于特定国家的属地管制。因此,即便是理想浪漫如国际仲裁上诉院者也无法彻底实现不受地域干扰的属地管制。
(2)仲裁裁决环节的属地控制是全程控制。由于仲裁裁决是整个仲裁活动的逻辑结果,是仲裁活动的高度浓缩,因此,整个仲裁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仲裁裁决的回溯性逆向展开,被请求国则可以通过仲裁裁决的属地管制来实现对仲裁活动的全局性监管。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列示了若干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情形,包括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仲裁庭的组建、仲裁事项的范围、仲裁程序的进程以及仲裁裁决的法律状态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被请求承认和执行地国尽管直接面对仲裁裁决,但通由仲裁裁决这一仲裁过程的终端却可以无限展开它的监管视域,以实现仲裁活动的全程管制。
(3)仲裁裁决环节的属地控制是复合性控制。仲裁裁决环节的属地控制首先和直接地掌控在被请求承认和执行地国,但被请求国显然并不是唯一地运用本国法律标准对仲裁裁决的质量进行把关,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之规定,被请求国除了依据本国法对仲裁裁决事项的可仲裁性、仲裁程序的正当性、仲裁裁决的合公共秩序性进行审查外,尚需附加若干其他国家法律以强化属地控制,这些国家法包括:当事人属人法,用以调整当事人缔结仲裁协议的能力问题;仲裁地国法,用以调整仲裁庭的组成或确定仲裁程序规范;裁决地国法,用以调整当事人缔结仲裁协议的能力问题或确认仲裁裁决法律状态;仲裁实体问题准据法,用以确认仲裁裁决的法律状态。从理论上讲,被请求国除受国际公约限制外,它不仅可以唯一地依据本国法对仲裁裁决并借此对仲裁整个过程进行监管以外,它也可以将属地管制进行泛化,把仲裁所涉相关国家的法律合并地对仲裁裁决及其过程进行复合控制。后一种方法显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与实践,通过将仲裁过程予以分解,为仲裁活动的每一方面设立一个类似的本座或者连接点,再由该本座或连接点指向的国家法对仲裁的特定方面进行管制,[64]而这一切属地管制最终得以在仲裁裁决这一终端处统一由被请求国实施,因此,仲裁裁决环节的属地控制不仅体现了被请求国的法律价值,也满足了相关所属国家的法律审美要求,它以被请求国为主体实施一种复合性控制。
四、启示
国际商事仲裁一方面试图超越世俗国家管制而独立自为的“去身份化”运动,与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跌落回世俗国家并在世俗国家之内寻求支持的“属地”命运之间,存在着一个张力结构,在超越与跌落、出世与入世之间国际商事仲裁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表现出游移不定的趋向。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性与去身份化是以各国仲裁立法在仲裁问题上依据身份而采取非国民待遇情况下进行的一种法律规避,隐藏其后的本质规律是最大化积极司法监督(司法支持)和最小化消极司法监督(司法否定)。这一结论通过分析国际商事仲裁去身份化与属地化的矛盾运动所致达的法律效果尤得以澄明:
一方面,包括国际商事仲裁“非内国化”在内的去身份化运动总是试图摆脱世俗国家的法律框架,在仲裁协议效力、仲裁法律适用、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等环节上独立自治,排除世俗国家因偶然的但为进行国际商事仲裁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属地关联而介入并干涉国际商事仲裁的机会。由于世俗国家进入国际商事仲裁的正当性根据总是攀援于直接的或可转化的属地连接点,因此为抵消属地连接点对国际商事仲裁系属于特定世俗国家的身份定位作用,国际商事仲裁必须通过多元化、中立化、虚拟化属地连接点来营造一种身份的无化效果。可见,国际商事仲裁去身份化运动的直接要求是规避世俗国家法律之“天罗地网”,最小化来自世俗国家法律体制的可能的消极影响或司法监督。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垄断了一切强力救济,即便国际商事仲裁超越出国家法制框架但仍然无法动用为国家所禁止的民间私力强力救济,包括国际商事仲裁证据、财产等保全措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强制执行等环节的有效实现必须求助于特定的国家,从而使国际商事仲裁在这些方面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跌落回世俗国家的怀抱,通过综合权衡与博弈,最终达成国际商事仲裁与世俗国家的建设性或互利性对话,即国际商事仲裁以让渡自己的自治为代价,将自身交付与特定国家的属地管制之下,以此为条件来换取世俗国家的强力支持。应当指出,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化运动并非完全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交易,它更是仲裁与司法之间的一种妥协,妥协是一种艺术。通由妥协国际商事仲裁方能于入世之中成就出世之性。当国际商事仲裁入世之属地连接点一旦确立起来,仲裁将被再次国内化(re-nationalized),[65]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遂得以定位,依据此一定位相关国家被赋予了监管仲裁的权力同时也被施加了予仲裁以司法支持的责任。可见,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化运动既是它无从逃逸的命运枷锁,也是它无须逃逸、甚或主动寻求的命运归宿,它的直接要求是最大化相关国家的属地支持。
国际商事仲裁去身份化运动在绝对意义上是失败的,即便真正达到了去身分化的效果,没有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因此这只能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有利于仲裁、支持仲裁的结果选择性的理念。而且只有当这一理念真正立足于地域性支持的时候才能得以无限接近和广为实践,如同立足大地的树木只有在它的根须越往土地深处生长,它才能获得越往天空伸展的力量和支撑。国际商事仲裁的生存方式或许就是在世俗国家法律框架之内于边缘处游走,它与处于核心正统地位的国家诉讼机制保持必要的张力,在离心与向心运动中通过良性竞争所带来的动态平衡,仲裁与诉讼得以双双成就。
On Identity, De-Nation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y Zhang Chunliang
The ident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decides its legal status, and obtaining of the identity resort to a particular territory. To avoid the negative fette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its award brought by territorial identity, the trend of thought and the campaign of de-na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have started to show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De-nationalization is different from non-local. The manifestation of de-nationalization includes online arbitration, the arbitration roaming, arbitration in terra nullius and neutral countries, arbi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And de-nationalization is institutionalized in autonomy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adjudication of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supra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directly substantive law of arbitr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B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he judicial support, especially the re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rbitral awards,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territorial support, which makes them show a strong sense of territoriality. De-nation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ity form the tensil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such two concepts as support of arbitration and territory constrai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urvives at the edge and within the law framework of secular states. It maintains the necessary tension with the national litig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at the core of the core position of a country. The dynamic balance brought by the healthy competition between centrifugal and centripetal movement brings about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dentity De-Nationalization Territoriality
*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及Ghent University在站博士后。本文为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后研究课题《国际商事仲裁的案件管理》的阶段性研究成果(This paper is the partial achievement of Case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hich is post-doctoral research project in Ghent University)。
① 关于“最大化主义”、“最小化主义”,以及二者的上述评价详见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p.46-50.
② 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46-47.
③ 汪祖兴著:国际商会仲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页。
④ W.Laurence Craig,William W.Park and Jan Paulsson,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rbitration,3rd ed.Ocean Publications,INC./Dobbs Ferry,NY.P.497.
⑤ Bulletin ASA,1997,PP.316/319-330.
⑥ see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Arbitration at the Olympics:Issues of fast-track dipute resolution and sports law,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pp.10-103.
⑦ 谭兵等著:《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⑧ 汪祖兴著:《国际商会仲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⑨ 杨良宜著:《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⑩ 施米托夫著:《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页。
⑪ 杨良宜著:《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⑫ W.Laurence Craig,William W.Park and Jan Paulsson,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rbitration,3rd ed.Ocean Publications,INC./Dobbs Ferry,NY.pp.85-90.
⑬ 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217.
⑭ 韩健:“仲裁协议中关于仲裁机构的约定——兼评我国仲裁法中有关条款的规定”,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4期,第30页。
⑮ 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216.
⑯ 蔡鸿达:“海运合同中的‘北京仲裁条款’问题的探讨”,载《法学杂志》,1998年第3期,第26页。
⑰ 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361.
⑱ 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362.
⑲ 该案详见Court of Appeal,England,November 4 1991,ASA Bulletin,1992,p.555.
⑳ 谭兵著:《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但也有相反观点认为,英国1996年仲裁法要求仲裁协议“无论在争端发生之前签署还是之后签署,都必须是书面形式,或者其他可记录形式。”详见【英】道格拉斯.斯蒂芬:《工程合同仲裁实务》,路晓村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21] 以上案件详见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p.205-206.
[22] Philippe Fouchard Emmanua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 Fouchard Gaillard 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PEN PUBLISHERS, INC., NY, 1996. PP.312-313.
[23] 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176.
[24] 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8年第3期,第109-110页。
[25] 对该案的评价可参见刘想树著:《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9页。
[26] 刘想树著:《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27] 详见赵生祥、刘想树等著:《国际私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8] 有学者盛赞法国法代表了国际仲裁国内立法自由主义的方向,“法国法在国际仲裁协议方面是如此的自由以致于断难想象某份根据外国法有效的仲裁协议依据法国法却是无效的。”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p.239-240.
[29] 本段落下文关于此类连接点的阐述均见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p.224-225.
[30] See ICC Case No.5730/1988,Société de lubrifiants Elf Aquitaine vs. A.R.Orri,117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1990,PP.1029-1032.
[31] 刘想树著:《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7页。
[32] 刘想树、张春良:“关于仲裁条款独立性的两个乌拉特——兼评我国《仲裁法》第十九条”,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第70-71页。
[33] 汪祖兴著:《国际商会仲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34] 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231.
[35] 刘想树著:《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36] 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229.
[37] see Philippe Fouchard Emmanua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 Fouchard Gaillard 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PEN PUBLISHERS, INC., NY, 1996. p.396.
[38] 有学者对仲裁自裁管辖说与法院决定论两者的关系作了考究,认为二者事实上是一种等级关系,而不是平行关系,“如果当事人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作出的关于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仲裁庭的管辖权有异议,可向有关国家的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对此作出裁定。法院的裁定是终局的。”详见赵秀文著:《国际商事仲裁及其法律适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7页。
[39] 赵秀文著:《国际商事仲裁及其法律适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17页。
[40] W.Laurence Craig,Some Trend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Law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30 Texas Int’l L.J.Winter,1995,p.24.
[41] 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500.
[42] 刘想树著:《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43] See ICC Case No.4695/1984,in XI Year Book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86,p.149.
[44] 汪祖兴著:《国际商会仲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296页。
[45] 刘想树著:《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44页。
[46] 赵生祥等著:《国际私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47] 汪祖兴著:《国际商会仲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48] 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p.445.
[49] See Egyptian company vs. Dutch company,J.D.I.922,1984,P.111.ICC Award No.4265/1984
[50] 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841.
[51] 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p.808-813.
[52] 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720.
[53] F.Ramos Mendez,Arbitrage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et Measures Conservatoires,Rev.Arb.1985,p.51.
[54] 常怡等著:《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页。
[55] 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721.
[56] 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634.
[57]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VII,1982,P.290,299.转引自赵秀文著:《国际商事仲裁及其法律适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58] 朱克鹏:“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院干预”,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第49页。
[59] 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647.
[60] 赵秀文著:《国际商事仲裁及其法律适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61] 仲裁与法院之间的对话效果问题,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存在不同的效率。有学者认为,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此类对话是一种“聋人之间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deaf people),而在英美法系中则相对较好。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973.
[62] 转引自B.Leurent,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Arbitration Awards,12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3,p.269.
[63] 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982.
[64] 如有学者认为,国家仲裁法最经常影响国际商会仲裁的五个方面是:1.仲裁协议效力问题。2.诉讼事由的可仲裁性。3.仲裁的前提条件。4.临时措施。5.裁决书的审核。而这些问题通常由不同国家法律进行调整。W.Laurence Craig,Some Trend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Law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30 Texas Int’l L.J.Winter,1995,PP.496-497.
[65] 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46.
(责任编辑:余蕊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