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技术”的本质看现代技术的无根性
——以庄子的“技术”思想为例
陈徽
(同济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092)
从古典“技术”的本质看现代技术的无根性——以庄子的“技术”思想为例
陈徽
(同济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092)
作为一种解蔽方式,古典“技术”优游养德、通达大道,它不仅统一了“成己”与“成物”,也使“人之性”与“物之性”得到了充分的展开。相反,现代技术由于先天的观念缺陷和在世态度的无根性,既虚无化了物,又桎梏了人的自由。欲解现代技术之蔽,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解放,唯在于人的生存态度的根本转变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真诚平等的对话。
古典“技术”;解蔽;现代技术;无根性
在古典与现代,技术具有迥然不同的内涵与表现,二者之别,主要在于“生存态度”。具体来说,就是两种技术对物的领会和应对方式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相对于古典技术所彰显的灵动精神与丰富意蕴,现代技术展现了处世态度的虚无性:它既使物失去其性,将物虚无化,又因此而深化了人之生存的无根性。
鉴于技术一词已被现代化,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其义愈疏离于古典,其用亦益融于流俗之见,本文以“技术”指古典技术,以别于现代技术。
一、庄子对古典“技术”的思想阐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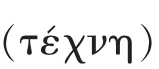
在《庄子》中,存在着许多出神入化的技艺展示,如庖丁之解牛、轮扁之斫轮、佝偻之承蜩、津人之操舟、丈夫之游水、梓庆之为鐻、臧丈人之钓、工倕之旋矩、“大马之匠”之捶钩等。这些技艺皆属人伦日用之技。甚至有“匠石之斫垩”者,其技还与日用无关,而仅为“游戏”之行。但庄子并未轻慢诸技,其于上述诸技之运,多有欣赏,赋予其美感,并申之以言道;对于那些“能工巧匠”,亦多有尊重和推崇。在上述诸例中,最著名的当属“庖丁解牛”了。从此例入手,可窥庄子的“技术”思想之大体。《养生主》云: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郄,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
首先,“技术”的充分展开表现为自由运作的过程。牛作为“大物”(《说文》),其体态浑沦,倘欲解之,非为易事,从哪动刀,如何运刀,皆不可随意。故常人之于解牛,必将有无所措手足之感。即使对于庖人而言,其间亦有“良庖”与“族庖”之分。以庖丁之见,庖人解牛之技的高低,可凭其刀的更换频率为据:“族庖月更刀”,显见其技之劣;“良庖岁更刀”,以见其技之精;而庖丁之刀虽历经“十九年”之运、数千牛之解,依然“若新发于硎”,则其技实已臻于化境。技之作为能力,只能在“运作”中表现出来,解牛之技亦然。庄子并没有具体描述庖丁是如何解牛的,仅以其体态和运刀的声音、节奏来拟其技之展开。这种拟写恰恰又烘托了庖丁出神入化的解牛技艺:一方面,庖丁的动作轻盈飘逸,切合音律,富有节奏,散发着美感;另一方面,所谓身、心一体,动作如斯亦是其心如斯,故“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者,固然是言刀的自由运行,何尝又不谓庖丁解牛时的优游之心!而“满志”之说也表明:技艺的自由运作还导向心灵的“丰满”或充实。基于庖丁解牛之喻,庄子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技术”运作的自由场景,一个身心无碍的生存境界。
其次,“技术”的自由运作是“道德”的自然呈现。面对文惠君的“技盖至此乎”之叹,庖丁对云:“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进乎技”亦即“进于技”,是谓由技而“进”之义。“进”乃“登”义(《说文》:“进,登也。 ”),故“进乎技”即谓由技而“登”(按:此“登”即“升”义),其“所登(升)”者,庖丁所好之道也。陆长庚云:“技精而进,至于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则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技若臻于化境,自然彰显道妙。此时技已不可仅被视作技,自是道体之现。得道即为成德,道、德本非为二:德从心上说,道就行而言,庄子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 ”(《庄子·天地》)
可见,“道德”之成,也可以“技术”为“进路”。此“进路”因人而异,或为解牛(庖丁),或为斫轮(轮扁),或为承蜩(佝偻丈人),或为操舟(津人),或为游水 (吕梁丈夫),不一而足,然不可弃技(事)而独冥其道,否则,所谓修道必入于寂灭之途。《天地》云:“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 ”“兼”者,“并也”(《说文》),“技兼于事”义为技与事“并行”也,技之运作亦即事之展开。“并”又有“兼并”义,若从此义,“技兼于事”就是技统摄于事,亦即技“依附”于事,更不可独行。技之能有所“艺”(涵养与通达),皆在人伦日用之中。钟泰指出:“盖诚用心于一艺,即凡天下之事,目所接触,无不若为吾艺设者。必如是能会万物于一己,而后其艺乃能擅天下之奇,而莫之能及。技之所为进乎道者,在此。”技艺之成,事之圆满,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操练”。正如庖丁解牛,其始习此技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与“族庖”无异;“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可谓“良庖”;待其技成,则身心无碍,游刃有余,事(解牛)得圆满,道德完备,且道德亦因技之展开而昭彰无遗。黄宗羲云:“工夫所至,即其本体。 ”此虽是就理学的“本体工夫之辨”发论,借以言庄子关于道(“本体”)、技(“工夫”)关系的思想,同样贴切。
复次,作为修道工夫,“技术”的涵养指向心、物为一的境界。道之运行自有其理路,此之谓“道理”,体现在事或物上,是为“事理”或“物理”。 庖丁解牛之技的自由运作也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过程。 “理”谓牛的肌脉纹理,其天然如此,故曰“天理”;“固然”之“然”指“大郄”与“大窾”(二者皆谓骨节间之空隙),亦天然如此,是为“固然”。庖丁解牛的技艺之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曰 “官知止而神欲行”。“非止不能稳且准,非行不能敏且活也。”此谓神、形(或曰心、身)一体。神、形虽一体,然以神为主,故王夫之云:“行止皆神也,而官自应之。”只有神、形一体,方能心驰体畅。二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此为神会“物理”,亦即心、物为一。如是,奏刀运技自能游刃有余。二者中,神、形一体又当统摄于心、物为一,倘若心、物为二,心驰体畅亦无从谈起。
庖丁之技究竟是如何成就的?《养生主》虽未具言,却也指出了技艺长期“操练”的重要性:所谓“始……解牛之时”、“三年之后”以至“方今之时”者,即谓技艺的“长进”是有时间性的。在《达生》篇中,庄子以“佝偻承蜩”为例,详细论述了“技术”的“生成”过程。其中包含了两个进路:一为单纯的技艺“操练”;一为涵养心神,以达于“凝神”(“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之境。基于前者,技艺的运用可达于精熟,或曰可达于心、身为一;基于后者,心与物能融会为一。这两个进路实为一体之两面,彼此交融、互为其根,本不可强作分别。
二、古典“技术”的本质
在“庖丁解牛”之例中,古典“技术”表现出以下特点:它既成就了物(物为事之物,是为“事物”,在此表现为解牛之事),也成就了人(即使庖丁成其为庖丁);既通达于道(所谓“技者,进乎道也”),也昭彰了“德”(表现为身心一体、心物合一的“游刃有余”境界)。这种“技术”观与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所谓解蔽性和真理性的判定,是非常通融的。
实际上,古典“技术”的上述特点在汉语的源初语义中已有所蕴含,并导向着它的本质。就字义而言,技与巧互训,《说文》云:“技,巧也。 ”又云:“巧,技也。”作为操作之巧,技又通于术。术本作“術”,从“行”。“行”在甲骨文中指道路,术(術)之本义亦为道路,《说文》云:“术,邑中道也。 ”道路有其所通达处(目的),是行之所由,象征着“行走”的途径或做事的方法。正是在此意义上,术与技相通,“引申为技术”,遂有“技术”之说。 所以,作为操作之巧,技或“技术”是通达于道或者以道为指向的。不仅如此,技或术还通于艺,合而言之,是为“技艺”或“艺术”。艺本作“埶”,《说文》云:“埶,种也,从丮、坴。 丮,持种之。 《诗》曰:‘我埶黍稷。’”坴谓土块,丮乃“持种”,埶(艺)的本义为亲手种植。种植五谷或桑麻是为了获取果实。欲达此目的,尚须培育之功,故埶(艺)又引申为培育或涵养。艺的内涵表明:技、术除了能成就某物、做成某事,还因其导向道与通达道,学习、掌握“技术”便也成为领会大道、成就己德的过程。《礼记·乡饮酒义》云:“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郑玄注云:“术,犹艺也。 ”)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
显然,古人以“六艺”行教,孔子主张“游于艺”(《论语·述而》),其意并不止于“技术”或“技艺”的掌握,而在于优游养德、通达大道。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道不是一个抽象的、高居于现实生存之上的超验之物,作为体,它显现于用,并范导着用。关于体、用,王夫之说:“当其有体,用已现;及其用之,无非体。盖用者用其体,而即以此体为用也。 ”“技术”的运行亦属于用,此用若臻于化境,则道妙毕现。所以,作为一种操作之巧和“供人行走”的“道路”,古典“技术”的本质在于它的通达(“术”)性与涵养(“艺”)性。 其所达、所养者,曰道也、德也。
既然是道之彰显,且以达道成德为鹄的,“技术”的“涵养”和展开便成为人与物深入“对话”的过程:一方面,人之于物要“无所保留地”敞开自己,“诚心” 向道,“虚而待物”(《庄子·人间世》),不能心怀功利、恃技傲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应答”或“回应”,物之于人也才会“无所保留地”敞开自身,无有遮蔽。循此以进,“技术”若达乎神妙,其运作不仅“游刃有余”、自由无碍,事物之大用亦得昭彰。正如庄子以“梓庆为鐻”喻之曰: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庄子·达生》)
《礼记·中庸》有“合外内之道”与“赞天地之化育”之说,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又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古典“技术”的自由运作之功有似于此:它既以心、物的相互敞开为前提,则心未尝封闭(“自闭”)于物,物也未尝封闭于人,世界的无限可能性、物的无限丰富性都在彼此的相互敞开中得到了实现。物因此成其为物(即“成物”,海德格尔称之为“物化”),世界因此成其为世界,人也因此成为自由的存在(即“成己”。按:此仅就技与道的关系而言,不考虑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 所以,“成己”与“成物”一体而在:“成物”是人的存在使命,且只有通过“成物”,才能“返回”(反过来)以“成己”。 人与物、“内”与“外”,本为一体,相互生发,无有止境。所谓道之生生性,尽在于此。
在古典“技术”的运作中,物自然也要被对象化,从人的生存世界中“突兀”出来。这种“突兀”或对象化并非意味着物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他者矗立在人的面前,它仍然是生存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未疏离于世界。且物亦是“活”的,而非“死的”、“无生命的”寂然之在。它与人本来就是“气息相通”的,只是因为“进入”某事被人所“关注”,以致“突兀”出来,成为对象。同时,技中自有规矩在。各种规矩展现了物和世界的某种数量关系,它们可被计量,立为法度,传之于人,普及于世。但技又不等同于规矩:掌握了规矩并不等于就具有技,就可以被视为能工或巧匠。孟子云:“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庄子亦以轮扁之口言曰:“斫轮……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庄子·天道》)轮扁之所以能成为轮扁,关键不在于通晓规矩、精于计量,而在于洞达物性(比如:所斫之木的材质和性状,所成之轮的形制,这些轮子将被用于何种车辆,这些车辆将被用于承载什么,主要在何种道路上行驶,等等。总之,物性必深契于人伦日用之行),与物为一。这种洞达与一体性是在长期的“操练”中成就的。“操练”是与物真诚地“对话”,是虔诚地“倾听”世界。在“操练”中,“技术”逐渐“成熟”,人与物也相互融合,亲密无间,“以天合天”(《达生》)。 就此来说,古典“技术”具有个体性特征,尽管其运作可以有各“技术”单元的分工与合作,但大规模的、量化式的专业化生产不适合它,商业化的生产更会伤害它。
如果遗忘了自己的通达性,丧失了道、德的关切,以技为技或者恃技济私,“技术”便会发生“异化”,失去其原本富有的生生性与通达性。对此,庄子以“机心”之说论曰: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
文中之“机”本作“機”:“机”乃木名,“機”则为弓弩上的发射机关(《说文》云:“主发谓之機。 ”)。 二者义本悬绝,简“機”为“机”是现代的事。弓弩不同于一般的弓,它杀伤力大,制作更加精巧,需要更高的“技术”。精巧与“技术”往往体现在“機”上,“機”实集制弩技巧之大成。 故“機”既有“機巧”之义,又可谓“技术”的象征。“械”本为刑具,“械,桎梏也。”(《说文》)后引申为器具或工具。“機械”者,就是機巧之械,或曰機(按:下文之“機”,皆从今俗作“机”)巧之具。在庄子看来,“机械”因其制作精巧对于成就事功效率更高,然惟因如此,也才会使人滋生“机心”。“机心”谓机巧之心,是指对“机械”的期待、依赖之心。“机心”若生,则“纯白不备”(喻真知沦丧),便会以技为技,执技忘道,以至道无所载。顺此而行,“机械”越精巧,“技术”越“进步”,它们与道也就越“遥远”。
庄子对于“技术”的态度和他关于“技术”本质的思考是一脉相通的。“技术”既然在人伦日用中不可或缺,是达道之方与养德之术,人们便不应轻视它,更不应否定它,而应积极地学习和精通相关技艺,以彰显事功、领会道妙、成就己德。但对于“技术”,人们亦须保持审慎和“虚无”之心,不迷恋“技术”,消弭“机心”。 唯有如此,所谓“虚而待物”、开放性地融入世界方才可能。
三、现代技术及其问题
相对于古典“技术”的生生性和通达性,现代技术则表现出显著的滞碍之弊。今人多从异化的角度批判现代技术的压抑性,以彰其与古典“技术”之别。其实,古典“技术”何尝没有异化?又何尝没有压抑?如庄子就以“机心”之说论述了“技术”的异化。至于技术为权力所用,成为社会管理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古今亦然。只不过,当今之世,这种情形更为严重甚而极端而已。当然,就资本对于技术的驾驭和影响而言,这是古典社会所缺乏的,但此非古典“技术”与现代技术区别的根本所在。二者之别,主要在于生存态度之异。具体来说,就是两种技术对于物的领会和应对方式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且因此不同,两种技术所表现出的异化与压抑,亦有区别。
现代技术的智力来源是现代科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代科学对于世界的态度也塑造了现代技术的世界观。在探讨现代技术之前,先来看现代科学是如何对待自然或物的。
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学科的实证性,它的世界观是世界的数学化。在数学化的世界里,物是自我封闭的,物与物之间也是纯数量的关系。物的自我封闭性源于物和人之间的相互封闭与相互对峙,它意味着思想上的二元论。二元论明确了科学主体与科学对象,是“科学的专门化的先决条件”。二元论虽以笛卡尔哲学为代表,其开拓者却是伽利略。胡塞尔指出:伽利略通过“对自然的数学化”,使“自然本身成为——用现代的方式来表示——一种数学的集”。于是,
伽利略在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这种抽象的结果是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人们可以说,作为实在的自我封闭的物体世界的自然观是通过伽利略才第一次宣告产生的……显然,这就为二元论开道铺路。此后不久,二元论就在笛卡尔那里产生了……把 “自然”理解为隔绝的、在实在方面和理论方面自我封闭的物体世界这种新观念很快引起了整个世界观的彻底变化。可以说,世界被分裂为二:自然世界和心灵世界。
世界的数学化为现代科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并成为现代科学家的基本世界观,正如W·海森堡在《物理学与哲学》中所云:“对于原子物理学家来说,如果他终究要使用‘物自身’这一概念的话,那么,物自身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数学结构。”世界的数学化最终还消解了二元论。因为,无论是物还是人,皆可定量化,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相对于物,人具有主动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物进行摆布而已。马尔库塞进而认为,由于自然的被动性和思维的主动性,笛卡尔的二元论最终又导致了科学主体“把自然设想为控制和组织的潜在工具和材料”的“技术先验论”。10]137
自然的这一遭遇,海德格尔称之为自然的对置性存在。对置性是事物在场的一种方式,关于其特征,海德格尔说:“它先行把提问的可能性标画出来。任何一个在科学领域内出现的新现象都要受到加工,直到它适应理论的决定性的对象性联系。这种对象性联系本身时而会变化。但对置性本身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对置性反映了现代科学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也昭示了现代科学的本质,二者如影随形,不可分割:“倘若这种对置性被放弃掉,则科学的本质也就会遭到摒弃。 ”在科学的视野下,诸物便受到“由在场者之对置性来规定”,“自然就是依照这种对置性,作为一个时-空的、以某种方式可预测的运动联系呈现给表象”。顺此思路,“一切对现实的对象化都是一种计算”。
自然的对置性存在区别于古典“技术”所蕴含的物的对象化。后者表现为人与物、人与世界的相互“渗透”、彼此交融和共同展开;对置性则是人对自我封闭之物的摆布、加工和利用,就是对自然的“促逼”。在此过程中,自然的本质丰富性便被深深地遮蔽了。因此,尽管世界的数学化和自然的对置性存在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思想前提,但世界的存在性、自然的无限丰富性也随之被剥夺或清除了。现代科学的这种“促逼性”无疑是抽象和粗暴的,展现了“处世态度”的虚无性:它使物失去其性,使物成为虚无。海德格尔曾精辟地说道:
科学始终只能针对它的表象方式预先已经允许的东西,亦即对它来说可能的对象……科学知识在它自己的区域里,亦即在对象区域里,是强制性的。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科学知识就已经把物之为物消灭掉了。原子弹的爆炸,只不过是对早已发生的物之消灭过程的所有粗暴证实中最粗暴的证实:它证实了这样一回事,即物之为物始终是虚无的。物之物性始终被遮蔽、被遗忘了。物之本质从未达乎显露,也即从未得到表达……这种情形已经发生过,而且还在发生着,它如此根本地发生着,以至于不仅物不再被允许成为物,而且根本上还决不能作为物向思想显现出来。

对置性转变为那种根据集置(Ge-stell)而得到规定的持存物(Bestand)的持存状态(Beständigkeit)。主-客体关系于是就获得了它纯粹的“关系”特征,亦即订造特征,在其中,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作为持存物而被吞并了。这并不是说:主-客体关系消失了,相反,它现在达到了它极端的、根据集置而预先被规定的统治地位。它成为一个有待订造的持存物。
所以,现代技术似乎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利器,人们可以凭借科技的不断进步“促逼”自然无休止地提供其所需要的东西,改造自然成为其所期望的样子。在此过程中,人本身也被技术所“摆置”、所“促逼”,成为被订造的持存物,丧失了作为人所应有的自由:“此集置咄咄逼人地把人拉扯到被认为是唯一的解蔽方式的订造之中,并且因而是把人推入牺牲其自由本质的危险之中。”这种物之为物的被遗忘和被遮蔽、这种“物我两失”的无根状态,用庄子的话来说,是“成心”使然,根本上源于人的“自闭”。这种“自闭”也封闭了物,封闭了人与自然的对话空间。
然而,揭示现代技术的消极性并非否定现代技术的积极价值,更不是要摒弃它。社会的进步、人类生存状态的不断改善,离不开现代技术之功。且目前诸多世界性问题(如:人口爆炸、资源乏继、环境恶化,等等)的解决,亦需借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力。现代科学、技术之“过”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现代人生存视野的狭隘性:它们本来只是人之于存在的众多解蔽方式之一,却不幸地被视为“一种决定性的方式”。由于现代科学强调实证性而拒斥形而上学问题,胡塞尔批评其概念是“残缺不全的”。概念上的残缺不全实为现代科学在世态度残缺不全的具体表现,这种残缺不全性又必然延展至现代技术对自然与物的态度上。
欲解现代科技之蔽,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解放,在马克思看来,需要物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就必须“返乡”。“返乡”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为解科学之蔽,“返乡”是以沉思来追问各门科学无可回避却又始终忽视以致遗忘的不可接近之物(如自然、人类、历史、语言等);为解技术之蔽,“返乡”则是重新体认技术的古典意义:“从前,不只是技术冠有的名称……也指那种把真带入美之中的产出。也指美的艺术的(产出、创作)……艺术仅仅被叫做。艺术乃是唯一的、多重的解蔽。”两种“返乡”实则是同一个过程,都是试图从本原处对无可回避之物的容纳、承受和倾听。在此过程中,物的自闭之门渐渐开启,敞开于世,接纳着人。在这种人与物的相互敞开中,所谓真理、美感、意义和信仰等才不会被遮蔽,也才不会残缺不全。
[1][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明]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清]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4.
[6][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吴 勇)
B223.5
:A
:1001-862X(2013)04-0101-007
陈徽(1973—),安徽凤台人,哲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