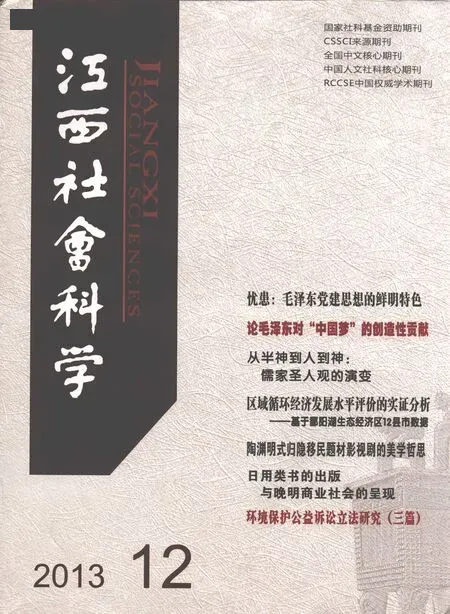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中适格原告的认定
邓冰宁
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中适格原告的认定
邓冰宁
我国司法实践承认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司法解释对近亲属关系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适格原告的范围过于宽泛,有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复杂的亲属关系和庞大的人口基数,被告将被迫对一个连直接受害人自己都很难确定的潜在原告群体承担近似无限的侵权责任。美国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以明确的亲属关系为基本判断标准,近年来又以实质性情感联系为标准进行更加深入的评价,以确保在完善救济受害人的同时有效兼顾对行为人自由的维护。参照美国法的成功经验,构建一种明确的亲属关系和实质性情感联系两大标准统一的全新机制,有助于为我国司法实践中适格原告的认定提供有效参照。
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适格原告;实质性情感联系;近亲属
邓冰宁,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吉林长春 130012)
我国司法实践承认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具体规定于2001年颁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侵权责任法》颁布后,虽然没有直接将这种责任吸收于具体规定之中,但是,实践中,法院仍然认可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司法解释对适格原告的规定过于简单,①导致其范围过于宽泛,主要表现为:司法解释没有细化判断继父母、养子女和同居者是否属于适格原告的标准,甚至以“其他近亲属”作为一个兜底条款。有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复杂的亲属关系和庞大的人口基数,被告将被迫对一个连直接受害人自己都很难确定的潜在原告群体承担近似无限的侵权责任。实践中,被告不仅需要向与直接受害人之间不具有正式婚姻关系的同居女友负责,②甚至需要向直接受害人的侄子女负责。③
美国法语境下,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bystander liability)的含义是:与受到严重身体损害的直接受害人具有密切亲属关系的第三人(原告),可以就因知悉事故的发生而蒙受的严重精神损害,向有过失的侵权行为人(被告)主张的金钱损害赔偿责任。美国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形成了体系完善的责任构成和责任承担机制,其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对于我国明确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本质及其紧密亲属关系要件的判断机制,以求平衡救济受害人和维护行为人自由两大侵权责任法的核心利益,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美国法划定适格原告范围的目的在于限制被告的责任范围,维护侵权责任的可预见性。“原告和受害人之间必须具有紧密的亲属关系这一要求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考量:必须为可救济性判断寻找到评价规则,而通常情况下,目睹具有紧密亲属关系的人遭受伤害的原告,将比那些目睹不具有紧密的亲属关系的原告受到更严重的精神震撼。”[1]为了实现这一功利主义目的,美国法并没有采用高度概括的方式为“紧密的亲属关系”做出一个具体的定义,也并没有提出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相反,美国法在具体个案中根据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不同种类的关系而进行分门别类的判断。具体而言,有可能符合紧密的亲属关系要件的潜在原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直接受害人具有明确亲属关系的原告;二是与直接受害人不具有明确亲属关系的原告。
一、与直接受害人具有明确亲属关系的原告认定
具有明确亲属关系的原告包括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如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具有法律上认可的正式亲属身份的养父母子女和配偶,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远亲以及与直接受害人共同生活的继父母子女。此类原告并非当然适格,在某些严格限制原告范围的州,只有那些与直接受害人具有紧密和明确的亲缘关系的原告才能够获得救济。华盛顿州就认为符合亲属关系要件的原告仅仅指:“妻子、丈夫、本州内登记的伴侣、儿童包括继子”以及“父母和兄弟姐妹”。[2](P565)美国法院在寻找可以作为判定可救济性标准的客观因素时,选择 “明确的亲属关系”的原因是:“法律推定,具有紧密亲属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律所要求的感情纽带。 ”[3](P223)
(一)判断父母是否适格的方法
第一,亲生父母当然适格。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亲生父母当然符合紧密的亲属关系的要求,“本案中的原告是胎儿的母亲,而且在胎儿死亡以及死胎出生时均身处现场并目睹整个事件。故原告当然可以提起诉讼”[4](P98)。
第二,继、养父母并非当然适格。(1)在严格限制的州中,养父母能否适格的关键在于被告是否知悉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紧密的亲属关系。Mobaldi案中,原告目睹她的养子因输入了过量的葡萄糖而引起严重的脑损伤,法院认为:“只要被告已经知道原告和她儿子之间关系的本质,可预见性的判断就已经得到了满足。”[5](P726)由于原告经常带她的养子到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被告应当知道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深厚感情,故法院认定:“本案中可以合理地预见到,因原告养子遭受损害而给原告造成的精神痛苦将远远超过养子的亲生父母所能遭受的。”[5](P726)(2)在相对自由的州中,亲生父母和具有监护人身份的养父母均可适格。[6](P6)除了上述两种以外,其他类型的父母均不能成为适格原告。《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第2315.6条明确规定伤者的“父母”可以作为适格原告,该州的“父母”包括亲生父母和具有监护人身份的养父母,但是法典并没有规定继父母的处理办法。法院据此认为:“当法律规定清晰和无歧义时,没有必要探寻立法者的真意。因此,我们不会将民法典中明文规定的‘母亲’扩展到继母。”[7](P841)(3)在最为自由的州中,只要原告能够举证存在紧密的关系即可获得救济,所有类型的父母均可以举证紧密关系的存在而成功起诉,并不局限于亲生父母,“原告和伤者或死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限定于血缘或婚姻。既然父母、配偶、兄弟姐妹等关系符合要求,那么继父母和继子女的关系同样符合要求。是否符合亲属关系要件要求的关键在于举证,原告负有证明紧密亲属关系的举证责任,被告可以进行反驳”[8](P740)。
(二)判断祖父母是否适格的方法
一方面,有的州只要原告是直接受害人的祖父母,就可以当然获得救济。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就明文规定:“伤者的祖父母或者其中一人”[9]有权获得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另一方面,其他州只有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实质性情感联系的祖父母才能适格。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明确亲属关系本身并不能当然证成紧密亲属关系的存在,原告仍然必须证明这种关系具有实质性的情感联系,“我们确实曾经认可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具有紧密的亲属关系。但是,被告误读了我们对于祖父母和孙子女关系的信赖程度……特定法律上亲属关系本身只是证明个案中亲属关系紧密程度的证据之一……”[10](P954)
(三)判断兄弟姐妹是否适格的方法
第一,源于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当然适格。美国法院依据通常观念认定这种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当然适格。Garrett案中,原告和她的亲弟弟在电影院外的栅栏上看电影,遭到了警察的驱赶,一辆没有打开任何灯光的警车碾过了原告的弟弟,造成严重身体损伤。法院认定:“依据本案案情,原告可以请求被告赔偿她因目睹她的兄弟受伤而蒙受的精神损害。”[11](P143)
第二,各州在其他旁系血亲中的兄弟姐妹能否适格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法中,适格的堂兄弟姐妹必须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相互关爱的、实质性情感联系。判断实质性情感联系的客观标准包括:(1)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是否具有血缘、婚姻或者共同组成一个家庭组织的相互关系;(2)双方是否具有物理联系、是否生活在一起;(3)一般理性人能否合理预见,原告是否目睹直接受害人遭受损害;(4)双方的物理联系和情感联系是否稳定和持久。[12]Guzman案中,原告和她的远房表姐一起长大,于事故发生时生活在一起。原告能够证明他们是因为稳定的情感联系而共同居住在一起。原告目睹她的表姐在人行横道上受被告驾驶的汽车撞击致死。虽然原告和她的远房表姐之间存在一定的感情联系以及共同居住的物理联系,但是,双方却并非传统意义上家庭结构的成员,法院认定双方的关系并不是固定和永久的,双方的亲属关系并不具有值得救济的紧密性,“本案中,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并不符合紧密型的要求,因为二人共同居住的关系是转瞬即逝而非永久性的,本案中并不存在‘异常的情形’足以证明她们亲属关系的紧密性。由于他们共同居住关系不具有永久性本质,原告不能请求被告承担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13](P3)。
第三,姑嫂叔舅妯娌连襟和继兄弟姐妹一般并不适格。一般情况下,法院拒绝认可姑嫂叔舅妯娌连襟和继兄弟姐妹,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紧密的亲属关系。加州上诉法院认定,虽然姑嫂叔舅妯娌连襟和继兄弟姐妹是广义上的家庭成员之一,但他们与直接受害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并不具备值得救济的紧密性,“‘亲属’一词不仅包括继子,也包括连襟,堂兄弟姐妹和数之不尽的亲戚们。但是,没有法院认可所有的亲戚都可以成为适格的原告”[3](P222)。 该法院认为,一旦向姑嫂叔舅妯娌连襟和继兄弟姐妹提供救济,将迫使法院详细查明所有姑嫂叔舅妯娌连襟和继兄弟姐妹与直接受害人之间真实的情感状态,徒增不必要的司法成本,“如果法院必须查明所有这些姑嫂叔舅妯娌连襟、继兄弟姐妹和继父母子女与直接受害人之间情感联系的真实状态,将导致法院面临巨大的负担”[3](P223)。 例外情况下,当法院概括承认所有家庭成员均可以作为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原告时,姑嫂叔舅妯娌连襟和继兄弟姐妹才能成为适格原告。[14]
(四)判断配偶是否符合紧密的亲属关系的方法
一方面,具有该州法律所认可的、正式的婚姻关系的配偶当然适格。法院一般不会审查夫妻之间真实的情感状态,而是概括地将所有具有正式婚姻关系的配偶视为具有紧密亲属关系的适格原告。[15](P6)另一方面,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非婚同居者才能适格。加州民法典就明确规定:“本州中,共同生活的伴侣和具有正式婚姻关系的配偶一样,有权获得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16]其中“共同生活的伴侣”指的是:“两个希望以亲密和互相忠实的关系共同生活的成年人”。[17]这些法院在评价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符合紧密的亲属关系要件要求的情感联系时,可供考虑的因素包括:(1)双方是否互相依赖地共同生活;(2)双方是否为了共同生活而努力;(3)双方是否有过结婚的打算;(4)双方的共同生活方式是否符合社会一般观念要求;(5)双方共同生活是否具备实质性情感联系的外观;(6)双方是否订婚;(7)双方同居关系是否登记;(8)一方是否将另一方指定为人身保险受益人;(9)一方是否为另一方支付保险费用; (10)双方是否共同养育了子女。[18]只有具备这些相对客观的要素的人,法院才认定其为适格原告。
二、与直接受害人之间不具有明确亲属关系的原告认定
大多数州拒绝向与直接受害人之间不具有明确亲属关系的原告提供救济,这就导致许多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紧密的人际交往关系的群体不能获得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这些州拒绝救济与直接受害人之间不具有明确亲属关系的原告的原因仍然在于:限制被告的责任范围,确保被告仅对具有可预见性的损害负责,“在赔偿无形损害的案件中,仅仅依靠可预见性标准确定诉权是不够的。为了避免被告承担漫无边际的责任,确保被告的过错程度与责任程度相适应,必须对原告的诉权进行限制,否则,无法保证所有潜在的被告们承担合理的责任”[19](P826)。实践中,美国法院通过两种方式,在维护侵权责任可预见性的前提下,向不具有明确亲属关系、但是能够证明与原告之间存在实质上情感联系的原告提供救济。
(一)将与直接受害人之间不具有明确亲属关系的原告类推为直接受害人的家庭成员
有的法院依据原告对于自己与直接受害人之间真实情感的证明,认定原告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等同于紧密亲属关系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将原告类推为直接受害人的家庭成员。例如,一旦法院认定具体个案中存在某些能够反映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等同于紧密亲属关系的真情实感的客观要素,而应当向原告提供救济时,法院会将原告类推为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之一,从而适用只有紧密的近亲属才能主张的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些能够反映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真情实感的客观要素包括:原告和直接受害人是否共同居住;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否稳定和持久;双方是否经常共同进行社交活动;双方的关系是否具有可信的、有形的外观,足以符合类似家庭成员的程度。[20](P891)一旦原告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这些极其特殊的社会关系时,少数法院就会类推原告属于直接受害人紧密的家庭成员之一,“共同生活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就可以等同于家庭组织结构”[20](P895)。这种做法将相互之间不具有血缘或亲属关系、仅具有能够通过客观环境证据证明的亲密感情的群体,与符合紧密的亲属关系要件要求的家庭成员等同起来,最终扩张了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当定义的灵活性已经成为其它法律领域发展的重要方面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在侵权法的发展和实践中同样如此。很明显,在侵权法中适用‘紧密的亲属关系’一词时,必须考察双方真实的情感状态而非机械地适用概念”[21](P1254)。
(二)纯粹依据实质性情感联系向与直接受害人之间不具有明确亲属关系的原告提供救济
这种方式不考虑原告与直接受害人之间是否具有明确的亲属关系,也不将原告类推为直接受害人的家庭成员,而是在庭审质证的基础上统一交由陪审团判断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具有可救济性的、实质性的情感联系。由此,法院承认与直接受害人之间不具有血缘或亲属关系的主体也有可能成为适格原告,并且向这些能够证明自己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实质性的情感纽带的原告提供救济。例如,虽然不具有正式婚姻关系也未同居,但是,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的情侣关系已经维持了8年,双方开设了联名账户,并且共同承担日常生活成本,直接受害人是原告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原告也将直接受害人纳入自己的医疗保险和牙医保险的共同受益人范畴,这些客观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具有可救济性的社会关系,故法院认定原告的精神损害具有事实上的可预见性。[22]
三、我国适格原告认定机制之完善
以美国法的优秀实践成果和丰富实践经验为参照,我国法院在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案件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时,应当将原告分为三类进行分别判断,并且遵循一条统一适用于三类原告的例外规定。
(一)三类适格原告的分别规定
由于设置紧密亲属关系要件的功能价值在于限制侵权责任的范围,那么,只要维护这一前提下,完全可以适当拓展适格原告的范围。美国司法实践中,向具有明确亲属关系以外的原告提供救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为了全面维护受害人的权益,我国法也应当向下列三类具有较强可预见性的原告提供救济,“我们可以借鉴英美法上‘精神打击’的相关制度,推定近亲属与直接受害人具有此种足够亲密的感情关系,除非有相反证据才可以推翻此种推定;对于近亲属以外具有其他关系的第三人,则需要对其与直接受害人之间亲密的感情关系予以证明”[23](P110)。
第一,当然适格的原告认定。依据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我国法中当然适格的原告应当仅仅指的是配偶、父母和子女。当然适格的原告无须额外举证是否存在实质性的情感联系。为了确保侵权责任的可预见性,配偶仅仅指的是具有正式婚姻关系的夫妻而不包括同居者;父母指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生父母和具有监护人地位的养父母,不包括继父母;子女指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子女和具有被监护人地位的养子女,不包括继子女和义子女。
第二,拟制适格的原告认定。法院可以根据由原告举证的、原告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的实质性情感联系,将部分具有明确亲属关系的潜在原告拟制为适格原告。此类原告仅需证明自己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与明确亲属关系相适应的情感联系即可。拟制适格的原告包括:继子女、继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继兄弟姐妹、姑嫂叔舅妯娌连襟和同居者等等。
第三,类推适格的原告认定。法院也可以基于由原告举证的、原告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的实质性情感联系,将部分与直接受害人之间不具有明确亲属关系的潜在原告类推为适格原告;类推适格的原告需要承担比拟制适格原告更重的证明责任,“这些可能的原告群体在证明重要的感情联系时必须承担更重的证明义务”[24](P115)。原告必须证明自己与直接受害人存在特殊的社会关系,例如,“在事故发生时,原告对于直接受害人负有救助义务”[25](P42)。类推适格的原告包括直接受害人的同事、朋友、同学、室友、师长、校友、邻居、义兄弟姐妹、商业伙伴、公会成员、医患和具有共同爱好的熟人等等。
(二)统一适用于三类原告的例外规定
美国法中,法院也开始倾向于依据实质性情感联系而不是亲属关系判断精神损害的可救济性。故为了兼顾被告的行动自由,应当增设一条例外规定:“当被告能够证明原告与直接受害人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情感联系时,原告不能获得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这一例外不仅适用于类推适格和拟制适格的原告,也适用于当然适格的原告。这一例外规定确保了适格原告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可救济性的真情实感,从而维护了侵权责任的可预见性,“即使父母、兄弟、夫妻朋友也要依照个别事实认定,而不当然成立亲密关系”[26](P31)。
评价实质性情感联系的因素包括:“双方之间社会关系持续时间、双方相互依赖的程度、双方对共同生活的贡献程度、双方共同经历的内容和质量、以及双方是否是同一家庭组织机构的成员、双方彼此之间的情感信赖、双方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双方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生活的外观”[21](P378)。 此外,也可以额外评价被告是否能够合理预见该类原告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实质性情感联系这一问题。[25](P42)
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案件中,借鉴美国法优秀成果,完善我国适格原告认定机制的重要意义在于,预防极端不公平的结果:承担侵权责任时,被告只能自己一力承担;追究侵权责任时,被告却要面对来自整个世界的非难。
注释:
①本文中对适格原告的讨论,仅限于依据原告和直接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判断原告能否提起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范畴。
②参见“吴丽华与高荣妹等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上诉案”,(2013)浙湖民终字第82号,法宝引证码CLI.C.1345066。
③参见“翟玉珍等诉高长社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2008)博民初字第564号,法宝引证码CLI.C.240385。
[1]Restatement(Third)of Torts:Phys.&Emot.Harm §48,comment f(2012).
[2]Shoemaker v.St.Joseph Hosp.and Health Care Center,56 Wash.App.575,784 P.2d 562..
[3]Moon v.Guardian Postacute Services,Inc.,95 Cal.App.4th 1005,116 Cal.Rptr.2d 218.
[4]Johnson v.Ruark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ssociates,P.A.,327 N.C.283,395 S.E.2d 85.
[5]Mobaldi v.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55 Cal.App.3d 573,127 Cal.Rptr.720.
[6]Bayer v.Monroe County Child&Youth Services, F.Supp.2d,2007 WL 3034009.
[7]Daigrepont v.Louisiana State Racing Com'n, 663 So.2d 840.
[8]Eskin v.Bartee,262 S.W.3d 727.
[9]LSA-C.C.Art.2315.6(4).
[10]Lozoya v.Sanchez,133 N.M.579,66 P.3d 948.
[11]Garrett by Kravit v.City of New Berlin,122 Wis.2d 223,362 N.W.2d 137.
[12]See Kriventsov v.San Rafael Taxicabs,Inc., 186 Cal.App.3d 1445,229 Cal.Rptr.768,p770,Trapp v.Schuyler Construction,149 Cal.App.3d 1140,197 Cal.Rptr.411,p412,Guzman v.Kirchhoefel,Cal.Rptr.3d, 2005WL 1684978,P3.
[13]Guzman v.Kirchhoefel,Cal.Rptr.3d,2005 WL 1684978.
[14]Dale Joseph Gilsinger,J.D.:98 American Law Reports ALR5th 609.15.Bystander's sister or brother in law,2002.
[15]In re Smith,Slip Copy,2012 WL 2341571.
[16]West's Ann.Cal.Civ.Code 1714.01.
[17]West's Ann.Cal.Fam.Code 297.
[18]See St.Onge v.MacDonald,154 N.H.768, 917 A.2d 233,p236,Drew v.Drake,110 Cal.App.3d 555,168 Cal.Rptr.65,p66,Graves v.Estabrook,149 N.H.202,818 A.2d 1255,p1262,Arnott v.Liberty Mut.Fire Ins.Co,2010 WL 8544209(Trial Order),Lozoya v.Sanchez,133 N.M.579,66 P.3d 948,P958.
[19]Thing v.La Chusa,48 Cal.3d 644,771 P.2d 814.
[20]Borough of Glassboro v.Vallorosi,117 N.J.421,568 A.2d 888.
[21]Dunphy v.Gregor,261 N.J.Super.110,617 A.2d 1248.
[22]Arnott v.Liberty Mut.Fire Ins.Co,2010 WL 8544209(Trial Order).
[23]张新宝,高燕竹.英美法上“精神打击”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借鉴[J].法商研究,2007,(5).
[24]James v.Lieb,221 Neb.47,375 N.W.2d 109.
[25]Colin E.Flora,Special Relationship Bystander Test:A Rational Alternative To The Closely Related Requirement Of Negligent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For Bystanders[J].39 Rutgers Law Record 28,2011-2012.
[26]潘维大.第三人精神上损害之研究[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责任编辑:胡 炜】
D913.7
A
1004-518X(2013)12-016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