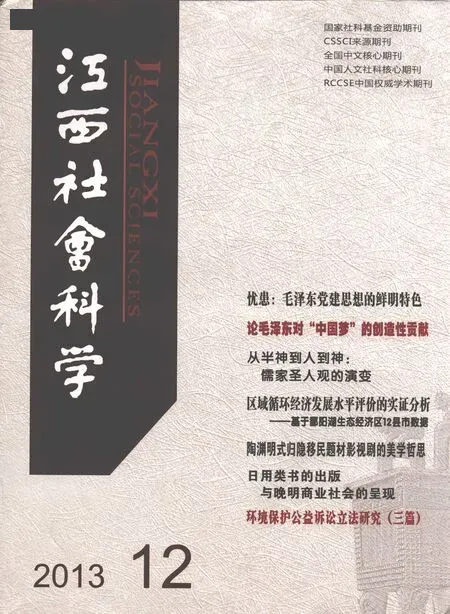论葛兰西哲学的语言学起源
■吴昕炜
1937年,当年仅46岁的葛兰西在饱受法西斯残酷迫害和自身病痛折磨溘然长逝后,他的名字除了在意大利和共产国际之外,还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随着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进,新左派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运动和思潮的勃兴,葛兰西的名字及其哲学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他本人也被尊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他的哲学也被公认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反对教条主义的典范而受到深入的讨论和研究。葛兰西哲学之所以如此富有魅力,原因就在于其鲜明的民族特性和个性特征,还在于其“重视语言,以语言来定义哲学,说明哲学的基本问题,开展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1](P530)这一特点可以追溯到葛兰西的学生时代,从那时起,他就对语言学产生浓厚兴趣,开始了系统的语言学学习,即使被捕入狱也未曾放弃语言学研究的爱好。追寻葛兰西的哲学创新之路,我们有必要对葛兰西哲学的语言学起源问题进行考察,并由此揭示葛兰西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贡献。
一、从大学生到革命者:葛兰西语言研究的发端
历史地看,葛兰西对语言学研究的兴趣始于在都灵大学学习的青年时代。1911年秋,葛兰西以优异成绩考取阿尔贝托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进入都灵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入校不久,他就引起了对其今后理论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巴托利教授的注意。
巴托利教授其时在都灵大学讲授语言学,他对撒丁语言很感兴趣,认为撒丁语在拉丁俚语的传播和创新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所以非常注重搜集和研究撒丁语的各种材料。由于文学系来自撒丁岛的学生不多,而葛兰西恰好是撒丁岛人,撒丁语也讲得很好,巴托利立即与他取得联系,并与他合作进行撒丁语研究。初入大学的葛兰西对这一研究投入了极大热情,他一方面在巴托利教授的语言学课堂上认真听课,一方面精心为巴托利教授提供其研究所需的撒丁语信息。他曾专门为自己把握不准的一个单词在撒丁语里的准确发音写信问自己的父亲,并特别叮嘱父亲“要用福尼的方言……并明确指出s在什么时候发清音,什么时候发浊音”[2](P76)。在大学校园里,葛兰西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交际甚少,不喜欢看戏,也无暇光顾咖啡馆,每天除了去教室听各种课程,就是沉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埋头读书研究。他对撒丁文化和语言研究的执着和痴迷令巴托利教授赞赏有加,他们的接触也因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频繁,有时,他们甚至可以长时间站在教授家附近的廊柱下讨论语言学问题。语言学课程结束后,巴托利教授给葛兰西打了满分并且给了一个很高的评语。从当时的情形看,巴托利教授应该是对葛兰西今后从事语言学的专门研究寄予了厚望,正因为如此,葛兰西才会在1927年3月19日从狱中发出的那封信里无比感伤地谈道:“我生平最大的‘内疚’之一是给我的良师、都灵大学巴尔托利教授带来的巨大痛苦。他确信我是最终摧毁‘新语法学派’的大天使。因为他本人作为他们的同代人,同这些声名狼藉的学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表态时出于礼貌和对行将就木的学说的尊敬,不敢越雷池一步。”[3](P55)虽然葛兰西没有如巴托利所愿成为一名语言学家,但他还是从巴托利那里得到了关于语言学的长久兴趣与启发。
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语言学课程,与巴托利教授合作进行撒丁语言研究外,葛兰西还很喜欢意大利文学课。与其他文学系学生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同,葛兰西并不仅仅满足于此,而总是试图从文学作品中发现比艺术价值更多和更重要的东西。这一点令当时讲授意大利文学课的科斯莫教授印象颇深,他也因此成为葛兰西最为亲近的老师之一。如果说巴托利教授的语言学激发了葛兰西的理论兴趣,那么科斯莫教授的意大利文学课则让葛兰西展示出极强的研究能力。在1916年11月29日的《前进报》上,他对自己的大学时代是这样评价的:“关于他的大学启蒙时期,他 (撰稿人)清楚地记得,教师们通过讲课使他了解到,研究方法是经过几世纪的努力才逐步完善起来的。例如……在语言学方面,是怎么经过传统的经验论的尝试和失败才达到历史的研究方法,以及例如德桑克蒂斯在写意大利文学史时所遵循的准则和惯例是如何经过繁重的研究和体验才逐步成为真理的。这是学习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正是这种创造精神使我们掌握了渊博的知识,使我们在知识界新生活的烈火中得到了锤炼。”[2](P78)1915年春季,葛兰西通过大学最后一门考试——意大利文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大学毕业后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后的葛兰西依然延续了学生时代的语言学研究兴趣。这方面的佐证就是他一直思考意大利语言统一问题并专门撰写了关于意大利语言学的论文。1930年11月17日他在给塔吉娅娜的信中就提到了自己的这篇论文。葛兰西在信中说:“10年前我写过一篇曼佐尼论语言问题的论文,它要求对意大利文化组织有一定研究,自打书面语(所谓中期拉丁语,即从公元5世纪到14世纪的书面拉丁语)同民众的口语彻底割裂,罗马集中化中止,就分化出无数方言。在这种中期拉丁语之后是俗语,俗语又重新被人文主义拉丁语所吞灭,产生一种学术语言,就其词汇是通俗的,而不是指音韵学,更不是指从拉丁语中重构的语法:于是继续存在两种语言,民间语言或业余语言,和学术语言或知识分子及有教养阶级的语言。曼佐尼本人在重写《婚约夫妇》时,在关于意大利语的论文中,其实只注意到语言的一个方面——词汇,没有注意到句法——任何语言中本质的部分,从而千真万确:虽然英语有60%多的拉丁语汇或新拉丁语汇,但它属于日耳曼语;相反,罗马尼亚语有60%多的斯拉夫语汇,却属于新拉丁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3](P280)葛兰西在信中提到的10年前即1920年,他时年29岁,正为刚成立不久的《新秩序》周刊担任撰稿人,组织“共产主义教育小组”并亲自参与占领工厂运动。在如此繁重的革命工作中还会写出研究意大利语言问题的论文,这初看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当我们联系他在大学所受的专业教育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就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情了。当时,意大利还没有统一的语言,不同地区的意大利人各自使用自己的方言,作家进行文学创作也是使用方言。葛兰西在信中描述的就是意大利缺乏统一语言的这一事实。他不仅梳理了意大利语言问题复杂局面形成的历史因素,还指出它造成了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之间产生分裂的严重后果。如何克服这种分裂就是当时意大利知识分子阶层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葛兰西在信中提到写作《婚约夫妇》的曼佐尼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人物。曼佐尼是意大利著名作家,他有感于国家缺乏统一语言的情况,用佛罗伦萨方言托斯卡纳语和伦巴第语融合拉丁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意大利文学语言和表达方式,《约婚夫妇》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意大利历史小说。在小说获得良好反响后,曼佐尼进一步提出建立统一的意大利民族语言的设想,即,把作为佛罗伦萨方言的托斯卡纳语推广成为意大利的官方语言。葛兰西对此是不赞同的,他撰写这篇论语言问题的论文很可能就是要指出曼佐尼语言政策的问题,当然,由于葛兰西的这篇语言学论文现在已经无法找到,我们无从得知它的具体内容,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葛兰西在另一个地方为我们保留了其哲学的语言学起源的较为完整的轨迹,这就是他的《狱中札记》。
二、从《笔记本1》到《笔记本29》:葛兰西《狱中札记》的语言学研究线索
1929年2月,被捕入狱两年多的葛兰西获准可以在狱中写作。他决定系统地进行阅读,并深化对某些问题的研究。为此,他先从翻译入手,开始记读书札记,在笔记本上标注了“1929年2月8日”,这就是《狱中札记》的第一本——《笔记本1》。在这本笔记的扉页上,葛兰西写下了狱中研究的提纲共16个题目。两年前,在1927年3月19日的信中,葛兰西就提到过自己准备在狱中研究4个方面的问题:一是19世纪意大利公众精神的形成,二是比较语言学,三是皮兰德娄的戏剧以及意大利戏剧趣味的变化,四是连载小说与文学中的民众趣味。[3](P54-55)《笔记本1》扉页上的16个题目就是葛兰西对这4个方面问题的细化。其中,标号为12和14的题目就是直接关于语言学的:前者是“意大利的语言问题:曼佐尼和阿斯科里”,后者是“新语法学派和新语言学派(‘这张圆桌是方的’)”。[4](P99)这两个题目代表了葛兰西语言学研究的大致思路,即,一方面是从曼佐尼和阿斯科里关于语言问题的交锋中批判曼佐尼的语言观,另一方面则是从新语法学派和新语言学派的比较中批判克罗齐的语言观。
首先,葛兰西支持阿斯科里对曼佐尼的语言观进行批判。正如在1930年11月17日给塔吉娅娜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葛兰西认为,把语言仅仅理解为词汇是不够的,这正是曼佐尼语言观的缺陷所在。而在现实中,曼佐尼却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推行统一的规范意大利语。针对这一现状,语言学家阿斯科里提出了与曼佐尼不同的看法。在阿斯科里看来,民族语言不是强制推广的,而是通过人们的交往而逐渐发展出来的。[5](P28)阿斯科里的这一见解来自于他的底层语言学说,即语言的演化受底层语言的历史影响。他认为,人们在使用第二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同时,还会保留母语的一些习惯,它会对第二语言的学习产生抵触作用。阿斯科里就是用这种近似于人类生物学的语言学观点来批评曼佐尼推行的意大利语言统一运动,认为曼佐尼的这种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曼佐尼是把一种官方语言强加给先前人们所使用的方言土语,也许人们会使用这种官方语言,但是先前的方言土语作为底层语言将对官方语言产生持续影响和强大压力。
其次,葛兰西通过新语法学派和新语言学派的对比批判了克罗齐的语言观。克罗齐在当时的意大利思想界名望极大,他对历史主义和人的文化创造性的强调给葛兰西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马克思早年深受黑格尔影响一样,葛兰西思想的形成也深受克罗齐的启发。然而,葛兰西对克罗齐的接受并不是全部的,也经历了一个批判的过程。被捕入狱后,虽然葛兰西在很多笔记中都涉及对克罗齐的批判,但是他一直存有一个从语言学的语法角度来切入批判克罗齐的想法。在1927年12月12日致塔吉娅娜的信中,他就提到要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我已放弃写作一篇论文的计划 (迫不得已,因为不可能获准使用写作所需的材料),论文的题目是《这张圆桌是方的》。我想让这篇论文成为现在以及将来囚徒知识产品的样板。可惜这一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得不到解决,这使我有点遗憾。但我向你保证,这一问题存在并已展开讨论,计有几百篇学术论文与争鸣文章。这不是个小问题,如果你想它意味着‘什么是语法?’,并且每年在世界各地不可胜数的语法被无数人类精英贪婪地吞噬,而不幸的民族对自己被吞噬的语法无精确意识。我不想向你展开我的论证,即使提纲挈领也不,因为书信的容量不够。”[3](P116-117)葛兰西在这里提到的《这张圆桌是方的》最终出现在《笔记本29》中。这本标号为29的笔记本也是他在狱中完成的千页笔记中的最后部分,被葛兰西命名为《语法研究笔记》。在这本笔记中,葛兰西对新语法学派和新语言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梳理,赞成新语言学派注重考察语言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观点,而批评当时欧洲所流行的新语法学派强调语言变化的语法和语音规律。他所赞成的新语言学派的观点恰好来自于大学时代的语言学导师巴托利。在巴托利看来,新语法学派的理论家们只是把语法当作词和语音的集合体来研究,这种只考虑语法、语音,而把语言与人的生活、历史、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割裂开来的做法并不是真正的语言研究。与之不同,巴托利强调,语言是一种精神活动,其运用和变化都体现着个人创造和意志。而且,“语言不仅仅只是语法和词汇,语言、政治和文化是全球历史进程不可分割的相关部分”[6](P26)。这种把语言与社会、文化、历史联系起来考察的思想成为葛兰西批判克罗齐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在笔记的开篇,葛兰西引用了克罗齐对“这张圆桌是方的”这一句子的看法,认为克罗齐赞同传统语言学家的观点,即,合乎语法但在逻辑上说不通。此外,克罗齐还进一步指出这种句子在美学上也是说不通的。语法与逻辑、美学不同,它不是科学,而是一种需要遵守的语言规则,除了判断是否符合这种语言规则外,没有其他的判断功能。也就是说,语法分析只能解决语法规范问题,而不能判断它是否合乎语言表达的习惯。克罗齐的这种看法表达了他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和美学表现的观点。
在关注语言的表现性这一点上,葛兰西对克罗齐是肯定的,但是葛兰西对克罗齐的观点并不满意。他进一步指出,克罗齐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给语法下定义。葛兰西认为,即使是像“这张圆桌是方的”这样有语法错误的句子也是一种表现,它表现了这个句子在含义上的可笑和荒谬。所以,即使以克罗齐自己的哲学观点来看,他的这篇文章也是有错误的。[5](P179)为了解决克罗齐的问题,葛兰西对语法进行了分析,这些关于语法问题的论述和关于世界语问题的观点构成了他揭示世界观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隐喻。
三、语法问题与世界语:领导权的政治隐喻
由于克罗齐没能对语法加以定义,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特别对语法进行了精细分析。在《笔记本29》中,他把语法分为内在语法和规范语法。[7](P90)所谓内在语法,指的是人们不自觉的语言习惯。所谓规范语法则与内在语法不同,它指的是:“相应的监测,相应的教学以及相应的由类似‘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请你更明白地表述’等问题所表达的审查,还有模仿和梳理。”[5](P180)规范语法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语法体系。在确定了两种语法后,葛兰西进一步阐述了两种语法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首先,葛兰西为规范语法赋予了政治特征,认为规范语法是经过内在语法的政治选择而形成的。正如曼佐尼希望把托斯卡纳语推广成为意大利官方语言一样,这种行为就是政治选择,而托斯卡纳语就在这种政治选择中由内在语法变成了规范语法。其次,内在语法和规范语法有历史的联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在《历史的和规范的语法》一文中,葛兰西明确指出:“我们在处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就像历史和政治,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两者像历史和政治一样分开。另外,由于作为文化现象的语言研究是从政治需要中产生的(或多或少自觉地表达),对规范语法的需求给历史的语法及其‘合法概念’施加了影响(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种传统因素自上世纪以来,已经加强了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把语言的历史当作‘语言科学’来研究的方法)。”[5](P185)在这里,葛兰西把自己和实证主义者以及自然主义者作了区分,他并不否认内在语法具有内在性,但他所理解的内在性会受先前的规范语法或者历史形成的思维定式的影响。这意味着,由于具有政治的特征,内在语法与规范语法的关系十分微妙。正因为如此,在葛兰西看来,语言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文化或者美学问题。
除对两种语法进行区分外,葛兰西还通过阐发世界语问题揭示出语言蕴含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所谓世界语,指的是一种人造语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曾经提到过它,指出:“人造语只要还没有流行开,创制者还能把它控制在手里;但是一旦它要完成它的使命,成为每个人的东西,那就没法控制了。世界语就是一种这样的尝试。”[8](P114)葛兰西对世界语问题的思考时间跨度很长,从1918年参与世界语的论战到《狱中札记》,他在很多场合都对此有过论述。1918年2月16日,葛兰西在《人民呼声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单一语言和世界语》的文章就是首次涉及这个问题。葛兰西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对自己和《前进报》关于世界语的论战进行一个总结。当时,为了与曼佐尼的语言方案相抗衡,意大利社会党是主张用世界语作为意大利通用语的。《前进报》作为意大利社会党的机关报,积极支持党所提出的鼓励学习和推广世界语的主张。葛兰西曾对《前进报》的观点进行过批评,但是《前进报》并不接受葛兰西的批评,认为即使葛兰西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世界语在实践上也是有用处的。[5](P26)葛兰西在文章中对此做了回应并批评社会党推广世界语是把自己选定的语言强加给人来使用,这是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他认为:“语言学的压力只能是从底层自下而上引入。”[5](P30)
如果说曼佐尼的语言方案或多或少还带有从底层语言中吸收精华的意思,那么,意大利社会党的世界语方案就是完全脱离使用者实际情况的一厢情愿。被捕入狱后,葛兰西在多本笔记中又提到了世界语。例如,在《笔记本3》中,葛兰西以“语言问题与意大利知识分子阶层”为题,对比了书面拉丁语和通俗拉丁语,认为书面拉丁语“不能与口头的、民族的和历史的活的语言相比较,虽然它既不能被误认为一种标语或者一种类似于艺术语言的世界语”[5](P168)。在《笔记本23》中,葛兰西在谈论皮兰德娄的戏剧时指出:“文学语言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一种‘世界语’,局限于部分的注意与感觉。”[5](P268)虽然葛兰西在这些地方谈论的都是文学艺术问题,但是他的主要意图并不在此,而是通过世界语的渠道表达这样的理念:语言的创造和传播过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隐喻。在葛兰西看来,由意大利政府主导的语言统一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同化和奴役底层群众的政治运动。由于统治阶级选定的语言只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相适应,而与被统治阶级毫不相干,所以,在接受这种语言的过程中,统治阶级的生活丝毫不受影响,而被统治阶级往往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通过强迫被统治阶级接受语言,统治阶级既实现了语言统一,也达到了控制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目的。与之相类似,意大利社会党主张的世界语方案也是与底层群众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由于它完全抽掉了语言的群众根基,注定不能成为全民族的通用语。
总之,葛兰西对语法和世界语的讨论并不是单纯的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考量。他用内在语法和规范语法的概念赋予语言以政治的意蕴,用世界语的概念描述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领导权,这就是利用语言把统治阶级的文化和世界观强加给被统治阶级,迫使他们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保持一致。
四、转向语言的哲学:索绪尔、维特根斯坦与葛兰西
通过对语言、语法和世界语等问题的研究,葛兰西在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也为自己搭起了与两位语言大师——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对话的一个平台。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相似性,同时也是有巨大差异性的。从相似性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在当代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而从差异性中,我们则可以读出葛兰西哲学创造的鲜明特点。
葛兰西与索绪尔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葛兰西的大学时代。那时,葛兰西就在巴托利教授的语言学课堂上接触到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虽然葛兰西在其作品中也使用语言(lingua)和言语(linguaggio)两个词,但它们并不是索绪尔的langue和parole。他们两人在理论上的真正交集在于对语言的分析思路。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的意义是在共时结构中产生的。因此,索绪尔非常重视在语言的共时结构中探寻意义的产生过程。与之相仿,葛兰西也把语言研究的重点放在人如何通过语言理解并传递不同的信息和意义。例如,不管是内在语法还是规范语法,都必须在语言的共时结构中获得认识。如果不涉及语言的共时结构,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语言的意义。然而,葛兰西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将语法引入日常生活,引进竞争机制。例如,规范语法就用监测、教学、审查和梳理等手段塑造了人们必须遵从的社会法则,而真正的规范语法的形成应该是所有内在语法竞争的结果。由于存在相互竞争,这种规范语法形成的过程将更能体现民主与公平。此外,他还强调应该研究语言历史的遗忘现象,即人们通常会遗忘语言的历史。由于这种遗忘往往发生在那些备受压迫的被统治阶级身上,所以,研究这一现象就必须突破语言学的界限而进入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这一点,索绪尔没能更进一步追问,而葛兰西则敏锐地觉察了。他不仅对此进行了说明,还使之融入自己的实践哲学中,指出了用语言重塑人们思考和表达方式并获得领导权的道路。
如果说葛兰西与索绪尔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对语言问题的学习形成的,那么葛兰西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联系则是通过葛兰西的好友,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斯拉法形成的。在葛兰西入狱期间,斯拉法为葛兰西在书店设立专用账户,慷慨无私地向他提供研究所需的书刊,同时,也将他的思想分享给维特根斯坦这位在剑桥的同事。于是,在葛兰西提出人人都是哲学家,人人都有包含语言、常识和宗教在内的自发哲学的时候,维特根斯坦也提出了言谈、规则与语言游戏。[9](P1240-1255)从表面上看,维特根斯坦与葛兰西对语言转向的把握确有相似性,但就哲学传统而言,他们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别。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转向,继承的是分析哲学的传统,强调的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葛兰西则是文化哲学的传统,是把语言看作具有基础性、总体性的文化形式,注重开掘语言的文化和社会历史功能。在葛兰西看来,语言就是哲学的世界观,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个人语言表达着独特的思考和感觉方式,同时,语言又具有历史性、集体性和民族性,表现了一定民族的文化传统。因此,如葛兰西所说:“语言问题,也就是集体地达成一种单个的文化‘气候’问题。”[10](P262)显然,葛兰西对语言的这种理解并不是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路向,而只能是属于文化哲学的。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葛兰西通过对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意大利民族哲学的崭新领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之路,这就是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
[1]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葛兰西.狱中书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Antonio Gramsci.Prison Notebooks Volume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
[5]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6]Dante Germino.Antonio Gramsci:Architect of a New Politics.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
[7]Peter Ives.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London:Pluto Press.2004.
[8]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Amartya Sen.Sraffa,Wittgenstein, and Gramsci.Journal of Economic.Vol.XLI.2003.
[10]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