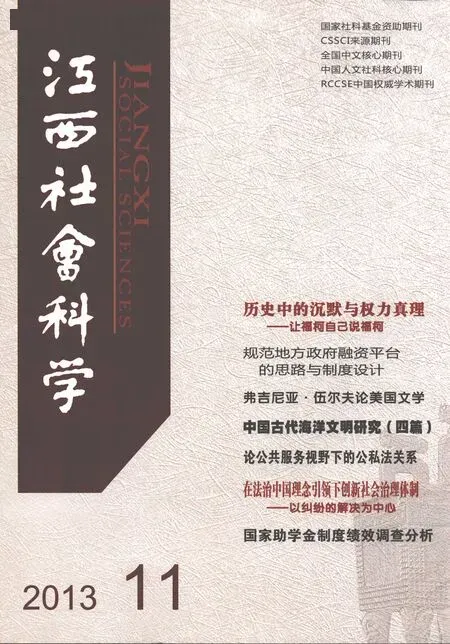历史中的沉默与权力真理
——让福柯自己说福柯
张一兵
历史中的沉默与权力真理
——让福柯自己说福柯
张一兵
福柯的新历史研究方法被他指认为考古学,其新颖之处在于,这种研究反对理性主义的目的论和总体性的连续历史描述,而转向断裂性地关注边缘和黑暗处的异类生存。同时,福柯试图在微观层面捕捉权力在日常生存细节中的关系布展,在他看来,通常被人们非反思拥戴的认知真理恰恰是这种新型权力统治的隐性支撑点。真理、权力和个人品行,作为主体的构形,是福柯一生思考的主题。
福柯;沉默历史;考古学;权力;真理;主体
张一兵,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3)
过去,我们写一篇关于文本解读的导论,除去生平介绍之外,通常要绞尽脑汁编出一个对解读对象上手的总体性座架装置系统,比如基本思想起源和基本学术倾向,比如基本概念群,比如认知构架、方法论和整体连续性的逻辑线索。可是,面对福柯,一个不断将手榴弹扔向自己的家伙,你有再大本事恐怕也无法提供一个同一性的学术透镜。于是,我不再总体地、连续地、有逻辑目的地概说福柯,干脆,让福柯自己介绍自己的一些文本构境思路和支援背景。关于这一点,我在《回到海德格尔》一书中已有初步的尝试。①好在,福柯在其一生中有过大量公开的对话和访谈式的言论,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涉及我们过去的主要文本解读中没有直接遭遇到的支援背景和专题讨论过的东西。看起来,它们似乎是在我们的主要文本解读之外,却是文本思想构境中所无法直接看见的复杂支撑点。
一、历史中的沉默:疯子与病人
福柯在《古典时期疯狂史》一书中首次提出要研究历史中的沉默。他也将这种思考命名为“沉默的考古学”。对此,罗兰·巴特的解释是:“疯狂的沉默:因为疯狂根本不拥有用于言说理性的元语言。 ”[1](P62)当然,福柯是从疯狂在历史中的缺失和不在场开始这种思考的。他发现,关于疯狂的历史记载总是 “少于历史中生成的东西”。
正是这 “少”(<moins>)要受到询问,并且首先要消除它所含的任何贬义。从最初的述说起,历史时间就是把沉默(silence)加在某些东西上面,随后它们就只能在空洞、无意义、子虚乌有的门类下被理解。历史只是在一种历史缺席 (absence d'histoire) 的基础上, 在巨大的喃喃低语(murmures)的空间中才可能,沉默把这种不在场当作使命和真理来守候。[2](P5)
为何缺失?因为历史从来都是围绕光亮的王权的辉煌史,大部分平常生活的真实细节都被当作低于值得记载的废物和空无所删除和抛弃了。在福柯看来,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有其“不可避免的空无”,故而,“历史的每一次诉说都伴随着不在场的发生”。[2](P5)现在,福柯说,我们只有质疑这种历史中的高低标准,排除对“低”的贬义,找到历史中不入法眼的 “巨大的喃喃低语”,才有可能真正发现被排除的历史黑暗中的缺失和沉默。
二、面向庶民:黑暗传奇中“声名狼藉的生活”
在福柯看来,如果过去的历史学研究的本质其实是面向帝王将相的 “辉煌史”,而历史真实的一面常常被遗忘在黑暗的沉默之中,那么他就要主张,历史研究应该关注那些在宏大连续性历史研究中陷入沉默的平凡人的命运,关注那些被历史宣判为“不正常”的声名狼藉者的生活,让他们从光亮理性逻辑背后走到历史前台来。福柯的这种观点,与朗西埃的“无产阶级之夜”的原始档案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的妻子正好是福柯的助手。并且,通过这种黑暗谱系学对平民生活的关注,也才可能发现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布展。
1977年,福柯亲自编辑了一个文集,收集了1670—1770年一个世纪中拘留所和警察局的一些档案,名曰“声名狼藉者的生活”。这是一个面对沉默的新式考古和谱系研究的十分鲜活的例证。
首先,福柯说,这是一本“关于生存的文选(anthologie d'existences)”[3](P101)。 这个生存,相对于被历史学家用一种入史标准栅格化后的所谓光亮的历史事实,自然是黑暗中的沉默。因为福柯在这个文集中所选入的文本,通常都不是伟大功绩和宏大故事,而只是不为人知的平凡人的各种生活片断,并且这些人都通常被视作“不正常的人”打入疯人院和收容所,如疯子、鸡奸者(用文明一些的语言叫男同性恋者,这实际上也是福柯自己的性生存)、酒鬼和妓女。有的时候,福柯也将其称为庶民(plèbè)。为此,福柯提出了一个编辑原则,依我的看法,这也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涉及的人必须真实存在 (existé réellement)过”,这是因为从医院和监狱中获取的档案往往不会经过御用文人和历史学家的编造;“他们的存在既默默无闻又命运多舛”,“一生与苦难、卑贱、猜忌与喧哗为伴”,这些人的存在显然不会是辉煌和奇迹般的,因为他们没有财富、地位和英雄品质,他们属于那些“注定要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芸芸众生”;与宏大的大写的历史不同,记载他们 “小写的生存史 (l'histoire minuscule de ces existences,)”的故事越短越好,他们的存在只是一个个片断。[3](P103-104)恰恰是这些片断,才是历史存在的真实层面。
当然,对于这些声名狼藉者生存片断在历史记载中的现身,需要“有一束光(lumière),至少曾有片刻照亮过他们”,这就是权力之光。
这些生命本来能够、而且应当处于无名的黑暗之中,然而,与权力的一次偶然相遇(rencontre),却把他们从黑暗之中拖拽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冲突,绝不可能留下只言片语来记录他们转瞬即逝的一生。权力监视(guetté)着这些生命,追踪着他们,密切注视着他们的抗议和不法行为,片刻也不放过。[4](P103-104)
这个与权力的偶然相遇,只是因为他们犯事儿了,当他们被抓起来时,历史长河中藉藉无名的他们才会被从权力的利爪下突显在聚光灯下。福柯说,这正是谱系学要捕捉的 “黑暗传奇(Légende noire)”[5](P106)。 在福柯看来,黑暗传奇的特点恰恰是反连续性的历史观的,因为往往“它被剥夺了传统,只是通过间断、擦抹、湮灭、重组和再现之后, 它才流传到我们这里”[5](P106)。 也由于,这种小写的历史本身是从不被记载的,“这些生命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只是在与权力发生冲撞后才得以幸存,而权力原本想要毁灭他们,或者至少抹去他们存在的痕迹”。黑暗传奇的主角通常都是被这个社会体制否定和专政的对象,可是恰恰因为这种打击和“消灭”才让他们得以在历史上被记载。
其次,福柯通过这种对不入史的“声名狼藉者”生活的谱系研究,细心地观察到自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社会治理体制和微观权力系统的生成。在福柯看来,相比于基督教神学对日常事务的关注,资产阶级对日常生活(quotidien)的浸透更加微观化,因为日常生活被第一次完全纳入话语(认知)与权力体系之中,“调查充斥着无关紧要的违法行为和骚乱的微小领域”,“权力、话语和日常生活之间,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被建立起来,形成一种全然不同的控制和阐述日常生活的方式”[3](P109)。由此,“整个政治链(chaîne politique)与日常生活的结构交织(entrecroiser)在一起”,话语将“个人的不端行为、耻辱和秘密都送交到权力的股掌之中”③[3](P111)。
三、权力研究的异质性眼光
福柯认为,权力问题是他始终关心的内容,但是在早期的《疯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两本书中,他还没有直接使用权力概念。外部的原因在于,当时人们还只是在政治—法律话语场中来描述宏观权力,比如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认的“国家机器(d'appareils de l'état)”和“阶级统治”,只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基层的日常斗争,真正发现生活细节中的微观权力。福柯说,在过去的宏观权力观中,“人们把权力等同于一种说‘不’的法律,认为权力尤其具有剥夺权”[4](P436)。在福柯看来,这恰恰是消极的权力观。今天资产阶级的“权力得以稳固,为人们所接受,其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它不只是作为说‘不’的强权施加压力,它贯穿和产生物,引发乐趣,形构认知,生产话语(produit du discours)。应该视权力为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生产性网络(réseau productif),而不是将它看作一个仅仅行使压制职能 (fonction de réprimer)的否定性机构”[4](P436)。这就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权力的另类发现。
首先,福柯看到了从17—18世纪起,“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种开始通过生产和劳役来行使的权力。这主要是让人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提供生产性服务。为此必须实现一种真正的权力归并,即权力必须达到人的身体、举动、态度和日常行为”[4](P440-441)。这是说,资产阶级的权力是从劳动生产内部发生的,由此达到人们的全部日常生存。其次,福柯指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大工厂内,“发展一整套对人类进行驯服的技巧,把他们禁锢在特定的地方,进行监禁、奴役、永远止息的监督”[5](P30)。 这也就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管理”。
在福柯1976年写下的《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的第一卷“认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中,第4章 “性的部署 (Le dispositif de sexualité)”第2节的标题为“方法”,其中,福柯集中说明了自己对资产阶级权力的独特看法。
福柯先说了三个 “不想”:他不想把权力说成是一种由国家机构和装置 (appareils)组合起来的一种可见的 “特定的权力”,不想将权力理解成 “一种奴役的方式 (mode d'assujettissement)”,不想将权力看成“一套普遍的统治系统(système général de domination)”④[6](P60)。显然,这都是对应于传统社会中那种与国家强制和外部专制压迫的权力,而福柯眼中的资产阶级权力则完全不是这样:
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 (des rapports deforce),它们内在于自己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自身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加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塑形成链条或系统 (former chaîne ou système),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⑤[6](P60)
资产阶级的权力不再是可见的、能够直接占有的东西,它通过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布展为一种不可直观的力量关系,它不像皮鞭那样实在,却比外在的强制和控制更有力量。因为在不同的力量角逐关系中,恰恰是资产阶级权力部署的方式,这是一种从根本上塑形存在的链条和网络。所以,依福柯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新型权力不再是集中于某种高的权力“中心点(point central)”,而是要在各种力量关系建构起来的社会场(champ social)中发现它们的踪迹。因为,“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旋转柱石永不停息地通过它们不平等的关系引出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资产阶级布展的关系性的权力无所不在(Omnipré sence du pouvoir)。[6](P60)这是由于,权力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产生出来。资产阶级的“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给予的一个复杂的策略性情境(situation stratégique complexe)的名称”[6](P61)。
基于此,福柯还具体指认了资产阶级这种新型权力关系的特征:其一,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或分享的某种物(quelque chose)。它会是从无数不平等和变动中的互动关系中发生。其二,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 [经济过程、知识关系 (rapports de connaissance)和性关系],相反,它们内在于其他关系之中。也只有在这些有关系的发生中,权力才能部署自己。其三,权力不是来自上层,而是发自下层(bas)。这是说资产阶级的权力不再是君王那种可见的高高在上的王权,而是发生和作用于生活细微层面的支配。其四,权力关系既是有意向的,又是非主观的(non subjectives)。资产阶级的权力发生恰恰是自然性的,自发中的意图实现是最高明的统治。其五,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résistance)。这一点尤其重要,权力恰恰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points de résistance)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这些抵抗点在权力网络 (réseau de pouvoir)中到处都有”[6](P61-62)。
在1982年的一次讲座中,晚期福柯又进一步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权力解读为四种控制和支配的技术。“(1)生产技术:使我们能够生产、转换或操控物;(2)符号系统技术:使我们能够运用符号、意义、象征物,或者意指活动;(3)权力技术:它决定个体的行为,并使他们屈从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或支配权,也就是使主体对象化;(4)自我技术: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完美不朽的状态。”[7](P241)
在福柯看来,这四种权力技术都与某种支配类型相关联,它们很难独自发生作用。他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人们可以发现操控物的与支配权之间的关系”,即第一种技术与统治的关系,而他自己则更关注后面两种权力技术,即“支配的技术和自我技术”,甚至,在福柯眼中的历史,“就是关于支配权及自我的认知所编成的历史”[7](P241)。这其实是福柯晚期思想的思考焦点。
四、真理是个坏东西
与传统那种标识正确认识的真理观不同,福柯将真理视为权力的帮凶,既然认知就是权力,那真理则会是权力支配中的核心骨架。这又是耸人听闻的断言,从中我们不难听出尼采言说的回声。为什么?福柯说,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真理制度,都有其作为真理起作用的各种话语的一般政策(politique générale);都有其“用于区分真假话语的机制和裁决机构(lesmécanismes et les instances),用于确认真假言说(énoncés vrais ou faux)的方式;用于获得真理的技术和程序”[4](P445-446)。真理即合法存在的依据,谬误则下地狱。故而,真理本身就是切割存在与不存在的权力(la vérité est elle-même pouvoir)!用德勒兹略显夸张的话语来讲,就是“绝没有一种真理模型不指向某种形式的权力,也绝没有一种知识科学在行动上不展现为或含括某种操作中的权力”[8](P40)。在1980年福柯自己为《哲学辞典》撰写的“福柯”辞条⑥中,他甚至认为“真理游戏”(jeux de vérité)直接进入了存在本身。[9](P1451)这其中深嵌着晚期海德格尔的本有论思考。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关于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五个从历史上看极为重要的特征: 真理以科学话语 (discours scientifique)的形式和生产该话语的制度为中心;它受到经济和政治的不断激励(经济生产和政治权力对真理的需求);它以各种形式成为广泛传播和消费 (diffusion et consommation)的对象(它流通于社会肌体中相对广泛的教育或新闻机构);它是某些巨大的政治或经济装置(大学、军队、新闻媒体)的非排他的、但居主导地位的监督之下生产和运输的;最后,它是整个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意识形态斗争)的赌注。[4](P446)
这根本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真理。福柯眼中的真理,是指一整套隐性支撑社会统治的有关言说(énoncés)的生产、规律、分布、流通和作用的有规则的程序。真理以到处受到遵从的流通方式与一些支持它的权力制度相联系,并与由它引发并使它继续流通的权力效能相联系。这就是真理制度。该真理制度不只具有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 (idéol ogique ou superstructurel)的性质;它甚至是整个“资本主义塑形和发展的一个条件”(une condition de form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4](P447)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说他自己关于疯狂和性的研究,都“不是要写一部有关禁止的社会历史,而是要写一部有关‘真理’的生产的政治历史”。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迈向真理’。我指的是,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以此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并获得特定的权力。获取‘真实的话语’(可是这些话语又在不停地变化)是西方的核心问题之一。有关真实的历史,这还是一块处女地”。 [5](P36-37)
也是在这个语境中,福柯才根本否定传统理解中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研究。因为,意识形态总是被当作真理 (真实)的反面——“妨碍真实的话语生成的东西”——虚假关系建构的存在幻象在场的,意识形态似乎是谎言的运行机制。福柯说,这恰恰是假象。资产阶级合法统治的真正秘密就在于“真理的生产”和“权力的效应”[5](P43)。如果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正是真理话语。
五、认知话语对象化的实践
1969年,福柯候选法兰西院士,职位是思想系统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这真是一个反讽,因为福柯在学理上正是要否定系统的思想研究方式,可是他在现实中却又不得不获取这个“坏的”学术权力话语。也为此,他不得不提供了一个以法兰西学院允许的话语体系中的候选陈述。我不敢确定,其中是否存在一定的表演性。⑦其中,他有些收敛地谈及自己过去和未来的研究。
福柯说,在自己最早的 《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中,他主要是想弄清楚“疯子在一套怎样的机构和实践体系中受到约束和界定”。结论有二:一是这种约束和界定首先与“一整套精确明晰的认知”相关。二是它具体实现为“一种有条理的日常活动”[10](P78-79)。虽然福柯已经发现,疯子与正常人的区分恰恰取决于正常与不正常的认知标准,但实际上,包括不久之后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福柯都是从实践的视角切入认知如何具象地支配和控制社会生活的。进而,福柯专门指认说,在后来的《词与物》中,他却是在一个与具体实践相反的方面进一步思考认知(词)对更大尺度上存在(物)的支配问题,这就是所谓认识型的理论。他说:
不考虑整个实践和制度层面 (不过并没有放弃有朝一日重新讨论它的念头);而是考虑特定时期这些认知领域中的少数几个(17、18世纪的自然分类、普通语法以及财富分析)。依次考察它们,以便界定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和使用的概念的类型,以及界定它们所检测的理论的类型。[10](P79)
其中,1-(i/2K)为线性衰减系数,列表中位置越靠后的点对距离的贡献越小,Ia(i)返回列表Oa中位于第i位的数据点P,例如图1中Ia(0)返回点a。Rb(P)返回点P位于列表Ob中的位置,由于列表里只包含前K个最近邻居,点P有可能不存在于Ob中,故Rb(P)为:
显而易见,他没有直接指认认识型这样的概念,只是淡淡地说到认知的概念或理论类型。而对于《认知考古学》一书,福柯只是强调了认知是介于意见和科学之间的一个特殊层面,“这种认知不但体现在理论文本或者经验方法之中,也体现在一整套实践活动和制度之中”[10](P80)。在那里,认知对象化的话语实践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福柯已经在将认知话语更多地置入到社会现实的权力效应研究中。
在对自己在法兰西学院的下一步教学计划的勾描中,福柯说自己的思考点仍然会集中于有关认知的三组问题上:一是认知的位置和界限,以及描述它的方式;二是认知与科学话语之间的关系;三是认知序列的因果关系。这三组问题又与认知的三重表现相关联:“它对一系列实践活动和制度的描述、汇集和协调;它是各门科学建构过程中不断变换的焦点;它是复杂因果关系的构成成分,科学的历史就处于这种关系之中。”[10](P81)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第一年的授课“认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1970-1971)”的确是上述计划的实施,但是,他更关注的却是以认知对象化的话语实践为核心的现实历史分析。他提出,“话语实践并非生产话语的纯粹和简单的方式。它们体现在技术进程中、在机构内、在一般行为的诸多样式里,在传播与扩散的形式中。也在同时利用并维护话语实践的教育形式中体现”[10](P81)。也是在这一讲的最后,福柯开始提出要关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政治斗争。这也是不久之后的《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前奏。
六、权力与主体
1982年,晚年福柯写下《主体与权力》(Le sujet et le pouvoir)一文,试图总结自己20年的研究。这一回福柯说,自己的研究中心既不是权力现象,也不是权力现象发生的现实基础,而是要“生产出一种历史(produire une histoire)”,其中真正想分析的东西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人的存在被主体化的不同方式(des différents modes de subjectivation de l'être humain dans notre culture)”[11](P280)。这也就是说:“我研究的一般主题(le thème général),不是权力,而是主体。”[11](P281)在1980年福柯自己为《哲学辞典》撰写的“福柯”辞条中,他曾经这样谈到自己对主体问题的追问:“是什么规制了主体,或者说,在何种条件(condition)下主体才得以确立,他必然具有何种身份(statut),在真实(réel)或想象(l'imaginaire)中他必须占据什么位置(position),以生成(devenir)一种属于这种或者那种类型知识(connaissance)的合法的主体(sujet légitime)。”[9](P1450)相对于福柯历来的自述,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改变和游移,即从认知、权力到主体。我觉得,突显主体问题在谱系研究线索中的重要地位,是福柯晚年对自己过去的思想努力的一种重新定位。
在这里福柯说,首先,他关于主体问题的研究工作就是分析“将人的存在(êtres humains)变成主体的三种对象化方式(trois modes d'objectivation)”:
第一种是质询模式。它们试图将科学地位赋予自己。比如,在普遍语法、语文学(philologie)和语言学中,将说话的主体(sujet parlant)对象化;再或者,在第二种模式中,在财富和经济分析中,将生产主体(sujet productif)、劳动主体对象化;又或者,第三个例子,在自然史或者生物学中,将活着的存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事实 (seul fait d'être en vie)对象化。[11](P280)
很显然,这是福柯对自己在《词与物》一书中的认识型断裂和转换研究的一种新的解释。
其次,福柯说自己研究的第二部分是关于主体对象化中的 “区隔实践”(《pratiques divisantes》)。区隔,这是指主体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既自我界定、也与他人区隔开来的实践活动。福柯的例子是:“疯子与正常人、病人与健康者、罪犯和‘乖孩子’(《gentil garçon》)。”[11](P281)这分别对应他的三本书:《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区隔,也是布尔迪厄重点讨论过的社会学问题,但福柯这里显然思考的主要是政治区隔。
最后,是福柯当下的工作,即关注人使自己变成一个主体的方式。他选择的例子是性(sexualité)。这也是他最后的著作:四卷本的《性史》。
虽然福柯明确说自己研究的真正对象是主体,但也因为追寻主体的生成和对象化,他才深深地卷入到权力问题中。权力只是主体被建构的一个必然的机制。福柯说:“我很快就发现,人这一主体在被置入生产联系和意义联系(relations de sens)的同时,他也会同样地置入非常复杂的权力联系 (relations de pouvoir)。”[11](P281)他说,马克思研究了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形式主义和语言学结构主义涉及了主体意义构境的发生,而他则真正关注了权力关系对主体更基始的日常生活存在中的建构。福柯分析道:
权力形式一旦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运转,就会对个体进行归类。在他身上标示出个体性,添加身份(identité),施加一套真理法则 (loi de vérité),这样,他本人和他者(autres)都能借此认出自己。正是权力方式,使个体成为主体。“主体”一词在此有比重意义:凭借控制和依赖 (le contrôle et la dépendance)而屈从他者(autre);通过意识或自我认知(la conscience ou la connaissance de soi)而束缚于他自身的认同(identité)。两个意义都表明了权力方式的征服和奴役(subjugue et assujettit)。[11](P284)
我觉得,这很像拉康的象征域中大他者支配下的伪主体建构论。权力在日常生活中建构主体,是通过认知话语和真理体制 (拉康那里叫象征符号系统),由此,主体界划和建构起理性的自己与反指性的他者。通过这种双重认同,主体屈从于他性权力,这是一种自我奴役的自拘性。
当然,福柯也告诉我们,在历史上人类主体对强加于他们的权力压迫有过顽强的反抗和斗争。这些斗争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反对统治的形式(formes de domination,伦理、社会和宗教的统治);反对将个体和他们的产品分割开来的剥削形式(formes d'exploitation);反对个体自我束缚并因此屈从于他人的行为(这是反对臣属、反对屈从和主体性形式的斗争)。 ”[11](P284)在福柯看来,反对剥削的斗争在19世纪占了上风,而在20世纪,他所揭示的反对屈从和重新争取主体性的斗争则越来越重要。
七、晚年小结
1984年,晚年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对自己的全部思想历程提出了一种概括。福柯说,在他完成的全部学术文本中,其实是想“提出三大类问题,即真理(vérité)、权力(pouvoir)和个人品行(conduiteindividuelle)。这三个经验领域只有彼此关联才能理解,若相互割断便不能理解”[12](P515)。这最后一个所谓个人品行,即上述主体的构形问题,是福柯晚年着重思考的方面。
在另一个地方,晚年福柯说,这三类问题都是通过谱系研究得以解决的,这也就使谱系研究形成三个领域:“第一,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与真理问题相关,通过它,我们将自己建构成认知主体;第二,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与权力相关,通过它,我们将自己建构为作用于他们的行动主体;第三,我们自身的存在论与伦理相关,通过它,我们将自己建构为道德代理人。”[13](P305)在最后一个方面,关于个人品行的研究也被指认为伦理主题。福柯说,这同时也是三个思考轴心。这三个轴心同时出现在《疯狂史》中,而《临床医学的诞生》和 《词与物》探讨了真理轴心,《规训与惩罚》则研究了权力轴心,《性史》关注的是伦理轴心。[13](P305-306)这三者,说到底都是主体的构形问题。这是福柯晚年对自己思想历程的最后说明和定位。
八、福柯如何看待人们读他的书
在 《古典时期疯狂史》一书的第二版序言(1972)中,福柯这样谈到一本书的命运:
一本书产生了(produit),这是个微小的事件(événement minuscule),一个任人随意把玩的小玩意儿(petit objet)。从那时起,它便进入反复的无尽游戏(jeu)之中;围绕它的四周,在远离它的地方,它的化身们(doubles)开始群集挤动;每次阅读,都为它暂时提供一个既不可捉摸,却又独一无二的躯壳(corps);它本身的一些片段,被人们抽出来强调、炫示,到处流传着,这些片段甚至会被认为可以几近概括其全体。到了后来,有时它还会在这些片段中,找到栖身之处;阐释 (commentaires)将它一拆为二(dédoublent),它终究在这些异质的论述中显现自身,招认它曾经拒绝说明之事,摆脱它曾经高声伪装的存在。一本书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再版,也是这些化身的一员:既不全为假象,亦非完全等同。[14](序言P1-2)
之所以如此大段引述福柯的文本,因为它太重要。这几乎可以算是他关于文本学的基本看法。显然,福柯并不指望人们能够还原式地诠释他的文本,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解释学的所谓逼真性的努力。他所发明的考古学正好是反对解释学的。
一本书自它从作者手中交到出版社,即成为一个历史性文本对象。问世后的文本永远是一个孤苦的从来没有人触到的自在之物。在它的四周,远远地会有不断出现的解释学“化身(double)”⑨。这是康德的一种变形式在场,文本与解释物的关系永远会是自在之物与直接的现象世界间不可打破的分立。在福柯看来,所有诠释物都只是文本的一种暂时的话语肉身,每一种解释和理解都会是一种异在的重新构境,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翻译之境就更是如此。在福柯这里,文本的写作是一个活生生的构境事件,成书的文本不可能是死去的现成的物,好像我们可以从这个不变物中取到同样现成的原初意义和作者意图,相反,它是一种动态的“事件—对象(objet-événement)”,当它在世之后,甚至连“生产它的人,永远不能提出主权要求”,它的命运必然是“被人重抄、断碎、反复、模拟、分裂,终致消失”[14](序言P2)。这简直就是咒语。
注释:
①参见拙著:《回到海德格尔——走向存在之途(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②中译文有改动。参见 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Paris,Gallimard,1994.p.199.
③中译文有改动。参见 Michel Foucault,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La volontéde savoir,Paris, Gallimard, 1976.p.121.
④中译文有改动。参见 Michel Foucault,Histoire dela sexualité,La volonté de savoir,Paris, Gallimard, 1976.p.121.
⑤中译文有改动。参见 Michel Foucault,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La volonté de savoir,Paris, Gallimard, 1976.p.122.
⑥1980年初,于斯芒(Denis Huisman)向福柯的助手埃瓦尔德(F.Ewald)提出建议,修改他将为法国大学出版社准备的《哲学词典》中的关于福柯的辞条。埃瓦尔德转告了福柯,当时,福柯已经草拟了《性史》第二卷的第一稿,他为了这本书专门写的一节回顾了他过去的研究工作。这也就成了福柯交给于斯芒“福柯”辞条的文本,他只是加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和参考书目。有趣的是,福柯签上了以 M.F.为简称的“Maurice Florence”的化名,并且就这样出版了。《哲学辞典》中没有写明这个辞条是由福柯撰写的。参见“Foucault”,in Huisman(D.),éd., 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es,Paris,P.U.F.,1984,t.I, pp.942-944.并参见 Michel Foucault,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76-1988,Paris, Gallimard,1994.p.1450-1455.
⑦关于表演性的存在特征,可参见拙著:《回到海德格尔》(第1卷)导言部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⑧ See“The Subject and Power”(“Le sujet et le pouvoir”;trad.F.Durand-Bogaert),in Dreyfus(H.)et Rabinow(P.),Michel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nt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pp.208-226.
⑨这个double在法文中,通常指两倍、双份,也有复本和复制品的意思。林志明先生将其意译为"化身"是精妙的。——本书作者注。
[1](法)罗兰·巴特.偏袒[A].吴琼,译.福柯的面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2](法)福柯.福柯集[M].王简,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3](法)福柯.声名狼藉者的生活[A].唐薇,译.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法)福柯.福柯访谈录[A].蒋梓骅,译.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5](法)福柯.权力的阐释[A].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法)福柯.性经验史(增订版)[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7](法)福柯.自我技术[A].吴燕,译.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法)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M].杨凯麟,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9]Michel Foucault,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76-1988,Paris,Gallimard,1994.
[10](法)福柯.法兰西学院候选陈述[A].刘耀辉,译.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法)福柯.主体与权力[A].汪民安,译.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2](法)福柯.道德的复归[A].蒲北溟,译.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13](法)福柯.论伦理学的谱系学:研究进展一览[A].上官燕,译.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4](法)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林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责任编辑:龚剑飞】
B565.59
A
1004-518X(2013)11-0005-09
国家“十一五”社科规划重大招标项目“当前意识形态动态及对策研究”(08&ZD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