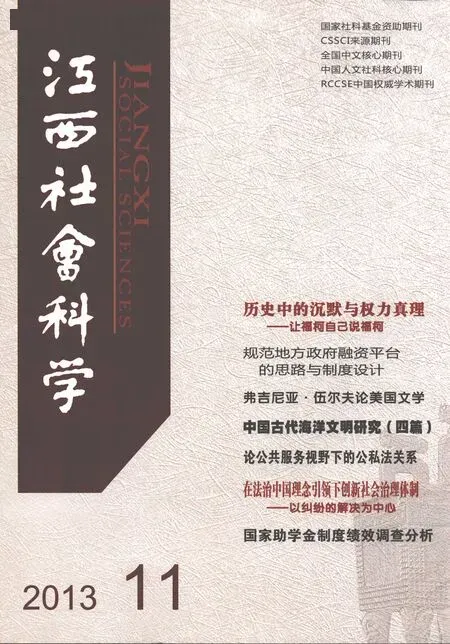从民族和民族性到文化认同
——欧洲民族学核心概念的转变
(德)白瑞斯文 吴基诚 马倩霞译 王霄冰校
从民族和民族性到文化认同
——欧洲民族学核心概念的转变
(德)白瑞斯文 吴基诚 马倩霞译 王霄冰校
民族和民族性是欧洲民族学史上的两大核心概念。民族(ethno)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后来被用来指代作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人类群体。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了“族群”的定义,并在想象的群体和真实的群体之间加以区分。从俄国学者史禄国开始,民族学对于“族群”有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等多种定义法,以至于“民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性”概念不断遭到质疑。今天的人们更倾向于使用“认同”这一新的主导概念,长期以来处于中心地位的民族和民族性概念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民族;民族性;文化认同;欧洲人类学;民族学
白瑞斯,德国波恩大学民族学和古美洲学教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吴基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马倩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广东广州 510420)
王霄冰,女,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广东广州 510275)
欧洲民族学在不同阶段往往会对一些特定的主题和理论给予特别的兴趣。19世纪人类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为进化论,20世纪上半叶则为功能主义,从20世纪中期开始,民族理论与民族性又成为核心主题。本文将介绍这两个概念的流变与危机,从中探析当代欧洲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动向。
一、概念
欧洲各国语言中对“民族”(ethnos)与“民族性”(ethnicity)两个专业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达,但它们都派生于同一个源于古希腊语的基本词。它写作 εθνο□,意为“陌生的、非希腊的人类群体”。这个词基本毫无改变地被从希腊语引入到了所有欧洲的科学语言中,成为民族学学科方方面面的有机组成部分(见表1)。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它已经被用来指代人类文化的基础科学“民族学”,而不像美国和英国那样用“人类学”来为此学科命名。

表1 一些欧洲语言中以”民族”为词根的术语
在各种语言中时常会有更加古老和口语化的表达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的方式,比如德语中的Stamm(部族)、Volk(人民)或Nation(民族),英语中的 nation(民族)。要注意的是,这个词引申出来的含义并非在所有语言中完全相同。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苏联以及1945年后在其政治及军事统治下的东欧国家,ethnography(民族志)的使用比之前的ethnology(民族学)更加普遍。 这些地区的主流专业期刊如 《苏联民族志》(sowjetskaja etnografija) 和东德的 《民族志考古期刊》(Ethnographisch-archaeologische Zeitschrift), 跟西欧地区,如西德的《民族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和瑞士 《苏黎世民族学期刊》 (Ethnologische Zeitschrift Zürich)在用词上有所不同。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欧洲民族学的术语系统和各种概念还是较为统一的。
二、民族和民族性理论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人们都没有仔细地去思考过,作为民族学研究对象的民族到底指的是什么。最初长期在中国工作的俄罗斯民族学家史禄国 (Sergej Shirokogoroff,1887—1939)自1912年起提出了一个民族理论,并于1935年编撰成书出版,但其中所用的主要案例在他1929年关于通古斯人的研究中就已展示。因为他的这两本书,欧洲开始将注意力投向这一主题。其实在史禄国之前,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已概括了“族群”的概念,但由于它藏身在一本社会学著作中,所以未被人们发觉:
对部落亲族关系的信仰,不管它是自然形成还是有何客观基础,都有可能对一个共同体——特别是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带来重要后果。要么由于体貌或习俗近似,或者由于两者兼有,要么由于殖民和迁徙的记忆,从而对共同血统抱有主观信仰,这种信仰对于群体化的宣扬十分重要,但这样的群体又非“宗族”(Sippe)。我们应当称之为“族群”,至于是否存在着客观的血缘关系则无关宏旨。族群不同于被准确认定了身份的宗族,不像后者那样是个有着实际共同行为的群体。我们这里所说的族群自身并不构成一个群体,而只是为群体的形成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另一方面,它主要是一种激发对共同的种族渊源之信仰的政治共同体,不管它是如何被人为组织起来的。这种信仰即使在政治共同体瓦解之后仍会继续存在,除非它的成员在习俗、体貌,尤其是语言上的重大变异成为障碍。①
韦伯将作为形而上的想象存在的群体和有实际共同行为的群体区别开来,这一观点并未被其后的学者(包括史禄国)所接纳。史禄国把民族作为一个本质概念来定义,他的这一倾向比韦伯更为强烈。他认为此概念中描述的因素是人类社会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但他并不接受韦伯关于想象群体和真实群体的区别。与史禄国一样,当今人类学的专业词典仍将民族定义为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能相互理解的、文化上具有同质性、族内通婚、并以此作为行为规范的人类群体,比如瓦尔特·赫须贝格(Walter Hirschberg)自1988年初版后不断再版的《民族学词典》(Woerterbuch der Völkerkunde)。
这种宣称能为所有人准确解释什么是民族的本质主义定义,直到20世纪末才被普遍接受。这种定义操作性很强,在使用过程中能使判断变得容易。一种非常有效的操作方法是通过头饰、发型、头巾和服饰来判断[1],这种方法已经在前科学时期的描写中初见端倪[2]。这一传统定义因为看起来好用而从未被质疑,人们只对此作了小小的修正和补充,如格奥尔格·埃尔维特(Georg Elwert,1947—2005)在以下描述中,更致力于将民族的概念与其他邻近概念确切区分:
(民族是)一个涵盖和跨越诸多家族的、并有集体自我认同感的群体。使它与别的概念区分开来的归类准则具有可变性。但相对于其他归类准则而言,它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民(Volk)这一概念和它相比含糊而带有政治色彩,而与国家(Nation)相比,民族所包含的意义更为广泛,因其不受制于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机器和唯一国籍的因素。[3](P440-464)
显然,现在人们谈论的是集体内部成员给予自己的文化认同,并试图把民族更为准确地放置到社会团体的概念梯级中,这些概念从小到大:起源于家庭,衍变到宗族/氏族,经由部族,最后成为国家,而民族就被置在国家之前的位置。韦伯也曾如此认为,他极其重视民族和国家之间相邻阶段的连接。虽然其后韦伯和史禄国的某些基本观点遭到上述埃尔维特[3]和君特·施雷(Guenter Schlee)[4]等人质疑,特别是在共同语言和共同出身对于民族的必要性上,但这套标准并未被完全否定,就像较后出现的 “民族性”这一构词所显示出的极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的存在有两个原因:由认识论出发的对“本质主义”概念的拒绝,以及因为后殖民和高流动性而形成的当代现实情况,让这个概念需要根据实践做出调整。直到1950年前后,有利于殖民管理机构的严格的人群定义和人群区分仍十分盛行,而今天的学者们则更多地关心当事人尤其是跨国族群 (如德国的土耳其人,美国的墨西哥人)的社会现实和自我描述。如今自我定位已成为最重要的评判准则,不过他者定位也一如既往地重要。
史禄国的《民族理论》(Theory of the Ethnos)包含的内容并不仅仅是静态的“民族单位”的描述。同当代学者们一样,他将民族的表现形式放置于巨大的关系网和时间的发展中去看待。为此他创造了许多辅助概念,其中最重要的为“多民族杂居环境”(interethnic milieu)、“民族级差”(ethnic grade)、“民族平等”(ethnic equilibrium)、“民族压迫”(ethnic pressure)。史禄国理论的优势在于他能够使用刚刚提到的概念来描述民族的生存动态。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他根本不知道的韦伯的定义。史禄国民族理论中的这一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理查德·图恩瓦尔德(Richard Thurnwald,1869—1954)为西欧人“发现”了这一理论,但并未在其著作中发表,而他的学生威廉·埃米尔·穆尔曼(Wilhelm Emil Muehlmann,1904—1988)第一次将此民族学理论在西欧发表并使之流行起来,特别是他1956年的一篇文章以及1964年的著作《种族,民族,文化》(Rassen,Ethnien,Kulturen),当然还有这里未能详列的出版物。不久之后,挪威的弗里德里克·巴尔特(Fredrik Barth)1969年在一本论文集中延续了其观点[5],而他的贡献在国际上得到了比穆尔曼更多的关注。这两位虽在本质上没有超越史禄国太多,但他们把史禄国试图添加的能与其理论联系起来的不必要枝节和难以信服的关联部分去除掉了。就连当时东欧阵营(东德、波兰、苏联等国家)非常流行的用民族学理论来解释由一些强势的民族单位形成国家的研究,也要归功于史禄国和穆尔曼的推动作用。[6](P272-287)
与民族性有关的一组概念在欧洲日益变得重要的事实,除了刚刚提到的用“民族学”来命名人类学的核心专业之外,也反映在以下三个例子中:首先是后人从史禄国的《通古斯人的精神心理情节》(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1929)出发,试图将其中提及的民族学主题深化和扩展。由此,穆尔曼(1964)创造了北亚东部的一个长时段的多民族共存体系。他相信可以重现出以下的民族梯级关系:文化上最为先进的汉族中国人对集中在北部边界上的满族形成压力,而满族则把这一压力转嫁给通古斯诸族,进而转嫁给尤卡吉尔人(Jukagiren)。尤卡吉尔人不能承受其文化压力,只能放弃自身的族群特征。图恩瓦尔德的学生沃尔夫冈·鲁道夫(Wolfgang Rudolph)在雅库特族的案例上采用了不同的观点。此外,即使跟最初的作者韦伯、史禄国、图恩瓦尔德和穆尔曼已无关,而案例多数来自非洲和美洲[4],且不再如穆尔曼那样仅单线论述,对该学说模型的讨论也仍在持续着。
穆尔曼和巴尔特之后20年,民族性的概念在欧洲已相当流行,许多学术会议 (1982—1984年多次于杜塞尔多夫,2004年于波恩)[6],瑞士(1995年于伯尔尼)以及德国政府赞助的特殊领域研究项目 “非洲西部的大草原”(始于1993年)都专门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1869年创刊的 《民族学期刊》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在1990—2000年的年度合集中,几乎每隔一期都有对此主题的专题研究,有时甚至有多篇论文涉及这一主题,而在以往期刊的论文标题中,民族性这个词汇却从未出现过。如今,民族性在各种标题中被提及:“多民族的”(multiethnic),“族内和族际关系”(intra- and interethnic relations)(1993—1995),“族群”(ethnic groups)(1995),“民族性”(ethnicity)本身这一核心概念(1995—1999)。对该主题的强烈关注也带来了新的理论观点,它们比起史禄国的“精神心理”概念或者穆尔曼“民族压迫”的模糊概念来,能更好地解释民族的动态特征。它们是一些来源于经济学的量化概念,如“机遇最优化”,“边际效益减少”,“为交流付出的耗费”。[4]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在很早前就有萌芽的观点认为,民族是一个科学上的精神建构,各种各样的对象(人类群体)都可以归入其中,特别是在非科学的和政治话语中,它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说是虚拟的存在。这种看法重新反映出了把概念理解成是由社会决定的建构这样一种普遍趋势,并即刻遭遇到了解构主义的批评。此概念至今仍充满争议和疑惑,因为当今的民族学家分别属于以下四个流派的追随者: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
三、概念的多样化问题
自从穆尔曼在1964年出版了《种族、民族、文化》一书,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弗雷德里克·巴尔特的著作《族群和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aries)在1969年问世以来,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概念和针对过程及在理论上试图对此过程进行描述的民族性概念,正如笔者之前指出的,在欧洲民族学中受到了极大欢迎。这导致了这一概念如今出现了诸多不同的定义类型,正如在瑞士卢塞恩大学工作的德国民族学家贝蒂娜·贝尔 (BettinaBeer)2003年所指出的:
民族性这一概念不仅常被用于 (指代)民族的存在而且也用于(指代)民族意识的存在。另一些作者在对民族性的理解上强调民族边界,或将其理解为基于共同民族出身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又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性是以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的形式划定民族边界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研究民族性这一主题时,重要的是确定作者使用的是哪一个民族性定义。[7](P53-72)
人们曾狂热相信,能够通过民族性定义来描述和解释大多数该学科感兴趣的群体现象和群体过程,最终这种狂热已转变为怀疑。这一概念的定义形式显得太过于多样化,以致它无法在科学话语中起到帮助理解的作用。专门从事东亚研究的民族学家和汉学家贺东劢(Thomas O.Hoellmann)在其1992年发表的论文《对于民族学中的民族概念的批判性思考》(Kritische Gedanken zum Ethnos-Begriff in der Voelkerkunde)中将这一怀疑表达得淋漓尽致。他通过例举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的群族指出,此概念在具体运用中非常不清晰,因此他呼吁彻底放弃民族性这一概念。[8](P177-186)
事实上,民族性研究也由于不能预测或解释1960年以来频繁发生的族群武装冲突而令人失望。这些冲突发生于苏丹南部、卢旺达、巴尔干地区,最近以来在北美和近东地区也经常出现伊斯兰教徒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冲突。正是出于这种失望,欧洲学界有关民族性方面的研究自2000年以来急剧减少。西方人类学尽管仍然致力于运用科学知识服务于人类福祉 (如参与 “南北对话”),但关注的问题却已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生态人类学)、由经济发展带来的 “公平交易”(fair trade)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与歧视问题以及移民国家中的难民及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等等。
四、民族性的普及化和政治化
虽然民族性这一概念在学科内部遭到了质疑,但它在周边领域以及在政治和社会口语中也扩散开来。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早已令人厌恶的武装力量冲突中,确切地说出现在1991年至1995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当时的人们已经谈论“种族净化”(ethnic cleansing)、“种族大屠杀”(ethnocide)和“种族灭绝”(genocide)。②1994年东非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内战,曾致使800 000人死亡,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也被称为 “种族大屠杀”或“种族灭绝之战”(Genozid)。与此同时,这一概念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和平环境,比如在德国,人们会谈及“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或“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y),而之前则用的是“外来人”或“外国人”。
民族性这一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意义使得 “族群”和个人清楚地了解到,认同这样的一个族群不会像迄今为止那样给自己带来不利,相反会带来明显的利益。这些利益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通常有以下这些:免税或甚至得到国家财政支持;拥有可以利用某些资源的特权,而在这一国家里另外的公民却被禁止使用这些资源,如猎杀受保护的动物或砍伐林木、经营赌场、放宽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名额分配的规定更轻松地进入中小学和高校等教育机构、更容易得到避难许可从而移民到一个可能的接受国等。特别是加拿大、美国和中国,与之相关的程序和特权较多,并被明令规定,同时也成为立法和已付诸实施的日常政策的组成部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一些地区引发了激烈的竞争,人们争相加入某个为国家所认可的民族,而另一方面又遭到来自该民族成员的拒绝,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特权由此而受损。这些由政治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反作用现象已成为民族性研究的一个全新的且重要的领域。君特·施雷不仅提到了这些现象,而且直接触及它的政治层面。他写道:
在许多国家,被认可为少数民族可能带来利益。因为它关系到地区性代表的席位,或只有“传统意义上的猎人和渔民”才有资格享有的狩猎权和捕鱼权;关系到对于升值后的部落土地的领土权,因为它们被圈入城市边缘,或者因为那里发现了矿藏;关系到一个允许开设赌场的法律上的特殊地位。[4](P375-390)
五、认同(Identity)作为新的主导概念
民族性的多样化定义会让富有责任感的人类学家感觉不适,以至于民族和民族性这两个概念在专业词汇和官方话语中逐渐消失。这也导致了一些专业机构的更名,即删除其名称中的组成部分Ethno-(民族)或德语的Voelkerkunde(民族学)(见表2)。
与此同时,传统上习惯于使用“民族学”作为学科名称的一些西欧国家的研究机构,自新世纪开始也纷纷改名,倾向于使用“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这一转向也意味着学科研究焦点的转变,即从之前对于族群集体之实质性存在的兴趣,转而关注社群及个人,他们的文化创造及其象征性的表现方式。其中,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主题当然仍然占有主流地位。

表2 欧洲主要民族学博物馆的更名表
尽管如此,民族和民族性这一类事实和研究问题却没有消失,只不过学界对其问题性的描述有所不同,即描述得更加深入彻底。如今人们不再单纯地研究被认为已存在的“民族单位”,而是以这样一些主要是建构而成的、在当事人的想象中虚拟存在的以及根据社会环境而改变的群体为研究对象。人们已经认识到,所有这些想象都以认同的概念为基础。民族认同作为诸多认同中的一种,可以容纳一个人或一个集体。认同的社会概念与社会学中早已存在的“角色”概念接近。③但认同本身更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现象,因而它远远超出了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能力范围,虽然认同的某些特殊方式也包括了民族学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概念所涵盖的内容。
今天的人们不再关注复杂多变的民族和民族性现象,转而聚焦于身份认同的各种不同方式,并适当地使用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或文化史学的方法和提问方式来进行研究。随着认同被确立为新的基本概念,民族学的研究也从怀疑和停滞的境地中找到了出路。
注释:
①Weber,Max.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Grundriß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3 Bände.Tübingen:J.C..Mohr,1921;译文参考了中文版的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②原文中的词根都是“民族”(Ethno),这里根据习惯译法译为“种族”。
③Dahrendorf,Ralph,Homo sociologicus,1964。
[1]Schubert,Gabriella.Von den‘Nationaltrachten’zur europäischen Stadtkleidung.Wandlungsprozesse im Kleidungsverhalten der Donau-Balkan-Völker.In:Mitteilungen der 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12,S.69-83.Berlin:Verlag der BGAEU,1991.
[2]Das Yunnan-Album Diansheng Yixi Yinan Yiren Tushuo.Illustrierte Beschreibung der Yi-Stämme im Westen und Süden der Provinz Dian der Sammlung Hermann Freiherr Speck von Sternburg aus Lützschema.Leipzig: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2003.
[3]Elwert,Georg.Nationalismus und Ethnizität:Ueber die Bildung von Wir-Gruppen,In:Koe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41,Heft 3,1989.
[4]Schlee,Guenther.Interethnische Beziehungen,In: Hans Fischer& BettinaBeer(Hg.).Ethnologie.Einfuehrung und Ueberblick.Berlin:Dietrich Reimer Verlag,2006.
[5]Barth,Fredrik.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organization ofculture difference Oslo:Universitetsver-laget,1969.
[6]Willenberg,Ursula.“Ethnos”-“Ethnogenese”-“Nationsbildung”und das Problem der Staatsentwicklung In: Etnographisch-Archäologische Zeitschrift,28,Heft 2,Berlin(Ost),1987.
[7]Beer,Bettina.Ethnos,Ethnie,Kultur.Hans Fischer&Bettina Beer(Hg.),thnologie.Berlin:Dietrich Reimer Verlag,2003.
[8]Hoellmann,Thomas O..Kritische Gedanken zum Ethnos-Begriffin derVoelkerkunde.Am Beispielfestländisch-suedostasiatischer Bevoelkerungsgruppen.Tribus, 41.Stuttgart,1992.
【责任编辑:王立霞】
C95
A
1004-518X(2013)11-025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