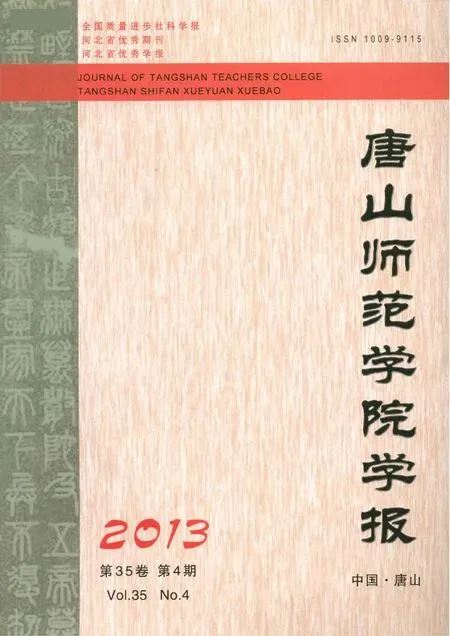元末士大夫视野中的农民战争及其思想意义
展 龙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在天崩地解、国破家亡的大事变中,元末士大夫的心灵世界受到了空前强烈的震撼。期间,他们围绕国家之兴亡、民生之否泰和自我之命运等时代命题,对农民战争进行了深刻反思和自觉总结,发表了一系列独特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元末士大夫复杂多样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而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士大夫对农民战争的基本倾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一、对农民起义态度:从仇恨到接受
“元末农民战争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这一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1,p268]。很多士大夫虽对元王朝的腐败政治深为不满,但因为他们多出身地主阶级,享有免除差发等特权[2,p84],加及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所以当农民战争蓬勃兴起之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站在元廷的立场上,对农民起义抱持刻骨铭心的仇恨心理。这种意向,在元末士大夫的诗文和行动中都有充分地表露,如杨维桢、顾瑛、王逢、谢应芳、张宪、宋濂、刘基、戴良、王冕、陈高、陈基、郑玉、赵汸、王毅、李祁、王礼、成廷珪等,莫不如此。在他们看来,农民发动起义不具有合理性,“朝廷何负尔辈,乃敢弄兵反”[3,卷19,p920]。所以,他们在竭诚为元效忠之时,诅咒起义军为“妖”、“盗”、“贼”、“魔”等,力主加以镇压,“扫荡妖氛清社稷”[4,卷3,p322],以达到消弭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诚如陈基作诗云:“生民苦涂炭,群妖方弄兵。大将肃旗鼓,三军严视听。所重奉天讨,慎勿妨农耕。鲸鲵示两观,熊虎行四征。努力平南服,以之答圣明。”[5,卷2,p12]刘基在亲眼目睹了“至今盗贼辈,啸众如蜂蚁”[6,卷19,p333]的情形,也不免“愁心如汶水,荡漾绕青徐”[6,卷12,p422],遂作诗云:“人言从军恶,我言从军好。用兵非圣意,伐罪乃天讨”[6,卷28,p340],颇“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6,卷2,p81]。陈、刘二人虽然此后分别投靠了张士诚、朱元璋,但在农民战争初期,他们仇视农民起义的意思仍很鲜明,上述诗中无不洋溢着同农民起义军的不共戴天之情。
同时,一些士大夫为镇压起义的元军大唱赞歌。刘嵩《槎翁诗集》卷三《罗明远杀贼歌》、《战敖原美周公瑾》、《马将军歌》等即是歌颂义士杀“贼”的诗文。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州一战,元军对农民起义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成廷珪特作《悲徐州》一诗赞颂“王师”之功绩。至于颂扬镇压起义军的余阙、李黼等的诗文,在士大夫的文集中更是不胜枚举。不仅如此,一些士大夫还直接参与或组织地主武装协助元军镇压起义军,甚至依仁蹈义,为元丧命,“此身许国誓不二,义不与贼同戴天”[7,卷3,p736]。这些思想倾向相联系,针对元廷招抚张士诚、方国珍的“怀柔”[6,卷23,p431]举措,很多士大夫亦表示不满。例如朝廷对方国珍惮于用兵,一意招抚,台州达鲁花赤泰不华和时任浙东元帅府都事的刘基就坚决反对,力主剿捕,认为“方氏首乱,罪不可赦”[8,附录,p787]。可以说,仇视、镇压农民起义军是元末士大夫的共同基调,在他们的思想中,“没有任何的民族思想,也不对农民起义抱有丝毫的同情”[9,p290]。
元末士大夫之所以仇恨农民起义,其原因与历代士大夫的观点并无二致:一是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元廷仍为唯一合法的统治政权,其正统地位是天经地义、不可悖逆的;而农民起义的斗争目标则是要打破现有的统治秩序,建立新的政权。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士大夫对农民起义的对抗情绪急剧增强。二是对农民起义破坏因素的畏惧与不满。身处战乱,士大夫亲眼目睹了士大夫“寇盗不仁还掠地”[10,卷2,p34]、“杀守令、据城邑”[11,卷3,p35]的历史事实,这对士大夫的生命财产、文化生活、道德理想等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尤其是起义军剥夺士大夫(地主阶级)特权利益的斗争目标,使士大夫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敌对关系进一步加剧。如刘基坚持镇压方国珍,就与方氏军队“烧掠沿海州郡”[12,卷26,p203]的行为有关。
当然必须明确的是,元末士大夫对农民起义的仇恨心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大体来看,在农民起义初期,元廷的镇压方针成效显著,故士大夫主张镇压起义军的思想倾向占主流地位。至正十五年(1355年)以后,元军接连溃败,战局向有利于农民起义的一边发展。在此情况下,士大夫深感元廷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战尘飞空暗南北,出门每恨山河窄”[13,卷4,p190],“喟皇天之不祥”[6,卷1,p204],很难依靠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开始与元政权疏离,同时对起义军的敌对态度渐次缓和,甚而开始向起义军的阵营靠拢。
二、渴望天下安定的忧患意识
元末群雄起兵后,士大夫原来安逸的生活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一如钱穆所云:“元明之际,江浙社会经济丰盈,诗文鼎盛。元廷虽不用士,而士生活之宽裕优游,从容风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自有山林江湖可安,歌咏觞宴可逃,彼辈心理上之不愿骤见有动乱,亦宜然矣。”[14,p139]由此,经过战火的洗礼,元末士大夫厌恶战争,渴望安定的情绪日益高涨,在其诗文中,随处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如陈高:“元日将堪喜,今年贼定平。天心占节候,人事厌戈兵。”[15,卷5,p5]许恕:“乾坤将厌乱,吴楚未休兵。梦想归田里,狂歌托圣明。”[16,卷5,p345]吴当:“废兴知运数,海内厌兵戈。”[17,卷4,p291]郑玉:“头白深知忧国事,身闲且复寄精庐。何时四海收兵甲,还向师山理旧书。”[18,遗文卷5,p96]又云:“干戈欲定知何日,江汉相逢慰此生。”[16,卷4,p339]刘基:“城上几时罢击柝?愁见海云蒸晚霞”[6,卷23,p479],“愿闻四海销兵甲,早种梧桐待凤凰”[6,卷23,p444]。舒頔:“书生亦是避世人,江海何日宁风尘。”[19,卷7,p154]上所引摘,皆透露出士大夫对时代命运的忧虑和对战争的厌恶,以及追求一个有序、安定的政治社会的强烈愿望。为此,有人甚至企图通过迷信宗教以消弭战乱,如张昱曾至普陀洛伽山寺,作佛事七昼夜,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拯救群生于水火,他说:“丞相函香致此诚,愿深海水救群生。慈悲谓可消诸恶,征伐容将息大兵。金色圆光开宝髻,玉毫妙相络珠璎,手中示现杨枝露,愿洗干戈作太平。”[20,卷3,p565]与此同时,士大夫伤时悯乱,抚今怀古,时常表现出对“大元”盛运的深沉眷恋,诗谓:“逝水自流人自老,依楹长忆至元年”[6,卷23,p469];“四海正歌垂拱日,百年犹忆至元春”[4,卷3,p330];“独不念至元延佑年,天下无城亦不盗”[6,卷17,p261];“疲氓真可怜,忍令饲豺虎。追忆至元年,忧来伤肺腑”[6,卷20,p363]; “父老歌延祐,君臣忆至元”[21,卷8]。可见,结束战争,实现安定已成了元末士大夫的普遍愿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社会失序的情况下,元末士大夫渴望结束战争的心态,实质上表现出及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一方面,他们虽然对元朝弊政心存不满,但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战争,仍恪守正统意识,站在元廷的立场上,希望朝廷早日平定战乱,恢复统治秩序,进而实现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使广大生民的生活有所保障。这种理念既包含着他们对元朝统治的并未全然丧失信心,也表明他们对身处战乱的黎民百姓的同情。另一方面,在大乱已极,元祚垂尽的情况下,一些士大夫的政治立场趋于多元,到底依靠谁来实现社会的安稳呢?他们不惟寄希望于元廷,也开始寄希望于农民起义队伍。所以,在农民战争的中后期,一大批士大夫投附农民起义军,除了谋求个人的功名利禄外,希望通过直接参与农民起义军,并借助其力量以实现社会的安定统一。这种观念上的转变,虽然有悖于传统的正统意识,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大夫渴望安定的愿望是极为鲜明的。但必须承认的是,美好的愿望毕竟代替不了残酷的现实,士大夫呼吁安定的努力纵然代表了时人的普遍心声,亦符合统治者的基本意愿,但并不能阻止和改变群雄纷争,社会动荡的历史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传统社会,尤其在时势变幻莫测的情势下,士大夫的言论是苍白无力的,极难作为一种力量来影响和改变当权者的统治理念,更无法扭转时势的发展大势。
三、基于农民起义对统治者的训诫
元末士大夫联系时代的厄运、国家的艰危和民众的疾苦,通过探讨治乱之源,明确而尖锐地提出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并向统治者发出了警戒,表现出了作为智虑之士的独到见解。在他们看来,“盗之起者,为饥寒所廹也”[3,卷19,p1531-1532],要避免起义的发生,统治者须以安顿民生为政务之首要;民众的生活状况是统治者赖以存在的基础,要从根本上解除危机,就须重视民生,体察民瘼。至正二十年(1360年),顺帝不顾民生之困厄,欲修上都宫阙,时任参议中书省事的陈祖仁极言上疏,表示反对:“愿陛下以生养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信赏必罚,以驱策英雄,亲正人,远邪佞,以图谋治道。夫如是,则承平之观,不日咸复,讵止上都宫阙而已乎!”[22,卷186,p4273-4274]陈氏满腹忧国忧民的情怀,据以儒家仁政学说,承袭民本主义传统,认为在起义蜂起的情势下,朝廷应该“以生养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而不能大兴工役,否则只能加剧社会矛盾,“违天道,失人心,或致大业之隳废”。基于这一认识,元末士大夫进而认为,人心是关乎国之存亡的关键,“夫人心者,天命之所系,国脉之所关也”,欲在农民战争中取得胜利,“必先有以收天下之人心”[23,卷27,p14],“人心不一,而欲守之,固战之克者无也”[23,卷27,p15],用吴海的话说,则是:“兵甲为利者,以民心为之本也。”[24,卷1,p236]所以,杨维桢提出,战乱之际,地方官员既然“以诛讨贼虏,恢复王土”为己任,那就须“以收人心、固人心为第一义也”[23,卷27,p14]。
针对当时“生不自聊,而赋敛日蹙,刑罚日滋”[24,卷1,p236]的情况,元末士大夫建议朝廷推行有效的安民政策。一方面,各级官员要积极安抚疲于战乱的民众,“吏善抚之则易以治,不善抚之则易以乱”[24,卷2,p246]。另一方面,朝廷应及时减轻民众负担,这是争取人心的关键,所谓:“下诏蠲秋赋,为恩不亦宽。农安思报主,力尽敢辞难”[25,卷3,p855]。此外,元末士大夫认为,兴举教化也是缓和农民起义的重要措施。儒家文化的治国方略是以德治教化为主,教化是治理百姓的首选政策,尤其在社会紊乱,秩序失坠之时,进一步倡导教化,对于整齐人心,划一风俗,进而恢复和巩固蒙元统治意义重大。如在刘基看来,民众之所敢于犯法为“盗”,其原因在于“不知人伦”。所以,他力主推行教化,通过精神层面的熏陶,使民众“明人伦、爱其亲、敬其君”,如此才能端正人心,防止盗贼滋蔓,进而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6,卷3,p121-122]。与刘基相类,吴海亦认为元末之所以出现“盗贼连起,攻城剽邑,杀掠民庶”[24,卷1,p232]的局面,其原因亦在于教化不振,“夫民知礼则不犯上,知义则可服,使生厚则自爱。……夫民知教则良心生,教立则善人众,大家既服,小民视之而化,风俗无不美矣”[24,卷2,p247]。吴海将治乱归于人心,指出欲使起义的民众“回心而向道”,就须教之“圣贤之道”,使其懂得向背顺逆之道,如此“虽穷而不舍义,虽死而不为乱”[24,卷1,p232]。言语中虽然暗含着为统治者“以赋敛为饮食,刑辟为娱乐”[24,卷1,p232]行为进行辩护的意味,反映了其本身思想的局限性,但强调教化为立国、救国之本的意思亦昭然可见。所以,与多数儒士文人一样,元末士大夫亦坚信:救治天下失序的关键在于唤醒人们对精神价值的关怀和遵循,而不是单纯依靠武力镇压强制恢复社会的有序状态。
当然,元末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广的社会根源。故而,要从根本上解除社会危机,恢复和稳定统治秩序,除了重视安顿民生、争取人心而外,士大夫认为统治者尚需整顿朝政,振肃纲纪,澄清吏治。对此,刘仁本(字德元)有言:“今家国多故,兵革四出,所急者振纪纲,明法度,肃官府之政令,以挈人心而已”[10,卷5,p83]。林弼说:“元政既衰,令非其人,民不堪其虐,辄且挺而起,比寇平,则民以残矣。”[26,卷12,p522]吴海亦说:“自海内多故以来,民心皇皇,无所底止,虽守令饕残之所致,亦由任是职者不能提纲振纪,取国家立法之意。”[24,卷1,p232-233]同时,作为构造社会伦理的中坚,士大夫认为有意识的倡导和践行道德价值是人之存在的根本。由此,针对以元顺帝为首的统治者德行不修,致使天下大乱的局面,他们期盼君主的德行,认为“人君修德灾可弭”[27,卷4,p486],君主个人的道德影响是实现统治的要点,也是政治运作的原动力和天下治乱的根源。倘若统治者能够以身作则,以自身的道德感召力来引领风化,规约社会,便会在广大民众中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从而达到争取人心,恢复社会秩序的目的。如刘仁本在诗中所言:“礼乐将兴未百年,一时民物遽骚然。庙堂鼎鼐乖调爕,海宇兵戈苦结连。寇盗不仁还掠地,君臣修德可回天。独怜边将相蹂躏,纵立奇勋莫自全。”[10,卷2,p34]
总之,元末社会的大动荡,不仅是封建王朝再度更迭的历史重演,也是对士大夫人格的一次严峻的锤炼。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战争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士大夫对伦理教化、礼法秩序、政治理念、安民之道等重要问题的自觉思考,而对农民战争的直接评论,则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然而,在王朝更迭,治乱交替之时,士大夫的理性言论极难被元朝统治者所接受,更无法成为元朝拯救自我,恢复统治的思想向导。伴随着一大批士大夫相继进入群雄阵营,他们的许多识见成为起义军领袖治军行政的重要依据,这对于农民起义领袖思想观念和政权性质的转变以及农民起义的最终胜利,皆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可从朱元璋集团那里得到较为明确的认识,如朱元璋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即在于重整封建纲纪,维护汉族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而这一口号正是对元末士大夫政治见解的实际践行。
[1] 陈高华.元末农民起义中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动向:兼谈元末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A].元史研究论稿[C].北京:中华书局,1991.
[2]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3] 宋濂.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4] 成廷珪.居竹轩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5] 陈基.夷白斋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6] 刘基.刘基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7] 郑元祐.侨吴集(北京图书馆珍本古籍丛刊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刘基.刘伯温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9] 陈高华.元末浙东地主与朱元璋[A].元史研究论稿[C].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 刘仁本.羽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1] 余阙.青阳先生集(四部丛刊初编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2]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 郭钰.静思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4]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15] 陈高.不系舟渔集(敬乡楼丛书本)[M].民国十七年永嘉黄氏校印本.
[16] 许恕.北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7] 吴当.学言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8] 郑玉.师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9] 舒頔.贞素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0] 张昱.可闲老人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1] 贝琼.清江贝先生诗集(四部丛刊初编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2]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3]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4] 吴海.闻过斋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25] 蓝智.蓝涧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6] 林弼.林登州遗集(北京图书馆珍本古籍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7] 倪瓒.清閟阁全集(丛书集成续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