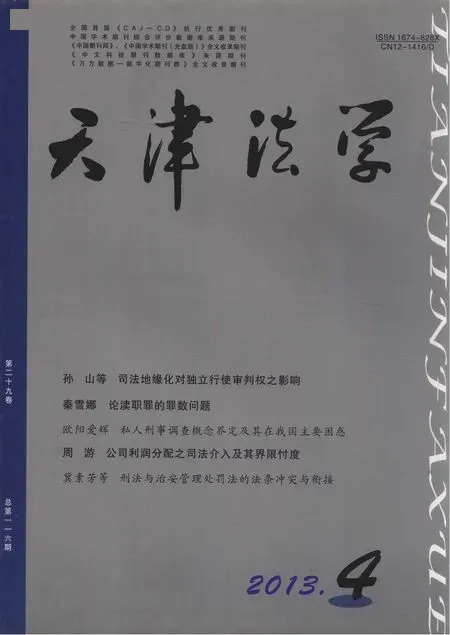公司利润分配之司法介入及其界限忖度
周 游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一、问题的由来
公司治理蕴含的自治原则与司法介入秉持的正义理念本应是公司法精髓的两大要素,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两者难免存在冲突。因此,如何在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中达至平衡是公司法研究的一个永恒命题。司法实践中,公司长期不分红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并不少见,但在现行公司法没有规定公司盈利就必须分红的前提下,法院如何在自治与正义之间进行理性衡量,便成为值得思考的争点。
以下案例属于上述命题思考中的一个典型①:深圳市某甲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甲公司)从2007年到2011年连续五年盈利,除2004、2007年以外,其余年度未向股东分配利润。公司长期未召开股东会,所有的分红决议均通过董事会决议作出。但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审查批准董事会提出的年度利润分配或弥补亏损的方案;同时还规定公司缴纳税款后的利润,在提取公积金与公益金后分配股息红利,并且,公司每年派发一次股息红利,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原告乙据此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分配其股息红利108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实现至少应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司具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二是股东会作出向股东分配利润的决议。由于被告公司多年未召开股东会,更谈不上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必须经由股东会审议批准的程序,所以,被告董事会作出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违法的,亦是无效的,被告公司应将未分配利润派发给原告等股东,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分配合理利润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判决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法院在双方均未提交2012年度审计报告的前提下,主动依据以往年度报告中列明的未分配利润为分红基数,并以公司章程中规定税后利润的80%为分红比例,为原告计算出分红款为13749.93元,比原告的计算结果还要高。实际上,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公司利润分配纠纷。但是法院并未如惯常之做法那样驳回股东的诉讼请求,而是判决股东胜诉,如此特殊的判决留下诸多问题值得商榷:第一,此案中司法介入的程度是否恰当?第二,在往常的诸多判决中,法院都对利润分配之诉求持审慎态度,其缘由为何?第三,公司利润分配之困境,是否可通过司法介入能得以彻底解决?抑或是,造成利润分配纠纷不断是另有原因?第四,倘若认为司法介入公司利润分配理应审慎,那是否说明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得以实现?这些疑点紧密相连,并成为本文思考的主线。
二、法院为何不宜替代公司进行利润分配
有限责任公司股利分配实质上是公司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于公司内部事务。法官不是商人,不能过分夸大自身在司法裁判中的能力。正如1976年在美国K a m in v.A m e r ican E x p.C o.一案中,法官业已明确指出:“充分探讨经营问题的地点,董事会的会议室要比法庭更合适”②。即便司法获得介入的权限,也并不意味着法院能代替公司行事。因此,法官仍要明确定位自身角色,否则违背公司法秉持已久的诸多原理与规则。
(一)公司自治:尊重公司独立法人格地位
公司自治是公司法人格独立的体现。而“公众公司区别于其他企业组织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独立人格”[1]。在近年的司法判例中,法院愈加重视公司自治、肯定公司对税后利润之用途的理性决定权也成为一种趋势。如在个案中法院就明确表示:“公司盈余的使用属于公司股东会自治权利,股东会有权自行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公司发放红利的权利。③”这也理应是司法介入公司利润分配的一个重大前提性考量。在中国场域下,公司自治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公司独立于公权力;其二,公司独立于股东。
首先,公司独立于公权力而享有自治权。这一层面的公司自治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中已然不言而喻,在我国仍要强调实属历史遗留的问题。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多年,因无视市场的自我调节而导致企业的独立性丧失。自实行市场经济以降,尽管新旧公司法逐渐强调公司法人格独立的重要性,但是理论和实践中对此肆意践踏的现象一时难以杜绝。倘若司法介入如前述案例那般过于武断,同样对于公司自治产生负面影响。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公权力介入公司自治并非绝对的不正义,因为,公司自治本身亦存在局限性,它并非完全的私法自治[2]。公司的决议因其实行多数决并由此预设假定性的意思一致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挑战性因素,为弥补此中的缺憾,司法介入也便有其正当性,但这种司法介入的正当性只能在公司自治失灵时方能彰显。
其次,公司独立于股东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自治的体现。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尽管公司设立的目的大多是增进股东的收益,然而当公司解散时更要顾及职工、债权人等多方利益,但此时要承担责任的是公司而非股东。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逐渐分化是现代公司的特征之一,这种分化的实现,就要使得公司的行为不被认为是投资者的行为[3]。因此,公司在存续期间就不能仅仅以股东利益作为唯一的目标,这导致公司与股东的利益不能达到绝对一致。而尊重公司意思正是公司自治的要求。当公司决定不发放股利,可能因为留存利润能应对公司当前以及未来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又或是奠定公司发展的基础,这些都属于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案例中法院片面顾及小股东的权益,并未对公司留存利润目的之不合理性予以明确,这实为因小失大的举措。
从更为深入的理论层面来看,“国家对经济是干预还是自由放任,是经济法制演变过程中永恒存在的一对矛盾”[4],尊重公司独立法人格地位则是旨在调和这一矛盾在公司立法中的体现。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皆有其边界,而对公司人格的尊重则是两者边界划定的基本准则。
(二)股东平等:不能只对个别股东发放股利
同股同权与同股同利是股东权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5]。对于股利分配来说,除非全体股东另有约定,否则应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取股利。同时,股东平等原则还意味着个别股东与公司的关系不应当影响到其他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因此,公司不能作出只对特定股东分配股利的决议,法院更不能作出公司只对特定股东分配股利的判决。这在以往的司法裁判中亦已得到体现④。由此可见,上述案例之判决违背了股东平等原则。当然,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规则,其他股东并未起诉公司,那么法院也不能擅自判决其他股东也和原告乙一样获得近几年来的股利,这又似乎证明法院的判决是妥当的。然而,正是这种矛盾说明法院所作判决存有问题,也成为司法不宜贸然介入公司利润分配的重要原因。既然如此,法院是否应当追加其他所有股东为当事人?这似乎也不妥,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多个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情形,而此时公司与所有股东之间的诉讼标的只是同一种类。况且,对于股东众多的公司来说,此种做法也不现实,然而法院执意作出如此判决,则可能导致其他股东提起类似的诉讼,这难免增加了法院不必要的负担。由此可见,法院作出责令公司向原告乙分红的判决,绝非明智之举。
此外,有观点认为司法应该介入公司分红权纠纷是为了防止控制股东滥用鼓励政策损害小股东利益[6]。诚然,保护小股东利益也是实现股东平等的重要策略,但是通过司法介入公司利润分配来对小股东利益进行倾斜性保护应当有一定的前提性限制,那就是法院必须判断公司不分配利润的行为本身是不合理的,但如果上述行为符合商业目的,就不能认为控制股东违背诚信义务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合理预期[7]。故而,立法与司法在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同时,同样要防止小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大股东合法权益,产生“少数人暴力”之现象,这当然也不符合股东平等原则的理念与要求。
(三)债权人保护:基于公司形式派生出来的独特风险
公司法不仅强调股东保护,还关注债权人保护。对于后者,合同法有关债权人代位权、撤销权对于公司的债权人同样可以行使。然而,“公司的债权人面临着由公司形式派生出来的独特风险”[8],因此,在公司法中也设置了诸如揭开公司面纱等制度对债权人加以保护,以防止股东滥用有限责任。有学者认为,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劣后于第三人对于公司之债权[9],此种说法并不严谨。当公司面临破产清算时,债权人利益的确优于股东的剩余价值索取权,然而在公司存续期间,股东在公司获取分红并不以公司业已清偿债务为前提。尽管公司分配利润前必须先行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由此是旨在确保债权人的利益不因公司利润分配而受到负面影响,然而,实践当中此种账面数据往往不能完全取信,查明真实财务状况是具体诉讼中不可忽视的阶段。
有法院曾在司法裁判中准确地表明:“如果公司的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法律的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上述规定的性质应系强制性法律规定,旨在保持公司资本的稳定性,维护债权人的利益。⑤”但是在本文讨论的案例中并未发现法院对债权人利益有任何考虑。公司连年盈利也并不意味着公司已经提取足够的公积金,也不意味着公司就一定满足分配股利的条件。法院倘若执意要求甲公司向乙分配股息红利,那么也必须查明此举是否危及公司债权人利益。而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有必要的,按照法院的判决,其依据以往年度之审计报告中列明的未分配利润为分红基数,而此分红基数几乎是2011年度未分配利润的两倍。由此,倘若其他股东也要求公司分配股利,根据股东平等原则,其他股东同样应当按该分红基数为准分取红利,由此导致的结果已然不是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护,而有可能是整个公司因资不抵债而面临破产的问题。况且,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因为个案中的利润分配出现问题,就认定整个私人自治都出现了问题,并由此进一步认定法院的主动判决及其强制执行就能获得正当性⑥。如此一来,我们极易陷入“空想分析法”(Ni rv ana A ppr o ach)的谬误,即通过简单比较理想规范与并不完美的现实规范之后就进行制度安排[10]。
(四)小结:股权本质与公司价值
前述探讨可归结为:倘若司法无视各项公司法原理和规则而贸然介入公司利润分配,那么实际上是其未能准确理解股权的本质和公司的价值所在。在理解公司股利政策问题上,一种误区在于股东投资设立公司,公司就应当给股东分红。此种观点并不完全错误,但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诚然,股东的分红权的确是股权的应然成分,但如果过分夸大分红权的重要地位,可能会阻碍我们看清股权的真正本质。其一,股东持有股权若仅仅单纯为了分红,则与将金钱存入银行获取利息之做法没有实质区别,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以“债”的观念来审视股权,由此难以理性认识股权的本质。其二,股权的价值主要不体现在分红之上,而是侧重彰显于股权增值乃至股权转让价格提升等方面。毋庸置疑,当公司连年盈利,即便公司不分红,公司的增值也就意味着股权的增值,故而“公司资产的充足,或许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股东亦可博取水涨船高之利”[11]。在这样的情况下,倘若立法与司法还过分要求公司必须分红,则有可能导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失衡,而公司利益减损所带来的后果从长远来看实际上还是由股东来承受。其三,公司的股利政策往往与公司的长远发展与价值相关。当然,这需要公司在不断的商业实践中渐次形成良好的内部治理,使得留存的利润能真正落实到公司的未来发展当中去。此外,有时公司不分红还基于税负的考虑。公司制之下所存在的“双重征税”主要就是体现在利润分配问题上。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税负,公司完全有可能将本年度的利润转化成公司资本,这就同时增进了股权价值与公司价值。故而,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立法并没有强迫公司必须分红,司法也不宜替代公司分红。
三、造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不断的深层原因
公司股利分配纠纷极为复杂,这就意味着此类纠纷的频发势必存在更为深层的原因。通常认为股利分配纠纷是因为控制股东压榨小股东而引起的,从而得出控制股东滥用权利是造成此种纠纷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上述案例的逻辑所在。然而,这样的观点无疑是片面的。实际上,公司是否向股东分配股利与控制股东是否滥用控制权之间并不存在当然的因果关系。而基于大股东大权利、小股东小权利的生态法则,处于劣势的小股东又往往会将控制股东做出的任何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结论,都看作是控制权滥用。这对于控制股东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对于公司的发展也多有不利。因此,探究造成利润分配纠纷的深层原因对于问题的解决也显得极为必要。笔者认为,公司增资困难、股权回购条件过严、公司章程地位虚化等是造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不断的深层原因。
(一)公司增资困难
法律对于增加资本的条件一般不予以强制性规定,这不仅因其属于公司自治的内容,同时还因为增资能使公司资本增加、实力增强,这对于债权人保护也是有利的。然而,在我国司法裁判中,涉及公司增资纠纷的案件并不多见,这不能说明公司增资未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恰恰说明的是增资很有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困难⑦。一旦公司增资困难,那么往往就会迫使公司尽可能地少发甚至不发股利来留存利润,以防不时之需。
公司增资的困难并不在于法律的严格规定,而在于增资会受到来自公司内外不同障碍的影响。一方面,在内部增资情形下,股东不同意增资的理由既可能是因为其自身资金不足,又或是忧虑不同比增资引起股权被稀释,从而降低其在公司的影响力,因此,增资决议必须通过绝对多数决方可通过。正如学者指出,导致股权的稀释和股权结构的调整是直接影响现有股东利益并可能引发严重利益冲突的公司重大事项[12]。因此,内部增资决议的作出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外部融资途径的匮乏,更使得公司融资难上加难。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趋势加强,中小企业特别是县域及以下中小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增加,资金供需矛盾较为突出[13]。在此情形下,通过提取公积金获得经营资产已经成为很多公司无奈的选择。而转增资本也正是公积金的主要用途之一,公司为了未来存续与发展而留存利润、不分股利,也是现行法所默许的公司融资规则。由此,对于法律为何没有强制将公司盈利时不分股利作为特别决议的内容之一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股权回购条件过严
根据现行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若干情形下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这种权利也被称为评估权。其中一种情形则为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本文探讨的案例中实际上也存在类似情形,然而因为甲公司并未连续五年不分配利润,所以原告乙也无法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此外,公司转移主要财产也是回购条件之一,但是如何认定哪些财产是主要财产则在司法实践中标准不一⑧。这些情况都反映出当前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股权的条件过于严苛。
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因受公司人合性特征的约束而颇受限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股东在与公司决议产生分歧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基于决议理论之缺位[14]、公司法有关股东对决议存在异议的纠纷解决途径之空白,则进一步使得股东难以从此种境地中挣脱出来。况且,评估权的适用范围又极为狭小,并具有法定性:根据现行《公司法》第75条的规定,股东能请求公司回购股权的情形是法定的,而且没有兜底性条款,亦即公司章程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另行规定的权能。从传统公司法理论来看,这主要因为“原则上公司股东不得抽回或者变相抽回资本,这是资本维持原则的体现”[15]。如此一来,股东依据评估权而退出公司的可能就难以实现,尤其是连续盈利但连续不分红之情形,容易被公司规避,这也加深了公司股利分配的矛盾。
(三)公司章程地位虚化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内部宪章,然而一直以来,投资者之法律意识不足,在公司法领域则表现为对公司章程的忽视。这种将章程地位虚化的做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章程制定时并未仔细商讨相关条款,导致纠纷产生后难以解决,这在有限责任公司场合经常发生,因为人合性特征致使公司设立时各股东之间出于情感与信赖关系而认为诸多条款都可以不写入章程约束各方。二是即便章程的规定较为完善,然而日后在公司运营期间又将相关条款予以架空、视而不见,这无疑也与人合性有一定关系,一旦发生纠纷,被架空的条款也有难以适用的可能。而章程地位虚化,实际上是公司治理紊乱的体现。公司治理紊乱也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股利政策对公司发展的重大意义。
正如本文讨论的案例,公司产生利润纠纷实质上也与章程被虚化不无联系。首先,2005年公司法业已删除有关公益金的规定,因考虑到公益金制度并未发挥应有作用,反而在实践中存有不少问题。然而,该案例中直到2012年仍未见公司修改章程,章程中仍规定在分配利润之前必须首先提取公益金。当然,这与公司一直不召开股东会有关。其次,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每年派发一次股息红利,同时也规定股东例会每年举行一次,然而一直未见有股东提议召开股东会,也未向法院起诉责令公司召开股东会。案例中原告乙绕开股东会的召开问题而直接请求分配利润,不能理解为穷尽内部救济之后的迫不得已,此种做法只能说明章程地位虚化的同时股东也缺乏真正的自我保护意识。
四、公司利润分配纠纷之缓释进路
从以上分析可知,司法不宜介入公司股利分配,因其违背了公司自治、股权平等以及债权人保护等原理与规则,造成公司内外各主体利益失衡。公司股利分配纠纷的产生与现行法其他制度的弊病以及投资者缺乏足够的法律意识有关。而对于必须严格遵行法律规定的法官而言,这些缺失并非其要致力解决的问题所在。应当明确的是,司法审慎介入与法律制度完善应为同步进行的过程。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公司利润分配纠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求根本解决之道几乎不可能实现,这毕竟涉及到公司法改革的全局性考量。但试图通过省思既有规则,并省察规则革新的可能策略,不失为一种理智的缓释进路。
(一)现时解决方案:严格遵行相关程序
法官要明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司法不介入公司股利分配并不意味着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司法途径得以救济。具体而言,法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公司解决股利分配所产生的问题。
第一,找到支撑司法裁判的明确的法律依据。诚然,本来这已是不言而喻的命题,只是因为在日益纷繁的社会中,情感宣泄不免会影响法官裁判,对于很多不应干预的事务法官都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而法律却并未赋予其作为的依据。法律定会有缺憾,法官也不应机械地适用法律,而问题是当现行法已然给定完备的规则时,法官就不能逾越。在司法实践中,以往诸多案例都驳回股东要求公司分红的诉讼请求,正是因为法官在公司未作出分红决议之前根本无法找到相关法律依据而强制公司分红。在本文案例的判决中,则存在逻辑错乱之处:法院首先认为股东会决议是公司分配股利的两大条件之一,但最后的判决恰恰未以股东会决议为前置程序,此种做法颇为荒谬。
第二,责令公司召开股东会。无论是现行法的规定还是甲公司的公司章程都已经明确规定股东会召开的相关事宜,同时也明确了分配利润要通过股东会决议方可实现,由此可知,法官只有在股东会作出决议之后,介入利润纠纷才获得了相关的依据。所以,责令公司召开股东会理应是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第一步。当然,这其中的问题是,原告乙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分红而非召开股东会。对此,法院应运用其释明权,建议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命令公司召开股东会,讨论利润分配方案。倘若原告不愿变更,法院可驳回其诉讼请求。这在表面上看似乎未能体现司法救济的功能,然而,程序正义往往是实质正义的前提。在公司法并没有也不可能规定有限公司必须强制分红的法律环境下,司法介入公司利润分配的合理性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就有赖于股东会的决议,倘若公司不召开股东会、不作出股东会决议的话,司法介入片面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也将导致新一轮的利益失衡。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我国至今只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之诉由,却没有“公司决议不存在”之诉,故而,股东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前提下请求利润分配实际上也存在着巨大的法律障碍。
第三,通过判明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对股东利益予以保护。这也应是法院在保护小股东利益时最为正当的举措。倘若《公司法》业已提供可操作的规则,且公司拥有较为完备的章程条款,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只要各项决议和计划均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各主体之实体权利的维护与平衡也就最有可能实现。如果说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公司股利分配问题予以干预,那么也正是在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效力认定上能有所作为。上述案例中,当法院责令公司召开股东会以后,若股东会作出不分红决议,那么股东仍可以决议的内容违反了章程每年必须分红之规定而请求法院撤销。当然,若在章程没有规定每年必须分红的情形下,股东仍可提起撤销之诉,只要其有证据证明该决议受到控制股东不当影响,或控制股东已凭借其优势地位获得巨大个人收益。正如有学者所言,此时法律最大的效力就是关注控制者是否将价值从公司转移到他自己名下[16]。他可以通过提高薪酬,加大在职消费,或者通过不公平的关联交易,从交易价格与公平市场价格的差别中,获得事实上的收益[17]。而此时也正是体现法官智慧的时候,法官可依据这些相关因素来衡量决议的妥当性,从而依据公司法第22条的相关规定作出是否撤销的裁判。
第四,股东会无法作出决议时司法救济仍存有可能性。倘若公司最终仍然无法作出决议,也就无所谓撤销决议之可能。然而,现行法对于此种情形仍为小股东提供了救济措施。极端的做法则为请求解散公司。有学者指出,虽然新公司法第183条并未直接规定股东会不能作出决议时少数股东可请求法院解散公司,但它所表达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实际上包含了股东会不能作出决议这一情形[18]。然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以利润分配请求权受到损害为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⑨。这无疑又使得此种解决路径存在一定的障碍。
(二)缓释路径优化:相关制度的完善与投资者法律意识的提高
要妥善缓释公司股利纠纷,不仅依靠法官的智慧和公司章程条款的合理程度,还需要对现行法相关制度加以完善,因为从上文分析可知,造成公司股利分配纠纷的主要原因并非法院所能左右。当然,这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多,例如公司融资渠道的拓宽、公司治理的优化等内容,这些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在此仅就其中最为突出的股权回购制度稍作分析。前文已提及,回购条件过严是造成公司股利分配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法律之所以对于评估权持谨慎态度是因为资本维持原则的引导而出于对债权人保护的需要。然而,债权人保护的策略是多维度的,而不仅仅停留在严格限制评估权的行使方面,本文案例也已说明,即便股东请求回购股权失败,但最终却分得红利,这同样未顾及债权人的利益。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回购条件过严是一种片面保护债权人而不利于保护小股东的举措。较为妥当的方式是允许公司章程在一定条件下设定更为宽松的回购情形,所谓的“一定条件”,主要是要求公司用利润而非资本来回购股权,这样也不违背资本维持原则。倘若用利润回购股权,也就不会导致公司资本减少,这为许多国家公司法所允许[19]。
此外,投资者的法律意识亟待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公司法场域,投资者法律意识淡薄的主要体现是股东对于公司章程的不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资者法律意识不足的境况之下,法院的态度显得更为重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就因此获得肆意干涉市场主体内部事务的权力。法院更应在这样的形势下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只有法院能够严格遵行相关法律程序并尊重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和股东才有可能意识到这些程序与规定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这些程序与规定的效用才能达到最优化。
五、结 论
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征之一正是较高的人合性,故而司法介入务必慎之又慎。股利分配纠纷尽管矛盾重重,但法院直接替代公司进行分配不仅不能缓和矛盾,往往还可能造成公司内外各方利益失衡。纠纷的产生源于多方面的因素,而不能片面地理解为控制股东滥用其优势地位侵害小股东利益。本文讨论有限责任公司股利分配,旨在阐明此种纠纷的解决应尊重公司自治以及司法程序。而完善现有制度以及提高投资者法律意识则是缓释纠纷的妥当进路。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保护小股东决不能片面为之,“控制股东”一词业已被丑化,这也是过分鼓吹保护小股东的后果。而控制股东的作用得不到重视,可能正是法官不太顾及公司长远发展的原因之一,由此而作出的裁判只关注眼前利益也就不可避免。真正要达到保护小股东的目的不能仅仅依靠司法途径,也不能仅仅寄托于立法的完善。有学者指出,少数股东保护的实质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该问题的全面解决,必然要有赖于法律之外的管道[20]。因此,对于公司股利分配纠纷来说,司法应在充分尊重公司自治的前提下,从公司决策程序以及股东具体请求权保护方面介入。当然,最后要指出的是,本文侧重探讨的是有限责任公司场合的利润分配问题,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而言,情况可能就大有不同,后者因其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公共性而波及范围极广的投资者之切身利益,这些因素就可能会使得在特殊情况下上市公司被要求强制分红存在着妥当的法理基础。但无论如何,尊重公司自治理应成为解决公司法律纠纷的第一步。
注 释:
①该案为笔者在深圳市某区人民法院调研时所研究的案件之一,作为本文样本时笔者对案情略有修改。
②86 M i s c 2d 809,383 N.Y.S.2d 807(S u p.C t.1976).
③参见“唐国洪诉汝城县兴鑫化工有限公司诉汝城县兴鑫化工有限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案”,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1)汝民初字第170号。本文所引案例均源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④法院认为,“股东与其所投资公司之间的投资收益之债的成立条件不同于普通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一经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成立。投资收益之债在公司有净利润可分的前提下,还应当经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或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能成立。如此方能避免损害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并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故个别股东与公司单独达成投资收益分配协议不足以构成股东收取投资收益的条件。”参见“上海市宝山区房屋建筑材料总公司与上海浦东宝房混凝土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718号。
⑤参见“北京蓝色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北京嘉年华旅行社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民终字第2476号。
⑥如有学者曾进行研究,认为转轨经济时期法院的强制执行效果还不如私人之间的制约机制。See Hamish R. Gow Johan F. M. Swinnen, Private Enforcement Capital and Contract Enforce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cs, 83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86-690(2001)
⑦根据北大法律信息网的数据统计,截止2012年年底,在与公司有关的近6000个案例中,涉及公司增资纠纷的案件仅有19个。相关新近案例,例如参见“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等与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1号。此案还是备受争议的我国“对赌协议”司法第一案。
⑧例如参见“翁启凡与杭州余杭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请求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商终字第742号。
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gt;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二款。
[1]左传卫.公司制度流变考[J].河北法学,2011,(1):140.
[2]蒋大兴.公司自治与裁判宽容——新《公司法》视野下的裁判思维[J].法学家,2006,(6):70-78.
[3]Leonard W. Hein. The British Business Company: Its Origins and Its Control [J].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1963,(15): 137-138.
[4]王涛.变迁时代的经济与法(1600-1911)[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189.
[5]甘培忠.企业与公司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10.
[6]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273.
[7]王洪伟.公司股利分配法律制度研究——以相关主体利益平衡为中心[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132.
[8](美)莱纳·克拉克曼等.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M].刘俊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3.
[9]刘俊海.公司法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4.
[10]Harold Demsetz. 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 Another Viewpoint [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9,(12): 1-22.
[11]刘俊海.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12.
[12]赵旭东.公司法学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3.
[13]王艳霞.民间融资规范化探析 [J].天津法学,2011,(3):90.
[14]陈醇.商法原理重述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6.
[15]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55.
[16](美)马克·罗伊.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政治环境与公司影响[M].陈宇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40.
[17]邱海洋.公司利润分配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2.
[18]杨勤法.公司治理的司法介入——以司法介入的限度和程序设计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5.
[19]沈四宝.西方国家公司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84.
[20]蒋大兴.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Ⅰ:法律哲学amp;碎片思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