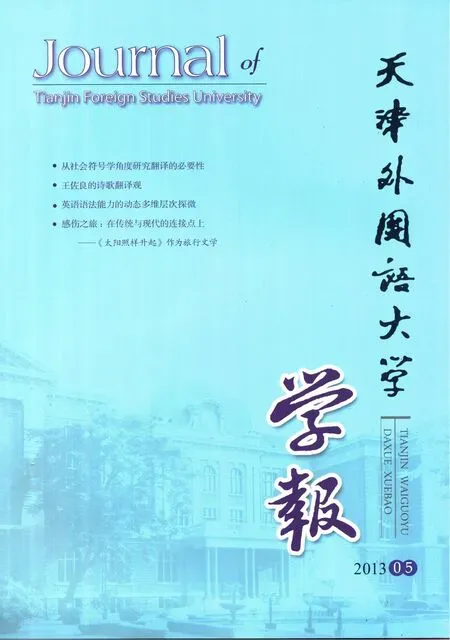感伤之旅:在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上——《太阳照样升起》作为旅行文学
陈红梅
(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210037)
一、引言
《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1926,下文简称《太阳》)是海明威的第一部小说,甫一出版即大获成功,并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经久不衰的关注。大多数批评关注的是小说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荒芜和迷惘主题、各色人物的个性特点和作家划时代的创作风格,也有论者关注到了小说的消费主题和人物对“菲勒斯(Phallous)”的无望追求(于冬云,2005:5-14;李长亭,2011:106-113)。实际上,小说叙述的是一群有着相似经历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在巴黎自我放逐时到西班牙观看斗牛消夏的一次旅行。对于这部小说的旅行主题,有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以旅行目的地为编排标准的《剑桥美国旅行文学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Travel Writing)认为:“在塑造一定限度本地化而非单纯的旅行者和波西米亚小资男性美国人形象上,没有别的美国作家(比海明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正因为这个原因,《太阳》是美国旅行文学的伟大典范之一。”哈佛学者艾利森·纳迪亚·菲尔德(Allyson Nadia Field)则从体裁上论证《太阳》虽为虚构小说,但由于作家采用一些体现真实的技巧,实际上其文类甚至可归为旅行见闻录,承继了旅行指南的文学传统,起到了旅游手册的作用。但前述论者们都没有深入分析“人在旅途”的状态对其人物“迷惘”产生的影响。仔细阅读小说可以发现《太阳》事实上以不同的着墨描述了三重旅行,即浓墨重彩的巴黎消费之旅和观看西班牙斗牛之行,还有隐含在文本之外但其魅影却无处不在的流放者之旅,本文将细致分析小说中不同旅行的叠加对人物产生的心理冲击,认为这是战争创伤造成他们颓废之外但常为人们忽略的原因。
二、流放者之旅
旅行由于抛弃了日常生活的程式,发生在新奇的环境中从而给旅行者提供了认识自身的机会,因而常常意味着摆脱羁绊和发现自我。与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华顿等到欧洲去开阔视野、接受其厚重文化熏陶不同,《太阳》的主人公们离开家乡来到巴黎追寻自由和自我。杰克们在巴黎时间甚为长久之前的旅行发生在文本之外,但却在文本之内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除科恩外,杰克和其他人都在法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程度地受到战争和家庭的创伤,回国之后又到巴黎相聚。战争的炮火轰走了旧日的传统成规,战争的洗礼冲走了必须倚靠的道德规范,他们习惯于从一地到另一地“换防”。他们之所以迷惘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创伤,用美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学者马尔考姆·考利(Malcolm Cowley)(1996:6)的分析来说:“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无根之木,在外地上学,几乎和任何地区或传统失却联系。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应付另一种生活,而不是战后的那种生活,是因为战争使他们只能适应旅行和带刺激性的生活。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试图过流放的生活。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不接受旧的行为准则,并因为他们对社会和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形成了一种错误的看法。这—代人属于从既定的社会准则向尚未产生的社会准则过渡的时期。”
可以看出,以杰克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不仅经历了战争和战后“过渡的时期”,也身处传统和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即实行禁酒制度,强迫人们节俭自制。对这些习惯了战时自由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根本受不了这么严酷的约束,还有家乡中规中矩的安稳生活。所以,就像多次被谨守新教勤勉克己的父母警告要“停止那好吃懒做的浪荡生活……否则你将一事无成”(贝克,1992:126-127)的海明威一样,他们也要回到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地方,去寻找曾经享有的自由,到欧洲、到巴黎将自我放逐,享受不再受父母管教、没有宗教约束的自由。对杰克们来说,离开故土到异国旅居是自我去中心化的途径,也是他们寻求自我的一种方式。
然而,到巴黎之后,杰克们果真追求到了当初想要的自己吗?从表面看,他们确实过上了想要的“历史上最放浪、最华而不实的纵饮行乐”(菲茨杰拉德语),将禁酒令和清规戒律抛在“三千英里之外”的身后。在这长久的自我放逐中,杰克们尽享了巴黎“流动的盛宴”。 他们在巴黎繁华的街上逡巡,透过漂亮的橱窗审视一个个闲适的消费场所,穿行在一个个咖啡馆、餐馆和酒馆中。但是在这些消费空间里,他们虽然逞一时之快意,却既不在此也不在彼,是既不属于家乡也不属于巴黎的“阈限人群”(liminal entities)①。他们既不是本地人也不是观光客,在他国异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在异域的边缘流连,流转于本我和客居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之外。然而,杰克没有认识到自己“既非此亦非彼”的阈限状态的要害,更没有想到要摆脱这种状态。一方面,他在巴黎过着貌似自食其力的生活,除了有时哀叹不能灵肉交融的爱情,可以充分享用美食,享受悠闲的生活;同时,他又神牵故土。还是从祖国来的比尔看出了杰克的问题所在:“你是一个侨民,一个流亡者……一个人只要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就再也写不出任何值得出版的东西来了……你已经失去了跟土地的联系。”(p.67) 比尔一语中的,击中了杰克的要害,道出了故土在自我确认中的重要作用。杰克们虽然纵情享乐,内心却空虚茫然得无以复加,一如海明威在题记引用的那节圣经,虽然短短几句话,却让《传道书》浓重的虚空悲伤即刻弥散开来,笼罩了全书。因为太阳急归的“所出之地”作为文化的空间载体拥有我们,界定了我们,是我们的位置所在。“我们成了我们想逃避的体制的一部分,于是这个体制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战胜了我们。”(考利,1996:11)在放纵和游荡背后,杰克们内心深藏的其实是跨越空间后自我迷失和无法确认的焦虑和恐惧,海明威主旨性的题记显示杰克们心灵追求的徒劳和无从着落的悲伤。
对杰克们的塑造表现了海明威作为上世纪20年代过渡性“迷惘的一代”亲历者和书写者的深刻洞察,可谓与文艺理论家乔治·卢卡奇殊途同归。后者在其更早的《小说理论》(1916)中将现代社会状况总结为“身体和心灵的永远流放”(p.41),认为在这个“为上帝抛弃的世界”里,“人们孤独寂寞,只能在自己的心里寻找意义和存在,而心却无所归依”(p.103)。海明威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努力追求,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逃不脱虚空的网罗,显示了人类命运的悲哀。杰克不是海明威的硬汉,他自怨自艾,沉湎于伤痛,想念故土却不能回家。虽然比尔让杰克掩藏伤痛,然而,说易行难,他们始终是巴黎的过客,是脱离母体文化的“无根之木”,是异域社会的无名之士,只会招致大街上、咖啡馆里人们诧异的眼光。流放者无法确认的自我和局外人的身份也许是行走在路上的杰克们不得开怀的重要原因。
三、消费之旅
《太阳》出版后受到欢迎不仅在于它切中了战后普遍的幻灭情绪,还在于表现了读者乐见的消费时尚。杰克们来到巴黎的重要目的就是能够不受约束享用美酒佳肴,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到巴黎去消费,去大把花钱的。跟随杰克们的脚步,我们看到了上世纪20年代正在兴起的休闲风尚。小说映入眼帘的是“大马路”饭店、“凡尔赛”和“雅士”咖啡馆等时髦消费场所,还有挤满了来自俄亥俄达顿朝圣的天主教徒和从蒙大拿来旅游的中产家庭的火车和海滨度假胜地。杰克们穿梭于斯特拉斯堡、布鲁日、阿登高地等度假胜地,欣赏到的是“这才叫乡野”(p.88)的怡人美景,在巴黎高雅时尚的街道转悠。杰克们在街上游逛、在橱窗外打量的形象让人想起文学传统中巴黎的“游手好闲者(flâneur)”(克朗,2003:68-70)和“人群中的人” (本雅明,1989:66-72)——身份不明地迷失在人群里享受人群中的孤独。杰克“游手好闲者”样的打量和悠闲既显示了他局外人的身份状态,也显示出物质商品的诱惑,现代化生产的物质产品召唤着人们去消费享用。杰克们尽情老到地消费,知道哪家店的咖啡地道,哪家餐馆的菜式可口。他们的消费不能算是消费主义或符号化的,但至少是时尚的。
被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转型裹挟的不仅有杰克们,还有“从平原和山区进得城来”的农民们。他们进城来卖掉劳作收获的农产品,买回去成褡裢的工业日用品,他们进城来还参加潘普洛纳的奔牛节。这些农民都住在偏远的小酒店里,因为“在那些小酒店里才觉得钱能顶钱用。金钱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意味着劳作了多长时间和售出了多少蒲式耳粮食”(p.114)。农民们住进廉价的旅馆,起初还计较价钱,等到狂欢开始,就再也顾不得钱花到哪里了。城里人到乡村去,农民们到城里来,都为了消费和休闲。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现代休闲已不像古时专属于特权和富裕阶层,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和必须。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认为休闲是异化的劳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是非生产性的,但却是一种价值生产时间——区分的价值、身份地位的价值和名誉的价值”(p.176)。与富裕了来法国游玩的美国中产家庭一样,旅行也是农民们消费生产所得的一种方式。旅行休闲在这里是来年劳作的新起点,实现了现代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消费,同时也突显出它的“区分价值”。舒活了筋骨、见过了世面的农民回到家乡少不得要与邻人分享自己的见闻。
虽然杰克们到巴黎来就是要享乐的,他们不断纵饮作乐宣示自我,但是对终日沉湎于餐馆、酒馆、咖啡馆等消费场所的他们来说,劳动才具有重要的“区分价值”和积极的自我建设作用。耽于消费不仅消耗金钱和时间,还消耗自我,因为人类生活中“地理空间按照不同的方式分类,而这些方式象征着社会地位。这样一个有序的地理空间,对什么事情应该发生在什么地方做出了一系列的道德和文化判断”(克朗,2003:62)。虽然杰克等挣脱了父母和某些戒律的约束,但是内化的文化观念依然管制着他们。长期浸泡在消费场所不但没有医治好战争带给杰克们的创伤,反而消磨了意志,使得他们更加找不到方向。比尔对杰克的批评点明了消费对自我的销蚀,表达了小说对不劳动的贬抑。比尔讥诮杰克“嗜酒如命,你沉溺于性事,不能自拔。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夸夸其谈上……你成天就在各家咖啡馆里泡着”(p.86)。消沉茫然的杰克虽然嘲讽自己的工作,称工作有时是“把朋友给打发掉的最好办法”(p.8),但劳动对他确认自我有着相当明显的作用。清早上班的路上,杰克看到行人都去上班,感受到劳动的美好,“赶着去上班让人感觉生机勃勃”(p.26)。限于叙述者就是杰克本人,小说对他的劳动伦理没有明显的赞许,但在铺张的消费描绘中,小说多次简约地提及工作,显示了它对消费的暧昧。杰克在消费和劳动间的游移显示出他在现代商业享乐文化中对传统劳动伦理的保留。
大规模的旅行和大手笔的消费终究是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的。杰克们尽管纵情享受,但是消费时尚提醒他们的是经济上捉襟见肘。不论在巴黎还是在西班牙,旅行和消费是杰克们的生活方式,钱的香味弥漫在小说中。除了杰克做着新闻记者的工作外,其他人都终日过着寄生虫的生活。但做记者挣来的钱并不能完全支撑杰克长期佳肴美酒加咖啡、慷慨给小费的生活方式,他还要靠家里寄来的坚挺美元维持生活;科恩依靠母亲寄来的支票过活,破产了的迈克尔借债度日,因为债务甚至与合伙人大打出手,布蕾特则消费各色男人。因此,杰克坚持不懈地要使他的钱花得有所值。“享受生活就是要学会如何把钱花得值,而且花得值的时候要懂得享受。”(p.111) 这不仅是他的“人生哲学”,更是那个时代的生活理念。依靠借债度日的迈克尔表现了历史上刚刚出现的信用消费,政府和金融机构合力怂恿人们贷款消费,但是这群人还没有完全接受大肆借款的做法,迈克尔不时赊账,却也记挂着要“拆东墙补西墙”。在比尔再三劝阻下,连街边一只“狗狗标本”都不敢随便购买的杰克时时被账户上的余额警醒着。这也许是他们不开怀的另一重隐秘。
四、文化之旅
在《太阳》中,占篇幅最多、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当然是到西班牙观看潘普洛纳奔牛节的旅行。以杰克们为代表的大众旅行伴随社会的转型而兴起,使得文化产品和服务处于流动状态,为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提供了平台。“旅游成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含义源自‘他者’……由于‘他者’变化不定,旅行的含义也常常飘忽不定。”(Rojek & Urry,1997:1)旅行者(及其携带的文化)与目的地的人们(和文化)往往相互凝视(gaze),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文化差异而显示出不同的微妙差别。不同于帝国公民到殖民地旅行时对当地居民(和文化)居高临下的蔑视性凝视,杰克和比尔在布尔格特钓鱼时与巴斯克人轮番共饮皮酒袋里的酒、到潘普洛纳观看斗牛时与市民和其他游客狂欢是游客和东道主平等的互动,是友好的交流。打出“葡萄酒万岁!外国人万岁!”标语的本地人敞开胸怀迎接杰克等外地人、外国人,来到潘普洛纳的杰克们也对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大感兴趣,主宾相互打量对方。杰克执意要买到西班牙传统的盛酒皮袋子,过把农民们“滋酒”的瘾。女人们盯着布蕾特现代的发型和装束看,开幕式上把她圈到跳舞的圆圈里,簇拥着杰克和布蕾特到酒馆喝酒,给她戴上大蒜头“花环”。可以看出,旅行带来的文化交流具有细致和全方位的特点,是促进现代社会变化和文化迁移的重要动因,昭示了后现代大众旅行文化的兴起。
应该说,杰克等人与当地人的群体交流处在比较浅表的层次上,他们与斗牛士罗梅罗等人的亲密接触才真正提供了深入关照异域文化和自我的机会。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中,双方都有了反观自己的“他者”,看到了平常忽略的自我。在观看斗牛的过程中,杰克和罗梅罗形成相互凝视的状态。斗牛,对杰克来说,有着既定的规则,是展示雄性力量、治疗创伤的重要文化活动,与平日耽于享乐、找不到方向的自我形成鲜明的对照。杰克因为斗牛士的果敢和阳刚而狂热喜爱斗牛活动,因而对具有“直接、纯粹和自然”技艺的罗梅罗产生了由衷的认同,观看斗牛使他忘记了痛苦,获得了暂时的救赎;而罗梅罗也知道这些外国朋友在热切关注自己,因此更加全心投入,让自己的一举一动主导杰克们的凝视,展现杰出的斗牛文化。双方在这“凝视”中都享受到身心的欢愉。
这次西班牙观看斗牛的旅行还给布蕾特与罗梅罗相互凝视的机会,性别差异给双方不同的视角和结果。布蕾特初次见到罗梅罗就叹服于他英气逼人,气质高贵,等她欣赏完他精湛的斗牛表演就更加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位比她小十几岁的斗牛士;罗梅罗则喜爱布蕾特的漂亮和现代,他们两人都深受对方吸引。罗梅罗是西班牙斗牛士传统男性文化的代表,布蕾特则是时尚的现代“新潮女郎(flapper)”,虽然为了爱情,他们做出了私奔的努力,但是双方都无法为了对方彻底改变自己,他们的爱情注定要无果而终。从罗梅罗方面看,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或源自对漂亮女士的爱恋,他下意识地崇尚外国文化,喜欢说英语,但他懂得“一个斗牛士竟然讲英语……他们会很不喜欢。斗牛士不该是这个样子”(p.140)。因为斗牛这部“悲剧三幕曲”(Wagner-Martin,2007:9)不是斗牛士的独角戏,而是在仪式、执矛手和投镖手的帮助下,在场上狂热的欢呼声中完成它最华彩的乐章,斗牛士与助手之间的默契配合、万众的瞩目与喝彩对斗牛士的成功至关重要。罗梅罗深刻地了解他不仅属于自己。同时,他对布蕾特的爱情避免不了传统男性的占有思想。罗梅罗觉得和布蕾特待在一起丢脸,但又想确保“(她)永远不撇下他”(p.184)。从布蕾特方面看,她与罗梅罗分手后似乎坦率地道出了心声:“我不想做一个糟蹋小孩子的坏女人!”(ibid.)实际上,她的放弃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他俩之间存在的不仅是年龄上的巨大差距,更重要的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性别观念鸿沟。布蕾特一方面热爱罗梅罗富有阳刚魅力的身体,另一方面遭受过传统婚姻伤害的她害怕在男权力量面前再一次丧失自我。“他想让我把头发留起来。我,留个长头发,那会是副什么德性。”(ibid.)罗梅罗被庆祝的人群抬举出斗牛场时无奈的眼神和布蕾特将罗梅罗献给她的胜利牛耳包起来塞到床头抽屉最里边为他们的爱情结局作了最好的注脚。罗梅罗与布蕾特爱情的失败在于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
杰克们的西班牙之行有片刻的欢愉放松,也有文化触摸和碰撞的失败,潘普洛纳之旅并不完全尽兴。小说结尾的那一幕非常引人注目:“‘哦,杰克,’布蕾特说,‘我们如果在一起,一定能过得开心死了。’”(p.188)这里布蕾特用的是虚拟语气,得到杰克解救的她此时虽然如释重负,但已完全没有了当初筹划西班牙之旅时高叫“这该有多棒啊!……我们得玩个痛快!”(p.63)的欢欣雀跃,而杰克的回答:“这么想想不也挺好吗?”(p.188)依然沉重,他简约的回答与题记弥散的悲伤和空虚形成了回响和呼应。旅行虽然不尽完美,生活总有缺憾,但还要继续,“太阳(会)照样升起”。倒是小说出版后,文学作品的旅行结出了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硕果。《太阳》获得了读者的热烈追捧,再加上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名人效应的推波助澜,之前仅为地区性活动的潘普洛纳奔牛节由于蜂拥而至的游客已成为世界性旅游圣地。当地政府为纪念海明威,特地在斗牛场门口塑立了一尊他的雕像。《太阳》在此意义上无疑是迈克·克朗所谓“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p.55)的最佳典范。
五、结语
离开日常生活的家园,人们摆脱日常陈规的限制去追寻自我和精神生活是西方文化的悠久传统,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宗教的朝圣。像海斯特到树林里寻求心灵的平静和宗教的救赎一样,杰克们通过旅行医治战争创伤、摆脱社会禁锢的自由,但除了战争带给他们的身心伤害,旅居生活造成“两不靠”的阈限状态、经济的制约、传统与现代不同观念这些文化因素随着时间的迁移是造成他们“迷惘”不可忽略的因素,忧伤如影随形,漂泊和探索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迷茫。在这部被菲茨杰拉德称为一个女人和五个男人的“罗曼司”和“旅行指南”(Aldridge,2007:123)中,《太阳》描画了正在兴起的现代社会消闲时尚,像庞贝城一样凝固了时代的风貌。庞德曰:“文学是历久弥新的新闻。(Literature is news that stays news.)”出版了近一个世纪的《太阳照样升起》在今天读来却毫无时代的隔膜,好像记述了几天前一群旅行达人的巴黎和西班牙之旅,依然时尚。
注释:
① 关于“阈限”概念的阐述,详见维克多 ·特纳的《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p.96-104。
[1]Aldridge, J. W. Afterthoughts on the Twenties and The Sun Also Rises[A]. In L. Wagner-Martin (ed.) New Essays on The Sun Also Rises[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Decker, W. M. Americans in Europe from Henry James to the Present[A]. In a.Bendixen & J. Hamera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Travel Writing[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3]Field, a.N. Expatriate Lifestyle as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Sun Also Rises and Experiential Travelogues of the Twenties[J]. The Hemingway Review,2006, (2):29-43.
[4]Lukács, G. The Theory of the Novel[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4.
[5]Rojek, c.& J. Urry. Touring Cultures: Transformations of Travel and Theory[M]. London: Routledge, 1997.
[6]Wagner-Martin, L. Introduction[A]. In L. Wagner-Martin (ed.) New Essays on The Sun Also Rises[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贝克.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M].林基海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8]厄内斯特·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M].冯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9]李长亭.《太阳照常升起》中的“菲勒斯”情结 [J].外国文学研究,2011,(2):106-113.
[10]马尔科姆·考利. 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M].张承谟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11]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3]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4]沃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
[15]于冬云.20世纪20年代美国商业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悖论——重读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J].外国文学评论,2005, (3):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