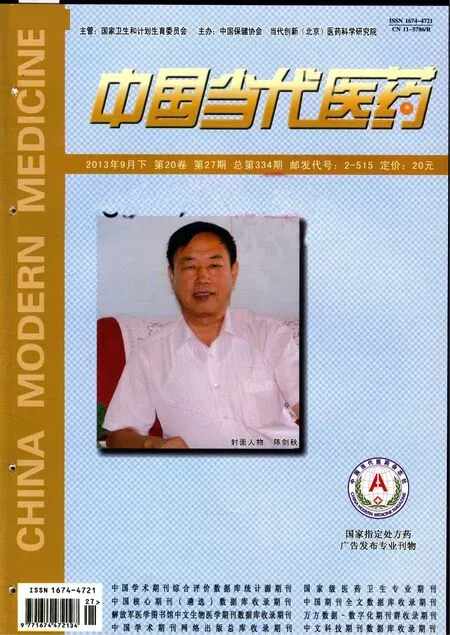患者家属角色转变后的心理分析及应对措施
刘虎子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医务科,太原 030024
医患关系是医疗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1],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几乎是每个医院都不可回避的问题,究其原因,很多是由于医患沟通不到位所致。医患沟通是减少医患矛盾,缓和矛盾激化程度的有效途径之一[2]。作为医务人员,因为出于保护性医疗策略的需要[3],医务人员更多的是在和患者家属沟通,所以与患者家属的沟通是否到位,决定了医患沟通的成功与否,要做好有效的医患沟通必须了解患者家属的心理。目前医学模式正在面临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4]。作为医务人员,掌握患者家属的角色转变后的心理情况非常重要。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只有充分地了解并理解患者家属的心理,才能主动有效地应对,从而化解、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1 患者家属角色转变后面临的心理情况
1.1 陌生环境适应
无论患者家属原来从事什么工作,到了医院后肯定会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患者家属。昨天在公司指点江山,今天到医院面临病痛的家人;上午在庄稼地挥汗如雨,下午到医院跑前跑后,伺候患者。身份的改变必然带来心理的变化,很多人不能马上适应这个陌生的新环境赋予的新身份,适应的过程因人而异,但无论谁都必然面临着这样一个适应过程。
1.2 多重身份转换
患者从发病到入院,患者家属刚开始可能由于沉浸在病痛中,无暇顾及其他,全心全意照顾患者,但是“患者家属”只是患者家属的一个临时身份,应当说,所有的患者家属都是多重身份或角色的扮演者,其在生活中是工人、农民、学生、商人、职员等不同的身份,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在医院停留时间的延长,本身固定的角色无法分身、分力兼顾时,如无法正常经商、种地、上班等,尤其是由此带来损失或不利时,心态就会失衡。是照顾患者,还是做好生意、上好班、种好地等,矛盾出现,但无法解决时,会出现应激障碍等问题,势必带来心理上的转变。“久病床前无孝子”,大概就是出于此。
1.3 知识需求增加
医学是一门专业学科,一名医学生经过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以及多年临床工作,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也不能穷尽其知识,而患者家属更是需要面对这门陌生的学科,所以,当患者家属面对诸多医学问题时,往往一片茫然。事实上,患者家属的一个签字就决定患者的手术做不做、药物用不用,甚至是生与死。扪心自问,就是一名医生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都是非常困难的,患者家属更是如此。在实际生活中,很多的患者家属从来都是在扮演服从者的角色,而不是决策者,面对从未见过的问题,要其决定患者的出路,而且是人命关天的决定,谈何容易。同时,个别医务人员在与患方沟通中没有做到充分的告知、沟通,导致患方未能从医方获得足够的关于自身疾病的资料,而是通过其他渠道,如熟人(可能是医务人员)、网络等,这样获得的知识往往是片面的,一旦与医务人员的解释有出入,势必增加对医方的不信任。
1.4 经济因素压迫
患者家属本来辛辛苦苦攒了一笔钱,准备给孩子上学或买房或买车,或者它用,往往没有考虑到看病使用,事实上,很少有人提前留出钱作为看病使用,而患者生病又很突然,因此患者一生病,计划完全被打乱。目前各种费用合理或不合理地增长,疾病复杂危重程度加大,医疗费用相对比较高,补偿机制又不是很完善,有的患者家属甚至把钱花光还不够,还需要找人去借,甚至借不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疗技术局限、患者的病情因素,可能钱花了,人没了,人财两空,患者家属往往是难以接受的。
1.5 惯性思维使然
由于“医生收红包、医生不负责”等关于医疗纠纷的负面新闻屡见报道,宣传医院的不好,夸大医院的不足,造成了患者家属对医院的不信任,防范甚至与之对立,加之有些医务人员工作确实不到位,长此以往,患者家属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存在严重的质疑心理,对医务人员不信任。2012年6月5日江西省高安市人民医院骨科某医师因拒收患者家属红包被打就是显著的例子[5]。
1.6 消费医学心理
很多人把看病就医作为一种商品消费,认为诊疗和购物一样,钱花了,就应当得到结果,而且是好的结果。实际上,看病就医与商品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医学是个不完善的学科,它永远跟在疾病的身后,注定了它的滞后,注定了它的局限与由之而来的风险。医学是一把双刃剑,在治病的同时又造成新的损伤、副作用乃至死亡,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道理。医学研究的是复杂的、存在许多未知信息的人,而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很大,经常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6]。
1.7 闹则有钱的诱惑
许多各种媒体的负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教唆”作用,致使发生医患纠纷后,部分患者家属不采取合法的途径,而是通过辱骂、动手打人、设灵堂、放哀乐、聚众闹事甚至砍杀等手段来进行处理,有的人甚至陈尸医院,以刚刚死去的亲人为筹码,给医方施加压力,索要赔偿。医院有钱,大闹多得,小闹少得,不闹不得,成了“共识”。 从处理纠纷的多起案例来看,许多平时看似忠厚老实的人,一旦卷入医疗纠纷,可以说是“原形毕露”,逐利本质马上暴露,与以往判若两人,全然无患者死亡后的伤心。
1.8 维权意识增加
21世纪,中国进入了权力意识高涨的时代。“在一个权利意识复苏和人权观念加强的时代,必然是诉讼的时代和对医师较少宽容的时代[7]。”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进一步健全,信息化的推进,患者的维权意识不断加强,但是由于目前法制正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加之其他各种因素,患者家属维权的手段不是法律武器,而是采取极端或原始的方法,形成各种各样的不良事件。
2 患者家属角色转变后心理情况改变的原因
患者家属心理情况的改变其实是由于角色改变引起的,它必然带来心理或行动上的变化。“角色”一词源于戏剧,自1934年米德首先运用角色的概念说明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份及其行为以后,角色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中。社会学对角色的定义是“与社会地位相一致的社会限度的特征和期望的集合体”。角色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具体的个人,其本质上反映一种社会关系,具体的个人是一定角色的扮演者。现实生活中,人们以不同的社会角色参加活动,这种因角色不同而引起的心理或行为的变化被称为角色效应。
由于每个人的教育背景、文化程度、职业分工、脾气性格、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不同,导致需要扮演一个新角色的时候,每个人的表现千差万别,对待同一件事情的处理和应对能力各不相同,结果也大相径庭。没有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每个人就会无序发展,更多的是去效仿,这时候,就需要进行干预,积极应对。
3 医务人员对患者家属角色转变后的应对措施
人的角色的形成首先建立在社会和他人对角色的期待,从角色认知的形成到角色行为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帮助和教育患者家属完成这一转化过程,是医务人员的职责。医务人员要把向患者家属灌输医学知识转换为引导,要主动合作。
医患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医患双方均为角色的扮演者,医务人员由于职业的关系,已经适应了自己所担任的角色,而对患者家属而言,犹如一个“刚入行的演员”,需要医务人员作为“老演员”、“导演”去引导或教导,其才能扮好自己的角色,互相配合,互相理解,共同演好“一出好戏”。要想演好这场戏,最大的需要就是换位思考。
3.1 医务人员要站在患者家属的角度考虑问题
医务人员要站在患者家属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也就是通常说的“同理心”。同理心,也称同感心、共情等,是指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感受他人的情绪和处境,并能正确理解以及不加任何评论地将这种了解传达给对方,它可以通过后天培训,加强认知结构及行为表现,从而使同理心成为一种人际沟通技巧[8]。“如果我是患者家属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应当时刻去扪心自问。
医务人员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沟通能力,快速识别各种状况,充分地调查了解患者家属的情况,如身份地位、经济能力、社会关系等。只有较全面地了解患者家属,医务人员才能在与患者沟通时,也就是角色扮演时,针对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期望值的人群,作出不同的应对方法。
医务人员在沟通过程中需要将患者的相关情况充分地向患者家属说明,绝大部分患者家属没有医学知识或者只有片面的知识,医务人员又无法改变患者家属的身份属性和接受能力,其给患者家属讲解的都是医学知识,这就注定沟通不成功,所以设身处地为患者家属思考,根据其期望获得的信息或结果主动作出反应,跟着患者家属思路走的同时也带着他们的思路走,形式上的被动,实际上的主动,掌控沟通的全程,充分交流互换信息,让患者家属感到医务人员是在为他着想,这样即使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后果,也会得到充分地理解。
《医患沟通制度》为医院的核心制度之一,因此沟通是医务人员的工作,是医务人员应尽的义务,医务人员要意识到,沟通与给患者采取具体的医疗行为同样重要,要保证充足的时间进行沟通。目前,由于国内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导致三甲医院人员聚集,每个专家半天接诊量都在30~40人,部分专家甚至超过50人[9],也是导致医患沟通不到位的因素,因而,医务人员必须合理地收治患者,量力而行,设法保证沟通的时间,充足的沟通时间是沟通成功的保证。
3.2 患者家属要站在医务人员的角度考虑问题
一部精彩的演出,需要角色之间的配合,同样,一次成功的医患沟通,也需要双方的理解,医务人员理解患者家属,同样,也需要患者家属理解医务人员。医患纠纷形成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患者家属对医务人员不理解所致。
如何让患者家属对医务人员了解并理解呢?如何让患者家属站在医务人员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呢?需要让患者家属换位思考。
医务人员无法改变患者家属,必须充分利用沟通技巧,让患者家属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是医生怎么办”,让患者家属充分了解并理解医务人员,理解医学的局限性,诊疗技术的风险性,疗效的不可预测性等,充分了解医务人员的想法,让患者家属理解医务人员的职业精神和牺牲精神,无论面对何种疾病,面对何种患者都会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偏袒[10]。医患双方是在一条船上,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患者,为了缓解、减轻、治愈病痛,医患双方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作的。让患者家属产生同理心,理解医务人员,理解疾病,理解医学。
胥志华等[11]认为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是导致双方关系失谐的关键因素,而信任危机又源于彼此沟通不畅,相互间缺乏尊重与理解,再加上现在医疗纠纷增多,医生和患者之间本来是一对默契的同疾病作斗争的战友,现在增加了很多不信任的因素,必然影响医患之间坦诚的沟通。医务人员要通过医患沟通,充分取得患者家属的信任,让患者家属站在医务人员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为了规避风险而过多地强调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要坦诚地沟通,实事求是地沟通,医患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而不是互相仇视的对手,风险是共当的,目标是一致的。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构建和谐社会又离不开和谐的医患关系[12],处理医患关系需要良好的沟通。想要避免或化解医疗纠纷,就要求医务人员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更多的人文知识,必须及时地补上心理学这一课,充分掌握患者家属角色转变后的心理变化,并加以分析,作好应对准备,充分地沟通,充分地互信,从而减少甚至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1]尹秀云.医患关系认识中的两个误区和伦理分析[J].医院管理论坛,2005,22(2):37-39.
[2]李晓东.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医患关系[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0,6(86):147.
[3] 李冬.谨慎用保护性医疗策略[J].中国医院院长,2012,(10):76-77.
[4]李鲁.社会医学[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6-30.
[5]沈洋,高皓亮,刘彬.江西:医生拒收红包被打医患关系再遭拷问[EB/OL].http://www.zhongguowangshi.com/web/Detail.aspx?id=128046,2012-07-30.
[6] 刘虎子.医患关系现状分析[J].中外健康文摘,2013,10(19):16-17.
[7]李国炜.瑞典病人保险制度述评[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0(1):24.
[8]侯文红,高娜.同理心应用于临床护理工作的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2005,19(9):1700-1701.
[9]中消协新闻发言人.患者就医是消费行为[N].法制日报,2000-03-16(3).
[10]武惠庭.医患和谐需要“双向道德规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0(6):39-41.
[11]胥志华,蒋淑媛,罗邦群,等.浅谈医患沟通[J].现代医药卫生杂志,2007,23(4):617-618.
[12]卢仲毅.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J].医院管理,2006,1(35):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