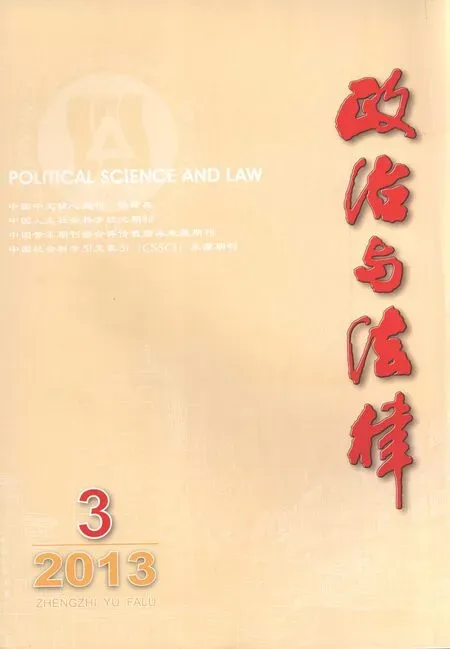法条竞合视野下渎职类犯罪罪名的适用研究*——兼论“两高”《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的理解适用
王 强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从原刑法时期的反革命破坏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和玩忽职守罪,到现行刑法中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刑法中“口袋罪”的遗传基因并未消亡。这些罪名中的空白罪状、罪量要素、兜底条款,不仅是研究立法明确性的重要素材,1而且也影响着司法实践对具体罪名的选择适用。刑事立法背离罪刑法定原则越远,刑事司法罪刑擅断的程度就越严重;刑法条文越模糊,司法实践就越有扩张的空间。在适用这些不明确的刑法条文时,司法实践的做法是:一方面尽量减少司法成本,另一方面尽量增大社会保护的功效。这种增大社会保护功效的做法使得这些罪名不仅变成了“口袋罪”,也变成了刑罚过剩的“恶罪”。2
一个罪名之所以成为口袋罪,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条文规定的模糊性,二是司法实践的曲解。正是由于刑法条文存在着空白罪状与弹性条款相结合的先天缺陷,在越权司法解释和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共同作用下,非法经营等罪从扩张走向变异,背离了刑法规定的原旨,逐渐变成笼罩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口袋罪”。3仅仅是条文字面的含糊并不足以导致口袋罪的出现,是否成为口袋罪的关键在于司法中如何理解“其他”的范围,如何信守罪刑法定原则,如何根据条文的内在涵义和逻辑进行解释。4因此,限制罪名的盲目扩张,预防其口袋化异变,当务之急是刑法解释学层面的努力。一方面,通过体系解释,善用同类解释规则,明确兜底条款(罪名)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妥善处置兜底罪名与相关罪名之间的竞合关系,对符合其他犯罪的,一般排除兜底罪名的适用。对前者的讨论可谓方兴未艾;5而对后者的关注并不够。是故,笔者以渎职罪为例,结合2013年1月9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相关规定,研究在竞合条件下作为兜底罪名的普通渎职罪即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之适用规则,以求严格限制和规范兜底罪名的选择适用。
一、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是法条竞合关系
一般认为,作为渎职罪一般条文(罪名)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与刑法第398条至第419条规定的各特殊渎职罪之间,系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之法条竞合特别关系。但也不乏想象竞合的主张,6甚至有学者主张不必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提倡一种“大竞合论”,但凡构成要件之间存在竞合关系,一律从一重处罚即可。7“从一重处断”系我国刑法理论公认的想象竞合处置原则,将所有竞合关系均从一重定罪处罚,实际上是完全否定法条竞合概念、所有竞合皆想象竞合的主张。但这种观点不仅承继了传统刑法理论有关想象竞合属性的误读,更抹杀了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二者不同的构造特征。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是源自大陆法系刑法的理论。从竞合论的视野,法条竞合是与作为纯正(真正)竞合的想象竞合相区别的不纯正(非真正)的竞合。之所以是不纯正的竞合,是因为法条竞合看似有数个构成要件可资适用,但事实上犯罪行为的不法内容和罪责内容只要适用其中一个构成要件,即足以全部包涵,基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排斥其他构成要件的适用,被排除的法律并不出现在有罪判决中;想象竞合则是一行为触犯数个刑法法规或数次触犯同一法规。同种类想象竞合,有罪判决必须表明数次触犯同一个刑法法规(“A因谋杀三人被科处终身自由刑”);不同种想象竞合,必须将所有同时被触犯的刑法法规一一列出(“A因犯强奸罪和重伤害被科处3年自由刑”)。之所以需要一一列出,是因为刑法的全部不法内容产生于所有被适用的刑法法规本身。简言之,想象竞合之一行为触犯了数个刑法法规,必须同时宣告数罪、适用数个构成要件,方能完整评价其不法全貌。8从罪数论的视野,法条竞合被认为是单纯一罪或者评价一罪。但不论单纯一罪还是评价一罪,都系本来的一罪,即犯罪成立上的一罪,被评价为该当一次构成要件之事实;想象竞合则是处断的一罪,即实体法上认定构成数罪、实质性的符合数个构成要件,只是科刑上以一罪处理。9
可见,不论是从竞合论还是罪数论的立场,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在构成上都存在本质区别:法条竞合是一行为该当一个犯罪构成(疑似该当数个犯罪构成),成立一罪,依该罪法定刑处罚(一行为一罪一罚);想象竞合则是一行为该当数个犯罪构成,构成数罪,只是科刑上作为一罪处理(一行为数罪一罚)。就构成要件的适用而言,法条竞合的构成要件是选择适用,而想象竞合可称为构成要件的累计适用,即所谓“想象竞合的明白记载功能(Klarstel lungsfunktion)”。10明白记载功能,就是要求对于想象竞合必须在判决中同时援引数个犯罪构成(条文),宣告成立数罪。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只是法定刑的从一重,而并非罪名的从一重,因此应该是论以数个罪名中最重罪名的法定刑,宣告行为人所应科处的刑罚,轻罪和重罪的条文均应出现在判决主文中全部加以引用。11这种法律评价、罪名宣告上的差异,正是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处置方面的重大区别。我国刑法理论常将想象竞合视为实质一罪(而非处断一罪),将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理解为按照法定刑最重之罪定罪处刑。这种观点忽视了想象竞合侵犯数法益、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数罪特征,误解了“从一重处断”真义,抹煞了想象竞合的“明白记载功能”。也正是在这种误解基础之上,才催生了“大竞合”的错误主张。12
综上,确有必要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那么,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之间究竟系哪种竞合关系?这涉及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标准。在笔者看来,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法条之间的包含或者交叉关系,仅仅是形式要件,甚至仅仅是法条竞合所涉及的数法条之间关系的表象而已。是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实际上依然是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判断问题:充分评价和禁止重复评价是判断准则,法益侵害则是判断的实质标准。一方面,当一行为侵犯的法益,非某一个犯罪构成能够完全评价时,就应当适用复数犯罪构成、宣告数罪,唯此方能充分完整地评价其不法全貌。只因是一个行为,故在评价上,仅能为单一不可分割的可罚性评价,其基本性质固属单一,但绝非犯罪单数,只是可罚性及法律效果的单数,此即想象竞合。另一方面,当一行为侵犯之法益,在刑法中存在两个以上为保护该同一法益而设立之数个犯罪构成可资适用时,就只能择一适用其中最能反映行为不法全貌的犯罪构成,而不能同时适用,否则即是被禁止的重复评价,此即法条竞合。可见,区分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实质要件是法益的同一性判断。
据此,在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与各特殊渎职罪之间,法条形式上的包容关系一目了然,而渎职罪实质上也都是以“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执行以及国民对此的信赖”13作为法益内容。当行为人之单一行为同时符合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的构成要件时,不能同时宣告数罪,否则定是对同一法益侵害事实的重复评价,而只能选择其中最能完整充分评价其行为不法全貌的犯罪构成。因此,作为普通渎职罪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与各特殊渎职罪之间是典型的法条竞合特别关系。刑法第397条“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之规定,正是关于法条竞合特别关系处罚原则的重申。正因如此,《解释》第2条第1款亦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犯罪行为,触犯刑法分则第九章第398条至第419条规定的,依照该规定定罪处罚。”
由此总结规则之一: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之间系法条竞合特别关系,当一行为同时符合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犯罪构成时,应当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以特别法条定罪处罚,不适用重法优先,14更不可认定为想象竞合。
二、罪体要素影响下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的选择适用
在定性为法条竞合关系的前提下,当行为同时符合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犯罪构成时,以特别法条定罪处罚,并无太大争议。不过,倘若具体的渎职行为不符合刑法第398条至第419条的特别规定,但却符合刑法397条普通规定时,能否适用第397条认定为普通渎职罪?《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因不具备徇私舞弊等情形,不符合刑法分则第九章第三百九十八条至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但依法构成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犯罪的,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对此又当如何理解?则确有争议。
周光权教授曾举例如下:合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5000元,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2000元15,对利用合同或者信用卡实施诈骗,犯罪人就想获取4000元,事实上也只得到4000元的行为,能否以诈骗罪论处?针对这一设例,他指出:“特别法条构成要件的类型化规定对于评价客体所做的选择,当然排斥普通法条的适用,既然普通法条的适用效力因为特别法条不再存在,按照特别法条不能成立犯罪的情形,当然不能以一般法条定罪。”16但这一结论遭到张明楷教授的反对,17并且就本文上一段提到的有关渎职罪的法条竞合问题的处理上,也将周光权教授的主张作为反面立场加以批判。18
在笔者看来,张明楷教授的批评意见中,可能存在误解周光权教授观点的嫌疑。无论是从周光权教授的前述设例、他这篇论文的内容提要中“对于行为性质符合特别关系的构成特征,但因数额、数量未达到特别法条要求时,不能以普通法条定罪”的结论概括,还是此文对“定型化的构成要件观念”的特别强调,都可以看出,此文上述主张是以“行为类型、性质已经符合特别法条的行为定型,只是行为(结果)程度尚未达到特别法条的罪量要求(但已达到普通法条罪量要求)”这一“中国式”法条竞合问题为前提的。而在张明楷教授的反驳意见中,存在一些突破这一前提基础的情状。例如,张明楷教授在批评周光权教授混淆了“不符合特别法条”与“根据特别法条不值得处罚”这两种现象时指出:“况且,根据特别法条不值得处罚并不等同根据普通法条不值得处罚。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非法拘禁的人或者其亲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他人的举报时,而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不符合第416条的规定(特别法条),但这种行为并不属于‘根据特别法条不值得处罚’的行为,相反,必须适用普通法条(第397条)。”在批评周光权教授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方法也存在疑问时,他举例:“当行为人以假币换取他人真币时,不能认为唯一的结论就是‘以假币换取真币’,相反,完全可能是盗窃、诈骗或者使用假币。换言之,当行为人不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时,就不能认为该行为不可罚;相反,要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盗窃罪、诈骗罪、使用假币罪的构成要件。”19显然,这些例证均属于行为性质并不符合特别法条之行为类型定型,但却完全符合普通法条之行为类型化描述,因而得以普通法条论处的情状。而这已偏离了周光权教授立论的前提——罪量要素影响下的中国式竞合问题。
事实上,因为行为类型不符合特别法条的情状,而以普通法条论处,这种观点周光权教授并不否定。在分析刑法第149条第1款的规定时,周教授指出,刑法第149条第1款关于行为在不构成刑法第141条至第148条之罪时,依照刑法第140条定罪的规定,主要是关于特别法条的构成要件(类型化)观念的重要性的强调。这里的不构成各该条,是因为行为类型不符合,而不仅仅是数额的问题。在生产、销售特殊的伪劣产品犯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行为定型上不同时,对于行为不符合特别法条,但符合普通法条的情形,不适用特别法条而适用普通法条,即便刑法第149条第1款不作规定,亦应如此处理。所以,特别法条对普通法条的适用没有制约。这与前述的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这种数额犯在行为定型上基本相同,特别法条不处罚时,不能适用普通法条的关系有重大区别。20在另一论文中,周教授也指出,根据法条竞合的法理,某种行为虽不构成特殊渎职犯罪,但是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滥用职权罪。21
由此可见,因为行为类型、行为性质不符合特别法条的行为定型,而转以普通法条论处,在这种因犯罪构成罪体要素而引发的法条竞合问题的处理上,张、周二教授的观点实际上是相同的。在渎职罪视野下,张明楷教授“行为主体虽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不符合刑法第398条至第419条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其行为符合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应当适用刑法第397条定罪量刑”的结论,和“行为主体具备刑法第398条至第419条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特殊身份,但行为方式不符合刑法第398条至第419条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构成要件,却符合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刑法第397条定罪量刑”的结论,22以及前述“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并非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而是滥用职权导致森林遭受严重破坏”、“司法工作人员不解救被非法拘禁的人,造成严重后果”等应认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处理意见,同样也是他认为持相反观点的周光权教授所认可的。
特别法条原本就是在普通法条基本构成要件的基础上,通过主体、对象、行为方式等要素的具体化、特别化,而形成的变体构成要件。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属于种概念与属概念、下位概念与上位概念的关系,特别法条构成要件的实现,必然包含普通法条的构成要件的实现。23只要特别法条不属于刑法为限制处罚范围而设立的封闭特权条款,当行为不符合特别法条行为类型时,就应当转而考虑普通法条行为类型的该当性。这既是符合法条竞合一般法理的当然结论,也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作为渎职罪一般条款、兜底条文的性质相匹配。可见,对于《解释》第2条第2款之规定,倘若是因罪体、行为性质(类型)要素不具备,而导致“不符合特别渎职罪之规定,符合普通渎职罪时转以普通渎职罪论处”时,此结论完全是符合法理的当然解释。
由此得出规则之二: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因主体身份、行为方式、行为对象等犯罪构成罪体(行为性质)要素而不符合特殊渎职罪的构成时,不可直接宣告无罪,而应当转而考虑其行为是否该当普通渎职罪的构成要件,若是,则应以普通渎职罪论处。
三、罪量要素影响下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的选择适用
在大陆法系刑法“仅定性”的行为类型立法模式之下,法条竞合问题就止于罪体要素引发的竞合关系的处理;但在我国“定性+定量”的“行为类型+行为程度”的刑事立法模式下,因罪量要素引发的竞合问题的处理就成为特有的“中国式竞合”问题。
在我国刑法视野之下,行为类型呈现包含关系的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之间,立法或司法解释有时候会确立不同的犯罪成立罪量标准,如前文提到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之间;再如渎职罪中,第403条滥用管理公司、证劵职权罪之“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立案标准》)第13条]与第397条滥用职权罪之“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解释》第1条);第408条环境监管失职罪之“导致3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与第397条玩忽职守罪的“导致20人以上严重中毒”(《立案标准》第19条、第1条)。这种情状下,若行为人以符合特别法条行为定型的方式实施行为,而实际罪量却未达到司法解释所确立的特别法条罪量标准,但又超出普通法条罪量标准时,能否转以普通法条论处?即《解释》第2条第2款中“因不具备徇私舞弊等情形”之“等情形”能否包括仅罪量要素不具备这一情形?此问题,才是上述张、周二位教授的观点真正的对立面。
笔者认为,考虑到罪量要素与罪体要素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对上述情形同样“转以普通法论处”有欠妥当。
其一,法条竞合原本就是在刑罚统一制裁体系、个罪仅定性的行为类型(罪体)的立法模式下的舶来品,在这一背景之下,法条竞合理论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构成要件、行为类型,但却无法体现行为程度的罪量要求。因为与罪体要素乃“横向、此罪彼罪的行为类型意义上作为区分标准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不同,罪量要素则是在行为类型(罪体)确定的基础上,从纵向、轻罪重罪(罪与违法)的行为程度意义上判断犯罪成立与否的构成要件要素;前者限定了公权力介入的界限,后者则是公权力处置内部分工的标准。罪体要素与罪量要素的上述差异,决定了二者在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中的位阶性,即首先通过罪体要素判断行为类型、该当构成要件的归属;然后根据罪量标准,判断行为程度,决定轻罪抑或重罪、犯罪抑或一般违法。此位阶性表明,作为行为类型判断理论的法条竞合的运用,应当在罪量判断之前完成;因罪量要素引发的“中国式”竞合问题,不能直接依照法条竞合一般原理进行处理。
其二,张明楷教授亦主张,对法定刑升格条件应区分加重犯罪构成与量刑规则,前者是刑法分则因行为、对象等构成要件要素的特殊性而使行为类型发生变化,导致违法性增加;而后者则是分则单纯以情节严重、数额巨大等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它们只是行为程度(量)的变化,违法行为类型或特征并无变化。24事实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罪体和罪量要素也同样如此。罪体要素决定了可能被作为犯罪处置的行为类型;罪量要素则只是行为程度(量)的变化,违法行为类型或特征同样不应有所变化。但依据“转以普通法条论处”的主张,因为罪量要素(行为程度)量的增减,而导致行为类型的变化,这与论者区分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立场不相一致。换言之,只要对法定刑升格条件区分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就应当承认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亦有罪体与罪量的区分。
其三,“转以普通法条论处”的另一重要论据是,在“没有章法的特别法条惟轻的立法或司法解释”前提下,转处普通法条是在司法救济立法错误,实现罪刑均衡、刑法公正的唯一手段。不过,无论这一前提论断是否为真,似乎都难以适用于渎职罪领域。1997年刑法对渎职罪的修改,主要是将1979年刑法通过以来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并针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增加规定一些具体的渎职犯罪行为。其一方面详细规定了各国家机关中可能出现的30类渎职犯罪,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符合罪刑法定的明确性要求;另一方面,保留玩忽职守罪,增设滥用职权罪,以这两罪起总体统领作用,用较为宽泛和原则性的文字将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他可能实施的渎职行为都纳入刑法调控范围,以免挂一漏万,体现了新刑法为有效打击此类犯罪所具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25可见,特殊渎职罪无非是基于明确性、分解口袋罪的考虑,将常见的某具体领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从口袋罪中独立出来,很难判断说这些特殊渎职罪相较于普通渎职罪即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所侵害的法益更多、违法性更重,属于普通构成要件的加重变体,亦即很难判断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在法益侵害、违法性上孰轻孰重。在此前提下,作为兜底条款、“小口袋罪”的普通渎职罪,与内涵更丰富、外延较狭窄的各特殊渎职罪相比,其法定刑配置幅度更宽、罪量标准确定得更广、更低。唯有如此,方能保障其兜底和补充作用的发挥。可见,“没有章法的特别法惟轻”现象未必存在于竞合的渎职罪名之间,上述论断也就缺少了立论基础。更何况,退一步讲,即便是立法、司法解释的确“没有章法”,也没有理由让行为人为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错误“埋单”。
综上,笔者不赞成转以普通法论处的主张。《解释》第2条第2款之“因不具备徇私舞弊等情形”应当限制在因罪体(行为类型)要素不具备的情形,而不应当包括仅因特别条款的罪量(行为程度)未达到的情形。
由此总结出规则之三:行为人行为性质、类型已符合特殊渎职罪构成特征(行为定型),但数额等罪量要素未达到特别法条罪量标准时,不能转以普通渎职罪论处,而应作为某特殊类型的渎职行为之一般违法处理。
需要补充的是,普通渎职罪的兜底性质,罪状的空白性、概括性,也导致其罪量标准的确定更注重普适性,即只能以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社会不良影响等一般普通事实为内容;而特别渎职罪更具体、外延更小,其罪量标准也更具针对性,如故意/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中的“秘密等级、秘密数量、泄露对象、泄露方式”等。这样,就可能引发一个问题:倘若行为性质已符合特殊渎职罪的构成特征,行为(结果)程度并未符合特别法条各具体的、叙明的罪量标准,而是达到了普通渎职罪所具体规定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不良影响等罪量要求时,应当如何处置?对此,有学者以食品监管渎职罪为例指出,倘若食品监管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没有达到食品安全的事故标准,即没有达到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案标准,则考虑普通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适用。26这种观点同样会导致罪量要素(行为程度)反制行为性质、行为类型(行为定型),值得商榷。不过,倘若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导致一定规模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结果时,都成立渎职犯罪,食品监管等领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不以犯罪论处,的确有失公允。对此,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司法解释关于特殊渎职罪的罪量标准,都存在“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之类的兜底规定,因此,只要在特殊渎职罪的各叙明、具体的罪量标准中,没有与普通渎职罪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内容和性质上相同的罪量标准条款,就可以将普通渎职罪之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叙明的罪量标准,作为特殊渎职罪罪量标准兜底条款所包含的内容,依此直接认定为某特殊渎职罪的成立。就上例而言,即便不能认定已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也可以将与普通渎职罪成立标准相当的一定规模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良影响等视为食品监管渎职罪中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直接以该罪论处。27
由此衍生规则之四:当行为性质符合特殊渎职罪的构成特征,而罪量事实与该特别法条之叙明的罪量标准均不匹配,但确符合普通渎职罪的叙明罪量标准时,可将该罪量事实视为符合该特殊渎职罪“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之兜底性罪量标准,直接以该罪论处,不再考虑普通渎职罪的适用。
另外,《解释》第1条对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罪量标准进行了调整,但未涉及其他特别渎职罪罪量标准的调整,导致的结果是,原司法解释(即《立案标准》)中原本在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中确立的某些内容相同的罪量标准,因为《解释》对普通渎职罪罪量标准的调整而变得不同。如根据《立案标准》的规定,滥用职权罪与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之立案标准均有“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玩忽职守罪与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立法标准均有“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4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7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而《解释》第1条将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罪量标准调整为“造成经济损失30万以上”、“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从而导致二罪罪量标准的差异。这种情况如何看待?是否仍适用上述罪量要素影响下的诸规则?
同一司法解释中,在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之间,如果解释者就相同性质、内容的罪量要素规定不同标准,表明解释者对特殊渎职罪特殊对待的基本立场,这也是适用上述各规则的实质理由;但倘若解释者在同一解释中,就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规定了内容完全相同的罪量标准,这表明解释者并无区别对待特殊渎职罪的观念立场,仅仅是在特殊罪名中对相同罪量标准的重申而已。因此,笔者认为,在没有关于特殊渎职罪罪量标准的新司法解释的出台、无法确定解释者观念立场是否改变的前提下,原司法解释对各罪上述罪量标准同等对待的立场应当维持。原司法解释中,在特殊渎职罪中规定的作为普通渎职罪罪量标准重申的、内容完全相同的罪量规定,也应当适用《解释》第10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即应根据普通渎职罪的罪量标准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上述情况亦不存在所谓罪量要素影响下的竞合问题。
四、渎职罪范围内的双包含关系
前文解决了普通渎职罪与特殊渎职罪之间基于罪体或罪量要素而引发的法条竞合特别关系的处理,那么,各特殊的渎职罪之间又存在怎样的竞合关系?应如何处理呢?
从渎职罪的立法规定不难看出,各特殊渎职罪之间并不存在分类意义上的标准,这就难免各特殊渎职罪之间内容上的交叉或重合。例如,我国《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食品安全由部门监管的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这样,商检部门、动植物检疫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农业行政部门、质监部门、工商部门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监管活动中的渎职行为,都可能成立食品监管渎职罪,也同时可能构成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罪名。再如,海关工作人员在负责查处一起价值巨大的走私案件时,徇私舞弊大事化小,代之以行政处罚,其行为同时触及放纵走私罪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两个犯罪构成。以上情状当如何处置?
对此,观点一主张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罚;28观点二主张应依据处理法规竞合的另一基本原则“重法优于轻法”来选择具体应该适用的罪名;29观点三认为应适用“特殊条款优先”的规则,食品监管渎职罪是特殊法条,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罪是一般法条。30观点四主张食品监管渎职罪与商检徇私舞弊等罪都属于特别法条,如何定罪取决于在食品监管过程中是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如果是,认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否则就应当认定为商检徇私舞弊罪等。31
观点一系建立在对想象竞合性质的误读之上。如前所述,想象竞合实为一行为侵犯数法益,符合数个犯罪构成,应当宣告数罪,只是处断上以一重罪的法定刑处罚。据此,若主张想象竞合,宣告数罪,一定是对某一具体渎职行为之“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执行及国民对此的信赖”的法益侵害进行了两次评价,有违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只要明确想象竞合“一行为数罪一罚”、“明白记载功能”等特质,想象竞合说的主张就应当避免。观点二的最终结论为笔者赞同,但将“重法优于轻法”视为法条竞合另一基本处断原则的推理依据,为笔者所不赞同。32观点三虽捍卫了特别法优先的法条竞合处置原则,但同为特殊法条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和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罪,为何前者是特别法,后者是一般法呢?而观点四无非是“食品监管渎职罪是特殊法条,商检徇私舞弊等罪系一般法条”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表述而已。食品监管失职罪与商检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罪等,都是通过对普通渎职罪部分构成要素特别化、具体化后形成的特别法条,但它们之间特别化的内容并不统一,前者是对监管对象(即食品)的特别化,而后者则是对监管流程、监管阶段不同监管职责的特别化(即行为方式、职责内容的特别化)。因此,很难判断二者谁是特别法谁是普通法。
笔者主张,特殊渎职罪之间是一种双包含(交叉)关系,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日本刑法第224条规定了略取、诱拐未成年人罪,第225条规定了以营利、猥亵等目的的略取、诱拐罪,当行为人以营利、猥亵等目的略取、诱拐未成年人时,两个条文发生竞合,日本学者称其为交叉关系(择一关系)竞合,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33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提到双包含关系,即两个不同刑罚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同时与另一法条之间呈现完全包含关系,例如甲法条构成要件是ABCD,乙法条是ABCE,丙法条是ABC,当一个具有ABCDE性质的行为出现时,除该当基本的丙法条构成要件外,也必然同时该当甲乙二法条。若甲乙都是加重规定,应从其最重者。34双包含关系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并不是像想象竞合犯那样在实质数罪的基础上的从一重处断,而是在坚持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基础上,尽量实现充分评价的结果。如上,对于具有ABCDE性质的行为,我们不可能同时宣告甲乙二罪成立,因为二者包含相同的法益侵害内容,但“以其中任何一个‘构成要件实现性’作为该事实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均不足以‘充分评价’,在罪刑法定的限制下,又仅能适用既有的构成要件,此时就必须改采‘尽量充分评价’;若处罚效果轻重不一,则以处罚较重之‘构成要件实现性’作为‘构成要件该当性’”。35
前述渎职罪的事例,食品监管失职罪就是甲法条ABCD,商检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就是乙法条ABCE,普通渎职罪就是丙法条ABC;放纵走私罪就是甲法条ABCD,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就是乙法条ABCE,滥用职权罪就是丙法条ABC。当行为人在对食品的商检中徇私舞弊时;或者当行为人以罚代刑,拒不移交刑事案件而放纵他人走私行为时,就相当于出现了一个具有ABCDE性质的行为,此时,应当在禁止重复评价的基础上,采尽量充分评价原则,只要各特殊渎职犯罪并不具有封闭的特权条款的性质,就应当在甲乙两条文中选择处罚较重的条文定罪处刑。
由此总结规则之五:某一渎职行为,同时符合数个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时,应当选择其中处罚最重的特殊渎职罪定罪处刑;若该渎职行为,行为性质符合数个特殊渎职罪的构成特征,但行为(结果)程度仅符合其中之一的罪量标准时,则应以符合之罪定罪处罚。
五、结语
限制与规范兜底条款、口袋罪名的司法适用,是明确性原则对刑事司法的当然要求。(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等口袋罪名,因为“列举+兜底”的例示立法方法,同类解释规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限制和规范方法。可是对于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这一口袋性质的罪名,却有不同。渎职罪的立法体例呈现“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总分式结构”,第397条在总体上规定了渎职罪构成特征的一般情形,第398条至第419条主要依据不同的职责属性将一般规定具体化为不同领域的渎职犯罪。但具体化的各特殊渎职罪,却未必能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之一般规定提供可资比照的同类解释标准,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职责种类繁多、千姿百态。可见,最传统的防止罪名口袋化的体系解释、同类解释规则,对同样作为兜底罪名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而言,恐怕作用有限。通过本文论证,可以发现正确处理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与其他各特殊渎职罪之间的竞合关系,只有在行为类型、性质不符合特别法条构成特征时,方可考虑转处普通法条;禁止仅因罪量要素导致的特别法条不该当时,转处普通法条;合理解释特别法条兜底的罪量标准等举措,对于兜底条文、口袋罪名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的限制和规范适用,具有一定裨益,也可在其他口袋罪名与相关罪名竞合时的正确适当罪名,提供一些借鉴。
注:
1参见陈兴良:《刑法的明确性问题:以〈刑法〉第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
2欧阳本祺:《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性规定的实证分析》,《法学》2012年第7期。
3高翼飞:《从扩张走向变异:非法经营罪如何摆脱“口袋罪”的宿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3期。
4孙万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
5如孙万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高翼飞:《从扩张走向变异:非法经营罪如何摆脱“口袋罪”的宿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3期;张明楷:《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等等。
6陈斌等:《渎职犯罪司法适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7参见陈洪兵:《不必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清华法学》2012年第1期;陈洪兵:《刑法分则中“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另一种理解》,《法学论坛》2010年第5期。
8参见[德]耶塞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73页以下;[德]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72页以下;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作者发行,2008年,第325页;柯耀程:《刑法竞合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9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有斐阁2007年版,第365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4页;陈子平:《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第460页;甘添贵:《罪数理论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第44页以下。
10许玉秀:《一罪与数罪的理论与实践(七)》,《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6年第84期。
11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作者发行2008年版,第308页、第319页;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第606页。
12、32详见王强:《法条竞合特别关系及其处理》,《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3、18、2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7页,第1091-1092页,第1092页。
14即便是认可“在特殊情况下,法条竞合也允许重法优先的补充适用”的观点,也认为在刑法条文明确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作为重法的普通法条的补充适用。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4页。
15根据2011年3月1日“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已提高到“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
16、20参见周光权:《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研究》,《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17、19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4页以下,第737-738页。
21周光权:《渎职犯罪疑难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11年第19期。
23参见陈志辉:《刑法上的法条竞合》,台北春风煦日论坛1998年版,第43页。
24张明楷:《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分》,《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
25参见赵秉志、于志刚:《大陆和澳门地区刑法中渎职罪之比较》,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六卷),第520页、第523-524页。
26、31储槐植、李莎莎:《食品监管渎职罪探析》,《法学杂志》2012年第1期;郭世杰:《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罪名拟定与立法体例》,《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2年第3期。
27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理解仅限于特别渎职罪的各叙明罪量标准与普通渎职罪的罪量标准在性质、内容上不同为前提的,倘若特别渎职罪有与普通渎职罪罪量标准相同性质、同一内容的罪量标准的叙明规定,则必须依该叙明的罪量标准判断。
28贾宇:《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及适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肖本山:《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若干疑难问题解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皮勇、郭斐飞:《渎职犯罪中的罪数问题》,载孙应征主编:《渎职侵权犯罪法律适用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29谢望原、何龙:《食品监管渎职罪疑难问题探析》,《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0期。
30安文录、虞浔:《食品监管渎职罪疑难问题司法认定研究》,《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9期。
33[日]山口厚:《刑法总论》,有斐阁2007年版,第368页。
34参见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23页。
35郑逸哲:《“择一关系”与“想象竞合”》,《军法专刊》第54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