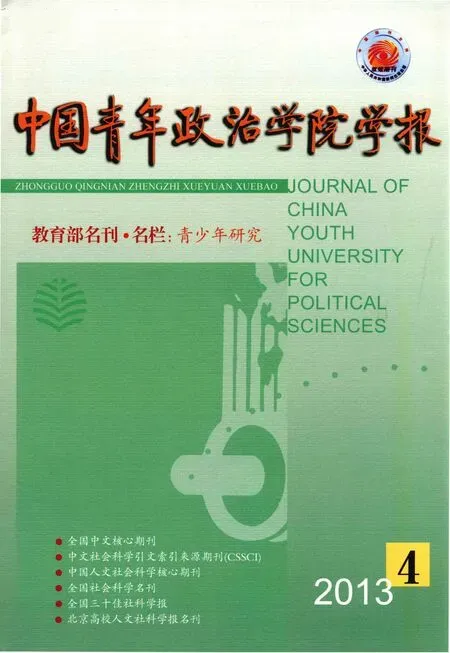宋初的隐逸精神与隐逸文化生态
刘 辰
(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湖南衡阳421002)
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中国文人隐逸之风源远流长。自上古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首阳,隐逸流风余韵不绝。乱世归隐是历史常例,然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苏轼《六一居士集叙》),宋初当属太平盛世而隐逸风气却盛行一时。《宋史·隐逸传》著录隐士49人,其中主要生活于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七十年间的就有十几人,还有见诸其他史籍的隐士。宋初不仅隐者数量较多,且以林逋、魏野为代表的真正意义上纯粹隐士的出现,成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
一
学者对古代文人隐逸行为详加分类,各种分类方法视点不同,隐士的类型划分也不同。从隐者遁入山林之因来划分,隐逸行为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无奈归隐。包括乱世归隐、个人科场或仕途不顺而隐;二是待仕之隐。士人把隐逸作为出仕的一种手段,走终南捷径;三是无为之隐。士人受道家清净无为思想之影响,为追求自由人格、无羁情趣的人生价值理念而避世隐居。第三类隐士才是遗世而独立、真正彻底的隐士,反映了隐逸精神的本质,是隐逸的最高境界。在历史上,真正超尘绝俗、不乐仕进而隐逸终老的纯粹隐士极为少见,大多数是被迫而隐或隐以求名者。盛唐文人在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下,士人昂扬进取,渴望建功立业,入世情绪高涨,隐逸本身作为一种与仕宦相对立的生活方式却沦落为出仕的一种手段,“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1]。当时最负盛名的几位诗人孟浩然、王维、李白的隐逸行为或多或少都带上了几分功利色彩。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社会呈现衰退之势,士人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选择了独善式的“中隐”。这种隐逸方式看似对山林之隐的扬弃与超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隐逸精神的蜕化变质”[2]。从盛唐文人的待仕之隐到中唐文人的吏隐或中隐,隐逸不再是士人为保持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而与政权保持距离的一种生命状态,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精神内涵的丧失。唐末五代乱世士人归隐多是避世之隐,隐逸成了当时文人无奈的选择。宋初隐风虽承袭晚唐五代,所谓“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宋兴,岩穴弓旌之招,叠见于史,然而高蹈远引若陈抟者,终莫得而致之”[3]。无论是处于乱世的避世之隐,还是以隐求仕的待仕之隐,抑或消解仕宦与隐逸差别的半官半隐,隐逸行为要么被蒙上了功利色彩,要么充满了无奈,因此根本不具备融自身于自然中物我两忘的隐逸品格。
宋初绝大多数隐士生性恬淡好古,不趋荣利,隐逸目的是为了逃离尘俗,亲近自然。他们绝意仕途,追求放情山水、宁静淡泊的隐居生活,以布衣终身。他们成为隐者,不是出于无奈,更不是隐以待时,而是出于对隐居生活的热爱。例如,林逋“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4];李渎“淳澹好古,博览经史。十六丁外艰,服阕,杜门不复仕进……往来中条山中,不亲产业,所居木石幽胜”[5];万适“不求仕进,专以著述为务”[6];魏野“嗜吟咏,不求闻达。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前为草堂,弹琴其中,好事者多载酒肴从之游,啸咏终日”[7];与魏野齐名的隐士杨璞(另作“朴”)“自称东里遗民,尝杖策入嵩山穷绝处,构思为歌诗,凡数年得百余篇。璞既被召,还,作《归耕赋》以见志”[8]。还有如曹汝弼“天禧、祥符间高蹈有声,与林和靖、魏野、潘阆等善,诗亦似之”[9],他有诗句“应惭非遁者,难久在烟霞”(《喜友人过隐居》),表明了彻底的隐居之志。林逋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尤喜曾无《封禅书》”之句,以全平生隐逸之志为喜。宋初大多隐士一旦选择隐逸生活,即使朝廷反复征召,绝不会再踏入仕途。据载,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诏邢敦为许州助教,敦让而不受①参见脱 脱等:《宋史》(第三八册,卷四百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431~13432页。。真宗祀汾阴岁,魏野与李渎并被荐,遣陕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臣实愚戆,资性慵拙,幸逢圣世,获安故里,早乐吟咏,实匪风骚……尤疏礼节,麋鹿之性,顿缨则狂,岂可瞻对殿墀,仰奉清燕。”[10]他们是自愿疏离官场,追求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境界,自觉地为隐居而隐居。可以说,宋初隐士大多为纯粹的隐者,其中林逋是中国隐逸文化史上最高的丰碑。
真正的、纯粹的隐者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为特征,主动疏远政治。然宋初名隐种放“屡至阙下,俄复还山”,频繁往来于终南与魏阙之间,其隐逸是为沽名钓誉、以隐待仕,为时人所不齿。种放是个例外,不代表宋初士人隐逸精神的主流。宋初还有部分隐士,隐逸生活也不是其自觉的主动选择,他们早年也有积极入世之心。例如,陈抟“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11];邢敦“太平兴国初,尝举进士不第,慨然有隐遁意”[12];戚同文“晋末丧乱,绝意禄仕……生平不至京师……纯粹质直,以道义自富”[13];潘阆早年也有志于功名,有过仕宦经历,不久被贬后归隐中条山,由此泯灭了早年的入世之心,四处游历,放浪江湖。从隐逸动因来考察,陈抟、邢敦、戚同文、潘阆均属无奈归隐,但他们一旦隐逸,便绝意仕禄,与唐代士人或先隐后仕、或仕而后隐、或时隐时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宋初以林逋、魏野为代表的隐士弃绝了功利,没有矫情,没有做作,是真正的隐者,体现了传统隐逸观所倡导的追求人格自由、与世俗价值疏离这一本体精神在宋初的回归,与盛唐文人以隐沽名待时而动、中唐文人在仕隐间徘徊、晚唐五代文人身处乱世无奈退隐判然有别,表明了宋初隐逸精神实质的嬗变。
二
隐逸之风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层面,受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发展和变迁,各时代隐逸文化的内质也在传承和嬗变之中。宋初太平盛世而隐者数量较多,隐逸之士大多都是真正的、纯粹的隐者,隐逸精神实质与唐代相比发生了嬗变,与当时社会隐逸生态环境有着很大关系。
1.宋初太平盛世下国势趋于衰微
宋初统一结束了唐末和五代十国数十年的纷乱局面,统治者采取了革除五代弊政、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等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励精图治,使得经济复兴,民心安定,从表面上看整个社会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天下太平的祥和之态,与初盛唐社会繁盛景象有相似之处。宋初一立国便实行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政策,文人地位大为提高。太祖有言:“宰相须用读书人。”[14]《宋史·文苑列传》序载:“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己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15]按常理,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人地位提高,会激发士人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文人就该弃隐入仕,但宋初却一反常态,比之晚唐五代隐逸者数量有增无减,且隐逸之士一旦选择隐逸生活,便绝意仕途。生当盛世却淡泊名利,这似乎是个矛盾。而实质上自安史之乱后,整个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宋自立国其国势便处于衰弱状态,远不及唐,且宋王朝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军事上软弱无力,掀开承平的外衣,有很多不安定因素,与政治清平、国力强大、经济繁荣的盛唐迥然有别。宋之立国便暴露了“先天不足”的弱点,开国伊始便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外有辽和西夏的威胁,内有“武将拥兵自持”之忧。宋太祖为用文人儒臣来抑制防范武将,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封建统治政权,采用了以文抑武、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在提高文人地位的同时,也造成了政治军事上的无力。经济上,立国之初民生凋敝,土地兼并严重,经济难以恢复。在宋初整体天下太平却国势趋于衰微的社会环境下,士人心理趋向两极: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表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精神;以林逋、魏野为代表的受老庄和禅学影响的士人则看透世事沧桑变幻,走上了逃避现实、回归山林的隐逸之途。而初盛唐士人身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蓬勃奋进、高昂进取的时代精神激发了士子的用世之心,追求隐逸只是士人仕途失意时精神调剂甚至是进入仕途的手段,故而频繁出入山林和魏阙之间的士人比比皆是,真正淡泊名利、隐逸终身的寥寥无几。在宋初表面太平实则衰微的社会环境下,士人既没有极盛之世隐逸之士潜藏的功利之心,也没有乱世中选择隐逸的无奈,隐逸行为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故而宋初隐逸之士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能自甘清贫,隐逸动机更为纯粹。
2.宋初统治者对隐士采取更加优待和礼遇的政策
中国历代统治者几乎都有招隐之举,唐代帝王也有征隐传统。比之前代,宋初统治者对隐士采取了更加优待和礼遇的策略,他们对待隐士的关怀大大超过前朝,也促使了隐逸之风的盛行。宋初统治者对隐士礼遇有加,多采用征召、遣使慰问、赏粟帛、免差徭、赐名号、下诏褒扬等形式。隐士被皇帝赐“先生”、“处士”之称的不胜枚举,如陈抟为希夷先生、林逋为和靖先生、高怿为安素处士、韩退为安逸处士、戚同文追号为坚素先生。魏野卒后,特赠秘书省著作郎①参见脱 脱等:《宋史》(第三八册,卷四百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431页。。皇帝对隐士不但赏赐名号,还不忘时常遣使慰问,更在物质上给隐士生活以极大的支持。隐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自然离不开物质基础的支撑。陈抟入宋后太宗待之甚厚,礼遇有加,“赐紫衣一袭……令有司增葺所止云台观”[16]。对李渎,“真宗祀汾阴,直史馆孙冕言其隐操,请加搜采,陈尧叟复荐之。命使召见,辞足疾不起。遣内侍劳问,令长吏岁时存抚。明年,又遣使存问”[17],其卒后诏表,“特赠秘书省著作佐郎,赐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蠲其差役”[18]。魏野被诏不赴,宋真宗“诏州县长吏常加存抚,又遣使图其所居观之。五年四月,复遣内侍存问”[19],卒后,“赐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免其差徭”[20]。杨璞也曾有过这样的恩遇,真宗朝诸陵,道出郑州,遣使以茶帛赐之。高怿“闻种放隐终南山乃筑室豹林谷,从放受业”,“诏州县岁时礼遇之,给良田五百亩”[21]。林逋二十年不入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22]。对种放更是礼遇有加,多次被召,加官进爵,赏金赐帛。咸平元年“诏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丧”[23],淳化四年,“复诏本府遣官诣山,以礼发遣赴阙,赍装钱五万”[24],景德元年十月,“屡遣中使劳问,赐以茶药”[25],以致其“然禄赐既优,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致争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26]。在宋初,几乎每位隐士都受到朝廷的褒扬和称许,朝廷从物质和精神层面给予隐士以全面的支持和关怀。对君王来说,优待隐士既可以借此教化百姓、息贪竞之风,又可赢得礼贤下士的美誉,客观上还有点缀太平的作用,利于天下安定。对隐士来说,自身的生存环境较为宽松和自由,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在举逸民、天下归心以及社会普遍崇尚隐逸的政治氛围下,隐逸也能成为部分士人的自觉选择和主动追求。
3.释道文化深入隐逸之士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
儒释道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思想。一般来说,各朝立国之初,由于连年战乱生产力低下,统治者大多会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以恢复生产。例如,汉、唐之初统治者都主要采用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来处理当时的社会矛盾。宋初三帝为恢复生产和缓和社会矛盾也主要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以治国,他们虽也尊崇儒家,但更为提倡道教和佛教。宋太祖多次召见道士问以治道。宋初名道陈抟、种放、丁少微、张守真、王怀隐等均与太宗有过密切交往,甚至为太宗制造真命天子的神话。太宗自晚年起全力倡导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尝公开宣称“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27]。真宗继帝位也离不开道士的帮助,还为《道德经集注》撰序,以为“《道》《德》二经,治世之要道”[28]。宋初统治者还一改后周世宗时的废佛排佛政策,实行保护和弘扬佛教的政策。为弘扬佛教文化,翻译佛经,太宗还建立了译经院,派人充任译经使,组织高僧,翻译佛教经典。太宗曾以新译经卷示宰相,说:“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朕于此道,微究宗旨”[29]。
在统治者的提倡下,宋初佛道之学极盛,上至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无不受佛道熏染,其中隐逸之士与僧、道关系尤为密切。宋初名隐陈抟即为道士,其他隐士如潘阆、种放、林逋、魏野等均从学于道士陈抟。《唐才子传》载:“洛阳潘阆逍遥、河南种放明逸、钱塘林逋君复、钜鹿魏野仲先、青州李之才挺之、天水穆修伯长,皆从学先生,一流高士,俱有诗名。”[30]宋初隐士所交游者僧侣道人颇多,他们与僧侣道人参禅悟道、交往唱答,熏染极多,从大量的酬赠诗歌中可见。据《全宋诗》,林逋存诗三百一十余首,其中与僧道有关的诗作有五十余首。魏野现存诗三百三十余首,与僧道交游诗有四十余首。宋初其他隐逸诗人也几乎人人有诗赠予僧人道士,或与僧人道士有关,或与寺院道观有关,可见受佛道影响之深。
以老庄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道家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它崇尚自然,向往清静无为,主张返璞归真,引导人们从虚伪、喧闹的俗世中返归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佛家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出世思想,其主旨是求解脱一切苦厄,以明心见性、心灵觉悟来洗涤世俗、摆脱俗念。就其本质来说,佛道文化与隐逸文化之间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天然的契合,它们对功名富贵的鄙薄、对世俗价值的疏离是相通的。儒家虽也谈隐逸,但其隐逸是以“邦无道”为前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是为待“有道之邦”暂时的隐逸。儒家之隐既是反抗现实的方式,更是待时而动的权变,其隐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相对来说,道家注重个体生命自由,而名利给生命本体带来负累,“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庄子·骈拇》),因此,道家之隐是以隐逸来摆脱外物所役,追求逍遥自由、不以物累的生命境界,隐逸本身便是目的。佛家把自然山水看作有佛性的生命以及心灵的外化形式,它促使隐士彻底避开尘世的喧嚣,从而全身心投入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因此,受佛道影响的隐士比之受儒家精神主导的隐士,其隐逸观摒除了功利成分,显得尤为彻底与纯粹。宋初在佛道极盛的文化背景下,本身淡泊世事的隐士们受佛道的熏染,更能真正摈弃世俗功利,以自然平淡的心态在大自然里寻找寄托,实现逍遥自适的人生境界。
结语:宋初太平盛世而多隐逸之士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宋初逐渐衰微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趋于内敛闭合的时代精神下,隐逸成为寻求精神家园的文人主动追求的生活方式。宋初统治者对隐士的优遇更促使了隐逸之风的盛行,佛道的熏染又使隐逸之士心境更趋淡泊宁静。同时,在此文化生态下,士人隐逸的心态和人格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宋初以林逋、魏野等为代表的纯隐士,既不是出于无奈,更无功利因素,是真正甘于淡泊、超然于物外、以精神追求为高的真隐士。他们出于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对隐逸生活方式的真正认同,主动摒弃功名利禄,追求人格之独立自由,追求超然物外、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反映了宋初没有功利的、纯粹以自然审美为旨归的隐逸精神特质,代表了传统隐逸文化的最高境界。
[1]欧阳修 宋 祁:《新唐书》(第一八册,卷一百九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94页。
[2]张仲谋:《兼济与独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3][4][5][6][7][8][10][11][12][13][16][17][18][19][20][21][22][23][24][25][26]脱 脱等:《宋史》(第三八册,卷四百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3417、13432、13429、13427、13430、13428、13430、13420、13431、13418、13421、13429、13430、13430~13431、13431、13432、13432、13423、13423、13424、13426 页。
[9]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18页。
[14]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1页。
[15]脱 脱:《宋史》(第三七册,卷四百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997页。
[27]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58页。
[28]李一氓:《道藏》(第13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29]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4页。
[30]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周本淳校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