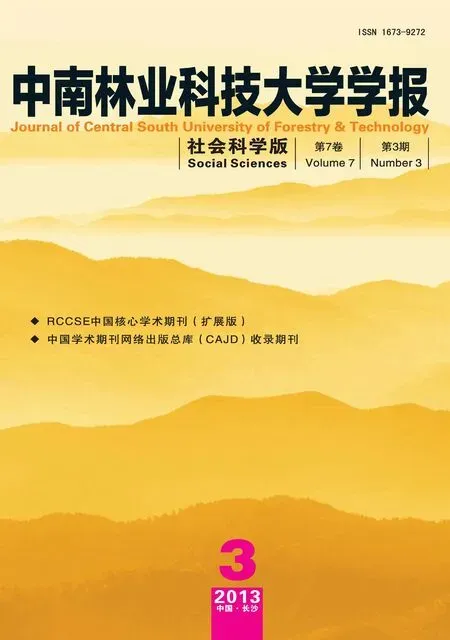论“无为而无不为”命题的伦理依寓
罗光强
(桂林医学院 人文社科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104)
论“无为而无不为”命题的伦理依寓
罗光强
(桂林医学院 人文社科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104)
“无为而无不为”命题只有依寓在道德王国里才能获得现实可能性。该命题的行为主体所指——圣人内涵着对崇高品性追求的伦理预设,其前提条件“无不为”和“无为”必然关涉到圣人“为天下式”和“功遂身退”的道德内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决定了该命题的语境性质全在伦理一维。
“无为而无不为”,伦理预设,道德关涉,伦理旨归
关于“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这个命题的现实可能性,自老庄以降,人们一致坚持:只要顺其自然,不妄为,“无为”就能“无不为”。但如果人们追问:不妄为,顺其自然地“为”为什么就是“无为”?我们怎样才能不妄为,顺其自然地为?“无不为”的理想境界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不仅影响老聃思想的发扬光大,更使中华道学文明的传承严重受阻。本文着力对此命题进行讨论,努力为人们的疑问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路。
一、主体指称的伦理预设
要理清“无为而无不为”的现实可能性的内在逻辑,释怀人们的千年大惑,我们首先应该厘清该命题的行为主体指称,也就是谁能真正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的行为主体指称是什么呢?众所周知,这个命题从表面形式来分析是矛盾的,“无为”即无所作为,“无不为”即无所不为。无所作为与无所不为这两种状态之间不存在必然性,行为的绝对空无要转化为行为结果的绝对最大化不存在任何偶然因素导致的“蝴蝶效应”式的无限可能。因此,明代李贽认为:“今之言无为者,不过曰无心焉。夫既谓之心矣,何可言无矣!既谓之为矣,又安有无心之为乎!”[1]然而,老聃却在其思想中明白指出:“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无为而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他把该命题作为充盈必然的现实可能性命题来陈述的,排除了任何偶然性的巧合。这个命题形式逻辑的“不可能”要想成为现实的可能,除非存在某种被人忽略的预设。陈鼓应认为,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道’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和作用,都是老子所预设的。[2]在上述命题中,老聃确实做了一种主体指称的预设,否则老聃就沦为了其学生孔丘所谓的狂简之人——信口开河却难以自圆其说。老聃对该命题的主体指称预设不是停留在宽泛意义的表层能指上,是有其确定所指。
从《道德经》一文分析,该主体指称在《道德经》中只有两种可能的能指选择,即“民”和“圣人”(这里要指出的是,《道德经》中人主、侯王将相、大丈夫等都是以圣人的欠缺状态在世存在的)。到底是“民”还是“圣人”是所指对象呢?在老聃的视野中,“民”的显著特征是:“争、盗、乱、有欲”(《道德经》第八章)“利、不慈、令而不均”(《道德经》第三章),“贫、不正、不化、不富、不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难成”(《道德经》第六十五章)、“难治、轻死、饥”(《道德经》第七十五章)。很明显,“民”不仅仅处于一种亟待教育的生存欠缺状态,更处于一种亟待教化的道德欠缺状态。这就决定了“民”缺乏“无不为”的潜在可能,老聃对“无为而无不为”命题的主体指称——圣人做了明确的推定。他说:“是以圣人之治,……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至此,“无为而无不为”行为主体已昭然展示。“整体理解老子全书,可看出‘无为’的行为主体为‘圣人’或‘侯王’,而非任何人。”[3]虽然从宽泛意义上来说,圣人指是在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的知行完备、才德全尽之人,但是在《道德经》的语境中,老聃对于圣人知和行、才与德的权衡更侧重于行和德。据此语境,孟子对这一观点予以具体化,他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言下之意就是,道德完满而不是高超生存技能应该成为圣人的终极在世状态。这更加明确了“无为而无不为”命题主体指称预设——圣人的道德充盈。
二、两个前提的道德关涉
“无不为”对于道德的关涉是“无为而无不为”成为可能应该具备的第一个前提。“无为而无不为”行为主体的确定为“无为”和“无不为”两种状态的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分析基础。这种限制使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现实可能性讨论范围相对来说简单的多。因为问题的针对性已经出现端倪,我们只需探讨圣人“无为而无不为”的可能性。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圣人“无为而无不为”命题要具现实可能性,一个先行的条件是圣人的“无为”和“无不为”两种生存状态都必须可能,否则该命题又会沦为假命题。我们首先来分析圣人“无不为”的可能性。因为“无不为”在逻辑上比“无为”更具优先地位。因为“无不为”不存在,圣人就不可能存在。
老聃认为,圣人是一个道德圆满、品性超脱、先知先觉的人,是一个确定的实体性存在,能够“无不为”。他“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道德经》第八章)”,……可托天下(《道德经》第十三章)”,“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道德经》第二十七章)”,“能成其大(《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也就是说,圣人不仅也处于俗世权利的顶点,而且处于道德权威的至高点,是一个真正得“道”之人。因此,他确实具备“无不为”的理论可能性。然而,仅从理论可能性就断言圣人能“无不为”理由还不充分,必须对这种可能性进行现实辩护,否则圣人“无不为”就会陷入形式逻辑的虚空。对圣人“无不为”的现实可能性问题的解答离不开圣人的处世方式,即“圣人之道”的语境分析。按老聃在《道德经》传递的信息,“圣人之道”表现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第二章);“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道德经》第二十六章)“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第二十九章)“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道德经》第五十八章)“被褐怀玉。”(《道德经》第七十章)“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执左契而不责於人。”(《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也就是说,“圣人之道”是通过一系列的“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作、生、为”、“终日行”、“处其厚、处其实”、“方、廉、直、光”、“被褐”、“自知自爱”、“执左契”和“不积、为人、与人”等纯然义务性活动来实现的。行为事实达到“无不为”的境界对于“为天下式”的圣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道德意义上达到“为天下式”才是圣人成为的完满境界。庄周“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第三十三》)的观点所内涵的“内圣”与“外王”的逻辑秩序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解。至此,圣人“无不为”的道德关涉已经展露,无需赘述。
“无为”的道德关涉是“无为而无不为”成为可能应该具备的另一个前提。从辩证法来看,无具有相对和绝对两种内在属性。圣人“无为”中的“无”是从相对意义上来定位还是从绝对意义上来定位的呢?在《道德经》中,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有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它们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相对性。[4]这可以从他对其本体论“道”的描述中推演出来。他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道德经》第一章)”“道”虽然玄远深邃,但毕竟存在,不是绝然空无。圣人以“有”的形式在世而为,他的任何举动不管以何种隐蔽的符合“道”方式发生,都会在时间和空间中留下痕迹,凭空消失是不可能的。上述推理可知,圣人的“无”作为“道”的表现形式,只是一种相对的无。“无”的相对性通过圣人“无不为”的主体间性表现,即它是由其对立面“民”这一他性的反应来崭露,而不是圣人本身自我行为认定的虚无化。在老聃对圣人的描述中,除其所述的确定性之外,他还存在不确定的一面。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内在的不确定性导致圣人本身难为人知,因而被“民”“虚无”化。这可以从老聃的下述判定中推出。他说圣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道德经》第十五章)”,“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第十六章)”,“无常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圣人的这些在世状态难于被“民”所接近和理解,因而其“无不为”随其本人一起被忽视,即被“虚”化。外在的不确定性指“民”在处理自身利益得失的时候把功劳完全归结于自身,根本没有意识到圣人的作用。老聃说:“太上,不知有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道德经》第六十六章)因为圣人“贵言”、“无事”“、“不重不害”,“民”“功成事遂”后竟然“不知(圣人)有之”,因而圣人之“无不为”被完全“无”化。朱贻庭认为,“‘无为’之用于社会领域,作为一种治国之道,……但同时又是一种道德实践原则。”[5]这就表明,圣人的“无”并不是其行为事实的绝对空无,而是因为功遂身退、淡泊名利的道德品性使他显得不触目,进而其“无不为”被“民”误读为无为。英国的李约瑟曾认为:“无为”的意思就是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亦即不固执地要违反事物的本性。”[6]如果像李约瑟一样片面凸显圣人“无为” 的自然性,其道德关涉被弱化。“无为”是道常存的方式,“无为”保证了万物自然而然地得到教化。[7]“无为而无不为”命题的逻辑推演就会陷入虚幻,难以获得现实可能性。
三、语境性质的伦理旨归
以上已对圣人“无为而无不为”行为主体指称的伦理预设和两个前提的道德关涉分析已经较为清楚,但问题依然存在。人们会质疑:普通人——用老聃的话来说就是“民”——不能“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什么却能“无为而无不为”呢?也就说,“无为而无不为”行为主体指称的语境依然蔽而不明。这是回答“无为而无不为”的现实可能性必须直面的关键问题。那些把“无为”解读为“不妄为、自然而然地为”的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避使得它们并不具备真正说服力。圣人能“无为而无不为”,而普通人——“民”则不能的原因只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圣人”具有某种不为“民”所拥有的能力。该能力使得他既能把能把“无为”转化为“无不为”,继而又“无不为”转化为“无为”。因而,探讨圣人“无为而无不为” 的可能性就演进为圣人是否具有把“无为”转化为“无不为”的能力的讨论。于是,对圣人的这种能力进行探究就成为解决“无为而无不为”现实可能性的基点。要甄别圣人异乎于“民”的能力,其先决条件是厘清圣人“无为而无不为”的语境性质。
“无为而无不为”的语境性质更多地包含对于圣人道德品性的苛求,是一种严格的道德语境。老聃在《道德经》末尾万取一收地做了评点——“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八十一章),这显然是他把“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实现的厚望寄寓在道德王国。从该文的语境分析,老聃“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旨归事实上全在于伦理一维。具体来说,“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为“民”难以具备的能够对“为而不争”这一崇高品性一以贯之的道德能力。“为而不争”让我们明白:圣人的“不争”是一种总是蕴涵着对“无不为”目的趋向的刻意勾连行为,因而其“无为”心态中存在某种趋向于“无不为”的主观愿望。而“民”的“无为”具有纯粹性,是一种几他两不利行为。“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为生存所困,没有能力“无不为”,因而根本不会去勾连“无不为”所内涵的纯粹利他的道德愿望。这种“民”所“根本不会去勾连”的道德愿望就是圣人之所以能“无为而无不为”的能力。“民”的道德意识中也许偶尔会闪过“不争”的念头,甚至不时地“不争”,但他难以坚持。《道德经》的语言性语境表明了这一点:圣人之“为”的环境是“众人之所恶”(《道德经》第八章),其“为”之术是“善利万物”,其心理准备是“去甚、去奢、去泰”, 其所遭遇的人生际遇是“受国之垢,受国不祥”(《道德经》第七十八章),待其功成之时却又“身退”(《道德经》第九章)、“不争”(《道德经》第八十一章)。“功遂身退”这种绝对的去功利行为在“民”论功行赏时找不到功劳的得主,于是让“民”形成一个偏激性的观念——“我自然”,也就是本来就没有圣人,一切都是我(“民”)自身努力的结果。老聃认为,圣人丝毫不关注其行为结果与名利获取之间的对等性,绝然恪守“为而不争”的道德信念,通过“功遂身退”的行为方式来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德追求。所以庄周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至人、神人、圣人”其实都是圣人的在世体现,庄周只不过从本体说、在世说、名相说三个不同层面的予以表述,以便人们对圣人“无为而无不为”语境的伦理旨归有更深层的理解。
[1] 张建业.李贽文集:第三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6.
[2] 陈鼓应.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老子注译及评介(修订增补本)[M].上海:中华书局,2009:1.
[3] 刘韶军.试论《老子》“无为”的行为主体及丰富内涵[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6):83-87.
[4] 张旭涛. 有为与无为的统一——老子无为说探析[J].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2000,(1):52-59.
[5] 朱贻庭.道家伦理文化及其现代价值[J].学术月刊,1997,(4):15-20.[6]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M].邹海波,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6.
[7] 丘乐媛.《老子指归》“无为”思想的易学渊源[J].周易研究,2011, (6):29-35.
On the Moral Context of the Proposition of “Non-action Means All for”
LUO Guang-qiang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Guilin Medical College,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The proposition of “non-action means all for” obtains realistic possibility only in the moral kingdom. The behavior subject——Saint of this proposition refers to ethical design of lofty character pursuit, the premises of “all for” and “Inaction”inevitably involve the moral connotation of” for the world “and” retire after winning merit” of Saint. The doctrine of “the Tao of Saint——action but not to strive for the interests” determines that the context of this proposition is in ethical dimension.
“non-action means all for”; ethical design; moral connotation; ethical orientation
B82
A
1673-9272(2013)03-0036-03
2013-03-02
罗光强(1972-),男,湖南邵阳人,桂林医学院人文社科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生命伦理学、中国传统伦理学。
[本文编校:徐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