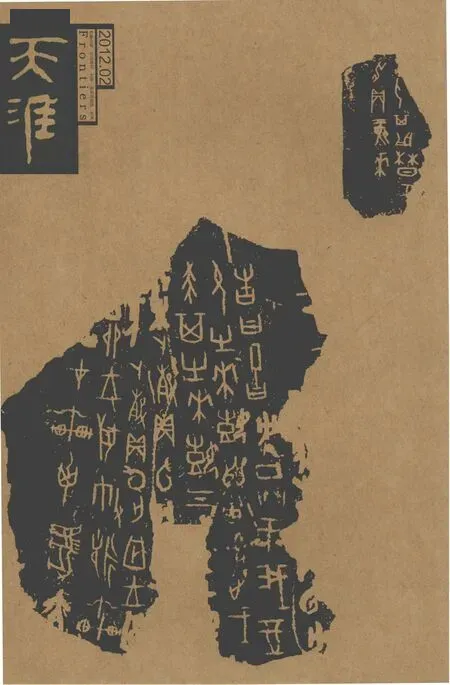迷恋午后的光
项丽敏
迷恋午后的光
我迷恋自然中那些日常又有神性的事物——早晨的露珠、鸟鸣;第一缕照到窗帘上的橘红;雨水敲打雨棚的声音;马路边的香樟树在路灯中投下的浓郁的影子……
在冬日,我居住的房间午后拥有的光也是叫我迷恋的,暖而明亮,从窗户中探进身体,斜斜地倚在墙上,画一扇印象派的窗,或在地板上懒洋洋地躺着,挥发着熟苹果的微醺气息。
这是属于我的光。是的,那么多的光当空照耀,笼着万物,唯独这一小束光是属于我的,在我的房间里赤着脚走来走去,静悄悄的。
当我捧一本书或一杯茶坐进这束光里的时候,光的手就会轻柔地抚摸过来——我的头发,我的额头,甚至我的嘴唇都能感受到光的恩宠。像一只被主人抚摸的猫那样,我微阂上眼睛,眼前盛开出一片蔷薇花园,耳边则听到来自天空的,如同融化了的太妃糖般光滑的音乐。
性感
圣女果就是小西红柿,是我喜欢的水果之一。不仅喜欢它的味道,它的颜色及形状都给我视觉的愉悦,日常,洗几枚,用玻璃盘盛着,放在眼前,便是一道可观的静物。在水果中,圣女果算得上性感尤物了。
很少在自己的文字中动用“性感”这个词,尽管我喜欢这个词以及它所表现的特质。十年前看安吉莉娜·朱丽主演的《原罪》,一下子就被她迷住,她的容貌以及周身散发的神秘气息,准确地诠释了“性感”这个词,定义了这个词的禁忌与美。
三年前听维塔斯的歌,看他在M T V中光头的样子,穿白衬衫或黑风衣,裹着大红围巾,那眼神要么忧伤得令人心碎,要么带着邪气的撩一下,又纯洁又妖娆地笑着,也是性感逼人。
性感是一个人天生的禀赋。但它也会在某一天离开拥有它的人。这和年龄有关——也不是绝对,有些人在年老时仍然性感,比如科恩。
科恩的性感来自他低沉而深邃、略带沙哑的声音。一个人的声音和容貌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有时我们听一个人的声音,就会在心里做出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听科恩年轻时的歌声倒是平常,他的声音是在逐渐年老的过程中变得独特的,又苍凉又温暖,予人深入魂魄的抚慰。
和科恩不同的是,安吉莉娜和维塔斯的性感在岁月中逐渐凋谢了。两年前,在中国巡演的维塔斯已明显发胖,多了媚俗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尽管那声音还是他的,那个人却不是之前令人惊艳到气绝的维塔斯了。
无论是科恩、安吉莉娜,还是维塔斯,他们都将性感的气息渗透到艺术中,通过作品放大了性感的魅惑。
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具备了性感就具备了很重要的渲染力。在摄影方面,早在上个世纪末,旅德艺术家王小慧的《花之灵》系列,就以细微的视觉表现了花卉震撼人心的性感。而更早——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一位名为奥姬芙的女画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生活并创作了半生,她所绘画的鸢尾花热烈而缠绵,充满了欲望,将植物的性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布列瑟农
已经忘了是哪一年听到《布列瑟农》这首歌,总之是多年前了,在我所买的一盘C D里有这首歌。很多个午后我盘腿坐在地板上,反复听着这首歌,完全沉浸于它温柔的诉说与绵延的忧伤里,在一种受难般的炽烈中迷醉难返。
《布列瑟农》这首歌的名字来自一个地名,是佛罗伦萨和慕尼黑之间的地方,一个被山村包围的小镇——这是几年以后,在我接触了网络以后得知的。在成为一首歌名之前,知道这个小镇的人并不多,尽管它有着童话中的宁静与美丽。
一个地名成为一首歌名,打破时空局限为世界流传——算得上奇迹了吧。这奇迹是爱情创造的。也唯有爱情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马修·连恩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在《布列瑟农》这首歌诞生之前,马修·连恩是一个漂泊的音乐家、一个环保主义者——为绿色和平组织工作。马修·连恩对自然的热爱来自童年时期的生活。在他还是五岁孩子的时候,父母便分居了,父亲决定离开圣地亚哥喧嚣的都市生活,独自去往加拿大的育空地区——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荒野之地,也是印第安土著的繁衍之地,有大量的野生动物,有浪花飞溅如白马的河流。马修·连恩七岁时第一次跟随母亲去往育空,沿途的北美风光袭击了他幼小的灵魂,他被大自然的原生之美震慑了——这次经历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走向。
如果说大自然意味着马修·连恩的父亲,那么音乐就意味着他的母亲了。是音乐寸步不离地陪伴他生命的成长,以温柔而宽厚的怀抱驱散他的恐惧与孤独。十一岁的时候,马修·连恩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钢琴。二十五岁时,马修·连恩发表了第一张音乐专辑。之后不久,便有了《布列瑟农》。
马修·连恩是为了一个女孩来到布列瑟农的。女孩也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他们在共同的工作中认识并相爱。年轻的爱情有着烈日的金黄,他们需要挥霍,需要触摸彼此的全部并融化彼此。
他们选择了布列瑟农这个有着纯净星空的小镇。
布列瑟农,哦,布列瑟农。因一段爱情而永恒的地方。教堂的钟声在小镇环绕,安抚着恋人们因离别而悲伤的心,而火车的鸣笛已近,车轮咔哒,将分别带走两颗破碎的心。马修·连恩把心爱的姑娘送上火车后坐上了另一趟火车,他要去的地方将远离姑娘所去的地方,布列瑟农是他们的幸福小镇,也是他们的悲伤小镇。然而极致之美的艺术往往诞生于极致的伤痛中。马修·连恩在火车上很快写下了《布列瑟农》,握笔的手指上尚留着姑娘的泪温。
1995年,《布列瑟农》这首歌被收在马修·连恩的第五张专辑里,这张名为《狼》的专辑获得了“北极光”最佳原声带奖,这一年马修·连恩三十岁。
从第一次听《布列瑟农》到现在,已过去很多年了。那张C D也早已损坏,而我隔一段时间还是会在电脑里找出这首歌,放大音量,反复地听。每一次听这首歌都像是经历着一场爱、一场别离,经历着生与死。没有一首歌能像这首那样,将我揉碎又展开,再揉碎。
也许我的心里也有一个布列瑟农吧?——也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布列瑟农——也许这就是它征服了这个世界的原因。你再也不能回到那个地方,那梦一样的城堡,浪漫的小镇——从你踏上火车之后。
一只苹果品尝了自己
一只苹果品尝了自己
通过你的手
致命的牙齿,以及舌尖
每个夜晚都会做梦。很多年了,也可以说,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我不知道那些梦是从哪里来的,它们犹如超现实的影片,给了我夜晚的另一面生活。如果没有梦,我的生活是多么单调,尽管梦是虚假的——也并不总是有美梦——很少有美梦。
大多数的梦会被我忘记,醒来的时候就忘记了,能记住的是给我强烈印象的。我无法控制我的梦,我的梦却能控制我。是的,我经常被自己的梦控制,就像一种蛊,摆不脱,会沿着梦的暗示走下去,把梦到过的在现实中演绎一遍。
在我的指甲上——几乎每个指甲上都有竖纹,据说这是神经衰弱的征兆。可能就是多梦导致了我的神经衰弱。我并不熬夜,每天晚上十点会准时上床,很快就能入睡,当然并不能够进入深度睡眠——我仍然能听见夜晚的声音,比如昨天夜里突然下起的雨,我听得清清楚楚,能听到每一滴雨落地时的寂寞。是的,我听到了寂寞,在下着雨的春夜,难免会有这样古老而忧伤的寂寞。
我在雨声中做起了梦,梦到写诗。
在梦中写诗,这是近两年来常有的,和我近两年来的写诗生活有关。白天的工作会影响到夜晚的梦境,白天的思想也会在夜晚的梦境延续。在梦里所写的诗是绝妙的。我似乎也知道自己是在梦中,带着喜悦,一遍遍地读着那些无与伦比的诗句,希望能够记下它们,在醒来时写下。但我从来没有记住过,一句也记不住。哦,那些诗,它们分明是长了翅膀的夜鸟,天一亮就飞走了。多么遗憾,那些从不存在的绝妙的诗,我失落了它们,就像失落了不曾拥有的美好爱情。
但是昨夜的诗我却记住了。先是“一只苹果品尝了自己”,然后是“通过你的手/致命的牙齿,以及舌尖。”我很快醒了过来,亮了灯,跳下床,在电脑桌上抓起笔和纸,把它们记下。
一只苹果品尝了自己——梦中的句子果然奇妙。回到床上我咀嚼着诗句,感觉到诗句的微妙和危险。但我不能确定——它确实来自于我,而不是我所看的某一本书。
无论怎样,我是满足的——这只夜鸟,在天亮之前终于被我抓住,在它飞走之前。
初夏
立夏日,路边已有红熟的野草莓了。以前曾在文字里说,对五月的期盼,就是为了能采摘那遍地的野草莓。而现在,面对野草莓已没有了采摘的欲望,看一眼,在心里打个招呼,就走过去了。
龙西小区对面,那家花店门口的蔷薇花也摆开阵势,和往年一样隆重地开起来。
花店是我每天都要路过的地方,每次路过时都会转头看看,有时看花,有时看人。去年以前花店里是两个人,一对花甲之年老夫妻。在早晨,通常是男主人把门打开,把屋子里的花一盆一盆搬出,给花们挨个浇水。偶尔我会在花店门口停下,取出卡片机给开花的植物拍照,女主人看见后就从屋子里走出,笑吟吟地指点着,告诉我那些植物的名字。
开春以后花店关门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开门时就只看见女主人,头发白了不少,脸上带着默默的哀伤。
今天的天气预报是说有雨的,早上阴沉了一阵,过了一会天就变蓝,到中午时阳光已有些灼人,毕竟是夏日了。
一幕
苏果超市门口,半人高的垃圾筒,不知是谁把一块甜瓜搁在上面(可能是超市里扔出来的坏瓜)。黄色的瓜瓤被绿色的筒盖托着,有些招眼。
垃圾筒边站着两个拾荒者,一男一女,六十岁的样子,灰黑的脸,灰黑的衣服,灰黑的手。
女人的手里也有一小块甜瓜。女人将甜瓜放进嘴里,眯着眼,细细地嚼着,仿佛品尝世界上最精美的食物。
男人站在对面,安静地看着女人,目光温柔而满足。
女人吃完了手上的瓜,和男人说了一句话,两个人都弯腰笑起来。
女人接着拿起垃圾筒上的那块瓜,准备吃的时候又停住,把瓜伸到男人嘴边。
男人的喉间吞咽了一下,伸出手,把瓜推回女人面前。
——这是中午经过苏果超市时看见的一幕。当时很想拿出相机,把这一幕拍下来。
犹豫片刻,忍住没有拍。走过去很远后,又回头看看他们。
宿疾
立夏很久了,我仍被春天的季节病——“花粉过敏症”纠缠着。
这不致命却能一夜间致人面目全非的宿疾,仿佛在我身上某个地方扎下了窝。多少年了,我仍然没有办法端掉这个窝,只好小心翼翼地对待它,和它说好话。在它完全不顾及我的颜面迅猛发作时,我便使出吞药的绝招——白色的、细小的药丸,早晚各一把。抗过敏的同时,也让我陷入昏天昏地的嗜睡中。
“真奇怪,你有花粉过敏症,而你却拍摄了那么多花。”一位朋友说。
也许这就是一个人宿命吧。被所爱的伤害着。
两千年前,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在诗中也曾说过:
经常,那些
我以温柔相待的
伤我最多
凉鞋
傍晚,在达芙妮店里给自己买了一双鱼嘴凉鞋,黑色,坡跟,边缘有细细的花朵镶边。
每年夏末我都会给自己买一双凉鞋,这个时候买凉鞋很划算,比夏初便宜很多。
这样说好像我是个很俭省的人,其实不是,一种习惯而已。夏末买凉鞋的习惯是哪一年开始的呢?大约有七八年了吧,记得当初曾在日记里写过,也和身边的朋友说过这件事,我说,买一双好看的凉鞋存放在那里,会觉得,就算为了穿上这双凉鞋也要活到第二年夏天。
那时候我对活着这件事可能没什么把握,总是摆脱不了生命的无常感。若仔细地想想,大概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愿意为之活。就像每个写作者都会遇到“为什么而写”的问题,每个人也都会遇到“为什么而活”这样形而上的问题吧?是这样的,人总是要为自己为什么活着找个理由,爱是最好的理由了,其次就是责任。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为爱而活的,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这个世界有我爱的人,哪怕看不见那个人也没关系,而如果那个人不在了,那么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是一片荒凉的废墟了。只是后来爱过的那个人没有死去,爱却在我心里死去了。怎么办呢?如果要活下去就得为自己再找个理由。这个理由并不难找,一个人若想为自己做的事找理由总是不太难的,比如为了看到明天的日出我要活下去,为了写够一百首诗歌我要活下去,为了吃到下一个春天的野草莓我要活下去,甚至是为了穿上一双好看的凉鞋我要活下去。
有孩子的人不需要为活着找那么多的理由吧?孩子就是唯一的理由——不可动摇的理由。记得很多年前在一个作家的散文里读到一句话,大意是无论如何要坚持活到女儿三十岁的时候才可以死。说这句话时他的女儿才刚刚出生,在这之前他大概也时常会被死的念头、或者为什么而活的念头纠缠吧,孩子的出生拯救了他的生之虚无感,一个需要依赖他而活的生命同时也成了他活着的依赖与信念。
前一段时间看了一部名叫《命》的电影,根据日本作家柳美里的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当柳美里的母亲得知女儿怀孕后欣喜若狂,大呼“万岁”,之所以如此兴奋并不是因为要升级当外婆,而是觉得,再也不用担心有过自杀史的柳美里某一天会突然不想活了,“有了孩子的女人是不会自杀的,你的姐姐会好好活下去的。”母亲目光湿润地对柳美里的妹妹说。
这也不一定,我就曾有一个远房亲戚在生下孩子不久后自杀了,那几乎成了我的一个心结,很多年不能解开,至今也无法想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怎么舍得丢下刚满周岁的孩子离世而去,况且她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开朗、很有责任心的。
我们永远不能知道另一个人内心的悲哀、凄凉——破败的里子总是被隐藏着,肯拿出来给人看的都是光鲜的那一面。
近两年来我已不太想着为什么而活的问题了,或许是血液里的热毒差不多已释放完了吧。也不是一次都没想过,当生的厌倦感再次围拢过来,我会对自己说:你没有什么理由不活,所以你得活着,体验着——像体验一次探险旅行那样,体验你生命的过程与细节吧。
就像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演变成一种风俗那样,每年夏末买一双凉鞋给自己也成了我个人的风俗,说起来还是跟俭省有点关系吧,比如这双达芙妮凉鞋,放在刚上市的时候,无论怎样喜欢也舍不得下手的。
立秋
昨天立秋。一个女人,身姿丰盈,浓密的长发随意在脑后挽了一个髻,漏下几缕碎发绻在脖弯,风一吹便飘起来,随之飘起的还有一种香,犹如大雨过后野草的香、烈日过后玫瑰的香。女人倚着一扇覆满青藤的木门,投向远方的目光隐约有些倦怠、怅然,然而又是清透的,沉静的,闪动着不为人知的幽秘的光。
——这是我对“立秋”这个词的想象。
在民间立秋的日子要吃西瓜,名为“咬秋”,不明白是什么来由,大概立秋之后西瓜就要下市了,趁着这个节气吃个痛快吧。记得小时候总会被大人警告,立秋时间不得下河或接触冷水,要得秋斑的。所谓秋斑就是皮肤上分布不匀的斑纹,白一块黑一块,很难看的印记。因为这我甚至不敢在那天去河里洗碗,谁知道什么时候是立秋的时间呢。
现在已很少有人讲究这些了吧。民俗正在失落,民间也已成为一个古老的、过时的词了。立秋是秋的开始,万物停止生长,果园即将成熟,但真正收获的日子尚未来临,离落木萧萧的光景也还有一段路程。这个时期更应该名为“晚夏”,经历了整个盛夏的暴风骤雨、烈日焚灼,容颜已有了一些沧桑,而色彩依然浓艳,气息也更为迷人了。
月色撩人
一个身着黑风衣的女人,像芭蕾舞剧中的天鹅那样,单腿立地,双手张开,微微倾斜地迎向天空,犹如夜鹰滑翔在云端的翅膀,海浪般的长发披散着,绻在耳边、肩头——在她身后,是一个巨大得如同房屋的月亮,温柔、神秘,笼罩着她和她的梦境。
——以上描述的是老电影《月色撩人》的海报,电影爱好者们大概都见过吧,就算没看过影片也会记住这张海报和片名,它确实撩起了人——特别是女人对于浪漫的幻想,渴望自己就是海报上那个在月亮女神面前情不自禁、翩翩起舞的佳人。
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之所以迷人,让人在经受痛苦和厌倦的同时仍然愿意活着,是因为,这个世界坚硬粗糙的背面还有轻灵柔美的东西,比如露珠、雪、月光,尽管它们无一不是短暂的、脆弱的,转瞬即逝一如幻象。
几天前——大概是一周前吧,撑着雨伞走在夜晚的小城,抬头的时候,竟然看到夜空有半轮明月,莹润洁净,禁不住叫起来,看啊,月亮,下雨天怎么会有月亮?身边的几位朋友也都抬头,说真是异象,下雨天也出月亮?
这几天我总在夜半醒来,醒来后就赤脚站在窗前,看当空的圆月,天地静阔,没有一丝尘埃。——不知此时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被一种具有魔法力量的光引诱着,醒着。
月亮确实是有魔法的,《月色撩人》里,已经年老的男人在月光下变成了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不再年轻的女人在月光下则变成了天使,明净而忧伤。
又是秋天了,年轻的海子说,“秋夜美丽,使我旧情难忘。”秋夜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盛大浩瀚的月光吗?月明之夜,孤独的狼会在山顶深情地呼嚎,那么人呢?人身体里隐匿的狼性会不会在月亮女神的召唤下苏醒?
长在路边的小花
几天前就看见这些小花了,长在路边的草丛里,桃红色,一串串,米粒一样大的花骨朵。
风一吹它们就起劲地摇摆,风停了它们仍然微微颤动着,像笑得止不住的女孩子,揉着腰,喘着气,惹人怜爱。
这些小花看起来弱不禁风,其实坚轫得很呢。近日来每天都有暴风雨,把路都冲塌了,大树也推到了,但是小花却一点事也没有,今天看见它们还是几天前的样子,依然单纯,向上举着嫩艳的小脸,在傍晚的光束里闪来闪去。
置身植物中间的人是最容易获得愉悦的,也最容易感受到爱,繁杂的俗世消失了,幸福感如泉般淙淙而出,就这样简单地活着、生长着,是多么美好的事。
光精灵
那光是长了脚的,一下一下地跳着。
它还有着翅膀,薄而透明;头上有着细细的、微卷的触角。
长了翅膀的光、会跳跃的光、头上有触角的光——该叫它什么名字呢?就叫它光精灵吧。
它的颜色——当然是金色的。看它一眼,再闭上眼睛,那金色的光会张着翅膀扑闪——满世界都是。
光精灵是从哪里飞来的呢?是不是很久以前就住在这里?哦,这调皮的、爱捉迷藏的小东西,从一根栏杆跳到另一根栏杆,像是故意引逗我,有时会停一停,等我靠近时,它的触角一晃,又跳到另一边去了。
谁能捉到光呢?——它的翅膀那么轻盈。
看,远处,湖面上有更多的光精灵在跳跃——它们是不是在湖里沐浴?
此时的湖面绸缎一样光滑。
白日的喧嚣停歇下来了,船靠在岸边,像一个疲倦的人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微阂着眼,沉默着,任落日蔷薇色的手轻柔地抚摸着额头。
有一只鹰从松林中飞出。被湖面的光蛊惑了一般,它徐徐地、径直地驰向湖面,钻入水底,很快又掠起翅膀,一群光精灵便快乐地驾在鹰的羽尖上了。
这只鹰大概是光精灵的老朋友了吧,黄昏时分,它们彼此邀约着,共享余晖。湖面空阔宁谧,此时的世界一如最初时的本真、浑朴——是它们的。
天空低悬,暮色四合,在湖里游戏了很久的光精灵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走了,也许是被鹰带入山林了吧。或者变成萤火虫,飞到孩子们的梦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