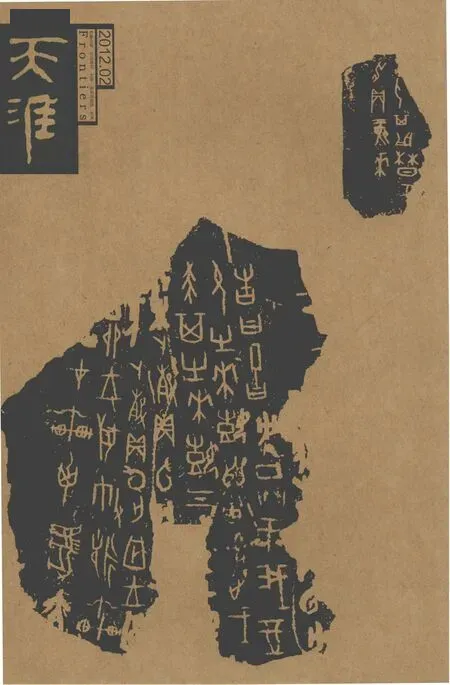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外一篇)
帕蒂古丽
那一年,地里的稻谷还没有收回来,大雪就像盗贼一样从南山那边扑过来,抢夺了村庄里收割的喜悦。
父亲悔得直跳:“嗨,就在地里多放了一夜,谁知道雪这个贼娃子,会趁村庄睡着的时候,把一地壮壮实实的稻谷全给埋起来了。现在镰刀磨得再利,又有啥用?”
“辛苦了一年的收成,总不能就这样送给雪贼,就是一点一点挖,一捧一捧捧,也要把它收回来。不然,娃娃们挨饿不说,连明年的稻种子都有麻烦。”妈妈低头看着隆起的肚子叹了口长气。
这天,村里的大人孩子全都出动了,扛着铁锹、坎土曼、铁叉、木锨,推着手推车,带着畚斗、簸箕、筛子,到雪地里刨稻谷。
稻谷躺在冰床上
雪有一尺多厚,要一锹一锹把雪铲成堆,再运到稻地外面去。等手推车推出去的雪在稻地四周围起冰雪长城,脚下的稻谷才从雪缝中戳出了一根根尖细的稻芒。
再往下铲,都是混了雪的稻谷,人踩过以后,稻谷和雪粒粘在一起,日头一照就结成了块,掰也掰不开了。
这天,全村的人都蹲在地里捡稻子,远远地看过去,就像是在雪海里淘金子。
我和弟弟妹妹跟着大人们在雪窝里淘稻谷,我们用双手把稻子旁边的雪刨开,稻子一棵棵躺在雪上,就像金丝金豆撒开在白白的棉花絮上,金闪闪的耀人眼。
小心地抠掉沾在稻穗上的雪渣子,再轻轻地剥掉裹在稻谷壳上的冰块凝雪,一棵完整的稻穗就躺进我们为它准备的畚斗里。
爹爹走过来,看到我们举着稻穗像看花骨朵一样就跺脚:“还不拿畚斗快点铲,铲起来倒进麻袋里,不把掀开雪层的稻谷赶紧铲起来,要是夜里再下场雪,它们就要烂在地里了。”
我们加快了手脚,满畚斗、满簸箕地撮起雪地里沾着冰粒的稻谷,把大一点的雪块挑出来丢在一边,把裹着冰衣,连着稻秸的稻谷,倒进大麻袋里,往麻袋里倒喳喳作响的稻谷,就像是在倒真金白银。
到日头偏西的时候,我们已经收了一半的稻谷。到日头隐在我们早上用雪垒起的白色长城后面时,所有的稻秸连着谷穗,都和冰冻的大地结成了一整块镶金雕银的冰面,我们终于连一粒稻谷都剥不出来了。
爹爹用一把小锄头在冰面上刨了一会儿,只在冰面上刨了几个白色的小坑。爹爹摇摇头,收起了锄头,套上了毛驴车,把六个装满稻谷的大麻袋放倒在车上,我和弟弟妹妹也一个接一个地爬到了麻袋上面。
大雪从人们手里抢夺过去的宝藏,又被人们抢夺了回来,尽管只抢夺了一部分,至少人们没有完全输给这场大雪。
不一会儿,马车、驴车和手推车都排成了队,跟在我们后面,就像运送宝藏的队伍在雪原上列队行走。还有一些人肩扛身背着麻袋,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朝回看,那样子就像是把孩子丢在了地里。
路上爹爹说,明儿个要起一个大早,把丢在地里的稻谷全都收回去,实在捡不起来的,就让牛羊、鸡鹅来觅食,这么好的粮食,一粒也不能白糟蹋了。
稻谷睡在大炕上
我们把本来躺在冰床上的稻谷,搬回了家里。
妈妈挺着大肚子,抱了一大捆干树枝在炕洞里点燃了火。爹爹掀开了大炕上所有的苇席和毡子,把六麻袋夹带着冰雪的稻谷全都倒在了大炕上,用木锨摊平。雪渣子一遇着热炕,很快化成了水,嗞嗞地冒着热气。
爹爹把苇席、毡子、单子、褥子,一层层铺开在摊开的稻谷和冰雪上,妈妈抱来的干树枝已经堆满了半间屋子。爹爹说:“孩子们,你们拉开被窝,就睡在稻谷上。我和你妈一起把炕烧热。”
我和弟弟妹妹和一大炕的稻谷一起睡得很香。
早上起来,我向窗户外一看,没有日头,鹅毛大雪像会动的棉花帘子一样厚厚地挂在窗玻璃上,一扑扇、一扑扇的。爹爹绿色的眼珠显得阴沉沉的。半屋子的柴禾,全都变成了死灰堆在炕洞里,妈妈坐在炕洞前,脸色像灰一样。
大雪一连下了半个月,每天早上起来,连门都被雪堵住,推也推不开。那些日子,我们不再去稻地里收稻谷,从早上到晚上,我们都在做一样事情,扫雪、铲雪。扫了屋顶上的,再爬下来铲院子里的,扫完院子里的,再铲羊圈里的。刚刚扫干净,又落下厚厚的一层。老天就像在弹棉花,大梁坡村被捂在巨大的棉花套里,掀也掀不掉。
雪停天放晴的那天,村里有很多人还是不甘心地到稻地里去,看看稻谷被雪埋了多深。人们没有一个扛家伙的,两只手筒在袖筒里去,又筒着两只手回来,脑袋和眼睛,像是被稻地里一根看不见的线绳牵拉着,一步一回头,好像那些稻子会在他们哪一次回头时,一下子从雪窝里窜出来,窜到他们跟前。
回来的路上,爹爹的头像霜雪压倒的稗子穗,一直戳进了肩胛里,硬是一次也没有回过头。我替爹爹回头看了看那片稻地,爹爹后脑勺上跟长了天眼似的:“丫头,再看也没法子把在地里的稻谷看回来了,还是赶快回去吧。”
爹爹的步子越走越急,我一路小跑跟到家里。爹爹进了院子,操起靠在墙根的一把木锨就冲进家门,连脚带鞋上了炕,把炕上的铺盖、毡席全掀到地上,他就像大锅里翻炒手抓饭一样,不停地翻搅满炕的稻谷,稻谷冒着腾腾的热气,土炕上不时地露出斑斑水渍。
妈妈、我和弟弟、妹妹抱起地上的潮乎乎的被子,晒到了院子里。本来薄薄的毡子浸透了雪水,变得比平时厚了几倍,我们四个人拽着又湿又重的毡子四角,好不容易拽到了柴草跺上摊平。
炕上的稻谷被爹爹一刻不停地翻搅了大半天。到傍晚的时候,我们把冻得像一张大铅饼一样的羊毛毡子,重又盖到了还没有干透的稻谷上。
晚上,睡在硬邦邦的冻毡子上,像睡在大冰块上,被子怎么也暖不起来,一股凉气从身子底下直往上拔。
“下面火炕烤,上面身子焐,稻谷干得快一点。”爹爹躺在被窝里说这话的时候,牙齿打着颤。
我们睡在稻谷上
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这是全家人睡得最踏实的一个冬天。我们每天晚上早早就躺在火炕上,用身子去暖那些稻谷。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能看到爹爹的胡须上,妈妈和妹妹的发辫上沾着细细的稻芒。
照镜子的时候,我还能看到细小的稻芒夹在我柔软的头发丝中间,它们就像是躺在稻草堆里那么舒坦。一个冬天,我们家的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新鲜稻谷的香气。
每天看着邻居家的大儿子喀力哈孜用石头舀子捣米,他们家每隔一天就都有一顿大米饭吃。那些稻谷躺在我们身子下面,我们一粒都没舍得吃。爹爹说,炕上的这些种子,吃掉一颗,明年地里就要欠收一捧米。吃到肚子里的只有变成粪,种在地里的才能长成粮食。
听了爹爹的话,就是看到有一颗稻谷掉在地上,捡起来偷偷含进嘴里,我都不舍得嚼烂,又悄悄把沾着口水的稻谷粒放进毡子下面盖好。我们硬是忍着,把一天三顿饭,减到一天只吃两顿,靠着喝玉米糊、吞高粱饼和吃地窖里的土豆、白菜,捱过了一个冬天。
冬天终于到了尾巴根上的时候,又一个弟弟降生在铺满稻谷的大炕上。本来睡在妈妈旁边的妹妹,把靠着炕洞和火墙最暖和的位置,让给了新出生的弟弟。
大炕上又多了一个娃娃,家里顿时热闹了很多。我家的门上还挂上了一根透着喜气的红布条。爹爹妈妈的脸也像五九过后的天气,渐渐暖和起来。
妈妈给小弟弟穿上妹妹刚出生时穿过的小棉袄,让我抱他到院子里看冰凌。屋檐下的冰凌吊得有三尺长,像透明的绳索垂挂在头顶上,滴答滴答往地上滴水。
“一九二九不是九,三九四九冻死狗,五九娃娃拍手,七九鸭子八九雁。九九加一九……”邻居家的女孩穿了鲜艳的衣服,扎了漂亮的麻花辫,一边唱一边跳橡皮筋,春天的气息就从她们的童谣、花衣服和头顶的蝴蝶花,弥漫到整个大梁坡村。
稻谷来到了春天
大梁坡村的春天,最先是沿着出去觅食的羊踩出的雪坑里走进来的,深深浅浅的羊蹄坑在春风里一行一行变得水汪汪的,厚厚的积雪覆盖的大地泥土最先从那一个个小坑里重见天日,小小的羊蹄坑从村庄四周越走越远,向着村庄外更远的地方散开去。
眼见着路边的杨树返青,河沿的柳树吐出苍绿的芽苞,结冰的渠沟在晴天里变得水汪汪的,春天的味道慢慢地从冰融雪消的田野上升腾起来。
清早,布谷的鸣叫从河坝那边飞过来,“布谷、布谷”的声音在窗户上、屋檐上飞来撞去,这声音撞到谁家,谁家就像得着了神谕似的,打开仓房,开始清理农具和闲放了一冬的马车和驴车。
爹爹修整好拉犁铧的绳索,把它套在老牛身上,起早摸黑到稻谷地里犁了三天地,他说,这片地去年吃下了那么多粮食,肥得流油,今年根本不用上肥料了。
我们把稻谷从大炕上扫起来,堆到场院里,爹爹给马套上了石碾子。马拉着石碾子在场院里撒了大半天的欢,那些连着稻秸秆的稻谷,舒服地躺在碾子下面打滚。我们在被爹爹的铁叉叉到了一边的干净的稻秸秆上打滚,就像在铺了新褥子的大炕上打滚。
我们把妈妈扬好了的稻谷,用木锨和簸箕铲进大麻袋里,抬到了车上。
爹把驴车赶上了高高的大梁坡。
我和弟弟妹妹坐在摞得高高的麻袋上,村庄一下子变得很矮很矮。我们被装满稻种的大麻袋托在半空中,天上软绵绵的云、地上暖洋洋的风,向着我们扑过来。
案例教学方法并不是将多个案例简单罗列起来,而是一套完整系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案例的设立不能单纯地为了提高教学趣味,而应该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教学安排等,即案例配合哪些章节和知识点,用于验证或运用哪些概念,强调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等[9]。
从坡顶上远远地看过去,冬天被雪埋掉过的那片稻地,已经被犁铧翻了个透,油黑油黑的泥土上,拢着淡白的水雾,日头照在雾气上,返出一道道、一圈圈紫蓝色的光晕,像虹一样。
弟弟和妹妹早已按捺不住,跳下高高的麻袋垛子,在翻得松软的泥土上奔跑。爹爹停好了驴车,卸下稻种,坐在新打的田埂上,卷上根莫合烟点着,美美地吸了一口,眯着眼睛看弟妹们在稻地里撒欢。
我问爹爹:“这么大一片稻田,这几麻袋稻种不够播咋办?”
爹爹捋了一把密密匝匝的胡茬子,对着稻地盘算:“就是种子播稀点,也得把这块地全都撒上种子。今年雪水这么足,这地里,播上一颗种子,就能活一棵苗子,说不定去年埋在地里的稻谷也能发芽。再等些日子,这稻地里就长满绿绿的稻秧了。”
爹爹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他湿汪汪的眼睛就像是两大块水田,成片成片的稻子苗浸在他的眼波里,那些在爹爹眼里疯长的绿色稻苗,一下子盖满了整个大梁坡,连大梁坡上刮过的呼啦啦的风,都被爹爹眼睛里的光染绿了……
担个日头回家
我和弟弟抬着一塑料桶柴油,追着日头往西边赶。日头矮矮的,从弟弟头顶的棉帽上,滚到他窄溜溜的肩上。
赶累了,弟弟蹲下来,把担子的一头撂在雪地上。日头从弟弟斜下去的担子那头,滚到了雪丘背后,像一个茸茸的毛线球,被几棵野柳拦住,在野柳枝挂了一下,就一骨碌扎进了雪窝子里,拦也拦不住。
家里的油灯,已经有几个月不亮了,就等着柴油点灯。
桶底最后一点柴油,被爹爹滴进了马灯里,只在夜里去羊圈看分娩的母羊时,才点一小会儿,然后又很快地被爹爹吹灭。他说,夜里没有了煤油灯,就等于没有了眼睛。
那是大人的说法,小孩子在没有灯的夜里,照样能找到乐子。
黑地里
每天夜里,我和弟弟就着月光做游戏,或者在墙上玩手影戏。做这些的时候,我们早就把耳朵竖在外面了,不等窗根底下邻居家的大个子阿里木那声短促的呼哨声落地,就会有十几个人集合在院子里。
黑黢黢的院子里,从羊圈、驴圈、狗棚子边上、小仓房里摸黑找到躲藏的伙伴,每回都会爆出一连串惊喜的大呼小叫。
没有谁会因为黑就辨不清方向,更不会磕伤头脚。大家熟悉驴圈里驴槽子的位置,知道哪根木柱子松动了,要绕过去,知道从木头梯子的底端上去,要抓住哪一根椽子斜出的枝桠,才不会一不小心从只盖了些茅草和干树枝的驴圈顶上掉进圈里。从那个漏顶的树枝缝里,可以看到受惊吓的驴子在圈里晃动的黑影子。
羊圈里一般是不会去躲藏的,胆小的羊一看有人进来,就像看到狼来了,全都躲在一边,把想藏进羊堆里的人晾在光地里。胆小的羊不会念着我和弟弟整日拔草喂它们,就给我们面子。
羊圈外的草垛上是藏身的好地方。把麦秸、棉花秆往身上一苫,在里面打会儿盹,等来找的人不耐烦了再出来也不晚。
狗棚子边上放着那架放荒好几年,木头车辕快要发芽的马车,马车下面可以躲两三个人,但只有我和弟弟躲进去,我家的大黄狗才不吭声,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敢藏进去的。
就是有人发现,也不敢到车下面来抓,旁边拴着大黄狗,来人要把距离放到狗的铁链子那么长,在一边等我们不慌不忙地从车底爬出来。
我和弟弟在自家院子里,不愁找不到藏身的地方。特别是那间没有窗户的小仓房,只要躲进去,来人就是把每个角落挨个摸过来,也不会被摸到,因为先进去的人眼睛是亮的,后进来的人眼睛就像瞎了一样,躲在那里看别人四处乱摸,最后忍不住要笑出声的。一笑,你就亮得跟灯似的,就是真的瞎子,也能一把就把你从黑房子里揪出来。
魏家庄
我们在太阳收回洒在雪窝子里的最后一点碎光前,抢着走完了一半的路程。弟弟回头朝我看了一眼,撂下担子的那头说:“姐,我的腿累累的,没有力气。”他乞求地把眼光投向不远处一丛灰白色的树窝子,那里是魏家庄。
爹爹带着我和弟弟住过魏家庄魏皮匠家。他们家有一排气派的平房 ,还有一排比平房还要气派的儿子,一共九个。爹爹给魏皮匠的八个儿子做过结婚的衣服,当然也给他的八个儿媳做过嫁衣。
我给弟弟打气:“我们晚上就住到魏皮匠家,再加把劲!”弟弟使劲点点头,然后蹲下身去,抬起了柴油桶。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魏家庄。
迎接我们的是魏皮匠家的狗,它叫了几声,过来嗅嗅我和弟弟,围着柴油桶转了一圈,甩甩尾巴走开了。
魏皮匠最小的儿子一掀棉门帘走出来,从屋内带出一股热热的雾气,我闻得出那是揪面的葱蒜味道,飘着魏皮匠特有的熟羊皮的膻味,每次我跟爹爹住几天回去,身上都沾了这股味,我家的大黄狗老远看到亲热地扑上来,嗅到这股陌生的气味,每次都会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我们。
魏皮匠家装了电灯,照得屋里明晃晃的,像是白天。
我看见弟弟吃饭的时候,圆圆的眼睛里拴了两个小灯泡。弟弟也扭过头小声地叫:“姐,你的两只眼睛里挂了两只灯泡。”
吃饱了肚子,弟弟央求魏老九:“夜里我们到院子里捉迷藏。”
魏老九笑笑,摸摸弟弟的头:“捉迷藏鞋子会湿掉,明天一早就赶不成路了。”
魏老九打开了一个电匣子,里面黑白的小人都是活动的,会唱会跳。我们对着那些个活动的小人傻坐了半个晚上。
夜里弟弟爬进了被窝还在嘟哝:“黑匣子那么好看,难怪九哥不跟我们捉迷藏。”
我拍拍弟弟的脑袋:“睡一觉,日头就出来了。”
“我要日头 ,不要电灯。”弟弟说完就打起了鼾。
担日头
早上睁开眼睛,日头明晃晃地趴在窗户上,探着头在催我们上路。
魏老九已经从锅里捡出热腾腾的玉米面馒头端到桌上。我和弟弟抹了把脸,一人捧了一个热馒头,就去找昨晚放在门背后抬柴油的木担子。魏老九冲我们笑笑,自个儿提起柴油桶子,一掀门帘,大步跨到了院子里。
我提了担子,拉着弟弟,一路追着魏老九在雪地里踩出的大脚窝跑。等我和弟弟把馒头丢进了肚子,魏老九的身影在很远的地方晃动着,只有一个小麻雀那么大。
我们在一片坟地里追上了魏老九。他立在坟地中间的雪路上等我们,见我们呼着热腾腾的白哈气跑上来,就弓下身子冲我们笑。
“过了那片坟地就是运河,从结冰的运河上走过去,大梁坡村就不远了”。顺着魏老九手指的地方看过去,能看到村口的那棵老榆树。
魏老九停在原地不走了,他看着我们抬着油桶走出坟地老远,还立在坟地中间朝这边招手。直到我们下了运河堤坝,从冰面上一边走一边滑到了对岸,魏老九的影子才往回去的方向慢慢移动。
弟弟说:“九哥有小匣子,就不捉迷藏了,鞋子也不会湿掉了。姐姐,我喜欢鞋子湿掉,夜里爹爹帮着我们烤。”其实我心里头也这么想,弟弟走在前面,看不见我点头。
“姐姐,昨个天黑我们经过了那个坟地了吗?”
“黑地有黑地的好处,黑地里,坟头也只是些矮矮的雪丘,没啥了不起。”我哄弟弟。
弟弟说:“我们朝着村庄走,日头也跟着我们回大梁坡,姐姐,日头肯定欢喜呆在大梁坡,不欢喜呆在魏家庄。”
“嗯。昨天我们快走到魏家庄,日头就藏进雪地里了。魏家庄有电灯,我们村没有,我们村有日头就行。”我应着声,换了个肩膀,日头从担子的左边移到了右边。
“对,日头出来,我们就去放羊,等日头睡了,我们就捉迷藏。”弟弟在前面看着那棵老榆树一路小跑。
我在后面护着柴油桶,它是我们担在担子上的日头,我生怕弟弟把它摇落了。
我跟弟弟说:“走稳了,咱们把日头担回家去。”
弟弟把小肩耸得高高的,冻得通红的手一甩一甩的。我在后面嘻嘻地笑,日头在担子上也乐得一颠一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