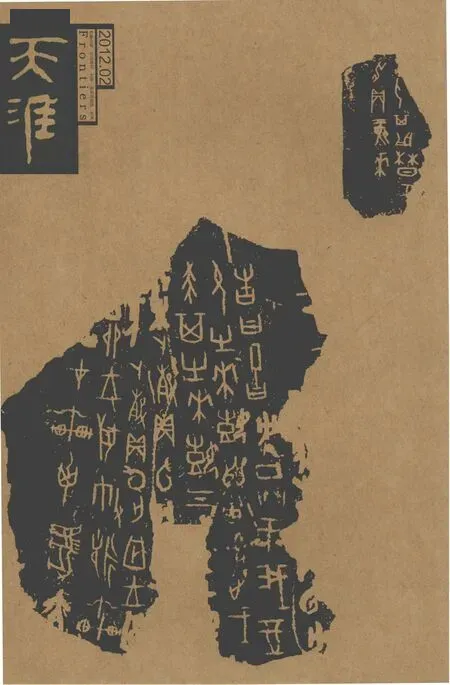我这三十年
王新华
父亲的“工龄”怎么算?没有进过一天校门的父亲,能牵住一条绳头的时候,就给人家放牲口了。今年,七十六岁的父亲还一个人拉着家里为他保留着的两亩地,种着麦子、花生、红薯。父亲的工龄约等于他的年龄。我的事情也简单,两段直线:从十八岁高中毕业到三十八岁出门打工至今,我种了整整二十年的地,打了十年的工。这个三十年,现在正浸泡在歌声的海洋中。
从高考的考场上下来回到家里的那一会儿,门锁着。此时正是三夏大忙。我把书包、铺盖放到猪圈上,一大一小两口黑猪都抬头朝我哼唧了一下,像是欢迎这个少东家。找到了地里,父亲正在麦茬地上耧黄豆,他高卷着裤腿,踏着一双破鞋。在前头给他帮耧(赶牛)的是队里的会计西吾,我们两家的牲口搭犑。一个带耧,一个拉耙。听说我考完了,西吾问:考得咋样?我说:不……不咋样。父亲往耧斗子里添着豆种,没有问。从七岁上学到今天的最后一天,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西吾说:不咋样就不咋样吧,回来跟你大种地,这年头阿老土地爷(种地),还真不赖!说完,西吾手里的树枝在牛脊梁上轻轻地悠一下,耧就晃晃荡荡地向地那头走去,耧蛋甩悠着木头,呱嗒,呱嗒。身后,是划破的三道黑土,湿漉漉的。抬眼望去,田野上热气烘烘。没有牲口的人家三两户搭帮,用人拉耧、拉耙,趁墒抢安庄稼。他们的脚步沉重却又轻快,像是刚上套的马匹。
这是八十年代的开头,人们刚刚分到土地,谁干是谁的。太阳光洒在田野里,遍地金黄。这一年夏收,西吾家人多家底好,舍得下本,一下子打了万把斤麦子。三夏结束,西吾被县里选派到郑州参加一个表彰大会,回来,又从县里推回一辆加重永久牌自行车。
转眼就是一年的腊月,除夕。除夕这一天,乡下人又闲又忙。上半天贴门神,下半天上坟地,烧纸。贴门神不光是门上的活,鸡窝、猪圈、牛槽、麦茓子上,都得贴。午饭才吃过一会儿,四面的爆竹就开始炸响了。野外,到处是一团一团的人和弥漫的烟雾。这会儿,人们都相信是自己深埋在地下的已经烂成泥巴的父亲、爷爷、老太……让他们今天又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外面的还没有断,村子里的爆炸声又接上了。一些动手早的人家开始吃年饭了。梗辣的鞭炮在一家家院子里爆炸,家里的狗也给吓懵了,以为末日来临,有的夹着尾巴往村外跑,有的钻到床底下发抖。整整半天的时间,村庄是在一刻不停的爆炸声中过去的。初一不出门。初二一大早,天寒地冻,有的人就出来了,早饭以后,路上的人就扯上了线,骑车的、步行的、背包的、擓筐的。这些都是到亲戚家拜年的。晚半天都是回头客了,路上,不断看到有人倒在地上,车子摔在一边,同路的拉都拉不起来。饭桌上敬酒、划拳、打通关……一路下来,不少人都喝大了。
那个时候的人喝酒都顺畅得很,像是夏天从地里回来抓住一瓢凉水。村子还没有通电,元旦的晚上我领着几个人到临村的一个亲戚家看文艺晚会,这家有一台黑白电视了。进门的时候,屋里有几个客人,还正在吃饭,主人说,迈门槛,吃碗饭,非叫我们再坐上喝几杯。离晚会开场还有半个小时了,我说,咱们推快点,不能耽误看节目。一桌人分两半,酒斟满,一对一的划拳,输酒的一方都端起来。晚会开场了,我们准时停了下来。老主人低头点了一下脚底下的空瓶子,半个小时,我们搞掉了六瓶白酒。
晚会上还没有小品,歌曲不少,有于淑珍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彭丽媛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个山东的乡下姑娘对着她的父老乡亲唱道: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
那时候,有的人家嫁闺女也不弄那些杂七杂八的了,干脆陪嫁一条牸牛(母牛)、犊子,脖子上系朵大红花,也像个大姑娘,那天早上跟着新娘子牵到婆家,排场得很。牸牛能拉犁,还能下犊。闺女是一心跟你过日子的。“要想富,三个破屁股”这句话过去没有,是乡下的新民谣,一是老母猪,二是老牸牛,三就是老婆了。
种完麦子,封好红薯窖,就入冬了。早上起来,地上白茫茫的。这个时候,我骑着车子去找洪举玩,我们已经半年没有见面了。洪举是我高中的同学,我俩睡在一个被窝里。洪举个子不高,一点脾气没有,又有点多嘴,是个巴掌垫子。对他我也是张口就骂,举手就打。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学过杜甫的一篇诗,洪举挨了打,嘴上就来一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这趟路四五十里,在一个河湾里摸到了他的家。可是,洪举不在。洪举已经在不远的一个学校里做了老师。按照他父母的指点,我找到了洪举。这个村办小学,一块砖头、红瓦都没有,全是低矮的土坯房。洪举的一间房子小得很,还要在里面烧饭。烧饭用的是一个小煤油炉子,烧的是柴油,火不旺,烟大得很。他摸上摸下的,脸都抓上了油灰。这顿饭,上面的米粒还是硬的,底下的已经煳了。饭菜好歹不说,老同学相聚连杯酒都端不出来。我说:是学校请你来的?洪举说,哪有那好事,是找咱主任介绍的。高中的主任跟洪举同乡,同姓,在学校他们就来往不少。洪举说:新华,你也要活动活动,进个学校。我没有搭腔。临走的时候,我说:洪举,你家里就没有田地吗?看你狗日的像不像个要饭的……
分地像一棵长篙,一撑,停滞的小船就轻快的离岸了。可是,以后的日子,再也看不到有谁真正推过一把。小船,便一年又一年的在水面上漂流,打转。
二十年里,我家的人口没有少过五个。几次重新调整,土地一直在十二亩以上,种植着小麦、红薯、烟叶、棉花、芝麻……
红薯是庄户人家的仆人,耐干旱,收成大。不管是十口八口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门户,没有不栽的。鲜红薯人和牲畜都吃不完,主要是晒干,从垄子里扒出来,就地一片一片的切开,撒满一地,晒干了,再一片一片的捡起来,下雨了,就烂掉。每年,好的、烂的就是几十麻袋,好几千斤。留够人吃,喂猪的,剩下的卖给县酒厂。1985年我要结婚,父亲拉了一大车子,是好的,八分钱一斤,卖了五十多块钱。
烟叶是村庄的一个入侵者。作为大田的庄稼,它带来的是不安。以前只有吸烟袋的老头子在房前屋后栽几棵,叶子老了就打下来用麻绳系着吊在屋檐底下晾干。现在这样的叶子公家不要,要烤出来的。几户搭伙脱坯盖一座烤房,像是个炮楼。买几吨煤堆在旁边。摘来几车子叶子,一片一片的绑在竹竿上,一层一层地架在炕上,一炕接一炕地烤。一炕要烤六七天。一季子要烤十来炕。三伏天,手上粘着的烟油子逮到出汗的脸上,小刀子划的一样疼。烧炕的人还要一回又一回的钻到七八十度的烤房里查看。烤得好的,叶片金黄,一斤卖个三块五块。烤得不好是黑的,几毛、几分一斤,柴禾的价钱。其实烟叶的质量在大田里就决定了,有的地块根本长不好烟叶。长不好不是地不肥,长不起来,是长起来的叶子很大,却烤不好。我家每年都种好几亩,我买了一些从种植到烘烤的技术书籍,认真地看,认真地做,可是没有一年是满意的。有一年烤房还起了火,几百杆子烟叶和烤房一起烧毁。烟草是专营商品,人和牲畜又不能吃,几百、上千斤的烟叶只能卖给县烟草局这一家。压级压价。很多农户种了多年烟,头两个等级没有卖过一斤一两。不少人家有时连化肥、煤钱都弄不上来。不种?有任务,完不成罚款。我们北面那个乡的一户人家实在不愿种了,没有留茬,都种了麦子,开春的时候乡里带人来犁他的麦地,他上去阻拦,压阵的派出所民警开枪打断了他的一条腿。
棉花是刚过门的娇媳妇,难伺候。棉花也有任务。提到棉花,首先想到的就是药瓶子,喷雾器、蚜虫、红蜘蛛、棉铃虫。棉铃虫厉害得很,它咬一口,一个棉铃就脱落了。村里用过的所有农药都治不住它。那天我在地里说棉铃虫,娘压低声音对我说:别老是棉铃虫棉铃虫的!我知道,娘已经把那个东西看作小仙家了,越说就越多。有的人没办法,一家人都下到地里逮,逮住一只就把它挣成两截。一块棉田,枝繁叶茂,像一片大海,你能逮住几个?这样干很过瘾,也不过是狙击手式的复仇。那天吃过午饭,我就背着喷雾器,拎着药瓶下地了。这又是一种新药,听说厉害得很。三伏天的午后,热得很。我们都相信,气温最高的时候喷药,效果会好一些。喷了两桶,就有些头晕。我的衣裳早已被汗水和药水湿透了。这样的时候,人的毛孔都在张开着,接触农药,容易皮肤中毒。我赶紧丢下喷雾器,下到地头的乌龙港里洗一下,就往家里走。回到家我没有吭声,就躺下了。妻子觉得不对劲,过来一问,知道我中毒了。这时我开始呕吐。妻子赶紧从外村请来医生,挂上阿托品……我过来以后,妻子怪我,中毒了咋还不吭声?我说,我一个壮劳力的,想等一会儿,没事就算了。去年这个时候,东边村上的老欧给棉花打药,中毒后死在了乡卫生院,他爹拉着他回家,十七岁的孩子了,架子车太短,两只脚在地上拖拉着。种地也不光是流汗。怀正被手扶拖拉机甩下来了,摔断了胳膊;闻二耙水田,指头粗的耙齿从脚底下扎进去,脚面上露出来;子亮犁麦茬,小四轮掉到沟里砸在身上,他自己又爬了上来,说没事,连皮都没有破。女人看他脸色不对,叫人把他送到乡卫生院,一瓶子水没下来,就胸闷而死;没有风,用柴油机带大风扇扬场,忙乱中,春娘身子碰到了扇叶上,胸腹被劈开,当场死去……这些,都是一家一户的私事。村庄上没有工伤。
麦子是爹娘。对麦子,用不着说什么了。麦子的颜色就是庄稼人的肤色。我家每年都种十来亩麦子,打六七千斤。这些麦子一家人一年吃不完,吃不完的都一袋子一袋子的卖掉了,变成零花钱。猪断料了,有时也灌一袋子粉一粉。麦子喂猪,心疼人。不过,麦子的头一个去处是粮管所。麦子还堆在场里,交公粮就开始了。交公粮其实不是交,是农户向国家出售商品粮,可是交公粮的人都不知道,或者都不相信这里头有一个“卖”字。我家每年上缴一千多斤,我一车子,父亲一车子。交粮的麦子摊得很薄,在毒日头底下晒,父亲还一遍又一遍地翻着,像是在锅里炒瓜子。午饭后,麦子晒得烫脚,趁热收起来。已经很干净了,还要再扬一遍。我挥着木锨把麦子抛向风中,父亲握着一把大扫帚在底下漫着,下落的麦子打在他的破草帽子上,像是一阵暴雨。父亲叉开弯曲的双腿,漫得很细,不放过一星儿杂物,一颗麦帽子。上缴的粮食不是自个吃的,验不上,再远的路也还要拉回来。粮管所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和车子,还有牲口。人们都巴望着自家的麦子能一下子验上,交掉,拉着一把空车子回家。一袋子麦子百十斤,光溜溜的,上了年纪的父亲已经搬不动了。可是一到验上了,抢着上磅下磅的那一会儿,父亲就能搬起来就走。磅好了,我们搬着麦袋子爬上一个梯子,进入已经淤满的大仓。金黄、滚烫的麦子像无边的沙丘。麦子上面斜摆着一趟木板,我们还要顺着木板爬上去,把麦子倒在最高处。这时,人的身上没有一点干的,裤头往下滴水。麦子倒完了,父亲搂着十几个空袋子出来。我在开票的桌子上领到一张票,不看一眼,就把它交给了守候在一旁的村会计。会计怀里抱着一个黑皮包,里面都是粮条子。二十年里,我这样交掉的麦子大约有三万斤,除了有时多出的那几斤,没有见过一分钱。总有一个两个慢腾腾的人,没有及时去交粮。村干部找到他们,训骂中总少不了这样一句:都不交粮,解放军、城里人没有一分地,他们吃什么?
后来,光夏季交麦子已经不中了。
麦子的价钱虽然在一分头一分头地长,从过去的一毛多钱一斤长到后来的六七毛,可是,麦子实际上是在一天一天掉价。过去的城里人,一个月拿三四十块钱的工资,可以买三百斤粮食,现在他们的工资起码能买三千斤。一斤米可以蒸三大碗干饭,叫一个人一天都不饿。一斤米却只是他们一根香烟的价钱。水子的舅舅在文教局工作,一家人都住在县城,吃商品粮。那时候我还小,每到暑假,水子的舅舅都会把两个儿子送到乡下来,吃倭瓜、吃红薯。我家和水子只隔一户,我和水子的两个表兄弟也玩得很熟,他们比我高,还不会凫水,两手在沟边上按着地,两只脚在水里扑通,不敢往当中趟。我们都叫他俩“沟趴子”,那是一种一天到晚都趴在水边的小鱼。现在我们都中年了,这些年里我没有在这个场院上再见到过他们。从县城到这里,坐车三块钱。有一天我随口问过水子,水子面无表情,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穷人没有富亲戚。水子种地细计得很,村里都知道。
麦子越来越不顶事了。记不得从哪一年开始,每年的秋季还要秋征。那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抢收抢种劳累一天的村民有的还没有摸到饭,黑暗中便被紧急召集到一起开会。会议传递上面的精神:秋征。就是秋季征收。一人多少,有钱交钱,没钱以实物折价。这一年,我们淮河流域遭受大水,这回征收的数额,大大超出了庄稼人的承受能力。会场上,有的叹气,有的咒骂。那一夜,劳累一天的我却无法入睡。我觉得一睡着,这个男人就算死了。我爬起来写了一点材料。第二天我边干活边开始活动几个群众代表,想一起到上头说说。没有想到的是,那几个在会上骂得很凶的人都不愿意跟我出去。他们把头埋在膝盖里,他们准备变卖东西,准备出去借钱,挺过去就安稳了……
麦子种完,一年的农活结束,这个时候,外工就开始了。
外工就是义务工。修路、垫地、挖河,每年冬天都有。也不只是在冬天,那一年修柏油路就在春夏,跟地里活搅了好几个月。
出来之前我出的最后一场外工是挖河。那是一条小河,它的名字我都写不出来。工程开始了。乡间的道路上都是向工地进发的人流。这些人都拉着架子车,车子上装满了粮食、铁锅、柴草、铁锹、铺盖,还有檩条、塑料布……现在有个人决定在这个地方筑一道长城,这道长城是一定可以起来的。只是,我怀疑当年修长城的民工,当地政府是管吃住的。民工从全国各地征发,粮草这些笨重的东西,千里迢迢,都是泥巴路,靠人拉肩扛能有多少?即使随身携带了,恐怕在路上就吃完了。长城不是十天半月的活。现在,挖河民工吃的米、面、油和烧的柴禾,都是管事的人拎着秤杆,按人头一家一户兑出来的。干外面的活,吃自己的。这样的活,男女老少干得都很有劲。不管是谁的活,摊到头上就是自己的。架子车的后面都拴着几条绳子,大锹把车子砸满,几个人倒拉着,爬上河坎,再飞跑起来,掌把的人瞅准时机,把车子猛地一扎,凭着惯性,一车子土就闪出去了。河埂在一点点地增高,河道在一点点地加宽,加深。三十几岁的我,正有劲。一尺多长的大铁锹,头点两下子,就登满了,锹把往后一扳,一块大土就起来了,几十斤的东西我顺势端起来,砸到车子上,车子摇摇晃晃,吱吱作响,扶车把的女人吸溜一下嘴,叫着:轻一点儿!车子是她家的。我说:你当家的比我还有劲哩!冬天的田野没有遮挡。男人尿来了,走开几步,低下头就凑合了。女人不管事大事小,是要露屁股的。有的还是个闺女。女人有事了,都是几个人撺掇一起,走出一段距离,然后并排站着,像是一段墙,一个一个的轮着在墙后面蹲下。夜里,几十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半夜里寒风会把棚子撕开,像野兽一样钻进去。这个夜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醒来。第二天,男人和女人都讲述着一个差不多的梦:夜里,身上的被子被人揭走了,或是掉进了一个雪坑里,怎么也爬不上来。
泥巴块子支起的一口口大铁锅,烧着几十个人的饭。在这样的锅里吃饭,饿得再狠,头一碗也不要盛得太满。要不,第二碗可能就赶不上了。
我们西面的那口大锅,是邻村的。那口锅上吃饭的一个老头子,该七十了,比我父亲还大。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露着棉套,天天端把铁锨给车子上土。吃饭的时候,老头子不像别人那样几个人伙着一个盆菜,他总是一个人蹲在一边,米饭上头放着一点青菜,嚼了半天才一伸脖子,咽下一口。他吃得慢,风吹着,吃着吃着米粒就硬了。这个老头我也熟悉,他有几个儿子,老大叫社会,老二叫主义,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上学。工地上没有看到他们,可能都外出打工了。老头子吃完饭,还要低着头,恶心一阵,吐几口。有人问他咋了,他也不吭声。那锅上的一个女人悄悄地告诉我们:老头子得了噎食(食道癌),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到年下的饺子……
2000年冬天,当世人纵情欢呼新世纪第一缕阳光的时候,我随着人流走出了黄淮平原那个沉寂的小村庄,来到江苏南端一个叫吴江的小城,成了一名外地人。
我找到的工作是给一个私人老板做水电工。我的面前:钢筋、混凝土、脚手架、吊塔……彻底地置换了田野、庄稼和牲畜。带班的看了一眼这个新来的:啥都不会,除了打槽!说着就把一把錾子、锤子扔到我面前。我赶忙捡起来。锤子在地上留下一个坑。
这个时候,我三十八岁。村庄上有一句骂人的话,没一个脏字,却厉害得很:你瞎活了这么大!这一刻,我知道,这半辈子白活了。
我的旁边,是一台混凝土搅拌机,巨大的料仓运转着,像一阵闷雷。一个人正把一袋百十斤的水泥搬起来,放进料斗里,铲破,袋子拉掉的时候,一阵粉尘腾起。这个人,像是一条滚好面粉的鱼。这个人头发差不多全白。他也是白活了。他比我走得更远。不知道是哪里人,但我相信他会撒种、会扬场、会使唤牲口,会编筐、会搓绳、会扎笤帚。这些都没用了。这样的年龄,在另外的人群里,他已经干完所有的活。不管以后再活多少年,他需要的东西都会凭着一种惯性,从他的身后源源不断地涌来。
这些年里,工地、老板、伙计像嫖客一样更换着。个别处的时间长一些的人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文化,就问:咋没弄个民办教师干干?现在,孩子也长大了。一天,我下班回来一身灰,多日没剪的头发被安全帽压得像个鸟窝。吃饭的时候,女儿忽然问道:爸,你——怎么没有教学呢?
我知道,说这种话的人,是在悄悄地审视、质疑着一个人。
这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洪举。我和洪举已经十几年没有联系了。一个夜晚,在自己的这台旧电脑上我打出这个人的名字,前面又加上一个地名,一搜,还真的出来了。那是县里举办的一次教学论文评比,在一个标题后面,是他的名字。黑白的页面上那两个字是红色的。老同学这么多年没有音信,这样的文字我也不想用指头把它找出来读一下。可是我知道了,洪举现在还在教学,在一所初中里。这么多年,身份几乎一点没有改变。这就是那个熟悉的、那个矮矮的、那个有些卑琐的洪举。可是,这些年里,我们村里的民办教师都转正了,成了国家的工作人员,连那个一直在校办的酿酒作坊里烧酒卖酒的“老师”都转了。不用说,这个洪举也早就转了。我不知道洪举现在拿着多少工资。我知道,洪举的工资是按月发的,星期天,节假日,刮风下雨,一年三百六十天都有。洪举还有一份个人档案,他这些年的劳动有人在专门记录着。2009,这个人的教龄也快三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