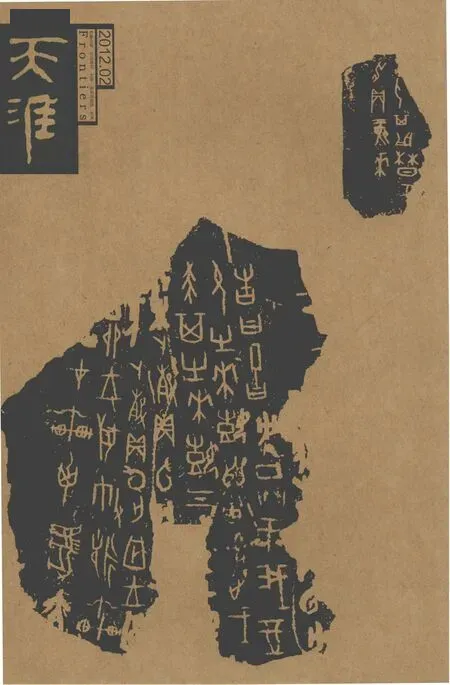谁能免除忧郁?
耿占春
这个社会里稍稍有一点良知的人,稍稍对生活怀有一点精神期待的人,或对生命自身的估价稍稍偏高一点点的人,这么说吧:任何一个稍稍想活得有点意义、有点尊严的人都可能患上了或重或轻的抑郁症。
抑郁的主体或者忧郁症的主体本身就是一个悖谬现象。抑郁的主体就是作为一种特别现代的和特别悖谬的现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出现在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生活中。抑郁瓦解了主体,抑郁消解了主体性,然而如果没有一种主体和主体意识的话,又不可能形成抑郁或抑郁症。这是一个悖谬,这是一种主体性缺失之下的主体,这是一个被动化的世界里残存的主体性感受,这是一种启蒙理性式的行为主体和浪漫主义的抒情主体精神的剩余物。就更贴近我们自身的抑郁状况而言,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意志全部消失之后的纯粹消极生活的一个后果。我们自身的抑郁症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结果中的抑郁症,就是说,不是那种快乐之后的有点疲惫和无聊的忧郁感,而是无法消除的伴随着屈辱感和失败感的那种抑郁。二者之间即使沾着一点浪漫主义文学的远亲关系,我们自身的抑郁症还是深深地烙印着极权主义社会的印迹。
抑郁状态的范围或许很宽广,从对琐事兴高采烈的无聊感、孤独厌倦到郁结之气无法散去,长期徘徊在失眠与生命的边缘,抑郁状态几乎容纳了志得意满之外的大部分灰蒙蒙的情绪领域。那么,抑郁是一种失败者的精神状态吗?
在抑郁真正形成之前,人们总是体验着无聊感、无奈感、孤独感。
无聊:没有意义,没有生活目标的状况。生活又过于琐碎、具体。或许,我们知道目前有一种共同的目标,然而却无法向着这个目标勇敢地走去。经济社会学所主张的最终价值即个人的快感,已经不合时宜地预先抵消了任何一种牺牲精神。人们知道,值得为正义牺牲,却不值得为实现人人皆有的快感而牺牲。这个不符合我们自己心中并不清晰的逻辑。
无奈:没有办法,一种稍稍带着屈辱性的无能无力感。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即使在功利主义之后,在个人在世的快乐主义之后,为个人生活留下的意义空间已经很小,这很小的意义也难以实现。我们知道一种话是假的,但不能不说;我们知道一件事是不对的,却不能去反对。因为,假如如此,你就会失去并不快乐的剩余的快乐,失去已经没有自由的政治与道德含义的自由。
孤独:没有交流。但是一种没有实质性交流的热闹环境也是一种更刺眼的孤独。或许,交流很热闹,但没有“交流伦理”,即没有“对话伦理”与“协商伦理”,没有共识原则对社会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一切有道理的话都与无道理的话一样沦为废话。而政治废话却支配着一切。你感知到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一个群体的孤独,几乎是所有社会群体的孤独。你说尽了一切,然而依然毫无意义。
抑郁是生活意义感的消失和有效交流的缺失。可以说抑郁状态就是一种孤独的主体性。在聚饮、旅行、性的交流的短暂瞬间之外,我们的生活时间被抑郁所充塞。
抑郁的形成有赖于一种特别现代的精神氛围,即有赖于一种特殊的个人敏感性。这是对关涉到一个人内心世界时的那种特别现代的敏感性,对自由经验的敏感,对尊严与屈辱的敏感,对快乐与痛苦的敏感,对情感及其内在复杂性的敏感。整个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化助成了这种人文主义的人格化的敏感性。通过被称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其之后的现代文学,尤其通过传播更加广泛的影视艺术,有多少本来只属于极少数敏感的个人所拥有的内心生活被提供给社会,被推荐给作为阅读社会的大众,被推荐给作为观众的人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构成的历史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文学性,有着文学叙述的参与。
抑郁的人是一种特别敏感型的人,或许可以说是一个特别文学性的人。一个培育了人们的普遍敏感性的社会就是一个浪漫化了的社会,一个使浪漫主义的抑郁氛围成为常态的社会。这是一个积极地体验着的社会,体验并积极寻求表达着、阐释着自身的社会,这是一个诗化或文学化的社会。人们敏感于爱,敏感于自由,敏感于尊严,敏感于屈辱、死亡、不自由、毁灭和一切负面经验。这是一个社会借以建构一个更富于人性化的社会的好时机。除了这一点,现代社会及其制度已经没有别的根基。
因此,并非所有的敏感型社会都必定是抑郁的。如果有效地实践着自身的敏感性,有效地将自身的情感、理性与意志诉求表达出来,并影响着我们身边的社会进程。
抑郁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主体性自身的状况。这是主体性的主体功能之丧失所导致的一种结果。丧失的主体性被主体意识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意识的疾病。抑郁是主体性所丧失的功能重新返回主体自身加入了主体的失败的自我认知。
除了敏感性的人置身于一种敏感型社会,抑郁症的出现或抑郁状态的流行意味着一种社会生活状态的出现:一是表达的无效、表达的无力感;二是主体及其行为的丧失。一个久已被文学话语所唤醒的主体性,却不知道如何去行动,他拥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他的行为受到什么力量比如法律的保护。
抑郁的一个表征是,抑郁的人很难把某种想法付诸行为,抑郁的人甚至很难把某种想法真切地表达出来。或许有着外部的压抑机制,然而也还有其自身的特性。抑郁不是别的,是抑郁的人自身的想法和自身的愿望带上了自我取消的因素。抑郁的人是思想自我缠绕的人。抑郁的思想就是自我缠绕的思想。现代思想因为其自身的自我反思、自我质疑的特性而带有这种自我缠绕的抑郁性。
或许,当整个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化在培育一种新的主体性时,在促进一种社会主体即政治、经济和法律主体向更具人文主义内涵的主体性转变时,文学就在同时培育一种近乎抑郁的主体性。文学培育了敏感型的人,培育了人的内在性,然而文学所表达的主体性总是倾向于其内在性,倾向于更复杂的感知而非外部趋向的行为。
当行为与认知过分脱节,启蒙式的理性主体同浪漫主义的情感型主体一样,都会面临主体的抑郁。
现代社会极大的激发了个人对社会生活的感知,即使在意识形态受控的社会和新闻管制的社会,互联网这一新型的媒介也极大的扩展了个人的知情权。这是一个没有政治真理没有政治领袖的政治成果,一个除开政治上中性的媒介之外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社会推进者的“进步”。然而,一个人获得了巨量的社会信息,却不知道如何做出回应。他的道德性的回应也会被封闭在一个无效的回声所产生的噪音状态。他知情,却不能对事情的进程有丝毫的影响,就像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你不喜欢的事情在眼前发生,却几乎束手无策。虽然"旁观"已经是一种积极的策略,但似乎永远旁观下去也徒然增加了看客般的无力感。
伴随着过多的、重复的、叠加的、复制的信息的大量传播,这些过多的过度的信息,就像无法消除了垃圾,也会返回到主体的感知之中无法消化。多余的信息似乎也在帮着制造出多余的主体性。
躲在虚拟空间里,躲在一个面具后面,一个人可以不停地发帖子,然而你的话可能引不起别人的注意与兴趣。你可以写博客,然而没有什么访问量和点击率。没有人听人说话是因为每个人都在说话。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的孤独景观。不错,或许这样的"写作"这样的信息的提供促进了社会生活的透明度,也提高了人的知情权,然而这些公共话语和表达方式根本无力触及个人内心最为隐秘的经验。公共话语与社会话题的巨大流量甚至一度遮蔽了它。
在有效性行为缺失的时刻,新的传播,大量的传播,制造了因过量的信息流量所带来的新的眩晕感、无助感与孤独感。这不是老式的信息封闭式的孤独,新的无助与孤独是信息的过多,难以回应和难以消化造成的。过量的道德灾难不只是带来道德情感的觉醒,也同时带来对道德情感失掉回应,带来迟钝与麻木。
抑郁意味着人们有太多的信息无法消化,当然也意味着太多的愿意没有实现,太多的情感没有表达,但这些还不至于致使人抑郁:抑郁是至少表面上没有了愿望,没有了情感,没有了表达的冲动。
传统社会里建立在集体生活和氛围中的荣誉感与尊严感随着社群基础的瓦解而消失了,也随着个人主体化的纯经济过程而丧失了。在今天的社会历史中,就像我们绝对地错过了民主精神与自由女神的青春时期,那些未曾实现的制度梦想连起理念都开始衰老了,欧美的经济危机(尽管这是一种福利社会的危机),让一部分人感受到自由女神与民主精神的迟暮感。至少是,伴随着民主与自由的历史青春时刻的那种政治荣誉感和对民主与自由的英雄式的热情已经被历史带走了。但是,我们所经历的热情的衰落并不是实现了爱情的婚姻生活中的激情消退,压根就是从激情的理念到没有激情的理念之间的衰落。
基于个人伦理的自由、尊严、意义感从没有能够作为一种制度被确立起来。
在一个较短暂的时期内,半自主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人们从压抑的内心生活和内在性转向一个经济生活上有效的行为空间。金钱和财富激发了人们在政治上毫无出路的剩余的热情。发财致富使一代人找到了精神生活的似乎是更加愉快轻松的替代物。自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人们开始在市场上在各种各样的小公司和皮包公司里找到了他们失去的自我。在所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官营匮乏经济体制内,权力支配了每一粒米,几代人度过了难以想象的贫困生活。虽然政治制度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但仅仅是社会生活中私人经济空间的出现,财富的奢华面容已经让一代人欣喜若狂。财富的狂欢节驱散了1980年代末笼罩在一代人头上的抑郁。对许多人来说,至少就最初的一批下海者来说,金钱成为最有效的克服抑郁的良药。至少对一批成功者来说是如此。
正是因为没有规范的市场,没有市场经济法,没有合法的市场经济必须有的自由工会组织,极少数的人们带着更深的原罪富裕起来了,大多数的人们再次成为牺牲品。人们一夜之间忘记了半真半假的对资本与剩余价值学说的诅咒。但是,毕竟,在最具垄断性的权富阶级之外,还是衍生了一批小资产者,衍生了渴望做小资产者的生活梦想。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一代人最富活力的时刻将消逝,权力体制在巨额财富的腐蚀下某些环节似乎因腐朽、腐败而松动了,但以权力资本或人们所普遍加以正确指认的权富资本或权贵资本的力量正在迅速掌握这个社会,在一个被权力操控的市场上,只有权贵资本才有其前景,没有权贵资本背景的新兴的较小的资产者,依然缺少参与推动社会进程的机会。这些中小资本者中的一些人、一些胸无大志并十分在乎那些蝇头小利之徒则满足于经济上的分一杯残羹的处境。他们中的一些具有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人则慢慢度过了金钱的陶醉状况,开始厌弃纸醉金迷的纯粹逐利目标的生活。这些中小资本者,尤其是一些中型的资本者,财富满足个人私欲和各种各样的虚荣心的动机已经唤不起他们对金钱的任何真实激情,然而财富的社会道德意义在现行制度中则根本无法显现,小市民式的献一点爱心之流的道德自欺自我感动一下的小把戏对他们纯属小儿科。然而,一个一度被金钱所驱散的社会学的和道德性的抑郁再次出现在这些富裕的人们身旁:他们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中和再生产、再投资这些行为之中依然根本找不到社会财富的含义,甚至也体会不到私人财产自身所带来的更深刻的尊严感。这些财富会满足任何一种熟知贫穷滋味的人的渴慕感和虚荣心,却唯独满足不了对财富的社会价值的自豪感受和受法治社会所保护的权利感。事实上,他们知道自身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贿者而已。他们的资本完全被权贵资本剥夺了政治能量和社会价值,而在更加贫穷的人们心中他们的资本却染上了难以漂白的道德污点。不仅来自于在行的行贿,也来自于对环境的污染和周围贫穷境遇的反差。目前他们最大的道德可能性是塑造出一个感伤的“慈善家”,偶尔出镜以驱遣忧郁。
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将自己在不合法的社会环境中从社会所获取的财富以富于社会价值的方式回赠给社会,他们渴望着将经济价值通过一种有益的社会行为和社会途径转账为社会财富和具有政治价值的财富。简单地说,他们渴望将经济财富进行社会的、道德的、政治的转账。这是中小资本者中最优秀分子的可贵之处。然而,权贵资本所垄断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是一种权贵政治。他们,这些没有完全放弃其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理念的中型资本者遭遇着权贵政治和权富资本的双重挤压。现在,不仅是贫穷阶层陷入新的贫富差异增大之中的极度抑郁,中小资本者中的一些怀着社会良知的人,也将再次陷入一种并非个人的、并非心理学的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抑郁。他们在希望从价值的自我实现的较低的经济生活层面上升至道德的、社会的、政治层面的时候,遇到了他们难以释怀的抑郁。说白了吧:他们不满意于一生仅仅是一个生意人,他们想做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更有尊严与价值的公民式的“政治动物”而非仅仅做一个“经济动物”却不能。有了钱也不能。
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比没有政治权利的中小资本者经济地位更低的阶层中。其中大多数依然是通过沿袭的考试制度实现了个人命运的改变,从较低的社会地位升迁至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恢复高考制度的初期,几乎每个幸运的人都会实现这一自我预期。然而近十年以来,这样的最基本的期待也常常会落空。不要说社会地位的升迁成为一个泡影,连就业都已经成为巨大的压力。不仅是心理的,还是经济的。一般经济状况的家庭供养一个孩子读完高等教育,就是一种投资,而它的产出日益没有保障。高考这一每年一度的兴高采烈的中举活动早就开始伴随着前途渺茫的忧郁。
出身于中低阶层的知识分子中会有一部分人在以后的职业生活中保持着他们的人文主义理念,然而,这个社会最大的抑郁正是压在这些人的命运之中。在一个没有理念的社会里,一个人心中还怀有理念的话就近乎一种疯狂。批判性的思想也产生自这个群体之中。正如中小资本者无法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空间里使单纯的经济资本转账为他们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一样,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无法在缺乏真实的公民精神的社会里将他们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政治力量。对权贵资本之外的中小资本者而言,财富脱离了社会,脱离了自我实现的价值秩序中的升值空间。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而言,理念也早已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社会实践空间,甚至脱离了生活本身。可悲的是,就像公权力变得十分堕落的时刻,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实现私人利益的的工具一样,人文知识者也将他们的人文理念和人文知识变成一种可怜的谋生工具。脱离了将任何合理的美好的社会伦理思想进行社会化的空间,甚至脱离了理念自身的有效传播,人文知识、理念和情感,变成了持久的抑郁状况本身。人文思想、人文知识,已经变成了一个更为狭小的圈子里的饶舌与炫技,变成了令人痛苦的腹语现象。
当然,并不是全部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已经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被权力所直接赎买;更大的群体是被体制通过自觉接受的学术规范、学科设置、重点基地及项目与学术奖励机制进行了一揽子间接赎买。他们以某种真实的政治与学术权力感,或狐假虎威的权威感远离了属于人文知识者内心的抑郁症。
中等阶层对统治阶层而言是最需要安抚的阶层,虽然这是一个同样无权的阶层,这个阶层的稳定与否举足轻重。这是一个能够通过有保障的工资、安全感和消费生活进行安抚的阶层。他们的未被满足的社会理念有时能够通过消费、大众文化和度假、娱乐节目加以化解。中等阶层既是一定隐性的反抗者——因为他们接受的一定程度的人文主义教育,因为他们的信息和某种程度上互联网带来的知情权;他们也是一定程度上的隐性的制度合作者——如果他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了的话,他们未被真实满足的社会伦理情感的受挫感依然能够在半消费生活、半娱乐生活中被化解。他们不仅反感专制,也恐惧底层社会或许会导致的社会动荡。即使此刻社会状况的延续会在他们的心底留下一丝丝挥之不去的抑郁。
这是一种难以轻易消散的忧郁,知情权被不断地通过互联网而扩大,却缺少应有的参与权,将会是这个中等阶层中持续酝酿着的阵发性的抑郁症。
这个时代,谁能免除忧郁?似乎只有倡导无为宁静的佛学和瑜珈行者会免于行为丧失而导致的忧郁。或许还有认真闭关修行的高僧,不仅将取消行为,还将自觉地取消意志作为终极目标。强调沉思、静思高于生活和行动的佛学不会造成主体的抑郁。
还有一类人不会成为忧郁症,那就是那些肤浅的人,通常是一些简单的行动分子或活跃分子。满足于生活的一般目标,满足于简单重复的娱乐活动,满足于既定的看法和既有的真理。一般而言,传统社会里单纯身体劳作的人也不会陷入主体的抑郁,简单的行为有时候也能够取消思想的自我缠绕。只是今天社会中的劳作者在其缺乏制度之善的环境中也总是伴随着抑郁。
人文价值的丧失其实一直暗中伴随着社会性的抑郁,抑郁与其说具有医学上的普遍性不如说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普遍意义。娱乐界的噱头逗哏是这一无聊状况的一个令人厌恶的变形。
人文知识分子是最为依赖这种人文气氛的生物,人文思想是这类生物的空气和食物,是他们的兴奋剂,当这种氛围消失在商业气氛和利益争端的吵吵嚷嚷时,就是人文主义者抑郁症加重的时刻。
不管在西方从亚里斯多德还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到其他人,不管多少人重复过这一对日常生活具有轻微敌意的话,这句话还是一个事实:他们中最优秀的人都是忧郁的。忧郁似乎就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是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而非例外的毒素。抑郁的知识人把抑郁作为他们自身的一个根据,抑郁的人把抑郁作为世界观。
对自身的抑郁症,人们常常羞于出口,似乎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其实一切疾病中都有一些没有澄清的道德缺陷。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当制度自身缺乏正义性、正当性或道义性的时候,一种个人的疾病其实完全可能属于抗体的表征。即使这是一种极其微弱的抗体。
每一种抑郁症都是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道德的能量被阻断的表征。难道阻断了一切正常的社会意见和思想的交换机制的权力本身就不会陷入它的抑郁症吗?
权力的抑郁症表现在古今独裁者的孤独上,这种孤独即使在权力的节日庆典上也分外刺目,没有民众的欢呼,甚至没有热情的旁观,权力的自我庆祝变成了分外谨慎的自我矛盾的炫耀。权力至高无上,权力脱离了道德,也不受法律制约,权力的抑郁症既表现在对异议者的流放和监禁上,表现在判处异己者死刑上,也表现在它渴望恢复政治与道德的联系的焦虑中。当如此重要的权力不能与道同在、不能被社会分享——除了分享它制造的灾害——时,总会有一些掌握了权力而良知未泯者期望恢复政治的道德含义,增进权力的社会伦理价值,而不是仅仅转换为一己私利和制造社会恐惧。尤其在个别拥有权力而富有人文主义理念的人身上。他们是权力阶级中的异己者,从1980年代至今,我们的社会依然不时能够在权力阶级中窥见他们忧郁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