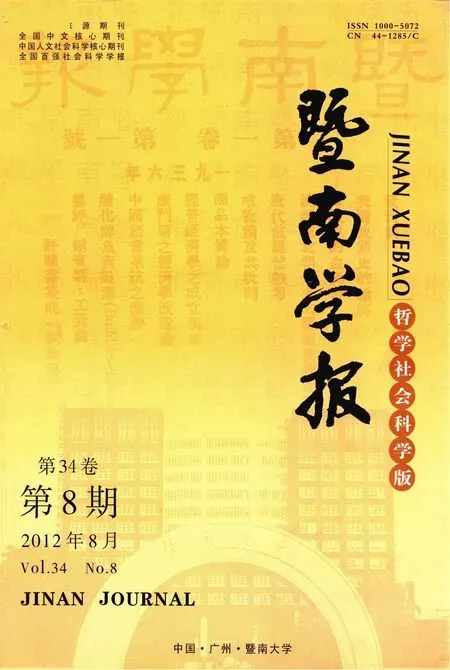藏族汉语诗歌的民歌传统
高亚斌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在各民族早期的文学中,民歌都是一种普遍的民间文学形式,如我国最早出现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由当时的史官在民间采集到的民歌。据记载,“孟春之月,群聚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上》)。这种由政府的史官采集到的各地的民歌,虽然经过了文人的加工润饰,但仍然具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特征。此外,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等,都是各民族人们早期广泛传唱的英雄史诗,体现了对于本民族英雄人物与民族精神的歌颂与礼赞。
一些相关研究者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民间文学普遍发达,从总体上远胜于作家文学”[1]230,特别是文化和文学相对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其民间文学就显得尤为兴盛。对于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来说,民间文学的影响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同时,民间文学又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片精神的沃土和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先祖对于后人丰厚的文化馈赠。藏族汉语诗歌虽然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广大的进藏干部、军旅作家和进藏大学生的促生下产生的,是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但它也受到了藏族民间文学的丰富滋养,尤其是在它的发生期,50年代出现以伊丹才让、饶阶巴桑、丹真公布、格桑多杰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藏族汉语诗人,更是民间文学哺育出来的民间之子,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浓厚的民间文学,尤其是民歌的特色。
一
“西藏是民歌的海洋”,在藏族传统的民间文学中,民歌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藏族民歌历史悠久,流传广泛,藏族早期的一些文献,如《玛尼全集》、《柱下遗教》、《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史》、《巴协》等,都留下了有关民歌的记载。据藏文史籍《拉达克王统世系》记载,“在德晓勒(赞普)时期,‘鲁’、‘卓’盛行。”其中的“鲁”就是一种徒歌,而“卓”是一种配乐的舞蹈[2]9,这就说明了藏族古代民歌繁盛的情况。藏族民歌包罗了广泛的生活内容,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生产生活,历史事件、地理风物等等,都在藏族民歌中得到了反映。从形式上来说,藏族民歌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三大类,谐体民歌、鲁体民歌和自由体民歌”[2]222。从它所反映的内容来看,藏族民歌包括劳动歌、情歌、生活歌、仪式歌等等,涵盖面极为广泛,具有深厚的社会内容和生活底蕴。藏族民歌由于通俗易懂,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在藏族早期神话、传说,甚至谚语格言等等民间文学形式中,民歌都是它们常见的表达手法与叙事体裁,如神话传说中的《斯巴形成歌》、《斯巴宰牛歌》、《青稞歌》、《吉祥羊歌》之类,以及一些有关吐蕃赞普、文成公主等人的历史传说,还有藏族民间谚语《松巴谚语》等等,都使用了民歌的文学形式,后来的《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等典籍以及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仓央嘉措情歌,也都受到了民歌的影响,藏族诗人伊丹才让就说过:“我认为仓央嘉措的时代,政治环境极其恶劣,蒙古人想废掉他,后来蒙古人又找来一个顶替他。环境很险恶,他有好的心境和宽裕的时间去喝酒、去找女人吗?他有那么多的自由吗?他写这些我想是他对民歌的喜好影响了他。”[3]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在藏族民歌中,以大约8—10世纪出现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最为著名,它“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学的最高成就”[2],被称作东方的伊利亚特,更因其在传唱中不断产生新的文本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叙述了藏族远古部落的英雄格萨尔的种种事迹,其英雄主义色彩、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昂扬奋发的民族精神,都对后世的藏族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藏族人都熟悉和喜爱格萨尔的故事,藏族谚语里说:“岭国每人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就形象地说明了它是如何地深入人心。藏族汉语诗歌无论在主题表达,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受到了《格萨尔王传》的影响,比如有人曾指出,在格桑多杰的诗歌《献给时代的贺辞》一诗中,“百头乳牛驯牧的地方”、“千头键牛犁耕的地方”、“百群羊儿觅食的地方”等诗句,“读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或听过藏族民歌的读者,或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4]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二
50年代的臧族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民歌的哺育。李佳俊在论及50年代的西藏诗歌时就曾指出:“这时期的青年作家在艺术上的共同特点和积极向民间文学吸取营养,不像同时代的老诗人那样刻意追求古典文学的华丽和典雅,表现出通俗、纯朴和清新的美,更接近于新民歌。”[5]许多藏族作家和诗人也都明确地表露过民歌对自己的哺育。从搜集、整理、翻译、研究民歌起步,开始进入诗歌创作的伊丹才让曾这样说过:“民歌是我诗歌创作的启蒙老师。”[6]他说:“我热爱民歌,民歌哺育了我的创作,民歌是我飞翔的翅膀,民歌是我诗歌的第一个老师。”[3]在他的诗歌作品里,他表达的仍然是这样的看法:“是的,我是来自雪山的歌者,/我懂得什么是诚实的歌唱,/为了校正心头音调的纯真,/时刻把耳朵紧贴母亲的胸膛。”“是的,我就是全部旋律的命题,/它输给我十万大山蕴藏的能量,/就像这周身沸腾的血液,/每一滴都来自母亲甘甜的乳浆——”(《母亲心授的歌》)伊丹才让还把这种民间文学作为诗歌的元素融入其间,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如在《母亲心授的歌》里,有这样的句子:“朦胧中我仿佛听见,母亲在讲/《阿伊(藏语,老奶奶)措毛和她的花牛犊》:/‘……花牛犊被魔鬼当了午餐,/晚上还要吞掉她的五脏六腑。’……”诗人自己注解道:“这是一个藏族民间故事,是母亲讲给我的第一个故事。”民间故事的楔入,一方面为诗歌增加了叙事性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它在诗人的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记忆。同样在这首诗里,他还用民歌为诗歌的每个部分收尾,诸如“我唱着跳着到蓝天上去,/要和天上的小龙把彩云舞;/我唱着跳着到石山里去,/要和山里的小野牛穿云雾。”还有“好啊,好啊,今朝好,/今朝的蓝天多明亮;/好啊,好啊,今朝好,/今朝的大地降吉祥”等等之类,前者是藏区流行的民歌,后者是婚礼歌中的赞词。这样的结构安排,既很好地表现了诗歌的主题,又彰显了作品的民族特色,这种尝试无疑是成功的,总之,在伊丹才让的诗歌里,明显可以找出其“既有个人独创,又有脉胳可见的民歌的渊源”[7]276的创作印迹。
饶阶巴桑也曾经深情地回忆过自己的出生地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澜沧江从它身边流过,那日夜不息的涛声,还有歌声,不断地撞击着我童年的心弦。我后来崇拜诗歌,信仰诗神,不能不感谢这个村庄的安排。……那悲凉的别离歌,那优雅的赞美诗,便是旅人们遗失在村庄里的财富。这样,年复一年,康藏各地的诗歌源源不断向这里流来,汇成海洋。自然,千百年来,经过这个村庄主人的挑选、加工、创作的百唱不厌的优美歌词,同样被旅客行人们不付分文地带走,撒向四方。”[7]273得天独厚的民歌资源给了诗人诗歌艺术的氛围,孕育了诗人的文学灵感,使他从此走上了诗歌的道路,难怪著名评论家谢冕在谈到饶阶巴桑的诗歌时,马上就指出了他的诗歌“有着深厚的本民族诗歌的渊源”[8]。
除了伊丹才让、饶阶巴桑之外,丹真公布也是受到民间文学影响而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据赵之洵回忆,“1950年,十五岁的丹真也许还不具备多少学识,但在对藏族民歌的掌握上,他却是个富有者”[9],他的诗歌整体上具有民歌的特色,而且他的长篇叙事诗大都源于在民间流传的各种故事。另一位老诗人阿旺·期丹珍在发表《花和果》之前,也曾从事过藏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积累了民歌创作的许多经验。此外,恰白·次旦平措在写作《冬之高原》等诗篇时,就使用了协体式民歌的形式……这样的例子非常普遍,几乎不胜枚举。当然,在对民歌的汲取过程中,藏族汉语诗人们并没有只是被动地接受民歌的影响,而是进行了“化民间”、“化传统”的创造性的融化和改造的过程,比如,伊丹才让就曾说过:“如何用民歌本质性的养料来灌溉诗的灵感,是我在思索而没有求得解决的课题。”[7]可见诗人在“化民间”的过程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因而谢冕在指出他的诗歌“有着深厚的本民族诗歌的渊源”的同时,又指出“但却不是简单的原始的民歌,而是全新的创造”[8]。饶阶巴桑也认为:“不管民歌本身怎样光彩夺目,毕竟不会轻易地将它的光辉倾注到我的作品中,给我们一个廉价现成的创作道路”[10]201,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同1958年内地出现的“新民歌运动”一样,西藏在50年代解放初期,也出现了大量的“新民歌”,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民歌热潮。这些新民歌主要以抒发对新生活的热爱,赞美共产党、新中国,歌颂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主题.它以西藏传统民歌作为依托,是对流传在民间的民歌的改造和变形,并为它赋予了崭新的思想和时代内容,其中程度不同地剔除了一些民间原生态的、自由自在形态的东西,体现出意识形态改造过的明显痕迹,具有强烈的政治话语色彩,如新民歌《只到北京转一趟》:“天上洁白的仙鹤,/请借我一双翅膀,/我不往别处飞去,/只到北京转一趟。”就是对仓央嘉措情歌的改写;其他像《都说叔叔是菩萨》、《活菩萨大显威灵》等等,在对解放军的赞美中,隐含着民间宗教主题的置换。总的说来,藏族新民歌里虽然充满了话语狂欢式的喧嚣,但另一方面,它又保留了传统民歌的形式和质朴清新的鲜活因素,显得生动活泼,为人民所喜闻乐见。这类藏族新民歌的出现,既同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民歌运动形成呼应,又是藏族诗歌民间传统的一次大规模呈现,并且向藏族汉语诗歌创作渗透。在某种意义上,“藏族新民歌是藏族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衔接点”[11],它激发了人民的创作热情,也促进了作家诗歌向民间学习的优良传统,促进了藏族古典文学的现代化转变。
三
新时期以来,随着藏族作家诗人们民族意识的回归,他们继续向民间文学汲取资源,阿来就曾说过:“我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知道在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强大的官方话语、宗教话语并没有淹没一切。”[12]他还说:“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特质。藏族书面的文化或文学传统中,往往带上了过于强烈的佛教色彩。”[13]他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民歌的本质与这种本质的力量”[14]。这种对于民间文学的倾心和自觉吸纳,也反映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在《灵魂之舞》一诗中,他就这样写道:“我们要在松木清芬的光焰下,/聆听嘉绒人先祖的声音,/让他们第一千次告诉我们是风与大鹏的后代,/然后,顺着部落迁徙的道路,/扎入深远的记忆。”而在扎西才让的诗歌里,也出现了诸如“童谣和诗篇涌现”、“民俗和爱情涌现”,以及“我手捧的曾经是种籽,/一百首谣曲,……/我手捧的曾经是我种族的命”(组诗《高原的阳光把万物照亮》)一类的诗句,表达了对于民歌的热爱和眷顾。
藏族汉语诗歌的民间文学传统非常强大,它赋予藏族诗人以独特的创作灵感和心灵体验,丰富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增添了藏族汉语诗歌的浪漫色彩,从而产生了激荡人心的艺术效果。这种民间文学的精神因素,一直持续至今,与宗教文化相结合,以一种“朝圣”写作的形态在藏族汉语诗歌中获得了绵延,对此,唯色也认为:“……在西藏,神话的力量一直是巨大的,只是它如今已被物质所遮掩,但它并未消失,它还在那里。它需要的是一双发现的眼睛,不,是那些迷惘的灵魂需要它的垂青。”[15]229惟夫在评论于斯(蔡椿芳)《向西》一诗时,也这样写道:“我们感受到了来自诗歌的巨大的神话冲动,我们的思想几乎被无所不在的弥荡在诗歌中的神话情感和神话想象所包围、所淹没。”“在这样的事实中,我们感受到了现代诗歌与神话的必然联系以及在诗歌与神话基础上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更准确地说是恢复)”[15]229-230,这种觉醒也是导致80年代寻根文学浪潮的一大诱因,朦胧诗人杨炼在进行最初的文化寻根时,就写下了《诺日朗》、《西藏》等与西藏有关的诗歌。
除民歌之外,其他民间文学也在形式和内容上启迪着当代藏族汉语诗歌,如江金·索朗杰布写的《文成公主》一诗,就是在流传于藏区的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还有的诗歌受到了民间谚语等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来说过,“我觉得,少数民族作家有的时候在写作资源上占一些便宜。对我来说,我还有一个巨大的写作来源——民间文学的来源。”[16]
[1]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1998.
[2]马学良,等主编.藏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3]藏人文化网.网址:http:∥people.tibetcul.com/dangdai/sdwt/200507/1423.html.
[4]杨恩洪.论格桑多杰诗作的民族特色[J].民族文学研究,1985,(4).
[5]李佳俊.写在世界屋脊的壮丽画卷[J].民族文学,1999,(8).
[6]伊丹才让.雪山集·后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
[7]吴重阳,陶立璠.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
[8]谢冕.和新中国一起歌唱[J].文学评论,1979,(4).
[9]赵之洵.雪域的溪流——试论藏族诗人丹真贡布的诗歌创作[J].西北民族研究,1997,(1).
[10]饶阶巴桑.从澜沧江出发·我的经验[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11]岗仁曲成,史坤.澎湃发展的藏族当代文学[J].西藏文学,1985,(8 -9).
[12]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J].民族文学,2001,(9).
[13]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N].中国文化报,2001-05-10.
[14]阿来.关于灵魂的歌唱[J].人民文学,1999,(4).
[15]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6]沈文愉.阿来:写作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冲动[N].北京晚报,2000-11-20.
——李福清汉学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