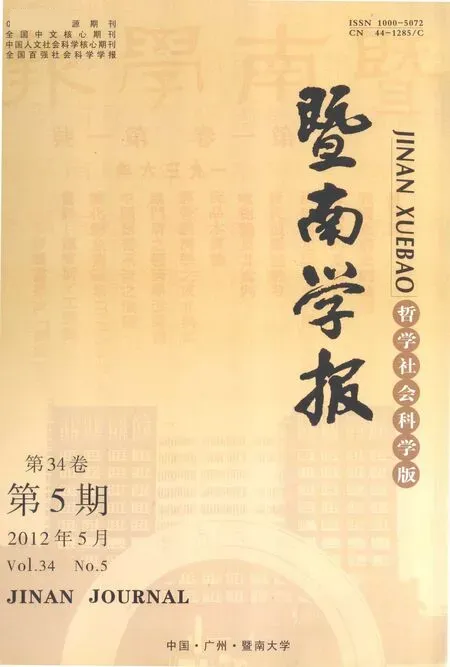《文心雕龙》之《韩非子》批评辨析
高林广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文心雕龙》之《韩非子》批评辨析
高林广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文心雕龙》在《铭箴》等十余篇中讨论和分析了《韩非子》及其文学特点,广泛涉及了《韩非子》的思想特点、辞采风格、言说方式、寓言运用等。刘勰以“弃孝废仁”评韩非“五蠹”说,以“华实过乎淫侈”论《韩非子》的文体和语言风格,对《韩非子》总体上评价不高。但同时,《文心雕龙》对《韩非子》辨正义理的言说方式,循名责实的判断标准,以及“著博喻之富”的表现手法等多所阐发和肯定,同时又大量引叙和容摄了《韩非子》中的义理范式、逻辑方法、文体文学实践及学术成就等。《文心雕龙》的《韩非子》批评,为后世的韩非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有益文学史料。
《文心雕龙》;韩非;批评
韩非是战国末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早期法家的思想精华,重法治而轻文艺,好质而恶饰,反对虚华。《韩非子》五十五篇,说理精密,文笔犀利,善用寓言,不仅充分展现了韩非子的法学思想,亦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对于《韩非子》的文学成就与不足,《文心雕龙》之《铭箴》、《诸子》、《情采》等至少十四篇予以了较为深入的评判和剖析,其中涉及到了《韩非子》的思想特点、辞采风格、言说方式、寓言运用等。《文心雕龙》的相关评述,对于后人全面解读《韩非子》的文章风貌、正确评判其成就得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对于韩非及其著述,刘勰总体上评价不高。在《诸子》中,刘勰以“弃孝废仁”评“五蠹”说,而《情采》篇则以“华实过乎淫侈”论《韩非子》。
1.“弃孝废仁”
《诸子》曰:
至如商韩“六虱”、“五蠹”,弃孝废仁;轘药之祸,非虚至也。[1]229
“六虱”之说出自商鞅,《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五蠹”之说出自《韩非子·五蠹》: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2]699
诗、书、礼、乐、孝、悌等,是儒家伦理思想和仁政观念的核心要素,在儒家看来这些都是神圣的,但《商君书》却将其目为害国虱子;《韩非子》更将学者(即儒生)视为“五蠹”之一。对于这些言论,刘勰以“弃孝废仁”论之,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刘勰论诸子,以“纯粹”和“踳驳”为标准予以评判,“其纯粹者入矩,其踳驳者出规”。像《庄子》与《淮南子》等,属“踳驳”之类,刘勰对其多有微词;至于《韩非子》,已不仅仅是“踳驳”,而是“弃孝废仁”了。
刘勰对商、韩等法家人物的批判和抨击,并非仅仅因为其著述中对儒学和儒生使用了污蔑性的言辞。以商、韩为代表的法家,提倡刑赏、农战,主张用严酷的刑法来实施统治,反对儒家的德教,这些思想和主张同样是刘勰所不能接受的,而这也正是刘勰不满于韩非等法家的关键所在。《诸子》称“申商刀锯以制理”,刘勰对商韩等法家重宪令、轻仁德之举持否定态度。《史记·商君列传》以“刻薄”、“少恩”论商鞅,《汉书·艺文志》以“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论法家,正与刘勰持有相同的立场。其后,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抨击韩非之说是“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可谓一语中的。不过,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对于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封建政治体制的形成和确立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韩非反对复古、主张革新的思想显然也具有积极意义。对此,刘勰并没有论及。可见,刘勰对韩非的认识和评判是不够全面的。
在刘勰看来,“五蠹”说实为暴秦苛令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刘勰不满于韩非的又一重要原因。《时序》讲:“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战国时期儒学衰微而诸子勃兴,秦国据“五蠹”、“六虱”之说,制定法令,推行暴政。因此,在刘勰看来,韩非的“五蠹”说是具有极端危害性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刘勰对有秦一代推行封建专制统治,禁锢文明,扼杀文化,实行愚民政策的行径多有批判。如,《明诗》“秦皇灭典”;《时序》“爰至有汉,运接燔书”;《练字》“秦灭旧章”等等。证之以史实,刘勰所论是符合事实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焚书坑儒,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这是不争的事实。暴秦燔书,独尊法家,这虽然并非韩非等人所为,但法家的有关思想和认识显然是苛政的理论基础。
上引《诸子》中,刘勰以“轘药之祸,非虚至也”这样激烈的言辞表达对韩非子“弃孝废仁”行径的愤慨。从文字表面上来看,似乎刘勰认为韩非之死是“最有应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刘勰对韩非本人的遭际还是同情的。《知音》曰:
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
刘勰此论本于葛洪。《抱朴子·广譬》曰:“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见其为人;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时。及既得之,终不能拔,或纳谗而诛之,或放之乎冗散。”[3]“韩非囚秦”事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刘勰以韩非等人为例,以证其“贱同而思古”之论,进而说明“知音其难”的道理。寻绎刘勰之言,他对韩非的遭遇有“愤愤不平”之慨,却无“幸灾乐祸”之意。《才略》篇以张华之《鹪鹩》比况韩非之《说难》,也可以作为佐证:
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其《鹪鹩》寓意,即韩非之《说难》也。
《鹪鹩赋》是西晋作家张华的一篇托物言志的作品。鹪鹩是一种“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的小鸟,“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文章取义于庄周“鹪鹩巢林,不过一枝”的论点,旨在阐释“位尊而险,无用安处”的道理。文章大量运用了对比反衬手法,以鹫、鹗、鹍、鸿、孔雀、翡翠之“负矰婴缴,羽毛入贡”,比衬鹪鹩之“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其立意及结构均表现出了轻灵俊脱、“奕奕清畅”的特点。韩非的《说难》论述了对人君的谏说之难,“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引旧注曰:“夫说者有逆顺之机,顺以招福,逆而制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4]254显然,《说难》具有强烈的愤激情绪,鲜明地体现了韩非愤世嫉俗的思想。刘勰以《鹪鹩》比《说难》,肯定了二文讥斥时弊、发抒感慨的意义,显示出对《韩非子》内在情感的深刻体察。
2.“华实过乎淫侈”
由上文可知,刘勰对《韩非子》的不满和批判,首先是基于其政治思想上的“弃孝废仁”。就文学角度而言,刘勰又评《韩非子》是“华实过乎淫侈”。《情采》曰:
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
采,当作“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在这里,《韩非子》所讨论的是“帝王之术”。他认为,君主应该谋求能够使国家安定强盛的实际功效,而不应该听信那些巧妙动听而又善于文饰的空洞不实之辞。韩非论文艺以功用为基本原则,提倡“尚质”、“尚用”,推崇自然美,本质美,反对文饰。其《解老》云:“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他将文与质从根本上对立了起来,体现出了重质轻文的倾向。刘勰以为,韩非的“艳采辩说”是就文采绮丽而言的。刘勰也强调质,但他同时并不反对文采,他主张“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崇尚文质彬彬的文章风格。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刘勰认识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显然远胜于韩非。
刘勰以“华实过乎淫侈”评《韩非子》,其实并不符合文学史实际。从创作理论来看,韩非重法制轻文艺,重功用轻虚华,重朴质轻文饰,但却并无“淫侈”之论。如,《外储说左上》曰:“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再如《亡征》:“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从创作实践来看,《韩非子》虽多用寓言说理,广譬博喻,但总的说来直言畅论、细密透辟,并不刻意追求文饰之美。总此两端,可知《韩非子》并无“华实过乎淫侈”之实。
刘勰“淫侈”的立论基础是时文之绮丽雕缛、“繁采寡情”,是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故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曰:“舍人处齐梁之世,其时文体方趋于褥丽,以藻饰相高,文胜质衰,是以不得无救正之术。此篇(《情采》)恉归,即在挽尔日之颓风,令循其本。”[5]99《情采》篇在列述《孝经》、老庄及韩非的文章趋尚及创作特点时,突出强调了“文质附乎性情”的文章风格,而“华实过乎淫侈”自然在摒斥之列。若以齐梁文坛的实际来考察,刘勰之论显然是正确的。
(二)
虽然刘勰对韩非的总体评价不高,但他对《韩非子》辨正义理的言说方式,循名责实的判断标准,以及寓言手法的大量运用等还是多所肯定和吸纳。另外,《文心雕龙》也大量借用或化用了《韩非子》的义理、事类和语辞等以评析作家作品,阐释其文章理论。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刘勰对《韩非子》的熟稔。下面择其要者,分别列述于下。
1.“总法家之式”
《奏启》曰:
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彊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但世人写作此类文时,往往吹毛求疵,挖苦谩骂。刘勰反对这样的做法,主张以《礼》为范,确立文章规范,“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何为“法家之式”呢?简单地讲,就是指法家重规范和标准的程式和方法。前文中之“立范运衡”、“理有典刑”等实际上就是“法家之式”。刘勰以为,奏体的写作要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而“辨析疏通”正是法家之所长。
上引一段文字中,刘勰还提到了奏文写作中“直方”的要求。“直方”最早见于《老子》第五十八章:“是以圣人方而不割,……直而不肆。”《韩非子·解老》对此作了阐释:“所谓方者,内外相应也,言行相称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韩非之论注重在名理辨析的基础上悬规立矩,逻辑严密,指向明确,较典型地体现了“法家之式”。尽管韩非所言之“直方”在内涵上与刘勰所言不尽相同,但其衡量取舍、辨正义理的言说方式为刘勰所重,因此刘勰才讲要“总法家之式”。
2.“循名课实”
“法家之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循名责实”。法家有“刑名”论,主张“审合刑名”(《韩非子·二柄》),慎赏明罚。《韩非子·定法》云: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所谓“循名责实”,即依其名而求其实,进而做到名实相符。在韩非看来,循名责实是维护君权、推行统治的最重要的手段和方法,故《韩非子·扬榷》讲:“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那么,如何去循名责实呢?《韩非子·奸劫弑臣》讲:“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二柄》有更为具体的论述:“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也就是说,君主按照臣下的陈述意见来交给他职事,然后根据他做事的实际结果确定奖惩,名实相符者给予奖赏,名实不符者予以惩罚。韩非的名实思想源于荀子。《荀子·正名》篇称,要“制名以指实”,“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并对“名”、“辞”、“辩说”的内涵和意义作了细致的辨析和论述。
抛开其政治功用不谈,韩非刑名理论中关于名、实关系的甄别和论述,以及其中所显示出的思辨色彩和理性精神,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建构不无启示意义。刘勰对韩非的这一理论多有吸纳。其《章表》云: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章为本者也。
章以谢恩,表以陈请,这两种文体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实际效用,所谓“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正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联系,章与表在写法上也自有其规范和准则,刘勰总结为“风矩应明”(章)和“骨采宜耀”(表)。这两方面是章表写作之“名”。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就应当据其名而求其实,进而创作出名实相符、规范典雅的作品来。很显然,韩非“循名责实”论成为了刘勰阐释章表创作原则时所运用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刘勰所谓“循名课实”与韩非的“循名责实”其实并无二致。名实相符、名理相因之论,在《文心雕龙》中多有体现,兹再举几例:
尹文课名实之符。(《诸子》)
名实相课。(《议对》)
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书记》)
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夸饰》)
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通变》)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论说》)
从上引文字来看,刘勰对刑名理论之原始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是熟悉的。《诸子》讲:“尹文课名实之符。”尹文乃战国齐宣王时稷下学者,属名家。《汉书·艺文志》有《尹文子》一篇。刑名(或称“形名”)论是《尹文子》的重要内容,实际上,韩非子的刑名思想就是在借鉴和吸纳名家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曹魏初期,名家与法家学说并行,这深刻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故刘勰《论说》讲:“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关于刑名之学影响曹魏文学的具体情形,刘师培先生有非常精当的论说:“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趣清峻。”[6]9就“论”体而言,傅嘏和王粲的论文颇能运用名理之学阐扬大义,考论道理,这从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爵论》等文中可以得到证实。因此,刘勰谓傅嘏、王粲“校练名理”,是符合实际的。
上引刘勰关于名实、名理的论说,不少是就议对、笺记、诗赋、书记等各类体裁的具体创作要求而谈的。刘勰认为各类文体的固有特征不同、其适用性和针对性各异,因此,其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也应当具有特殊的规定性,《通变》将此种情况概括为“有常之体”,《定势》则作了更详细的说明:“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作家应谙熟各体的基本特征,采取相应的写作方法,这样才可以做到名实相符、名理相应。此外,“循名责实”也被刘勰用以评判创作手法的是否恰当。《夸饰》言,夸饰手法的使用要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污”;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就会“名实两乖”。综上,韩非的“循名责实”思想被刘勰广泛运用于文体论、创作论、作家论等各个方面,刘勰对《韩非子》的借鉴和吸纳由此可见一斑。
3.“著博喻之富”
“诸子杂诡术也”(《诸子》),或许在刘勰看来韩非“五蠹”云云即属“诡术”之列。但诸子亦多所可取,因此刘勰主张“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具体到《韩非子》,刘勰特别提到其譬喻繁富的特点:“韩非著博喻之富。”(《诸子》)刘勰的这一总结是符合实际的,《韩非子》一书计有寓言300余则,居先秦诸子之首。韩非擅于运用寓言故事阐释其法治思想,既形象生动,又尖锐犀利。“他已不止是个别举引来充当说理的工具,而是视为一种文学体裁,有目的地收集整理或创作,而后分门别类编辑成为寓言故事专集,如内外《储说》、《说林》、《十过》等是。”[7]141《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故事,直到今天仍然广为流传,如“老马识途”(《说林上》)、“守株待兔”(《五蠹》)、“郑人买履”、“郢书燕说”、“荆刺母猴”、“画鬼魅易画犬马难”(《外储说左上》)等等。《文心雕龙》中即大量化用或借用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兹举几例:
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在于兹矣。(《议对》)
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楯,两难得而俱售也。(《定势》)
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疎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声律》)
上引《议对》一段文字中,运用了著名的“秦伯嫁女”和“买椟还珠”两则寓言。这两则寓言均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昔秦伯(秦穆公)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刘勰强调,“议”体之要在于“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若片面强调文辞,舍本逐末,“文浮于理”,则不明其事,亦不达其理。其势如“秦伯嫁女”,“买椟还珠”。《定势》中之“鬻矛誉楯”更是妇孺皆知,《韩非子·难一》曰:“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刘勰借用这一寓言旨在说明“雅”与“郑”(即典雅与浮靡)是两种不同的体式和风格,是不可以在一篇之中“兼解以俱通”的。《声律》篇以“滥竽充数”喻作家之才识粗疏、不谙声律,此典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寓言之外,刘勰对《韩非子》中的事典、语辞等也较为熟悉,《文心雕龙》也多有引用、借用或化用。兹举几例。
《铭箴》曰:“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其中“赵灵勒迹于番吾”和“秦昭刻博于华山”事,均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其文曰:“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棊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赵武灵王曾派人在播吾山上刻了一个宽三尺、长五尺的大脚印,并刻上“主父常游于此”几个字;秦昭王曾令人到华山上用松柏树的树心做了一盘大型棋局,并刻上“昭王常与天神博于此”几个字。刘勰认为,这虽然是刻石,但不能称之文铭文。铭的特点是“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而赵武灵王及秦昭王之刻石以虚夸荒诞之事夸示于后世,因此刘勰认为这是可笑的。从这则文字中可以看到,刘勰运用了《韩非子》中的材料,并借以阐释他对铭文创作的要求。《论说》评范雎的上秦昭王书及李斯的《谏逐客书》曰:“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其中,“逆鳞”一词出自《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在这里,刘勰既用其说,也取其意。再如,《奏启》批评按劾类文章写作中“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的不良倾向,其中“吹毛取瑕”即取于《韩非子·大体》中“不吹毛而求小疵”之说。他如,《书记》篇直接引用《韩非子》中的成言以诠释“关”这一文体的原始含义:“关者,闭也。出入由门,关闭当审;庶务在政,通塞应详。《韩非》云:‘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盖谓此也。”《声律》篇有“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之论,以《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对照之,可知,这已不仅仅是借用或化用,而是直接引《韩非子》之成言入文了。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对韩非及其著述有贬有褒,毁誉参半。所贬者,主要是韩非的“五蠹”说及其法制理论的妄诞,以及《韩非子》“绮丽以艳说”、“华实过乎淫侈”的文体及语言风格等;所褒者,主要是《韩非子》辨正义理的言说方式,循名责实的判断标准,以及“著博喻之富”的表现手法等。《文心雕龙》大量引叙和容摄了《韩非子》中的义理范式和逻辑方法,也大量征引或借用了《韩非子》中的文体文学实践、文学事典及学术成就,可见,刘勰对韩非及其著述是作过细致的分析和考察的。但另一方面,受“宗经”思想的束缚,刘勰对《韩非子》的思想特点和文体文学特征的解析又不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这些是需要后人认真加以辨析的。无论如何,《文心雕龙》的《韩非子》批评,为后世的韩非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有益文学史料,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1]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下引《文心雕龙》原文均据该本.
[2]张觉.韩非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下引该书只注篇名.
[3]葛洪.抱朴子·外编[M](卷三十九).《四部丛刊》影明本.
[4]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M](第三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7]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I206.2
A
1000-5072(2012)05-0066-06
2011-06-14
高林广(1965—),男,内蒙古察右前旗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唐宋文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研究》(批准号:11XZW004)。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