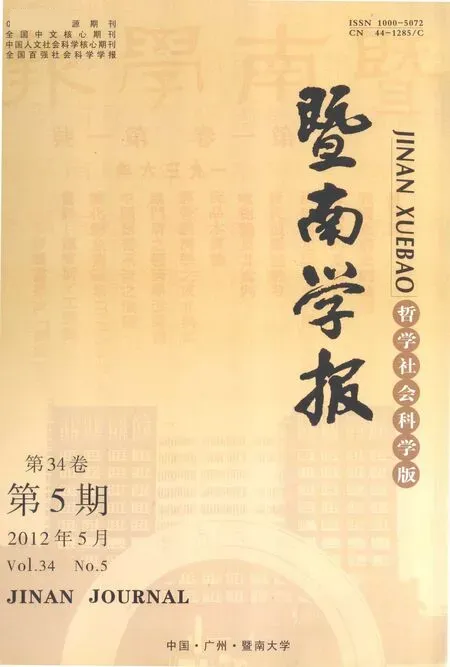超越规则:政策定向国际法学说之理念批评
刘筱萌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2)
超越规则:政策定向国际法学说之理念批评
刘筱萌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2)
政策定向学说的产生秉承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思潮影响,在创立之初即以动态的法律观念和实际的理念震动了国际法学界。该学派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与学派观点的新颖性,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公认的。但事实上,尽管政策定向试图糅合政治或其他社会科学进入法学研究从而构建一个新的法学特别是国际法学基础理论框架,但是这种全新的理论构建基础却并不稳固,从而使得政策定向的理论自创立之始,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以政策定向国际法理论的规则理念和价值理念两方面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政策定向的基础理论,对政策定向的国际法理论提出质疑和批评。
政策定向;纽黑文学派;国际法基础理论
如果说20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打破了牛顿经典物理学完美神话,那么现实主义在法律领域的兴起也使得传统法律研究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强调动态的功能主义逐渐取代了注重静态的结构主义[1],更强调现实的观点逐渐取代了法律形式主义,而这种冲击同样也影响了国际法研究领域的思考方式,“国际法学者长期以来困扰于国际法律义务的来源以及国际法同时处于国家‘之间’(of)和国家‘之上’(above)这样的理论难题之中。然而,围绕这种命题无休止的争论却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即国际法律规则,不论其是如何制定出来的,都能够对国家行为(State Behavior)产生某种影响,法律和权力(power)以特定方式相互作用(interact),而不是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分道扬镳。”[2]208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审视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成为许多国际法学者的必要工作。实际上,面对现实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强势,许多国际法学者做出了学术上的“适应性”调整[3]20。
也正是在这一现实主义思潮之中,1943年,耶鲁大学国际法教授麦克杜格尔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韦尔在《耶鲁法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法律教育的长篇论文《法律教育与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的职业训练》[4]203,在这篇论文中麦克杜格尔确定了其所认为的法学院的正确职能是为更全面地取得民主价值而培养和训练政策抉择者作出贡献。也正是从提出改革法律教育开始,一个全新的颠覆性法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全面展开,也就是政策定向学说(Policy-oriented Approach)。该学说在质疑传统的法律是规则的总和的概念的前提下,认为法律不仅仅是规则,还包括政策决策和一切有关的活动的全过程,并把这一理论运用到国际法,他们认为国际法不仅仅是表现为调整国家关系的国家行为的规则的总和,它必须是包括这些规则在内的国际权威决策的全部过程。这一方法的问世震动了国际法学界。该学派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与学派观点的新颖性,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公认的。不仅对于法理学特别是国际法法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而且其注重实际的理论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相当长时期的对外政策,其余波至今绵延[5]29。政策定向的学说在美国、欧洲、亚洲都有很大的影响,其所创造的一系列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得到许多国际法学者的青睐,同时也遭到不少的批评[6]378。
由于学术理论架构的隔阂,国际法学者多笼统地认为,政策定向的思路是“国际法否定论”,因此在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中是并不可取的。但是,另一方面,政策定向学者却从未否认过国际法的存在,而是指明自己只是更深入地理解了国际法规则的本质,超越了国际法规则本身。这一认识论上的矛盾,使得不论是从实践的国际法角度还是从理论研究的层面,对政策定向学说以及其深层次的理论缺陷都具有讨论的必要。
一、法律规则概念重构的缺陷
(一)对法律概念的政策定义
法律作为一种权威抉择(Authoritative Decision)而不是约束性规则形式存在的概念,这是政策定向方法大厦建立的基石。正是基于这个框架,“法律”由此涵盖了在所有社会进程中涉及“权威特性”(Perspective of Authority)的抉择行为①在政策定向的语境中,这些抉择必须是“正确”(right)或者“适当”(appropriate)的。政策定向理论研究的术语“权威”(authoritative)、“正确”(right)、“适当”(appropriate)等等,意指一系列得到遵行期望的抉择。。这些抉择也并不仅限于行政机构、司法或者立法机构,但对于这些抉择来说,按照政策定向学说理论的要求,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控制”(control),即对行为的规制。这一条件引入了政策定向语境下权威抉择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能够对“行为”施加影响的权力。如果缺少了这种对行为施加影响的权力,那么权威只是一纸空文,但没有“权威”的权力(麦克杜格尔教授称之为“赤裸的”权力)则必定会被推翻[7]267。
通过强调权威与行为控制之间的紧密联系,政策定向的方法很难被归为一般政治学家对现实纯利益关系或者权力关系的界定范畴之中,但同时政策定向对“法律”的定义并没有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法律规则,而是将法律规则重新定义为权威控制,并且大大扩展了该定义的外延,使得规则在政策定向方法论的笼罩下如同滴水入海,似乎并不存在,但又无处不是。规则被抽象化为所有人的共同期待(shared expectations),从而受到社会进程政策选择中权力、利益以及价值等因素的影响。
此外,政策定向的方法将一个由合法或者正确抉择者作出的并且被广泛接受的抉择视为一个权威抉择,然而这个前提本身即存在严重的概念模糊问题,例如,国际社会的抉择者作出的抉择需要获得怎样的合法广泛性才能使得其抉择成为权威抉择?而经过一个在长期的时间之后,权威与有效的关系又当如何?更重要的是,在国际社会众多庞大复杂的抉择者的抉择之中,我们应当如何识别真正的抉择过程?[8]61
(二)对法律规则政策化的质疑
混淆法律与政策,否认从规范的层面对国际法的界定是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政策定向法法学研究理论如实地反映了白纸黑字的法律在社会现实中的脆弱和不切实际,但有许多批评者认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大多是基于对社会现实和法律之间关系的直观的感性认识,很值得推敲。因为它符合了某些国家不能依据现有的传统国际法规则,借以推行其国家政策的利益要求。白纸黑字法律的准确、明白和有据可查,使得这些国家难以寻找足以说服国际社会的依据,因而在此之外,创造出所谓的“做事情的正确方法”,“权威抉择”形成的规则为其不符合国际法的行为寻找借口,使其合法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定向学说所表达的理念为规避现实的法律提供了可能,即白纸黑字的法律是法律,但之外另有更为重要的法律(实际生活中“做事情的正确方法”)。
还有学者认为,麦克杜格尔并没有在法学意义上使用“法律”这个概念,而是认为“法律就是政策;政策就是人类尊严;而人类尊严则需要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成功扶植。因此,法律(在此)就成为了美国(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国家利益的陪衬。”法律也就不成为法律,而只是权力的增量(increment)[9]382。苏联国际法学家格童金教授则认为,如果把国际法同政策混为一谈,就必然导致否定国际法的规范性质,换言之,就是否定国际法,因为它淹没在政策之中,不再作为法律存在了[10]。梁西教授也认为,政策定向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权力、国家对外政策与国际法的关系,国际法诚然与国际政治势力和各国对外政策密切相关,但若将他们铸为一体,则显然悖于事理[11]。
固然,政策定向重新定义法律规则的方法另辟蹊径,但却不能回答一个最简单基础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立即判断一项具体的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如果我们按照政策定向的方法进行推理,那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被淹没在无穷无尽高度混沌的所有人的共同期待之中,一项行为,原本是规则指向的判断标准由此进入了一个充斥着共同期待、价值取向以及权力关系的世界。
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不把法律视为一组规则的话,那么这样的法律思想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虽然在规范的层面上,有关法律效力的论证可能只涉及社会、道义和政治因素,而不一定包括法律规则的全部内容,但如果选择了完全抛开法律规则的做法,那么所有的法律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在事实的层面上,如政策定向的学者一样把法律决策视为一个有别于其他决策过程的特殊的社会过程的做法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个社会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形成与某种法律规则有关的决策之意图[12]。
同时,政策定向的观点也就意味着承认法律制度的高度变化和反复无常。政策定向的观点认为,把法律界定为“一组规则”的观点,限制了社会、道义和政治因素在决策过程,特别是司法判决中发挥作用的空间[12]。他们指出:“在各种决策程序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可以做出权威性以及有强制力的决策的‘法律程序’(Legal Process)。权威性是一种与选举模式及合法性紧密相关的、以及与有能力参照何种标准及程序做出决策的人士所关心的‘预期结构’(Structure of Expectation)。决策中,我们必须合理地考虑权威的与非权威的声音。关注实际运作中对权威性的共同期望,这是我们对法律所理解的内容。”[13]欧兰扬教授(Oran R.Young)就指出,根据政策定向的概念,“显然法律就可能成为任何社会制度中高度变化或者反复无常的现象。如果关于价值分配的要求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优势地位并被普遍接受为权威时,所谓的法律的确显得稳定和相对容易识别[8];但是如果成功诉求的模式不断发生变化,鉴别所谓的法律就将会成为非常困难的任务。”①在高度稳定的社会之中,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共同期待相对容易得出,并且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会保持相对的稳定,但如果社会变化较为迅速、密集并且具有较大的随机性的时候,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形成并且调整社会关于有效权威社会抉择的共同期待就成为越来越困难的任务。“In highly stable societies,expectations of this kind will be relatively easy to arrive at and will not change much over time.As change becomes more rapid,extensive and unpatterned within a social system,however,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formulating and adjusting expectations about effectiveness and authoritative decisions in a meaningful fashion will mount steady.”因此,如果对国际社会的各种价值的判断不再依赖于正式的规则,法学变得可以与政治学或者其他社会科学合并并且停止发挥任何独立且有用的意义[14]。虽然政策定向分析了人们共享价值观对秩序构建的作用与意义,这种共享价值观包括:权力、财富、尊严、生存、技巧、教化、公正、情感等等,并把“人类尊严”作为最核心的价值观,但是该学派将国际法视为是一种社会进程的现实改造,无疑使有别于始终为利己利益而战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诸如公平、正义、道德等国际法所包涵的一些最基本原则或价值渐趋褪色,从而使国际法与国际法学的独立性受到挑战,甚至有沦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附庸之嫌[15]20。
(三)对国际法实体规则的忽视
事实上,对于视法律为政策科学的学者,如果说他们视国内法为决策政策措施的一个过程时,尚为法律保留一点独立身份的话;那当他们视国际法的功能只是国际政治现实或进程中利益交换的体现而不是对行为的制约时,则连类似于国内法的那点独立性都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这时,政策定向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逻辑中:法律成了政策,国际法成了外交政策,国际政治最终代替了国际法;外交政策目标是维护本国利益,国际法成了维护个体国家利益之工具;政策就是人类尊严,外交政策就是“人类尊严”,“人类尊严”与各国外交政策的自私本性搅浑一起。同时,在各国的外交政策中,又是因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使得其外交政策横行无阻,那这不变成最后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成为“全人类的尊严”?简单地讲,政策定向试图在现实主义强势下彰扬国际法的努力,无形中又落入了否定国际法的圈套中,国际法所固有的公平或正义之根本价值与外交政策中的权力法则难以分清,国际法也就成了赤裸裸的以权力法则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即其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价值[15]20。
对国际法实体规则的忽视可能使国际法的作用大为削减或降低,这些将实用主义与法律程序紧密联系的学者实际上是认为:“在国际事务中,国际法的作用不是对决策的做出影响多少,而只是(程序上)如何影响。”[16]208这不仅使国际法的发展产生重程序而轻实体的不良倾向,也使国际法本身的概念产生混淆。对此,政策定向的批评者指出:“将国际法的概念等同于程序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毫无疑问,法律可以通过程序来制定,也可以通过程序进行修改,但其本身决不能与程序等同。将法律等同于程序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即在具体的某个时间点,具体的规则是能够被识别的。”[17]而且,轻实体重程序的倾向使得政策定向理论始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18]201,“在没有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国际社会里,谁以及如何确定一项政策抉择具有权威和控制因素呢?由强国吗?如果是这样,政策定向学说与‘权力政治学说’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15]
二、“超越规则”认识方法的缺陷
(一)纷繁芜杂的规则外因素
诚然,国际法的规则属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而且只能研究国际法律规则文本的语义学意义,我们应当承认创制和适用国际法律规则的过程,并且也应当承认(Bear In Mind)在法律规则之外的诸如情势、价值等其他决定因子的存在。然而政策定向方法所采取的完全开源(Open-Ended)态度,引入与特定情势相关的所有依赖因素(包括影响抉择的政策与价值等),事实上几乎没有给适用法律过程中的规则自治(Autonomy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留下任何空间。
在政策定向的语境中,我们必须区分规则的创制(或者如政策定向方法所称“指示进程”Prescribing Process)与规则的适用。显然,国际法律规则的创制行为①即通过条约或者习惯法进程创制或者修改规则。,需要考量政策目标、情势、未来发展以及其他对达成合理完善结果相关的所有因素。然而如果我们按照政策定向的逻辑思路考虑国际法的实施层面就能够发现,在国际法的实施中适用法律的机构(无论是国家还是法院),在考虑所有上述因素时都反而会成为受到限制的主体,原因是在考察一项具体的规则针对某个特定事实是否具有约束力或者可适用性时,按照政策定向的逻辑进路,则必然会被引向一个由相关政策因素的规范组成的海洋之中,而这些规范或者标准就会成为司法机构在适用法律之时的次级规则,由此而在相关问题上带来新的限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或者政策与国际法完全不相干,也不意味着这种国家行为的模式可以忽略,而是上述的政策性因素考量的范围和界限应当严格由法律系统规制。政策定向的理论构架相当庞大,但是方法设计的缺陷在于有关背景和相关联的因素上所使用的完全开放的概念。政策定向的实践观点已经注意到在判断某项行为是否可以适用某项法律条文的过程中,政府或者司法机构需要考虑法律之外的各种因素,政府可能会逾越法律的授权,政府也可能会寻求改变法律,但政策定向的方法却不能解释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在仅仅依靠考量政策目的和社会情势的情况下最后却获得了法律拘束力的问题。从某些方面上说,笔者认为,法律必须独立于政治。尽管从广义上讲并没有完全独立机构,然而适用法律的机构必须保有某种程度的相对自治,才能保证整个法律运行过程的衡平和公正[3]。
同样,对于习惯国际法而言,政策定向的方法将习惯国际法看作是诉求、反诉以及“为限制权力和与行为一致的方式行使权力创造共同期待”的理解进程构成①Customary law as a process of claims,counterclaims and tolerances that“create expectations that power will be restrained and exercised in certain uniformities of behavior.”,政策定向所认为的习惯国际法被称为是“价值澄清”(Value-Clarification)的过程[8],认为国家实际的行为模式反映了“对普遍利益的认知”以及共同的目的②麦克杜格尔教授在文中强调了这一点,即“合理性”(reasonableness)是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但不仅仅是判断国家行为的一个标准。这无疑反映出政策定向方法在对待“规则性”问题上的双重悖论(“normative”double play),主张“‘公海制度’包括两套相互补充的规定......一套以‘海洋自由’为名......另一套......则尊重......可进行干涉的权利主张。对内行人来说,这些规定和术语不是绝无弹性的教条,而勿宁是有伸缩性的政策选择。让决策者......有极广泛的斟酌自由来推行重大政策。”根据这一解释,麦克杜格尔教授在文中把美国在太平洋岛屿进行的核试验说成是在美国托管领土的地区和附近的公海海面上合法行使其有限的权利,借口“美国国防及保护自由世界的需要”,从而否认美国违反了国际法。[19]356[20]648[21]35。如同亚当斯密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定向对合理性的假定以及对权力的限制理论使得各个民族国家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转换成为了能够为共同利益服务的法律。政策定向的这个概念,从某种层面上说,确实为判定国际习惯法规则的成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标准,但这个概念事实上极大地侧重的是现实状况(status quo)。尽管为了判断国家实践是否能够为全人类的价值服务政策定向学说引入了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但这一想法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如此庞大而复杂(尤其是加上所有政策定向所要求的变量),以至于从实际层面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确实,政策定向理论从来没有主张其所需要考量的因素就是判断国家行为合法与否的标准,也没有主张过国际法应当以美国的政治目标和价值为基准[12],但政策定向主张的是某项行为或者抉择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其与“国际社会根本目标的一致性”③“Consonance with the fundamental goal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而这种“国际社会根本目标”又高于在国际法律规则、条约以及司法判决中体现出来的政策的“次级表述”(Secondary Expressions)。根据政策定向的方法,国际社会根本目标能够通过对人们实际保有的价值观念进行经验研究而得出。这样的观点看似完美无缺,然而我们应当如何考察当今世界逾60亿人实际的价值观念?对于政策定向的学者来说似乎这并不是问题,尽管他们没有实施任何调查但已经看似合理地推断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Overwhelming Numbers of People of the World)需要和平、安全、尊重以及自决的权利等,这些也就成为了政策定向所说的八大核心价值④按照政策定向的观点,麦克杜格尔教授采纳了拉斯韦尔教授所概括的人类社会八项价值:权力(power)、启蒙(enlightenment)、财富(wealth)、福利(well-being)、技能(skill)、情爱(affection)、尊重(respect)和正直(rectitude)。这八项在麦克杜格尔看来包容了各个方面的价值,是政策定向学说衡量法律的标准,构成政策定向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政策定向的观点,这些价值已经在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法律文件中得到宣示[21]35,然而这些价值总是作为基本原则出现的,无疑其用语是在最广泛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意味着描述这些价值的术语本身包含了最广范围的不同解释。而从二战之后美国和欧洲的角度理解,则很自然地就将其与自由民主的政治信条联系在了一起。那么从另一种层面来说,这种价值观念就并不是全球共有的。且不论世界上许多专制政权反对这样的西方式自由民主价值,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之中也有蔑视其他文化、试图征服其他人的价值存在。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否还能仅仅依靠经验式的判断就得出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坚持尊重个人价值的结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考量人类真正的价值需求问题上,政策定向的方法需要更多的升华和理性观念。
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政策定向学说在现代的发展之中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认为原有的政策定向理论并没有认识到国际社会各个地域在“人类尊严”的影响上是不同的,进而在其意义的理解上也是不同的;它们相互作用、产生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尊严”概念,但这一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①Hari M.Osofsky,A Law and Geography Perspective on the New Haven School,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2,2007,p.452.。但这一论述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政策定向学说在人类尊严的架构上所应采取的立场问题,即如何保障和进一步规范上述动态的“人类尊严”,而动态的标准如何判定,也成为该理论新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难题。
(二)根本目标与强国逻辑
此外,从政策定向的逻辑推理当中,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任何一项具体且明确的国际法律规则或者条约义务,如果不能与国际社会的根本目标相符,都可能会被否定②雷斯曼教授认为,尽管最后国际司法机构的判决可能会与双方的协议规则或者一般国际法规则都不同......,但判决是否合法并不是看它是否与这些国际法的二级规则相一致,而是看其是否与国际社会的根本目标相符。“Though the decision may diverge from the purport of either the special rule of the compromis or a general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the test of the decision's lawfulness is not its conformity to these secondary express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cy,but its consonance with the fundamental goals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Emphasis added.)[23]2011。无论一项国际规则或者一个国际司法判决如何忠于法律和事实,都有可能会被政策定向的理论指责并认为是无效的,只要这项规则或者判决被认定与国际社会根本目标不符。初看起来并无问题,但这又回到上文所述的问题上来,如何定义国际社会的根本目标?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至极端,我们甚至可能得出一个近乎荒谬的结论,那就是任何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例外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显然任何例外都是对基本原则的背离。
同时,这种推论还带来一个隐含的危险前提,即“人权高于主权”是存在的,而且即使某些国家以人权或者人道主义为由试图干涉别国内政或者对其他国家行使武力,在政策定向的理论前提之下也都能找到合法的理由,而这显然是与国际法律现实和国家实践相悖的。③例如,对于公海自由这个“基本原则”来说,任何对公海的限制性规则都是无效的;而我们也同样可以认为,一个国际司法机构,例如国际法院,在伊朗德黑兰人质案中的判决是无效的,因为它在承认外交豁免的同时限制了作为基本原则的国家主权。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但反映了政策定向在逻辑上的危险漏洞,使得法律规则能够被轻易废止。尽管政策定向的方法与彻底法律现实主义者所持有的规则怀疑主义(rule-skepticism)并不尽相同,但政策定向学者所主张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仍然留给了适用法律机构以巨大的裁量权力,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宣称其不受某项国际法律规则约束,只要其认为遵守这项规则可能会造成对基本原则或者价值的减损。这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的法治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这种逻辑更大的危险却在于,当这些更高层级的价值或者原则是由某个强国的特别政策决定之时,国际法律规则就彻底演变成为该强国推行政策的工具。尽管国际社会是由完全政治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但国际社会的价值是多元的,如果强国利用强大的资源优势,其利益的诉求很容易超越其他国家,一旦这些国家的行为被认为可以作为维护国际社会基本价值的行为,甚至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从而获得超越国际协定或者国际习惯的效力,那么整个国际法制体系就形同虚设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基本价值没有意义,相反,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以及对一切义务(erga omnes)概念的出现反而标志着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然而这些价值并不应当以损害法律基础的代价去实现,也就是说,一个受国际法律规制享有国际法上权利承担国际法义务的实体,不应当由其自身决定其是否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受到国际法的规制。国际法主体可以不遵守国际法,但必定也会由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甚至也可以作为国际法制定者试图寻求改变国际法规则,然而就仅其国家政策本身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应构成足够的基础推翻既有的国际法规则。
现代的国际社会国家体系是建立在平等多元的基础之上的,国际社会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一个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的“世界权威”(Global Authority),国际社会在“离心”和“向心”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得以达到平衡[24],同样,也不应当存在一个超越其他主权的一国政策,使得无论多么稳固的协定或者是习惯,只要与某国政策所宣称的国际社会根本价值相冲突,都成为被无视的对象,进而使得规避法律规则成为可能,而这种单边规避如果是出于对国际协调机构(无论是政治性组织还是其权力机构)或者司法机构的不信任而起,则国家会更加倾向于否定国际规则,而一旦规避或者否定国际法规则成为常态①例如发达国家经常采用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以及预防性自卫行动等,但分析这些行动的性质问题已经超出本文探讨的范围,故在此不予详述。[25]226[26]49[27]107,不仅国际法治的权威和信任都将面临巨大的危机,更危险的是历经几个世纪建立的国际社会秩序规则都将沦为大国手中强权的工具。正如著名诗人叶芝在《第二次圣临》中所说,“猎鹰已听不到驯鹰者的呼唤”[28]。
三、国际社会权力控制论的缺陷
根据政策定向的观点,法律源出于世界社会进程中关于价值分配的主张与反主张不断的遭遇和冲击,然而在所有的进程中“权力”(power)作为工具性的价值都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并作为最终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存在,由此而生的抉择进程中必然就会包含政治的过程[29]。那么如前文所述,法律也就成为众多抉择之中同时获得权威性和有效性的一种成功记录,由此关于价值分配过程中的每一次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立法的尝试[8]。如前所述,这种概念所包含的混乱不仅使得法律规则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出现,更使得识别法律成为一项艰难的任务,分析法律与社会其他各种方面的关系也就成为经常性的难题[30],尤其是在国际层面这个以非集权式(decentralization)为特征的主权平等社会之中,这项任务显得更为困难和不可完成。
事实上,尽管国际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组织化的趋势[24],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高度分权化并且各个主体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31],如前所述,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体系中我们很难找到清晰可辨的权威抉择制定过程,甚至可以说,在这样的国际社会层面中关于价值的分配根本不存在能够产生有效(effective)、权威(authoritative)的抉择的一般抉择制定过程(Gener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②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政策定向的这种抉择制定过程理论更加适用于中央集权的国内法律体系,而不是各个国际法主体相对独立和权力分散的国际社会。“...[C]onception of law yields distinctly more conclusions when it is applied to relatively well-integrated domestic systems than when it i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highly decentralized international system.”。政策定向理论仍然没有解决在国际社会层面是否存在具有可操作性的确定抉择权威性(authoritativeness)的系统标准问题,当权力这种工具价值反而成为决定社会抉择过程有效性的中心价值时,国际社会中的有序过程就沦落成为了瓜分权力的混沌过程。
为解决这一困境,政策定向的理论采用了一种“法律子系统”(sub-systems)的方法,认为在一个整体国际体系之中,还包含着数个平行的法律和秩序系统,而非一个与整体国际体系共存的单一法律体系[32]1。也就是说,政策定向的逻辑认为在国际社会层面上,可能并存着西方法律体系(Western System of Law)、东方法律体系(Eastern System of Law)或者第三世界法律体系等多个体系,但即使是政策定向学者自己也无法确定这些法律子系统之间的界线和所包含的内容如何,更遑论在今天各大法系相互交流融合之中如何识别各个法律体系,进而判断在整体国际法律体系中的抉择过程了。但也有部分政策定向的学者认为,目前的国际社会秩序体系或者说法律体系相对于国内社会来说,仍然处于高度幼稚的萌芽时期(Embryonic System)[8],但仅仅指出这一现实显然是不够的,这种辩解不仅没有明确解决现存的具体问题,同时这个“萌芽”概念本身又带来更多的困难,例如,一个公共秩序体系的最低标准是什么?而一个胚胎系统和一个完善的体系之间区别又何在?这些问题将政策定向关于法律规则和社会科学联系的观点带入了一个无限循环,那就是用政策解释规则,又认为一部分政策可以成为规则,进而演变成政策解释政策,而这时才发现应当构建一个规则体系,为时已晚。事实上政策定向方法寻求理论结果的方向与通常可行的理论方法南辕北辙,政策定向通过引入大量的影响因子讨论抉择过程而不是试图通过尽可能地去除无关因素建立起简单的事实模型,这种方法尽管全面,但却造成了政策定向的国际法理论成为了在一个充满了逻辑可能但却没有更多实质性内容的大集合之中寻找真相[8],并且在分析中根本无法全面掌握如此之多的决定因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定向理论毕竟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理论阵营的;它是建立在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的基础上,而不是以权力现实主义(power realism)为导向的基础上,因此,麦克杜格尔也严肃地指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低估了规则和法律过程的作用,过度地强调了权力的重要性。但是,从政策定向的理论构架中又不难发现存在的法律与权力的矛盾与纠结,尽管随后的新政策定向理论仍然坚持对国际法怀疑主义的批判,但其多元化研究的范式和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反而在实质层面上削弱了国际法的适用能力。
四、国际法价值与目标的悖论
(一)关于规则与价值的悖论
政策定向的理论方法主张,所有对法律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应当以价值为导向,政策定向由此也设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良好的世界秩序应当建立在尊重和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尊严的理念之上[33]203,进而政策定向将人类尊严定义为尽最大可能地产生价值、分享既存价值,以及所有人参与的价值分配决定过程。但是,政策定向的价值概念,显然是深深植根于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观念之上的,且不论这种价值观念是否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有主体接受,仅就这个概念本身而言也存在着自相矛盾的问题。
1.参与悖论(Participation Dilemma)。首先,最大程度的参与分配价值(Maximum Participation in Determining the Distribution)看似能够不断地创造新的价值,但是政策定向却忽略了另一个方面,最大程度的参与抉择过程所带来的成本消耗本身就会导致对产生新价值的资源的巨大减损,而这在国际社会的层面上尤为明显。简单地说,国际社会进程所有参与者都能够作为国际法的立法者固然能够保证所有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但是这一过程本身在实际国际社会之中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为巨大的民主过程往往会拖垮国际机构的效率,特别是国际社会的民主过程仍然处于相对不完善的萌芽阶段。对于这种价值冲突来说几乎是不可调和的。
2.再分配悖论(Redistribution Dilemma)。按照国内法理学的观点,法律的运行过程也必然包含正义价值的重新分配过程[34],同样,作为国际层面的国际法也会在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正义以及其他价值的再分配问题,然而政策定向所忽略的一点在于当涉及到正义价值的重新分配时,或者说为了达成人类尊严的目标时,却必需减损对某些人来说必要的尊严,这时所遇到的矛盾应当如何解决?这种冲突在国际社会层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必须采取的国际强制行动等等。按照政策定向的方法论推断下来,我们甚至会得出一个近乎荒谬的结论,那就是在产生新价值的分配之中,甚至在大多数社会体系中维护最小公共秩序(Minimum Public Order),只有采取完全的平均主义才是最优的选择。而这显然是与国际社会现实不符的。
对于政策定向的理论来说,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和悖论并不能仅仅通过单纯地承诺应当达成尊重人类尊严的最佳世界公共秩序来完成,这对于政策定向理论试图在国际社会中提出这种广泛涵盖诸多棘手问题的概念来说尤其如此①例如,关于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中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价值分配和交换问题(“redistributive problems underlying the emerging North-South confrontation”),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关于人口、环境、人权等一系列问题(“the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 and the impetus to headlong modernization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third world.”)。。尽管政策定向的理论一再强调全世界的人都应得到尊重,但政策定向的理论实质上依然带有某种盲目的美国情怀,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才是最完美的制度,而美国也理应成为世界民主的灯塔和航标灯;尽管政策定向的理论在考虑全世界所有人的人格尊严的宣言之下也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境遇,但显然政策定向的理论并没有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殊发展状况以足够的注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崛起和发展的今天,一方面需要面临本国发展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需要努力融入当今国际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体系、需要参与地区事务的处理等等问题[35],然而政策定向的理论无论是对于当时后冷战时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还是国际社会之中面对压力使用强力(有时甚至是武力)促进社会变革的各个集团,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可圈可点的关注和分析[8]。
如前所述,显然在一些基本的观点上,政策定向的理论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实践一些特殊领域之中已经盲目地接受了美国的一些特别“成就”(establishment),诸如氢弹试验案(Hydrogen Bomb Test Case)、古巴导弹危机、关于越战的看法以及关于冷战问题等[36]597[37]1[38]235。而也正是如此使得政策定向的理论开始成为美国对外关系实践行为的注释者,从而与政策定向所一直主张的维护所有人人格尊严的世界公共秩序自相矛盾[39]914。事实上政策定向的理论观点是如此关心价值的中心作用,但却在实质性的结论中被一系列含糊不清的规则行前提所干扰,这种自身的矛盾可能不仅仅是由时代背景决定的,而可能是政策定向理论所建立的价值基点问题。
从学术思想或研究路径看,一方面,政策定向继承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认为必须通过具体的经验或观察来发现国际法的内容。实际上,由于政策定向的目光落到比国际法规制下的国家行为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的层面,它实际上比实证主义国际法学还更为“实证主义”。另一方面,与现实主义者一样,政策定向也意识到实证主义法学以规则为“实体”来定义的法律概念的严格限制性——由此涉及国际法是否是“法”以及即使是“法”,也是一种原始类型或松散型法律的问题。不过,与认定国际法是以规则为基本要素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无足轻重的现实主义者不同的是,政策定向并没有为了迎合权力政治的需要去漠视及排斥国际法,而是努力将现实主义强调的权力因素归纳到法律分析要素或者法律之外的背景因素的范畴之中。换句话说,政策定向谨慎地将现实主义者的核心观点包容进法律程序的分析框架,但并不是以排斥国际法的作用为代价[14]。
(二)世界公共秩序(World Public Order)的错误定位
政策定向的学者向来关注的一个重点即是关于世界公共秩序的理论[40]771。政策定向的理论通常将世界公共秩序定义为国际体系中为法律规则所保障的社会与政治过程②这里所说的“保障(protection)”概念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模糊,也许可以认为是某些特定模式的抉择间接暗示了对社会系统某些特性的维护,但如果认定实际上是这些决定本身在保护社会系统的这些特性就显得比较奇怪了。“While it is possible to say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certain features of a social system is implied by a given pattern of decisions,it seems peculiar to argue that it is the stream of decisions itself which actually protects these features of the social system.”。也就是说,世界公共秩序与基本社会与政治安排或者关系相关联,而这样的社会和政治安排又为社会体系中源源不断的有效与权威抉择所维护。[32]政策定向的学者有时也简单地即将世界公共秩序定义为对国际社会中“未授权”(unauthorized)强制行动的禁止(prohibit)或者“最小化”(minimization)①关于“未授权”(unauthorized)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政策定向的理论甚至没有解释清楚在国际社会中是否存在清晰可辨的被认定为“权威”(authoritative)的抉择过程,因此所谓的“未授权”的概念也仍然是含糊不清的。[41]337,在这里,世界公共秩序被更多地作为“和平”的意义使用。尽管政策定向理论试图将传统国际政治讨论的世界秩序问题与国际法相联系,但仍然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在世界秩序研究之中清楚地区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并不是容易的任务,从某种角度来看,甚至在国际社会的公共秩序之中都不存在任何法律因素、法学观点或者方法,除非有限定性的规则规定整个国际秩序研究必须包含在法律分析的类别之中。总之,世界秩序通常是基于政治基础,而其核心问题也在于社会政治关系而非法律问题。因此,即使并没有传统的可归因因素例如法律体系(包括立法、司法以及执法机关等)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也不能形成政策定向所谓的权威抉择过程的社会体系,也可能表现出某种稳定的秩序,在这种社会体系之中,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更大程度上则是政治规则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功能作用[42]。
应当承认,政策定向方法试图将国际法律与世界公共秩序相联系的努力为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研究都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研究路径,但是政策定向的理论从来没有成功明确国际法与世界公共秩序之间的真正关系,而是一直作为政策定向理论大厦中的灰色角落而存在②政策定向关于世界公共秩序概念的模糊性其实并不奇怪,相反,这只是学界对于“世界秩序”这个概念普遍无法精确定义的一个例子。。因此,新的政策定向学说开始了对这一公共秩序的反思,认为新时代的政策定向理论多应当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备多元的特性,因此不得不无奈地承认,单一的“世界公共秩序”其实并不存在,“尽管这一理念是政策定向学派为之奋斗和期望的”[43]328。新的政策定向学者们认为,理论应致力于国际社会的多样性、致力于国际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公共秩序。由此可见,尽管政策定向的理论发展试图修正其所不能解决的国际问题,但是在面对新的问题之时,政策定向仍然似乎倾向于抛开通过法律以达到最优公共秩序的理论机制[44]359。
[1]L.Kalman.Legal realism at Yale,1927 -1960[M].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6,14.
[2]Burley,Anne - Marie Slaughte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Dual Agenda[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3,87.
[3]刘志云.纽黑文学派:冷战时期国际法学的一次理论创新[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9).
[4]Harold D.Lasswell&.Myres S.McDougal.Legal Education and Public Policy: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J].Yale Law Journal.1942 - 1943.
[5]邵沙平、黄颖.新多边主义时代中国国际法的使命[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6]Stanley V.Anderson.A Critique of Professor Myres S.McDougal's Doctrine of Interpretation by Major Purposes[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57.
[7]Schachter O.McDoual's Jurisprudence:Utility,Influence,Controversy[J].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1985,79.
[8]Young O R.International Law and Social Science:The Contributions of Myres S.McDougal[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72,66.
[9]Anderson S V.A Critique of Professor Myres S.Mcdougal's Doctrine of Interpretation by Major Purposes[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63,57.
[10](俄)格·童金.国际法理论问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11]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12](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3]Mcdougal M S,Lasswell H D.The Identification and Appraisal of Diverse Systems of Public Order[EB/OL].International Rules: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ck R J,Arend A C,Lugt R D V.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96.
[14]Beck R J,Arend A C,Lugt R D V.International Rules: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96.
[15]刘志云.纽黑文学派:冷战时期国际法学的一次理论创新[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9).
[16]Burley,Slaughter A.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Dual Agenda[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3,87.
[17]Arend A C.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Legal Rules[EB/OL].International Rules: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ck R J,Arend A C,Lugt R D V,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6,290.
[18]白桂梅.政策定向学说的国际法理论[J].中国国际法年刊,1990.
[19]Mcdougal M S.The Hydrogen Bomb Tes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55,49.
[20]Mcdougal M S,Schlei N A.The Hydrogen Bomb Tests in Perspective:Lawful Measures for Security[J].Yale Law Journal,1954,64.
[21]彭汉英.当代西方的法律政策思想[J].外国法译评,1997,(2).
[22]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Z].1948.
[23]Reisman W M.Nullity and Revision:the Review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Judgments and Award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
[24]梁西.国际组织法总论(修订第五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25]Butler M J.U.S.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Crisis,1945- 1994:An Empirical Inquiry of Just War Theory[J].Journal of Conflict Research,2003,47.
[26]Parekh B.Rethink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Rethink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7,18.
[27]Goodman R.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Pretexts for Wa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Pretexts for War[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6,100.
[28]Yeats W B.The Second Coming[Z].
[29]Lasswell H D,Kaplan A.Power and Society: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0.
[30]Jr.Marion J.Levy.“Does it Matter if He's Naked”,Bawled the Child[M].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Knorr K,Rosenau J 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31]Young O R.A System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R].Princeton:Princeto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8.
[32]Mcdougal M S,Lasswell H D.The Identification and Appraisal of Diverse Systems of Public Order[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59,53.
[33]Lasswell H D,Mcdougal M S.Legal Education and Public Policy: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J].Yale Law Journal,1942,52.
[34]李龙.法理学[G].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5]Falk R A.The Status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36]Mcdougal M S.The Soviet-Cuban Quarantine and Self- Defense[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63,57.
[37]Moore J N.The Lawfulness of Military Assistance to the Republic of Viet- Nam[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67,61.
[38]Moore J N,Underwood J L.The Lawfulness of 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the Republic of Viet Nam[J].Duquesne Law Review,1967,5.
[39]Higgins R.Policy and Impartiality:The Uneasy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Law[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69,23.
[40]Mcdougal M S,Feliciano F P.International Coercion and World Public Order: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War[J].Yale Law Journal,1958,67.
[41]Mcdougal M S.Some Basic Theoretical Concepts about International Law:A Policy-Oriented Framework of Inquiry[J].Journal of Conflict Research,1960,4.
[42]Claude I L.The Changing United Nation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7.
[43]Paul Schiff Berman,A Pluralist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2,2007.
[44]Christopher J.Borgen,Whose Public,Whose Order?Imperium,Region and Normative Friction,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2,2007.
Beyond the Legal Rules:New Haven Approaches on International Law
LIU Xiao-me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Wuhan University Wuhan,430072China
The generation of policy-oriented theory of law uphold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t of realism,which regards the law as a dynamic concept conserning a real shock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research circles.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New Haven Approach holds the complete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legal buildings.But in fact,the policy-oriented attempts to blend into the law of other social sciences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foundation of law,in particular,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while the basis of this new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not solid.S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theory is faced with various challenges.
Policy-oriented Theory;New Haven Approach;Fundamental of International Law
D922 291
A
1000-5072(2012)05-0030-11
2011-05-27
刘筱萌(1984—),男,河南南阳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国际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国际法、国际组织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晶晶 责任校对 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