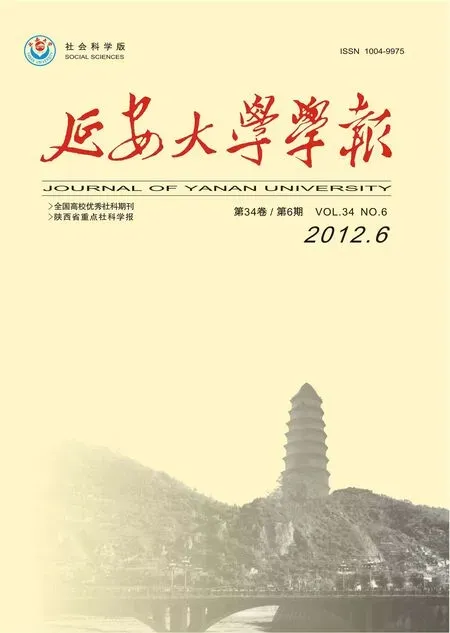从脑体矛盾的演化看教育的本质属性
毛善成
(淮阴工学院 图书馆,江苏 淮安 223003)
教育属性的探讨是教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教育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教育的属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多种观点,如上层建筑说、生产力说、多重属性说。这些研究都揭示出了教育的一些基本属性如社会性、阶级性等,现在又有产业属性和经济属性、公益属性之说。由此可见,单纯的教育属性的论争不能达到任何共识,表明了学术界对教育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事物的本质属性通常是与事物的内在矛盾紧密联系的,是事物相互区别的显著特征。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之所以区别于其它的社会存在,一定有其特殊矛盾。教育本身表现为一种宏观运动现象,它的微观基础是人的活动。只有通过对人的特殊结构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发现它的特殊矛盾。伍雪辉基于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的思考,“从人的结构与人的存在来探讨教育的属性”。[1]笔者把“脑体矛盾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2]并用脑体矛盾的演化规律解释了许多教育现象。根据脑体矛盾来探讨教育的本质属性也许是一条可行的思考路径。教育本质属性及其规律的发现,能从根本上揭示教育过度行政化的错误。
一、教育的本质属性
(一)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党性
研究事物的本质属性必须从分析事物内在的特殊矛盾性入手,这是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人是教育的细胞,如同商品是经济的细胞那样。马克思从商品分析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笔者认为通过对人内在矛盾的分析同样可以揭示教育的运动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从猿到人的进化中,就存在脑体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脑体矛盾的第一发展阶段),即“类人猿肢体的进化显著快于脑的进化”,[3]是脑体矛盾的最原始的表现形式,肢体为该过程的主要矛盾方面。随着脑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不平衡消除了,但大脑的发展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形成了新的不平衡现象(脑体矛盾第二发展阶段),即人类脑力发展显著快于体力(能)发展,是“人类体力(能)发展的有限性和脑力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矛盾运动”[2]所推动的结果,这是教育的自然属性。教育的自然属性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之一,是指教育具有提升人类智力活动和知识水平的客观要求,无论古今、中外的教育都是如此。像古代中国的教育,尽管历史悠久并源源流长,但由于带有愚民政策的致命弱点,使中华文明无法孕育出近代自然科学的巨人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巨人,其结果众所周知,违背教育的客观要求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人的智力水平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也就提高了。这是教育属性“生产力说”的来源。历史上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都与人类的智力水平提高直接相关。由此可见,人类体力(能)发展的有限性和脑力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运动,不仅是教育发生发展的推动力,也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动力。所以说,教育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生产力进步、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脑体矛盾也表现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分工、分裂。在原始社会末,人类先后进入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代。文明时代的到来,预示着原始社会的解体。随着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三次生产劳动大分工。即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再次,是商人与直接商品生产劳动脱离来从事贸易。这三次分工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物质财富的获取直接相关,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创造了物质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文明时代的真正到来。只有脑力劳动者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才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从此人类才真正结束蒙昧和野蛮时期。文明的三个显著特征是文字、城市和青铜器具,并至少要具备其中的两条,但文字是必须具备的。进入文明时代,人类创造了象形文字,产生了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艺术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奴隶主在城市修建宫殿、宅邸、宏伟的庙宇、祭坛,开展了艺术、科学的研究。从此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与分离。脑体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是教育尤其学校教育产生的基础。教育中的分层、分类现象开始出现,如少数人受教育而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教育或学校之外;富人的子女受教育而穷人的子女被排斥在教育之外;上流社会的人员受到教育而劳动人民被排斥于教育之外等,这些是教育的社会属性的具体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脑体劳动逐渐走向融合,许多国家实现基础教育的义务化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教育的分层现象少了。表明教育的社会属性在不断淡化。
由于脑体劳动在社会上的分离,随之出现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对立和阶级统治。教育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统治阶级对教育过程如教育教学的内容、教育资源的掌控以及剥夺那些人受教育的权利等具有绝对权威,这就是教育具有阶级属性的表现。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四类分子”的子女不准接受中学以及高等教育,这就是教育的阶级属性的具体表现。经过改革开放和“拨乱返正”,我国的阶级矛盾已基本消亡,所以,教育的阶级属性(党性)已逐渐淡化。现在,我们鼓励服刑人员接受高等教育。这些现象,表明教育的阶级属性随着脑体矛盾的对立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教育的本质属性,必然在教育学和教育研究中有所表现,使教育学具有社会科学的特点和鲜明的党性,使教育和教育学具有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征,所以在大的学科分类中,我们把教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来看待的,教育和教育学也经常成为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学研究常常受到社会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中国建国后教育学理论和教材几乎都来自红色苏联,随着中国的改革开发和意识形态的淡化,才开始重视把欧美的教育学理论译介到中国。李刚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范型变迁的总结提供了更好的证明:“陶行知研究的演进主要不是基于学术内部学理的变化,而是受制于外在的政治”;[4]“陶行知研究范型的嬗变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继承与突破、政治社会的现实制约、气候和社会风尚、研究共同体的学识情感复杂互动的结果”。[5]确切地说,是教育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在教育研究和教育学理论建构上的表现。教育的自然属性也同样在发挥作用,例如,德国学者赫尔巴特(1776-1841)最先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定为心理学,国内学者认为“人类学是教育学理论创新的‘它山之石’”,[6]表明他们对教育的自然属性的某种考量。
(二)教育本质属性的演化
教育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是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由脑体矛盾的逐渐演化所产生的,也必将随着脑体矛盾的进一步演化而变得此消彼长。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开始走向融合,脑体对立的现象也在不断下降,所谓蓝领和白领在经济收入上的差别也在不断缩小。脑体矛盾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教育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的不断下降直至消亡。
自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已经发生了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人类的学校教育不断得到加强。从基础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普及都是教育的自然属性及其矛盾运动所主导的。教育的自然属性是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加强的。可见,教育和教育学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是教育本质属性的发展变化规律,也是教育的发展规律,更是其它教育规律的基础。违背这一规律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中国高等教育过度行政化的后果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脑体矛盾的演化决定教育规律的实证研究
(一)中美基础教育之比较
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中美教育的比较研究”文章和来自中国人撰写的美国教育考察报告,这里摘录一二。
20世纪70年代,我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等教育。考察团写了一份3万字的报告:“学生无论品德优劣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法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眼里,让地球掉个个儿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重音体美,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7]而美国高年级的学生就开始忙碌了,以便作好进大学的准备,据说“美国高水平大学对高中生的选课和课外活动很看重。很多十一年级的孩子,夜里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要从课内忙到课外”。[8]中国学生可以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很累,其实,他们只忙学习这一件事!而上大学后却轻松多了。
再看看美国的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干什么?玩和运动!张金梅对美国一所托幼中心全日班一日活动的观察表明,美国的幼儿教育注重户外活动。“上午70分钟,下午85分钟;上午集体跳圆圈舞20分钟,下午为10分钟。园内的活动区有玩具区、阅读区、角色游戏区、美工区、建构区、其他类(聊天、自由玩、哭闹等)”。[9]每天在幼儿园670分钟只有20分钟读书时间。
从美国的中、小学教育的数学和科学文化测试成绩来看,其教育教学水平在全世界的排名为28-30名,落后欧洲所有国家,北美国家水平也在美国之上,和中国就不能比了。中国中学生的国际比赛,经常包揽国际上的数理化金牌。新华日报2000年10月13日报道,美国从1945年后,诺奖得主的2/3是美籍人。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共培育了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97位知识型亿万富翁。诺奖颁发100多年,建国已60年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还只作家莫言一人在本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美国的学生相比较,可以说中国的学生是打赢每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教育教学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加本质的原因:是对基础教育规律的遵守还是违背。是什么样的规律在支配着教育教学的逻辑发展?这个规律就隐藏在人类早期的进化史中。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体脑进化的不平衡是普遍现象。按照吴汝康先生的解释,由于劳动,类人猿腿骨和手骨首先进化,进化速度较快,而脑的进化较慢,这是体脑进化不平衡的原因。类人猿进化首先是肢体的运动和手脚的解放,然后才有脑的发展和发达。这种现象对于儿童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的意义,较早期的文献称之为“教育的重演律”,[10]也就是历史决定教育教学的逻辑。正如卢梭(1712-1778)所说,“有了体力,他/她运用体力的智慧也就跟着发展起来了”。[11]
从容量上讲,人脑的三分之二是0-3岁期间完成的,3-6之间脑量增加显著放慢,6-8岁儿童的脑量已接近成人的脑量,但脑量的多少并不是人脑聪明的唯一决定因素,而脑的内质(好比电脑的内存,是进行复杂计算和理论思维、抽象、逻辑推理以及知识学习等智力活动的基础)才甚为关键。在脑容量增加以后,脑的内质提升进入关键期(4-6岁),刚好对应于幼儿园教育。无论脑量的增加还是内质的提升,都需要血液循环,需要带有丰富营养的血液在大脑血管内充分的运动。这个过程必须有儿童肢体运动和手脑并用活动来维系。游戏、玩耍、户外活动、跳圆圈舞、绘画、搭积木甚至哭闹等都有利于儿童脑部的血液循环的整体运动。脑部的血液循环的整体运动,是提升大脑内质的重要手段。一项研究儿童玩电子游戏成隐机理的研究表明,儿童玩电子游戏时其大脑只有局部异常活跃,而做数学题时其大脑整体活跃。大脑内质的提升过程将一直持续到12-14岁的初中阶段。所以到高中阶段,美国的高中生开始忙碌起来,一直从书内忙到书外。有良好内质的大脑,才是后天智力竞争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智力源泉。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仅要有智勇双全的将帅和士兵,更要符合战争规律,教育也是如此。所以看似“病入膏肓”的美国教育却在教育发展的最后阶段——高等教育阶段取得辉煌胜利。脑体矛盾不仅是推动人猿分离和人类进化的有力杠杆,也是推动教育发生发展的根本矛盾。脑力发展的无限性和体力发展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也是教育必须遵守的逻辑规律,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所面对的客观问题就是如何开发人类的脑力来弥补人类体力的不足,实现脑力和体力的相互转化。教育科学的理论建构必须围绕脑体矛盾这根红线展开。
(二)我国教育行政化的后果
教师和教育研究人员对我国当前的教育行政化不断加强,表示出许多担忧,并斥之为不懂教育规律乱弹琴,让大学长大,让学生长大,让先生自主的呼声不断。齐鲁晚报在教师节发表评论员文章,呼吁“别让教师成为‘高危行业’”。[12]学者必须呼吸自由的空气才能成为大师,有大师才有学派。郭齐家认为“教育、行政有各自的规律,拿行政的规律套教育规律肯定是行不通的,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当代难出大师、难出学派。当前对学术管理过严过细,学术自由的空气不足,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学里学派难以产生”。[13]本来,教育行政化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教育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如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大师,希望中国能生产出有世界影响的科学成果,使中国成为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大国、创新强国。然而,教育行政化的过度扩张却事与愿违,难以收到好的效果,使人才也更加难出了。因为,教育行政化违背了教育本质属性的演化规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的自然属性理应得到加强,而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党性)应该减弱或者淡化。这才符合教育的发展规律,即教育本质属性的此消彼长的规律。教育的自然属性是指智力发展的无限性和体力发展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呈现出的本质特征,是教育区别其它社会活动的本质而永恒的特征。正如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所强调的大学目标“永远是理解和保护理智力……因为理智力是教育和研究的唯一基础。对知识原理进行发展、详尽阐述和精炼提纯的活动,才是大学的最高活动之一,也是大学教授应该从事的活动”。①参见施晓光《为“理性人和民主社会”的高等教育——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思想辨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年第3期,第167-175页。
(三)教育去行政化的当下困境
首先,教育去行政化存在现实的困境。郭齐家认为,“当前,去行政化最大的阻力是用什么观念来领导大学,是让学术自由发展,还是由行政管住学术”[13]。众所周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是现实的影子。现阶段,我国的脑体矛盾还比较严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还有很大的差别。我国体力劳动者的主体构成为农民工,农民工的社会
地位还无法与城市的普通市民相比。具体地讲,农民工在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救助、子女入托和就学方面还无法与他们所劳动和工作的城市的市民相比,二者的差距还特别大,甚至他们的户籍也不能迁人城市。从经济收入上看,我国现阶段的脑力劳动者的主体构成为国家公务人员、律师、科学家、医生、教师、等国家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以及企业的管理人员、研发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员的经济收入普遍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收入一般为体力劳动的3-5倍。王春超等的研究表明,“城镇职工收入平均是农民工收入的3.43倍。”[14]尽管近些年城市“用工荒”、大学生就业困难等现象的出现,农民工收入有所增加,却难以撼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实。其次,中国政治的强势地位。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权力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让路,中国的教育体制就不会得到有效变革,教育去行政化只能是空谈,行政化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南方科技大学的去行政化尝试被国人喻为“南柯一梦”就是很好的例证。“依法治校”等观点的提出是教育行政化的持续发挥,一旦实现,教育将更加万劫不复。
教育学是一门关于“脑力和体力相互转化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为脑体矛盾。脑体矛盾运动和发展不仅推动着人类自身的进化和发展,也是教育发生发展的最原始的动力。脑体矛盾首先表现为脑力发展的无限性和体力发展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运动形成了教育的自然属性。所以提高人(受教育者)的智力活动和知识水平是教育活动最显著的特征,是区别于其它活动的本质特征。故研究智力和知识活动的水平可进行实测,如智商的测定,考试卷的打分量化等,表明教育学具有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像脑科学、心理学以及实验教育学等研究成果都是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也说明人类智力活动和知识水平的提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人类智力活动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可以通过人类“大脑内质”这一概念来说明。大脑内质,好比电脑的内存,是进行复杂计算和理论思维、抽象、逻辑推理以及知识学习等智力活动的基础。大脑内质的提升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需要重演人类的进化史,即遵守教育过程的重演律。可见,大脑内质是教育学意义上概念而非心理学或生理学上的概念。这样,教育的发生发展也可以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考察。基础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升学生的大脑内质,而不是什么学习和考试分数。我国的幼儿教育、小学和初中教育表面上看比美国同阶段的教育要成功得多,但由于忽视了学生大脑内质的提升,所以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普遍不如美国的学生,这正是我们赢在起跑线却输在终点线的原因。
教育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是教育的本质属性,是脑体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自然属性是教育的永恒特征,是教育有别于其它活动的标志。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显著下降,这是教育本质属性的演化规律。如果把“知识就是力量作为教育学第一定律”[7],那么,教育本质属性此消彼长的规律可称为教育学第二定律。我国当下教育的过度行政化就明显违背这一规律,不可能有好效果。
[1]伍雪辉.人的本质及其教育立场——基于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的思考[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79-82.
[2]毛善成.从科学问题的分类看教育学的研究对象[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4):113-117.
[3]吴汝康.中国猿人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劳动创造人类”理论的意义[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l):25-32.
[4]李刚.“从人民教育家”到“教育万能论者”——评20世纪50年代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再评价[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4):1-14.
[5]李刚.陶行知研究范型的嬗变(上)[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2):10-19.
[6]杨孔炽.教育理论创新的“他山之石”——从人类学研究的几个特征谈起[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4):95-99.
[7]李希贵.一个中国教育局长眼中的美国教育(上)[J].人民教育,2006(10):11-13.
[8]樊未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教育:轻松背后的繁重[J].基础教育,2007(8):20-21.
[9]张金梅.对美国一所托幼中心全日班一日活动的观察与反思[J].学前教育研究,2008(3):49-54.
[10]毛善成.从日、美、德的创新路径看创新教育的基本规律[J].淮阴工学院学报,2001(5):44-45.
[11]卢梭.爱弥儿论教育: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1.
[12]沙元森.别让教师成为“高危行业”[N].齐鲁晚报,2012-09-11.
[13]郭齐家.教育者要找回丢掉的心[N].中国科学报,2012-09-19.
[14]王春超,荆琛.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对经济产出的贡献与收益分享[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2):144-153.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