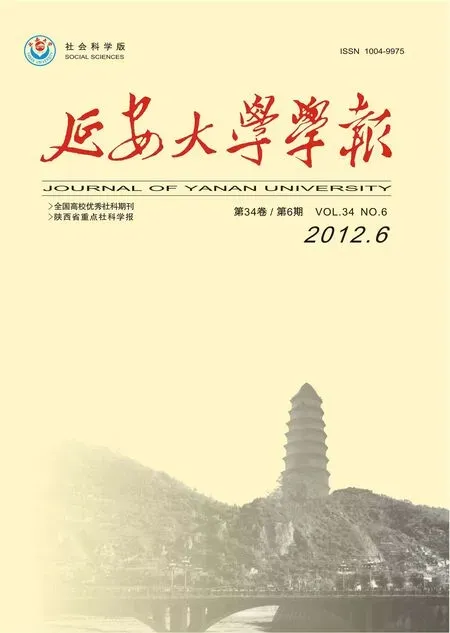艾森斯塔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研究
刘晓庆
(宁夏大学 政法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艾森斯塔特,一位以色列的社会学家,通过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以及其他文明的对比研究,认为“轴心文明”是以西方文明为核心提出的,现代性被单纯的理解为西方化。在对“轴心文明”的质疑中,艾森斯塔特提出了“第二轴心时代”,他的“多元现代性”理论也由此成熟。所谓“多元现代性”是指现代性不是单一的西方化而是多元化,现代世界的文明史是多元的文明史,现代性也应该是多元的现代性,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现代性不断变化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也遵循着中心渗透边缘的规律,不断完善、成熟。因此,艾森斯塔特认为“理解现代世界(包括在当代的历史背景下,更准确的来说,是在现代性的历史背景下宗教范围内的高涨和复兴),最好的方式是将它看成一个现代多样文化不断发展和连续重组以及具有特色的现代制度模式的发展过程。”[1]
在各种文明现代化的过程中,探索适合于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成了主要任务,政治、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甚至会出现各种呼声、各种运动,原教旨主义运动就是其中的一种。艾森斯塔特认为,原教旨主义运动属于形式现代、内容传统,“从其意识形态建构的视角来看,它们(原教旨主义运动)构成了彻底的现代运动,这种现代运动传播一种反现代的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2]289从根源上剖析,原教旨主义运动所内含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根植于所在地区的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宗教文化中的异端,其核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革新的乌托邦宗派主义”[2]289,而研究原教旨主义的方式是“将之既置于其文明的历史经验的语境中、其多种多样的宗教传统的语境中,还得置于现代性的文化与政治规划的语境中”[2]289。在此背景之下,艾森斯塔特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行探究。
一、普遍主义的乌玛理想
穆罕默德接受神启后创立伊斯兰教,结束了阿拉伯人的多神崇拜,结束了部落、宗教纷争,将阿拉伯人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伊斯兰教从此成为阿拉伯地区的普遍信仰。伊斯兰教作为一神教信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它强调单神崇拜,信仰真主安拉,这种独一性和普遍性使得乌玛社团成为“穆斯林”的共同理想王国。艾森斯塔特认为,这种乌玛的理想,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建立自己独特的政治动态和宗派主义模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同样也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形成的源泉。
第一个乌玛社团是622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在这之前阿拉伯半岛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氏族的人群并存,矛盾重重,穆罕默德迁入麦地那后,针对此问题,提出了“穆斯林皆兄弟”的口号,维持团结和统一,之后与各氏族、各宗教信徒协商,订立了《麦地那社团章程》,“将迁士、辅士,以及麦地那的犹太人和异教徒,组成统一的社团,从而突破氏族制外壳,建立以宗教为纽带的地域性组织。”[3]这个章程明确了穆斯林内部和外部关系以及和平相处的理想、矛盾处理的办法,为“乌玛”的实现作了有力的奠基,最终麦地那实现了统一,初步建立起以“乌玛社团”为形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社团内部成员享有“原则性的政治平等”。[4]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麦地那的乌玛社团强调的是宗教信仰的统一性、政治宗教的合一性和族群成员的平等性。
到伊斯兰帝国的全盛时期,四大哈里发致力于对外扩张,使得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地方伊斯兰化,实现“乌玛社团”的统治。至奥斯曼时期,乌玛社团所管辖的范围东达亚美尼亚和花剌子模,西至北非的昔兰尼加。但是,在领土扩张的同时,乌玛内部问题重重,穆罕默德的归真使得继任者的选择成为了一大难题,教派内部展开激烈的角逐,帝国内部教派林立,出现了了逊尼派、什叶派以及哈瓦利吉派,各派之中又分裂出小的支派,以宗教思想为凝聚核心的乌玛也面临着分裂。随着教派的分立,加上统治范围的扩大所造成的管理不善,世俗世界也出现分裂的特点。在伊斯兰的土地上,诸多王朝建立起来,并且更迭不断。在政权方面,第四任哈里发阿里被刺杀,阿巴斯王朝建立,“在政治制度方面,统一的政权不复存在,而实际掌权者不是像哈里发那样来自古莱氏部落,而是靠武力夺得和维持权力,政治制度已经完全背离了伊斯兰乌玛观念”,[5]“实现伊斯兰的原始图景、政治和宗教共同体间理想的融合以及重建乌玛的可能性,事实上从伊斯兰教形成和扩张的相当早的时期就放弃了。”[2]316从历史来看,从四大哈里发之后,伊斯兰世界逐渐衰落,乌玛社团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
尽管这样,“乌玛理想被后来不同学者和宗教领袖不断传播,并且与非常强烈的乌托邦取向联系在一起。”,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乌玛社团不断的被假想化、完美化,成为“原初乌托邦”[6]。对于乌托邦,曼海姆认为,乌托邦是超越现实并打破现存秩序的一种理想,“历史的道路总是从一个托邦经过一个乌托邦而导向下一个托邦”[7]。最初的乌玛社团就是在阿拉伯地区部落冲突等内外矛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但是在社团内部,政治清明、人人平等,社团如同“大同”社会,并且随着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带来了伊斯兰版图的扩大、统治的艰难以及教派的分裂,之后又面临外敌的威胁,在这种动荡不安中,希望安定和平,回到先知统治时代,成为了广大穆斯林的美好愿望,乌玛社团紧紧的与乌托邦取向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乌托邦的观念或图景经常包含着强烈的千禧年和信仰复兴运动的要素。”[2]301伊斯兰教强调来世,如古兰经中多次提到了末日审判,在末日审判的那天,曾经生活在现世中的人会逐一接受审判,最终决定是进入乐园还是入火狱。什叶派中的大派十二伊玛目派,认为将第十二任伊玛目马赫迪并未失踪而是隐遁起来,并在末日出现,匡扶正义,除恶扬善,拯救大地,使之回归善的本原,艾森斯塔特称之为“终极的原生状态”。“这种末世状态不仅要恢复穆斯林的先知预言经验,而且要恢复亚当的原初秩序,要恢复亚伯的世系,要恢复一切神圣使命——如娜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耶稣和穆罕默德所肩负的那种神圣使命”。[4]当然也包含着乌玛社团的回归,这种来世观与千禧年有着共同的特点:对来世充满期盼,是在时间上对现实的一种超越。乌玛社团——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的超越图景本身就为后来伊斯兰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范本,为宗教信仰的复兴以及末世观提供了想象的前提。
二、分离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产生
1.伊斯兰教中本身所具有的变革因素
施路赫特在分析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时曾经指出“伊斯兰教不具备革命的经济思维”[8]。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伊斯兰教中,真主是至高无上的,穆斯林对真主只能无条件的信仰,服从安拉,并且“伊斯兰教信奉前定论而拒斥普世救赎论,它在现世中无需承担过于沉重的救赎使命……其宗教伦理与现世秩序之间难以形成持久的张力,伊斯兰世界中的人们往往生活的轻松自由,从而避免了悲观厌世的倾向的产生”[8],从而得出伊斯兰教没有鲜明的变革倾向,神圣与理性的张力在伊斯兰教中可以被消解的结论。
而艾森斯塔特认为,韦伯的观点有误,伊斯兰教中存在着变革的因素。在他看来,恰好相反,在伊斯兰国家,存在着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之间的张力。在伊斯兰文明中,承载着《古兰经》以及沙里亚思想精髓的“乌玛社团”一直以来都是穆斯林所期盼的完美世界,乌玛理想作为伊斯兰文明的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之间的紧张和裂隙不可避免。在伊斯兰教形成初期,这种观念仅存在于一些“小群体”中,这些小的群体主要指思想上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包括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教徒,以及政治、文化领袖),之后范围逐渐扩大,成为社会成员的共识,最后这种本体论的观念被制度化,成为伊斯兰社会“支配性”的前提,影响统治精英或次要精英的理论、实践的导向。于是“特定的世俗秩序是不完善的、劣等的,通常,至少在某些方面,是邪恶的或受到污染的,并且需要加以重构”[2]289,这种观念在各种社会中心尤其在各种社会精英中就产生了。由此使得伊斯兰社会各种集团、运动将“试图根据适当的超越图景、更高的本体论秩序或道德秩序的规则,重建世俗的人类个性和社会——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2]289。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世俗秩序重建的一种倾向应运而生。
2.伊斯兰理想与政治分离
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真主是世间唯一的主宰,统治者是真主在世间的代治者,一切决定必须遵循教法,并对伊斯兰教的理想承担间接责任。这种“代治者”的观念,决定了在伊斯兰理论上可以废黜不义的哈里发,政权存在改革变迁的可能性,这是导致伊斯兰社会频频出现反抗运动的教义、教法因素。
在现实社会中,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在阿巴斯王朝实现了苏丹与哈里发的分离,尤其在逊尼派中,统治者的合法性表现在“社会中所有这类统治者的合法性——确保穆斯林社会的和平生活,维护伊斯兰的法律(伊斯兰教教法)——然而,同时也强调这样的统治者以及政治秩序与原来的理想的基本距离的强制性质”[2]317,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融为一体的哈里发成为了在政治领域有所威望的苏丹,而非宗教领袖。乌里玛或哈里发逐渐承担了监督的任务,成为社会以及宗教的监管者。对沙里亚监督的“乌里玛以及哈里发通过在法律学派、瓦克夫和苏菲派教团中的活动,构成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公共领域”[9]。这种公共领域的活动更易引导广大的穆斯林为了维护超越秩序而形成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回归传统,正本清源。
3.伊斯兰公共社会中的张力
在乌玛理想中,伊斯兰世界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由于现代化的发展,伊斯兰世界理想与政治也发生了分离,政治从宗教中脱离出来,表现为苏丹与乌里玛的分离。苏丹在政治领域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这个框架内,统治者只要确保了穆斯林社会的存在,维护了教法(沙里亚),就能够取得合法性”[4],并且取得相应的政治权力,确保穆斯林能够顺应其统治,保证伊斯兰社会的稳定以及政策的贯彻实施。但是,由于伊斯兰教法的特殊性,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深入人心,乌里玛以其宗教地位而享有司法、教育等特权,在教义、教法的解释方面具有权威,在人们心目中,乌里玛才是伊斯兰社会规范的解释者、调节者,因此,在伊斯兰社会,乌里玛相对独立于苏丹而存在,形成“伊斯兰社会君主与宗教精英二元化的政治体制”[10],乌里玛负有监督统治者行为的职能。“乌里玛创造了庞大的网络,把不同的种族和地缘政治群体、部族、定居的农民、城市群体聚集在同一个宗教保护伞(经常也是社会文明的保护伞)下,使之相互冲击、相互作用。”[4]在这个框架内,穆斯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表自己的观点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在宗教的意义上平等,“西方学者霍奇森指出,正是乌里玛通过其在法律学派、瓦克夫和苏菲教团中的活动,构成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公共领域。”[2]349在公共领域内,穆斯林获得了参与权,在不能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之下可以参与宗教活动以及社会规范的解释。
虽然乌里玛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穆斯林享有自己的权利,尤其是政治领域方面的权利,但是这种政治上完全的平等,强调的是过程的平等,而非结果上的平等,在决策过层中,“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事务,尤其在外交或军事政策方面,以及在税收、维护公共秩序、监督官员等国内事务方面,统治者一般都是独立于公共领域的行动者。[4]”在穆斯林社会,公共领域肩负着维护穆斯林利益以及解释经文的重任,同时在政治领域中,没有很多机会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去。因此,为了维护利益,有些穆斯林会选择“激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
三、复原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诉求
从参政方式的角度,有的学者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为温和派和极端派两个派别,艾森斯塔特还加入了一种形式,即隐遁的形式。他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具有革新倾向和政治倾向,但是“这种革新成分可能倾向积极地参与中心,参与其破坏或转化,或者倾向于有意识地从中退出”。[2]318艾森斯塔特这里提到的隐遁形式,指的是什叶派和苏菲派虽然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参与的形式是隐性的。这种隐性主要表现在教义上。苏菲派强调内在的心灵纯净、寂灭于真主,对仪式、礼仪没有足够的重视,因此,法学家称苏菲派为内学派。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在教义上采取新柏拉图学派的学说,对《古兰经》重新注解,认为“默示不过是‘内心的澄清’”,《古兰经》含着表面的和内容的两种意思,应该揭开物质的帷幕,以达到最纯洁的精神境界。因此有人又称他们为‘内含派’。什叶派伊玛目派属于什叶派中的一大教派,而伊玛目派中最重要的是十二伊玛目派,第一任伊玛目是阿里,其次是阿里的儿子哈桑,再次是侯赛因,直到第十二任伊玛目,即约于伊斯兰历260年隐遁的穆罕默德·马赫迪。该派认为,第十二任伊玛目将在末日来临时再度出现,使大地充满正义。什叶派认为,伊玛目是精神领袖,在本质上和行为上都高于众人,它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法律的执行人,什叶派给予了伊玛目或哈里发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不能对伊玛目政权予以反抗,只有当第十二任伊玛目出现时,才有力量战胜敌人,黑暗才会退去。这种“隐遁”的思想,使得伊玛目没有掌权,也不为世人所知,没有公开进行原教旨主义的运动,成为一种新的表现。而我们知道,“马赫迪”意为正道者,受人期待的伊玛目。马赫迪现世,意味着黑暗结束,光明即将到来,世上的一切非正义将会消失。虽然伊玛目隐遁了,伊斯兰正统社会的原始图景在什叶派的教义中也可反映出。
不论是采用合法手段的温和派,还是暴力恐怖的极端派,甚至是秘密活动的什叶派,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都是希望复原伊斯兰经典时期,依照古兰经、沙里亚法建立政教合一、安定团结的伊斯兰社会。
艾森斯塔特基于现代性的一般理论,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行研究,并将其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展开。乌玛理想与现实秩序的分离,使得伊斯兰世界一直在寻找弥合间隙的模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其中一种,它根植于伊斯兰文明的异端、宗派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带有千禧年以及末世论的因素,崇尚先知乌玛时代的理想生活方式(君主既是有德行的乌里玛,又是英明的统治者,在文化上,奉行《古兰经》、沙里亚法的规定,穆斯林享有平等的政治权以及其他权利),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政治图景在伊斯兰国家得到广泛的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在与西方化以及现实政权的不断对抗中壮大,成为影响伊斯兰国家政权、政策的强大力量。
在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为伊斯兰世界探寻现代化模式提供了一条道路。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理论是基于各种文明的独特性而提出,当今世界的现代化需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在本国实际的基础上建立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现代化模式。在全球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着力于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都面临着不断的变迁,由于工业化首先在西方实现,因此,世界各国现代化模式大多都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追求政治的民主化、科学化,经济的工业化,文化的自由、人性化以及社会的城市化。但是在传统伊斯兰世界,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国家政治上实行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度、文化、经济带有深刻的伊斯兰教烙印,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就使得伊斯兰世界现代化模式应当寻找自己独特的方向。倡导回归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道路。近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在积极寻求现代化的道路。如“瓦哈比教派”,它代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一种重要类型。它主张在教义上严格遵循认主独一以及《古兰经》、圣训的教义,在思想上,去除奢靡的风气,主张回归纯朴,净化心灵,在政治上,穆斯林团结起来,建立学者体制和长官体制密切结合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要求社会伊斯兰化并创造一种适当承认伊斯兰的政治秩序”[2]339。虽然瓦哈比王朝被奥斯曼帝国镇压并最终灭亡,但在穆斯林心中,瓦哈比运动所探索的伊斯兰道路与伊斯兰社会的美好理想是和谐一致的。由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倡导的回归伊斯兰传统、对教义、伊斯兰传统持有保守的信仰,为建立伊斯兰世俗秩序提供了一种选择,“构成了现代性文化和政治话语的一部分”。[2]287-289
[1]S.N.Eisenstadt.The reconstrucuion of religious arenas in the framework of“multiple modernities”millennium[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0:591-611.
[2]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
[3]金宜久.伊斯兰教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1997.
[4]艾森斯塔特.伊斯兰文明的宗派主义[J].二十一世纪,2002.
[5]吴冰冰.乌玛观念与伊斯兰宗教共同体的构建[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3).
[6]Henry Munson.Jr.Islam and the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
[7]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8]冯璐璐.消解张力的融合型价值论理[J].西亚非州,2010(12).
[9]吴广义.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新态势[J].亚洲纵横,2004(3).
[10]黄民兴.中东现代化中的公共领域问题[J].山西师大学报,2009(6).
[11]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