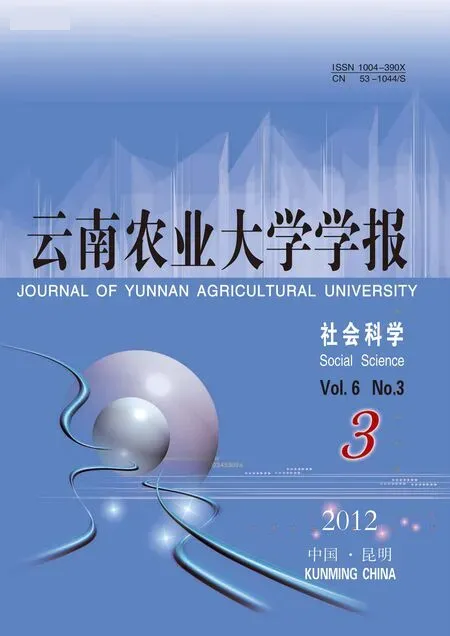老子“道”论对庄子美学思想的影响探析
毕 东
(云南农业大学 图书馆,云南 昆明 650201)
一、“道”是老子美学的中心范畴
从《老子》全书看,“道”具有以下五方面的性质和特点:
其一,“道”是原始混沌。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就是说,“道”是在天地产生之先就存在的原始混沌,它不依靠外力而存在,它包含着形成万物的可能性。老子所谓“朴”、“玄”、“恍惚”等等,都是对于这种原始混沌的形容。“道”不是什么人创造出来。我们找不到“道”的创造者,因为它早在上帝之先就存在了(“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是生来就有的。
其二,“道”“产生万物。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也即世间万物都是由阴阳交合的混沌之气产生的。[1]
其三,“道”没有意志,没有目的。老子说:“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1]这是说,道效仿自然,就是自然的样子。道虽然产生万物,但它并不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主宰。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的产生都是自然而然的,浑然天成的,并不是上帝的有意安排。
其四,“道”自己在运动。“道”并不是静止的、不动的。它作为一种万物运行、变化的规律,处于永恒的“逝”、“远”、“反”的运动之中,处于永恒的“独立”运动即自己运动之中。正是“道”的这种有规律的变化和运动,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宇宙万物及生命。
其五,“道”是“无”与“有”的统一。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从作为“天地之始”来说,“道”是“无”。所谓“无”,就是“无名”、“无极”、“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1]也就是无规定性、无限性。所以“道”是没有具体形象的,是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是不能单凭感觉把握的。这就是老子所谓“寂兮寥兮”、“大象无形”、“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所谓“夷”、“希”、“微”。另一方面,从作为“万物之母”来说,“道”又是“有”。所谓“有”,就是有了规定性、差异性和界限性。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道”(混沌之气)产生的。这就是“有”。所以“无”和“有”并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两种属性。 也即,“道”是无限和有限的统一,是混沌和差别的统一。[2]
叶朗教授认为,有的学者说“道”产生万物,但“道”本身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2]因此,认为老子的“道”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在《老子》全书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道”的精神性的明确规定。“道”产生万物,但产生万物的东西不一定是精神性的东西。“道”看不见、摸不着,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精神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赖以生存的氧气。当然,在《老子》全书中,我们也找不到关于“道”的物质性的明确规定。但是老子说过:“道法自然”。老子还说过:“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也即,“道”在先帝之前就存在了。老子用这个无意志的“道”,否定了有意志的“上帝”和“天命”。据此,可以说,老子的哲学体系在总体上带有唯物论的倾向。[3]
二、老子“道”论对庄子美学的影响
老子把“道”作为世界的本源,把他美的最高理想归于他的中心范畴——“道”,即把“道”作为美的本体。在老子看来,这至高无上的“道’,才是绝对的善和美,他谓之“大美”。老子的“有”、“无”统一,“虚”、“实”结合的思想,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标准。[4]
(一)老子 “道法自然”思想对庄子美学的影响
“自然”一词首先由道家开创者老子提出的。老子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人亦应当顺其本来的自然,不可有意作为,其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篇)道之所法,是自然的;而天之法道,亦法其自然,地当然不能勉之,究其实,人也是法道,即当法自然。对人为的弊害,老子则提出尖锐的批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攻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上篇)此即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下篇),老子认为人要求无败无失,只有顺自然而无所作为,故其云:“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下篇)老子反对人为,故菲薄智巧。其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上篇)老子认为惟有废弃一切智识、德行、技术,然后天下方能清明太平。“抱朴”是老子自然说的中心观念,他主张“复归于朴”。
在老子看来,“自然”即“道”,“道” 即 “自然”。这样,老子的“自然”与“天”、“无为”、“道”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老子思想体系的基础,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系统,体现出老子思想强烈的特点和个性。我们知道,美学是在哲学的基础上诞生的,传统意义上的美学是艺术哲学,是哲学在艺术和审美上的延伸, 老子的美学观念同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 “道”有着直接的关联。老子的“道”, 就是他以自然之美为核心内容的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在我们看来, 老子把自然无为的“道”作为美的根源。他的自然之美的思想,体现了 “道” 所派生的特征, 也体现了“道”的自然延伸。美的本质就是自然之美。老子以“道” 作为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宣告了我国美学系统理论的诞生。[5]
庄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最高的、绝对的美。《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天地的“大美”就是“道”。“道”是天地的本体。圣人“观于天地”,也就是观“道”。这是一种静观(“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庄子认为,对于“道”的观照,乃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田子方》中以孔子和老子对话的形式,说明了这个道理: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谓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所谓“游心于物之初”,就是游心于“道”,也就是对“道”的观照。所谓阴阳“交通成和而物生”,所谓“莫见其形”、“莫见其功”、“莫知乎其所穷”,就是对“道”的描绘。庄子认为,能够实现对于“道”的观照,就能得到“至美至乐”。
在《田子方》中接下去还有一段对话,说明游心于“道”的方法:孔子曰:“愿闻其方。” 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
这段话说明,为了实现对“道”的观照,观照者胸中必须排除一切生死得失祸福的考虑。简单说,就是要“无己”。但是普通人都“有己”。“有己”,就有生死、寿夭、贫富、贵贱、得失、毁誉种种计较,所以就不能游心于“道”。只有“至人劳、“神人”,“圣人”才能游心于“道”,因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的自然论,比老子更明晰,但主要思想仍不出老子所言的范畴。在老子那里,尚没有以天与人的两个观念相对立。分别天人,始自庄子,庄子认为一切人为都是自扰,结果必自受其害,天的力量极为伟大,实不可抗,人只有顺随自然,更不要想改变天然。庄子云:“物不胜天久矣。”(《大宗师》物是不能胜天。便只好任天的。故而庄子主张:“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即不可用心以背道,不可有为以变天。只应顺其自然,更不要有所损益。(外篇),崇尚自然之论更为详尽。其云:“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在宥》)人道有累,天道则无累。人应当“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助天尚不可,灭天当然更不可了,何为天?何为人?天与人的分界在哪里?其云:“无为为之之谓天。”(《天地》)“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凡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是天,反之,则是人。人为,以毁伤自然则有余,以改善自然则不足。一切作为,皆会带来很大的弊害,所得实不偿所失。如任自然,则:“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斯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骈拇》)未受人为损毁的自然,本来圆满无缺,任天之极,以至忘天人之辨,方是纯任自然。任天而忘天,便是完全“天而不人”(《列御寇》)了。庄子认为人要做到真正无为,一任自然,便必须达到一种“忘我”、“丧我”、“心斋”的境界。[2]
(二)老子“涤除玄鉴”的命题对庄子建立审美心胸的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老子认识论中关于“涤除玄鉴”的理论,在美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老子说:涤除玄鉴,能无疵乎?(《老子》第十章)。“涤除”,就是洗除垢尘,也就是洗去人们的各种主观欲念、成见和迷信,使头脑变得像镜子一样纯净清明。“鉴”是观照,“玄”是“道”,“玄鉴”就是对于道的观照。“涤除玄鉴”的命题包含有两层含义。这两层含义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涤除玄鉴”的第一层含义,即是把观照“道”作为认识的最高目的。《老子》第一章所谓“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就是讲对“道”的观照。老子认为,一切观照都要进到对于万物的本体和根源的观照,即进到对于“道”的观照。这就是认识的最高目的。这就叫“玄鉴”。“涤除玄鉴”这个命题的主要含义即在于此。
那么, 这种对于“道”的观照是怎么实现的?人们怎么才能从对于具体事物的观照进到对于“道”的观照?对具体事物的观照和对“道”的观照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老子并没有讲清楚。有的作者认为,老子的“玄鉴”讲的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观,实际上是一种内心观照。有的作者认为,老子的“玄鉴”讲的是理智与经验统一的直观。还有的作者认为,老子的“玄鉴”讲的是一种否定感觉经验的唯理论的认识论。本人同意叶朗教授的观点,这几种说法的根据都不充足。因为就“涤除玄鉴”这个命题本身来说,它既没有直接包含重视感觉经验的意思,也没有直接包含排除感觉经验的意思。所谓“玄鉴”,也只是说要求得对“道”的观照,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轻视感觉经验,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神秘主义。前面说过,老子的“道”具有“无”和“有”双重属性,是无限和有限的统一。就“道”的这种性质来说,也并不绝对排除人们通过感觉经验把握它的可能性。至于老子说的“绝圣弃智”、“为道日损”、“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等等话,在历史上从来就有不同的解释,也并不足以论证老子就是一个否定感觉经验和知识的神秘主义者。总之,我认为,老子“涤除玄鉴”的命题,只是说人们应该求得对于“道”的观照。至于通过怎样的认识途径实现这种观照,老子并没有明确的回答。在这一点上,老子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补充和发挥的余地。
“涤除玄鉴”的第二层含义,是要求人们排除主观欲念和主观成见,保持内心的虚静。上面说,老子并没有回答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对“道”的观照的问题。但是老子强调了一点:为了实现对“道”的观照,观照者内心必须保持虚静。老子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于“涤除玄鉴”的这一层含义的发挥: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复”,即回到老根。“观复”,就是观照万物的根源、本原。这段话意思是说,人心只有保持虚静的状态,才能观照宇宙万物的变化及其本原。
老子“涤除玄鉴”的命题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的发端。庄子上述关于“心斋”、“坐忘”的论述,突出强调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的主体必须超脱利害观念,则可以看作是审美心胸的真正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审美主体的发现)。庄子的这一发现,在中国美学史上有重大意义。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可以说就是由庄子建立起来的。后来宗炳关于“澄怀观道”的论述,郭熙关于“林泉之心”的论述,都是这一发端于老子而由庄子建立的理论和继续和发挥。[7]
需要指出的是,审美的心胸(超脱利害观念的空明心境)是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的一个精神条件,是一个前提。在这个限度内,庄子关于“心斋”、“坐忘”的理论是合理的。但是,审美的心胸本身并不等于审美创造,有了空明的心境并不等于获得了创造的自由。庄子把这两者等同起来,这就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错误使他陷入了宿命论。[2]
庄子(庄子学派)是否对创造的自由一点认识也没有呢?似乎也不是。庄子在《养生主》、《达生》等篇中,通过一系列生动的寓言故事,对于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作了很好的描绘。这些描如古铜古玉(龚自珍《书金铃》)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宗白华也认为:“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8]庄子的启示扩大了人们的审美的视野,使人们注意从生活中去发现那些外貌丑陋而具有内在精神力量的人,从而使得中国古典艺术的画廊中,增添了整整一个系列的奇特的审美形象。
三、老庄美学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影响
老子提出的一系列范畴,如“道”、“气”、“象”、“有”、“无”、“虚”、“实”、“虚静”、“自然”等等,对于中国古典美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点,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客体、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和艺术生命的一系列特殊看法,中国古典美学关于“澄怀味象”(“澄杯观道”)、 “气韵生动” 、“境生于象外”、 “平淡”和“朴拙”等理论,以及 “虚实结合”的原则,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等等,它们的思想发源地,就是老子哲学和老子美学。
庄子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最高的、绝对的美,而现象界的“美”和“丑”则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因为“美”和“丑”的本质都是“气”。在绝对意义上来说,“美”和“丑”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庄子的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逻辑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美”与“丑”并不是最高的范畴,而是属于较低层次的范畴。对于一个自然物或一件艺术品,人们最看重的并不是它外在的“美”或“丑”,而是它是否充分表现了宇宙一气运化的生命力,也即是否能够实现对“道”的关照。
庄子美学的核心内容,是由对“道”的关照而引发的对“自由”的概念的讨论,以及对于“自由”和审美的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在美学史上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庄子关于主体必须超脱利害得失的考虑,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获得“至美至乐”的论述,在美学史上建立了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另一方面,庄子在“庖丁解牛”等寓言故事中关于创造的自由就是审美境界的论述,在美学史上一次接触到了美和美感的实质。这两个方面,在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另外, 庄子通过“象罔得到玄珠”的寓言,用老子“有”“无”“虚”“实”的思想对《系辞传》“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作了修正,强调只有有形和无形相结合的形象(“象罔”)才能表现宇宙的真理(“道”)。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的意境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总而言之,老庄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不研究老庄美学,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美学的历史渊源与流变。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欧阳年.从老子的“道”看美的本质[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1):43-45.
[4]张少华.老子美学思想探微[J].美与时代,2009(11):32-33.
[5]靳青万,赵国乾.论老子“道法自然”说的美学内涵及意义[J].郑州大学学报,1997,30(5):32-38.
[6]赵国惠.老子哲学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J].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8,80(1):41-43.
[7]王国维.人间词话[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8]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8.
[9]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0]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