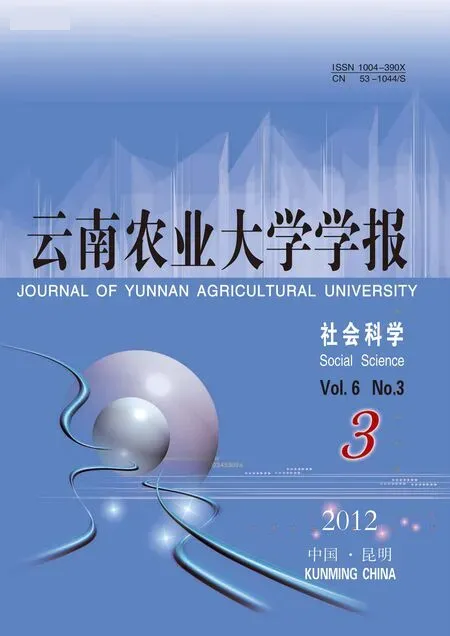论审美惊奇的生成动因
李潇云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审美惊奇的客观基础在于事物或艺术作品本身之“奇”,这种“奇”可以表现在形式、内容或意境上,给审美主体带来的是平素不常感受到的强烈美感,多以“惊奇感”的面目出现,属于审美心理的范畴。对于审美主体而言,他所能感受到的惊奇美必定非司空见惯之物,而是存在于日常审美视野之外,或者说司空见惯之物虽拥有能引起惊奇感的特质,却被庸常的审美疲惫所遮蔽,导致客体无法向审美主体无限敞开。一般而言,能引起审美惊奇的客体,在主体心里必然处于“缺失”状态,所以一旦它有机会进入审美主体的视野,就会带来超越审美疲劳的美感狂欢。即是说,这种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一旦得到补偿,将使主体产生豁然贯通胸臆、震撼心灵的强烈美感。
生成动因与审美惊奇产生的心理动势紧密相关,心理动势在此强调一种心理欲求的倾向性,是一种虚以待物的心理状态。从艺术欣赏层面而言,它是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具有的心理状态,这也是审美惊奇重要的生成动因。此状态以某种审美惊奇体验的缺失为前提,在审美主体的经验世界,一旦缺失之客体进入审美主体的视野,即引发审美主体强烈的审美感受,体验到惊奇和快意。这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创作层面虚空心境的培养,二是接受层面虚空的心理状态,前者为审美惊奇的发生创造了可能性,后者则是由于客体在审美主体心里的缺失所引发的审美惊奇得以发生的强大内驱力。袁枚曾对艺术之“空”的妙用有精彩描述:“严冬友曰:凡诗文妙处,全在于空,譬如一室内人之所游焉息焉者,皆空处也。若窒而塞之,虽金玉满堂而无安放此心处,又安见富贵之乐耶?钟不空则哑矣,耳不空则聋矣。”[1]实而不空,不能成为艺术;空而有实,又能恰到好处,则为艺术的上层。对于审美惊奇而言,客体在审美主体内心的虚空,即意味着其在审美主体经验世界的缺失,这是将主、客联系起来的线索链。实际上,无论创作或欣赏,皆需要虚空、空灵,而不可皆实。那看似渺渺的虚空之中,正蕴育着艺术的佳境。苏轼对此体会甚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廖师》)这其实是对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进一步发挥,他告诉我们静中有动、空纳万境的艺术辩证法,极言艺术“空白”的妙用。就像绘画中的“虚白”,那虚空处,正是满目的山岚烟云,无尽的高山流水,满纸皆气,酣畅淋漓;满眼皆情,涤荡心胸。实际上,无论创作或欣赏,皆需要虚空、空灵,而不可皆实。循此,以下从“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和“审美惊奇补偿”两个方面来谈。
一、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
缺失的审美体验,意味着客体在主体审美经验世界的缺失。就审美活动而言,则意味着此客体外在于审美主体的审美活动,或者说,主体没有遭遇过此类客体。而对于审美惊奇而言,则又意味着,审美主体没有经历过此类的惊奇体验,换言之,此类体验在审美主体经验中处于缺失或不在场状态。
我们不妨把下述言说方式植入到审美惊奇体验中。《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立刻就有了光。连续六天里,上帝依次创造了天空,大地,日月星辰,鸟类、鱼类,走兽和爬行动物以及统辖万物的人。从“要有……,要有……,……”这一言说方式可以看出,“要有……”就意味着“没有或者需要……”,也就是说,此需要之物在经验世界处于缺失(或不在场)状态,它需要被纳入经验世界并被经验世界所吸纳。就在缺失之物纳入经验世界的一刹那,犹如电光石火、奔雷惊电,照亮并强烈震撼了在场者。
可以说,使接受者产生审美惊奇之物,在接受者的经验世界里处于缺失(不在场)状态,而接受者根据经验世界的审美实践或直觉,判断出自己需要、渴求此缺失之物。因此,接受者通过各种方法试图找到它,一旦缺失之物突然闯入接受者的视野,就在这一刹那,接受者将会因惊奇而错愕、目瞪口呆,甚至手舞足蹈、欣喜若狂,体验到惊心动魄、心驰神颤的审美惊奇感受。这对接受者来说是难得经验到的,但这种惊奇体验,对个体生命来说又是必要甚至是必须的。因为这体现了人这一精神生命,不同于它物的独特之处,人也须得通过审美惊奇这一强烈感受超越日常经验世界的钝化,宣泄内心各种芜杂的烦闷情绪,获得精神的超越、审美的提升、心灵的慰藉与安顿。实际上,就像审美主体遇见惊人之美一样,常态的美在最初进入审美主体视野的刹那,一般也是由审美惊奇开始的,只是它由此长驻人们的审美经验世界,逐渐变得常态化,人们便不再像初见时惊奇。即是说,在人们的审美经验世界,它不再处于缺失状态,也就失去了补偿的内驱力,审美惊奇也就不再发生,但在某种情况下,它仍然存在再一次跃出常态美,飞升为惊奇之美的可能,然这取决于主体的审美经验,也和主体的审美心理紧密相关。 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就产生之前的心理状态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其一,完全的缺失或“无”。即某一客体从未进入过审美主体的视野。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客体总是有限的,他仅可以经验到自己审美实践范围内的美感,审美惊奇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审美惊奇是一种极致美感,它占据着美感体验的制高点。由于审美惊奇感的发生必须满足诸多条件,譬如,对审美主体而言,客体的新颖、奇特,主体的心理状态、心境,艺术修养、情感经历等,还包括某种艺术作品的形式、内容、质料等特征恰好符合主体的审美理想,多重因素的风云际会,恰好能引起审美主体的惊奇之感。这要求多种因素的适当配合,故此,在审美活动中,体验到某种客体所触引的审美惊奇感的概率并不高。
一般而言,在主体经验世界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动势,促使主体向审美惊奇靠近。这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力,也意味着审美惊奇感得以产生的无限可能。就像苏轼的“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所表达的剧烈的审美焦虑。众所周知,庐山烟雨、浙江潮水乃天下奇观,从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及众多历代诗人、词人的《望海潮》名作中,约略可以窥见二者的风姿及奇伟景象。那么,苏轼对此景象的渴盼与想往,就不难想像了,它彰显着一种巨大的审美向心力,蕴含着此种焦虑可以假道前往观赏消解的可能性。完全的缺失,意味着此种审美惊奇体验的缺失或未曾经验,也预示着其惊奇的审美体验呼之欲出的态势。
其二,曾获得但又丧失(或“有”)。即某一客体曾经进入过审美主体的视野但后来再未经验过。即是说,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曾经验过某种客体带来的惊奇之感,并且此客体也曾深深地打动、震撼主体的心灵,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此后,审美主体再未体验过此种惊奇感。这种经历沉淀为回忆,而人们对审美惊奇体验的回忆,必然直接关涉到已有的审美惊奇经验。然而,此经验只属于人生的偶遇,绝非常态,但人们却往往会因此产生审美惊奇体验的焦虑,消解的方式常常是假诸回忆。这种强烈的美感经历一直牵引着人们的美感神经,成为栖居繁冗时光里的美好希冀。康德认为:一切情感,尤其是应当引起如此异常的努力的情感,都必须在他们正处于自己的高潮而还未退潮的那一刻发生它们的作用,否则,它们就什么作用也没有:因为人心会自然而然地回复到自己的自然适度的生命活动并随后沉入到它自己原先的那种疲乏状态中去;因为被带给它的虽然是某种刺激它的东西,但却绝不是什么加强它的东西。[2]
正像康德所假定的那样,审美惊奇的强烈情感,曾在它发生时,带给人们惊心动魄的震撼,我们必须承认“人心会自然而然地回复到自己的自然适度的生命活动并随后沉入到它自己原先的那种疲乏状态中去” 这一现实,可问题在于,我们试图从“它自己原先的那种疲乏状态中”,把它打捞上来,重新照亮我们乏味的生命。人们不断地追新逐奇,并享受由之带来的狂喜,即便明白审美惊奇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短暂插曲,即便转瞬即逝,也要试图努力去尽可能延长这种刺激,仿佛要把它们一个个串起来挂在胸前,镶嵌进他们贫弱的想象力一般。
这种心理状态最让人不堪,因为它所带来的痛苦和怅惘甚至比惊奇与狂喜本身更多,也更让人觉得心理折磨,它让人忘不了欣喜,忘不了迷狂,忘不了震撼灵魂的审美感受。当惊奇感消逝之后,人们常常陷入对此美好刹那的回忆,让他们久久不能忘情这种惊心动魄的审美体验,尤其在抚今追昔之时,更让他们感到无法排遣的痛苦。然而,人类的快乐与痛苦之间,往往有一种奇妙的平衡。就此意义上讲,缺失状态恰恰又是积极的东西,因为它使人们感觉到它的存在,这包孕着此审美惊奇感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心理状态,在回忆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表达较多,它常常也伴随着一种沉甸甸的失意与惆怅。
其三,上述两种情况的中间状态(或“无”和“有”的中间状态)。即此客体已经出现在审美主体的经验世界,但尚未足够使之惊奇,须待进一步发现。审美活动中,惊奇感的发生需要契机,需要审美发现。日常经验之物,往往由于其司空见惯很难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便它本身具备了诸多符合我们审美理想的质素。客体,在等待着人们的慧眼,使之从被遮蔽、被掩盖的昏昧中敞亮出来。就如一个年深日久的古董,一旦擦去蒙在其上的尘垢,它便敞现出使我们惊讶的美来。在西方文学艺术理论中,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 理论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与此相近,前者主张使“石头更像石头”,破除日常经验的遮蔽,改变对生活的司空见惯、无动于衷的惰性和被动性,恢复对日常生活和艺术的新鲜感受;后者旨在使“石头不像石头”,使人产生惊讶与好奇。什克洛夫斯基说:“艺术的手法是事物‘陌生化’的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之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3]布莱希特则简单明了:“什么是陌生化(间离效果),对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进行陌生化,首先很简单,把事件和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悉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4]其实就是对象众所周知,但要把它表现得陌生而已。就像“漂亮”一词,本是通过“漂”这种程序,使事物本身的美感特质“亮”出来,虽然没有增加什么新质,但它无疑是一种审美“发现”。正是这种发现,使得客体美的本质冲破被遮蔽、被埋没、被掩盖的暗黑,刹那焕发出夺目光彩。
由是观之,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表征了某种可能引发审美惊奇之物,在审美主体经验世界的缺失状态,即是说此客体外在于主体的惊奇之感。但也正由于其审美体验的缺失,才激起主体极大的探究冲动,才促使主体积极寻找与审美惊奇相遇的契机。大而言之,审美距离可以说是使心“虚空”出来,为某种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蓄势。在某种程度上,审美距离也是使审美惊奇补偿得以发生的前在性因素,当然,这必须是适度的审美距离。而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有待在审美活动中加以补偿,它预示着一个非同凡响的审美惊奇体验的到来。
二、审美惊奇补偿
个体生命挣扎于尘世繁杂琐事中,承接并抗拒着来自苦难、无常、时间、空间以及死亡等各种异己力量的压力。作为精神生命,他必须在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中,找到生命的诗性补偿,获得精神的超越与提升,审美的悦适与狂欢。而个体生命的审美惊奇补偿,即是对上节所云缺失的惊奇美感体验而言,主要指某种客体所引起的审美惊奇感而言,此客体可以是文学艺术、自然风物、一种氛围、一种境界等。这是个体生命可遇不可求的审美契机,也是以惊心动魄和恣肆狂喜为心理特征的审美体验的最高形态。它是心灵世界缺失已久的体验所产生焦虑的瞬间释放,使之在惊奇的刹那,假道语言而得以补偿:诗人的职责就是使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件发出光辉,赋予它们以一个较高的价值、一个较深的涵义。……假如幻想受到不必要的或不适当的制约,它将以语言和描写的较大自由来取得补偿。[5]
语言使受到制约而难以驰骋的想象力取得补偿,就审美惊奇的接受而言,文学艺术的作用即是使缺失的惊奇美感体验,通过审美活动得到补偿。这里隐含着一个问题: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一定会得以补偿吗?答案是否定的。缺失的惊奇美感体验,是审美惊奇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准确地说,只有在主体审美经验中缺失的惊奇美感,又恰好能与审美主体相遇时,审美惊奇才会发生,倘若此缺失一直外在于主体,那么,审美惊奇就不会发生。简而言之,审美主体经验世界缺失的惊奇美感体验,有些会取得补偿,有些则不会;有些能引起主体的审美惊奇感,有些不能。这将取决于审美主体与此独特客体是否能够相遇(或称之为“打照面”),设若二者不能相遇,虽然审美主体内心对某种客体有强烈的审美焦虑,并且此客体也在召唤主体的发现,假如没有契机,一切终将枉然,此客体所可能导致的审美惊奇感也就不会发生。
譬如主体在某种审美焦虑的驱使下,去找寻这种对他而言极其独特的客体,结果是发现并经验到此客体带给他的、缺失已久的惊奇美感体验,得到审美惊奇补偿,获得惊奇的美感。反过来讲,倘若主体有此缺失的惊奇美感体验,也葆有找寻的冲动,但却迟迟未付诸行动或根本没打算行动,或者,即便付诸行动,也没有找到想见的独特客体,那么此种状况,这种缺失就不能得以补偿。就是说,只有他恰恰缺失此惊奇美感体验,接着他又到了此独特客体所在之处,恰恰见到了想见之客体,又体验到心驰神荡的惊奇美感,从而产生了审美的快意与惊奇,如此,缺失的惊奇美感体验才算得以最完满的补偿。这样阐释总有些抽象,不妨举例试以分析。“灯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缭乱。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却拂僧床褰素幔,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吹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王安石《渔家傲》)我们暂且不考虑此缺失的审美体验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着眼点在于:时值正月已半,山南山北花影处处,词人听闻初春洊亭春水上涨,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动,想要前去体验一番。对词人而言,“洊亭春水上涨的状态”即为缺失的审美体验,或者说这种审美体验不经常出现在主体审美经验的世界里。不难想象,伫立春光之中,满山花开绚烂,溪泉叮咚鸣响,松风阵阵,经历了漫长冬寒相煎的心灵,该是何等惊奇快意。至此,缺失已久的审美体验,在个体生命的探求活动中,得到审美的补偿,获得惊奇的体验与美感。又如“客中多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般横系大江心。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陆游《度浮桥至南台》)在“客中多病废登临”的苦闷人生中,诗人看到了飞卷的怒涛,奔腾的长江,听着古寺的钟磬之声,颤悠悠地荡漾在云烟之间。遭逢如此奇景,诗人鬓发斑白然豪气依旧,以至于“醉吹横笛坐榕阴”。诗人陶醉于眼前的奇景,缺失已久的审美体验(“客中多病废登临”)终得以实现。
一般而言,审美的焦虑常常要经历一个压抑或缺失的过程,“如所谓惊澜奔湍,郁闷而不得流;长鲸苍虬,偃蹇而不得伸;浑金朴玉,泥沙
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云阴蔽蒙而不得出”[6]。缺失得越持久、越剧烈,所淤积的力量也就越大,一旦得以宣泄或补偿,其势也越猛烈。这里还包含一个重要条件,即上文所论及的“契机”,可以看出,此即为引发积蓄已久的强烈审美焦虑得以瞬间迸发的绝妙契机,也是缺失之情感得以宣泄与补偿的催化剂,更是审美惊奇得以发生的巨大动力。
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个体生命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未必能在现实中得以补偿,特别能引发惊奇体验的经历更是少之又少。然而,厌倦了凡俗客体的人们需要通过审美惊奇的剧烈体验,获得生命的快感与激荡。这就需要寻找别的方式来解决此困境,缘此,文学艺术的想象活动无疑成为人们的首选。比如唐朝诗人薛涛的《赋凌云寺二首》:“闻说凌云寺里苔,风高日近绝纤埃。横云点染芙蓉壁,似待诗人宝月来。闻说凌云寺里花,飞空绕磴逐江斜。有时锁得嫦娥镜,镂出瑶台五色霞。”(薛涛《赋凌云寺二首》)凭借审美想象,人们得以遨游太空、御风仙冥、凌云山川,穿越时空的阻隔与惊奇之美相遇。人生,也正是有了审美想象活动,才变得飞动、多彩和快意。毫无疑问,无论何种补偿方式,皆可能使现实人生超越凡俗与郁闷,获得审美的惊奇与升华。
[参考文献]
[1]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73.
[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13.
[3]方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北京:三联书店1989:6.
[4]布莱希特论戏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22.
[5] 刘小枫.诗化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6.
[6]初学集·虞山诗约序[J]//[韩]朴璟兰.钱谦益的文学本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2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