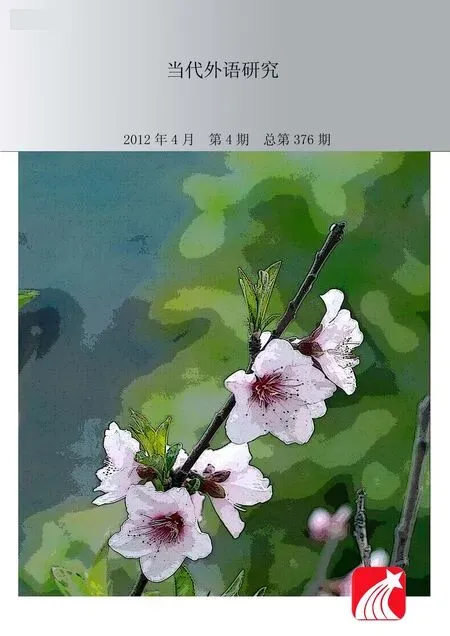刺激贫乏论诠释
王 强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400065)
1. 引言
20世纪上半叶,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观点认为,儿童语言习得是反复学习的结果,语言是习惯系统,新表达式的产生和理解是类比的直接结果。然而客观事实却恰好相反:儿童在短短两三年中,在接触极为有限的语言经验或刺激后,即可逐步习得一门语言。刺激贫乏论(Argument from Poverty of the Stimulus,简称“APS”)是儿童语言习得和语言学理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生成语法学家用来研究UG(Universal Grammar,普遍语法)原则的工具,也是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经典观点的变体之一,现已成为认知科学的一个主流课题。Chomsky(2010)在第八届生成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GLOW-in-Asia VIII)上的主题演讲,更是激发了学界对APS及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和探索。本文尝试诠释刺激贫乏论,首先阐明它的内涵,继而分析各种相关证据,重点分析结构依赖性,然后评论反对刺激贫乏论的各种观点,最后总结全文。
2. APS的内涵
2.1 APS的缘起
APS可以追溯至生成语法理论研究的开端。Chomsky(1955/1975:61)认为,一种语言的说话者观察到该语言的有限话语,基于这些有限的语言经验,就可以产生无限多的新话语,且这些新话语能够立即为该语言社团的其他成员所接受。他(1957:15)指出,说话者基于有限的和偶然的语言经验,就能够产生和理解无限多的新句子。这其实是说明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受到的语言刺激是贫乏的,最终获得的语言知识却是极为丰富的。这初步勾勒了语言输入与语言知识或能力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是APS的前身,也是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
明确提出APS的是Chomsky(1980a:34)。他认为人类心智和身体发展的范围和限制都由内在的生物基因决定。作为心智的组成部分,语言知识的发展也由作为内在生物基因组成部分的普遍语法决定。但是为什么儿童能够在贫乏、混乱的环境中获得具体的、复杂的语言结构知识呢?原因就在于APS。可以看出,Chomsky的这一表述进一步廓清了APS的内涵与外延,尤其是把它与内在的生物基因联系起来,从而把语言知识放到生物语言学大框架中去研究。
2.2 APS的精髓
纵观APS的发展历程,特别是Chomsky(2010)的成果,可以把APS的精髓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刺激贫乏是普遍存在的(ubiquitous),是所有生物具有的基本属性之一,比如小鸡一孵出来就会啄食,蜜蜂不用教就会跳舞等等。刺激贫乏适用于人体生长和发育的所有方面,比如人类胚胎中发育出手臂和腿,而不是翅膀;我们拥有哺乳动物特有的视觉系统,而不是昆虫的复眼。这些都不是受精卵的营养环境和后天的营养供给所能决定和解释的。基于语言官能的语言习得也是一个自然生长发育无意识的过程,儿童无需做出努力,无需他人指引,与人的其他认知能力无关。刺激贫乏适用于语言的各个方面。语言中的APS只是人类在生物界具有唯一性的众多诠释中的一个。本文所指的APS是狭义上的APS,对应于生成语法中所指的语言知识的来源问题,即为什么人类儿童在较少直接语言经验的情况下,能够自然、快速、一致地学会语言?①
与刺激贫乏的普遍性紧密联系的是它的另一方面,即刺激贫乏是不言而喻的道理(truism)。人体和语言的自然生长发育,都是生物基本属性的表现,是由基础基因决定的,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不言而喻。如果一定要讲道理的话,那也是人类数百万年进化的结果。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突变也好,渐变也罢,语言的现状就是如此,而刺激贫乏渗透在语言的各个方面,尤其体现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Chomsky(1972:102-113)认为,习得和使用语言是人类物种独有的能力,必然有深层次、限制性的原则来决定人类语言的本质,这些原则植根于人类心灵之中。儿童能够快速地习得某种语言,同一种语言的不同习得者发展出的语法又几乎完全一致,而他们的智力和习得语言的条件可能相差很大,这说明儿童构建语法的任务具有基因导向(genetic guidance)的特征。简言之,语言习得是基因导向,而不是由父母导向。前者不言而喻,其结果是刺激贫乏;后者并不自明,其结果是刺激丰富。
3. 支持APS的证据
刺激贫乏是一个现象,APS是基于此现象提出的一个关于知识获得的问题。Legate和Yang(2002)把APS的逻辑界定为:如果一个人知道X,且X不是通过经验学会的,那么X知识必然是天赋的。问题是儿童的哪些知识是天赋的?儿童语言习得,尤其是句法习得过程中发生的客观事实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提供了线索:不是从语言输入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基于语言的基本图谱等内在性原则而获得的即为天赋的。下面尝试从句法、音系和形态等三个方面讨论支持APS的证据。
3.1 句法证据
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语法规则的结构依赖性(structure dependence)。结构依赖性是语言最基本的属性之一,也是APS研究中最熟悉和最有力的说明。它是指在没有外部指导或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所有儿童都能够正确地使用计算复杂的结构依赖规则,而不使用计算简单的和在语言机能以外看来更容易使用的线性规则。
关于结构依赖性的论述最早见于Chomsky(1965:55-56)。他认为语法转换必然是“依赖于结构的”,表现为这些转换只把次语符列分配给语类。因此,可以用公式来表示一个转换,该转换可以把助动词的全部或部分成分插入到它前面的一个名词词组的左边,而不管属于这些语类的语符列多长,多复杂。在讨论语言学对心智研究的贡献时,Chomsky(1968:54)再次论述了结构依赖原则,如下所示:
(1) a. The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who enjoyed the play will stand.
b. Mary has lived in Princeton.
c. The subjects who will act as controls will be paid.
分别对(1a-1c)最后一个单词实施前移,按单词音位的长短从低到高排列单词,把第一个will移到句首,可以得出(2a-2c),如下所示:
(2) a. stand the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who enjoyed the play will
b. in has lived Mary Princeton
c. will the subjects who act as controls will be paid
这些针对一串单词实施的操作,丝毫不考虑作为短语系统的抽象结构,不依赖句子结构或成分结构(constituent structure),而是简单地基于单词出现的顺序,故称为结构独立性。事实表明结构独立操作无法造出合法的句子。与结构独立性相对的是结构依赖性。它是指先识别主语名词短语,再把主句中的助动词提前至句首,该操作明显依赖于句子结构或成分结构,故称为结构依赖性。只有考虑单词组成短语之后的结构,再对最小语言单位(可能是单词,也可能不是单词)实施操作,得出的句子才是合法的,如下所示:
(3) a. Will the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who enjoyed the play stand?
b. Has Mary lived in Princeton?
c. Will the subjects who act as controls be paid?
以(1c)为例,当它转换成(3c)时遵循结构依赖性,因而是(1c)合法的疑问句形式。而(2c)把内嵌从句who will act as controls中的助动词will提到主句句首,违反结构依赖性,因而不合法。这体现的就是一种语句的结构层级性,即虽然从句who will act as controls中的助动词will离主句句首更近,而原主句will be paid中的will离主句句首更远,但语言机制在生成疑问句时,保留了完整的内嵌从句,而把离得更远的will be paid中的will提到句首,这样做的原因是原来的主句是the subjects will be paid,它们是在同一个较高的结构层次上,而原来的内嵌从句who will act as controls是在另一个较低的结构层次上。结构依赖性注意到小句之间的界限,而结构独立性无视此界限。
虽然输入过程中没有任何语言特征排斥结构独立性,但是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并不坚持仅由线序施加的限制,而始终坚持结构依赖假设,只构建结构依赖的语法,即使有些基本语言素材与结构依赖假设和结构独立假设都吻合(参阅Chomsky 1971;1975:30-35)。这种观点也得到了Crain和Nakayama(1987)的支持。他们发现儿童有时造出(4a),有时造出(4b),但从未造出(4c),如下所示:
(4) a. Is the boy that is watching Mickey Mouse happy?
?b. Is the boy who’s watching Mickey Mouse is happy?
*c. Is the boy who watching Mickey Mouse is happy?
在成人看来,(4b)的可接受性程度不及(4a),但两句都遵循结构依赖原则,而且(4b)还遵循UG中的复制原则,只是在复制后没有删除第二个is罢了。(4c)违反结构依赖原则,而符合结构独立原则,但儿童从不这样造句。
另外,儿童倾向于结构依赖原则,不仅体现在造句上,也体现在句义理解上,如(5)所示:
(5) Can eagles that fly swim?
显然,fly离can要近一些,而swim离can要远一些,但我们不是问Can they fly,而是问Can they swim(参阅Chomsky 2010),儿童也都知道我们发问的意图。儿童经验中没有证据说明这个现象,但他们几乎从未出现任何误解。因此,这种现象绝对不是基于某种一般的计算复杂性(computational complexity)②。相反,把can与更近的动词fly联系,比与稍远的动词swim联系,在计算上要简单得多。事实上,儿童对句子的理解不是按照表面的线性,而是讲究成分结构和结构层级性的③,这一点是任何传统语法或教学语法都没有包含的,也是无法教给儿童的。客观事实表明,儿童听到的是成人的一串声音,而不是短语结构树,儿童也没有学过结构依赖性或成分结构,我们成人更无法给二、三岁的儿童解释什么是主句和嵌套从句,或什么是短语结构,那么结论就只能是儿童自己构建短语结构。
我们认为,结构依赖性是规则的性质,而层级性是语法系统的性质,两者不同,相互独立。结构依赖性(即最短结构距离)当然预设着结构,而在基于合并的系统中,结构就是层级的一种形式。结构依赖是一条独立的原则,而且很可能是更为普遍的计算高效性原则的一个子原则。语言官能的初始状态,即UG,包括结构依赖性这种内在的性质。因此,UG不是学会的,而是由外部刺激触发的,这和其他基因因素是一样的。而且,从这个一般意义上讲,语言与人类的其他生物性并无区别。仅依靠刺激,儿童学不会结构依赖性,学不会UG,因为UG无需学习,也不可学。另一方面,刺激又受限于UG,不能违反UG。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UG的作用是中心性的或决定性的,刺激是边缘性的或触发性的;UG是先天的前提,刺激是后天的条件。
从语言设计角度,可以把内在化语言视为概念意向(思维)系统,与作为感觉运动(交际)系统的外在化语言相对。总体上,概念意向(思维)系统和语义诠释系统都不基于词序,因为在那里根本无词序或时序可言,而只基于层级和结构。结构依赖基于结构关系,即成分之间的支配(dominance among constituents),而不基于时序,即单词之间的居前(precedence among words)。严格说来,在句法和语义中都不存在线序。倘若这些是合理的话,一切语法规则就很自然了。相比之下,虽然口头言语是线性的,但这种线序是另一个系统,即外在的感觉运动系统的属性或体现。概而言之,线序属性只与外在化有关,是语言差异所在,也是不完美交际语的体现;结构层级性与内在化有关,是语言原则所在,也是完美思维语的体现。
3.2 音系和形态证据

英语动词过去式的习得是语言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Yang(2002)对儿童习得不规则动词和从文本中提取词汇的研究,也为APS提供了有力的音系和形态证据。研究表明,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能够把不规则动词按照音系规则或过程分成几类,如lose-lost、shoot-shot属于元音缩短,而bring-brought、think-thought属于-t后缀化-韵基等,并按照特定的音系规则进行定义。而不规则动词的习得过程涉及给定的特殊规则与缺省的-ed规则之间的博弈,-ed规则可能是UG的一部分。Yang还提出规则-竞争模型(Rules and Competition Model),强调儿童不是单个地记忆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式形式,而是记忆构成不规则过去式的音系规则,主要包括后缀化(suffixation)和重新调整(readjustment),并把不规则动词和规则动词都放到生成音系这个认知系统中,认为不规则的过去式也是由音系规则生成的。这更好地解释了儿童音系习得过程中出现的过度规约(overregularization)等错误,同时证伪了Pinker(1999)认为的不规则动词是把词根与其相应的不规则过去式形式单个地、直接地记忆,以及通过类比或音系相似性而构成过去式的观点。
3.3 小结
在接触到少量相关刺激甚至完全没有接触到任何相关刺激的情况下,儿童迅速激活句法、音系和形态知识。如果把它们归因于人类的内在天赋,并认为语言能力是内在的,并具有丰富的结构,就很容易解释。这不是偷懒,也不是回避,而是以求实的精神探索一种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如果语言知识需要儿童后天反复学习的话,那么必然会有很多儿童犯错,而这种错误甚至将是不可更正的,并且数量将是不可估量的,最终的结果必将是无法习得一种语言,这也是“语言不可学”(Language is unlearnable)命题的主要理据。
语言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这是自然的,犹如苹果往下落,而不是往上飞,抑或像伽利略实验中质量不同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这些都可以由牛顿定律来说明,都是自然法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赞同儿童语言习得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snap),APS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trivial problem)。
4. 反面观点及讨论
APS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在语言习得中亦是如此。然而,自从APS提出以来,反对声不断,尤其是来自经验论者的反对。他们反对天赋论者的内在激发的学习(innate priming learning),而倡导素材驱动的学习(data-driven learning)。这一节评论近二三十年来有代表性的反面观点。
4.1 经验论者的哲学批评
经验论者的三位代表人物Goodman(1967,1969)、Putnam(1967,1980a,1980b)和Cowie(1999)都坚决反对APS。Laurence和Margolis(2001)在长达60页的文章中系统驳斥了这三位经验论者针对APS的一系列哲学批评。总体上看,Goodman和Putnam的批评歪曲了APS的内在逻辑,低估了语言的复杂性和支持APS的证据,没能提出质疑APS有效性的任何严肃的理由,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符合科学探索或比较心理学的标准方法。他们首先无法解释语言习得中最根本的事实,即线性距离更短的移位是一种引诱性错误,但儿童却经受住了这种诱惑,毅然选择了结构依赖性,放弃了更简单的、更自然的结构独立性。其次,经验式学习的工具(如归纳、概括、类比)是非常有限的,儿童不可能仅利用它们习得语言,因此经验式的学习者不是成功的学习者。Lasnik和Uriagereka(2002)也指出,从经验角度否定APS的经验论者,无法跨出第一步,即无法说明儿童如何仅仅依赖正面语料推断出儿童语言习得的结构依赖假设。再次,如果认为儿童是经验式的学习者,还将面临三大阻碍,包括自然语言复杂的音系、歧义和把普遍原则应用到具体的词序中。而经验论者的第三位代表人物Cowie(1999)的批评则完全错误。他忽视了语言习得的问题远远超越了任何归纳推理问题,从而贬低了APS。标准的归纳推理通常选择最简单和最自然的假设,存在于其他知识领域中,但不适用于语言知识的获得。Cowie倡导的概率式信息、整体式推理及片段式学习等都不是儿童语言习得的特征。
4.2 《语言学评论》专号
《语言学评论》(TheLinguisticReview)在2002年安排了一期专号讨论APS,赞成和反对APS约各占一半。今天看来,其中的观点仍不乏真知灼见,极具代表性。从根本上说,这一期的反面观点并非真正与APS有关,而只与一个问题有关,即为什么助动词倒置(Aux-inversion)依赖于最短结构距离,不依赖于最短线性距离,而实际上这个原则与其他所有句法操作都相同。
具体来看,站在反对APS的立场上,Sampson(2002)的观察是无关痛痒的。他所举例句都是关于最短线性距离的。比如他统计发现普通家庭出身的三岁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一共会遇到145次含有助动词序列的句子,相当于每周会遇到一次,背景更好的家庭出身的儿童遇到的次数会更多,但儿童依然学会该结构。他因此而认为儿童受到的语言刺激是丰富的,而不是贫乏的。表面上看,这些刺激足够丰富,但实际上这里存在的问题很明显。这145个助动词序列句子有些形式是重复的,并没有涵盖所有形式,即有些形式可能就没有出现在儿童面前,但是儿童却可以造出他们从未听过的助动词序列的句子。这说明儿童无须接触到所有可能的助动词组合形式。他们能够基于听到的少量句子,推导出其他可能的组合形式,这正体现了刺激的贫乏。
Sampson在提出反对APS时还认为,支持APS的观点所用的语料都是标准的书面语,而不是儿童真正听到的活生生的口头语。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在研究APS时考虑口头语是必要的,但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从未真正观察过口头语。毋庸置疑,与书面语一样,口头语也有着清晰的结构。即便与书面语有出入,它的表现方式也可以在其他语言中找到。这正是UG在起作用。Hyams(1987)研究发现,英语本族语儿童在早期语言习得过程中经常说出零主语的句子,而这正是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特征。Crain和Pietroski(2002)也发现儿童英语中表现出日耳曼语族其他语言和罗曼语族语言的结构。事实上,儿童在语言习得阶段听到什么类型的语料,与语言习得的最终成功是无关的。研究所选用的语料不仅限于儿童听到的口头语,标准的书面语也可以成为研究语料,因此,APS支持者的做法并没有错。
Pullum和Scholz(2002)的反对并未深化我们对APS问题的认识,而只是揭示冰岛语中主语的习得过程以及丹麦语和挪威语中V2的习得。他们注意到了最短线性距离和最短结构距离之间的关系,并从《华尔街日报》收集了少量的wh-移位语料,尝试从wh-移位中得出结论,这显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虽然他们做得很仔细,但不是在提出一种学习理论,而是在学习理论可能的运作方式上犹豫不决。而且,从《华尔街日报》中收集的语料也不能代表儿童在语言习得早期接触到的语言输入或刺激。
Sampson(2002)以及Scholz和Pullum(2002)都强调负面语料在儿童语言经验中的作用,这也是反对APS的一种表现。Chomsky(1981:8-9)区分了儿童语言参数调整的三类语料:正面语料、直接负面语料和间接负面语料。其中,直接负面语料就是指成人对儿童所犯语言错误的纠正。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如(6)所示:
(6) CHILD: Him naughty teddy.
ADULT: He’s a naughty teddy, yes.
这里,成人对儿童语言的纠正就是一种负面反馈。不过,这对儿童语言习得是不重要的。首先,这种纠正不是经常的;其次,儿童经常对这种纠正充耳不闻。成人试图反复纠正的儿童语言错误,只有在儿童准备改变的时候,才会得到纠正,否则成人的这种努力将是白费。UG原则排除了儿童几乎所有的错误概括,他们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出现的所谓错误,相对于儿童说出的数量庞大的句子,尤其是合法的句子而言是少量的。
所谓间接的负面语料就是指关于某些结构从未出现的语料,如英语本族语儿童从未接触过dinner after、cake eat这样的语料,儿童以此得出结论“英语不是中心语居后的语言”。但是,儿童要想知道英语不允许中心语居后的短语,并不需要接触某些结构不出现的负面语料,而只要依赖于中心语居前的短语出现的正面语料。无怪乎Chomsky(1986:55)得出结论:“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儿童只是依赖于正面语料而习得语言。”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考虑。假设儿童得出某假说X,预测到某现象Y可以自由出现,但实际上只有Y中的某些子类Z出现,那么负面语料可以构成将X修改为X’的基础,从而做出正确的预测。简言之,正面语料足以使儿童获得一种语言,负面语料乃多余。
在这期专号中,最能支持APS的量化证据来自Legate和Yang(2002)。两位研究者在CHILDES儿童语言习得语料库中搜索了Nina和Adam子语料库,其中在Nina子语料库中的46,499个句子中发现20,651个疑问句,其中没有一个类似于Is the boy who is in the corner smiling?这样的是非疑问句,只有14个类似于How could anyone that was awake not hear that?的特殊疑问句;在Adam子语料库中的20,372个句子中也没有发现一个是非疑问句,只发现4个特殊疑问句。Legate和Yang运用语言习得的量化和比较模型,做了最有力的实证,结论认为儿童要想在36个月大之前习得这些疑问句的造句规则,需达到1.2%的刺激率,而实际的刺激率仅为0.045%,两者相差悬殊。足见APS的合理性,也足见经验刺激的贫乏。
4.3 当代计算认知科学的儿童语言习得统计模型
当代计算认知科学研究者尝试借助统计分析,从儿童语言习得的材料中得出反对APS的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统计模型包括Reali和Christiansen(2005)、Clark和Eyraud(2007)、Clarketal.(2008)、Clark(2010)和Perforsetal.(2010)等。他们都试图用各种方法解释助动词倒置,从而证明语言是可学的,而APS是不合理的。Berwicketal.(2011)对此作了专门回复,发现这些尝试只涉及弱生成能力,不能代表结构依赖性,更不能解决APS。这些研究者提出的某些算法,如贝叶斯算法(Bayesian),在理论上不必要,也不相关,答非所问,并未超越前人。
我们注意到,当代计算认知科学试图通过精密的统计分析得出“语言是可学的”这个论点,相关论文也不断出现,但遗憾的是每个精密的统计分析都以失败而告终。即便这些分析是成立的,也不会影响最终的结论,因为完全相同的统计方法只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即某种假语言(pseudo-language)运用最短线性距离原则,而非最短结构距离原则。甚至于在该领域的某些文献中被标榜为“成功”的那些论文也只是对人类的研究中明显缺乏合理性的众多案例中的一小部分。我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这些做法都应该最终抛弃。
5. 结语
本文概述了APS的缘起和精髓,说明刺激贫乏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和不言而喻的道理。文章还讨论了支持APS的句法、音系和形态证据,并驳斥了经验论者和当代计算认知科学研究者对APS的批评。我们认为APS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是一项未尽的事业。相信在生物语言学的框架中,这些探索必将对研究人类的语言知识及语言的本质产生积极的影响。
附注:
① 除此以外,我们认为还存在一个广义上的APS,体现为自然界生物体的生长和发育。问题的关键在于刺激贫乏与生物体成熟状态之间的鸿沟。归纳起来,在关于知识问题的研究中,APS的相对位置可以刻画为:语言知识的来源问题/狭义APS<柏拉图问题(关于知识的获得。问题的关键在于刺激贫乏与所获知识之间的鸿沟)<知识论<广义APS。
② “计算复杂性”本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术语,现已广泛应用于评价语言理论的优劣。在生成语法中,CHL被视为在生物学层面上实现的物理系统,并遵守计算高效性的物理法则,即使用尽可能少的能量、时间和空间。结构依赖性所采用的计算就是这样高效的,例如在句子Istheboywhoissleepingsmiling?中,如果儿童按照复杂关系小句NP→NP+CP或关系小句的递归结构来计算这个句子,就会觉得很轻松。如果采用结构独立性,按照线序来计算的话,就会走入死胡同。从计算理论角度看,前者的确更为复杂,但从语言习得角度看,前者更为经济,也更符合物理法则的高效性。复杂度越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消耗更多能量。儿童无须像程序员那样为计算输入的句子而设计一套算法,因为儿童与生俱来就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工具,高效地解决复杂的语言问题,可谓神奇。与弱生成能力分析相比,复杂性理论更直接、更精细、更准确,因此已成为一种理论探针。关于计算机科学和儿童语言习得中的计算复杂性问题,可以分别参阅Papadimitriou(1994)和Bartonetal.(1987)。
③ Read和Schreiber(1982)以及Stromswold(1990)的研究发现,儿童拥有对成分结构的隐性意识,没有一个儿童能够正确地重复非成分的句子片段(non-constituent fragment),儿童还可以本能地区分主句和助动词。
④ 元音转移可以有效地组织人脑的记忆,把貌似无序的材料用有力的模式和原则性的方式组织起来。如此,儿童只需接触到少量的刺激或经验,即可利用这些规则或原则组织和丰富语言知识(参阅Chomsky 2004:133)。
Barton, G., R. Berwick & E. Ristad. 1987.ComputationalComplexityandNaturalLanguage[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Berwick, R., P. Pietroski, B. Yankama & N. Chomsky. 2011. Poverty of the stimulus revisited [J].CognitiveScience35: 1-36.
Chomsky, N. 1955/1975.TheLogicalStructureofLinguisticTheor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omsky, N. 1957.SyntacticStructures[M]. The Hague: Mouton.
Chomsky, N. 1965.AspectsoftheTheoryofSyntax[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Chomsky, N. 1968.LanguageandMind[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Chomsky, N. 1971.ProblemsofKnowledgeandFreedom[M]. New York: Pantheon.
Chomsky, N. 1972.LanguageandMind(enlarged edition)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homsky, N. 1975.ReflectionsonLanguage[M]. New York: Pantheon.
Chomsky, N. 1980a.RulesandRepresentation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N. 1980b. Discussion of Putnam’s comments [A]. In 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 (ed.).LanguageandLearning:TheDebateBetweenJeanPiagetandNoamChomsky[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N. 1981.LecturesonGovernmentandBinding:ThePisaLectures[M]. Dordrecht, Holland: Foris.
Chomsky, N. 1986.KnowledgeofLanguage:ItsNature,OriginandUse[M]. New York: Praeger.
Chomsky, N. 2004.TheGenerativeEnterpriseRevisited[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Chomsky, N. 2010. Poverty of stimulus: Unfinished business [R].GLOW-in-AsiaⅧ, Beijing.
Chomsky, N. & J. Fodor. 1980. The inductivist fallacy [A]. In 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 (ed.).LanguageandLearning:TheDebateBetweenJeanPiagetandNoamChomsk[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N. & M. Halle. 1968.TheSoundPatternofEnglish[M]. New York: Harper & Row.
Clark, A. & R. Eyraud. 2007. Polynomial time identification in the limit of substitutable context-free languages [J].JournalofMachineLearningResearch(8): 1725-45.
Clark, A., R. Eyraud & A. Habrard. 2008. A polynomial algorithm for the inference of context free languages [R].ProceedingsofInternationalColloquiumonGrammaticalInference. Springer, London.
Clark, A. 2010. Efficient, correct, unsupervised learning of context-sensitive languages [R].ProceedingsofCoNLL. Uppsala, Sweden.
Cowie, F. 1999.What’swithin:NativismReconsidere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rain, S. & N. Nakayama. 1987. Structure dependence in grammar formation [J].Language63: 522-543.
Crain, S. & P. Pietroski. 2002. Why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a snap [J].TheLinguisticReview19: 163-183.
Goodman, N. 1967. The epistemological argument [J].Synthese17: 23-28.
Goodman, N. 1969. The emperor’s new ideas [A]. In Hook, S. (ed.).LanguageandPhilosophy[C].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Hyams, N. 1987. The theory of parameters and syntactic development [A]. In Roeper, T. & E. Williams (eds.).ParameterSetting[C]. Reidel: Dordrecht.
Lasnik, H. & J. Uriagereka. 2002. On the poverty of the challenge [J].TheLinguisticReview19: 147-50.
Laurence, S. & E. Margolis. 2001. The poverty of the stimulus argument [J].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52: 217-76.
Legate, J. & C. Yang. 2002. Empirical re-assessment of stimulus poverty arguments [J].TheLinguisticReview19: 151-162.
Papadimitriou, C. 1994.ComputationalComplexity[M].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erfors, A., J. Tenenbaum & T. Regier. 2006. Poverty of the stimulus? A rational approach [R].Proceedingsofthe28thAnnualConferenceoftheCognitiveScienceSociety. Vancouver, Canada.
Pinker, S. 1999.WordsandRules:TheIngredientsofLanguage[M]. New York: Basic Books.
Pullum, G. & B. Scholz. 2002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stimulus poverty arguments [J].TheLinguisticReview19: 9-50.
Putnam, H. 1967. The ‘innateness hypothesis’ and explanatory models in linguistics [J].Synthese17: 12-22.
Putnam, H. 1980a. What is innate and why [A]. In 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 (ed.).LanguageandLearning:TheDebateBetweenJeanPiagetandNoamChomsky[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H. 1980b. Comments on Chomsky’s and Fodor’s replies [A]. In 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 (ed.).LanguageandLearning:TheDebateBetweenJeanPiagetandNoamChomsky[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ad, C. & P. Schreiber. 1982. Why short subjects are harder to find than long Ones[A]. In Wanner, E. & L. Gleitman (eds.).LanguageAcquisition:TheStateoftheAr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ali, F. & M. Christiansen. 2005. Uncovering the richness of the stimulus: Structure dependence and indirect statistical evidence [J].CognitiveScience29: 1007-28.
Scholz, B. & G. Pullum. 2002. Searching for arguments to support linguistic nativism [J].TheLinguisticReview19: 185-223.
Sampson, G. 2002. Exploring the richness of the stimulus [J].TheLinguisticReview19: 73-104.
Stromswold, K. 1990.LearnabilityandtheAcquisitionofAuxiliaries[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Yang, C. 2002.KnowledgeandLearninginNaturalLangua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