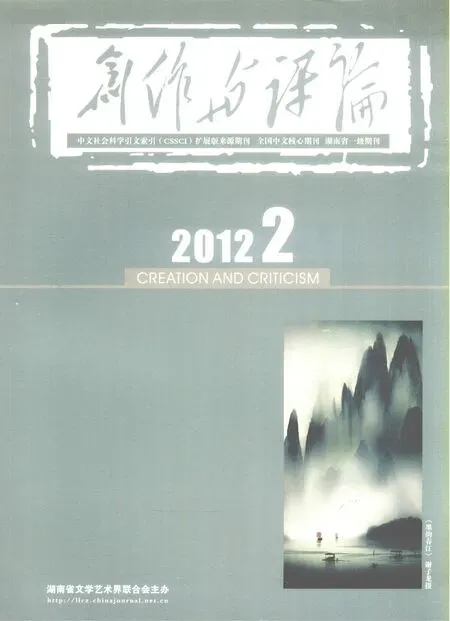历史之痛与忏悔之思——评莫言的《蛙》
■ 周志雄
莫言在谈到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时说:“写作新小说时我只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二是如何创作唯有自己才能写出来的文体和结构。”①这何尝不是莫言自己创作的夫子自道。作为一个已经写出了《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许多优秀作品的作家,莫言写作《蛙》时有很高的起点,对于像莫言这样“重复自己是可耻的抄袭”的成熟作家来说,写作最大的困惑是如何面对已有作品的挑战,在阅读《蛙》时,我们会不自觉地追问,《蛙》在何种层面上构成了对莫言以往作品的超越?《蛙》如何处理莫言在谈大江健三郎时提出的两个问题?《蛙》的创作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
中国当代历史是一个急速变革的历史,历史的机缘在不同的时代为人物的命运变化带来了丰富的戏剧性,在历史宏大的机制下,个人的身影是卑微而渺小的。小说叙事的魅力在于可以自由地穿行于虚构与历史之间,以历史性和想象性混杂的人物故事去重新整理和评价历史,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并获得反思历史的机会与展望未来的可能性。在命运的播弄和历史的夹缝中,人性的卑微和屈辱在小说家的故事叙述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政治学家对历史时代的描述不同,小说的历史叙事既有丰富的生活细节,人性的可能性想象,也有超越于时代政治的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甚至是哲学的思索和启示。小说家与社会历史学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需要直接回答他的社会诊断,一切皆在人物、故事、场景等想象之中,充满模糊意味的隐喻和人物故事孕育着多种理解生活的可能性。小说历史叙事的目的就是把读者带回到历史之中,重新回望并思索历史,在文字的缝隙中,找到人性的多重可能性和历史的某些症结。
《蛙》就是这样的一部充满历史叙事魅力的小说,小说穿行在建国后的历史时代之中,小说叙述的是关乎国人生活重要方面的生育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从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上,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是必要而成功的。中国又是一个有生育传统的国家,计划生育国策与国人的香火观念、生育权利之间又是有矛盾的。当代中国生育问题对国人的生活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严重的人口问题。生育问题不仅仅是国家政治,也是老百姓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人口数据的变化,也是饱含着普通老百姓血泪情感的历史事实。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以深深的责任感,看到了这样充满悖论的历史现实。
《蛙》的难度在于计划生育是一项无可质疑的“国策”,表现这样的“敏感”的社会题材,是不能超出这个基本前提的。如何处理这样的重大题材?其文学的意义在哪里?莫言的处理方式是以大跨度的历史年代进行对照,书写在历史的变迁中人们所受到的生育政策的影响,以人的命运变化写历史,以生育线索为中心串起了人物的爱情史、社会生活史、阶级斗争史、心理发展史、精神血泪史,以毛茸茸的人物故事呈现充满悖谬的历史黑洞和人性本色。姑姑(万心)是小说的主人公,1950年代国家提倡生育人口,姑姑是一个接生能手,接生了数千个婴儿,是受高密东北乡人敬重的圣母般的人物。在阶级斗争年代,姑姑因为恋人飞行员驾机投敌受牵连,她成为社会的专政对象,受政治打击和身心摧残。在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姑姑是一个优秀的计划生育干部,她铁面无私,为工作鞠躬尽瘁,万死不辞。她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为革命工作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她为维护国家的法律,赴汤蹈火般地迎接一个个的任务。这是个为时代牺牲的人物,在她光辉的历史下,她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重重伤害。作为计划生育干部,姑姑成为非法生育妇女的敌人,头上被人打棍子,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身上有很多伤疤,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给她最沉重的精神负累的是她逼死了几个怀孕的妇女,被人诅咒。她的晚年是在“罪感”中度过的,一个人仿佛受了历史的欺骗,陷入矛盾的撕扯之中。她害怕青蛙,隐喻了她一生所背负的罪恶之源。姑姑的精神矛盾分裂症是时代造成的,它隐喻了历史现实对个人的巨大伤害。这个曾经的“政治斗士”,其悲剧如小说的叙述人蝌蚪所说的,她“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但姑姑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斗士”,她医术精良,很有同情心,她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在看到违法怀孕的小孩出生的时候,她作为妇科医生的本能也会被唤醒,甚至在面对母牛难产的时候,她也会出手,她还不止一次地无私地将自己身上的血输给病人。这样一个充满精神光辉的人物,最后变成了剧作家蝌蚪代孕生子的帮凶,曾经的正直品格,完全化解了。姑姑的人生命运和精神心理变化质疑的是时代对个人的压迫,在大时代中,个人不过是一枝随风的芦苇,姑姑是时代观念的受害者,是历史运动的受害者。
除了姑姑,小说中的蝌蚪、小狮子、陈鼻、王肝等何尝不是历史的受害者。“蛙”所象征的生殖文化在当代社会左右了众多人物的命运。蝌蚪作为一个剧作家,他最终也成为“香火”观念的不自觉继承者,追随姑姑战斗了一生的小狮子充当了观念的帮凶。高密东北乡最漂亮的姑娘陈眉外出打工在一场大火中被毁了面容,被迫与人代生孩子充当“孕奴”为父还债,又被出尔反尔的袁腮等人欺骗,精神上饱受摧残。王肝、王仁美等女性在国家、家庭、历史所构成的复杂困境中作为生育的“容器”丢掉了生命,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二
据莫言自己的讲述,《蛙》的写作有一波三折的经历,早在2002年就写了15万字的初稿,主要是采取主人公坐在舞台下观看舞台上上演他创作的话剧的方式展开构思,穿插主人公的回忆,再描写剧中人的表现和观众的反应,可谓是一个多角度叙述表现历史的构想,后来觉得自己这样的写作太过“混乱”了,可能会构成对阅读者的折磨。②这篇小说后来采用了剧作家蝌蚪写信的方式,以5封短信、5篇故事叙述加上一个剧本构成,既有多维的叙述角度,又有叙事上的明晰性,符合中国读者的接受习惯,这构成了小说结构上的创新性。
《蛙》分为三种语言叙述故事,书信、小说讲述、戏剧融为一体。内容上,三者相互映衬,书信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戏剧是真假混合的,小说以这种真真假假的方式切入时代,让读者深思,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新颖变化,而是引导读者从小说表层超离出来,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如同小说中李手对蝌蚪所言:“文明社会的人,个个都是话剧演员、电影演员、电视剧演员、戏曲演员、相声演员、小品演员,人人都在演戏,社会不就是一个大舞台吗?”现实和戏剧的内在本质被人物一语道破,在这里获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蛙》中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书信是以一个文学青年向一个文学家请教的口吻写的,涉及的主要事情是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如何将姑姑的事情写成文学作品。这种叙述的方式极大地扩充了小说的内容,使小说有了多重意义空间。比如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这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讲的,形成了对故事的补充和映衬。再如在另一封信中说:“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镜下。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我是为自己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当然可以算作为自己写作,但还不够;我想,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在这样的段落中,说出了小说写作的意图,引导读者去忏悔,去深入地思考小说故事叙述中沉甸甸的一面。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是剧本,这个蝌蚪创作的剧本在内容上是小说故事的延伸,采取的形式是戏谑的,历史上的高密县令高梦九断的案子是今天的,官府被买通,采取了一种遮人耳目的方式断案,这个颇有寓意的情节戏谑了历史没有进步,在经济发展的当下时代,政治黑幕并不比历史上任何时代少。
《蛙》的叙述很紧凑,毫不拖泥带水,故事的推进很快,没有过多的冗繁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描写很简练,看上去像是一幅幅工笔画。小说选取的是几个不同时代的片断性的故事,以几个核心人物为中心,进行发散,小故事大时代,以少胜多,在20多万字的篇幅中书写大跨度的历史时代。莫言早期小说中那种感官铺张的“炫技”式写法在《蛙》中有较大的改变。莫言有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但他的叙述定位是中国式的,他采用的是中国式的讲述,写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清晰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中国当代历史,中国的社会现实,都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
《蛙》的中国式叙述也体现在小说所塑造的人物的精神气质上。小说所写的人物多是高密东北乡的奇人,小说以奇事来写奇人,这与中国古典小说中那种适当神化、拔高人物的写法极其相似。奇人,或是一种有独特个性的人,或是有特殊艺术才能的人,或是有传奇人生经历的人。姑姑是一个奇人,精神上的血脉可以延伸到《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式的奔放人格,泼辣大胆,敢作敢为,勇于担当。姑姑的奇还在于她传奇般的接生技术,那种敢于赴汤蹈火的工作热情,以及聪明干练的工作方法。秦河、郝大手的奇在于捏泥人的手艺,王胆的奇在于痴情,袁腮的奇在于算卦、给人取避孕环等“奇技”。奇人奇事是中国传统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塑造的多是类型化的人物,但莫言面对的是21世纪的读者,他当然不能简单地写类型化的人物,而是在传奇人物的个性中增加了多面性,比如上文分析的姑姑形象,再如剧作家蝌蚪是个性格暧昧的人。与奇人相联系的是他们的奇事,陈鼻的经历,陈眉代孕,蝌蚪的婚恋史等等都具有传奇意味。《蛙》也不是简单停留在传奇故事上,还揭示了这些人物故事背后溅着血泪的一面,传奇故事中有着深厚的心理基础,还有饱满、生动的生活细节,小说不是简单地天马行空虚构奇事,而是将严肃的社会批判与传奇式人物故事的讲述结合在一起。
莫言多次说到小说家的风格就是作品的语言风格,这部小说的语言创新体现在莫言自如地运用了多重笔墨。一是政治语言。这体现在文革时代的人物语言中,以姑姑的讲话为代表。“姑姑严肃地说,你们年轻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要想歪门邪道。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头等大事。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典型引路,加强科研。提高技术,措施落实。群众运动,持之以恒。这段姑姑的话很夸张,塑造了一个深受政治影响的人物形象,在字里行间隐隐地表达了历史的揶揄。第二种是朴素、简洁的叙述语言。“在河边钓鱼的闲人杜脖子亲眼看到我姑姑从对面河堤上飞车而下,自行车轮溅起的浪花有一米多高。水流湍急,如果我姑姑被冲到河里,先生,那就没有我了。”这段语言很简洁,但很有神韵,很幽默,姑姑泼辣、豪爽的形象从叙述中呼之欲出。第三种是一种诗意化的戏谑语言。比如:“她眼里饱含着泪水,是因为爱孩子爱得深沉。”这段话是对艾青诗歌的戏谑,在嬉笑中蕴含了人物严肃一面。当然《蛙》的语言不只是这三种,莫言是个很注重语言的作家,他积极吸收了民间的生活语言,古典散曲的语言,注重语言的气势,小说中常有一些铺排的感性书写语言,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蛙》的语言风格总体上向朴素的叙述回归,作者有意压低了那种铺排的感性叙述风格。一个作家使用的语言不是通常的生活语言,而是经过提炼的一种个性化的语言,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呈现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莫言正是这样一个有语言自觉的作家。
三
莫言的小说不是戴维·洛奇所说的“现代主义小说”,不搞纯文学试验,而是有现实的责任和关怀;不是向内转去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有明晰的人物故事;也不是用开放性或含混性的结尾,而是有鲜明的倾向性。莫言的小说艺术建立在中西小说资源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民族历史,积极吸收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形式,并对之进行当代化的改造和推进,以现代的思想和理性精神贯注其中,符合民族读者的阅读习惯,又给读者以精神的滋养和启迪。经过多年的写作磨炼,莫言的小说在艺术上已经非常成熟,艺术个性非常鲜明,达到了自由创造的境界。《透明的红萝卜》对生命的疼痛感的表达,《红高粱家族》对人性自由与生命本色的张扬,《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以大跨度的历史变迁书写人性之思与一个民族的精神之思,《酒国》、《红树林》、《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十三步》、《檀香刑》在叙事方式上的革新,等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蛙》的写作建立在莫言多年写作的基础上,艺术上进一步推进,以更广泛的人类意识和忏悔意识,在清晰的故事中蕴藏着对人类生存的深层思索。
我们不难看到《蛙》与莫言已有作品的联系,如对“高密东北乡”文学地域空间的书写,对民间语言的积极吸收,对民间传奇式人物故事的叙写,对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尊重,等等。但《蛙》又是对莫言创作的一次推进和创造,莫言在积极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候,又在积极地发展传统,对此,除上文已涉及的外,还突出的表现在小说意义空间的营造和对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上。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蛙》在主旨上超出了故事本身的内涵,这是莫言在叙述上所采取的艺术手段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其中主要是隐喻手法的恰当运用。这是小说中的一段:“蛙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人跟蛙是同一祖先,她说,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状相当,人的卵子与蛙的卵子也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你看没看过三个月内的婴儿标本?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与变态期的蛙类几乎是一模一样啊。”这段话解释了小说的题名,说出了小说的深层含义,它隐喻了生殖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主人公蝌蚪的名字也有隐喻意味,一个讲述生殖文化的剧作家本身就是生殖化的。小说的封面设计为在红色的底色下站着一个孩子,又像是一个青蛙,有一股强烈的生殖气息。书中的人物以人体的器官命名也隐喻了人的身体是生殖文化的产物,个人的生死悲苦与特定历史背景下生殖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蛙》提出了关乎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时代,我们该如何反思我们的生育传统?小说中姑姑嫁给郝大手的过程也是有隐喻意味的,姑姑被一群青蛙追逐,被青蛙撕去了衣裙,这件事说起来不具有现实性。但具有内在情理上的合理性,它暗指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姑姑对自己罪恶的忏悔通过自己的丈夫将那些被流产的婴儿重新捏出来,以赎回自己的罪恶。有罪的人不只是姑姑,叙述者蝌蚪,接受信件的杉谷义人,等等,很多人都是有罪的,如莫言所说:“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当某种社会灾难或浩劫出现的时候,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必须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做了需要批评的事情。”③因此,小说就不仅仅是写历史,写民间传奇故事,而是在故事之中有深层的人性反思和文化反思,这就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意蕴空间。
《蛙》在叙述清晰的故事,塑造鲜明的人物之外,也对人物进行适当的心理精神分析。通过对人物进行成长式的对照,对人物内心的精神冲突进行解剖,当然不是那种细腻深入的心理分析,而是一种在白描式的简练的人物形象勾勒的基础上,以人物富有个性的语言和简练的心理描写表现人物命运的心理机制。《蛙》的历史跨度较大,人物的性格、心态前后有很大的变化,作者并没有细致地展示人物内在精神脉络,但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分析空间。
如上文所述,《蛙》无疑是一部有批判性的小说。《蛙》在批判现实上是有自己的抱负的,但莫言批判的力度还是有限的,《蛙》对社会现实黑洞的揭示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新闻报道?多大层面上进入了对当代文化体制的深层反思?对人类的生存问题有没有天问式的追问?莫言仍然是有所保留的,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另外,《蛙》有忏悔的角度,但忏悔的灵魂并未被撕开写,而是融入在一些隐喻性的情节设计之中。
任何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莫言不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他的思想没有超出我们这个时代,但不容否认《蛙》是一部致力于创造的小说。莫言的创造是一种不断积累的综合创造,他直面历史问题和时代问题,以小说的魅力去呈示那些历史陈年旧事,启示着读者思考。在这个网络写作娱乐化泛滥的时代,在各种小说理论扑面而来的时代,执守小说艺术的创新是艰难的,但无疑又是必要而可敬的。
注 释
①莫言:《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在大江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西部》2007年第9期。
②莫言等:《对话:在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之间》,《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③杨桂青:《莫言 写作时把自己当罪人》,《中国教育报》2011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