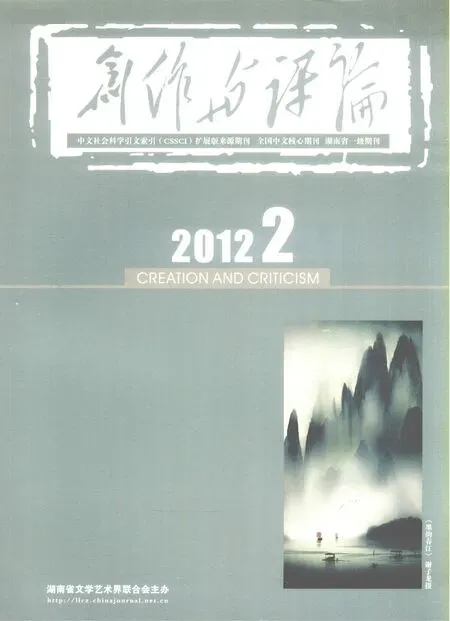匮乏中的繁复与反复——解读张炜《你在高原》系列
■ 徐勇
一、繁复与反复
张炜的《你在高原》系列十部给人印刻最为深刻者,莫过于它的无处不在的繁复与反复。这一繁复和反复既表现为小说的出版发表上,也表现在叙述语言和情节内容,甚至章节编排上。系列小说虽集结出版于2010年,但其实是张炜前此阶段创作和出版的一次全面总结与回顾。这十部小说中,有些如《家族》和《我的田园》属于旧作修订后的重版,而后收录在《你在高原》系列中;《橡树路》则以单行本的形式,和《你在高原》(作家出版社)系列几乎同时出版;有些如《忆阿雅》和《曙光与暮色》,则分别是此前《怀念与追忆》和《你在高原——西郊》修订重版后的更名而成;而即使是系列名“你在高原”也是沿用作者此前的小说名《你在高原——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我的田园》《你在高原——西苑》和《你在高原——怀念与追忆》)。若从小说的情节发展和设置来看,《你在高原》系列其实是在张炜早期长篇小说《柏慧》的基础上的极大的扩充。其中,有些篇章如《父亲的海》几乎完全取自《风姿绰约的年代》中的同名篇章;《金黄色的菊花》和《穷人的诗》两篇章,则均是《风姿绰约的年代》中相同篇章的缩写。《如花似玉的原野》中的有些情节也被重新叙述后进入《你在高原》系列中。而《风姿绰约的年代》中“风姿绰约的年代”一节则几乎被全部移入了《家族》当中。至于章节编排上,系列小说更是错综繁复:“你在高原”乃总的系列名,之下是各部小说名,而后分卷和章,再下就是各个具体的中短篇名如“父亲的海”等。而事实上,各个中短篇很多都可以独自成篇,很多如前面提到的《父亲的海》、《金黄色的菊花》、《穷人的诗》、《风姿绰约的年代》等等,都曾以中短篇的形式发表或出版过。可见,如果不欲从张炜创作的整体上通观,显然是很难有效地把握这一繁复和反复的现象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这十部小说,其实可以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换言之,这十部小说大可看成一个叫宁伽的中年男性主人公的个人传记。因为这十部小说的主体部分都是以第一人称“我”——即宁伽——的口吻讲述“我”和与“我”有关的故事。而之所以分为十部,是由于十部小说分别从十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进入,故而整个系列中,常常有大量的重复——情节、人物、结构乃至文字上的重复——,这无疑给人以絮叨和繁复之感,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种重复实则乃作者的有意经营,毋宁说是作者数十年沉积于心底之诉求和吁求的表征。
二、寻找与追问
要理解张炜的这十部小说,仅从情节上考察,看来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这其中有大量的情节互相重复交叠。在这里面,倒是有一些对立的范畴始终贯穿整个系列小说,这对理解小说十分关键。这些范畴有城市/野地、平庸/浪漫、定居/流浪、平原/高原、现实/历史,等等。而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范畴的对立冲突和矛盾运动,起到了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即叙述者“我”的行止:城市平庸而单调的现实生活,促使“我”不断远行(或重述历史),而一旦“我”远行到某一个地方,驻足不久,又再一次踏上了流浪的路途。如此循环不已。在这些范畴中,“高原”似乎又是理解的关键。“我的梦中有个高原。在这条通向高原之路,粉色的苹果花纷纷落下来,它遮住了我奔波的身影,送我进入一个又一个香甜的长夜。高原……高原……我总能感到穿过遥遥旅途射来的那道目光,那是她的永恒的高原……”(《我的田园》)“她先我一步站在高原上。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有一双永不停歇的脚。”“可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她又为什么在高原上久久伫立?还有,我真的认识她吗?”(《我的田园》)看来,“高原”毋宁说就是某一模糊而朦胧的目标,“她”诱使叙述者“我”不断的追寻,永不停歇,至于这一目标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追寻,叙述者自己也似乎不甚了了。
在这里,与其沿着叙述者“我”的思路去弄清追寻的目标“她是谁?”,不如反过来去追问叙述者“我”是谁?而事实上,叙述者追问“她是谁?”的意图也是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因为,一旦弄清楚“我”所要追寻的目标是什么,她来自何方,又要到哪里去,也就能明白“我”是谁,“我”为什么要不断地流浪和出走了。这样也就能理解,系列小说为什么始终要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并以有关“我”的故事贯穿始终。对叙述者“我”而言,似乎只有弄清楚追寻的目标——“她”是谁,才真正明白“我”所来何处。“我”之不断的出走和流浪也似乎是源于因应“她”的呼唤;这似乎是一个循环:是先有“她”的神秘的呼唤,还是先有“我”的不断的出走。叙述者“我”翻来覆去的倾述,颠来倒去的出走,最终只是表明叙述者的迷惘,“我”既不明白“她”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只有在这个时刻才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我明白:自己属于一片无边无际的野地,我只有与土地、土地上滋生的这一切面面相对时,才会感到内心的愉悦。”(《我的田园》)读到这里,忽然明白,叙述者一生不停的奔波,似乎总与童年时代的记忆纠缠在一起。实际上,童年时代在山林中的流浪记忆,正贯穿于《你在高原》系列的始终:那大李子树,那林中的小茅屋,外祖母和母亲,以及始终缺席的父亲(父爱)。而这一切,某种程度上,又是源于某种匮乏:因为显然,这一切美好的记忆很快就成为了历史,因为父亲的所谓不可洗脱的“罪责”,“我”被迫长期离家,从此浪迹山林,永难回头;而且,美好的童年中的“故地”也正遭受毁灭性的开垦和破坏。可见,从这个角度看,“回到了原来”并不是要“原来”重演,而是要在记忆和叙述的回返中达到对匮乏的想象性解决。
在这里,“回到了原来”带有重写历史的意味。因为“我”从哪里来,显然涉及到历史。而事实上,整个系列都一直在写“我”的家族,乃至祖先的故事,这在《家族》、《忆阿雅》和《人的杂志》中有鲜明的表现;而“我”要到哪里去,则显然关乎未来。如果说历史还能通过叙述的力量去追溯的话,未来则有赖于当下了。但问题是,叙述者“我”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平原。这并不是说现实不接纳“我”,而毋宁说是现实不接纳“我”的历史,因为,通过叙述的力量建构的有关“我”和“我”的家族的历史,只是一部通过“我”的视角叙述和呈现的野史,并不为正史所认可:“我”的父亲和外祖父进入不了历史。而实际上,他们也已早已为历史遗忘和歪曲,因此,对于“我”而言,要想进入现实也就意味着必须忘记家族前史,但忘记“历史”,也就注定了“我”是一个无根之人。叙述者十分清楚,没有历史,也就难以安置现在的“我”。看来,这只能是一个无解的悖论:“我”能通过叙述讲述历史中的“我”(和“我”的家族)的故事,但这一故事只能存在于“我”的讲述中,“历史”于“我”似乎只是镜像,“我”只能在“历史”的讲述中获得完满和自足,一旦进入现实即告破碎:“我”注定了要不停的流浪和寻找。可见,“我”之为“我”有着先天的匮乏。从这个角度看,正是这匮乏,促使张炜二十余年如一日地不懈写作——也是叙述者“我”的始终絮叨不已,他的写作客观上就带有弥补这先天匮乏的意图之所在。
三、絮叨与孤独
卢卡奇曾把小说写作视为一项孤独而历险的事业,这在某种程度上正符合张炜。张炜(叙述者)把他的孤独化为不停的写作和寻找,在他那里,写作和寻找其实是同构的。在这个意义上,张炜其实是把孤独的写作视为一场对话和较量,他通过虚构和讲述,既在与假象中的读者,也在与目标“她”对话和较量。这从题目“你在高原”可以看出。“你”既是假想中的对话者(读者),也是矗立在“高原”中的“她”,叙述者“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因此,就有了叙述者的急不可耐,故而难免絮叨和重复;就有了叙述者想试图说服假想中的“你”,故而出现不断地诉说和表白。这似乎很反讽,张炜(和叙述者)的孤独,固定在笔端,却生出无限的絮叨。
这也决定了《你在高原》的文体形式,这是一种介于故事体和小说之间的混合文体。说其是故事体,是因为整个系列都是以叙述者“我”的所见所闻作为基础,用本雅明的话说,就是立足于“经验”的讲述和传递。在故事体中,还有一个因素不可或缺,那就是听故事的人。连接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的基础——共同的经验。故事表现在情节上虽然曲折离奇,但终究还在经验能理解的范围内,故而能交流能被理解。在张炜这里,听故事的人就是假想中的读者“你”(也包括作为“她”的“你”)的存在。这里除了假象中的“你”的存在外,还预设了“你”与“我”的对话关系。我们拥有共同的经验基础,故而能互相交流。但另一方面,通过叙述者“我”讲述的故事,却是明白无误的“经验的毁灭”。因为显然,我们之间经验之基础的东部平原正一步步走向毁灭,现代文明正一步步侵袭着古老的平原;平原在萎缩,我们的共同经验也将荡然无存。从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以“故事”的讲述的形式,完成的“小说”写作实践。张炜的写作,希求的是与读者的经验交流和对话,其结果,带来的是交流的不可能。小说的写作正是这种交流之不可能后的孤独的文化实践。“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写小说则意味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活深刻的困惑。”①“历史”的先天匮乏,经验的破碎,“生活总体性”的缺失,邪恶之现代文明的长驱直入,张炜以他不倦的写作,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一点;但他同时又试图以自身总体性的重建来抵抗这种缺失。这一努力赋予张炜的写作格外地带有悲剧性和挽歌色彩。但问题是,他的努力,他的通过把历史与现实勾连和对接重建起来的,只能是他自己的总体性,这一总体性并不为他人和社会认同,叙述者的家族前史不为正史认可,叙述者的喋喋不休和奔波流浪也不为当世人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张炜从事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战争”(张炜语)。张炜的写作虽然絮絮叨叨,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孤独终老。
这似乎是一种悖论:越是孤独,张炜越表现出喋喋不休絮絮叨叨;社会越是变化莫测,张炜越是表现出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坚韧;文化越是走向快餐化,张炜越是要越写越长。这诸多矛盾对立奇怪地纠结在张炜的写作当中,既相安无事又彼此互不相容。这与其说是张炜在考验读者的耐心,不如说他是在考验自己,他是在拿自己的青春时光参与的一场豪赌。二十余年的坚守,十卷近五百万字的篇幅,繁复的叙述,一己的呢喃,到头来,都只能交付给素昧平生的听众,而事实上听众已演变为孤独的读者。毕竟,在听众和叙述者之间,可资交流的共同经验正日趋萎缩:这不禁让人疑问,张炜以如此恢弘的篇幅建立起来的阅读/对话机制还能持续多久?显而易见,张炜其实是在以热热闹闹的文字,写作最为孤独的人生“体验”。
四、成长等于流浪?
其实,如果把十部系列小说中重复(或重合)的情节和叙述文字删掉,然后加以重组,《你在高原》系列大可看成是一个人的成长史,这就不妨从“成长小说”的角度来解读这个系列。正如巴赫金在谈到《巨人传》之类成长小说时指出的:“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所以,未来在这里所起的组织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且这个未来当然不是私人传记中的未来,而是历史的未来。发生变化的恰恰是世界的基石,于是人就不能不跟着一起变化。显然,在这样的成长小说中,会尖锐地提出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问题,自由和必然问题,首创精神问题。成长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②可以说,《你在高原》就是这样塑造叙述者“我”的,它把“我”放在“我”的家族前史,七八十年代中国的社会转折以及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全球化进程这一复杂脉络当中加以形塑,因而虽然始终讲的是“我”的故事,但其实早已同家/国之间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家/国”的“前世今生”显然内在地决定了“我”的未来走向。
但事实是,叙述者/主人公“我”甫一出生,其实就意味着衰败和下降:父亲的难以洗脱的罪愆令“我”一家始终笼罩在灰暗之中,“我”的命运早已于冥冥之中由“我”的家族和先祖的命运决定了,“我”不过是再一次重复先人的人生轨迹;但“我”又似乎不甘于这种宿命,因而就有了“我”总是不停地流浪和出走。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系列又可以看成是当代的“流浪小说”。“我”的血液里先天留有先人流浪的禀性,因而从出生一刻起就注定了要不停地流浪。流浪任何年代都有,但流浪(汉)小说的产生乃至大量出现,却是近现代才有的事情。张炜小说中的流浪汉,内涵极为复杂,这很像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形象,他们作为经验的被剥夺者,逡巡在现代大都市的边缘地带,他们其实是以破碎的经验对抗现代文明的震惊和巨大冲击。显然,叙述者“我”并非如三毛(《三毛流浪记》)一样社会的底层或边缘群体,也并非不被社会接纳和认可,事实上,如果愿意,“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到社会秩序中去,可见,“我”的流浪汉形象更多是一种“心象”,是“我”的心灵不甘寂寞,“我”有家庭,有妻小,有亲友,但“我”却想着打破它们,冲出牢笼。“我”拒绝秩序,拒绝安定,向往野地。但问题是,野地茫茫,最终会把“我”引向何方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张炜在一篇创作自述中就曾这样写道:“我觉得我踏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这条路没有尽头。当明白了是这样的时候,我回头看着一串脚印,心中怅然。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寻找和解释一样东西,同一个问题——永远也寻找不到,永远也解释不清,但偏要把这一切继续下去。”③如果略去写作时间,再把它随便置于《你在高原》系列中的任何一部当中,其与系列小说中的文字叙述之间,简直难分轩轾看不出任何区别。以此观之,《你的高原》系列,其实还可以看成是作者的精神自传,是作者早年创作追求的叙述实现。在这里,叙述者/主人公“我”某种程度上其实就等同于作者“我”。
但问题是,当作者在写作中不知不觉混淆了这种叙述者/主人公“我”和作者“我”的区别时,他的写作其实就已暗藏了种种危险。因为,这势必造成叙述距离的消失,作者往往不由自主地隐没于叙述者乃至主人公身上,其结果是,作品不可避免地变得没有节制和感性泛滥;而事实上,一部成功的作品总是能很好的处理这种距离的。另一方面,这种混淆,也会造成认同上的混淆。因为写作毕竟是虚构,现实主义虽能达到“仿真”“乱真”的效果,但实际上在这其中仍有距离的存在,而一旦作家在写作中忽视了这点,反而可能导致效果上的“失真”。张炜的《你在高原》系列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把握好。在小说中,“我”似乎总在寻找,但一佚找到,如换工作、办杂志和开垦葡萄园等,“我”却又在想着新的启程(《我的田园》、《曙光与暮色》、《忆阿雅》等),如此往复,没有穷尽。可见,寻找,对叙述者“我”而言,重要的并非目标和结果,而似乎是过程。既如此,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找下去呢?而如果艰苦卓绝的寻找不是为了某一目标,这样的寻找又有什么意义?难道就是“为了寻找而寻找”“为了流浪而流浪”吗?这到底是叙述者/主人公的寻找,还是作者的寻找?事实上,这其实是以对没有结果的“高原”的追求而牺牲了路边的美丽“风景”:“我”并不“人道”。小说中,很多人物形象往往只如道具一般出场退场,无始无终,似乎就只为了形塑“我”的流浪汉形象,叙述者(抑或作者?)可以随意弃之不顾。小说中“我”的妻儿因为“我”的永难安定而处于一种长期被离弃的结果,“我”之为“父”为“夫”的责任何在?而即使是像《我的田园》中的小姑娘鼓额和《曙光与暮色》中的姑娘小冷——这样的形象在小说中还很多,当她们等待着“我”去救赎的时候,“我”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信赖和依托,其意义何在?等等。这些虽然都是发生在小说文本内,但其实已不知不觉间从想象和叙述的层面颠覆了作者的形象及其文学实践。
而最为致命的是,一旦叙述者“我”的寻找沦为一种无需结果和目标的永远的过程时,张炜实际上通过这种写作揭示出人生/叙述的荒诞之本质:没有结果和目标的寻找,其实就是一种不断的重复(或反复),重复(或反复)似乎注定要成为我们总也逃不脱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看,“高原”其实如同“戈多”,其有无早已无关紧要,对于我们而言,所能做的,似乎就只有翻来覆去的写作和不断的重复了。
注 释
①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启迪》,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9页。
②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2-233页。
③张炜:《一辈子的寻找》,《文学角》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