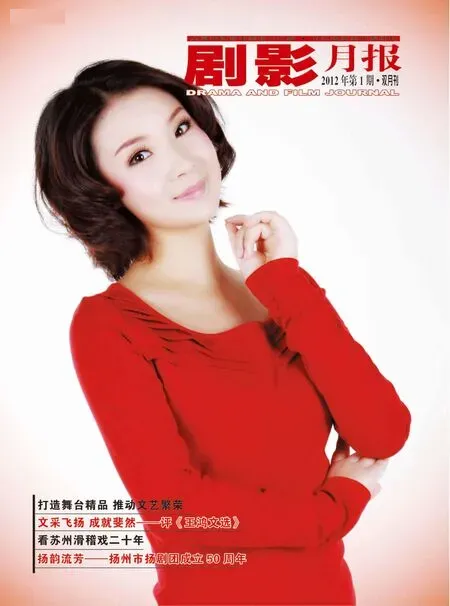我用古提琴演奏《二泉映月》
■府剑萍
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是我国著名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1893——1950)的代表作之一,自问世以来流传至今。作品于50年代初,由音乐家杨荫浏(1899——1984)先生根据阿炳的演奏录音记谱整理,后被出版广播,继而风靡全国。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男女老少中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爱。1993年被评为世纪华人艺术精品。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在第一次聆听此曲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说:“这首乐曲太感人了,像这样的乐曲应该跪下来听”。多年来,《二泉映月》不仅在民乐领域中被人们乐于演奏,而且还被改编成多种演奏形式,如小提琴独奏,弦乐四重奏,二胡与乐队等无不绚丽多彩,各得其趣。此曲后被搬上银幕,成为电影《二泉映月》的主题音乐。
古提琴(又名提胡)——属弓弦乐器,此乐器在一般的民乐团中不多见,很多人包括搞器乐专业的演奏员对它也不一定熟悉和了解,目前常用于苏州道教音乐、道家醮仪法事、民间堂名音乐班和昆曲的伴奏。据记载古提琴始于南宋,至今约有八百年的历史,道教的传统乐器,明代戏曲家、戏曲改革家魏良辅把古提琴运用到昆山腔中,最早的昆山腔的伴奏乐器(三弦、提琴、笛、笙,后称为昆曲四大件)使得昆腔的音乐发展更加成熟、完备。提琴的琴筒是用椰壳、梧桐板制成(有点类似中音板胡),琴杆要比一般的二胡长的多,相对来说左手把位比二胡大了许多,传统用丝弦,提琴的定弦(a—d)纯四度,音域宽广,音色低沉带点沙哑。
在众多的演奏形式中,人们对《二泉映月》的内涵把握也有着不同的见解。此曲内涵与创作者及演奏者集于一身的瞎子阿炳当时的境况与遭遇是密不可分。在中国音乐史占有重要地位的瞎子阿炳,其遭遇是十分不幸的。《二泉映月》就是阿炳在流浪卖艺,苦苦挣扎的生活中不断演奏、不断加工而成的,乐曲委婉动听、意境深远、手法特独,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首乐曲就像是他悲惨凄凉一生的真实写照,作者抒发了对旧社会苦难生活的愤怒之情,表现了宁折不屈的坚强性格,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炳自幼跟随父亲华清和在无锡雷尊殿道观里当小道士,学习二胡、琵琶、笛子、鼓等民间乐器,12岁就能熟练地演奏各种道教音乐,被誉为“小天师”。25岁时父亲去世,他继为雷尊殿的当家道士。后因交友不慎,沾染上恶习,中年时害眼疾无钱医治而失明,从此人们都叫他“瞎子阿炳”。他流落街头,为谋生计,靠卖艺糊口,自编自奏自唱,沦为街头艺人,在黑暗和贫困中挣扎着,尝尽了人世间的辛酸苦辣,加之当时正值社会动荡混乱,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历史变革时期,作品无疑带有这个时期的社会"气息",带有阿炳对这个社会的情感反映。他把自己的苦难、屈辱、欢乐、希望都倾注在乐曲中,演奏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他只有在音乐中倾诉自己的心声。这是一首阿炳自传式的凄惨欲绝的悲歌。全曲由引子和六个段落组成,它的结构是(引子、A、A1、A2、A3、A4、A5),即同一题材的五次变奏。由于《二泉映月》的原谱较长,重复乐段较多,目前演奏曲谱(引子、A、A1、A2、尾声)是二胡演奏家的前辈们为了更加适合舞台的演奏,经过精心研究和不断探索,把原曲的六个段落压缩和删减成三个段落作为现在的演奏谱。
[引子]是一个音阶下行式的短小乐句:这仿佛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不堪回首往事而深深地叹息。引子要作渐慢渐弱的处理,运弓要稳中带着沉重,好似从胸中发出的一声深深地长叹,古提琴沙哑的音色较二胡更能体现作者的如泣如诉,悲愤地追忆渗透了对黑暗社会的忿恨,对光明的追求,流露出愁怨与辛酸和苍凉的感觉,更能引起听众的共鸣。
主题(A)由三个乐句组成:第一乐句是倾诉性的往事沉思,全句以宫音作终结音,给人以平稳的感觉。第二乐句旋律如心潮起伏,富于变化,抒发了作者的无限感慨。第三乐句旋律在高音区流动,一开始就出现了八度的跳跃,递增的力度奏出继续上扬的旋律,柔中带刚。通过旋律区的上扬、变化音的应用、力度的大幅度对比和节奏动势的变化,特别是一开始的顿逗使音乐表现起伏强烈,情绪更为激动。犹如是旧社会民间艺人在倾诉内心的痛苦和愤慨时欲言又止,哽塞难言的激动声调。主题音乐从开始时的平静深沉转为激动昂扬,深刻的揭示了作者内心的生活感受和顽强的生活意志。
接下来的二段(A1、A2)变奏主要通过句幅的扩充和减缩,并结合旋律活动音域的上升和下降,来表现音乐的渐层发展和迂回前进。它的多次变奏不是表现不同音乐情绪,而是为了深化主题,所以乐曲所塑造的音乐形象是比较集中的。在主题的三个变奏段落中,重点是在第三乐句的变化和发展,它的每段分a、b两部分,a是收拢抑制的,落在宫音,表现出内涵婉转,诱人深思;b是舒展亢进的,结在徵音,作大幅度跨越,旋律激荡昂扬,拟心弦。a、b两部分承上启下,相互衬托,情趣深刻,富有魅力。深刻揭示了“月色虽明,世道则暗;泉水虽甜,人生却苦”的哲理。主要采取“重尾变头”手法,将音乐加以引申展开和收缩,着力表现愤慨、挣扎和反抗之情,层层深化,逐步推向高潮,鲜明的表现了阿炳在苦难中磨练出来的倔强而刚毅的性格和对黑暗势力不妥协的斗争和反抗精神。《二泉映月》的节奏变化不大,但其力度变化幅度大,在每逢演奏长于四分音符的乐音时,用弓轻重有变时长时短,忽强忽弱,乐曲时而高潮,时而低缓,时而不安,时而平静,时而躁动,时而阴柔,音乐时起时伏,扣人心弦。
在演奏几段主题时,由于古提琴弦线的张力比较松,弦较二胡弦软,音准控制相对要比二胡要难,由于左手把位大,演奏的手法也和二胡不同,按弦和其他的拉弦乐也是不一样的,在演奏提琴时,按弦一定要松,不能太压弦,稍不注意控制按弦力度,就容易出现音准问题。揉弦也要松松的,左手要控制好,轻轻的揉弦中带压,演奏时必须能领悟弦上的感受,左手充分运用“揉弦”、“压揉”、“迟到揉弦”、“不揉弦”、“颤抖的弦音”等手法,右手要掌握好“浪弓”的演奏技法,运弓的速度有慢有快、力度有轻有重、长弓似断非断,摸索着两手默契的配合,全身心地融入到乐曲中去,这样才能把阿炳此曲中凄凉、悲伤、忧伤的倾诉,柔和、甜美、朦胧的幻想,深邃的意境演奏的惟妙惟肖。虽然难度大点,但是你会发现较二胡演奏此曲无论从音色、力度各方面都由过之而无不及,是一种新的演奏形式。
2005年应台湾中华道教总会邀请中国道教音乐团访问台北、台南、台中、高雄等地演出,由我担任《二泉映月》的二胡独奏,在苏州玄妙观老道长的启发下,尝试用古提琴来演奏,把原来纯四度(a—d)改变为纯五度(g—d)定弦,用琵琶的E弦(二弦)——A弦(一弦)来代替传统的丝弦,使它的音色有了新的变化,低沉、柔中带沙哑,经过不断地探索和不断地练习和磨合,我在伴奏配器的形式上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和处理,充分运用了道教的打击乐和弹拨乐,好似感觉阿炳在道观里演奏此曲的意境。在北京集训排练和彩排审查,得到了著名学者田青等专家的认可和赞扬,在台北国家大剧院首场演出获得成功,得到了中国道教音乐团团长——全国人大常委张继禹的肯定,得到了台湾记者和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获得了台湾观众的一致认可,可以说是《二泉映月》的一种成功的新的演奏形式。
《二泉映月》是我国民族器乐曲的瑰宝,是一部惊世之作,我国几代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项祖英、刘长福、闵慧芬、宋飞等(可以说会拉二胡的)都演奏过此曲,《二泉映月》亦被改编成小提琴曲,各种演奏形式相继产生,都获得了观众的好评,用古提琴独奏此曲也成为其中一种,《二泉映月》是东方艺术史上璀璨的明珠,在演奏形式上也出现了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样化局面,演奏者各展其长,异彩纷呈。这也正是民族艺术不断蓬勃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胡曲“二泉映月”演释[1]的多元化与一元化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