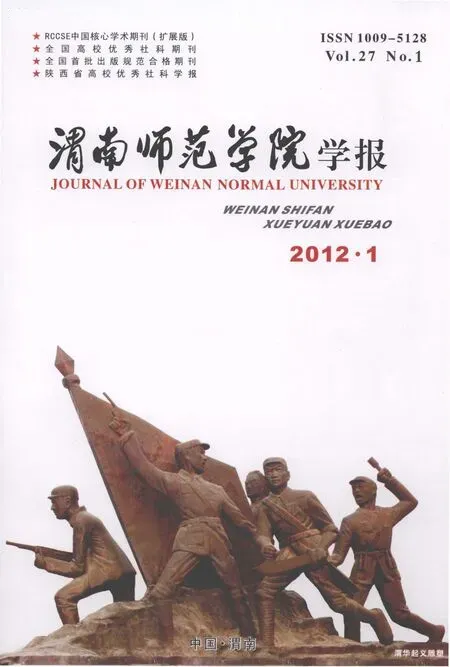《史记·刺客列传》到“刺客戏剧”的嬗变
刘永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史记·刺客列传》到“刺客戏剧”的嬗变
刘永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史记·刺客列传》改编的刺客文学蔚为大观,其中由刺客故事嬗变而来的刺客戏剧更是流传深远。刺客戏剧以时间为轴,以地域为面,经纬交错,种类繁多,而且在近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刺客戏剧无论从主题还是到审美都在接受中发生着演变。文章就“刺客戏剧”的嬗变进行剖析,以求梳理刺客戏剧源流和嬗变情况,更好地了解我国古典文化中的刺客文化和精神。
刺客列传;刺客戏剧;主题嬗变;审美嬗变
“刺客”一词始见于《史记·刺客列传》,但刺客的行为至少在《春秋》“刺公子堰”[1]325中就已经出现。《墨子·明鬼篇》记载,杜伯曾刺杀周宣王。虽然刺客的行为出现的很早,但是,战国时期并没有刺客的概念,“刺客”这一名称的确立更是直到西汉《史记·刺客列传》的出现。《说文解字》解释说:“刺,直伤也。”[2]182可以理解为,“刺”就是杀人。所以《公羊传》在解释“刺”字时就说:“刺之者何? 杀之也。”[1]195孟子的说法也表明这个意思:“刺人而杀之”(《孟子·梁惠王上》)。简单来说,刺客就是怀揣利器,突袭杀人的实行者。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3]3183故此,司马迁在《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用浓墨重彩、饱含激情地描写了郭解、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一大批侠义之士。《刺客列传》篇末有司马迁的高度评述——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3]2538司马迁其人重侠慕义,又遭李陵之祸,创作《刺客列传》自在情理之中。正如《索隐》述赞所言:“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3]2538刺客行为不仅使得刺客留名,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侠义这一宝贵的民族精神。
宋元之后,随着戏剧的发生发展,后世戏剧改编自《史记》的剧本很多,刺客戏剧亦不在少数,无论在杂剧还是传奇中,许多刺客故事被搬上了戏剧舞台。(见下表)从地域上讲,我国北方地区几乎都有刺客戏的流传,南方省市亦不鲜见。从剧种上讲,几乎所有的戏剧类别都有刺客戏的剧目,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中一直流传着刺客戏的保留剧目。单举一例来讲,《秦腔剧目初考》中的秦腔刺客戏剧至少保存有《太和城》、《富贵图》、《豫让剁袍》、《刺侠累》、《荆轲刺秦》、《羊角哀》、《张良刺秦》等。
刺客戏剧无论剧种还是历史绵延,都值得探讨研究。受篇幅局限,本文主要从元杂剧和明传奇对《史记·刺客列传》的接受和嬗变,以杨梓的元杂剧《忠义士豫让吞炭》和叶宪祖的明杂剧《易水寒》为主要蓝本,分析总结其嬗变情况,并探讨其内在规律性原因,以求对刺客戏剧文化的梳理和概述。
一、主题嬗变
经过元杂剧和明传奇对《史记》的重构和改编,《史记》故事的主题在一千多年的流传演变时间里自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总的来说,史书记载的戏剧演出的主题嬗变情况无非如下几种:有些是把原本的故事主题延续下去,深入到更高的一个层次;而有些则是淡化原本的故事主题,在其旁支中突出另外一个主题;还有一些就是改变了故事的情节和结局,贯入了编者的思想感情和创作理念。
(一)思想主题的深化与转移:从忠义、侠义到正义、道义
司马迁独创《刺客列传》是有其多方面原因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3]3315似乎是彰表信义,司马迁又不认可韩非子的观点,认为:“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蔬食不厌。死而已四百年,而弟子志之不倦。”[3]3181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讥,非言也。儒敝乱法,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学士多称于世者,故太史公引韩子,欲陈游侠之美。”[3]3181说明司马迁对这些游侠、刺客寄以深切感情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3]3181由此可知,史家何以为这类人物作传的原因了,而且,忠诚守信、知恩图报、舍生取义等品性是游侠、刺客的必备特质。

表1 刺客人物改编戏剧简表①《羊角哀鬼(死)战荆轲》由今人赵景深在其《明清曲谈·薛旦的九龙池》一文中考证,认为《战荆轲》为杂剧。其实,《羊角哀鬼(死)战荆轲》中的“荆将军”并非谋刺秦王政的荆轲。“宋代以来某些文献之舛错,大概是由‘荆将军’望文生义,或民间因羊左和荆轲事迹都具有传奇色彩和义烈性质,而把相隔约三百年的人物硬拉到一块,让他们合演一出惊天动地的鬼魂大战戏剧,从而化历史为传说,以讹传讹,最后被后代的通俗文艺渲染敷演,发展成为现在所见的冯梦龙《羊角哀舍命全交》这样的虚构小说。”(饶道庆的《〈羊角哀舍命全交〉本事考辨》)这也足以表现荆轲故事的流传和影响的深远。根据邓长风在《关于〈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的几个问题》中的考证,庄一佛先生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第1256页徐沁之下《易水歌》、《丰乐楼》、《芙蓉楼》、《广寒香》四种,当为汪光被作,后两种近已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五集。”(邓长风《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简评——兼谈清代曲家曲目著录的若干问题)笔者本着有疑存疑的态度记录下来,仅供参考。
到戏剧兴起之后,反映忠义品质的作品并不少见。杨梓杂剧《忠义士豫让吞炭》的正名是“贪地土智伯灭身,忠义士豫让吞炭”,叶宪祖传奇《易水寒》的正名为“老田光舍身激友,智燕丹下士成名;烈樊期金台高义,壮荆卿易水离情”,两剧单是剧名就皆有一个“义”字,可见一斑。在《忠义士豫让吞炭》和《易水寒》中都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明确表述。例如:“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容。”(《忠义士豫让吞炭》【二煞】)“〔末〕荆卿,常言道:女为悦己容,士为知己死。即当往见,幸勿多辞。”(《易水寒》)所以,“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易水寒》)“万金酬士死,一剑答君恩。”“人生留得丹青在,纵死犹闻侠骨香。”(《易水寒》)义的意味无处不在,然而,戏剧里的“义”的内涵和外延与《史记》的“义”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仅有恩义、忠义和侠义的意思,甚至萌生了一些正义和道义的东西。
在杂剧《忠义士豫让吞炭》中,已然出现了对正义的考量。远高于“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这种狭义上的知恩图报的复仇的境界。如下:
【混江龙】休为一朝之忿,不思量旋踵丧其身。上个尊周朝皇帝,下不闻阃外将军,独自兴心独门立,却不道半由天子半由臣。待驱兵领将,积草屯粮。平白地要把邻邦困。可不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正末唱)自古为君先爱民。圣人道不患寡而患不均。若是近大臣,远佞人,则这的是经纶天下本。
这里表达了作者对于“义”的深度思考,提出人不可凭一时义气,做出无可挽回的措施。甚至提出了江山非为天子一人所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明辨忠奸,亲贤人,远佞人,方能治理好国家的正确论断,这已经不完全是一个门客的做法了。豫让借助暴君商纣王来劝谏说:“昔者纣王无道,以酒为池,经肉为林。使男女裸体相淫。杀贤拒谏,骄侈无度。今日赵襄子有何罪?”(《忠义士豫让吞炭》)明确指出不可学暴君无道,行为处事要以道义为先的道理。
后世有些刺客,已经没有或丧失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意念,只为贪图养者的名利待遇,沦落为职业杀手。这种刺客与《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是有本质区别的,刺客不是杀手,更不是恐怖分子。通过历史的洗涤和时空的转变,“义”的“深化”与“转移”因为社会转型时期理性道德的异化和转折期内情感道德的放纵而导致,使得刺客主题得以嬗变与丰富。
(二)矛盾关系的转化和激化:从侠义复仇到呼唤英雄
元朝社会的特殊性为刺客戏剧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经验和基础,元代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更是促成了刺客戏剧的嬗变。“元代的许多杂剧作家,大抵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还有不少是高才博艺之人。当他们把目光注视着社会现实,他们对社会矛盾作了若干有力的剖析;同时他们也从历史上寻求寄托,他们的这种历史回顾,往往是对失去的、或在当时很难实现的‘理想’的向往,也是表现现实状况与他们的理想的冲突”[4]。矛盾冲突的加剧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生存现状,从古人那里借鉴生活经验,表达内心愤懑,找寻宣泄出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复仇,且不仅仅是狭义层面的复仇,而是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并且矛盾关系在不断地发生改变。
政治环境和文学氛围的改变使得“元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与理想受到极大挫折和打击,所以也就大多只能空怀壮志,也就只能借用文学作品来抒发、吐露这一怀抱,在感叹那些已经逝去的英雄豪杰的同时,抒发自己的英雄情怀与爱国热情。表现在元杂剧创作上,就是往往以怀恋的心态、羡慕的神情描写久远的往事和历史英雄,聊以自慰”[5]。越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人们越是渴望英雄的出现。“想当初秦穆公在临潼会上。设一会名曰斗宝。驱十七国诸侯都来赴会。某文欺百里奚。武胜秦姬辇。拳打蒯聩。脚踢卞庄。挂白金剑为盟府。戏举千斤之鼎。手劫秦王。亲送关外。(专诸云)将军真乃世之虎将也。”(《说专诸伍员吹箫》)这些“世之虎将”和“真英雄”莫不是元朝百姓渴望救世主出现而大力倡导和宣扬的。元杂剧以浓重的笔墨来描写这些英雄,也是因为元人迫切地需要这样英雄般的人物来帮助他们改变这个充满黑暗和不公的社会,但现实的无力与苍白只能令他们在这些元杂剧的作品中寻求安慰。
“谁恋你官二品,车驷马,待古有德行的富贵荣华。想着俺那有恩义的主人公放不下,我故来报答。报答的没合煞,到惹一场傍人笑话。”(《忠义士豫让吞炭》【眉儿弯】)这段唱词强烈地表达了英雄人物不与黑暗势力苟且屈服的立场和决心,似乎暗示了元代文人对元朝统治的强烈不满,表达了人民群众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节操和对统治者分道扬镳的决绝之心。矛盾关系从侠义复仇到反抗黑暗统治的转化是这些戏剧的一个特色,对英雄人物的呼唤也只是对这个黑暗社会无能为力的无奈之举。
明朝嘉靖到崇祯时期,吏治腐败,政局黑暗,颇有些“四海尘迷,五方鼎沸。风云会,尽要雄飞”(《易水寒》【仙吕北点绛唇】)的境遇。但是现实的压迫只能令英雄人物“连城白璧,肯无端献楚。自悲啼,且沈山瘗影,被褐藏辉。高挂着冯欢囊里铗,牢收了朱亥袖中锤,江湖飘泊,市井追随。逃名溷俗,纵酒忘机。喜来时唱几曲短长歌,闷来时洒几点英雄泪。凭人拍掌,任我舒眉”(《易水寒》【北混江龙】)。只能是“你是风胡红。霜蹄碧碎,岂无识者回车!自有明王持。且休嗟数奇,且休嗟数奇!待时藏器。佯狂游世,和你醉如泥。本是钟和磬,权为埙与篪”(《易水寒》【南桂枝香】)。所以剧中自有这样的提问:“早难道轻把少年掷?镇日酒垆中,把壮志消靡!”并得出“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易水寒》【南长拍】)的答案。这或许也是当时文人的心态和写照。渴望英雄的出现或者自己本身扮演英雄的角色,重塑这个社会,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刺客在这里不仅仅是复仇的侠客,更是救世的英雄。
(三)故事情节的脱离与演变:翻案补恨
为了表现某一精神和理想的需要,或是因为统治者的镇压和束缚,或是由于历史久远的隔阂等原因,元杂剧和明传奇作家对《史记》故事必然进行了重构。对这些经典性的文本进行重构,必然会有它的得与失。在经过元杂剧和明传奇的重构之后,一些《史记》故事的结构更加严谨完整、情节更加曲折动人、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语言更加生动活泼,也更加迎合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人们对其故事能够耳熟能详,争相传颂,有利于《史记》的流传与延续。元杂剧和明传奇还依托于消费市场的需求,使得《史记》故事更广泛地走近了普通市民。
当然,元杂剧和明传奇对《史记》的重构也存在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够完美的地方:一方面故事矛盾关系的转化淡化了《史记》中描述的广阔的画面和风云诡变的时代背景,一些情节的增添,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史记》的审美力度;另一方面,翻案补恨的剧作削弱了悲剧的力量,大团圆结局一味迎合民众使得一些《史记》戏剧饱受批评和争议。《忠义士豫让吞炭》全剧总共四折,但是前两折戏讲的是智伯贪图三家领地反遭灭身的故事,详细讲述了双方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剧情虽然较《史记》大为展开,但是过分削弱了豫让刺赵襄子这一主要事件的紧凑性,全剧虽然更加完整但是也过于松散。
而《易水寒》的故事与历史大相径庭,甚至结局完全相悖。历史上荆轲不仅没有刺死秦王,更连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甚至还连累燕国速亡。叶宪祖将荆卿刺秦王败改为生擒秦王,尽归六国之地。此剧结尾为今人所诟病,认为是作者的败笔。荆轲刺秦的遗憾是叶宪祖能补的了的?也有人认为叶宪祖是“团圆迷”,是“补恨”的代表作家,“专以改古之悲剧而后快”。叶宪祖一生笃信佛教,晚年尤甚。其构思意在不忍实写荆卿的败亡,表现出对荆卿的爱慕,对正义行为的崇敬,但归隐入仙的结局,终归还是败笔。《易水寒》改变了故事结局,过分削弱刺秦事件本身的悲剧力量。如果单纯的以结局定义一部作品的性质,那未免有所偏颇。但是,对于这部戏的批评也存在不同的声音,甚至有完全相反的评价。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就将此剧列入雅品,“荆卿挟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即事败身死,犹足为千古快事。桐柏与死者生之,败者成之,荆卿今日得知己矣”[6]157。
但是无论如何,戏剧是一种表现矛盾对立激化的作品,主题鲜明,情节紧凑,而《忠义士豫让吞炭》表现出的冗长拖沓是不合时宜的,故事情节的脱离与重心的偏移有损豫让刺赵襄子的这一事件的针对性的。《易水寒》进行的翻案补恨虽然褒贬不一,但是把历史上荆轲刺秦的悲剧改为喜剧终究是不妥的。
二、审美嬗变
但凡文学作品,无不以某种倾向的审美观念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意图。而审美品质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环境的改变和作者创作理念的更新以及消费人群的接受水平的不同进行着多方面的不断嬗变。由史家实录的历史到作家创作的戏剧,其审美的嬗变情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作者以及消费者的不同而发生重大改变。
(一)“义”的渐变
刺客与生俱来的品质是知恩图报、舍生取义。“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3]3182-3183故此,“义”是侠士必不可少的品行,甚至有时为了“取义”,不惜以“舍身”取之。《史记》中伸张正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施利不图回报、言必信,行必果、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在元杂剧中广布渗透。
“(豫让)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3]2519方及智伯被赵襄子灭杀,“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3]2519行刺失败后,赵襄子欲以厚待收为己用,豫让回道:“谁恋你官二品,车驷马,待古有德行的富贵荣华。想着俺那有恩义的主人公放不下。我故来报答。报答的没合煞。到惹一场傍人笑话。我这一片为主胆似秋霜烈日。觑那做官心似野草闲花。”(《忠义士豫让吞炭》)豫让以“秋霜烈日”、“野草闲花”作比,视当官求财为粪土。赵襄子见其忠义,想要放了豫让,豫让则唱道:“和你是剜心摘胆两事家。怎肯喜悦和洽。我活呵谨防着断头分尸。我死后你放心再称孤道寡。”言不报君仇誓不罢休。赵襄子问豫让:“你曾事范氏中行氏。智伯灭了他二家。你不报仇。今日如何却为智伯报仇。”豫让回答道:“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故以常人待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待之。”智伯之于豫让的知遇之恩,豫让终以其舍身相报。《忠义士豫让吞炭》因为“自古为君先爱民。圣人道不患寡而患不均。若是近大臣,远佞人,则这的是经纶天下本”表现出的正义思想,我们有理由相信“义”经过历史的打磨,发生了渐变。
《易水寒》在剧作之初也表现的是田光报主之恩,寻访荆轲,不惜以自己生命的代价激荆轲为燕太子排忧解难。而荆轲成为燕太子丹的门客之后,感激其对自己的礼遇之恩,答应刺杀秦王。可是在荆轲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的作法上,不是简单刺杀秦王了事,而是欲图生擒秦王要挟其尽归六国失地,还天下太平。
简单来讲,“义”不仅仅是侠义复仇行为所具备的忠贞义气,它加入了更多的道德的考量。它从信义、恩义为出发点发展到忠义、侠义,最后走向了道义和正义。这也体现出剧作者和观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对于“义”的品质的深层次思考。
(二)人物形象嬗变
戏剧不同于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戏剧可以大量运用心理刻画来表现人物。戏剧作为一种综合的舞台艺术,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表现人物,体现矛盾冲突,人物性格的塑造要求必然更高。戏剧为了迎合广大市民阶层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就要求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内赋予戏剧更为充实的内容,用强烈的矛盾冲突把观众牢牢地吸引在剧场上。因此剧作家们为了突出戏剧性,便把复杂的矛盾关系转化到剧中对立双方的主要人物身上,经过这样的重构之后,剧本的正义与奸邪的斗争更加尖锐,戏剧矛盾更加集中,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也更加鲜明。《史记》中的人物形象经过了元杂剧剧作家们的重构之后便发生了改变。
(正末云)巨闻忠臣不怀情于君;孝子不畏死于父;存忠尽节,受斧钺而无怨。主公,今上有周朝天子,不尊王命,无故索地,与咱是人情,不与是正理。今日无故称兵,大不祥也。
(正末唱)自古为君先爱民。圣人道不患寡而患不均。若是近大臣,远佞人,则这的是经纶天下本。(《忠义士豫让吞炭》)
这里的豫让不再是一个愚忠报仇的剑客,他分得清是非黑白,明白为人做事义与不义首先取决于正义。他懂得忠孝仁义的道理,甚至是经纶天下的治国安邦之策。他敢于劝谏,明白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人物特征多了起来,形象更加饱满。
再来说赵襄子。赵襄子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不能简单以“忠”、“奸”来概括。《史记》载:“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3]2519《忠义士豫让吞炭》则说:“(赵云)想智瑶无道,吞谋众卿,妄窥晋室,罪在不宥。左右,即便斩讫报来。还将他首骨,漆作饮器,方趁我心也。”(《豫让》)在人艺话剧《刺客》之中,濮存昕扮演的赵襄子集残暴与仁爱的统一体,在第一幕开场不久,下边送来智伯的人头,他一边抚摸着,一边用台词功夫描述智伯当年的眼睛、鼻子、嘴巴是何等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突然,他一转身,叉开两腿,撩开袍子,将智伯的脑袋置于裆下,并做撒尿状,一会儿,回转头来,把人头放于地上,道:“这家伙的脑袋当夜壶倒不错!”之后在一阵哄笑声中退场。在这里,编剧将历史上智伯的脑袋被做成酒具改成了做成夜壶,可谓神来之笔。出于对义士的敬重,他几次三番释放了刺杀自己的豫让。(赵云)“可惜豫让死了,左右将尸首抬出,以礼葬埋。我明日奏过晋侯,追封官爵,旌表忠义,劝化风俗。”此外,为了使戏剧更加完整,《忠义士豫让吞炭》添加了一个重要人物正末“张孟谈”。正是“张孟谈兴心反间”,才有了三家剿杀智伯,故事才能发展下去。
《易水寒》则是借用很多《燕丹子》的内容丰富了荆轲的形象。例如:
然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为人博闻强记,体烈骨壮,不拘小节,欲立大功。尝家朴卫,脱贤大夫之急十有余人,其余庸庸不可称。太子欲图事,非此人莫可。(《燕丹子》)[7]8
层层铺垫让荆轲在未出场前就已先声夺人,显示出高超的叙事技巧。当田光劝说荆轲投靠太子丹时,荆轲说:“有鄙志。常谓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诺不违。”刻画了荆卿“士为知己者死”的侠士性格。为了表现太子丹对荆轲的厚爱,小说《燕丹子》虚构了很多匪夷所思的情节:
轲拾瓦投龟,太子令人奉槃金。轲用抵,抵尽复进。轲曰:“非为太子爱金也,但臂痛耳。”后复共乘千里马。轲曰:“闻千里马肝美。”太子即杀马进肝。暨樊将军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来归太子。太子为置酒华阳之台。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轲曰:“好手琴者!”太子即进之。荆轲曰:“但爱其手耳。”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槃奉之。
而荆轲刺秦王时,秦王的脱险更有戏剧色彩:
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暴海内,不知厌足。於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海内报仇。今燕王母病,与轲促期,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
这样的改编大大丰富了荆轲甚至秦王的形象。明传奇历史剧在塑造历史人物时,不断地描述人物新的境遇,将人物置于更大的环境中来显示其精神内涵,直至最终确定其本质的性格特征,这就使剧情饱满,具有了艺术的张力,故而,荆轲在这样风起云涌的时代才能尽显身手,一展宏图。
(三)通俗的美学追求
《史记》叙事艺术的突出表现就是人物对话的个性化,而作为表演形式的元杂剧更加注重人物的对话描写,这也是二者的相通之处。所以,元杂剧“史记戏”还继承了《史记》的语言表达,许多元杂剧的剧作家们把《史记》中精彩的人物对话仅稍加改动便写入剧本之中,甚至有一些语言描写几乎是原作的直接照搬。例如,《忠义士豫让吞炭》中豫让与赵襄子的一段对话:
【赵云】这人形体好似豫让。【正末云】我就是豫让。当日宫中刺你不著。因此向山中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变了形容。务要刺杀了你。为我主人报仇。【赵云】你曾事范氏中行氏。智伯灭了他二家。你不报仇。今日如何却为智伯报仇。【正末云】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故以常人待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
此段话与《史记·刺客列传》原文几乎一般无二:
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3]2521
以及豫让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些忠义之语都是被元杂剧作者一字不变直接写进剧本的。原本作为史传文体的《史记》与说唱表演形式的元杂剧之间在语言上应是有着明显区别的,但是,元杂剧的剧作家们却能够将《史记》的语言移接到剧目中,使得《史记》精彩的人物对话描写不仅能够存在于史传文学的书面语之中,更能够使其在元杂剧的说唱形式中获得生动体现。元杂剧作家大多是平民阶层出身,因此在内容题材上主要反映平民生活,具有明显的平民化倾向,很少歌功颂德。从成就上讲,元杂剧是中国戏曲的一个黄金繁荣时代,明人臧懋循在《元曲选》序中说:“大抵北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之乐府。而粗者杂以方言。”王国维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约:自然而已矣。”两人都对元杂剧自然质朴,不假雕琢的本色予以高度评价。“语言自然朴实,词曲悲壮深沉,悲则欲泣欲诉,怒则欲杀欲割。”其中的说白部分由诗和话夹杂而成。
《易水寒》叙事清楚,层次分明,主题鲜明,风格俊朗,所以王玑评赞说:“史迁《荆轲传》是顾虎头(恺之)、王摩诘(维)画手;六翁(六桐)《易水寒》是马东篱(致远)、关汉卿作手,千载下犹有生气。”本剧关目均匀,文字本色,格律严谨,风格豪放,文学性与戏剧性兼具。第一折:田光在燕市访得荆轲,推荐给燕太子后自刎;第二折:燕太子宴请荆轲,穿插徐夫人赠剑和樊于期献头;第三折:易水分别,补叙高渐离击筑高歌以壮形色;第四折:荆轲胁迫秦王就范,归还诸侯领地。全剧结构清楚,分折均匀,又层层递进,高潮迭出。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评叶宪祖《渭塘梦》杂剧云:“桐柏之词以自然取胜,不肯镌琢。如此剧乃其镌琢处渐近自然,则选和练妙,别有大冶。”[6]158此评论也适用于《易水寒》。这表明叶宪祖的戏曲语言朴淡自然、本色当行。叶宪祖精通音律,“词以自然取胜,不肯镌琢”(祁彪佳《剧品·渭塘梦》)。《易水寒》第一折【北混江龙】荆轲唱:“高挂着冯欢囊里铗,牢收了朱亥袖中锤,江湖飘泊,市井追随。逃名溷俗,纵酒忘机。喜来时唱几曲短长歌,闷来时洒几点英雄泪。凭人拍掌,任我舒眉。”文字不雅不俗,读来琅琅上口,颇具节奏感。活脱脱刻画出荆轲那外冷内热、待机而动的壮士情怀。第三折【北收江南】荆轲唱:“呀!你看这无情易水呀,下西风刮面飕飕。只觉得芦花夜冷入孤舟。只落得桑乾远度望并州。要重逢可自由,谁道丈夫有泪不向别时流。”这段唱词言辞恳切,壮里含悲,兼以情景交融,表达出了荆轲与高渐离的深挚情谊,堪称曲中上品。青木正儿也是非常欣赏这部戏剧的:“此曲事既壮烈沉痛,曲调亦相称,彼之杂剧中,此为余所最爱者。”[8]223
这种通俗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追求既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剧作家和消费者之间契合的焦点,更是文学从文人走近普通人民大众的表现。
三、结语
元代社会和明朝中后期,吏治腐朽、社会黑暗,明君贤臣的理想社会与现实相差甚远,尤其是在元朝,文人地位低下,刺客戏剧是文人表达自己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手段。刺客戏剧的兴盛不仅是因为这些侠义之士的精神为剧作者所敬仰,最为重要的是,在黑暗腐朽的社会状况下,他们迫切需要有胆识、有能力的侠义之士为他们伸张正义,改变现状。当然,反映市民消费需求这一要求也在密切地影响剧作者的创作。
终于,刺客戏剧在对《史记》的批判精神、侠义精神和悲剧精神的继承和对《史记》语言艺术等方面的继承之后进行了重构,实现了从《史记》到刺客戏剧的主题嬗变和审美嬗变,并在以后的刺客戏剧发展历史上不断的传承和创新,为我国古典文化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
[1]杜预.春秋三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汉]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邓绍基.论元杂剧思想内容的若干特征[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4):1-8.
[5]曹萌.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祁彪佳.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远山堂剧品[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7]程毅中点校.燕丹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上[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The Change:From The assassin Commentary Section in Historical Records to“Assassin Drama”
LIU Yong-hui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The assassin literature that was adapted by Sima Qian in Assassins Biography of Historical Records presents a splendid sight,in which the assassin drama that was evolved from assassin stories is spread widely and farther.The assassin drama takes the time as the axis and the region as the range.It not only has a great variety,but also is developing both in topic and i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during the spread in thousand years.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assassin drama so as to arrange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helping us understand the assassin culture and spirit better in our Chinese classic culture.
The assassin Commentary Section;assassin drama;theme evolution;aesthetic evolution
I206
A
1009—5128(2012)01—0048—07
2011—07—12
刘永辉(1986— ),男,河北邢台人,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詹歆睿】